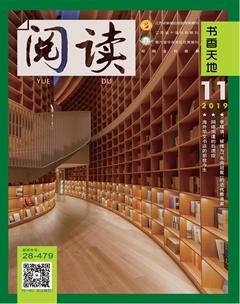收集燈泡的藝術(shù)
〔美〕邁克爾·基默爾曼
幾年前,我遇見了休·弗蘭西斯·希克斯。他是巴爾的摩市中心的一個牙醫(yī)。一天下午,他把我?guī)нM(jìn)了他樓房的地下室,向我展示了所有他花了將近七十年時間收集來的收藏。希克斯醫(yī)生的藏品是燈泡。他于2002年七十九歲去世時,累計收集了七萬五千只燈泡。如果告訴你這是世界上最大的燈泡收藏,你恐怕也不會感到驚訝。希克斯醫(yī)生正式將他的收藏地變成了一座博物館,取名“弗農(nóng)山熾熱照明博物館”。它的藏品包括曾是世界上最大的燈泡(五萬瓦的瓦數(shù),高四英尺,有一個灌木叢那么大),以及最小的燈泡(你得透過顯微鏡才能看得見)。藏品中還有愛迪生早期的試驗(yàn)性燈泡,連里面的蠟光卡紙燈絲都是原始的,其中一盞還能點(diǎn)亮。希克斯醫(yī)生還有很多獨(dú)一無二的珍品:如在廣島投擲原子彈的“埃諾拉·蓋伊”號轟炸機(jī)上的三盞燈,也有些燈泡的模樣滑稽,特意做成貝蒂娃娃的樣子,還有可以點(diǎn)亮的男士領(lǐng)帶。整個地下室就像一個過度擁擠的兔窩。地下室的盡頭有一間房,里面有一張鋪著塑料印花桌布的大圓桌,希克斯醫(yī)生在那兒招待來參觀的學(xué)童們吃餅干。在去參觀之前,我先打了電話。因?yàn)楫?dāng)時沒有病人,他就在辦公室里和我見面,然后領(lǐng)我到了樓下,把一盞盞燈打開。
人們?yōu)槭裁从惺詹氐膼酆茫克囆g(shù)的慰藉以多種形式出現(xiàn),對有些人來說在于創(chuàng)造,對另一些人來說則在于擁有。對希克斯醫(yī)生來說,藝術(shù)的慰藉在于獵尋、收集這些閃閃發(fā)光的紀(jì)念品。對很多人來說,藝術(shù)的慰藉可能只是去欣賞像希克斯醫(yī)生這樣的人收集而來的物品——可能僅僅是去觀賞別人薈萃一堂的珍奇。希克斯醫(yī)生說他長大后,在學(xué)校里發(fā)現(xiàn)了其他燈泡愛好者,并開始和他們交換燈泡。為了收集燈泡,他甚至不惜行竊。有一次在巴黎度假時,他在一個地鐵站的一面墻上發(fā)現(xiàn)了一排1920年代的鎢絲燈泡。他匆匆忙忙地偷了一只下來,一時間整個地鐵站變得漆黑一團(tuán)。那些燈泡是用串聯(lián)電路連接起來的,他沒辦法把那只偷來的燈泡再旋進(jìn)插座,于是他決定逃跑。在博物館里,他把這件贓物放在一個展示盒里,盒上的標(biāo)簽注明“炙手可熱型”。一些精神科醫(yī)生來找他面談,問他為什么做收藏,他給他們講威廉·J.哈默的故事。哈默是愛迪生手下的一個工程師,在1900年前收集了十三萬只不同類型的電燈泡。后來這些燈泡藏品流散了。哈默是在希克斯醫(yī)生出生的那個月份去世的。希克斯醫(yī)生問那些精神科醫(yī)生:“你們相信輪回轉(zhuǎn)世嗎?”直把他們問得目瞪口呆。
這些年里,我看過一個垃圾博物館。我訪問過新澤西州一名宣揚(yáng)絕對戒酒的虔誠教徒。在他的地下室里,他收藏了幾千只袖珍酒瓶,還有從舊煙盒上弄來的幾十幅袖珍瓦加斯美女像(他也不抽煙)。我曾經(jīng)看過光線雕塑家詹姆斯·特瑞爾在亞利桑那州收藏的一小部分汽車和飛機(jī)。特瑞爾是個典型的充滿矛盾的收藏家。構(gòu)成他藝術(shù)的是萬物中最轉(zhuǎn)瞬即逝、最虛無縹緲的光線,但他收藏的卻是大個頭的笨重的機(jī)器。我猜想,這些藏品除了實(shí)用——可以將他從一個地方運(yùn)到另一個地方——之外,一定還滿足了某種私人的需求。
人們理所當(dāng)然地認(rèn)為,倫勃朗的作品是值得收藏的,因?yàn)樗鼈兪撬囆g(shù),同時也很昂貴。但是,希克斯醫(yī)生的例子證明,差不多任何東西都可以成為收藏家的目標(biāo)。收藏家并不一定期待他們的藏品有什么美學(xué)或金錢上的價值。和藝術(shù)品一樣,一件收藏品的魅力在收藏家眼里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當(dāng)一件藏品的價值只是象征的時候,它真正的價值也許才是無以計量的。當(dāng)藏品失去了實(shí)用功能時,它就具備了象征意義。一個在斯大林勞改營里服過刑的人收集了很多鑰匙,只是那些鑰匙能開啟的鎖早已廢棄不用了。一把鑰匙如果屬于巴士底監(jiān)獄,那就不僅僅是一把鑰匙;正如一只針線包,如果貝特西·羅斯(傳說美國第一面國旗的制作者)用它做過針線活,那它就不僅僅是一只針線包。研究收藏的作家菲利普·布洛姆指出:“收藏家收集的是被社會遺棄的物品。它們已被技術(shù)進(jìn)步所取代,常常是用舊的、一次性的、老式的、不受重視也不再時髦的物品。”因?yàn)闊o用,反而可貴:它們搖身一變,成了它們所屬的那個業(yè)已失落的世界的圖騰和殘片。
當(dāng)然,一些收藏品,即便是日常生活中的物件,也可以給我們的生活帶來神奇和精彩,因?yàn)檫@些物件一旦進(jìn)入了收藏家的收藏,就不再是日常的物件了。愛好藏書的瓦爾特·本雅明說:“有這么一本書,也許本來收藏家從沒想過去碰它,更不用說會戀戀地看它一眼,但因?yàn)樗X得這本書在市場上太孤單、太無依無靠,他就把它買下來,還給它自由。收藏家搶救這樣一本書的那一刻是他擁有的最美好的記憶之一。”他補(bǔ)充說,“你知道,對一個藏書人來說,所有的書,只有落到他的書架上,才能享有真正的自由。”
收藏家收藏什么東西各有他們私人的理由。他們努力從混亂中建立秩序。艾伯特·C.巴恩斯在上世紀(jì)初靠一種不用處方就可購買的消毒藥品——弱蛋白銀(弱蛋白銀是一種治療初生嬰兒結(jié)膜炎、有助于視力的藥物)——發(fā)了大財。他用賺的錢收集來的一批藏品是世界上最壯觀、最特異的作品匯集之一:既有大量塞尚、馬蒂斯和非洲藝術(shù)中的優(yōu)秀作品,又有很多小的金屬裝飾物和民間小擺設(shè),比方說門上的鎖和一只用橡樹果雕刻出來的小蟋蟀。他把所有這些藏品都放在費(fèi)城外的一幢富麗堂皇的大房子里展出,各式展品混在一起,擺放的方式也很古怪——如果巴恩斯博士在不同的畫中看出了類似的三角形或?qū)蔷€的構(gòu)圖方案,他會把這些畫擺在一起來突顯它們的構(gòu)圖設(shè)計。
展品中還有幾十幅雷諾阿的小幅油畫;它們大多數(shù)很糟糕,但有一些還是很優(yōu)秀的。不同時代的作品和現(xiàn)代藝術(shù)中里程碑式的作品——比如像亨利·馬蒂斯應(yīng)巴恩斯之約創(chuàng)作的壁畫——掛在一起。那幅壁畫是現(xiàn)代藝術(shù)中最有智慧、最卓越的作品之一。邀請馬蒂斯創(chuàng)作壁畫是巴恩斯的天才之舉。事實(shí)上,馬蒂斯也喜歡巴恩斯的古怪作風(fēng)。在馬蒂斯看來,將不同作品以特異的方式陳列,有益于公眾更深刻地欣賞藝術(shù),因?yàn)檫@樣人們可以“體會到很多學(xué)院里不會講授的東西”。馬蒂斯的話很有道理。巴恩斯和其他人觀看藝術(shù)的方式都不同。他出身工人階層;為了上醫(yī)學(xué)院,他靠打職業(yè)棒球來支付學(xué)費(fèi);在藝術(shù)欣賞上他是自學(xué)成才的。因此,眾所周知,對于藝術(shù)界的權(quán)貴階層,他極度敏感且態(tài)度惡劣。對于愛搭架子的人,不管是誰,他都不惜公開與其爭吵。他的藏品只對“老百姓,也就是每天在商店、工廠、學(xué)校、店鋪或類似場所掙錢糊口的男人和女人們”開放。據(jù)說,知名的藝術(shù)史家歐文·帕諾夫斯基得喬裝成轎車司機(jī)才能混進(jìn)去參觀。
曼哈頓的一位心理分析師沃納·明斯特伯格寫了一本書,名叫《收藏:難以駕馭的激情》。在書中,他提出:收藏可以有很多解釋,但有一點(diǎn)很明白,收藏或多或少是失去的童年的再現(xiàn)。像在孩提時代一樣,收藏家渴望父母的安撫。他或她的收藏品,好像嬰兒吮吸的拇指,成為母親乳房的替代。
我們談到的燈泡收藏家、拿地下室做博物館的希克斯醫(yī)生跟我講起那些來和他面談的精神科醫(yī)生。他說:“他們真逗。他們一本正經(jīng),連眼都不眨一下。他們花了四百萬美元采訪世界各地的收藏家,最后得出結(jié)論,收藏家做收藏不為別的,只因?yàn)樗麄儗λ麄兪占奈锲分浴3兜〗o我一百萬,我就會告訴他們這個結(jié)論。”
(摘編自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碰巧的杰作》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