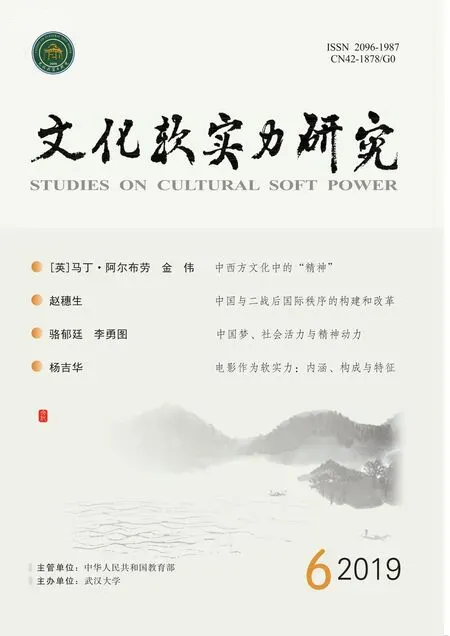中西方文化中的“精神”
[英]馬丁·阿爾布勞 金 偉 萬蕊嘉 譯
對于今天試圖了解中國的西方人來說,中西方文化間存在著許多悖論。其中之一就是關于中國領導人在多次講話中提到的“精神”。在西方,提及“精神”就意味著宗教。因為公共政策是世俗的,而宗教是留給個人的。那么,西方人可能會問,在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為何會在公共話語中賦予“精神”如此重要的地位呢?因為在西方的理解中,“精神”在歷史唯物主義的話語中是沒有任何地位的。相反,從中國人的視角出發,他們也會對西方文化中的“精神”表現出不解:個人主義在西方被高度重視,宗教自由經常被視為一種核心價值觀,而在公眾辯論中卻很少訴諸“精神”。
2000年初,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在他撰寫的許多文章中都談到了精神,這些文章都發表在《浙江日報》上,并于近期翻譯成英文,收錄在ANewVisionforDevelopment(《之江新語》英文版)一書中。筆者認為精神很好地詮釋了“科學發展觀的指導思想”。習近平總書記在《之江新語》這本書中提到“精神”不少于69次,有時候是指人類努力的品質,比如“求真務實精神”;有時是強調集體的反應,比如“臺風救援精神”;有時是表示集體的屬性,比如“黨性”。在對中國文化中的“精神”作更廣泛的論述時,我們也做了類似的三重區分:一是個人模范的精神,如雷鋒精神;二是典型事跡的精神,如紅船精神或長征精神;三是集體鼓舞的精神,如抗洪精神或上海精神。
最能有力證明“精神”在中國公共話語中的重要性的,應該是在2000年7月中共浙江省委全體會議上,會議高度強調了 “精神”的重要性,并由此凝練出“浙江精神”,即“自強不息、堅韌不拔、勇于創新、講求實效”。2006年2月5日,習近平在一篇題為《與時俱進的浙江精神》的文章中又重申了“浙江精神”,并對其進行了全面的闡述,其中包括對“誠信”“和諧”“開放”“圖強”等內容的補充完善。他認為,2005年9月廣大人民群眾對于臺風侵襲的應對“更是一場弘揚‘浙江精神’的偉大斗爭”,抗擊臺風的救災精神“與時俱進地豐富了‘浙江精神’”,體現了“萬眾一心、眾志成城的團結意識,相互協作、自立自救的自強信念”和“百折不撓、堅韌不拔、連續作戰的拼搏精神和紀律嚴明、招之即來、來之能戰的優良作風”。(1)習近平:《之江新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5頁。
就敘事分析而言,“精神”是一種比喻,指代的是一種經常重復的映射,用以闡述不同經歷或事件之間的聯系。但是,轉向敘事分析層面可能會轉移人們的注意力,削弱人們對“精神”在社會科學工作中重要性的理解,這是現實社會生活中的一個重要因素。
馬克思從開始接觸青年黑格爾運動起就堅定地走上了科學之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他將唯物史觀與唯心史觀進行了對比。其中,唯心史觀將歷史解讀為“漸進的精神意識”。眾所周知,馬克思斷然反對青年黑格爾派追隨他們的導師,把歷史變成了“人類抽象精神”的故事。而這種說法經常被誤解,這里的關鍵詞是“抽象”,即“抽象”的東西把“精神”從“真實的人”身上剝離開來。但實際上,“精神”是“真實的人”的一種內在品質,人類的實踐能力可以將精神與物質緊密結合在一起。
這就意味著馬克思可以輕而易舉地在歷史語境中談及“精神”。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描述了18世紀法國各個階級是如何被商業精神俘獲的。(2)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MECW 5,p.411.馬克思在1853年3月7—8日為《紐約每日論壇報》撰寫的一篇文章中對英國政治和未經改革的議會發表了評論,這些評論在今天幾乎仍然適用。他寫道,大臣克蘭沃斯勛爵的講話既融合了“輝格黨的真正精神”又融合了“貴族主義的真正精神”。(3)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MECW 11,p.517.恩格斯于1857年在《紐約每日論壇報》上也發表了有關“中國人民精神”的文章(4)Marx on China:Articles for the New York Daily Tribune,Lawrence and Wishart,London,p.48.,并將他的這些文章與1842年的文章進行了比較。
馬克思之所以能夠用這些簡單的方式去描述“精神”,是源于他早期撰寫《巴黎手稿》的經驗,以及他對唯心主義者和早期唯物主義者思想的深入研究。他強調了二者對立的人的本質,并指出了這種“對立性”在人類實踐活動中可以獲得解決的方式。事實上,哲學創造了一種理論上無法解決而只能在現實生活中才能得以解決的對立。這就是精神和物質的對立性。(5)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MECW 3,p.302.
概括來說,精神和物質是現實事物的兩個方面,這些現實事物可能存在于自然界、人類事務或技術層面。比如說森林、社區或衛星都是真實存在的事物,包含物質和精神兩個層面。當談及人類社會時,我們觀察到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類所推崇的目標和價值觀,以及人類生產商品和集體設施的實際方式。
那么西方關于“精神”的描述是什么呢?在此筆者盡可能地概括一下,歡迎提出指正觀點或反對意見。目前,筆者還沒有對西方文化中的“精神”做過詳盡的研究,但可以提出一些假設:首先,馬克思、恩格斯確實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摧毀了黑格爾式大廈,使精神作為人類歷史驅動力的觀點失去了可信性。其次,基督教設法保持了對精神的控制,把精神作為一種只屬于基督教信徒的特殊財產。最后,工業的進步和技術文明的勝利給依賴于機械論和原子實證論的實驗科學賦予了聲望。
對于這些宏大問題,筆者這里不做過多贅述,只想簡單提一下被稱為“20世紀最重要的社會科學文獻”——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我們發現這本書的標題使用了“精神”一詞,但可以看到馬克斯·韋伯是怎么處理的——他并沒有試圖總結資本主義的主要特征,而是通過參考18世紀美國著名人物本杰明·富蘭克林的著作,闡述了他所概括的理想類型。馬克斯·韋伯選取了一些他認為最能體現資本主義精神的段落,并將這些段落作為理想范式,隨后用于其對世界宗教倫理學的比較研究。
但韋伯在這些比較研究中使用的方法是將他選取的那些段落進行分解,而后再在其文章的上下文中單獨提及各個分解成分。因此,他在孔子的儒家思想中找不到思想共鳴,他認為在亞洲宗教中普遍存在的貪婪是沒有限制的,他沒有領會到新教所特有的內心世界的禁欲主義。
幾年后,他修訂了自己的最初表述,并將其以書的形式出版。在之后的表述中,他將資本主義的“精神”定義為一種“有規范的、有約束的、裝扮成‘道德’的生活方式”。“道德”在引號之中,“精神”也在引號之中。事實上,對這些引號的使用,反映出馬克斯·韋伯在使用一種非科學用語時的不安。而他在別處關于“官僚精神”和“普魯士精神”的敘述中也同樣使用了引號。
在此,筆者認為韋伯的做法恰恰反映了西方對于引用“精神”時的一種矛盾心理,主要原因在于精神已經從人類實踐中分離出來了。在這方面我們需要注意的是,韋伯采納了當時在西方廣為流傳的一種觀點,即中國的宗教是一個虛幻的、精神崇拜的領域。韋伯曾經引用過一位權威人士的觀點,這個觀點宣稱:“中國人從來不懂邏輯上的矛盾,他們無法理解兩種形式的信仰是相互排斥的”。(6)A.H. Smith,Chinese Characteristics,p.295.馬克思指出,克服精神和物質分裂的必要條件就是對立統一。
今天,當中國政府宣布“絲綢之路精神具有數千年來代代相傳的文明時”,它所指代的是一種人類產物,一種始終保持著相互聯系的人類活動的組合,而并非一套脫離人類實踐的觀念。中國領導人在號召長征精神或臺風救災精神時,不僅僅是簡單地采用馬克思對 “精神—物質二分法”的否定,而是表達了一種深深植根于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的世界觀。
我們扎根的這個世界是一個具有“精神”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