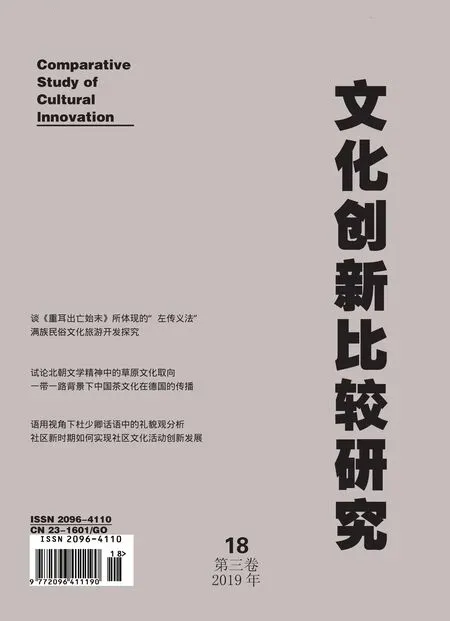談《重耳出亡始末》所體現(xiàn)的“左傳義法”
段全林
(三亞學(xué)院人文與傳播學(xué)院,海南三亞 572022)
微言大義,又稱《春秋》筆法、《春秋》義法。本指《春秋》行文中作者不直接闡述對(duì)人物和事件的看法,而通過人物言行方面的細(xì)節(jié)描寫、詞匯的選取和材料的篩選,委婉而微妙地暗含褒貶、表達(dá)作者主觀態(tài)度的寫法。如三個(gè)表示殺的動(dòng)詞殺、弒、誅,其實(shí)各有深層含義,殺指無罪而殺,弒指以下犯上而殺,誅則指有罪被殺。作者在行文中,選取不同的詞,就暗含了作者對(duì)此事的褒貶態(tài)度,這就是《春秋》義法。
自古以來,人們講“《春秋》義法”,都是針對(duì)《春秋》經(jīng)而言的。“《春秋》三傳”都是為了闡明《春秋》經(jīng)的“微言大義”,即所謂“《春秋》義法”的,而不是說《春秋》三傳本身還存在什么義法。時(shí)至今日,很多古代文學(xué)史教材仍然只提《春秋》筆法,而不提“《左傳》義法”,學(xué)生也不懂什么是“《左傳》義法”。事實(shí)上,《左傳》一書不僅在文學(xué)描寫技巧上,而且在表達(dá)“微言大義”方面,也有一個(gè)獨(dú)立于“《春秋》義法”之外而存在的“《左傳》義法”。下面,以《重耳出亡始末》為例,分析作者如何通過文中的幾位女性形象來展現(xiàn)《左傳》的微言大義,即“《左傳》義法”的。
1 季隗身上所體現(xiàn)的“大義”:“信”
叔隗、季隗都是狄國的狄人以俘虜?shù)纳矸荻謩e贈(zèng)給趙衰和重耳作妾的。當(dāng)重耳要離開狄國到齊國去的時(shí)候,曾對(duì)季隗說:“待我25年,不來而后嫁。”季隗回答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qǐng)待子。”[1]對(duì)于季隗來說,重耳的話等于給她一次獲得自由的機(jī)會(huì)。相對(duì)于25年,重耳的離去,若非她對(duì)愛情的堅(jiān)貞,即使改嫁,能算是背叛嗎?然而,季隗愛上了重耳,因此在回答時(shí)她說若等25年的話,她可能已經(jīng)進(jìn)棺材了。一句“則就木焉”,既包含著不愿分別之情,又包含著對(duì)重耳的哀怨之情。接下來的一句“請(qǐng)待子(我等你)”,多么動(dòng)人啊,包含著對(duì)重耳的理解與支持。后來,重耳回到晉國后,我們從“狄人歸季隗于晉”的細(xì)節(jié)中,可以看出季隗確實(shí)等了重耳多年而未改嫁。至此,作者通過一個(gè)對(duì)話和一個(gè)細(xì)節(jié)(這些都是“微言”)給我們塑造了一個(gè)“信”字當(dāng)頭(“大義”),對(duì)愛情忠貞不渝、出嫁從夫的典型女性形象。
2 姜氏身上所體現(xiàn)的“大義”:“智”
人們常說一個(gè)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個(gè)偉大的女人,重耳后來能夠稱霸,當(dāng)然少不了他與懷贏的特殊關(guān)系——懷贏為重耳贏得了秦國軍事上的支持。另一個(gè)女人,也功不可沒,她就是姜氏。
姜氏是重耳在齊國時(shí)娶的妻子,重耳滿足于這種和姜氏卿卿我我的生活而樂不思蜀。如果這樣長(zhǎng)期待下去的話,必然消磨了重耳的意志,影響他將來的稱王稱霸。在這種情況下,子犯等人在桑樹下密謀,讓重耳盡早離開姜氏、離開齊國的計(jì)劃,卻被在桑樹上采桑的采桑女聽到。采桑女回去把聽到的密謀告訴了姜氏。為防止走漏消息,姜氏忍痛割愛,殺了服侍自己多年的采桑女。之后,姜氏對(duì)重耳說:“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意思是說你重耳有胸懷天下的大志,可你們的計(jì)劃被采桑女聽到了,因此我殺了她。這一對(duì)話和細(xì)節(jié)就顯示了姜氏的機(jī)智果敢。姜氏愛重耳,但為了讓重耳將來成就大業(yè),她并不貪戀眼前這段感情反而勸重耳盡快離開,并且一針見血地指出:“懷與安,實(shí)敗名”(懷戀安逸的生活,茍且偷安,實(shí)是敗壞一個(gè)人名聲的原因)。[2]更為難得的是,在重耳執(zhí)意不走的情況下,她出謀劃策,灌醉重耳,重耳才被送出了齊國。這一細(xì)節(jié)同樣彰顯了她的機(jī)智。這些機(jī)智,通常連男子都很難做到,可作者選取這些材料,通過這些言行細(xì)節(jié)的描述(“微言”),表現(xiàn)了姜氏的大“智”(“大義”):對(duì)丈夫最偉大的愛就是讓其名垂于世,而自己的眼前的兒女之情,不應(yīng)是男人走向成功的羈絆。
3 僖負(fù)羈之妻身上所體現(xiàn)的“大義”:“禮”
僖負(fù)羈之妻所在的曹國,國王可能有刺探他人隱私的嗜好,居然“欲觀其裸浴”,即偷看重耳洗澡。僖負(fù)羈之妻聽說這件事后,就對(duì)丈夫僖負(fù)羈說:“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于諸侯。得志于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3]僖負(fù)羈之妻以自己敏銳的政治眼光,看出跟隨晉公子重耳的這幫人,都有國相之才。憑借這幫人的才干,晉公子重耳必然能夠回到晉國稱王。如果重耳能回到晉國稱王,日后必然在諸侯各國中享有威望并稱霸諸侯。到那時(shí),第一個(gè)受責(zé)問并被誅伐的必然是曾經(jīng)偷看其洗澡的曹國。因此她建議自己的丈夫僖負(fù)羈采取與曹國國王截然不同的態(tài)度,希望給重耳等人留下一個(gè)好印象,以保佑他們?nèi)椅磥淼暮推桨矊帯Y邑?fù)羈聽了妻子的話,就派人“饋盤饗,置璧焉”,即送去一盒晚餐,把一塊璧玉也藏在晚餐里。從這一段話和細(xì)節(jié)的描述(即“微言”)中,我們能體會(huì)到僖負(fù)羈之妻見常人所不能見、言常人所不能言的政治頭腦,我們能感受到的是作者給我們塑造了一個(gè)“禮”字當(dāng)頭(“大義”)的僖負(fù)羈之妻的形象:對(duì)客人要以禮相待;不要只看到客人一時(shí)的落難與窘迫,要有長(zhǎng)遠(yuǎn)的眼光。
4 趙姬身上所體現(xiàn)的“大義”:“義”
當(dāng)年,趙衰跟隨重耳流亡到狄國,狄人送給趙衰一小妾,名叫叔隗。叔隗給重耳生下一兒子趙盾。后來,重耳回到晉國稱王后,重耳將女兒趙姬許配給趙衰為妻。古代男子通常有三妻四妾,妻妾之間難免存在爭(zhēng)風(fēng)吃醋的矛盾。可不同于一般女性的是,趙姬居然強(qiáng)烈建議趙衰迎回叔隗及其子趙盾。在趙衰執(zhí)意不肯的情況下,趙姬說:“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4]意思是說,如果趙衰得到我這個(gè)新寵而忘記舊好叔隗,以后還怎樣使用別人?所以,一定要把叔隗母子接回來。在趙姬的“固請(qǐng)”(堅(jiān)決請(qǐng)求)下,趙衰才答應(yīng)下來。這是細(xì)節(jié)一。在迎叔隗之后,趙姬發(fā)現(xiàn)趙盾很有才干,于是,“固請(qǐng)于公,以為嫡子,而使三子下之”,還請(qǐng)求“以叔隗為內(nèi)子,而己下之。”意思是說趙姬請(qǐng)求趙衰把叔隗作為正妻,而自己甘愿做妾,并且以趙盾為嫡長(zhǎng)子而使自己親生的三個(gè)兒子位居趙盾之下。這是細(xì)節(jié)二。以上這兩個(gè)細(xì)節(jié),真可謂《重耳出亡始末》中的“微言”,也是《左傳》中的“微言”。然而,這樣的“微言”卻表現(xiàn)了《左傳》的“大義”:為維護(hù)家庭的長(zhǎng)久興盛和國家的未來發(fā)展,做女人的寧肯不要虛名,也要以寬廣的胸懷和善良的品行去做賢內(nèi)助。應(yīng)該說,在趙姬身上,體現(xiàn)了中國女性共有的賢淑、善良等傳統(tǒng)美德。趙姬用她一顆真誠、善良、寬厚的心在歷史上留下了美名,其行為看起來“若愚”,其實(shí)是大寫的“義”字。后來的歷史證明,趙盾不僅在趙家的繁榮興盛過程中成為重要的接力棒人物,同時(shí)也是晉國中流砥柱式人物,并為晉國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趙姬身上所體現(xiàn)的“義”,意義可謂深遠(yuǎn)。
5 介之推之母身上所體現(xiàn)的“大義”:“仁”
重耳回國即位后,跟隨他出亡的大臣都有了相應(yīng)的官爵和俸祿,而介之推因說了幾句怨言,且沒主動(dòng)找重耳為自己爭(zhēng)取俸祿,而在封爵的事情上被重耳遺漏。于是,介之推想隱居起來。
他的母親問他:“你何不也去請(qǐng)求俸祿,不然的話,苦死了又能怨誰呢?”介之推答道:“明知是有罪的事情,效仿它,罪更大呀!因說了怨言,就不吃他的俸祿。”
介之推的母親又問道:“你隱居的事也讓重耳知道一下,怎樣?”介之推答道:“言語,是身上的文采,身子都隱藏起來了,哪還用得著文采?”說到這里,介之推的母親接著說:“如果是這樣的話,我與你一塊兒去隱居”。
作品通過介之推母子間的幾番問答(“微言”),把一位慈愛、開明,明事理,不慕富貴的母親形象展現(xiàn)在我們面前,突出的是一個(gè)“仁”字(“大義”):為成就兒子的志向,自愿與兒子一起歸隱山林,過清苦生活。
介之推之母的所為,造就了中國歷史上一位著名的隱士——介之推,也直接導(dǎo)致了中華民族的兩個(gè)重要節(jié)日“寒食節(jié)”和“清明節(jié)”的誕生。
以上幾位女性形象在《重耳出亡始末》中都是配角,但作者恰恰是通過這些配角的言行和諸多細(xì)節(jié)的描述,鮮明地表達(dá)了作者的看法和態(tài)度,那就是儒家所倡導(dǎo)的仁、義、禮、智、信。這種寫作方法就是“左傳義法”,就是《左傳》的“微言大義”。
《重耳出亡始末》一文證明,在表達(dá)“微言大義”方面,《左傳》有一個(gè)完全獨(dú)立于“《春秋》義法”之外而獨(dú)立存在的“《左傳》義法”。其特點(diǎn)是《左傳》在敘事時(shí)貫穿著一個(gè)基本的指導(dǎo)思想,就是表達(dá)儒家諸如仁、義、禮、智、信等方面的做人的思想。《左傳》中的這些“大義”與《春秋》經(jīng)所暗示的、已被歷代學(xué)者們論述過無數(shù)遍的“大義”是迥然不同的:《左傳》重點(diǎn)表達(dá)了一種關(guān)于做人的德性思想,而《春秋》經(jīng)重點(diǎn)表達(dá)了一種經(jīng)世安邦的思想。這一點(diǎn),從唐宋以來,特別是清代的桐城派的諸多名家的研究中早已得到證實(shí)。[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