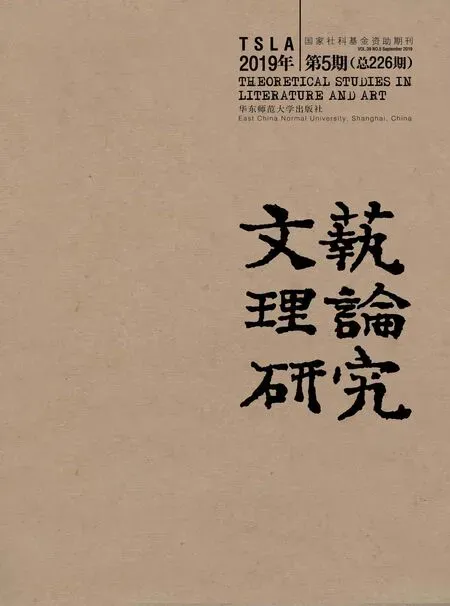試論朗西埃的現代虛構觀
曹丹紅
虛構問題是文學研究無法避開的問題,同時還因其涉及現實、語言、思維與真理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而始終在人文學科諸多領域占據著重要位置。法國知名學者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對虛構問題的關注由來已久,近年來更是出版了《消失的線——論現代虛構》(Le
fil
perdu
.Essais
sur
la
fiction
moderne
2014年)《虛構的邊界》(Les
bords
de
la
fiction
2017年)等專論,對現代虛構的本質進行了思考。朗西埃在其中提出的現代虛構觀頗為獨特,我們認為,對這一獨特虛構觀做出一番考察不僅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朗西埃的思想,也有助于反思虛構觀念本身。一、 什么是傳統虛構理性?
在《消失的線——論現代虛構》的引言中,朗西埃開門見山地指出:“在《情感教育》與《吉姆爺》的時代,虛構發生了一些變化,它失去了秩序與比例,而秩序與比例是此前人們判斷虛構作品是否優秀的標準。”(Le
fil
8)《情感教育》與《吉姆爺》的時代跨度很大,從《情感教育》第一版出版的1843—1845年直至1900年,橫跨整個19世紀下半期。那么,在這翻天覆地、風起云涌的半個世紀里,西方的虛構究竟產生了怎樣的變化?變化產生之前的虛構如何,變化之后的虛構又如何?朗西埃本人面對這種變化又持什么態度?對朗西埃來說,這些問題的答案似乎顯而易見: 變化之前的西方虛構遵循亞里士多德確立的摹仿傳統,變化之后的虛構則走上了相反的道路。《虛構的邊界》一開篇,朗西埃即對亞里士多德《詩學》展開回顧,并為《詩學》所創立的虛構傳統總結出以下幾條核心原則。首先,在亞里士多德看來,虛構摹仿的是行動。在《詩學》中,亞里士多德反復強調,“摹仿者表現的是行動中的人”(38),或者“此類作品之所以被叫做‘戲劇’是因為它們摹仿行動中的人物”(42)。不過這番話并不意味著人物是摹仿的重心,因為亞里士多德隨后指出,“悲劇是對行動的摹仿,它之摹仿行動中的人物,是出于行動的需要”(65)。另一方面,《詩學》結尾提到史詩時說,“史詩詩人也應該編制戲劇化的情節,即著意于一個完整劃一、有起始、中段和結尾的行動”(163)。鑒于戲劇和史詩對亞里士多德來說意味著全部詩歌類型,因此也可以說,對亞氏而言,文學即意味著對行動的摹仿。“行動”一詞在亞氏倫理學體系中占據重要地位,暗含了行動主體、意愿與選擇、目的性等豐富內涵,由此使傳統虛構內在地具有了某些重要特征。
其次,虛構排除了偶然性,也就是說虛構是個有機整體,它的情節環環相扣,事件根據必然性或可然性原則得到組織,這里朗西埃想到的應該是亞里士多德的名言,“詩人的職責不在于描述已經發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發生的事,即根據可然或必然的原則可能發生的事”(《詩學》81)。對亞里士多德及其繼承者來說,根據可然性或必然性來組織情節,這是詩歌區別于歷史的最根本特征。在虛構作品中,必然性或可然性原則又體現為相互關聯的兩方面,一方面,情節的發展遵循因果邏輯,另一方面,虛構中的時間都與情節發展的某個環節有關,都是有效的行動時間。
最后,虛構強調行動的認知價值。亞里士多德對認知的重視由《尼各馬可倫理學》可見一斑,亞氏在其中提到,行動的目的是對幸福的追尋,而終極的幸福是過上一種智性生活。在《詩學》中,亞氏指出,事件的發展不是神力干預的結果,而是行動者認知狀態導致的結果,更確切的說是由行動者在無知狀態下犯下某個錯誤所導致。例如《詩學》十三章中有言:“一個構思精良的情節必然是單線的[……]它應該表現人物從順達之境轉入敗逆之境,而不是相反[……]人物之所以遭受不幸,不是因為本身的邪惡,而是因為犯了某種后果嚴重的錯誤”(98),《詩學》十四章又強調,詩人組織行動的最好方式,是將人物的行動描寫成不知情情況下做出的舉動,“如此處理不會使人產生反感,而人物的發現還會產生震驚人心的效果”(107)。認知錯誤引發蝴蝶效應,最后導向不幸結局,行動者面對悲劇結局意識到自己的錯誤,完成了認知過程。而認知達成的一刻也是真相披露、行動突轉、命運變換的一刻,這一刻令悲劇觀眾對人物命運產生憐憫或恐懼,悲劇的凈化功能就此產生。
以上由亞里士多德確立的虛構原則與精髓,朗西埃稱其為傳統虛構理性(rationalité或raison fictionnelle),后者概括來說就是“虛構知識組織了事件,活躍的人通過事件,從幸運走向了不幸,從無知走向了知識”(Les
bords
10)。朗西埃認為,如果說亞里士多德之后的虛構確實被這種虛構理性左右,那么19世紀以來的文學創作——尤其是福樓拜、康拉德、左拉、伍爾夫、普魯斯特等人的創作則逐漸擺脫了這種虛構理性,而傳統虛構理性的顛覆既意味著文學觀念與實踐從再現體制(régime représentatif)進入到美學體制(régime esthétique),也意味著某種文學與政治新關聯的誕生。二、 從行動的推進到感性的共存
由上文可見,對朗西埃來說,傳統虛構理性最重要的原則是對行動的摹仿,而他的反撥也由此入手。通過兩個步驟,他完成了對傳統虛構理論的顛覆。
1. 從行動的主人公到不行動的大多數

Les
bords
9),但實際上,“行動主體的數量是有限的,因為大部分人嚴格來說并不行動: 他們只是制造物品和孩子、執行命令或提供服務,在第二天重復前一天的事。這一切之中沒有任何期待,沒有任何期待的落空,不會犯任何可能令人從一種條件過渡到其反面的錯誤。傳統虛構理論因此只跟很少一部分人及人類活動有關,剩下的全部受制于無秩序、無緣故的經驗現實”(Les
bords
9)。朗西埃在現代虛構作品中觀察到的,正是這些融入日常生活的不行動的大多數,他們進入文學并成為了后者的表現對象。他指出:“在巴爾扎克和雨果的時代,文學也許最先對日常生活背景及形式所具備的承載歷史的力量給予了肯定,不僅如此,對于這一內在于無名事物、存在及事件的力量,文學還把它變成了某種斷裂的原則,來與過去從幸運到不幸、從無知到知識的重要轉變模式拉開距離。”(Les
bords
11)這一觀察并不是朗西埃一廂情愿的判斷,因為它也符合某些理論家總結出的文學發展規律。在《寫作的零度》和《什么是文學?》中,巴特與薩特就曾不約而同地指出,文學應表達社會上升階級與新興力量的訴求。隨著資本主義經濟與社會發展,尤其在標志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最終決裂的1848年革命以后,匿名的大多數逐漸成為法國社會中對抗資產階級統治的主要力量,理應成為新虛構的表現對象。2. 從行動的推進到感性的共存
然而,不行動的無名的大多數及其生活成為文學表現對象,這只是朗西埃意義上的現代虛構的必要不充分條件。為理解這一點,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朗西埃現代虛構觀的其中一個理論來源,也就是奧爾巴赫及其在《摹仿論》中提出的文體混用原則。奧爾巴赫論證的出發點是古希臘羅馬文學所確立的文體分用原則,朗西埃將其概括為文類性準則和得體性準則(朗西埃7—13),這兩個準則又與虛構準則密切相關。一方面,不同的文類用以表現不同的對象,《詩學》即明確指出“喜劇傾向于表現比今天的人差的人,悲劇則傾向于表現比今天的人好的人”(38)。對象的等級進而決定了文類的等級,因為悲劇摹仿對象在社會身份與地位上高于喜劇,悲劇在古希臘的地位與重要性便高于喜劇,這一點反過來又影響了西方文學史上“嚴肅”或“高雅”文學的主題與形式。另一方面,不同的風格用以表現不同的對象,體現了形式與主題的適應。奧爾巴赫通過考察西方文學史,發現由亞里士多德奠定的文體分用原則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命運有所不同,自19世紀初以來越來越明顯地被作家僭越。奧爾巴赫本人對違背這一原則的作家或文學運動表示贊賞,在他看來,“司湯達和巴爾扎克將日常生活中的隨意性人物限制在當時的環境之中,把他們作為嚴肅的、問題型的、甚至是悲劇性描述的對象,由此突破了文體有高低之分的古典文學規則”(652),他們的創作“為現代寫實主義開辟了道路,自此,現代寫實主義順應了我們不斷變化和更加寬廣的生活現實,拓展了越來越多的表現形式”(653)。
朗西埃的現代虛構觀無疑深受奧爾巴赫影響,但他比奧爾巴赫走得更遠。談到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和伍爾夫的《到燈塔去》,奧爾巴赫認為包法利夫婦吃一頓晚飯的事件盡管日常,拉姆齊太太量襪子長度的舉動盡管平凡,這些微不足道的事件卻在敘述中獲得了某種象征力量,“人們相信,信手拈來的生活事件中,任何時候都包含著命運的全部內容,也是可以表述的”(645),對奧爾巴赫來說,這兩個例子是用高文體來嚴肅對待“低等”主題的范本。但朗西埃并不滿足于此,他發展了“奧爾巴赫發現卻沒有明確提出”(Les
bords
13)的東西,在他看來,發掘普羅大眾身上的高貴之處,揭示吃晚飯、量襪子這樣的日常舉動所包含的悲劇性,令尋常物嬗變成藝術品,這種邏輯仍然是重構行動的嘗試,因而還沒有擺脫傳統虛構邏輯。真正的新虛構應試圖打破的,是整個再現邏輯。這從他對《包法利夫人》的解讀可見一斑。在他看來,農民的女兒愛瑪愛看騎士小說,這件事本身不但無可非議,還意味著匿名大眾從此也可自由獲取知識,而知識不再專屬某個階級的事實反映出19世紀法國社會民主程度的加深。愛瑪的問題在于,她那愛幻想的頭腦總是試圖按照她所讀過的舊小說的模式來安排自己的生活,也就是總試圖回到與再現邏輯相適應的舊制度中去。朗西埃認為,福樓拜正是出于對等級分明的舊制度及其意識形態產物——再現式文學的深惡痛絕,而不是覺得“放任了愛瑪一段時間之后,斷定這種民主過度了”(鄭海婷90),才會在《包法利夫人》中為愛瑪安排了死亡的結局。朗西埃進而借福樓拜的觀點,拓展了奧爾巴赫的理論,同時確立了自己獨特的現代虛構觀。在一封寫給露易絲·柯萊的著名信件中,福樓拜曾說:“主題沒有美丑之分,而且我們幾乎可以依據純藝術流派的觀點確立一條準則,即根本不存在主題,唯有風格才是看待事物的絕對方式。”(Correspondance
345—46)這便是現代虛構所產生的變化,現代虛構“并不僅僅意味著[……]普通人的情感與‘偉大靈魂’一樣,也能成為激發詩歌創作的靈感,它還意味著某種更為徹底的局面,從此以后,再無主題(sujet)存在”(Politique
19)。主題暗示了統一性與一貫性,意味著主次、布局與比例,“再無主題存在”則意味著這一切的消失。但是,無主題的寫作似乎難以想象,它究竟是怎樣一種寫作?朗西埃認為現代虛構“執行了兩個操作,第一個操作將匿名能力的表現分解為無數無人稱的感性微型事件(micro-événements sensibles),第二個操作將寫作的運動等同于這一感性組織的呼吸本身”(Rancière,Le
fil
32)。這段話還需結合朗西埃一貫的美學思想加以理解: 首先,個體具備審美能力,任何人都能感受到任何情感,這種能力是實現個體平等的基礎。其次,個體感受力是一種類似濟慈所說的“消極能力”(negative capability),個體并不像傳統虛構中的主人公那樣去行動,而是任由事件與感覺降臨到自己身上。因而個體的感性體驗遵循的不是有始有終的英雄模式,而是波德萊爾筆下的漫游模式。個體在夢游般的遐思之中與來自外界的紛擾事件相遇又分離,在環境、情感與思想共同作用下,獲得對事件的短暫的、碎片式的感受。最后,這些碎片式感受彼此平等,“都被整體的力量賦予了生命”(Rancière,Le
fil
89),這“整體的力量”及上文提到的“匿名能力”“內在于無名事物、存在及事件的力量”都是一回事,都是“大寫的生活,穿過并超越每個個體生活的普遍的生活”(118),朗西埃的美學思想是對“生活范式(paradigme de la vie)”(127)的推崇。因此現代虛構盡管書寫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但它并不意味著普通人與日常生活成為文學的“選民”,就此獲得高貴的地位;日常生活在現代虛構中分裂成無數感性微型事件,后者是碎片化的感覺,被虛構作品表達后,它們是無主的話語,可以是任何人的感受與表達,體現出一種無人稱性,仿佛“無限微粒的永恒運動,在某種永恒的顫動的中央,時而聚攏,時而分散,或者重新聚攏。正是這個運動構成了新虛構的質地”(Le
fil
34)。福樓拜、左拉、康拉德、伍爾夫、普魯斯特等作家的作品中體現的正是這種無人稱的微粒運動。以伍爾夫《到燈塔去》第二部分為例,這一部分的內容大多在描寫更迭的四季、交替的晝夜、靜止或變化的自然環境,以及在這一切包圍影響下逐漸毀損的拉姆齊家海濱別墅。這些描寫很難找到敘事學意義上的視點與敘述主體,即無法確定是誰在觀察誰在說話。奧爾巴赫評論《到燈塔去》時,把文中無法確定說話人的自由間接引語看成對“多個人的意識描述”(633)或“多元意識鏡像”(647),此時他考慮的“多個人”主要還是書中的人物,無人稱性則意味著作品中的觀察、感受與表達再也找不到主人,任何讀者都可以將其據為己有。文中也涉及人物行動,但主語常常是“人們”“一個身軀”“一只手”……也有有名有姓的人出現,也就是別墅管家婆麥克奈布太太,面對歲月流逝感嘆憂愁的長久、生活的單調,自問還能活多久。但伍爾夫對麥克奈布太太的描寫無疑是抽象的、詩意的,甚至有些失真,描寫她只因她也在環境之中,也是熙熙攘攘的感性微型事件中的一件,她的嘆息與思考融入環境,失去了個人色彩,她的名字完全失去了“以名舉實”的作用,她可以叫任何一個名字,她可以是任何人的代言人,她與周圍環境一起,被生活的氣息與洪流裹挾而走。因此,現代虛構看似沒有放棄對人物命運的講述,實際上是將原子一般的無人稱狀態組合在一起,它不再是某個英雄或悲劇人物的故事,而是所有“無名事物、存在及事件”的狀態組合,是“偉大的無人稱生活(grande Vie impersonnelle)”(Le
fil
33)的自行展現。當微粒的永恒結合與分離運動打亂行動,滲入虛構并改變后者的質地,傳統虛構理性中與行動密切相關的另兩個原則——虛構根據必然性或可然性安排情節,虛構重視認知價值——也被顛覆。在新虛構中凸顯出來的是一種“感性狀態并存的秩序”(Le
fil
33),也就是大量“感性微型事件的并置”(Malaise
13),面對這些事件,無論對人物、作者還是讀者來說,比起運用智力進行分析,更為重要的似乎是發揮感受力,去充分“體驗內在與外在的融合”(Politique
71)。三、 從敘述到描寫
由內容的差異產生了現代虛構與傳統虛構的另一個差異: 當行動不再是虛構關注的中心,虛構文的寫作方式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描寫——尤其是細節描寫開始取得重要地位。描寫與敘述的歷史同樣悠久,但與敘述相比,描寫在虛構傳統中始終處于較為尷尬的地位。對描寫進行過深入研究的法國當代文論家哈蒙(Philippe Hamon)指出,在很多理論家眼中,描寫具有無法控制的膨脹與擴張傾向,同時還會在文中引入古怪的或太過專業的詞匯,損害表達的自然流暢及文學作品的統一性,影響讀者的閱讀體驗,阻礙文學發揮自己的教化或娛樂功能。因為這些缺陷,所以在16至18世紀的法國修辭學與詩學理論中,“描寫并沒有真正的理論地位”(Hamon10)。另一方面,描寫又受到嚴格的限制,它的主要功能是為行動提供時間、地點、背景等信息,或者為人物提供側寫,幫助讀者理解其道德、情感與行為,總之,它必須對行動的敘述起到輔助的作用。從19世紀初開始,隨著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文學的興起,因為司湯達、巴爾扎克、福樓拜尤其左拉等人的努力,描寫的地位有所改善;20世紀的新小說更是賦予描寫一種人類學意義上的重要性。但將描寫視作手段而非目的的觀念卻始終存在,即便是福樓拜、左拉等作家在面對描寫時都抱持一種曖昧的態度,而盧卡奇、雅克布森、瓦萊里等理論家也都曾從不同立場強調過描寫的“危害”,并勸告寫作者克制描寫的沖動。
在這種描寫觀中,不難想象細節描寫遭遇的抵制。朗西埃認為“描寫所具備的過度‘現實主義’傾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闡釋,從這一闡釋中能夠獲得一種有關虛構詩學與虛構政治學關系的全新認識”(Le
fil
10),由此重新定位了現代虛構作品中的細節描寫。其論證從反對巴特與薩特的描寫觀入手。在著名的《真實效應》(L’Effet de Réel)一文中,巴特就福樓拜中篇小說《淳樸的心》的描寫展開了思考。福樓拜在《淳樸的心》開篇花不少筆墨描寫了女主人公費莉西泰幫傭的歐班太太家的房子,觸動巴特的是其中一句描寫“正房”的話:“晴雨表下方的一架舊鋼琴上,匣子、紙盒,堆得像一座金字塔。”(3)巴特認為晴雨表“這個物體不突兀卻沒有任何意義,初看之下并不屬于可被‘記錄’的東西范疇”(Barthes84-85),因而很難從結構功能的角度得到解釋,進而將晴雨表歸入西方普通敘事作品中隨處可見的“無用的細節”(Barthes85)行列,并思考了其“無用之用”: 細節通過自己具體、精確卻無用的特征,令讀者“感覺自己所看到話語的唯一法則就是對現實的嚴格摹寫,以及在讀者與現實世界之間建立直接的聯系”(Todorov7),也就是說制造出了令人信服的“真實效應”。由此可見,巴特的分析還是沒有脫離其符號學思想。在薩特看來,“福樓拜寫作是為了擺脫人和物。他的句子圍住客體,抓住它,使它動彈不得,然后砸斷它的脊梁,然后句子封閉合攏,在變成石頭的同時把自己關在里面”(薩特163)。薩特認為,作家精雕細琢描寫文字,制造出一個與現實世界隔絕的抽象世界,似乎想通過這一舉動表明對資產階級當權的世界漠不關心,由此來與資產階級劃清界限。但實際上他們的能指游戲無法為新興的無產階級所理解,也無法對其產生任何作用,因而風格游戲體現的,其實是作家向社會保守勢力的妥協。朗西埃指出,以上兩種觀點表面看來有些矛盾,實際上殊途同歸: 巴特與薩特都將描寫視作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在文學上的反映,他們的思路仍然沒有擺脫舊的再現邏輯,因而都“錯過了問題的核心”(Le
fil
20)。在他看來,福樓拜對外省生活的描寫,伍爾夫對資產階級生活起居的描寫,左拉對工人生活的描寫,康拉德對大海的描寫等等,所有這些描寫只為自身存在,被描寫的細節是“感性微型事件的并置”,是經緯交錯的知覺與情感,是它們編織出現代虛構文本的網絡,而對行動的敘述轉變成了網絡中的網眼。《到燈塔去》第二部分明顯體現出敘述與描寫的地位變化。在占據全書不到十分之一的篇幅里,作者講述了十年間發生的事。那些本該為傳統虛構大書特書的事件——全家核心人物拉姆齊太太的死亡以及最美麗的女兒普魯的婚姻與死亡都被壓縮至短短幾行,與人物行動與狀態相關的簡短文字全部被放置于括號內,仿佛只是無關緊要的背景介紹,除此之外的文本空間都被描寫占據。這里有兩點需要注意,朗西埃盡管沒有總結,卻在論述中不斷提及。第一點,描寫增多并不僅僅意味著在作品中增加一些畫面(tableaux)。現代文學中大量出現的描寫受到19—20世紀保守批評家的批評,后者氣惱地指責作家用畫面取代了行動。但朗西埃認為,這些畫面“并不是靜止不動的。它們是差異,是移動,是強度的累積,外部世界通過這些活動滲透入心靈中,而心靈制造了它們生活的世界。正是這個感知與思想、感覺與行動交融其中的肌理”(Le
fil
29)構成了現代虛構中人物的生活。也就是說,現代虛構作品中的描寫并不意在精確描繪外部世界,它們是世界、心靈、思想、情感彼此影響、彼此交織的產物,因而往往籠罩著某種夢境色彩,《包法利夫人》中的外省風景描寫,《到燈塔去》的房屋描寫,《吉姆爺》中的大海描寫等莫不如是,朗西埃也正是據此認為注重描寫的“現實主義根本不是對相似性的價值的肯定,而是對相似性起作用的框架的摧毀”(Le
partage
34)。另一方面,盡管人們時常給現代虛構貼上“印象主義”的標簽,但朗西埃認為不應受所謂“印象主義”的欺騙,因為作為現代虛構肌理的感性微型事件彼此之間是平等的地位,它們都試圖脫離中心,或者說它們全部是中心,不可能將這些并置的感性事件拼湊成一個完整的畫面。第二點,敘述與描寫篇幅的增減只是新虛構質地變化的表象。從更為本質的角度說,敘述與描寫篇幅的此消彼長首先當然源于現代虛構中行動重要性的減弱。其次也因為現代虛構“將事件分解為感受與情緒的單純游戲”(Politique
68)。舉例來看,《包法利夫人》中,愛瑪的人生觀、價值觀與魯道爾夫截然不同,卻可以說是突然之間對他產生了愛意。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農業評比會上,魯道爾夫坐在愛瑪身邊,愛瑪聞到魯道爾夫頭發的香味,回憶起昔日的舞會和難以忘懷的子爵,看到遠處的“燕子車”,回想起舊情人萊昂,這些回憶彼此交織疊加,作用于她的情緒,使她最終無力抽回被魯道爾夫握住的手。《吉姆爺》中,富有英雄主義情結的吉姆在帕特那號遇難進水之時突然棄船逃生。這一切又是如何發生的?吉姆在意識到船只必沉無疑并且自己無力拯救船上幾百名乘客時,他看到墨黑的烏云吞噬了船只和星光,看到暴風雨來臨的先兆,感到浪涌晃動了大船和他自己的大腦,看到有人死了,聽到已經逃離的人不斷呼喚死人的名字,在種種刺激下,他產生了可怕的幻覺,不由自主跳下帕特那號,逃到救生船上。《包法利夫人》與《吉姆爺》表明,如果說在傳統虛構中,行動轉變與人物認知有關,并且遵循因果邏輯,那么在現代虛構中,行動轉變往往是一連串感性事件作用下的突變,而對行動的敘述也自然被對感性事件的描寫所取代。總而言之,在現代虛構中,“描寫的膨脹損害了構成現實主義小說特殊性的行動,但它不是對渴望確立自身永恒性的資產階級世界財富的展露,也不是人們忙不迭指出的再現邏輯的勝利,相反,它標志著再現秩序的斷裂,以及構成其核心的行動的優越地位的顛覆。”(Le
fil
20)四、 感性的分配與文學的政治
以上我們對朗西埃的現代虛構觀進行了簡要的評述,這一現代虛構觀包括兩方面內容,首先是對亞里士多德《詩學》確立的傳統虛構理性的批判,其次是對席勒、濟慈、福樓拜、伍爾夫、奧爾巴赫等作家學者思想的繼承,它指出現代虛構不再以摹仿某個有機整一的行動為核心,而是著力表現并置的感性微型事件。內容的改變導致了現代虛構形式上的變化,傳統虛構中被邊緣化的描寫獲得了與敘述同等甚至更為重要的地位,從根本上改變了現代虛構的質地。朗西埃所舉的例子基本都是19世紀后半期20世紀前半期的作家及其作品,但很多當代虛構作品的特點都印證了他的現代虛構觀的中肯性,例如勒克萊齊奧的《訴訟筆錄》《沙漠》《看不見的大陸》等作品都可以看作是對朗西埃所說“偉大的無人稱生活”的記錄。與此同時,在讀者戲稱“小說不如生活精彩”的當今社會,舊有虛構模式遭到越來越多的質疑與挑戰,朗西埃的現代虛構觀為反思今日文學虛構理論與實踐提供了一種新穎的視角。
不過,作為哲學家、思想家,朗西埃在提出現代虛構觀時瞄準的并不僅僅是文學領域,他對傳統虛構理性本質的認識即表明了這一點:“自亞里士多德起人們就知道,虛構并不是對想象世界的創造,它首先是一種理性結構: 一種呈現模式(mode de présentation),令事物、處境或事件變得可以感知與理解;一種關聯模式(mode de liaison),在事件之間構建起并存、先后、因果等種種形式,并賦予這些形式以可能性、現實性或必要性等特征。”(Le
fil
11)虛構是一種呈現與關聯模式,這意味著虛構是我們在某種思維模式影響下,賦予世界以秩序進而認識世界的手段,不同的虛構理性因而體現的是對不同社會秩序的理解與把握,《克萊芙王妃》所展現的井然有序的空間與《包法利夫人》所展現的被物品擠滿的空間是不同社會秩序、不同感受性的象征。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朗西埃提出虛構并非文學作品的特權,政治行動與社會科學遵循同樣的虛構邏輯,而“虛構秩序的紊亂反過來促使我們思考詞與物、感知與行動、重復過去與展望未來、現實感與可能感、必要感與逼真感之間的新關系,社會經驗與政治主體性的形式恰恰由這些關系構成”(Le
fil
13)。在這一點上,朗西埃對現代虛構本質的認識自然地與他的美學觀相對接。對朗西埃來說,美學是“對時間與空間,對可見與不可見,對話語與噪音的切分,這一切分同時決定了作為經驗形式的政治的場所與關鍵”(Le
partage
13-14)。文學與其他藝術活動一樣,背負著與政治行動、社會科學同樣的任務,或者說對朗西埃來說,文學實踐本身就是政治,以現代虛構為例,它重新切割布置時空,打破階級與身份限制,利用匿名的大多數的感受力,將消極被動的人群引入舞臺,令不可見變得可見,令無意義的噪音變成清晰的話語,總之,文學有能力借助對感性的重新分配,創造出一個人人平等的全新的“人世共同生活”(Les
bords
147),這是朗西埃賦予文學的解放力量。但是,徹底顛覆傳統虛構理性是難以想象的,朗西埃也清楚意識到這一點。包法利夫人、吉姆爺、拉姆齊太太的死亡也許確實象征著傳統虛構邏輯的失敗,但它們作為故事的結局,卻體現出情節也就是傳統虛構理性的勝利,因此,盡管“新虛構的本質是一元論的,它的實踐卻只能是辯證的,只能是無人稱生活的偉大抒情曲與情節安排之間的張力”(Le
fil
67),也就是說,兩種虛構理性的并存是文學虛構作品的現實,文學的矛盾性由此而來。在朗西埃看來,這一新舊辯證法也許永遠不會消失,而保持文學的這種辯證性或許就是最深刻的文學的政治。注釋[Notes]
① 亞里士多德并沒有直接探討“虛構”問題,不過德國學者漢伯格(K?te Hamburger 1957年)、法國學者熱奈特(Gérard Genette 1991年)、謝弗(Jean-Marie Schaeffer 1999年)等人均建議將《詩學》的核心概念mimesis翻譯成fiction。熱奈特曾特別指出“亞里士多德,我重申一下,把我們稱之為fiction的東西稱作mimèsis”(Genette 227),謝弗也在其影響廣泛的《為什么要有虛構?》(Pourquoi
la
fiction
? Paris: Seuil, 1999年)一書中不時將mimèsis與fiction混為一談,朗西埃更是在新著《虛構的邊界》的引言中先直接指出“詩,應該理解為對戲劇虛構或史詩虛構的創造”(Les
bords
7)。引用作品[Works Cited]
亞里士多德: 《詩學》,陳中梅譯注。北京: 商務印書館,1996年。
[Aristotle.Poetics
. Trans. and Ed. Chen Zhongme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66.]——: 《尼各馬可倫理學》,廖申白譯注。北京: 商務印書館,2003年。
[- - -.Nicomachean
Ethics
. Trans. and Ed. Liao Shenba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3.]奧爾巴赫: 《摹仿論》,吳麟綬等譯。北京: 商務印書館,2014年。
[Auerbach, Erich.Mimesis
. Trans. Wu Linshou, et al.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Barthes, Roland. “L’effet de réel.”Communications
11(1968): 84-89.居斯塔夫·福樓拜:“淳樸的心”,《福樓拜小說全集》(下卷),劉益庾、劉方譯。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3—28。
[Flaubert, Gustave. “A Simple Heart.”The
Complete
Fictional
Works
of
Flaubert
. Trans. Liu Yiyu and Liu Fang. Vol.3.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2.3-38.]- - -.Correspondance
. Deuxième série (1847-1852). Paris: Louis Conard, 1926.Genette, Gérard.Fiction
et
diction
. Paris: Seuil, 2004.Hamon, Philippe.Du
descriptif
. Paris: Hachette, 1993.Rancière, Jacques.Le
partage
du
sensible
. Paris: Galilée, 2000.- - -.Le
fil
perdu
:Essais
sur
la
fiction
moderne
. Paris: La Fabrique, 2014.- - -.Les
bords
de
la
fiction
. Paris: Seuil, 2017.- - -.Malaise
dans
l
’esth
étique
. Paris: Galilée, 2004.- - -.Politique
de
la
litt
érature
. Paris: Galilée, 2007.雅克·朗西埃: 《沉默的言語》,臧小佳譯。上海: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
[Rancière, Jacques.Mute
Speech
. Trans. Zang Xiaojia.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6.]讓-保羅·薩特:“什么是文學?”《薩特文學論文集》,施康強等譯。合肥: 安徽文藝出版社,1998年。69—291。
[Sartre, Jean-Paul. “What Is Literature?”Sartre
’s
Critical
Essays
on
Literature
. Trans. Shi Kangqiang, et al. Hefei: Anhu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8.69-291.]Todorov, Tzvetan. “Présentation.”Litt
érature
et
r
éalit
é. Eds. Gérard Genette et Tzvetan Todorov. Paris: Seuil, 1982.7-10.鄭海婷:“我們需要怎樣的現實主義文學”,《文藝爭鳴》12(2017): 89—94。
[Zheng, Haiting. “What Kind of Realistic Literature Do We Need.”Literature
and
Art
Forum
12(2017): 8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