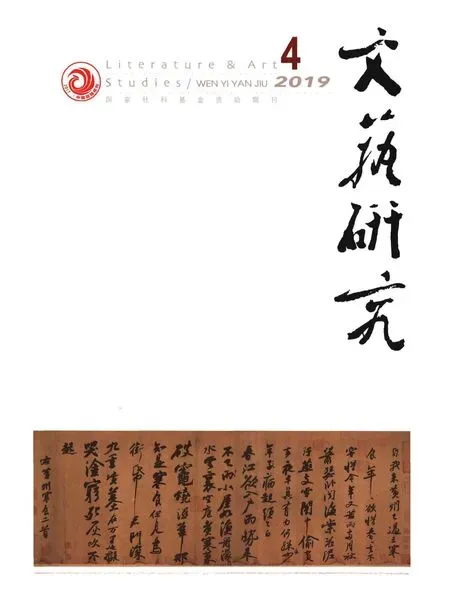以書自名,必有深趣
——李邕書史地位及其行書創(chuàng)變價值芻議
王福州
一
初唐書法初顯絢爛之光,與太宗李世民的個人修養(yǎng)和決策息息相關。貞觀二十二年(648),李世民借編修《晉書》之機,匠心獨運,精選出晉宣帝、晉武帝和文學家陸機、書法家王羲之四位歷史人物,并為之題贊。尤對王羲之書法贊賞有加,所謂“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王羲之傳贊》)①。他還親自下詔征集鑒藏歷代名家法書,其中就包含“天下第一行書”《蘭亭序》。實際上,就太宗自身書風和帝王氣度而言,對王書的推崇,更大程度上還在于他能超乎技法之外,體味王書之道。太宗以藝術家的敏銳把握書法技、道之理,更以政治家的身份和責任擔負起整理文化遺產和治理國家之重任。他將書法視為化育天下的不朽盛事,這與初唐后期孫過庭書學、魏征文學的思想主張是完全一致的。與此同時,太宗在選官、教育、學術等國家制度中推行書法。書法不僅為開科取士的科目,也是銓選官吏的重要標準,這些措施為有唐一代的書法繁盛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社會氛圍。“唐代書家之盛,不減于晉,固由接武六朝,家傳世習,自易為工。而考之于史,唐之國學凡六,其五曰書學,置書學博士,學書日紙一幅,是以書為教也。又唐銓選擇人之法有四,其三曰書,楷法遒美者為中程,是以書取士也。以書為教仿于周,以書取士仿于漢,置書博士仿于晉,至專立書學,實自唐始,宜乎終唐之世,書家輩出矣。”②太宗本人一生鐘愛文學、書法,特別是書法,不僅擅作飛草,更以行書入碑,《晉祠銘》《溫泉銘》即是他留給后世的不朽銘刻,書法史上頗富盛名的《圣教序》,文字亦撰自其手。
要言之,王羲之書法不僅符合太宗本人的審美,更契合文化發(fā)展和精神統(tǒng)治的需要,其在初唐的流行實乃時局發(fā)展之必然。
李邕(678—747)善行書,工碑文。自幼天資聰穎,勤奮好學,翰墨文章,少已知名。他身處初唐和盛唐書風轉變的關節(jié)點,書法受“二王”及初唐歐、虞、褚等楷書大家影響,但其能不為所囿,以筋骨立形。他既能尊奉同朝先賢,參歐、虞、禇之瘦硬圓勁,唐太宗、孫過庭之豐潤飽滿;又能取法碑學,涉其雄壯與潑辣。筆圓形方,方圓互用,陰陽互藏,其書既有圓潤、中和、灑脫之韻味,又有陽剛、勁健、揚厲之美感。故何紹基在《東洲草堂金石跋》卷五稱:“北海書發(fā)源北朝,后以其干將莫邪之氣,決蕩而出,與歐、虞規(guī)矩山陰者殊派,而奄有徐會稽、張司直之勝。”③這一變化,今天看來似乎較為平常,但在當時卻殊為不易。初唐書壇,視王書為正宗,朝野書家一承舊習,須臾不離。藝術創(chuàng)作有別于一般的物質生產,不可模式化、標準化和集約化,作品應當追求才情、個性和獨創(chuàng)性,每個時代同樣也應該有屬于這一時代的審美特征,是謂“時運交移,質文代變”④。“二王”風靡之際,李邕潛沉潮底,潮涌之時,敢逆流而上、獨出機杼。“邕初學變右軍行法,頓挫起伏,既得其妙,復乃擺脫舊習,筆力一新,李陽冰謂之‘書中仙手’。”⑤他以行書為突破口,擺脫結字和美、用筆姿媚的“二王”書風,并將行書書體廣泛應用到刻碑勒銘的實際需要,探尋行書入碑之理,由此再反哺于書法。由碑頌探玄妙之意,自碑刻尋幽深之理,從而創(chuàng)變和豐富了自己的行書特征。具體而言,體現(xiàn)在三方面:一是專注以行書入碑,使行書之用途發(fā)生了社會普遍性的轉移;二是突破藩籬,改革行書筆法;三是強調個性結字之法,突出心性與結字體勢上內在關系的一致性,將書家個性與書法表現(xiàn)充分結合起來。
二
唐以前的碑文,多為隸書或楷書,不見行書。太宗以帝王身份首倡用行書寫碑,但并未形成氣候,畢竟行書更適合在手札、尺牘上書寫。另外,從藝術的社會功用及審美角度來說,行書于碑銘缺乏莊重嚴肅之感,入碑亦少厚重之美,與碑石之氣象殊難統(tǒng)一。
自李邕始,這種現(xiàn)象發(fā)生了明確改變。正如清人錢泳在《書學》中所說:“古來書碑者,在漢、魏必以隸書,在晉、宋、六朝必以真書,以行書而書碑者,始于唐太宗之《晉祠銘》,李北海繼之。”⑥或也可以說,李邕一生都在致力以行書入碑。在某種程度上,他的行書用筆和結字的突破,亦和入碑的要求密切相關。換言之,李邕行書創(chuàng)法的成功是從入碑的實際運用中悟來,是從實踐中產生又用于實踐的典型。自李邕后,效仿者漸多,行書入碑也漸漸普遍起來。“銘刻必正書之”發(fā)生變化,“至邕始變右軍行法,勁拙起伏,自矜其能,銘石悉以行狎書之,而后世多效尤矣”(鄭杓、劉有定《衍極并注》)⑦。李邕在碑刻上的傾心,亦與其文名有關聯(lián),他在撰文的同時勢必關注書寫創(chuàng)作。李邕文名獨步有唐四十年,《舊唐書》本傳即稱李邕早擅才名,尤長碑頌,《緯略》中據(jù)唐人所述確記李邕曾撰寫碑文達“八百首”之眾⑧,應是史上撰文碑頌數(shù)量最多的書家。李邕書文并茂,書藝出眾,文富情致,特別是他在嚴酷的現(xiàn)實中被壓抑的個性,通過書法痛快宣泄,彰顯出其過人智慧和眼界。故《朝野僉載》贊其“文章、書翰、正直、辭辨、義烈皆過人,時為六絕”⑨。
行書入碑,必須要加強用筆的力度和拙厚之美,同時結字亦要勁峭、篤定。李邕以撰碑頌、書碑刻知名天下,深厚的碑學基礎和帖學功底使其運筆不落窠臼,顯露縱勢、奔突、荒率之生機,昭示初唐以來少有的別樣藝術魅力(盡管,書法史上所謂“碑帖融合”是一個更晚近的概念)。在筆法上,李邕取北朝書家之長,吸納北方書體筋骨取勝的審美理念而融入行書入碑之實踐,加強用筆的力度、線質的篆籀氣、節(jié)奏的鏗鏘度,避虛就實而恣肆開張。據(jù)粗略統(tǒng)計,從開元元年(713)到開元二十七年間,他共完成碑刻20通、銘贊2品、書帖2部,書法風格個性突出,傳承脈落清晰。《葉有道碑》作于李邕括州刺史任上(717),三年之后在淄州刺史任上又創(chuàng)作了著名的《李思訓碑》,兩件早期書作結體俊逸,筆畫瘦硬,頓挫起伏,神采奕奕。不難看出《集王圣教序》之影響,王字筆意若隱若現(xiàn),但又絕非王體的復制臨摹,筆態(tài)自如,自成一格。作于唐開元十八年的《麓山寺碑》,筆法上不再單純注重用鋒的中、側,而強調以指腕運筆書寫,改變單純捻指,最大程度地豐富指腕的推、壓、抵、轉等動作,其行書之審美張力陡增。用筆上超越六朝王僧虔倡導的“心圓管直”(《筆意贊》)⑩,荒率而沉厚、攲側而端凝,追求虞世南所言之“粗而能銳,細而能壯”(《筆髓論·指意》)?的藝術境界。就審美而言,相較“二王”,李邕的字雖少了江南書家的含蓄與空靈,卻凸顯了蒼茫強勁,以其銘石之氣息彰顯書家人格之自信,也正暗合蓬勃向上之盛唐氣象。正所謂“氣體高異”,“一點一畫皆如拋磚落地”?,讓人不敢亦不能虛妄造次。故明董其昌贊其書法“李北海如象”?,清馮班稱“李北海如俊鷹”(《鈍吟書要》)?,包世臣則言“北海如熊肥而更捷”(《藝舟雙楫》)?。
欽州遵化縣尉任上(727),李邕又創(chuàng)作《端州石室記》,三年之后再作《岳麓寺碑》,至于特別值得贊賞的《法華寺碑》,則作于唐開元二十三年,其時李邕已年過半百。這些后期作品,表面氣息貌似小王,實則不同,雖為行書,用筆全系楷法,落筆嚴謹,運筆緩中帶急,一如太極,用筆老道,日臻化境。如石濤所評:“隨筆一落,隨意一發(fā),自成天蒙。處處通情,處處醒透,處處脫塵而生活。自脫天地牢籠之手,歸于自然矣。”?《云麾將軍李秀碑》立于唐天寶元年(742),李邕時年64歲,人書俱老的年歲仍不斷擺脫熟膩,追求“窮變態(tài)于毫端,合情調與紙上”?的高境。此碑用筆方圓并施,結體欹側奇崛,風流與法度兼具。《任令則碑》作于唐天寶四載,李邕已是67歲的老人,作字橫毫入紙,如逆水行舟,盡顯雄渾浩蕩的風采,即便是轉折,始終筆不離紙,在點畫內完成提按頓挫過程,筆調老辣至極。書法是韻律化的藝術,如張懷瓘所言乃“無聲之音”(《書議》)?。李邕碑刻運筆無論快慢疾徐、遲重凝澀,皆痛快淋漓、毫不遲滯,通篇韻律貫穿,彰顯書家獨特的藝術情感與審美追求。
李邕行書結字,拒絕固步自封,于峻峭中透倔傲之氣。其豎畫突破“弩不得直,直則無力”?的傳統(tǒng),挺直而渾厚有力;橫畫則杜絕水平走向,強調向右上倚側之異勢,將橫畫的傾斜做到極致且毫不回避。其結字之規(guī)并未遵循孫過庭《書譜》中所謂“初學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絕”?的遞進模式,而是突破“平正”直追“險絕”,加強布局中宮之丘壑,顯得方勁雄奇。他又憑借扎實的碑帖功底,脫離唐楷矩矱,結體、行氣、布局承繼北碑余緒,結字整體呈上松下緊,字形隨勢右傾,體勢拗峭平衡,伸展的筆勢極大地拓展了視覺空間。起筆方折,碑味十足,滌去妍美與輕佻,呈現(xiàn)李字特有的磅礴氣勢與開張氣象。典型若《李思訓碑》,此碑結字取勢頎長、奇宕流暢,骨力潛藏于風神,形于點畫。筆力遒勁舒展,秀逸縱橫,于妍麗中展現(xiàn)雄強。通篇布局則一反常態(tài),銳意新奇,左大右小,頭重腳輕,字形上寬下窄,呈現(xiàn)壓迫感,取勢險絕,夸張變形,氣韻生動。經(jīng)營某些字構時,突出主筆,以實現(xiàn)結構變形,將本應長方或正方的字,寫成左右伸展的橫扁狀,樸拙立顯,憨態(tài)可掬。誠如劉熙載所言:“李北海書以拗峭勝。”?
清人朱履貞評價“李北海筆畫遒麗,字形多寬闊不平……惟李北海行書,橫畫不平,斯蓋英邁超妙,不拘形體耳”(《書學捷要》)?。舉一綱而萬目張,李邕行書結字的這一特色,要在其活用筆法,只有領會此中要旨,筆法、結字方能互為彰顯。李邕雖初學右軍行法,既得其妙,復乃擺脫舊習,筆力一新。如果說王氏父子的行書“雄逸”,李邕行法則可稱“雄健”,他以行書入碑,遍學北朝書家的用筆,融會貫通,展現(xiàn)出一派荒率雄沉與桀驁不馴的書風。王羲之遒美俊逸的行書風格,被李邕以奇崛拗峭的藝術風格更新后,裹挾著碑書的剛正和力量,其氣節(jié)與骨力盡展盛唐氣象與精神風貌。以奇為正的造勢,使結字變得有韻致、有個性,而在書寫過程中又需把握好一個“度”。武術講求“長拳短打”之訣,視短為長,短中見長,移喻書法,就是筆短意長。李邕字形欹側得勢,然而并未過度,亦非虛張聲勢、怒容駭人、劍拔弩張。當然,李邕行書整體風格的凸顯,除用筆、結字而外,與其章法上的行間處理也不無聯(lián)系,通篇上下有承接,左右有呼應,筋脈相連,絕無刻意雕琢之痕,一氣貫注,神不外散,恰如園林藝術之“相地合宜,構園得體”?。
三
書品與人品的關系是傳統(tǒng)書論中的重要議題之一。在儒家思想影響下,論者通常認為書法的點畫之間蘊含著一種倫理色彩。漢代揚雄提出,“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雖然說的是文字(書),但強調它的書寫形態(tài)是書寫者內心道德的視覺表達。書品與人品之間的這種對應關系,從創(chuàng)作者角度來看,因為人的品性滲透在書寫活動中,所以創(chuàng)作活動與道德修養(yǎng)密不可分,高尚品德成為書法創(chuàng)作的必要前提。清代朱和羹在《臨池心解》中寫道:“書學不過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關頭。品高者,一點一畫,自有清剛雅正之氣;品下者,雖激昂頓挫,儼然可觀,而縱橫剛暴,未免流露楮外。故以道德、事功、文章、風節(jié)著者,代不乏人,論世者慕其人,益重其書。書人遂并不朽于千古。”?就觀者而言,他可以透過書法中的點畫、結構、章法等形式因素發(fā)現(xiàn)蘊含其中的書寫者的道德品質,進而獲得一種道德升華的教化作用。明代項穆在《書法雅言》中對這種功效做了非常細致的描述:“大要開卷之初,猶高人君子之遠來,遙而望之,標格威儀,清秀端偉,飄搖若神仙,魁梧如尊貴矣。及其入門,近而察之,氣體充和,容止雍穆,厚德若虛愚,威重如山岳矣。迨其在席,器宇恢乎有容,辭氣溢然傾聽。挫之不怒,惕之不驚,誘之不移,陵之不屈,道氣德輝,藹然服眾,令人鄙吝自消矣。”?要言之,在人品與書品的關系上,書品即人品。
在初唐楷書大家身上,人品與書品皆完美統(tǒng)一。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這些書家遵循儒家的道德規(guī)范,為人行事耿介端方,發(fā)之為書,端莊肅穆;另一方面也與楷書這種字體有關,形體方正,筆畫平直,可作楷模。唐太宗就稱譽虞世南為“博聞、德行、書翰、詞藻、忠直,一人而兼是五善”?。另一位楷書大家褚遂良,性格剛毅正直。在接受太宗托孤后,于永徽四年(653)升為尚書右仆射,執(zhí)掌朝政大權。永徽六年,唐高宗因王皇后沒有子嗣,遂有廢立之心。褚遂良與長孫無忌強烈反對這一舉動,并在高宗召集廷臣商議此事時以死直諫,最終左遷潭州。中唐以后,儒學復興,書品與人品統(tǒng)一的論調更趨普遍。縱觀書法史,如果書家僅有官方背景、特殊身份或書法技藝超群,但無獨立人格和思想,其人其書都是難以進入主流視野的,也很難得到主流評價體系的關注或認同,作品更難流傳有序。故蘇軾說“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茍非其人,雖工不貴也”?。李邕極富個性,能文善書,且一生為官,同時能以如椽筆墨“或寄以騁縱橫之志,或托以散郁結之懷”?,書法是其展現(xiàn)人格氣象的載體,其一生致力高潔人格和卓越書格的磨礪,嫉惡如仇,故不容于俗眾,屢遭貶斥。同時代的盧藏用稱“邕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
另一方面,李邕堪稱史上第一位賣文鬻字收入最多的作家,他早年家無厚積,《舊唐書·李邕傳》載:“邕早擅才名,尤長碑頌。雖貶職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齋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數(shù)百首,受納饋遺,亦至鉅萬,時議以為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這充分反映了其能文養(yǎng)士且重義愛士之情。李邕在括州刺史及淄、滑二州刺史任上,興利除害,留下很多佳話。他的才氣和率真讓當朝的許多名流俊士為之仰慕,更深得著名學者內史李嶠和監(jiān)察御史張廷珪的賞識,同向朝廷推薦,遂被詔為左拾遺(諫官)。當然,這樣的品性也會產生驕矜之情。詩人李白本身就是一位個性鮮明,不拘禮俗,喜歡放言高論,縱談王霸之名士。他在探望李邕時,李邕露出“頗自矜”?之色,李白對此甚是不滿,所以臨別時寫下《上李邕》詩,云“宣父猶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輕年少”?,語氣頗不客氣,以示“回敬”。此為雙方均頗具個性之一例。事實上,李邕慧眼獨具、辨才識能、胸襟寬闊,亦善于贏得晚輩與之交心。因此才有天寶四載歷下亭設宴雅集,與高適、杜甫、李之芳等縱飲暢談,說古論今。杜甫“海右此亭古,濟南名士多”?之佳句也因此流傳不朽。所有這些,都反映出李邕是十足的性情中人,而這和他的書風尤其是行書書風的創(chuàng)變、風格的形成緊密相關。
道無所不在,但不可執(zhí)而求之;法可執(zhí)而求,但得法未必得道。書法道技并重,尤需修養(yǎng)作保障,同時還要有敢為人先的魄力和勇氣,所謂“為將之明,不必披圖講法……為書之妙,不必憑文按本”?,欲與歷代書法大家并轡齊驅,拒絕拾人牙慧、步人后塵,李邕甚至敢向皇帝毛遂自薦,擁“相才”而遭斥“渾言”,更因性格剛直,嫉惡如仇,致使“邪佞切齒,諸儒側目”?。眾所周知,書法水平的高低,往往是書法家審美取向的集中反映,其所具有的藝術價值,蘊含著修養(yǎng)、技法、風格上的多重內涵,關聯(lián)著個體人格、態(tài)度和意趣的取向,可以說是綜合素養(yǎng)的體現(xiàn)。李邕雖為唐代書法較早的改革倡導者,更多專注于“囊括萬殊,裁成一相”?與“探文墨之妙有,索萬物之元精”?的藝術創(chuàng)作能力,但其忽視了許多影響個人成功的外在或“次要”因素,終歸官場失意,遭李林甫構陷而至身死,其成就亦被書史輕置。李白亦感嘆:“君不見李北海,英風豪氣今何在?”(《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在傳統(tǒng)社會中極具個性的書家似乎都有相似的命運,宋人蘇軾、黃庭堅莫不如此,唯有米芾裝瘋賣癲方可置身事外。然而,這恰恰又是李邕書法之所以獨具特色和成就非凡的關鍵。沒有高潔人品和倔傲的性格,沉雄峻峭的書風恐難形成,而這種由內而生的書風,自是他人不可及、不可學的。所以,李邕書法“人不敢以虛憍之意擬之”?,故意學其用筆,刻意仿其左低右昂的結字,終得單薄、輕佻之弊,粗野、“墨豬”之病,皆為心性不同使然。“李北海書以拗峭勝,而落落不涉作為,昧其解者,有意低昂,走入佻巧一路,此北海所謂:似我者俗,學我者死也!”?所謂“書如其人”,在李邕身上得到了最好詮釋。
四
在唐代書史及書論記述中,李邕之書名并不在顯赫之列。關于唐代書風的變遷與李邕之關聯(lián)、李邕在書法史上的地位,唐代史學家及書論中大多諱莫如深、不予置評。《述書賦》始撰于乾元初年(758),距李邕之卒僅十一年,其歷評秦漢至唐乾元年間書家,卻不見李邕之名。從《述書賦》注中所引時人之語可知,李邕其時并不為《述書賦》作者竇氏兄弟以書家身份相許?。事實上,李邕書法能夠自開戶牖,其藝術成就和人格魅力皆令時人和后輩傾心推戴且心悅誠服。杜甫有贊“聲華當健筆,灑落富清制”?,即足見其對李邕之推重。惜杜甫并不以書法見長,其說在書壇自是難以產生如同文壇般的影響力。直至唐末,《續(xù)書評》中方見李邕之名。而李邕書名與大家并列,始于五代亞棲《論書》。直至元、明之際,李邕書名才日益顯著并為論者所重。作為在創(chuàng)新實踐上有獨特建樹且能啟一時代之風范的書法大家,聲名享譽可謂姍姍來遲。
時間終還歷史以公正。宋人歐陽修在《試筆》中稱李邕“以書自名,必有深趣”?,其后的蘇軾、米芾等名家也開始關注并研習李邕之法,其行書的藝術價值遂逐漸獲得認同。《宣和書譜》亦贊“邕精于翰墨,行草之名尤著”?。元代趙孟頫更是為李邕筆力所傾倒,“每作大書,一意以擬之矣”?。明代楊士奇評曰:“北海書矩度森嚴,筋骨雄健,沉著飛動,引筆有千鈞之力,故可寶也。”?清代以至晚近,李邕聲譽漸高,臨習取法者日眾。王文治以詩贊曰:“唐代何人紹晉風,括州象比右軍龍。《云麾》墓道殘碑在,萬本臨摹意未慵。”?這是對李邕在書法史上的杰出貢獻的高度肯定。
唐代尚法,嚴格意義上是針對盛唐楷書而言的。盛唐楷書法度謹嚴、氣魄雄偉,在一定程度上充分表現(xiàn)出唐朝鼎盛時期國力富強的大國氣象和勇于開疆拓土的進取精神,昭示恢弘氣度和闊大境界。從創(chuàng)新的角度,顯然這種變革在書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但是,法的一致性會導致書風的雷同或近似,千人一面是可悲的,更會成為書法藝術發(fā)展的桎梏。所以,唐楷既有時代進步的因素,也有自身帶來的消極影響。可以說,“法度”既充分體現(xiàn)著盛唐氣象,隨著時間的推移又逐步使其消解。從創(chuàng)造性的角度而言,楷書、草書、行書在唐代都體現(xiàn)出了藝術創(chuàng)造的本質,但楷書、草書是最為突出、最為廣泛的,能充分體現(xiàn)出時代特性,行書則相對弱化,李邕、顏真卿是其中的突出代表。正因如此,李邕在行書上的創(chuàng)造,更顯珍貴。他以一流書家的敏銳性和藝術創(chuàng)新意識敢率先而為,從大千世界汲取生命和運動形式之美,化作自己的筆墨語言。觀李邕行書,喜勁健者可從中賞其金石趣味,好婉約者可從中品其柔美風致,尚玄思者可從中會其人格之美。以有法之字抒無羈之心,鏗鏘的線條和倔傲的體勢寄托生命的律動和性靈的絕俗。李邕以自己的方式詮釋著“字如其人”“風格即人”的藝術主張。張丑亦云:“北海太守李邕,始變右軍行法,其頓挫起伏,奕奕動人。”?
李邕的行書融入篆籀之法,將折釵股和屋漏痕等自然之意運用在行書的書寫過程中,突破了王羲之手札書法俊美之規(guī)范,并將鐘王攲側取勢向前推進一步,增添峭拔、奇崛之美。同時,李邕書法暗合盛唐奮發(fā)向上的浪漫主義情調,踐行書法“抒情達性”的藝術理念,他在行書中找到了表現(xiàn)自我精神氣質、性靈內涵和理想指歸的恰當形態(tài)。唯有沖破藩籬、展示個性,富有理想的書法家才不至于被時代埋沒。李邕的貢獻便在于把書法抒情表意的藝術特性,通過用筆和結字之變,在“行書”上得以具象化,并在碑刻實踐中得以推廣。更重要的,是其通過自己的努力,在已有的王羲之行書書風之外,建起另一種倔傲而沉雄的個性審美新范式。
余 論
書法風貌與其時的人文思想和社會環(huán)境緊密相聯(lián)。李邕生活在開元天寶年間,整個唐代社會充滿勵精圖治和昂揚向上的精神力量,此時的盛唐,以其大氣磅礴的胸襟兼容異質風采,南亞的佛學、醫(yī)學、音樂、美術,西亞的教派、建筑藝術,西域的藝人和東鄰的僧侶,咸聚長安,大唐的首善之區(qū)遂成為聞名遐邇的世界級大都會。無論外在形貌還是內在精神,整個社會也都在追求與時代同步的脈搏。李白的詩歌、張旭的草書、吳道子的繪畫、裴旻的劍舞都代表了大唐盛世在藝術上達到的高峰,象征著盛唐的活力與自信。
盛唐書法崇尚雄健有力、豁達雍容。初唐流行的妍美書體和瘦勁書風已與時代潮流顯得格格不入,唐玄宗書法喜好又與太宗相左,此時的李邕,在“二王”之外,融碑銘法帖于一身,不修飾、不做作,以氣勢縱逸、奔突的用筆和奇崛跌宕的結構,創(chuàng)造出震撼心靈的筆墨形式,使觀者在藝術欣賞中產生共鳴,心靈得到凈化。書法創(chuàng)作本就應該體現(xiàn)出人性的覺醒、精神的升華,這是藝術的終極力量,也是藝術的魅力所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對李邕書法尤需加以重視,值得深入探究。李邕順應盛唐改革、向上、創(chuàng)造的時代精神召喚,適應書法審美形態(tài)的流變趨勢,自覺舉起創(chuàng)變之大旗,樹起迥異于姿媚的審美標桿,同時將個人氣節(jié)、操守、德行等熔鑄于書法文化之中,其在唐代書法第二次創(chuàng)變過程中居功至偉,對后世影響亦極其深遠。在唐代書法發(fā)展走向上,李邕事實上擔當?shù)氖且粋€“撥轉者”的重要角色。
從宏觀歷史背景看,唐代文化高峰的出現(xiàn),開元天寶年間文化的發(fā)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通變中樞作用。沈曾植曾言:“開元文盛,百家皆有跨晉、宋追兩漢之思。經(jīng)大歷、貞元、元和,而唐之為唐也,六藝九流,遂成滿一代之大業(yè)……人才之盛關運會,亦不可不謂玄宗之精神志氣所鼓舞也。貞元、元和之再盛,不過成就開、天未竟之業(yè)。自后經(jīng)晚唐以及宋初,并可謂元和緒胤。至元祐而后復睹開、天之盛,詩與書其最顯著者已。”(《開天文盛》)?
書法與詩歌一樣,作為李唐最具代表性的文藝樣式,之所以澤被后世,皆源于變。《周易·系辭下》云“變通者,趣時者也”。質而言之,變是發(fā)展之本。就書法而言,既有技法層面之變,也有章法形式之變。在書家輩出的唐代,李邕能廁身書史,就在于他敢于求變。即突破“二王”之法,擺脫舊習,自成一家。尤其是他說“似我者欲俗,學我者死”,不讓世人止于模仿自己,自己更不會停步在模仿之途,以此,才可以說他是“撥轉者”,引領了盛唐、晚唐乃至宋以后的書壇走向,對后世書法沿革及書法史構建的意義自然無法被忽視。換言之,李邕的革新精神是其書法成功至關重要的一環(huán),他無論以行入碑,使行書之用途發(fā)生轉移,還是突破藩籬,改革行書筆法,以及將書家個性與書法表現(xiàn)充分結合起來,無不處處活躍著一種革新的因子。李邕歷仕武后、中宗、玄宗三朝,因嫉惡如仇致仕途坎坷,但這并沒有阻礙他對書法的不懈追求,反而更使其生命富有韌勁,不斷鉆研,終成一代書法巨擘。
尤須指出的是,李邕對書法的追求與其人品的剛正底色密不可分,所謂“書者,如也。如其學,如其才,如其志。總之曰如其人而已”。書家若僅僅注重書品,窮其一生也不過是一個書匠,相反,若人品與書品均追求高標峻尚的風范境界,方可為垂范之大家。李邕之書正是其人格氣象的載體,書品與人品的完美結合在他的書法創(chuàng)作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xiàn)。反觀今日書壇,亂象叢生,其源便在書寫者缺乏一種正氣與品格。在這個意義上,李邕在書法上的求變追新以及致力于高潔人格和卓越書格的磨礪,對書壇后輩無疑具有指導意義。這也是筆者作此文章的初衷所在。
① 欒保群編《書論匯要》,故宮出版社2014年版,第98頁。
② 馬宗霍輯《書林藻鑒》,文物出版社2015年版,第77頁。
③ 何紹基撰、汪政點校《東洲草堂金石跋》,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3年版,第109頁。
④ 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671頁。
⑤? 王群栗點校《宣和書譜》,上海書畫出版社1984年版,第83頁,第83頁。
⑥⑦⑩????????上海書畫出版社、華東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室選編校點《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2014年版,第626頁,第457頁,第62頁,第111頁,第550頁,第550頁,第655頁,第146頁,第129頁,第603頁,第311頁。
⑧ 高似孫:《緯略》,中華書局1985年版。
⑨ 張鷟:《朝野僉載》,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87頁。
? 石濤:《苦瓜和尚畫語錄》,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39頁。
? 孫過庭著、陳碩評注《書譜》,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4年版,第80頁。
? 張懷瓘:《玉堂禁經(jīng)·用筆法》,《歷代書法論文選》,第219頁。
? 計成著、陳植注釋、楊伯超校訂、陳從周校閱《園冶注釋》,中國建筑工業(yè)出版社1988年版,第56頁。
? 汪榮寶撰、陳仲夫點校《法言義疏》,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160頁。
? 朱和羹:《臨池心解》,《叢書集成續(xù)編》第86冊,上海書店1994年版,第204—205頁。
? 項穆著、趙熙淳評注《書法雅言》,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4年版,第196—197頁。
? 劉饣束撰、程毅中點校《隋唐嘉話》,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6頁。
? 蘇軾撰、白石點校《東坡題跋》,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年版,第162—163頁。
?? 張懷瓘:《書議》,《歷代書法論文選》,第148頁,第148頁。
?? 《新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5757頁,第5756頁。
?? 《舊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5043頁,第5043頁。
?? 瞿蛻園、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661頁,第1146頁。
?? 仇兆鰲注《杜詩詳注》,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216頁,第1394頁。
? 張懷瓘:《評書藥石論》,《歷代書法論文選》,第232頁。
? 張懷瓘:《文字論》,《歷代書法論文選》,第210頁。
? 朱關田:《中國書法史·隋唐五代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99頁。
? 孫承澤撰,白云波、古玉清點校《庚子消夏記》卷六,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年版,第141頁。
? 楊士奇撰《東里續(xù)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第1238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639頁。
? 劉奕:《王文治詩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725頁。
? 張丑:《清河書畫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80頁。
? 沈曾植撰、錢仲聯(lián)輯《海日樓札叢》,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7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