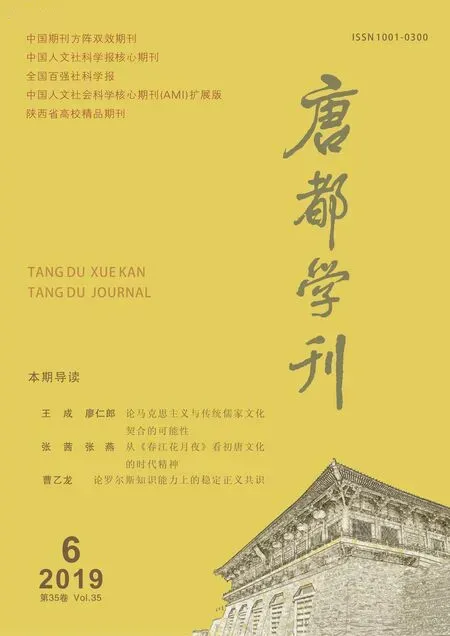文化地理學視野下的大秦嶺研究芻議
陳桂權
(四川文理學院 巴文化研究院,四川 達州 635000)
山脈作為國家的地理標識與民族的象征有著重要意義。我國山脈眾多,它們對于民族與國家文化的形成均發揮過重要作用。在我國的山脈中,位于版圖腹地、作為南北分界線的秦嶺山脈,又有著特殊的地位與意義。秦嶺之于中國有著重要的地標意義與文化價值,在中華文明的形成與演進過程中,大秦嶺地域的諸因素都曾以各自形式參與其中。源于秦嶺地域的秦人建立了強大統一的秦國,開創了一套治國制度,漢代秉承秦制續寫輝煌。以秦嶺為分界線,北有關中平原,南有漢中盆地以及成都平原,這些地區以其發達的水利、富庶的農業條件,作為基本經濟區,對國家穩定與經濟繁榮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也正是因為大秦嶺位于其中,對于南北兩側所形成的不同自然氣候起著基礎性的作用,進而又造就了多樣的人文文化。可以說,大秦嶺地區是一個在自然與人文方面極具典型性與代表性的地域。這一地域有多元的文化、不同的自然風光,其兼具南北方文化的特點,也發揮了溝通南北的橋梁作用。
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在視察陜西時的講話中,將大秦嶺定位到“中華地理的精神標識和自然標識”的新高度,其充分體現了以大秦嶺為載體,凝練中國精神、提升中華文明國際形象的新要求。應該說,這是我國對大秦嶺山脈對于中華文明重要性的再次肯定,體現了山脈之于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文化的重要意義。圍繞著“大秦嶺作為中華地理精神標識與自然標識”這一主題定位,學術界可以從生態地位、文化特色、經濟發展、旅游產業開發、山水文化產業、循環經濟等不同角度,進行經濟學、人類學、社會學、文化學、地理學、歷史學等多學科的綜合研究,以深入系統地探討“大秦嶺地區”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問題。文化地理學是地理學、文化學及文化人類學的結合。大秦嶺地區有著多元的自然以及人文文化特色,故本文擬從文化地理學的視角,嘗試探討對大秦嶺地區的研究理路與主要內容,不周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一、大秦嶺概念的界定
在上古地理學看來,中國大陸的所有山脈均屬于昆侖山系,故在《山海經》《禹貢》兩部古地理學著作中,秦嶺與昆侖山均被稱為“昆侖”。春秋戰國時期,在《詩經》與《左傳》中又以“南山”“終南山”來稱呼秦嶺,其意為秦國都城之南的山脈。這是具有鮮明地理標識意義的定義。西漢史學家司馬遷在《史記》中首次將此山命名為“秦嶺”并稱其為“天下之大阻也”。對于秦嶺起止的地域范圍,向有廣義和狹義兩種劃分。漢代辛氏所撰《三秦記》中就說道:“秦嶺東起商洛,西盡汧隴,東西八百里,嶺根水北流入渭,號為八百秦川。”北魏崔鴻《西京記》繼承了《三秦記》對于狹義上秦嶺概念的定義,并指出其作為雍州、梁州分界線的地理意義。《西京記》稱:“長安正南山,名秦嶺,東起商洛,西盡汧隴,東西八百里是也。關中指此為南山,漢中指此為北山,斯實雍、梁之大限矣。”[1]卷9我國古代地理區劃標準通常遵循“山川形便”與“犬牙交錯”的原則,《禹貢》九州的劃分就是采用了“山川形便”的分區準則。《西京記》中稱秦嶺為“雍、梁之大限”,其意為秦嶺是雍州與梁州的分界限。也就是說,狹義的秦嶺僅指陜西省境內的中南部分,位于北緯32°40′~34°35′,東經105°30′~110°05′,東西長400~500千米,南北寬150~200千米,平均海拔2 000米左右,主峰太白峰,海拔3 767.2米,是我國大陸青藏高原以東最高峰[2]。廣義的秦嶺地域范圍更廣,它西起甘肅南部西漢水與黑虎溝的分水嶺,東止河南伏牛山,北臨渭河,南瀕漢江,東西約占八個經度,(東經104°30′~112°52′),南北約占兩個緯度(北緯32°20′~34°45′)[3]。秦嶺是長江、黃河兩大水系的主要分水嶺。大秦嶺的地域范圍即指廣義上的秦嶺概念。根據秦嶺古洋盆的演化發展和夷平作用地層的分布,大秦嶺的真實地理范圍是由秦嶺、巴山、神農架、桐柏山和大別山構成的巨大山系,其所涉行政區劃包括河南、湖北、重慶、四川、陜西、甘肅五省一市,涵蓋30多個地市和100多個區縣。
二、大秦嶺文化意義的闡釋
秦嶺地處中國腹地中心,從地理劃分上看,具有南北分界線的意義。不僅如此,在文化方面,大秦嶺地域對于中華文化也有著重要的象征意義。以秦嶺為界限,其北是傳統意義上的北方,其南則是南方地域范疇。中國地域劃分中的“南北”象征著兩種不同的文化意象,如“南稻北麥”“南船北馬”“南人食米、北人食面”,等等。歷史上,北方地區作為中原王朝的統治中心,開發較早,當南方還處于“火耕水耨”的原始農業階段時,北方農業已相當發達,關中平原被稱為“天府之國”。不過,北方地形以平川為主,從地緣政治看,其一直處于少數民族政權的包圍之中,故而抵御少數民族騎兵的南犯,是統治者們做軍事布局的重要內容。戰國時期,長城的修建,秦始皇派大將蒙恬北戍,以抵御匈奴,再到漢武帝與匈奴的多次戰爭。多數的對抗中,漢民族取得了勝利,但是,中原王朝也有失敗的時候,這就是東晉的“衣冠南渡”,唐代的“安史之亂”,宋代的“康王南渡”。政治中心的南移,隨之一同發生的是三次經濟重心的南移。在這影響中國歷史發展的三次歷史大事件中,大秦嶺地區作為橫亙在南北之間的重要屏障,對于保護南方政權起到相當大的作用。從這一層面看,秦嶺之于中華文明延續的重要作用更加凸顯。
西安位于大秦嶺北部地區,是我國古代重要的政治中心,自周、秦、漢、唐等13個王朝在此建都。西安之所以成為我國古代建都最多、定都時間最久的城市,與“南山”,也就是秦嶺所起的巨大屏障及資源供給作用密切相關。西漢初年,在定都洛陽與西安的選擇中,朝中大臣的意見分為兩派,高祖劉邦最終采納尚書婁敬的建議,定都長安。婁敬的主張就全面地分析了定都關中長安的優勢,他說:“都關中上……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專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4]卷55清代地理學家華湛恩在《天下形勢考》中基本上完全繼承了婁敬的這一說法(1)華湛恩《天下形勢考》,選自王錫祺《小方壺輿地叢鈔》,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都長安,為建瓴之勢,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有也”;“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這是政治家從軍事地理、政治地理的角度闡述關中長安作為首都的地理優勢。這樣先天的地理優勢,當然與南面的秦嶺有著密切的關系。不僅如此,秦嶺還是關中地區主要的水源涵養地,其北翼塑造了涇河、渭河,北部山麓又發源了六條河流,即灞河、浐河、灃水、滈水、潏水和澇水,這些河流在環繞長安后匯入渭河。《三秦記》所言“嶺根水北流入渭”[5],就是指的這六條河流。它們與涇水、渭水一同構成了“八水繞長安”的形勝,同時也塑造、滋養著關中平原。因為這些河流發源于秦嶺山區,其攜帶了寶貴的腐殖質土壤,這些泥土就成為發展農業得天獨厚的條件。漢代時,有民謠“涇水一石,其泥數斗”,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可見國都之南的秦嶺對于關中地區的滋養。山區除了是水源涵養地之外,還是重要的資源富集地。秦嶺地區豐富的自然資源使得它成為長安的后花園,是修建皇家園林與行宮別院的首選之地。歷代宮殿有阿房宮、山林苑、鳳凰宮、仙游宮、太和宮等,這正如唐代詩人祖詠在《蘇氏別業》中所描寫的那樣:“南山當戶牗,灃水映園林”。
秦嶺是我國南北、東西文化的匯聚地和融合區,其中本土的道、儒和外來的佛教、基督教的祖庭均產生于此,在中華文化中具有重要的文化象征意義。“華夏文明”是中華文明的代稱,《尚書·武成》中有“華夏蠻貊”之說。章太炎曾說古代漢族稱華或夏與華山、夏水有密切關系。在遠古時期,先民對大秦嶺山系統稱為“華山”。傳說上古時期,陜西藍田的“華胥國”曾在大秦嶺地域創造過燦爛的文明。其女首領華胥氏“治國有方,民無嗜欲,自然而已,是為盛世樂土”。以至于讓人文始祖軒轅帝羨慕不已,便有了“黃帝夢游華胥之國,而后天下大治”的典故。現在的秦嶺山系中還保留許多帶有“華”字的山名,如“華山”“少華山”“翠華山”等等。而夏水故道則是從湖北沙市東出,流經監利縣北部,折東北至沔陽縣治附近如漢水,自此以下稱夏水。也就是說,夏水其上源為漢水,而漢水發源于陜西省寧強縣蟠冢山,自西向東流入湖北后在武漢注入長江。《尚書·禹貢》記“嶓冢導漾,東流為漢”。清《嘉慶一統志·漢中府·山川》:“漢水,在寧羌州北,源出嶓冢山。東流經沔縣南,又東經褒城縣南,又東經府治南鄭縣南……東南流入興安府石泉縣界。”嶓冢山亦屬于大秦嶺地域范疇。故代稱中華文明的“華夏”一詞,其文化基因中與大秦嶺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從對外交經濟文化交流來看,西安是絲綢之路東段上的重要節點,古代絲路上的許多國家,均以“秦”代稱中國。這當與秦人在絲綢之路上發揮的重要作用有直接關系,也是秦帝國曾經輝煌的體現。學界對于中國英文名China的來源也存在諸多說法,其一派觀點就認為它來源于秦(chin),對此問題雖無定論,其也可說明以大秦嶺地域為中心所形成的文化對于中國的影響之大。黃河為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那么秦嶺堪當中華民族的“父親山”。秦嶺經過的甘肅隴南山區、關中平原和川西北、鄂西、豫西秦嶺山區,是秦人最初的家園和最早建立基業的地方。
《史記》中稱秦嶺為“天下之大阻也”。說明當全國一統后,秦嶺這座橫亙在中國內陸腹地的群山險隘對南北交通的阻礙。這是由自然地理條件所決定的,古往今來一直如此,這種體現“秦嶺為天下之大阻”的觀點在文人詩詞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如韓愈《左遷藍關示侄孫湘》中有“云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元稹《酬樂天書懷見寄》也說:“秦嶺高崔嵬,商山好顏色。”帶有傳奇色彩的唐代女詩人薛濤在《別李郎中》說:“花落梧桐鳳別凰,想登秦嶺更凄涼。”可見秦嶺之險于南北交通之阻礙。因為這種阻礙,無論是軍事進攻、經濟文化交流均受到影響。故開山修路成為溝通南北必做的事情。至今流傳于巴蜀地區的“五丁力士”故事,講的就是蜀道最早的開發。學術研究中的蜀道是指秦漢時期連接關中與成都平原,穿越秦嶺大巴山的川陜道路的統稱,起點在陜西西安,終點止于四川成都。蜀道以漢中盆地為中間站,分為南北兩段:北段以西安、寶雞等城市為起點,越秦嶺抵達漢中,從西向東主要有陳倉道、褒斜道、儻駱道、子午道;南端從漢中始,向南翻越大巴山、米倉山,最終到達成都等地,其中西為金牛道、中為米倉道、東為荔枝道,構成“北四南三”的蜀道交通網絡,并且聯結著難以計數的分支道路[6]。正是因為有秦嶺之阻隔,才有蜀道之交通。故在文化上,秦嶺與蜀道成為秦巴文化中的重要意象。唐代,由長安入蜀之人都要走蜀道、過秦嶺,其中的文人遷客們留下大量詩句,如白居易《送武曹歸蜀》:“月宜秦嶺宿,春好蜀江行。”許渾《送鄭寂上人南行》:“錫寒秦嶺月,杯急楚江風。”正是因為這些詩歌對秦嶺的描述,增加了其文化內涵與人文魅力。
另外,大秦嶺地區悠久的開發利用史,還使它積淀了厚重的歷史文化遺存,這些人文景觀與山地自然景觀,交相呼應、和諧融洽、相得益彰。大秦嶺地區的人文景觀有太白山拔仙臺、封神臺、黑虎關等古建筑;公王嶺和陳家窩藍田猿人遺址;樓觀臺國家森林公園的老子講學處、西岳華山的老君犁溝、劈山救母、韓愈投書、華山道教場、南五臺佛教圣地、姜子牙釣魚臺、千年古剎草堂寺、驪山烽火臺、華清池、兵諫亭等豐富的人文資源。這些都是秦嶺悠久厚重的歷史文化內涵的體現。
三、文化地理學視野下的大秦嶺研究
文化地理學的研究旨在探討各地區人類社會的文化定型活動,人們對景觀的開發利用和影響,人類文化在改變生活環境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該地區區域特性的文化繼承性,也就是研究人類文化活動的空間變化。它是人文地理學的重要分支,也是文化學的一個組成部分[7]。進一步劃分文化地理學的內容,其主要包括五個核心主題,即文化生態學、文化源地、文化傳播、文化景觀、文化區[8]。正如錢俊希、朱竑所說:“這一理論框架結合了人地關系、景觀研究、空間分析等人文地理學的研究傳統,傾向于將文化理解為具象化的物。”[9]運用這一研究范式,大秦嶺地區的文化地理學研究可從以下四個方面入手:
(一)文化源地研究
首先,大秦嶺地區是秦文化的源地。《史記》中說:“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制會盟,夷狄遇之。”其實,秦國的先祖是居住在漢民族與西戎之間的嬴姓部族。西周中葉,其祖非子為周孝王養馬,因其養馬有功,受封為西周附庸。后又因秦襄公救周有功,平王封他為諸侯,始與列國通使聘享[10]。公元前763年,秦襄公之子秦文公把秦人都城從西漢水上游的西陲,遷往寶雞境內鳳翔縣長青鎮。這一舉措邁出了秦人挺進關中、覬覦中原的關鍵性一步。之后,秦人重視農業,獎勵耕戰,通過變法迅速實現富強,為后來一統中國奠定了基礎。秦人的興起與占領秦嶺地區并將其作為后方根據地有密切的關系。因此,秦嶺無疑是秦文化的源地,研究秦文化有必要在大秦嶺地域范圍內展開。
其次,秦嶺也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發源地之一,研究中華傳統文化亦離不開對大秦嶺地區的觀照。地處秦嶺山水之間的西周王朝的周文王、周公旦,將數千年以來古人探索天人關系的成果予以凝練,從而形成論述天人關系經典理論——“天人合一”。這是中華傳統文化精神的最高價值追求,這種觀念最核心的承載體就是《周易》,其最高境界是“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此外,影響中國政治數千年之久的“禮制”,也是地處秦嶺山水之間的周公所制定。他不但從政治制度上構建了宗法秩序,而且從行為規范方面制定了嚴格的禮儀,成為中國古代政治重要的價值信念。另外,中國古代文化最重要的觀念是“和而不同”。在集儒、釋、道于一體的秦嶺,“和而不同”的文化表現得最為充分。在儒家文化發展演變中,秦嶺曾經起到過重要作用。西漢武帝在太學“置五經博士”;東漢經學家馬融少時在秦嶺師從著名學者摯恂研習儒家文化,后在此大辦私學;著名經學大師鄭玄也是通過在這里的學習奠定了其在儒學史上的地位。宋代大思想家張載所開創的關中學派也發源于秦嶺。秦嶺又是道教的重要發源和興盛之地,秦嶺還是中國佛教的重要“搖籃”之一,秦嶺中段的終南山則為中國佛教傳播的重要策源地和最早譯經重地之一。因處于絲綢之路的起點,自佛教初傳之時,即在終南山有所傳播。四大譯經家之首的鳩摩羅什則在此創立第一個國立譯經場,集四方英杰,開創中國佛教翻譯事業的新局面。史傳所載,在終南山弘法的高僧不計其數,其中不乏眾多開宗創派之祖師。更為重要的是,秦嶺還是中國佛教宗派創立、發展與活動之地,中國漢傳佛教八大宗派中,僅秦嶺及關中就集聚了六大宗派之祖庭。集儒、釋、道于一體的秦嶺,可謂是中華傳統文化的大熔爐[11]。
再次,大秦嶺地區也是巴文化的源地之一。在秦嶺南麓與巴蜀相接,歷史上這里曾經是巴人活動的中心之一。關于巴人起源,有一說就認為其起源于陜南地區,后不斷遷移,最后到達秦巴山區南部。殷周至漢,庸、濮、賨、蜑等各部族巴人生活在秦巴山區。巴人不但參加了武王滅商的戰爭,也參與了漢王朝的建立。在周秦時期,秦巴地區的文化已與周秦文化相融合,史載周公、王子朝及孔子奔巴楚之地,王子朝將檔案、文獻典籍,甚至樂工帶到南方秦巴地區,這些都促進了南北文化的進一步交流與融合。
綜上,大秦嶺地區既是秦文化的源地也與巴文化相關,同時這里也造就了中國傳統文化。故而,在本區之內就文化源地的研究工作,還有許多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文化傳播與文化源地是密不可分的兩個部分。開展文化源地研究,自然少不了關注文化傳播的內容,因此本文將文化傳播與文化源地研究合二為一。
(二)文化景觀研究
秦嶺地區特殊的自然地理位置與地質構造,形成了頗具特色的山地自然景觀。秦嶺北坡有著名的“七十二峪”,其主峰太白峰有保存完整的第四紀冰川遺跡,冰川湖、石海、槽谷、冰斗、冰階等冰蝕地貌、冰磧地貌、冰緣地貌等冰川景觀[12]。同時,秦嶺還有河流、瀑布、湖泊、溫泉等水域景觀類型,以及諸如華山日出、太白晴雪、驪山晚照、高山云海等氣象景觀;生物景觀有原始森林主要是針葉闊混交林與落葉闊葉林帶,野生動物有大熊貓、金絲猴、羚羊、云豹、羚牛、豪豬等。在人文景觀方面,大秦嶺地區也有較多的歷史文化遺存,前文已述。關中地區豐富悠久的歷史文化資源,自不待言了。楚漢爭霸中劉邦“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在此,鑿通西域的外交家、旅行家張騫的故地在秦嶺南麓城固縣的博望村。諸葛亮為克服中原,五次北伐,最終敗于五丈原,抵御蜀軍進攻的曹魏多少利用了為天下大阻的秦嶺。京劇經典劇目《失空斬》中的歷史原型,失街亭、空城計、揮淚斬馬謖,這些事都發生在秦嶺地域之內。可以說,大秦嶺見證了朝代的興亡、王侯的成敗,留下了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可供研究開發。在秦嶺山區還存留著大量的鄉土聚落,對它們的研究也是開發大秦嶺文化的重要內容之一。
(三)文化區研究
大秦嶺地區地處多種文化的交匯地帶,本身蘊含著豐富多元的文化。“其聲音山南近蜀則如蜀,山北近秦則如秦”[13],這正是對秦嶺地區多元文化環境的真實寫照。大秦嶺地區既有中原文化、秦文化、也有荊楚遺風,還有巴蜀文化。其北麓是典型的三秦文化,南麓是巴蜀文化,東部臨荊楚文化,西北又有隴南文化。總之,大秦嶺地區有著多元的文化區。在本區開展各文化區的專題研究,并在其基礎上進行各文化區的交流研究,將是一項十分有意義的課題。
(四)大秦嶺地區的文化生態學研究
文化生態學是指利用生態學的基本理念從人、自然、社會、文化等各種變量的交互作用中研究文化產生、發展的規律,用以尋求不同民族文化發展的特殊形貌和模式。在文化生態學看來,文化不是經濟活動的直接產物,它們之間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復雜變量。山脈、河流、海洋等自然條件的影響,不同民族的居住地、環境、先前的社會觀念、現實生活中流行的新觀念,以及社會、社區的特殊發展趨勢,等等,都給文化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特殊的、獨一無二的場合和情境。借鑒文化生態學的基本理念與觀點,我們可以分析大秦嶺地區的不同文化以及形成這些文化的因素。正如前文所論,大秦嶺地區地處南北過渡地帶,其自然環境復雜多樣,其人文各具特色,這些基本因素都為其產生不同的文化提供了條件,加之這里地處南北交通要道,文化交流頻繁,開放與保守兼具。可以說大秦嶺地區是運用文化生態學展開文化研究的典型地區。運用文化生態學,可以將上述文化源、文化區以及文化景觀研究統屬起來,綜合體現文化地理學的特色。
綜上所述,無論從地理標識,還是從人文區域劃分,大秦嶺地區均有其典型性。對于我國,秦嶺山脈及大秦嶺地區是民族文化的象征,因此,以大秦嶺為對象進行自然遺產、文化遺產的申報,這不僅僅是對秦嶺之于中華文化重要性的認可,也體現了山脈等地理生態系統對于人類文明的價值。圍繞這個主題,可以進行多方面、多角度的研究。本文僅從方法論上做了一個宏觀的闡述,若涉及具體問題的研究,學界不乏好的成果問世。結合新時代區域協同發展的契機,我們應在充分整合已有研究的基礎之上,再進一步完善研究的薄弱環節,對大秦嶺地區展開綜合研究,為大秦嶺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提供理論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