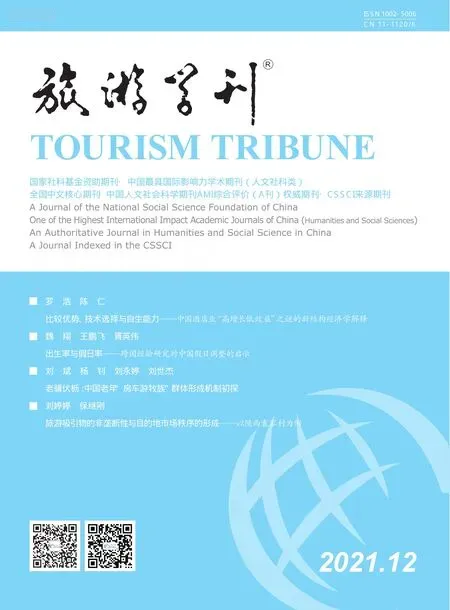親緣-產業二元網絡對內生型鄉村旅游小企業成長的影響
李秋成,張環宙
(1.浙江工商大學旅游與城鄉規劃學院,浙江杭州310018;2.浙江外國語學院國際經濟與旅游管理學院,浙江杭州310012)
引言
2017年10月,黨中央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明確了新時期“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的三農工作方向。近年來,旅游業在推動農村社會經濟發展轉型方面顯現了突出的功效,成為各級政府推進鄉村振興的重要抓手[1-2]。活躍、創新的市場主體是鄉村旅游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力量,尤其是根植于本地社區,由本地農民創業和經營的“內生型”旅游小企業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鄉村旅游業的區域競爭力,以及旅游業在推動鄉村社會經濟持續發展方面的綜合效應[3-5]。因此,對內生型鄉村旅游小企業成長規律及其培育路徑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以往有關內生型旅游小企業成長的研究大多沿襲一般企業理論范式,即將企業的成長視為收入、利潤、規模等量化指標的增長[3]。在研究導向上,已有研究大多關注這類企業對農村居民生計、社區增權等層面的積極影響。較少有研究將鄉村旅游小企業視作競爭性的市場主體,從“家庭作坊”向“企業實體”演進的視角探究這類企業成長演化的內在規律與動力機制。2018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海南考察時指出“鄉村振興關鍵是產業要振興”。可見,產業興旺是鄉村振興的關鍵依托,而兼具地域文化特色和市場競爭力的內生型旅游小企業則是鄉村旅游業持續興旺的基石。因此,不僅“量”的增長以及社區生計是鄉村旅游研究的要點,競爭和創新導向下內生型旅游小企業“組織屬性”的演變更是以旅游業推進鄉村振興的關鍵[6-8]。
基于此,本文依托小企業成長理論,從家庭作坊(family mode of production)向企業實體(enterprise mode of production)演進的視角解析內生型鄉村旅游小企業的成長邏輯,從家庭-企業空間分離、人員分離、目標分離3個層面對這一演變過程進行度量。基于社會網絡嵌入理論,本文進一步聚焦創業農民親緣-產業二元網絡,系統分析農民創業活動嵌入的兩種不同性質的社會網絡對旅游小企業成長的差異性影響,構建了內生型鄉村旅游小企業“網絡嵌入-企業成長”的理論模型,并以實證研究對這一模型進行了檢驗。本文為理解內生型鄉村旅游小企業的成長演進提供了一個新穎的視角,對地方政府和相關部門孵化、培育這類企業的管理實踐亦具參考價值,因此,文章在理論和實踐層面均具有一定的意義。
1 文獻回顧與假設推演
1.1 內生型鄉村旅游小企業研究概述
內生型鄉村旅游小企業是根植于鄉村社區,利用開放空間、優美環境、鄉村生產生活設施為游客提供休閑游憩體驗的小型、微型企業[3,8]。在國外研究中,這類企業涵蓋鄉村旅館(village inn)、寄宿家庭(home stay)、寄宿農場(farm stay)、接待農場(accommodation-based farm)等多種形態[9-10]。在我國,這類企業主要包括農家樂、牧家樂、漁家樂、鄉村民宿等形式[6,8]。規模小、非正式、依賴家庭是內生型鄉村旅游小企業的主要特點,尤其是其“家庭+企業”的雙重屬性受到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5,11]。縱觀已有研究,學者們主要從社會經濟效應、企業經營與績效、企業創業與發展等方面對內生型鄉村旅游小企業進行了探討。
內生型鄉村旅游小企業的社會經濟效應體現在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在微觀層面,其效應主要表現在促進農民家庭脫貧和致富方面。與外來資本和創業移民不同,內生型旅游小企業根植于本地社區,能夠保證本地家庭直接從旅游發展中受益,避免了旅游業收益“漏損”的問題[12-13]。另外,一些學者發現內生型鄉村旅游小企業的發展對提升農民本地文化認同具有重要功效[4]。在宏觀層面,其主要效應體現在對區域旅游產業競爭力和持續發展能力的顯著價值[6,14]。Lerner 和Haber 指出,相較于外來企業,內生型旅游小企業的產品和服務能夠更好地融入本土民俗、環境、生產生活場景等元素,這對旅游產業區域特色和市場競爭力的構建具有重要意義[15]。
在企業經營與績效方面,已有研究指出,作為一種“企業”,內生型鄉村旅游小企業經營發展的最大障礙在于其普遍存在的“非增長導向”,即經營者普遍關注家庭和個人生活,缺少追求企業經營創新和持續發展的動力[3,16]。此外,規模小、抗風險和創新能力弱也被認為是這類企業經營發展的主要短板。因此,集群發展、產業合作網絡構建對內生型鄉村旅游小企業的經營發展具有重要價值[13,17]。值得注意的是,如何衡量內生型鄉村旅游小企業的經營績效是以往研究中的難點。Lerner 和Haber、Ye等學者均指出,除了銷量、營業額、利潤等客觀財務指標外,經營者主觀感知績效(例如經營滿意度、創業幸福感)對企業的持續經營和發展往往具有更重要的影響[6,15]。
在內生型鄉村旅游小企業的創業與發展方面,一些學者注意到這類企業的創業動機具有顯著的特殊性。例如,Wang 等發現,鄉村旅游小企業創業者的初始動機主要是為了提高家庭生活質量、維系特定生活方式,而不像其他行業創業者那樣追求業務擴張和利潤增長[10]。創業動機的特殊性也導致這類企業在成長路徑上與一般企業差異顯著。Morrison 等發現這類企業大多增長緩慢,一些創業者為了享受和維持某種生活狀態甚至主動遏制業務的增長[16]。另一些學者將創業管理的理論框架應用到鄉村旅游小企業情景,對驅動本地農民旅游創業的關鍵因素進行了探究,這方面的一個重要趨勢是社會網絡和社會資本對農民旅游創業決策的影響日益受到關注[18-19]。
1.2 從家庭作坊到企業實體:鄉村旅游小企業的成長邏輯
以往關于企業成長的研究主要存在兩種理論觀點。一部分學者將成長視為企業規模的持續擴張,傾向于從“量”的層面衡量企業成長。相關指標包括投入性指標(如投資額)、價值性指標(如股票價格、資產總量)、產出性指標(如銷售額、利潤率)等[6,20]。另一部分學者則強調企業成長不僅指“量”的增長,還涉及組織屬性的變遷,即企業在組織形式、資產結構、運營模式方面的演化[3,6]。尤其在鄉村小微企業研究領域,對企業組織屬性演變的探究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創業活動的規律。在這方面,Lynch 和MacWhannell 等學者提出的旅游小企業成長理論提供了一個代表性視角[21-24]。
Lynch 和MacWhannell 的研究主要針對基于家庭設施和功能創業的旅游小企業(即內生型旅游小企業),他們將這類企業的初始狀態稱為“家庭作坊(family mood of production)”[23]。家庭在這一階段扮演著核心角色。家庭生活空間與企業經營空間相互重疊;家庭成員與企業員工身份相互重疊;家庭生活的維持與改善是企業經營的首要目標。在這種模式下,經營者往往缺乏進取心,很少有產品創新和企業發展的系統規劃[22]。隨著業務的發展,鄉村旅游小企業將經歷一個家庭要素逐漸與企業要素剝離的過程,家庭作坊逐漸向企業實體(enterprise mood of production)演進[24]。企業實體的主要特征是專業化與市場化。在極端狀態下,企業是與家庭完全分離的獨立主體,其勞動力為市場雇員,競爭力和盈利性是其經營的核心目標,住宿和娛樂體驗是市場需求導向下的“商品化”結果[3]。因此,從組織屬性和經營邏輯的演變來看,內生型鄉村旅游小企業的成長可視為從家庭作坊向企業實體的變遷,任何一個小企業均處于這一變遷軌跡中的某個節點。
Ye等學者進一步指出,鄉村旅游小企業成長演變實際上是家庭消費功能與企業生產功能的逐漸剝離[3,6]。在極端家庭作坊情境下,鄉村旅游小企業在空間利用、勞動力身份、目標導向等層面均以家庭“消費訴求”為核心;而在極端企業實體情境下,上述層面則均以追求利潤、競爭效率等“生產訴求”為導向。基于Lynch和MacWhannell提出的框架以及Ye等學者的分析,本文從家庭-企業空間分離、人員分離、目標分離3 個層面解構內生型鄉村旅游小企業從家庭作坊向企業實體的演變。其中,空間分離指設施空間在家用與客用之間的分離;人員分離指勞動力身份在家人與雇員之間的分離;目標分離指經營目標在生活導向與增長導向之間的分離(圖1)。

圖1 鄉村旅游小企業成長的邏輯圖示Fig.1 Growth logic of rural small tourism business
1.3 親緣-產業二元網絡與鄉村旅游小企業成長
關于哪些因素對企業成長具有關鍵影響,以往研究從創業者個人特質的微觀層面、社會網絡的中觀層面、市場和政策環境的宏觀層面進行了探討。其中,社會網絡視角因其有助于理解資源獲取和企業成長的動態過程而受到學者的廣泛關注[26]。社會網絡嵌入理論(social network embeddedness)因此成為研究創業與企業成長的重要框架[27]。本文將鄉村旅游小企業的成長界定為從家庭作坊向企業實體的演變,因此,從親緣-產業二元網絡嵌入的視角進一步探討鄉村旅游小企業成長的動力機制便為應有之義。
農家樂、民宿等鄉村旅游小企業的生成和發展“嵌入”在家庭、產業兩種網絡系統之中[20]。在鄉村相對封閉和落后的環境下,家人親戚組成的“親緣網絡”是農民旅游創業和經營所需資源的首要來源[28]。其次,旅游經營涉及與供應商、旅行社、金融機構、競爭者、主管部門、行業協會等主體的互動,形成“產業網絡”。這一網絡為企業的成長提供了另一條資源導管[29]。已有研究發現,親緣網絡和產業網絡對創業企業經營收入和規模的增長均有積極影響[29-30],但兩種網絡對鄉村旅游小企業從家庭作坊向企業實體演變的影響尚未有研究涉及。下文進一步分析親緣、產業網絡對鄉村旅游小企業成長的影響機理。
1.3.1 親緣網絡對鄉村旅游小企業成長的影響
家人和親戚構成的親緣網絡對農民創業和企業成長具有重要價值。Arregle等的研究發現,親緣網絡中的信息、資產和情感支持對激發農民創業、實現優良績效具有推動作用[30]。Davis 等指出親緣關系具有互信、互惠的“強連帶”特點,相較于主要由“弱連帶”構成的商業關系網,親緣網絡能夠提供質量更高的信息和建議,以較低成本提供資金、場地、設備等資源支持,因而對企業業務和規模的擴大具有推動作用[31]。
然而,親緣網絡雖然有利于業務的增長,卻未必有利于企業組織屬性的演進[32]。家族集體利益往往是親緣網絡支持的基本出發點。這意味著接受家人親戚支持的創業者需將家族的利益和期望融入創業活動。因此,如果創業者主要依賴家庭和親族的支持,作為一種“回饋”,家庭(族)利益和目標則可能凌駕于商業目標之上,成為經營過程中的優先考量,這將阻礙家庭要素與企業要素的剝離[33]。此外,親緣網絡提供的創業和經營資源大多是“冗余”(redundant)的家庭內部資源,嵌入在農民親緣網絡中的資源即使是多樣化的也難以在質上有根本突破[18]。例如,家人親戚提供的資產、場地、設施往往來自提供者自己的家庭;家人親戚提供的人力支持往往是親自出力幫忙;而情感鼓勵更可能是缺乏專業知識和客觀信息基礎上的“盲目支持”[30,34]。因此,在各種資源都具有深深“家庭印跡”的制約下,鄉村旅游小企業從家庭作坊向企業實體的演進可能受到阻礙。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下列假設:
H1:親緣網絡對家庭-企業空間分離具有負向影響
H2:親緣網絡對家庭-企業人員分離具有負向影響
H3:親緣網絡對家庭-企業目標分離具有負向影響
1.3.2 產業網絡對鄉村旅游小企業成長的影響
鄉村旅游小企業的經營涉及與供應商、分銷商、金融機構等產業環境主體的合作與互動。旅游管理部門、行業協會等組織也在企業經營過程中扮演管理、咨詢、服務等角色。這些與企業經營相關的外部個人和組織構成了農民創業者的產業網絡[35]。由商業關系主導的這種網絡為鄉村旅游小企業發展和成長資源的獲取提供了重要渠道。以往研究證實,產業網絡的資源共享與知識溢出效應能夠為企業的快速成長提供助力[36]。
與內聚性的親緣網絡不同,產業網絡主要由“弱連帶”構成[37-38]。產業網絡中的資源多樣性更強、異質性更高。尤其是源自產業網絡的信息、資產和心理支持等資源與經營者家庭無關,具有市場化的顯著特點。Arregle等指出,源自產業網絡的市場化資源能夠為小企業的規范化發展提供推動效應[30]。具體而言,借由產業網絡,創業農民能夠獲取更多同行信息和市場需求信息,這將激發創業者進一步發展企業、促進業務增長的進取心;旅游行業協會、產業管理部門提供的行業信息和經營培訓有助于企業經營者以更寬廣、更專業的視角看待自己的生意;來自產業網絡成員的建議和情感支持往往基于對企業經營現狀和行業前景的專業見解,相較于家人親戚的盲目支持,對企業的生存與發展更具價值[39-40]。因此,本文推測產業網絡對鄉村旅游小企業從家庭作坊向企業實體的演變具有促進效應,提出下列假設:
H4:產業網絡對家庭-企業空間分離具有正向影響
H5:產業網絡對家庭-企業人員分離具有正向影響
H6:產業網絡對家庭-企業目標分離具有正向影響
1.4 研究模型的構建
社會網絡是一個多維概念,Collins 和Clark、尹苗苗和蔡莉從網絡規模、網絡成員親密度、網絡資源異質性3個層面對個人或者企業的社會網絡進行了解構[41-42],受到后續研究的廣泛借鑒。基于此,本文從網絡規模、網絡強度、網絡異質性3個維度度量農民創業者的親緣網絡、產業網絡,并分別檢驗兩種社會網絡3 個維度對鄉村旅游小企業空間分離、人員分離、目標分離的驅動效應,系統分析親緣-產業二元網絡對鄉村旅游小企業成長的差異化影響。本研究的概念模型如圖2所示。
2 研究方法
2.1 數據來源與樣本概況
本文選取浙江省長興縣顧渚村、臨安市白沙村、浦江縣虞宅鄉進行問卷數據的收集。上述地區為浙江省內鄉村旅游發展的高地,民宿、農家樂等內生型旅游小企業快速成長且形成集聚發展的格局。問卷調研于2017年8月進行,由6 位研究助理協助完成。由于調研問卷內容較多,調研對象的接觸和溝通難度較大,本研究采用“便利抽樣”(convenient sampling)的方法進行問卷的發放和收集。為提高研究對象的參與度和數據收集質量,調研過程采取以下兩點策略:由當地村干部帶隊入戶,面對面進行訪談和問卷調研;贈送受訪者啤酒、洗衣粉等小禮品作為參加調研的酬謝。調研過程共計調查300 戶鄉村旅游小企業(顧渚、白沙、虞宅各100 戶),刪除填答不全和明顯隨意填答的24 份問卷,最終獲得有效問卷276份(回收率92%)。

圖2 研究概念模型Fig.2 Conceptual model of the study
276 家小企業樣本經營年限平均為6.33年,雇員人數均值為4 人(旺季),平均床位數量為30 個。大多數企業的經營設施較為多樣,囊括了棋牌室(92.4%)、卡拉OK(88.0%)、茶室(68.5%)、農事體驗(32.2%)、小酒吧(19.2%)等多種設施和項目。受訪業主男性較多,占比66.3%;年齡位于45~54歲的創業者比例最多,占比為37%;65.6%的業主受教育程度為初中及以下,具有大專及以上學歷的不足5.1%,說明鄉村旅游小企業創業者的文化程度普遍較低。
2.2 問卷設計與變量測量
問卷由研究概況、旅游小企業及業主基本信息、測量量表3部分組成。基于Lynch、葉順等的研究,本文采用5 個問項度量創業者家庭使用旅游小企業廚房、餐廳、客房、院子、娛樂配套等空間/設施的頻率,以測量家庭-企業空間分離(Likert 5 點法,1=使用頻繁~5=完全不使用);用員工中非親屬人員占比度量家庭-企業人員分離;使用2 個問項“經營農家樂/民宿是為了賺取更多利潤”“經營農家樂/民宿是為了家庭生活質量(反向問項)”度量家庭-企業目標分離(Likert 5 點法,1=完全不同意~5=完全同意)[22,24]。
如前文所述,本文采用網絡規模、網絡強度、網絡異質性3個維度度量農民創業者的親緣網絡和產業網絡。借鑒莊晉財等和劉暢等使用的量表,使用3個問項分別度量親緣網絡的網絡規模、網絡強度、網絡異質性;使用9 個問項度量產業網絡的網絡規模(問項1~3)、網絡強度(問項4~6)、網絡異質性(問項 7~9)[26,35]。上述問項均使用 Likert 5 點法由受訪者自評(1=完全不同意~5=完全同意)。主要量表的測量問項如表1所示。
2.3 數據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層次回歸(hierarchical regression)方法對研究假設進行檢驗。具體上,將度量鄉村旅游小企業成長的3 個指標(空間分離、人員分離、目標分離)分別設為因變量,以親緣網絡、產業網絡的3個維度(網絡規模、網絡強度、網絡異質性)為自變量,依次對鄉村旅游小企業成長的3 個指標進行回歸分析,全面考察親緣-產業二元網絡對企業成長的影響。此外,基于以往研究,本文將創業農民的文化程度(教育年限)、管理經歷(創業前是否做過管理工作)、企業年齡、企業規模(雇員數量)作為控制變量納入回歸分析。統計分析使用AMOS 22.0和SPSS 22.0軟件完成。

表1 驗證性因子分析結果Tab.1 Results of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3 數據結果分析
3.1 信度與效度檢驗
首先檢定測量量表的基本質量。本文采用驗證性因子分析對潛變量量表進行聚合效度分析,并結合Cronbach’sα信度系數、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CR)、平均方法萃取值(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等指標對量表的信度進行考察。驗證性因子分析的結果如表1所示。
分析結果顯示,本文4 個潛變量量表問項的標準化因子負荷均在p<0.01水平上顯著,具有較好的聚合效度。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數均大于0.7,顯示信度良好。組合效度分析結果顯示4個潛變量的CR值均大于0.7的一般要求,平均方差萃取值分析結果顯示除“空間分離”外,其余潛變量的AVE值均大于0.5的一般要求。測量模型擬合指標如下:χ2/df=2.524,RMSEA=0.074,GFI=0.885,CFI=0.931,TLI=0.913,IFI=0.931,PCFI=0.740,PGFI=0.634。綜合來看,本研究的測量工具具有較好的信度和效度。
3.2 回歸分析結果
在信度和效度檢驗的基礎上,本文使用層次回歸方法對提出的研究假設進行定量檢驗。回歸分析對潛變量做如下賦值處理:空間分離、目標分離按問項均值賦值;親緣網絡的3 個問項得分分別作為親緣網絡規模、網絡強度、網絡異質性的賦值;產業網絡測量問項1~3 均值作為產業網絡規模賦值,問項4~6 均值作為網絡強度賦值,問項7~9 均值作為網絡異質性賦值。層次回歸的結果如表2所示。
3.3 假設檢驗
3.3.1 親緣網絡對鄉村旅游小企業成長影響效應檢驗
基于親緣網絡三維度對鄉村旅游小企業成長(空間分離、人員分離、目標分離)的回歸結果(表2),本部分對H1~H3進行檢驗。
H1提出親緣網絡對鄉村旅游小企業家庭-企業空間分離具有負向影響。本文通過模型2對這一假設進行檢驗。回歸結果顯示,親緣網絡三維度中網絡規模對空間分離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β=-0.171,p<0.05),網絡異質性對空間分離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負向影響(β=-0.176,p<0.1),親緣網絡強度對空間分離則沒有顯著的影響。整體來看,H1得到數據的部分支持。

表2 層次回歸分析結果Tab.2 Results of hierarchical regressions
H2提出親緣網絡對鄉村旅游小企業家庭-企業人員分離具有負向影響。本文通過模型5對這一假設進行檢驗。回歸結果顯示,親緣網絡三維度中“網絡規模”對人員分離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β=-0.155,p<0.05),親緣網絡強度、網絡異質性對人員分離均未顯示出顯著影響。因此,H2得到數據的部分支持。
H3提出親緣網絡對鄉村旅游小企業家庭-企業目標分離具有負向影響。我們通過回歸模型8檢驗這一假設。分析結果顯示,親緣“網絡規模”(β=-0.261,p<0.01)、網絡強度(β=-0.174,p<0.05)對目標分離均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親緣網絡異質性對目標分離的影響效應則不顯著。因此,H3也得到數據的部分支持。
3.3.2 產業網絡對鄉村旅游小企業成長影響效應檢驗
與上部分類似,本部分通過回歸分析系統考察創業農民嵌入的產業網絡對鄉村旅游小企業成長的影響,對H4~H6進行檢驗。
H4提出產業網絡對鄉村旅游小企業家庭-企業空間分離具有正向影響。本文通過模型3對此假設進行檢驗。回歸結果顯示,產業網絡三維度中的網絡規模對空間分離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0.157,p<0.05),網絡強度、網絡異質性未表現出對空間分離具有顯著影響。因此,H4得到數據的部分支持。
H5提出產業網絡對鄉村旅游小企業家庭-企業人員分離具有正向影響。本文通過模型6檢驗這一假設。回歸結果顯示,產業網絡三維度中的“網絡強度”對人員分離顯現出顯著的正向影響(β=0.234,p<0.05),網絡規模、網絡異質性對人員分離均沒有顯著的影響效應。因此,H5 得到數據的部分支持。
H6提出產業網絡對鄉村旅游小企業家庭-企業目標分離具有正向影響。本文通過模型9檢驗這一假設。回歸分析的結果顯示,產業網絡的網絡規模對目標分離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0.203,p<0.05),產業網絡強度對目標分離也顯現出一定的正向影響(β=0.209,p<0.1),產業網絡異質性對目標分離的影響則不顯著。綜合來看,H6也得到了數據的部分支持。
4 結論與討論
4.1 主要結論
本文從家庭-企業空間分離、人員分離、目標分離3個層面對內生型鄉村旅游小企業從家庭作坊向企業實體演進的過程進行了解構,并探討了親緣-產業二元網絡要素對這一成長過程的影響機理。針對浙江省276戶鄉村旅游小企業樣本的實證研究基本驗證了本文提出的假設。圖3總結了研究的主要發現。整體來看,本文的結論可以總結為以下兩點:

圖3 主要研究發現Fig.3 Summary of research findings
第一,親緣網絡對內生型鄉村旅游小企業從家庭作坊向企業實體的演進具有一定的阻礙效應。研究顯示,雖然親緣網絡在經營建議、資金支持、情感鼓勵方面具有重要價值,但來自親緣關系網的支持往往具有強烈的“家文化”色彩[28]。源于對家人親戚支持的回應,創業農民在經營中也將難以突破“家文化”的窠臼。如實證研究的結果所呈現的,親緣網絡要素對空間分離、人員分離、目標分離或多或少均有負向影響,說明這一網絡整體上對內生型鄉村旅游小企業從家庭作坊向企業實體的演進具有一定的阻礙性。
第二,產業網絡對內生型鄉村旅游小企業從家庭作坊向企業實體的演進具有一定的促進效應。與上下游企業、行業管理和服務部門的互動所形成的產業網絡對內生型鄉村旅游小企業的成長發展具有重要價值。產業網絡提供的專業化、市場化的信息和資源有助于農民獲得有關現代企業經營的認知、結識更多的同行、拓展經營信息和資源的獲取空間。這些都有助于旅游小企業逐步脫離家庭作坊模式,從經營意識和經營策略上更加趨向于企業實體。研究結果證實,產業網絡要素對空間分離、人員分離、目標分離呈現的顯著影響皆為正向,因而在家庭作坊向企業實體的演進中主要起到促進的作用。
4.2 管理啟示與建議
本文的研究為地方政府和產業管理部門培育、管理內生型鄉村旅游小企業的發展提供了一些啟示:
第一,從市場主體持續競爭力的視角來看,地方政府和行業管理部門應當適度鼓勵民宿、農家樂等旅游小企業在經營資源和信息獲取方面擺脫對創業者家族網絡的過度依賴,通過行業培訓、規劃干預等措施引導這些企業在空間功能、人員角色、導向目標上與家庭要素適度分離,培育其“企業屬性”。
第二,地方政府和管理部門應通過鄉村旅游“產業網絡平臺”的構建,協助農民在企業經營過程中構建更多、更廣泛的產業網絡。例如,成立多方參與的鄉村旅游創業協會,加強鄉村旅游產業供應鏈的組織和管理;構建旅游創業專項融資平臺,拓寬農民旅游創業資金的信貸渠道;定期組織相關組織和專家向農民創業者介紹旅游產業政策和市場發展趨勢。上述措施將有助于增強鄉村旅游小企業的“企業屬性”,提升競爭力。
第三,地方政府和產業管理部門需要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地應用親緣-產業網絡對鄉村旅游小企業成長的差異影響。例如,對于以原真民俗文化為核心資源的旅游地,限制家庭要素與企業要素的過度分離可能更有益于構建小企業競爭力;而對于以自然風光為核心吸引的旅游地,促進家庭要素與企業要素的分離更有利于體驗產品創新和技術創新,有助于構建區域旅游小企業的持續競爭力。
4.3 研究不足與展望
本文在研究深度和研究設計方面還存在一定局限,也為后續研究提供了可行的方向:
首先,本文僅對內生型鄉村旅游小企業從家庭作坊向企業實體成長的路徑及其關鍵影響要素進行了探討。對于“什么是鄉村旅游小企業家庭-企業要素分離的最優狀態”,本文并未觸及。事實上,家庭與企業的過度重疊往往導致企業缺乏在產品、營銷、技術等方面創新的能力與動力[16,20],家庭與企業的過度分離也可能導致民俗文化的過度舞臺化、商業化而有損于游客體驗[3,6]。兩者均不利于企業競爭力構建。未來研究需將“績效”納入研究范疇,探索鄉村旅游地在不同資源依托和發展階段下,家庭-企業分離度與經營績效、創業幸福感、旅游滿意度等績效變量之間的理論關系。
其次,囿于有限的研究能力和條件,本文僅從創業農民主觀感知的視角對親緣網絡、產業網絡各維度進行了測量,這可能使實證研究結論的精確性和普適性具有一定局限。后續研究可以通過對親緣、產業網絡要素的客觀性度量,進一步驗證、比較兩種網絡對鄉村旅游小企業成長演進的影響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