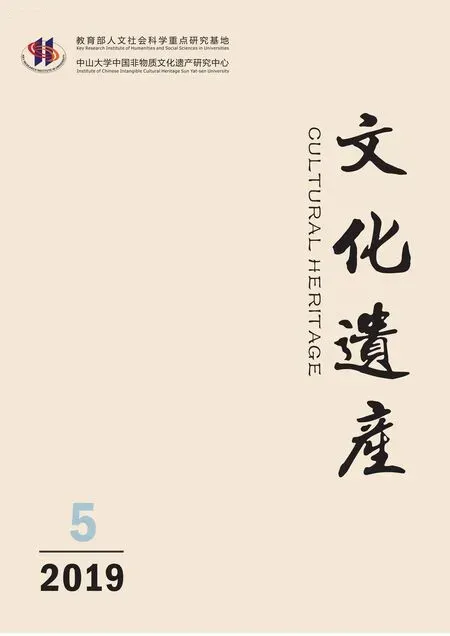“玉”禮器:原編碼中國
——《周禮》六器說的大傳統新求證
葉舒憲
根據文學人類學派新提出的文化大小傳統劃分和四重證據的研究方法,先于漢字而傳承的華夏文化大傳統的存在,是以神圣玉禮器為主要的信仰和神話觀念之原編碼方式的。甲骨文及其以后的漢字書寫,乃是華夏文明的文化再編碼。如何通過對文化原編碼的再認識和再發現,重新審視漢字記錄下的小傳統再編碼,成為一個全新的學術求證和探索方向。(1)楊驪、葉舒憲編著:《四重證據法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84-91頁。
一、《周禮》“六器”說的推陳出新
自古生產的各種玉禮器,每一種都是華夏文明所特有的神圣性意義的編碼方式,本文以其象征意義的解碼式闡釋(2)筆者對玉玦、玉璜神話內涵的解讀,詳見《中華文明探源的神話學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第230-235;對玉璧、玉人、玉柄形器、玉龍、玉戈、玉兔等神話內涵的解讀,詳見《玉石神話信仰與華夏精神》,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109-247頁。為基礎,排比新的考古發掘資料,說明古人在何時何地將玉禮器的生產和使用加以體系化建構,其演變過程又是怎樣的。過去的玉學研究盲目尊崇《周禮》的相關學說,將其“六器”說奉為上古時期華夏國家用玉制度的標配說明。如今,我們終于得以借助大量周代出土玉器實物的情況,來做出重新權衡判斷,認為《周禮》并不能真切反映西周時代的用玉制度,而是有很大偏差。“六器”說肯定不是西周以來的原生態的玉禮器組合,而是在秦漢時代重“六”的文化偏好背景下,派生出來的玉禮器體系觀。
以下我們將《周禮》“六器”說視為在文獻史學的時代里真假難辨的陳舊說法,目的就是要與時俱進和推陳出新,依據新出土的玉禮器實物情況,作為第四重證據,據此能重建出新的六器體系說(見彩圖1)。這也將是以實物證據糾正文獻記錄之誤的一個很好案例。
《周禮》所記舊的六器說,內容專指六種上古時期最基本的華夏早期文明國家級玉禮器組合:琮、璧、圭、璋、璜、琥。六種玉禮器的使用模式是,分別用來祭祀天地和四方,即以六器對應宇宙的六合空間——東、南、西、北、上、下。除了器形的對應之外,《周禮·春官·大宗伯》還同時強調六器在六種顏色上的對應: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3)賈公彥等:《周禮注疏》,阮元編《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762頁。
至于為什么用這六種玉器來分別祭祀天地四方,漢儒鄭玄的注釋給出標準版解答:“禮神者必象其類:璧圜象天;琮八方象地;圭鋭象春物初生;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琥猛象秋嚴;半璧曰璜,象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從鄭玄注釋看,六器的制作原理遵循著神話思維的類比原則:即用象征對應的方式,將不同的玉器制作為天地和四方四季的對等符號。圓形的玉璧是天的符號;方形的玉琮是地的符號;玉圭是東方和春天的符號;玉璋是南方和夏天的符號;玉琥是西方和秋天的符號;玉璜是北方和冬天的符號。漢儒鄭玄在這里所做的,是出于純粹想當然的推理,還是有所根據呢?就以玉琮在約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中起源的情形看,最初的琮脫胎于方形鐲子,原是戴在人手腕上的。根本不會有什么“八方象地”的意思。如此看來,鄭玄顯然沒有調研的功夫和實際根據。不要說鄭玄的時代,就是春秋時期最為好古和博學的孔圣人,也只說“夏禮吾能言之”。至于比夏朝更早的古代禮制情況呢,孔子也沒說他知道,那顯然是他不知道了。玉琮始于五千年前,若不清楚先夏之玉禮淵源情況,又何能稱“吾能言之”?
好在20世紀的考古大發現,提供了認識古禮源流的大傳統新視野,讓我們對先夏之禮,也終于可以說出“吾能言之”的自信話語。
早在千年之前的北宋時期,大文豪蘇軾就在《洗玉池銘》提出如下見解:“秦漢以還,龜玉道熄,六器僅存,五瑞莫輯。”蘇東坡所說的“龜玉道熄”,指的是以龜和玉代表神靈的深遠傳統被迫終結了,神圣禮器淪落為被后人玩賞的寶物而留存下來。玉禮器原來承載的代表天命和神意之符號功能都逐漸失傳,被人遺忘掉。蘇軾的這個判斷,具有高屋建瓴的歷史洞察力。不熟知本土的遠古玉文化奧秘,就無法做出此種判斷。他以秦漢大一統國家的出現為時代界限,認為“六器”和“五瑞”所代表的神圣大傳統終于到此而截止,后人唯有欣賞這些徒有其表的圣物外觀,卻弄不明白其所蘊含著的早期信仰和神話觀念。
如今,我們比蘇軾更有利的歷史認知條件,要拜近百年來的中國考古學之賜。若把考察的目光轉移到商周時代以前,分別審視六器在史前文化中的萌生和流傳情況,就能夠大致明確:文化大傳統的玉禮成分,哪些在向小傳統的演進過程中保留下來(有原樣保留的;也有變樣保留的),哪些玉器又被剔除淘汰,未能流傳后世。
《周禮》舊“六器”說的大傳統淵源和流傳一覽
1.玉璧:紅山文化(北狄),崧澤文化和良渚文化(南蠻),大汶口文化(東夷),龍山文化和齊家文化(西戎),陶寺文化。
2.玉琮:薛家港文化、良渚文化(南蠻),齊家文化(西戎),陶寺文化。
3.玉圭:陶寺文化,龍山文化,二里頭文化。
4.玉璜:興隆洼文化、紅山文化(北狄)、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凌家灘文化(南蠻),大溪文化(巴蜀),良渚文化(南蠻),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和齊家文化(西戎)。
5.玉璋:大汶口和龍山文化(東夷),越南、香港(南蠻),龍山文化(石峁)和齊家文化(西戎),三星堆(古蜀)、金沙(古蜀)
6. 玉琥:凌家灘文化虎形璜,石家河文化玉虎頭,西周玉琥。(《左傳·昭公三二年》:“賜子家子雙琥。”孔穎達疏:“蓋刻玉為虎形也。”)
在舊的“六器”體系中,玉琥一項,基本不能構成具有普遍性的玉禮器標配模式中的一種成分,應該是戰國秦漢時期的作者根據猜想而后加進西周禮器體系中的。即使玉琥在史前的凌家灘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中都有星星點點的原型呈現,但畢竟不能構成完整而確鑿的玉禮器傳承鏈條。
有關不同玉禮器的用途,唐人段成式《酉陽雜俎·禮異》說:“古者安平用璧,興事用圭,成功用璋。”這是說三種不同的玉禮器有不同的功用。參照彩圖1所示璧琮組合發源時的良渚文化墓葬,可知唐代人的猜測沒有實物的根據。班固《白虎通·文質》則說:“璋之為言明也。賞罰之道,使臣之禮,當章明也。”這是用諧音原理來解釋玉璋的隱喻意義。其實玉璋的使用情況并不理想(見彩圖2),在夏代滅亡之后,中原國家的禮制基本不用,只發現有零星的殘余而已(見彩圖3)。在班固所處的漢代,早就不再生產和使用玉璋了。他的說法也只能是反映著后人的推測之辭。 至于玉璜的用途,除了禮書中的各種解釋以外,漢代文豪張衡還做出一種音樂學的解釋。其《思玄賦》云:“昭彩藻與琱琭兮,璜聲遠而彌長。”從考古發現材料看,在六器之中,玉璜的出現無疑最早也最普遍。難道是玉璜所發出的美妙聲音,讓初民以為是天神的聲音?蘇軾《峻靈王廟碑》也有個說法:“古者王室及大諸侯國,皆有寶,周有琬琰大玉,魯有夏后氏之璜,皆所以守其社稷,鎮撫其人民也。”借用神圣玉禮器鎮守社稷和人民,其實也就相當于讓神明監護人世的生活。這就相當于解說了所有玉禮器的生產初衷和通用功能。由于甲骨學家在甲骨文“龍”字與“虹”字之間發現相似性,遂解讀出古人對彩虹這種自然現象的神話化想象結果:神龍介于天地之間的形象與玉璜為天橋的形象,就這樣重疊合一了(見彩圖4)(4)葉舒憲:《玉石神話信仰與華夏精神》,第172-193頁。。
再從天垂象的意義去思考,彩虹架設在天和地之間,東亞史前先民似乎從中看到溝通天地的神圣生物使者——龍的出現。他們還會聯想:在沒有彩虹的時候,龍又去哪里了呢?所謂龍能“潛淵”又能“升天”的想象,就這樣產生出來。若用更加實在的符號物來表示天地中介者龍的存在,就有了華夏史前文化中玉璜的普遍生產。神話想象的生物龍,和被神話化的物質——玉石,就這樣早早地在大傳統中結下不解之緣。筆者為2015年出版的《圖說中華文明發生史》特意設計一張封面圖,用考古發現的湖北荊州熊家冢出土的一件神龍載人升天的變體玉璜,來凸顯虹橋虹龍一類想象催生的玉雕藝術表現(見彩圖5)。
當我們完全依照神話學的原理解讀出玉璜等禮器的底牌意義時,再去看《周禮》所云六器禮四方天地六合的功能,就明顯意識到:如此嚴整的祭祀玉禮系統,真會讓人感到天衣無縫一般的合理和威嚴。只可惜,過去的學人根本不知道陰陽五行理論系統是在戰國百家爭鳴的背景中新鮮出籠的,西周時代還不可能產生這樣系統的宇宙論觀念。六器說的破綻就由此而露出。
從上古思想觀念的源流演變情況看,舊的六器說,無非是戰國時期流行的五色對五方的陰陽五行觀念的某種升級版而已。升級的方式也很簡單,即在原有的模式數字“五”之上,再添加一位數,變成模式數字“六”(5)葉舒憲、田大憲:《中國古代神秘數字》(增訂版),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139-165頁。。我們如今不能再相信它是對西周國家玉禮器的真實寫照,理由很簡單,在所有已經發掘出土的西周高等級墓葬中,迄今還沒有看到一座墓葬的隨葬玉禮器是按照六器模式來安排的!換言之,沒有一處西周或東周的墓葬中同時出現過琮、璧、圭、璋、璜、琥的“六器”組合。唯一的例外出現在西漢時代,甘肅禮縣鸞亭山西漢祭祀遺址,新發現六器共在的情況。這樣看,新發現的考古實物等于對舊六器說做出事實勝于雄辯的反證:六器同在的玉禮組合體系,顯然不是周禮,而似乎只能是漢禮!
二、新六器說:玉禮器五千年源流總譜
既然過去權威的禮書經典敘事內容遭到質疑和打假,那么玉禮體系的原編碼的過程究竟是怎樣的呢?下面是筆者依據出土文物的實際情況,重新編排出的一個新六器說的源流及演變圖表:
玉禮新“六器”說之源流
——從史前長三角到中原國家夏商周
1.馬家浜、河姆渡三器:鉞、璜、玦
2.崧澤文化六器:鉞、璜、玦、鐲、龍(6)玉龍,在古漢語中有個專門的字“瓏”。《說文解字》云:“瓏,禱旱玉,龍文,從玉從龍,龍亦聲。”可知瓏是為應對旱災而舉行的祈禱儀式用的玉禮器,不宜視為美化生活的裝飾品。近年新發現的崧澤文化玉龍是迄今所知南方最早的一批玉雕龍。其后被良渚文化所繼承和發揚。、 琀
3.良渚文化六器:鉞、璜、璧、琮、錐、 冠
4.龍山或夏禮六器:鉞、璜、璧、璋、刀鏟(圭)、璇璣
5.商禮六器:鉞、璜、璧、琮、戈、柄形器(圭)
6.周禮六器:鉞、璜、璧、琮、戈、柄形器(圭)
以上六器的6階段的發展演變過程,前面4個階段皆為史前期的文化大傳統,后面兩個階段方才真正進入到文字書寫小傳統。源流關系非常清楚明了,大大超越《周禮》時代和解經的漢儒時代的書本知識范圍。第1階段的馬家浜文化和河姆渡文化,是長三角地區距今7000年的考古學文化,其年代之早,大致相當于沒有玉禮器的中原仰韶文化初期。玉玦玉璜這兩種玉器,無疑都是來自北方興隆洼文化玉器。至第2階段的崧澤文化,距今6000年至5100年,始將二器發展為五或六器,即基本奠定了六器的規模和雛形。在距今5100年至4100年的良渚文化時期,六器已經齊備,其中鉞與璜二器是繼承崧澤文化而來,璧是繼承紅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和凌家灘文化玉器而來;其余三種——琮、錐、冠——則是良渚文化的創造。這三器中唯有琮一器被后世的龍山文化和中原文明所繼承,而玉錐形器和玉冠形器的傳統,則伴隨著良渚文化的滅亡而消亡了(見彩圖6)。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上古的玉兵器與玉禮器其實很難截然分開,二者關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所以被學界區別對待,主要還是囿于《周禮》舊六器說的權威地位,無人敢挑戰而已。凡是沒有進入“六器”種類的玉器,就不敢貿然當做禮器來看待了。這就是商周兩代出土玉器中大量的玉戈,竟然一直被排除在玉禮器之外的主要原因。如今我們必須尊重出土文物的客觀現實,放棄《周禮》舊六器說,重建新的六器說。準此,則發源于龍山文化,在商代周代大盛的玉戈和玉柄形器,都要理所當然地回歸到玉禮器之中,不再視為玉兵器或一般的玉飾品。因為古人絕不可能用珍稀的玉料特制成的玉戈拿到戰場上當實用武器去殺敵。玉戈從其起源地石峁古城的情況看,就和玉鏟玉刀等刃器一樣,專用于充當精神武器的辟邪功能方面。到商代以后還衍生出金玉結合的銅內(柄)玉戈,鑲嵌綠松石的銅內(柄)玉戈等(見彩圖7)。面對如此奢華的高等級權力象征物,我們還能拘泥于舊說,將其當成作戰用的兵器嗎?
最為持久不變的玉禮器是三種:鉞(見彩圖8)、璜、璧。
最短命的是玉禮器是五種:冠、錐、琮、璋、璇璣。
最缺少古漢語命名的玉禮器三種:冠、錐、柄形器。
最缺乏原創性的玉禮器發展階段是第6階段西周時代,幾乎完全照搬式的繼承商代傳統。在最短命的五種玉禮器中,玉冠飾一種,作為裝點在人頭部的玉禮器符號,早在華夏文明國家建立之前,便隨著良渚文化的消失而無影無蹤了。只是到明清時代又變相地以玉帽花玉帽正的形式,死灰復燃,回光返照。同樣命運的還有僅在良渚文化中輝煌一時的玉錐形器。玉璇璣則流行于龍山文化和夏代,在商周兩代遺址文物中雖偶有遺留物發現,卻已經失傳其本來意義和功能。琮和璋的情況也大體類似,不過這兩種玉禮器的實物流傳不遠,其名稱卻在古漢語中占據著高頻詞語的位置,不像玉冠和玉錐形器、玉柄形器等,就連個古漢語名稱也沒有流傳下來。“璋”字的流行,借助于合成詞“圭璋”的流行;“琮”字的流行,則除了借助于“璧琮”或“琮璧”的合成詞以外,還在宋代以后借助于一種模擬玉琮而生產的觀賞用瓷器——琮式瓶(見彩圖9)。玉禮器為何成為華夏文明原編碼,可以從這個派生的器物琮式瓶得到很好的說明。不過早在許慎寫《說文解字》的東漢時代,琮的禮器本義已經喪失殆盡,不然的話,他也不會說出這樣的比喻:“似車杠”(7)湯可敬:《說文解字今釋》(增訂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32頁。。文化的內涵早已隨著玉琮的廢棄而失傳了。琮式瓶徒有一個兼具方圓的華美端莊之外形,留給后代人做審美的擺設,以及發思古之幽情!
可以說,在20世紀后期良渚文化玉琮正從地下發掘出土之前,古人根本一點也不知道這種“似車杠”玉器的底蘊是什么,在清代最高統治者康熙乾隆的宮里,早有其珍藏的良渚文化的玉琮在,不過那也只是莫名其妙和不知所云的玩意而已。即使被公認為最有學識和教養的乾隆皇帝,也莫能例外。這是時代的知識所限,只能等到大傳統中國視野在20世紀被打開(見彩圖10)。
2018年11月,借助于長三角一體化上升為國家發展戰略,我們根據良渚文化玉器對華夏文明的特殊貢獻,又給“玉文化先統一中國”理論提出進一步細化的分命題,并具體表述為下一節的標題:
三、玉文化先統一長三角,再統一中國
這是根據史前玉禮器系統化過程的新認識,對玉文化先統一中國說的必要補充。旨在具體說明玉禮器如何經歷其數千年的漫長傳承過程,最后才落戶于中原王朝的。從玉禮器組合情況看,良渚文化的獨特貢獻之一,是玉冠及冠形器,包括三尖冠和玉梳背。后者在相當時間里也稱為玉冠形器,后因為在1999年浙江海鹽縣出土良渚文化完整的象牙梳,在象牙上鑲嵌為梳背的便是玉質冠形器,上面還雕琢出羽冠神人獸面紋(見彩圖11)。由此,在考古學界這種玉冠形器才被改稱“玉梳背”。我們看這件象牙梳的形狀,是細長條形的,完全不利于梳頭之用,更可能是插在高高盤起的頭發中用的。它確有梳子的外觀,但其實際功能還是承載神話觀念意義的冠狀器。
至于良渚文化先民為什么對冠如此青睞,神話仿生學的視角給予具體說明:人無冠而鳥有冠,崇拜鳥的結果,就是模仿鳥冠而制作人頭頂上方的冠狀器。生怕你不知道這冠是模擬鳥神的象征,就在冠上精細刻畫出鳥羽的形象。這就是反山M12出土“玉琮王”上八個羽冠神人像所潛含的信仰和神話底蘊。按照禮失而求諸野的國學傳統考據原理,在當今中國早已消失不見的薩滿巫師頭戴巨大羽冠的禮俗,還原封不變地保留在一兩萬年前自北亞遷移到美洲的印第安人文化中。彩圖12是筆者在荷蘭萊頓的人類學博物館拍攝到的那伐鶴印第安薩滿的巨型羽冠的實物照,這類民族學的旁證材料被文學人類學派稱為文化研究和文化重建的第三重證據,其重要的學術作用就是給文獻記載的難點和無言的文物等,提供一種語境還原的活態參照,發揮出“激活”的作用。
周代玉禮器體系,如果不拘泥于六器舊說,也不看今人所劃分的禮器與非禮器之界限,而是按照周代高等級墓葬中出土的數量多少來排序,那就是如下的十二種,而其中九種都可以溯源至良渚文化玉器:
1.玉魚、2.玉柄形器、3.戈、4.璜、5.龍、6.人像、7.璧、8.鉞、9.圭、10. 蟬、11. 琮、12.玉覆面。
玉琮在周代雖然也有,但是相比其他玉器,只是偶爾一見,多為前代生產的遺留物,西周人已經基本不再規模性地制造玉琮了。源于良渚玉禮器的玉琮,其神話信仰觀念及其祭祀功能在周代已經瀕臨失傳。
長三角地區史前的良渚文化本地“六器”中,有五器直接或間接進入華夏王朝玉禮器體系,只有玉冠這一項被終結在文明起源之前。這就是為什么說玉文化先統一長三角,再統一中國的重要理由。同樣,始于長三角地區崧澤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鳥形陶器如陶鬶、陶斝和陶盉等,也都先后傳播到北方和中原地區,成為夏商周青銅禮器的原型。這已經是玉文化之外的衍生問題,容在另文中再加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