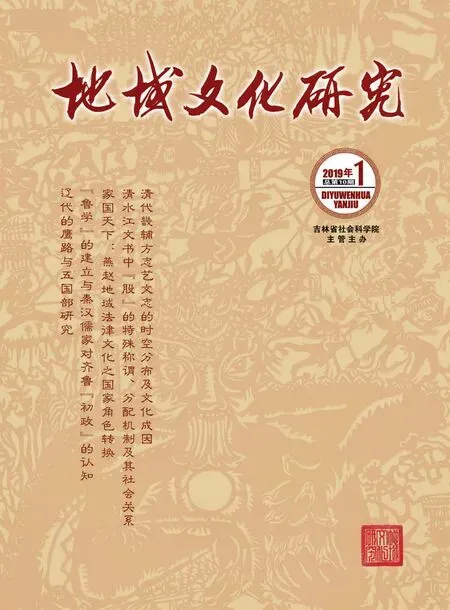“魯學”的建立與秦漢儒家對齊魯“初政”的認知
張沛林
《漢書·儒林傳》: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谷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谷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谷梁》。①(東漢)班固:《漢書》卷88《儒林傳》,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3618頁。
“魯學”“齊學”及《公羊》為“齊學”與《谷梁》本“魯學”的稱法即源于此。《漢書》中的這一段話,除在學史上提供了兩個名詞以及概念外,其蘊含的歷史及當時人的觀念訊息也是十分豐富的。
首先,漢宣帝初即位時,距漢高祖劉邦建國已有一百余年的時間,“齊”與“魯”這兩個西周初開始存在的諸侯國早已滅亡。雖然,在西漢也曾多次有同名的諸侯國設置,但其轄區頻繁變更,已和兩周齊、魯舊國地域的范圍大不相同了。大抵“齊”“魯”在西漢中期只作為地域名存在,這里的“魯學”“齊學”是一例,又如《史記》《漢書》的《儒林傳》往往直接表明經師是“齊人”或“魯人”。可以說在西漢中期的人心中,“齊”“魯”仍然可以算作界限清晰。
第二,也是更為重要的,文中“宜興”一詞最值得關注。“宜興”的原因絕不是谷梁子與韋賢等同為“魯人”,也不完全是皇帝有所私心或偏好,而群臣附和。因為這兩點原因都不夠“冠冕堂皇”,不可以對嚴肅的政治與當時和政治有極大關聯的經學給予合理交代,只可能是他們口中的“魯學”在某些方面較“齊學”有真正的“優勢”,才可以成為“宜興”的理由。為說明這種“優勢”的必要性,這里權做一個簡單假設:孔子是魯人。孔子的學說在魯地發源,孔子的弟子也多為魯人。任憑“齊學”先師在當時有多么高的權威,如果“魯”地有孔子最純正的學問,“魯學”是得到至圣孔子的真傳,借用司馬遷的話說“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那么“齊學”也必須讓“魯學”一頭。“宜興魯學”才能正式成為一個可議的官方議題,隨之才能以皇帝的旨意使《谷梁》成為官學。該“假設”并無佐證,但可以顯示“魯學”的“宜興”,也就是其較“齊學”的“優勢”,必須有在群體中高于個別權利的學理支持。
以上就《漢書·儒林傳》中這一段重要記載的兩點“言外之意”作了初步的論述。而今日讀者如果對西漢政治及經學有一定了解,在閱讀這一段話時,并不需經過深入的思考便可以意識到這兩個問題的存在。這樣的論述似乎同于“雞肋”,但其關涉到一個需要深入探討的根本問題。問題的提出就在于時間與空間的差異。假如在春秋、戰國時,齊、魯二國尚在,如果談兩國學術,畢竟可依據當時存在的國家或當時國內的學者劃分。而西漢中期時談“齊學”與“魯學”,空間、時間的憑據已減弱,學問也隨幾代學者的探求發生轉變。且韋賢所指的“魯學”,并非是單純的地域學術概念,已經轉換為孔子之后“《春秋》學”或“經學”上的概念。①“齊學”“魯學”或可移為《詩經》學上的《齊詩》《魯詩》,但就《儒林傳》中語,韋賢等人的話專就“春秋學”提出。時間與地域都不再完全適用,“魯學”的提出實在使人生疑。
根據上面的懷疑,需要探究的重要問題可以概括為:韋賢等人對“齊學”“魯學”兩個概念的內涵是如何認識的,其區別兩者是當以“齊”“魯”地域劃分?還是以學風和釋經方法劃分?還是以《公羊傳》及《谷梁傳》中具體不同的觀點學說劃分?或者可以說是韋賢等人在魯國滅亡、地域變更的情況下是如何建構“魯學”的,“魯學”與“齊學”是否在西漢中期時真的可以成立?
一
韋賢等人是否就“齊學”“魯學”有相對具體的認識,因文獻缺乏,我們已經不能了解當事人的具體說法。但就其當時情形,他們對兩個概念的提出,是為治國當以“王霸雜之”的漢宣帝,情感上突然對并不太看好而又需利用的“經學”產生的一些可貴傾向提供依據。這也體現了歷史的“或然性”:假如衛太子不曾好《谷梁》,假如當時《谷梁》傳習者依然同先師申公一樣言論不得皇帝之心,同先師瑕丘江公一樣口訥敗給董仲舒,兩個概念的提出及漢中后期《谷梁》學興盛一時的情況恐怕也不會存在。
但“無中生有”對任何人,尤其對身為政治家和學者是較難的事情,重要觀念尤其是使某些方面歷史軌跡有所改變的觀念一定有其學理上的基礎。即便這些概念是如今人常說的固化的片面的“貼標簽”,其“不準確”也是概念的某些方面不可以和事實相符合,但不準確的“標簽”一定是根據某些與事實相合的方面而“貼”出的。討論“魯學”“齊學”,就是要找到這些與歷史相合之處。
作為相對的概念,“差異”應最先討論。兩個“學”的不同,從兩個“名詞”上看,關鍵在于“齊”與“魯”的差異。作為單純的地域來談,其差別明顯。雖同在東方,“齊”臨海而“魯”為內陸,“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空間的差異也許會對民風、民俗產生影響。這方面區別,學者們從考古、歷史、民俗與人類學等諸多方面已有充分研究。這里僅就為后來史家及學者眼中關注的“齊”“魯”,也就是經過人為“改造”或“重構”后的“齊”“魯”再做一些考述。首先來看齊國:
《史記·齊太公世家》: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①(漢)司馬遷:《史記》卷32《齊太公世家》,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1785頁。
又,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瑯琊,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闊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圣,建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為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②(漢)司馬遷:《史記》卷32《齊太公世家》,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1820頁。
以上兩段,司馬遷以不多的語言,將齊國建國時姜太公治國的政策及在西漢初他親身到齊國體驗的感受作了陳述。太公的“因其俗”與司馬遷體察到的“其天性也”形成了互證,清楚地表明了齊國的“俗”在周初至漢初近八百年中基本未有大的改變。但太公“修政”不是無作為,“簡其禮”表現了周人的制度在有些方面還是在齊地推行開來。只是作為推測來談,“禮”不施于庶人,這些制度更多的是在上層社會的改變,以適用于行政的要求及齊國國政與周的對接。在社會進程發展較遲緩的時代,八百年而在下的民氓還是保持著“天性”則完全有可能。而司馬遷的親身印證,體現出他“實踐史學”,應為“實錄”。
有趣的是,司馬遷在《魯周公世家》中將“齊太公”和“魯伯禽”做了個對比:
《史記·魯周公世家》: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為魯公。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后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后除之,故遲。”太公亦封于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及后聞伯禽報政遲,乃嘆曰:“嗚呼,魯后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③(漢)司馬遷:《史記》卷33《魯周公世家》,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1835頁。
《史記》中的這一段,作為齊、魯“初政”與對后來齊魯文化特征的重要證據,近代以來學者多有引述,已屬“老生常談”。其中文字是司馬遷根據古史籍“轉譯”,或是據傳說書寫,周公三人的語言明顯不同于《尚書》中一些篇目的佶屈聱牙與周初青銅器上銘文的簡古。非當事者原話,基本可以確定。而對史料中具體情境與人物對話可靠性的懷疑,并不影響對該事的大致情況與在歷史中的真實性。從日后齊、魯的文化名人及風格,如“齊諧”“稷下”、孔子以及漢高祖滅項羽后“獨魯不下”等情況,“初政”內容對國民性格、操守以及文化諸多方面確有巨大影響,是沒有理由懷疑這種“初政”的不存在。“初政”也是討論“齊學”“魯學”在孔子之前最為重要的文化“基因”。而更為重要的是,不論在司馬遷的眼中,還是《史記》中的“周公”,他們將“齊”“魯”的未來發展都系在了這個“初政”上,也就是系在“初政”的執行者齊太公與魯伯禽身上。
作為先秦及漢初觀念上的“學”,多半是討論如何治理國家的。諸子學說的分野,也常是因對治國不同觀點產生的分歧。或許“名家”“陰陽家”等將一部分關注點放在了事物的名稱與性質上,但可以斷定,諸子學大多數是針對或指向政治之學的,“如何治國”是“學”的核心。而我們要討論的“齊學”與“魯學”雖是在“學”的觀念上已有轉變,也就是由儒家轉入經師,“政治之學”轉入“經典之學”的時期提出的,但其“學”的前提畢竟是“齊”“魯”,“初政”是一個重要來源。在文獻中,也就是在史籍書寫者及觀念提出者對歷史的回顧與重新構建中,我們討論的“齊學”與“魯學”,要從考察學者對“初政”差別及齊太公、魯伯禽差別入手。因為對同一歷史狀況,人們的思想有所不同,文獻書寫者的態度和文獻中對人物及事例的書寫會有所轉變。史學家重視的是實錄,而儒者經師重視的是信仰。
《說苑·政理》:齊之所以不如魯者,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后親,先義后仁也。”此霸者之跡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者,先內后外,先仁后義也。”此王者之跡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跡者,仁厚也;齊有霸跡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①向宗魯:《說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169頁。
上引《說苑》中這一段明顯與前引《史記》中一段所說是同一件事,而觀點卻完全相反。拋卻這段話的時間性、書寫者與《史記》中相關內容做一個對比,②應說明的是,《說苑》是西漢末劉向所編輯的,劉中壘向來以博聞見稱,其編纂書籍材料來源自皇家及群臣藏書,但終究難以確定某一則的來源。觀其編纂的《戰國策》等書,所述與歷史多有乖違,其雖然為“文獻學之祖”,但處理某部文獻的方式我們也不能確定。同樣,我們并不能知道劉中壘在編纂這段話中有沒有改寫,其反映是誰的觀念不可知,但大體是儒家的。其重點在周公對太公、伯禽的評價。首先《史記》中相對簡略,對于“治國”的優劣,周公肯定了太公的“簡易”③裴骃《史記集解》載有兩種不同的本子:徐廣曰:“一本云‘政不簡不行,不行不樂,不樂則不平易;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又一本云‘夫民不簡不易;有近乎簡易,民必歸之’。”但兩本大義都相近。,而對未來的預測是魯必然居于齊下,或可以說魯當為齊臣屬。而《說苑》所載的恰恰相反,首先,對“治國”優劣的評價者變成了文獻的書寫或改編者,他(們)認為,齊不如魯,太公不如伯禽,差別在于“王者”還是“霸者”,而文中的周公只是做了對未來的預測。
《史記·齊太公世家》:“蓋太公之卒百有余年,子丁公呂伋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就在這第五世齊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而“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丘人襲攻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齊國的確亂了。魯國雖中間有魏公弒幽公,但十世懿公為武公少子,為周宣王所喜愛而命為太子,即位后被其兄括的兒子伯御所殺,周宣王殺伯御而立孝公。司馬遷對宣王的悖禮與魯亂的后果用一句話作結:“自是后,諸侯多畔王命。”對照史籍記載,《說苑》中周公的“預言”是驚人的準確。
很明顯,《說苑》中的一段話是被修改過。而修改者應為劉向之前的儒家學者。對比《史記》,齊國與魯國的“初政”優劣得到了逆轉,并通過周公的“預言”對齊、魯的國史給予佐證。儒家經師是青睞魯國的“初政”的,對這種“王道”初政的認同,促使他們修改史料。推至“魯學”與“齊學”,在儒家看來,“魯”在其“基因”中自有優越之處。
二
儒家經師對比齊、魯的“初政”,自然伯禽為優。那么魯國“初政”的執行者伯禽在漢儒心中,尤其是在沒有同齊太公對比時的確切評價,則體現了“魯”與“魯文化”在漢儒心中較為準確的定位。
中國古代學者對于自己推崇的先賢,往往進行“神圣化”的塑造,賦予“預言”能力便是其中一種方式。對比《史記》《說苑》兩則材料,《說苑》中的周公是“神化”了的。而《史記》中的周公并不可以說是“神”,只是作為一個出色且有預見性的政治家出現。①在這里,不能說《史記》便是絲毫不差的實錄,這與前面提到司馬遷寫齊國風俗為實錄不同,它是具體的人物對話,來源于傳說或古代文獻,無法進行實踐驗證。
書寫者及改編者的目的各不相同。《說苑》神化周公是借其口評述“齊”“魯”優劣。而還有一種是將文獻中“對手”雙方都“神化”的處理,如文獻中有關于對周公和齊太公齊魯政治優劣的對話:
《呂氏春秋·長見篇》:呂太公望封于齊,周公旦封于魯,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謂曰“何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旦曰:“親親上恩。”太公望曰:“魯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其后齊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齊國;魯日以削,至于覲存,三十四世而亡。②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255頁。
這則材料還見于《淮南子·齊俗訓》《韓詩外傳》《漢書·地理志》等古籍中。文字雖異,大旨相同,這里不再引列原文。綜合上面《說苑》《史記》的材料,可以看出“齊”“魯”的“初政”問題在戰國、秦漢之際討論較為普遍。《呂覽》周公、齊太公皆被神化:太公以為“魯削”與周公以為“齊非呂氏”,預言都十分準確。文獻中二者似乎“勢均力敵”,周公稍稍勝出。而其想表達的是治國“尊賢上功”與“親親上恩”之異,亦應出自儒家手筆。此段情況與《說苑》相似,這里不為論述“齊”“魯”,是為引出接下來討論的問題,是否所有人皆可被當作圣賢而“神化”,伯禽是否具備這個資格。
在《說苑》中周公被神化,在《呂覽》中周公、太公望都被神化,因在歷史上他們都為王佐之才,所以在傳說中有被“神化”的資格。只是有資格的人中誰需要被“神話”由文獻書寫者決定。老子可以“化胡”,孔子是“儒童菩薩”。不論出于什么目的,“資格”必須具備,而小小的人物或許在后世文獻中能飛上云端作仙人,卻不能作“全知”高等的神。
伯禽作為魯國歷史上較為重要的人物,魯國的“初政”由其完成,魯國民風、民俗甚至“魯學”都和他脫不掉關系,他有被神話的資格嗎?從文獻中看,這類情況幾乎沒有,而夸贊的情況是存在的。
《毛詩·駉小序》:《駉》,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谷,牧于坰野。魯人尊之。于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③阮元等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第608頁。
《晏子春秋·內篇問上》:景公舉兵欲伐魯,問于晏子,晏子對曰:“不可!魯好義而民戴之,好義者安,見戴者和,伯禽之治存焉,故不可攻。”④張純一:《晏子春秋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127頁。
《孔叢子·公儀》:穆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公曰:“為之奈何?”對曰:“茍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鄰國,其
興也勃矣。”①張純一:《晏子春秋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165頁。
以上三則材料,或是贊魯僖公學伯禽,或以周公、伯禽并稱,或獨贊伯禽,都是夸贊的實例,但至于“神化”的形象則沒有。而文獻中存在大量的周公“教訓”伯禽的內容:
《史記·魯周公世家》: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發,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②(漢)司馬遷:《史記》卷33《魯周公世家》,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1785頁。
《韓詩外傳》卷三:成王封伯禽于魯,周公誡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于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發,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眾兵強,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強記,守之以淺者,智。夫此六者,皆謙德也。夫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由此德也。不謙而失天下亡其身者,桀紂是也,可不慎歟!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以衣成則必缺纴,宮成則必缺隅,屋成則必加措,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圣敬日躋。’誡之哉!其無以魯國驕士也。”③許維遹:《韓詩外傳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117-118頁。
《韓詩外傳》及《史記》中這兩段恰與前引《史記》《說苑》的情況相近,都是講同一件事而內容有差異。不同的是,《韓詩外傳》出現應在《史記》之前。那么《史記》沒有采信《韓詩外傳》中周公自“吾聞德行寬裕”至“誡之哉”的一大段話,有可能兩者都有相近的史料來源,《韓詩外傳》有所增添,也有可能是司馬遷刪去,這里不做討論。但《史記》所不取的一段確實“夸張”,引《詩》談《易》大似東周儒士。不論語言的多寡,兩段話都沒有豐富伯禽的形象,文獻的書寫者意圖或在記周公的思想,或借周公之口說話,伯禽的用途只是叫周公論道不“自言自語”而已。伯禽被“教訓”的情況并不少見,在文獻中可長可短。短者如《呂覽》中一語,④《呂氏春秋·貴公》:“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周公曰:‘利而勿利也。’”非受周公“教訓”的如《說苑》中有成王教訓伯禽⑤《說苑·君道》:“成王封伯禽為魯公,召而告之曰:‘爾知為人上之道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之門,撙節安靜以籍之。諫者勿振以威,勿格其言。博采其辭,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辭。”。伯禽總是一個淡化了形象的被“教訓”者。
孟子談“圣人”,在伯禽之前有伯夷、伊尹,在其后有柳下惠。相較于這些人,其事跡確實不顯。伯禽絕非乏善可陳,他的魯國“初政”是將宗周禮樂文化在東方推廣開來,在后世儒家眼中有大功勞。但伯禽是執行者而非創制者,他時常被“教訓”而或恭敬地執行,沒有“神化”的資格也沒有“神化”的必要。假如文獻中對伯禽有了形象的描述,那么也是為了在對比中完成抬高他父親周公的目的。
《荀子·堯問》:伯禽將歸于魯,周公謂伯禽之傅曰:“汝將行,盍志而子美德乎?”對曰:“其為人寬,好自用,以慎。此三者,其美德也。”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為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道。彼其寬也,出無辨矣,女又美之!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窶小也。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知如士,不與士爭知。彼爭者均者之氣也,女又美之!彼其慎也,是其所以淺也。聞之曰:‘無越踰不見士。’見士問曰:‘無乃不察乎?’不聞即物少至,少至則淺。彼淺者,賤人之道也,女又美之!吾語女:我、文王之為子,武王之為弟,成王之為叔父,吾于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者百有余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余人,于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吾所以得三士者,亡于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故上士吾薄為之貌,下士吾厚為之貌,人人皆以我為越踰好士,然故士至;士至而后見物,見物然后知其是非之所在。戒之哉!女以魯國驕人,幾矣!夫仰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為賤,舍富而為貧,舍佚而為勞,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①王先謙:《荀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647-651頁。
《荀子》中這一段話較長,大部分還是周公的言語。與前引《韓詩外傳》《史記》狀況不同:伯禽雖并未出場,但終于有了“為人寬,好自用,以慎”的形象。但隨之便得到了周公的否定。伯禽的三個在常人眼中的“美德”,引起周公感嘆:“以人惡為美德乎?”這一句如何解讀,以前的釋讀者或認為很簡單,不予說明。或認為“惡”是名詞,整句當理解為“把人壞的地方當作美德”,其實是錯誤地理解了。從整段話可以看出,伯禽的三個“美德”及周公所說的都是針對治民、取士的問題,而非泛泛地談治國。何況這三個“美德”無論如何也談不上是“惡”的。這里的“以人”是用人之義,如《荀子·大略篇》:“上臣事君以人”。而“惡”是疑問代詞,如《荀子·禮論篇》:“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整句話當理解為:“(為人寬、好自用、以慎三點)在用人上哪里是美德啊”。這句話作為一段的轉折,伯禽的“美德”與周公見識又形成對比。如文中的周公是以“道”德人的,對待士人也是靈活的采取不同態度。相比周公“兩邊不住”的“中道”“中庸”,伯禽的“美德”也偏向了一邊,不那么完善靈活。
前賢的“神”與“圣”,也同樣遵循著“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的原則,伯禽文獻中的形象在與周公對比中得到了體現:伯禽并未理解透徹作為圣人的父親的“教訓”,而保守謹慎地在魯國推行著“宗周文明”。最明顯的例子,在《漢書·古今人表》,《表》將人分九品,周公列在上上圣人,師尚父在上中仁人,而伯禽竟在第五等中中。與其一品的歷史名人還有齊桓公②管仲在上中仁人,對比下見班固對齊桓公功績的歸屬意見。、呂不韋等,明顯可以看出在漢儒心中對伯禽是“可以為善”“可以為惡”的普通人。
三
伯禽是魯文化形成中關鍵的人物,上文主要談西漢人對他形象的認識。而更為關鍵的是孔子對魯的看法。《論語·雍也》:子曰:“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先賢多以為孔子就時事而言,如包咸注:“言齊、魯有太公、周公之余化,太公大賢,周公圣人,今其政教雖衰,若有明君興之,齊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行之時。”其中雖談到周公、齊太公差別,但卻一律肯定。
《論語集注》: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余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強魯弱,孰不以為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為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修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于先王之道也。”①(南宋)朱子:《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90頁。
朱子注并引程子說,稍稍進了一步:對齊太公的態度,從儒家角度稍有貶損,更強調了“初政”的差別。也就是對《論語》中這一句話的解讀,從圣賢的差別,轉變為王政與霸政的差別。問題在于,時事與初政在這句話中,到底分別有多重的比例?《論語·八佾篇》所說的“三家者以雍徹”“季氏旅于泰山”這恐怕也并非一變即為“道”的魯政現實。而《論語·八佾》:子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子路》: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參考《論語》中以上二語,更可以得出,孔子對某國政治的評價,雖不能說一點也不顧及現實,但“探源”的意思是較多的。孔子說齊桓公“仁”,說“齊桓公正而不譎”,魯僖公雖然是“作頌賢君”,但依然不可以與齊桓相比,怎么可以說春秋時是“齊一變至于魯”。
“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中,當是“初政”的因素較多,太公“簡政”一變為伯禽之政,伯禽一變或能至于周公的“郁郁乎文哉”。結合前面所引戰國至西漢的文獻,伯禽不能與周公相比,“魯”的“初政”與周政相比打了折扣,孔子的話也是重要的印證。同樣實行周政,伯禽還是和周公有差異的,孔子或有意或無意,也參與進這種對歷史及文化形象的構建中。
歷史中真實的狀況無法完全復原,但在文獻中,伯禽的“形象”及其“初政”給魯人在秦漢時期人心中留的印象也可以通過文獻反映出來。在討論這個問題前,需要強調的是個體雖然接受著周圍文化環境的浸染,但還是有差異的。說齊國人都還保持著天性,但也應有純謹之人,如荀子弟子浮丘伯。與荀子的其他兩位著名弟子李斯與韓非,對此浮丘伯學《詩》是多么“不通達”,其所傳《詩》學日后還被稱為“魯詩”。魯國也并非無狂肆之人,如孔子的老友原壤,《論語》中載其箕踞等待孔子,《禮記》載其母死而敲槨木而歌,簡直“大逆不道”。但只要不針對個體,文獻書寫者便總喜歡歸類:
《史記·扁鵲列傳》: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洛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痹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②(漢)司馬遷:《史記》卷105《扁鵲倉公列傳》,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361頁。
上引《扁鵲列傳》的記載是對事實的絕對化,風俗、習慣的特點即成為地域整體人物的特點。諸子書中常將一類性格歸到一國人的頭上,如“齊人有一妻一妾”,宋人“守株待兔”“揠苗助長”而鄭人“買櫝還珠”,或荒唐或愚蠢。但在不同學派學者眼中,則有不同的看法:
《韓非子·說林上》: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欲徒于越,或謂之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為履之也,而越人跣行;縞為冠之也,而越人被髪。以子之所長,游于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乎?”①周勛初等:《韓非子校注》,南京:鳳凰出版社,2014年,第201頁。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夫少者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一曰。魯人有自喜者,見長年飲酒不能釂則唾之,亦效唾之。一曰。宋人有少者亦欲效善,見長者飲無余,非斟酒飲也而欲盡之。②周勛初等:《韓非子校注》,南京:鳳凰出版社,2014年,第316頁。
儒家眼中魯人的“規矩”,在韓非子看來,則稍為愚蠢,不知世事,不懂變通。而史家紀實,如《史記·貨殖列傳》:“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貰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③(漢)司馬遷:《史記》卷129《貨殖列傳》,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950頁。又“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于禮,故其民齪齪。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眾,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于周人。”《史記·游俠列傳》:“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④(漢)司馬遷:《史記》卷124《游俠列傳》,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2840頁。則記載魯人雖有一些觀念上的轉變,但始終應是學文學、以儒教的。而有時“魯人”的出場,也表達了一些態度,從而也反映了“魯人”在史家眼中的形象。在具體的歷史事件中,則可以是以半虛構的形象出現,如《史記·吳起列傳》中的“魯人或惡吳起”,《史記·叔孫通列傳》中的“魯有兩生不肯行”。
上文就“齊、魯初政及其在文獻中的評價”“文獻中伯禽形象”及“周季與秦漢文獻中魯人特點”三個方面進行研究。其目的在于較準確的還原“魯文化”在西漢儒者心中的定位,從而說明“魯學”在他們心中的位置。綜合來說,通過對《說苑》等文獻的分析,伯禽在漢儒心目中的定位得以初步的還原,魯國的“初政”是嚴格依照周禮推行的,文獻中伯禽的形象又被戰國、西漢儒家塑造成謹慎且稍顯教條的。伯禽雖遠不及呂尚,其“初政”也未達到周公治下的高度,但其行“王道”畢竟比行“霸道”優越,“魯”高于“齊”就是在這個方面”,但也并非盡善盡美。
而上文曾就孔子在兩概念提出中的影響做過一個猜測,但無論如何,說《公羊》是“齊學”則代表其不是純正孔子之學,在當時都會引起反感。況且“齊”與“魯”并提比較,從上文征引的文獻看,秦漢人有較固定的問題意識,便是“初政”及其后來影響。
還原了西漢儒家心中“魯”的位置,再來看韋賢等人所謂的“魯學”。
《漢書·儒林傳》: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余歲,皆明習。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谷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挽、伊推、宋顯,《谷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并論。《公羊》家多不見從,愿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并內《谷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余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谷梁》。由是《谷梁》之學大盛。”⑤(東漢)班固:《漢書》卷88《儒林列傳》,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3618頁。
從上引《儒林傳》事可見,所謂“魯學”壓過“齊學”而能大興,還要靠在具體的“經義”論辯中取勝。但這只作為“程序”,“宜興魯學”恐怕是作為“魯人”的私意,作為迎合宣帝的意旨,而結合西漢人心中“魯”與“齊”對比中的優越,而為達到興起《谷梁》的一個借口。如同當時漢武帝選擇《公羊》一樣。或許韋賢等人以更近“王道”的“魯學”勸諫“霸王雜之”的漢宣帝,但無論目的如何,“齊學”“魯學”在韋賢等人那里,算得上是一個刻意為之的概念。
四
以上考量了秦漢儒家對齊、魯“初政”及伯禽的認識與建構,可以說這是戰國、秦漢人的固有話題,韋賢等對“齊”“魯”優劣認識在“初政”上是較為清晰的。就此前“齊”“魯”的對比常在“初政”上,而經學上韋賢等是首次提出,移置《公》《穀》二傳說法比較含混。那么為什么“齊學”“魯學”是建立在這種固有“王”“霸”之分的認識上,而不是在西漢中期“齊學”“魯學”本來就因地域有界限清晰的區別呢?也就是“魯學”與“齊學”是否能在西漢中期實際的學術環境中得以成立。
蒙文通先生以為“魯學謹嚴,齊學駁雜”,“齊學之黨為雜取異義,魯學之黨為篤守師傳”,“就漢世言之,則魯學謹篤,齊學恢宏,風尚各殊者,正以魯固儒學之正宗,而齊乃諸子所萃聚”。①詳見蒙文通《經學抉原》,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年,第84-85頁。蒙先生將“齊學”“魯學”說的涇渭分明,其方法則是抓住史料中一二語或一兩例擴充到全體。如劉歆有“義各相反”一語,蒙先生則以為“《公羊》與《谷梁》反異”云云。作為不同著作,其“反異”是正常的。按今《公》《穀》傳文,其相同者也很多,如何定義這種“反異”?又如《漢書》載申公以訓詁教《魯詩》,最為近真,而轅固生及韓生采雜說,以此則知“魯學謹嚴,齊學駁雜”,則是從一個例推廣到全體。
蒙先生的方法是先接受了“齊學”“魯學”兩個概念,然后向其中填充內容,這種方法的錯誤在于先成立“概念”再套用“實際”。上文引《史記》并談到,兩國“初政”對兩國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也使兩國民風有所不同。
《管子·大匡》:“衛國之教,危傅以利。公子開方之為人也,慧以給,不能久而樂始,可游于衛。魯邑之教,好邇而訓于禮。季友之為人也,恭以精,博于糧,多小信,可游于魯。楚國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義,而好立小信。蒙孫博于教而文巧于辭,不好立大義而好結小信,可游于楚。”②黎翔鳳:《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361頁。
《漢書·鄒陽傳》:“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③(東漢)班固:《漢書》卷51《賈鄒枚陸傳》,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2353頁。
如上,從一些文獻中確實反映出戰國秦漢時不同地域人的性格不同。魯人較保守,齊人則較開通。子曰:“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假若曲解狂、狷的意思,正好可以拿來比喻“齊”“魯”人的性格。且上文也曾引及《扁鵲列傳》,證明各地愛好不同,如今人常談湘、川人愛吃辣,而東南愛吃甜,都屬這類。是將地域的大眾喜好,或大多數人風俗及文化、性格在語言及文獻上表達的絕對化。對于風俗,雖然一定有特例,但泛言無妨。可是因為學者數量是有限的,且分類要求嚴格,對學派的歸類是應避免這種浮泛的方法。學派中的所有學者都應在主要學說或方法上相同相近才能定為一類,其余若師承、地域等方面都難以作為統一標準,何況西漢經學,前后變化巨大,考量“齊學”“魯學”應當是嚴格的。
首先就所謂“齊學”“魯學”的代表看:
《史記·儒林列傳》: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者則闕不傳……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余,老,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①(漢)司馬遷:《史記》卷121《儒林列傳》,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766頁。
申公作為《魯詩》《谷梁春秋》學史上較關鍵的人物,忽略司馬遷特意提及的“老”字,②這里的“老”字或是馬遷有意書寫的,因年老可使人沉穩。其性格確實同于魯人性格。以一語談力行治國,與所謂“齊學”代表董仲舒動輒千言的《三策》是有所不同。《魯詩》則純以訓詁傳,無《傳》。察《漢書·藝文志》,數家獨《魯詩》無《魯傳》。申公的學問,確實像蒙文通先生說的那樣謹篤。
但在西漢中期,也就是漢宣帝即位前后一段時間,是學術變化的關鍵時期,學問風氣與漢初又大不相同。就“魯學”一詞的提出者們看:史高史料寡少。韋賢雖位至丞相,《漢書》特為立傳,但只是交代其為瑕丘江公弟子,為“鄒魯大儒”。可能是因為政治成就較高,對其學術少有談及。有據可依的是夏侯勝,《漢書·夏侯勝傳》:“從始昌受《尚書》及《洪范五行傳》,說災異。”災異事暫且不談,這里只看《尚書》學。西漢《尚書》多源自伏生,伏生傳張生,張生傳夏侯始昌,夏侯勝的《尚書》學若歸類當屬“齊學”。而蒙文通先生則以為大小夏侯《尚書》為“魯學”。小夏侯是夏侯建,《漢書》載其“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則又屬蒙先生所說“齊學之黨為雜取異義”類。如此看,“魯學”的代表學者有完全符合條件,如申公。有的竟符合“齊學”特點,如大小夏侯,可見蒙先生的分類與實際情況的矛盾。
再就時代學風的變異,也就是“災異學”看:
《漢書·眭弘傳》: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洶洶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后有白烏數千下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木臥復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臥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為“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非人力所為,此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漢家堯后,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順天命。”孟使友人內官長賜上此書。時,昭帝幼,大將軍霍光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孟妄設祅言惑眾,大逆不道,皆伏誅。③(東漢)班固:《漢書》卷75《眭兩夏侯京翼李傳》,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3153-3154頁。
上引《漢書》眭孟被殺一事,《五行志》等亦有記載。一方面眭孟的確迂腐,不知執政者的底線。兩個迂腐儒生湊在一起上書,且是卑微的學者,并非權臣,竟然想讓皇帝“禪讓”。何況眭孟所說的“先師董仲舒”,就曾因言“災異”而被漢武帝下獄“警告”。眭孟猶不以先生為前車之鑒,這恐怕并非偶然,而是“陰陽五行學說”在當時實在深入人心,成為學者們最重要的研究對象甚至是信仰,并不以為忌諱。元鳳三年(前78)至宣帝即位不到十年,因此事警戒,學者們或許不再“口無遮攔”,但學風業已形成,迥異于武帝之初。所謂的“魯學”,若在這種學風下毫無改變,不主動添加些所謂“齊學”作風,則絕不能適應現實需要。
察《漢書·藝文志》,也有如《谷梁外傳》這類的著作出現。《谷梁》屬蒙先生說的“魯學”,如何能有《外傳》?《漢書·五行志上》:“劉向治《谷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范》,與仲舒錯。”①(東漢)班固:《漢書》卷27上《五行志上》,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1317頁。“傳以《洪范》”當作“傅以《洪范》”,顏師古注:“傳字或作傅,讀曰附,謂附著。”劉中壘以《洪范》述《谷梁》,完全為順應時代學風,將《谷梁》推向一個高峰。如謹守師法,又如何以《谷梁》推“災異”?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說,申公《谷梁》學是申公之學,劉向《谷梁》學是劉向之學。兩者《谷梁》學尚且不能相合,何況將西漢經學簡單分為“齊學”“魯學”。
上文曾談到,如果討論西周、春秋以及戰國時魯國具體的“魯學”,為魯地學人做一個“學案”,從魯國存在的角度說,不論其內部有什么不同的派別,“魯學”是合理的。這種合理不是學派,而是以人及存在的國家地域劃分。西漢中期提出的“魯學”與“齊學”,作為概念,它首先必須在當時儒家與經學的范圍中得以普遍適用。如翼奉、匡衡、蕭望之同學于后蒼,傳《齊詩》。按理說三者都應該屬于一個“學派”,但翼奉上書動輒言“災異”,而匡衡多言禮制、經濟,蕭望之多談政事而偶言及“災異”。個人偏好差異還算明顯,所以經學內容的多樣性與學者的差別恐怕難以用一種固定學派的標準分類。
又,概念的成立,必然要有現實合理的因素。如西漢常見的“經學”“經術”等詞,在先秦并不多見。如果可見,也與西漢的含義不同。西漢的大量出現,是因為實實在在有共同承認的“經學”“經術”存在,并且常常使用,所以見于文獻的數量自然很多。“齊學”“魯學”則不同,在韋賢等人提出前,沒有人提出相同的說法,甚至其后的西漢末東漢之時也很少出現。從此側面也可得知這兩個概念的真實性。
以上,就秦漢儒家對齊、魯“初政”及伯禽的認識與建構與“齊學”“魯學”是否在西漢中期時真的可以成立兩個問題作答。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韋賢等人提出“齊學”“魯學”兩個概念依據了戰國以降儒家對齊、魯政治“霸道”與“王道”的認識,政治意圖較強,而并不符合實際學術情況。西漢《谷梁》學作為一門前后變化的學問,也不可將其視為所謂的“魯學”。今天討論經學史上“齊學”“魯學”的意義,恐怕并不如“齊文化”“魯文化”的意義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