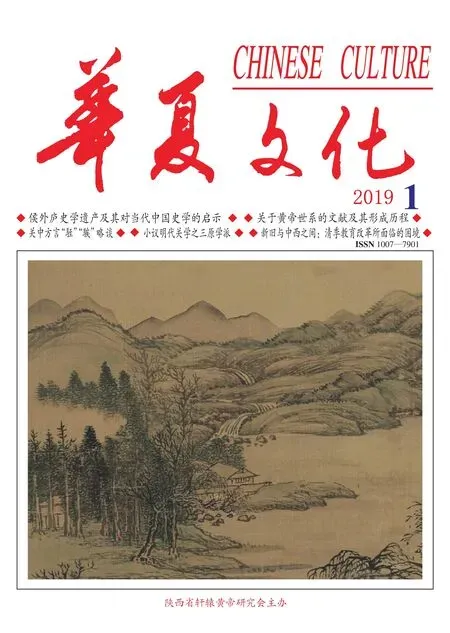《逍遙游》與道教丹道
□劉振宇
《逍遙游》是《莊子》一書的首篇,其中所蘊含的思想可以說是莊子哲學(xué)的核心內(nèi)容,一直是學(xué)術(shù)界研究的熱點。但是,在過往的莊學(xué)研究中,人們很少注意到其對道教丹道產(chǎn)生的深遠(yuǎn)影響和內(nèi)在聯(lián)系。陳鼓應(yīng)在《莊子今注今譯》一書的開頭部分寫道:“他的哲學(xué)思想不僅是我學(xué)術(shù)研究的重要對象,也逐漸內(nèi)化,成為我內(nèi)心世界的重要部分。每當(dāng)人生跌入困頓之谷,莊子的理念總是成為我最大的精神支柱,支撐我繼續(xù)前行。”(陳鼓應(yīng):《莊子今注今譯》,商務(wù)印書館2007年,修訂版序)陳先生的這番話促使我開始反思,做學(xué)術(shù)如果陷入文字的堆砌和義理上的無病呻吟,實在可惜,相對地,我們應(yīng)該積極尋求讓經(jīng)典內(nèi)化的方法。劉笑敢曾指出:“莊子很可能是借用當(dāng)時的氣功式健身術(shù)的修煉方法來發(fā)展自己的逍遙游理論的,他的逍遙游的境界很可能與氣功入靜以后的自我體驗有相通之處。”(劉笑敢:《莊子哲學(xué)及其演變》,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0年,第3頁)在對莊子哲學(xué)思想的內(nèi)化和運用上,對古中國修煉方法的繼承和發(fā)展上,我們應(yīng)當(dāng)注意到,道教的丹道修煉是非常值得稱道的。但是,這方面的研究還遠(yuǎn)遠(yuǎn)不夠,而本人學(xué)識也有限,不敢就《莊子》全篇展開討論,暫時以《逍遙游》為研究中心,以道教的丹道為切入點,試著對《逍遙游》進(jìn)行分析和解讀。
一、 何謂逍遙游
逍遙游既是首篇之篇名,亦是全書的一個核心理念,若要探討相關(guān)的東西,弄清究竟何謂逍遙游是必不可少的。
古往今來,很多人都就此問題進(jìn)行過研究,并各有結(jié)論。目前學(xué)術(shù)界的主流觀點認(rèn)為,莊子的逍遙游,其實質(zhì)是精神自由,且兼具消極與積極的色彩。陳鼓應(yīng)認(rèn)為,莊子的逍遙游是一種極高明的精神境界,其特點是順應(yīng)自然。莊子正視人類現(xiàn)實里的不幸,從而構(gòu)建出了一個精神上的自由世界,使人擺脫外在的苦難。在劉笑敢看來,莊子提倡通過修煉心靈來擺脫現(xiàn)實中的束縛與苦痛,他的逍遙游是一種心境突破后的精神自由狀態(tài)。在劉笑敢那里,他承認(rèn)莊子思想中確有消極一面,但這卻是因為莊子經(jīng)歷并洞察了現(xiàn)實生活與個體生命的不自由。于社會發(fā)展而言,這種逍遙也許是消極的,但這本就不是莊子的關(guān)注點,莊子是為了讓人實現(xiàn)自我的內(nèi)在超脫才寫下這些文字。因而,在對生命意義的探討和人心的修煉上,莊子的逍遙游又是無比積極的。陳來的觀點也相差不大,他認(rèn)為莊子所追求的是精神之自由和解脫。
但是,莊子本人從未說過,他追求的就是精神自由。甚至,我們也可以說他不追求道,他只是在描述修道的方法和得道的境界。在人修道的過程中,確要先求道,但繼而要放下和忘掉求道;而這種放和忘既不是有為的,也絕不是消極的,難以描述,故莊子多寓言。所以,我們閱讀莊子,不僅要明白他的話是什么字面意思,他的故事講了什么,更要學(xué)會破相,去體悟莊子借相立言的真意。在老莊那里,道是先天的,是混沌玄妙而無法言說的,超越物質(zhì)和精神之概念。所以,筆者私以為莊子的思想絕不會僅僅停留在精神超脫上。在閱讀了道教的丹經(jīng)之后,這種感覺尤為強烈。丹道中煉虛一步功夫圓滿后,渾不知神與虛是二是一,猶如莊周夢蝶,不知蝶為周,還是周為蝶。以丹經(jīng)言之,“吾神即太虛之虛,太虛之虛亦即吾神之虛”(黃元吉著,董沛文主編:《道門精要》,華夏出版社2016年,第14頁)。人修至這般境界,即可遷神出舍,游于無窮,道教謂之出陽神。從莊子書中描述的情況來看,相比于寬泛的精神超脫之概念,丹道功夫的陽神出游境界,和莊子的逍遙游更為接近。
二、 鯤鵬之喻
逍遙游里有種廣為人知的神物,即鯤鵬。從字面內(nèi)容上看,鯤鵬是種一而二,二而一的神異存在,它既可以是魚,也可以是鳥。除此之外,鯤鵬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大,而且是未知的大。在逍遙游中,這般神異的鯤鵬,所行之事說來卻極質(zhì)樸。用一句話概括就是,它自北冥之中由魚化鳥,借助風(fēng)力飛往南冥。以《莊子》本身內(nèi)容而言,有幾點值得推敲。逍遙游后面提出了無所待而游乎無窮的境界,那么在全書的最開始,他為什么要讓鯤鵬借著風(fēng)力而起,又為何讓它從北冥遷往南冥。對此,我們固然可以找出很多解釋,只要言之有理,自無不可。但是,奇妙的是,這短短的寓言卻與丹道修煉的核心內(nèi)容緊密相關(guān),若合符契。而且,道教丹道的一大特點就是嚴(yán)謹(jǐn),既講義理,也講實證,這種契合尤為值得深思。莊子很可能將當(dāng)時中國的內(nèi)煉方法和自己證得的境界,寫進(jìn)了逍遙游中。這種內(nèi)在的聯(lián)系,使得道家道教有了實質(zhì)上一脈相承的東西,而不是所謂的義理攀附,或者哲學(xué)宗教之分。
概而言之,丹道以性命雙修為根本,功夫有幾個層次,即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合道。鯤鵬的形象本身就寓意著性命本是一體,不可偏執(zhí)一端。鯤鵬同時也代表著先天一炁和先天真性,變化莫測,廣大無邊。陰長生注《周易參同契》有言:“水得火而升騰,金居水而潛匿,遞相變化,凝結(jié)器中也。”(魏伯陽著,朱熹等注:《周易參同契集釋》,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年,第8頁)就人身而言,下丹田就是北冥海底,人在色身虧損或心性不純的情況下,先天一點乾金藏于水底,即鯤宿北冥。逍遙游中,六月息為海氣動,氣動則風(fēng)起,鯤乘此時節(jié)方可化鵬沖舉。海氣動,為天地陽氣積聚到一定程度自然發(fā)生的,此為天地造化之機(jī)。于人身,丹道功夫亦然,欲還先天,先固后天,色身保養(yǎng)好了,精氣神充足則自然真機(jī)動,而后真陽生發(fā),一路向上,自臍至眉目皆有晃朗白光。鯤鵬自北冥至南冥,于丹道而言,便是移爐換鼎。丹法修行始于下丹田煉精化氣,終于上丹田煉神合道。逍遙游后文有言,水風(fēng)之積若不厚,則不能承負(fù)大舟大翼。丹經(jīng)則強調(diào),精氣之積若不足,則無以洞見本來面目。
由此可見,鯤鵬在逍遙游中絕非僅僅是一種瑰麗的幻想產(chǎn)物,更有可能是莊子借此來描述其身心修養(yǎng)功夫中的體驗。
三、 小大之辨,開拓胸次
莊子在描述完神秘的鯤鵬之后,筆鋒一轉(zhuǎn),寫到了蜩與學(xué)鳩這兩種小生物對鯤鵬的譏諷。后面,莊子又進(jìn)一步引出冥靈、大椿、彭祖這些傳說中的生命悠長的存在,并和朝菌、蟪蛄、眾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從內(nèi)容上看,莊子希望通過小大之辨來說明造化之神奇,指示人們放下個人有限的見解,打開心量,如此便可見識到更廣闊的世界。丹道東派祖師陸西星在注莊子時認(rèn)為,每個人的心體本都是廣大的,只不過人們大都被個人意見所束縛,于是不見廣大之心,只剩狹小的己見。茅山上清派陶弘景則說:“不以人事累意,不修仕祿之業(yè),淡然無為,神氣自滿。”(陶弘景著,王家葵校注:《養(yǎng)性延命錄校注》,中華書局2014年,第59頁)個體的意見在道教看來是后天的識神,只有去掉后天的意見,心性返于自然,先天的元神方能顯現(xiàn)。元神主事之后,人便從有欲的狀態(tài),轉(zhuǎn)變?yōu)闊o欲的狀態(tài),只有在這個狀態(tài)下修煉內(nèi)丹才是真功夫,否則只是幻丹,難以長保。這一段功夫在丹經(jīng)中被描述為:“心性一返于自然,斯后天之精氣亦返為先天之精氣。”(黃元吉著,蔣門馬校注:《道德經(jīng)注釋》,中華書局2012年,第81頁)
四、境界的轉(zhuǎn)變
小大之辨后,莊子將批判的對象從小蟲轉(zhuǎn)變?yōu)槭篱g的一些有成就之人,認(rèn)為他們對自身的認(rèn)知,在本質(zhì)上和前面所述的小蟲沒什么區(qū)別,都只不過是局限在自身的眼界之中而已。隨后,莊子寫到兩個人,一為寧榮子,一為列子。這兩人相較于世間的人,境界又要更高,但莊子認(rèn)為他們還是有不足。寧榮子定而未能忘定,辨而未能忘辨;列子雖可御風(fēng),但同時也必須憑依風(fēng)。最后,莊子提出了三種理想的人生境界,即至人、神人和圣人。在莊子那里,這三種境界應(yīng)該是并列的,并以“無”相通。道教的丹道修煉則進(jìn)一步把莊子的思想細(xì)化,如翁葆光注《悟真篇》:“后天地生有形有質(zhì)者,皆非至藥。蓋形而下者,非先天之道也。”(張伯端著,翁葆光等注:《悟真篇集釋》,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年,第17頁)同時,莊子所提及的境界也被道教吸收和改造,加入到丹道修煉的體系中去,并有了層次高低之分。《洞玄靈寶定觀經(jīng)》將修道的境界劃分為七個層次,其中沒有提到圣人,但神人和至人分別是第六和第七階段,分別代表著練氣成神和練神合道,都是極高的境界。
五、神人與中和
莊子在《逍遙游》中塑造了一種美好的形象,即姑射神人。在《逍遙游》中,他對姑射神人用了很多女性化的描述,但卻從未正面說過其性別。值得注意的是,古代在描述男性得道者時,常常使用女性化的描述。其實,在丹道修煉的理論中,人修煉內(nèi)丹,會逐漸模糊性別特征,男性在外表上會女性化,女性則會男性化。但是這種變化實質(zhì)上是平和自然的,而非不健康的身心變化。在陸西星看來,姑射神人之所以能夠?qū)崿F(xiàn)很多神跡般的事情,是因為他修到了練神的境界,從而自然達(dá)到“中和”的狀態(tài),并對周遭萬物產(chǎn)生良性影響。陸西星認(rèn)為:“其神凝,則中至而和亦至矣,故天地自位,萬物自育;和氣熏蒸,物無疵癘,而年谷熟。”(陸西星著,蔣門馬點校:《南華真經(jīng)副墨》,中華書局2010年,第8頁)“中和”是儒家《中庸》里的概念,而陸西星對“中和”的解釋更加偏向于內(nèi)丹修煉,強調(diào)神氣。儒家解釋“中和”又是另一番氣象,如朱熹認(rèn)為:“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fā),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fā)皆中節(jié),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第18頁)
六、無何有之鄉(xiāng)與道鄉(xiāng)
在《逍遙游》的篇末,莊子提出了無何有之鄉(xiāng)的概念。這個無何有之鄉(xiāng),在道教被認(rèn)為是比喻道之本鄉(xiāng)。丹道中,無何有之鄉(xiāng)絕非是一種虛幻的描述,相反,丹家認(rèn)為至虛之中有至實,至無之中有至有。丹家修行,不僅要煉精氣神,也要見真性。但是,性微無跡,難以捉摸,為了見到真性,人必須排除各種雜念妄想,進(jìn)入靜定的狀態(tài),即無何有之鄉(xiāng)。在無何有之鄉(xiāng)這個概念上,丹道修煉把老莊緊密地聯(lián)系了起來,那就是用“致虛極,守靜篤”來進(jìn)入無何有之鄉(xiāng)。河上公將“致虛極,守靜篤”注解為:“道人捐情去欲,五藏清靜,至于虛極也。守清靜,行篤厚。”(李耳著,河上公等注:《道德經(jīng)集釋》,中國書店2015年,第21頁)雖然名為無何有,但莊子卻要在這個無何有之鄉(xiāng)里種上一顆大樹。丹家亦然,在進(jìn)入靜定的狀態(tài)之后,又不能落于頑空,須在空洞無邊中尋出端倪,找到一個光明不昧者,這就是那棵大樹。但道教的丹道并未停留于此,丹家認(rèn)為這些只是丹道修煉的某個階段,等到丹道大成之后,究之何有何無,話到嘴邊,就是純?nèi)巫匀欢选?/p>
結(jié)論
逍遙游不僅是莊子精神超脫的表現(xiàn),更是包含了其身心修養(yǎng)之功夫,無論里面的哲學(xué)思想,還是古中國的內(nèi)煉方法,都對道教的丹道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影響。道教在將道家思想內(nèi)化的過程中,也在不斷進(jìn)行創(chuàng)新。最終,在先賢經(jīng)典的指導(dǎo)下,經(jīng)歷無數(shù)人的努力,完善的丹道修煉體系才得以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