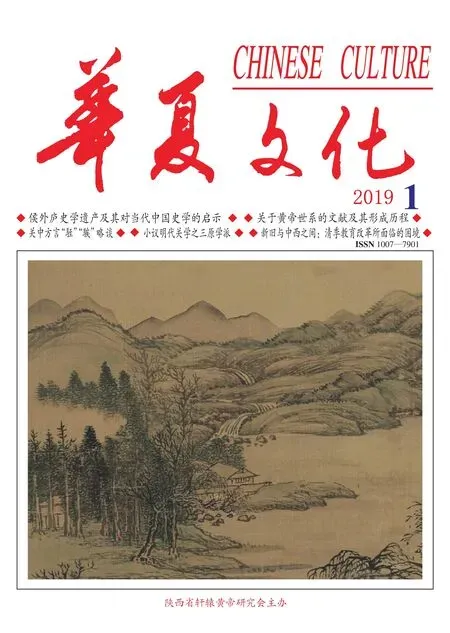氣質一元論
——淺析戴震的人性論
□劉 育
戴震字東原,是清代著名的考據學家、哲學家。胡適先生認為其思想對近代以來束縛人性的宋明理學具有根本革命的意義(參見胡適:《戴東原的哲學》,載《胡適文集》第7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這種革命意義充分表現在戴震的人性論思想中。關于戴震人性論的研究,學界多從細小處深入探究,并未將其人性論與其思想體系及當時的學術氛圍、時代背景相聯系,對戴震人性論與孟子“性善論”的比較也多言同,少言異,存在片面之處。本文擬從《孟子字義疏證》出發,對戴震的人性論從理論淵源、具體內容、意義影響幾個方面進行歸納梳理。
一、 戴震人性論產生的淵源
關于“性”的討論,一直是我國古代諸家學者研究的重點,尤其是儒家,對“性”的探討由先秦開始便一直延續,故戴震人性論的產生是有其歷史淵源的。
先秦時期,儒家先哲們就已經對人性產生了好奇,但由于時代條件的不同、人們思維水平的限制,對“性”的理解依舊是眾說紛紜的。在孔子那里,“性”是一個略帶神秘性的概念。遍觀《論語》,我們可以發現關于“性”的言論寥寥無幾。恰恰論證了子貢所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已矣”(《論語·公冶長》)。孔子直接提到“性”的就只有那句“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只是模糊地說明了環境與教育會對人性產生影響。而戴震卻見微知著地說道:“無人性即所謂人見其禽獸也,有人性即相近也,善也。”(《孟子字義疏證·性》)認為孔子的“性”是區別于禽獸的人性,故從孔子開始就有對人性的論述了。
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學說并在人性論方面作出發揮,他主張性善論,提出“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由此有學者認為孟子的人性“不只是自然生命,而且是自然生命所以然的本性”(張豈之:《中國思想文化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08頁),并以此為依據同主張性無善無惡的告子進行了多番辯論。在辯論中孟子以牛、犬、人三者之性是否相同詰問告子,并使其無言。這啟發了戴震的人性論,使其得出了“天道,陰陽五行而已矣;人物之性,咸分于道,成其各殊者而已矣”(《孟子字義疏證·性》)的觀點。
戰國末期的荀子主張性惡論,認為“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荀子·儒效》),提出“化性起偽”的概念。荀子理論上似乎與孟子的性善論背道而馳,但戴震卻認為荀子并“不知性之全體”(《孟子字義疏證·性》),認為其性惡論只是其尊崇圣人、倡導禮義學習的言論。并從荀子的人性論思想中推出“人性可善”的觀點。
荀子之后重視人性論探討的則是以二程、朱熹為代表的宋代學者。他們將人性論一分為二,分為“氣質之性”與“天命之性”。認為天命之性即是天理在人身上的體現,而氣分清濁,濁氣會掩蓋原本的天命之性,所以要通過“格物致知”修養身心以革除氣質之性,使人性回歸本始的純凈狀態。戴震與程朱的思想關系密切,他在二十歲前接受江永學派的教育,而入京后受顏李學派的影響對宋儒開始了批判,而人性論正是戴震批判宋儒的著眼之處。如胡適先生所說:“戴氏認清宋儒的根本錯誤在于分性為理氣二元,一面仇視氣質形體,一面誤認理性為‘天與我完全自足’的東西”(《胡適文集》第7冊,第261頁)。戴震也在《孟子字義疏證》中寫道“程子朱子其出所講求者,老、莊、釋也”(《孟子字義疏證·性》),指出宋儒多受佛、道影響,故其人性論重精神輕形體有情可原。在繼承與批判的基礎上,戴震撿起了宋儒不屑的“氣質之性”,建立起了自己的氣質一元論。
由上可知,戴震的人性論并不是天馬行空、平白而來的,而是奠基在多位儒學大家對人性的理解上的。他“既歸宗孔子、溝通孔孟,又融匯孟荀、擇善而從,還有直面程朱、針砭時弊……謀求人性理論中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的有機融合,實現中國傳統人性理論在更高層次上的深化與超越。”(陶武:《傳統人性理論再解讀——戴震人性可善論摭談》,《學術界》2014年第10期)
二、 戴震人性論的具體內容
(一)戴震對“性”及“性的實體”的定義
戴震對于人性論的具體表述多集中于《孟子字義疏證》卷中。從以下這段論述中,我們不僅可以清楚地看到戴震對“性”及其實體的定義,還可明白地讀懂其人性論的性質與根據。
性者,分于陰陽五行以為血氣、心知、品物,區以別焉,舉凡既生以后所有之事,所具之能,所全之德,咸以是為其本,故《易》曰:“成之者性也。”氣化生人生物以后,各以類滋生久矣;然類之區別,千古如是也,循其故而已矣……天道,陰陽五行而已矣;人物之性,咸分于道,成其各殊者而已矣。(《孟子字義疏證·性》)
戴震結合《易》、《大戴禮記》、《中庸》的論述對“性”下了一個定義——“性者,分于陰陽五行以為血氣、心知、品物,區以別焉”。也就是說“性”是由氣化為陰陽、五行之后經兩者相互雜糅而形成的,陰陽五行變化形成了多種類的人與物,由于種類之間的血氣、心知“有偏全、厚薄、清濁、昏明之不齊,各隨所分而形于一,各成其性也”(《孟子字義疏證·性》),“性”的種類雖然有所不同,但大致還是以類作為取去的標準。
“性”的實體也就是“血氣心知”,實際上就是指內在的思想和外在血氣的融合,即宋儒所排斥的“氣質之性”。不同于宋代儒學家所倡導的“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易·系辭上》),即將形而上的理與形而下的氣對立起來、帶有明顯唯心色彩的理氣二元人性論,戴震主張主觀與客觀的統一。他的人性論是帶有唯物主義色彩的氣質一元論。要真正理解戴震的人性論,僅僅知道其對“性”及其實體的定義是遠遠不夠的。我們應結合其對“道”與“才”的論述一并加以分析,才能深入把握戴震的人性論。
(二) 戴震人性論的性質及其依據
戴震人性論的性質要一分為二的進行理解。若以自然性或是先驗道德性作為評判標準,可知戴震人性論依據其“天道”觀念而得,是一種唯物的氣質一元論;若以善、惡為評判標準,可知戴震的人性論與其對“才質”的論述息息相關,據此而得出了“人性可善”的理論。
1.唯物的氣質一元論
戴震的人性論脫胎于他的“天道”觀。他的“道”并不像老子、莊子等人的“道”那樣帶有神秘色彩,也不像孔子、孟子的“道”那樣滿是仁義禮智,更不像宋儒的道一樣是形而上的萬物唯一依據的“天理”。他說:“道,猶行也;氣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謂之道。”(《孟子字義疏證·天道》)這表明他的道蘊含著兩種意思:“一是天道,一是人道。天道即是天行,人道即是人的行為。”(《胡適文集》第7冊,第254頁)戴震從《易·系辭》建立自己的天道觀,竟與荀子“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荀子·天論》)的天命觀不謀而合。戴震認為無論是形而上的還是形而下的氣化流行都是“道”的運行,這實質上是一種唯物的、自然主義的宇宙觀。
這種天道觀的唯物性質、自然特性無可避免地體現在戴震對人性論的認識上。天道運行依托于陰陽的運轉(陰陽是古人觀察自然界各種對立又關聯的現象而得出的概念,屬古代樸素唯物論),而“性”又分于陰陽以為血氣、心知雜糅而成。他又在《原善》中提出:“耳目百體之所欲,血氣資之以養,所謂性之欲也。……由性之欲而語于無失,是謂性之德。性之欲,其自然之符也。性之德,其歸于必然也。歸于必然適全其自然。此之謂自然之極致。”(《原善》卷上)其中明確指出血氣即是性之欲,是自然性的體現;心知即為性之德,可以指導自然的性之欲使其“無失”,這也是自然達到極致的體現。所以說,指導戴震人性論的天道觀是自然唯物的,化成“性”的陰陽五行也是樸素唯物的,就連構成“性”的實體的“血氣心知”都是自然的,戴震的人性論是唯物的氣質一元論便不言自明了。
2.人性可善論
前文已經提及,戴震的人性論有其歷史淵源,并且他認為孔子雖然慎言“性與天道”,但其“性相近”三字就足以表明孔子認為人性是有別于禽獸之性的。戴震說禽獸與人雖都由血氣心知成其性,但由于氣“有偏全、厚薄、清濁、昏明之不齊”(《孟子字義疏證·性》),禽獸之性與人性大相徑庭:“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限于知覺也”(《孟子字義疏證·性》),而人則可以擴充心知而擁有種種美德。因此戴震認為孔子所言“性相近”實際就是在說人性善。除此之外,戴震還在書中多次引用孟子言語佐證自己的人性論,并在孟子和告子爭辯幾千年后依舊為孟子辯護。這些足以看出戴震也主張性善論。
不同于孟子將性善論看成是絕對的,是人人生而有之的“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戴震性善論的絕對性只針對于禽獸之性而言,兩者的性相比,人性是善的。在更多情況下,戴震的性善論可從其對“才質”的論述中深入理解。他對“才”下的定義是“才者,人與百物各如其性以為形質,而知能遂區以別焉”(《孟子學義疏證·才》),認為這就是孟子所說的“天之降才”。也就是說才是性的表現,有什么樣的性就會表現出什么才質,就像桃樹只能開出桃花結出桃子而無法長出李子一樣,禽獸在趨利避害、保存生命方面的能力可能與人類相似,但卻無法像人類一樣擁有修德向善的才能,這就是因為“性”不同所以“才質”也不同的體現。
反過來講,才質的好壞也會影響到性的善惡,戴震的人性論是以才質為基礎的。他在《原善》中說:“耳能辨天下之聲,目能辨天下之色,鼻能辨天下之臭,口能辨天下之味,心能通天下之理義,人之才質得于天,若是其全也。”(《原善》卷中)這即是說明人的耳目口鼻心都有分辨好壞的能力,從而趨向更善的一方。故戴震的性善在人性方面并不是絕對的,只是因為人人都同有那些“可以知之性,可以具之能”,所以人人之性皆有“可善”性即為善的可能性。
綜上所述,戴震的“性善”只是針對禽獸之性與人性的比較而言,他的人性論實際上是基于“才質”的性可善論。
三、 結語
戴震以其氣質一元論批判程朱的理氣二元論,其現實意義是顯而易見的。儒學發展至宋明時期,思想已漸趨保守僵化,尤其是朱熹等人以天理禁錮人欲,用過頭的禮儀道德束縛人性,形成了冥頑迂腐的社會風氣。戴震年輕時受江永學派影響頗深,自然對宋儒言論有認可與繼承之處,但他又隨著時代變化受到顏李學派的影響,隨著清初實用主義的盛行而漸漸走上了對程朱進行批判的道路。戴震對程朱的批判是從天道開始的,但論述的重中之重則是關于人性,其目的則在于打破思維束縛“倡導‘體民之情,遂民之欲’的王道政治,回歸原始儒學的人本精神”(吳磊:《從義理之性到血氣心知:朱熹與戴震人性論的比較》,《蕪湖職業師范學院學報》2016年第2期)。
戴震的人性論是用自然主義的哲學思維去解釋人性的,也是其哲學思維的主要組成部分。在前文我們已經深入介紹了其人性論較之前人的進步性,卻并未對其缺陷進行評判。正如胡適先生所說:“戴氏的氣質一元的性論確是一種重要的貢獻,但他終不肯拋棄那因襲的性善論,所以不免有漏洞了。”(《胡適文集》第7冊第263頁)他的人性論實際上是一種“性可善”論,但他卻始終要用孟子的言語進行解釋。我們都知道孟子的性善論是具有先驗的道德性的,這就導致了兩者人性論的某種不可調和,在這種情況下,戴震仍舊堅持用自己的思想來為孟子立言,這造成了其人性論的缺陷。
總的來說,戴震的人性論仍然為我國古代儒學家對人性的探討注入了新鮮的血液,“在中國哲學史上,戴震是第一個從‘血氣心智’上為人性學立論的學者”(王智汪:《從血氣心智到內心和諧:論戴震的人性論》,《北方論叢》2011年第2期),他把人的屬性與自然聯系起來,從而推進了現代哲學的發展。直至當代,戴震的人性論依然對個人義利觀以及現代人格的培養具有啟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