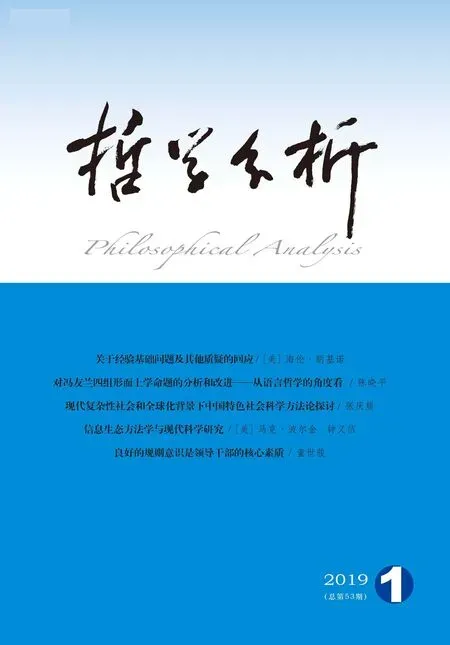論康德的建構性與范導性之劃分①
陸心宇
在康德哲學中,建構性—范導性之劃分與眾多議題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然而,它受到的重視程度遠不及其他康德式的二分法(諸如,現象—本體、直觀—概念、形式—質料)。那么,什么是建構性—范導性之劃分?任何一種簡化的回答都有著誤讀的風險。弗朗茨(Stanley French)是最早重視該劃分的學者之一。他認為,建構性命題描述感官世界,并且可由經驗證據來驗證。范導性命題并非描述事實,而是規定(prescribe)規范,即我們應當如何思考和行為。范導性命題都是非指稱的(nondenotative)和不可證實的(unverifiable)。“對于許多當代哲學家而言,一個關鍵問題在于如何理解那些由非指稱性語言所建構的并且不可證實的斷言。人們很少提及,康德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而我認為,這就是建構性—范導性之界別的要義所在。”①Stanley G. French,“Kant’s Constitutive-Regulative Distinction”,The Monist,Vol.51. No.4,1967,pp.623—639.弗朗茨的問題在于:他把建構性等同為對事實的描述,但是鑒于在康德的哥白尼式轉向里,建構性主要指向認知能力;他把范導性理解為不可證實的,但在自然科學中理性之范導性的運用(即預設自然作為整體的合目的性)恰恰是為了設定有待證實的研究目標。盡管如此,弗朗茨有其獨到見地,即試圖為建構性—范導性提供一種非康德行話的解釋,并且展現它與分析哲學(譬如吉爾伯特·賴爾的工作)之間的相通 性。
鑒于弗朗茨的得失,筆者試圖綜合而具體地描繪建構性—范導性在康德語境中與主要問題之間的關聯。概括地說,在這些語境里,建構性—范導性之語用形式為:“X是范導性的,而非建構性的。”在超驗領域,當理性的應用是范導性的而非建構性的,則它是正當的;反之,當建構性與范導性之關系顛倒,它是越界的,為理性之誤用。在這個劃分里,康德表達了對理念的雙重態度:借助對建構性原則之否定,他否認理念之實在性,拒絕承認一個與現實世界相平行的柏拉圖式的洞外世界;借助范導性原則,他承認理念之理想性,并借此鼓勵柏拉圖式的轉身。對此,康德寫道:“這里表現出在同一個預設那里思維方式的一種差別,這種差別相當細微,盡管如此,在先驗哲學中卻十分重要。我可以有充足的根據相對地假定某種東西(suppositio relative),但卻沒有權限絕對地假定它(suppositio absoluta)。如果所涉及的是一條范導性的原則,這種區分是對的;我們雖然認識它就自身而言的必然性,但卻根本不認識這種必然性的源泉,而我們假定一個至上的根據,僅僅是為了與——例如——當我把一個與純然而且先驗的理念相應的存在者設想為實存著的時候相比,更為確定思維原則的普遍性。”②KrV B 704. 本文對《純粹理性批判》的引用一般以B版頁碼為準,除專屬A版者。鑒于中譯本在頁邊也標注了學院版頁碼,對康德其余著作的引用則以“學院版卷數+頁碼”為格式。本文采用李秋零譯本。康德:《純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458頁。簡言之,該劃分表明:“X存在”并非“X有意義”的必要條件。作為理念,X之意義在于它作為實踐的啟迪,而非關于事實的斷 言。
一、信念作為理性之范導性應用
康德哲學的基本問題匯聚于理性的三個興趣:“(1)我能夠知道什么?(2)我應當做什么?(3)我可以希望什么?”③KrV B 833.建構性—范導性之劃分與它們全部相關。就知識而言,第一批判的基本問題是探討:“知性和理性脫離開一切經驗能夠認識什么、認識多少?而不是:思維的能力自身是如何可能的?”④KrV A XVII.由此,康德試圖對傳統形而上學之可能性或不可能性,及其在人類理性能力中的起源、范圍、界限加以界定。①KrV A XII.這項工作的特征可概括為一段著名的話,即限制知識,從而為信念留出地盤。②KrV B XXX.然而,這是一段極其容易引發誤讀的話。一方面,作為限制對象的知識不是科學知識,而是形而上學的獨斷論,“即認為無需純粹理性的批判就在形而上學中前進的成見”③Ibid.。它在本質上把道德實踐所需的公設轉變為顯象。這種轉變的本質是把理性的范導性偷換為建構性。另一方面,康德的信念概念不同于通俗意義上的宗教信仰,其本質是理性的范導性原則。綜合來看,康德把信念置于意見與知識之間。意見(Meinen)是在主觀和客觀上皆不具有充分根據的判斷;知識(Wissen)則在兩方面皆有充分根據。相比之下,“如果視之為真只是在主觀上充分,同時又被視為客觀上不充分的,那它就叫做信念(Glaube)”④KrV B 850.。
具體而言,康德區分了三種信念。實用信念是為日常生活之行動奠基的信念,并且它的有效性是偶然的,比如臨床醫學中的診斷。⑤KrV B 852.學理信念是在主客體關系之中“實踐判斷的類似物”⑥KrV B 853.,它是寓于思想之中的行動,比如:關于自然在整體上的系統性與合目的性是一個學理信念,它可以激勵科學研究具體地去證明它:面向具體的問題建立假說并且實驗驗證。但是,如果人們把自然的目的論當作自然本身的屬性,那么他們實際上就是把有待證明的結果當作原因。這構成了理性的誤用。康德指出:“把自然的系統統一性的范導性原則當作一個建構性的原則,并且實體性地把僅僅在理念中被奠定為理性的一致應用之基礎的東西預設為原因,這就叫做使理性混亂。”⑦KrV B 721—722.在此學理性的信念是理性的范導性應用,它適用于自然科學。弗朗茨認為范導性是不可證實的。然而,雖然自然的合目的性不可能一勞永逸地被證實,但是它在個案中可能具體地得到驗證。并且,就科學史的成就而言,這種可能性是有擔保的。道德信念是指在實踐理性的法則與意圖之間建立關聯的公設。并且,它們是“純粹理性的信念,因為惟有純粹的理性(不僅在其理論應用上,也在其實踐應用上)才是這種信念由以產生的源泉”⑧V 126.(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康德:《道德哲學文集》,李秋零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96頁。。就德性與幸福之間的統一而言,它只能是基于公設的信念,而非確信的知識。這意味著:一方面,它之實存缺乏完全的確定性;另一方面,它仍然是可能的,并且這種可能性對道德有著一種消極的助益,即既然人們無法確定地否認德福統一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本身就“雖然并不造成道德性和善的意向,但畢竟能夠造成它們的類似物,也就是說,能夠有力地遏制惡的意向的發作”①KrV B 858.。
由此可見,無論學理信念抑或道德信念,它們都源自理性的范導性應用。事實上,康德認為信念本身就是源于理念的指導。他寫道:“信念一詞僅僅關涉一個理念給予我的指導,關涉對我的理性行動之促進的主觀影響,這種促進使我堅守這個理念,盡管我在思辨方面沒有能力對它做出解釋。”②KrV B 855. 黑體為筆者所加。無論是出于對信念的解釋,抑或對范導性的探究,我們都有必要進一步考察什么是康德意義上的“理 念”。
二、物自身與理念
康德的物自身概念對應于柏拉圖傳統中的理念。在康德視閾里,理念即理想,或者說,理念之合理性在于它是指導行動的理想,亦即理性之范導性應用。康德寫道:“……人的理性不僅包含理念,而且也包含理想,這些理想雖然不像柏拉圖的理想那樣具有創造性的力量,但畢竟(作為范導性的原則)具有實踐的力量,并且為某些行動的完善性的可能性奠定了基礎。”③KrV B 597.另外,理想撇開了寓于理念之中的實體性。“對我們來說是一個理想的東西,對柏拉圖來說就是一個屬神知性的理念,是這種知性的純粹直觀中的一個個別的對象,是任何一種可能的存在者的最完善者,是顯象中一切摹本的原型。”④KrV B 596.這種實體性的因素則歸咎于理性之建構性的應用。康德對待理念與理想的雙重態度寓于其物自身的思想,并且在終極意義上理想即物自 身。
并且,在嚴格意義上,物自身即理想,并且“它也是人類理性所能有的唯一真正的理想”⑤KrV B 604.。物自身是一切實存的基礎和根據。它是“可能性的至上的和完備的質料條件”⑥Ibid.。若沒有它,那么“就會從中得出荒謬的命題:沒有某種在此顯現的東西卻有顯象”⑦KrV B XXVI.。康德以物自身為表象之根據,并且借以避免貝克萊式觀念 論。
關于現象與物自身的二元論,皮平(Robert Pippin)指出,康德的立場是雙重的:一方面他否認思辨理性能夠直接達到物自身,另一方面他要求至少能夠就物自身而思維(think about)。①Robert Pippin,Kant’s Theory of Form:An Essay on 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2,p.189.這牽涉關于康德哲學的古老爭論:既然我們無法認識物自身,那么又如何可能設想它之存在乃至各種規定性?事實上,在康德的批判哲學里,至少有兩類關于物自身的規定性:其一是先驗分析論以物自身為表象之原因或根基的論斷,其二則是先驗辯證論以范導性的原則設定先驗理念的體系。對此,皮平給出了三點解釋。首先,在物自身的問題上,康德訴諸反思而非認識。反思是純粹形式的,因而不包含任何朝向超越現實的形而上學跳躍。其次,在反思之中,物自身是范導性的而非建構性的理念。再次,物自身的概念是否定性的概念。②Ibid.,pp.189—190.
范導性的觀念在確立物自身概念中起到關鍵作用。皮平指出:正是基于對表象的“范導性”思考,才促使康德斷言表象必然有其超感官的根基,從而物自身可以被設想為現象的智性基礎(the intellectual substrate of phenomena)。物自身是不可認識的,但卻可以被思維,并且這種思維是范導性的。③Ibid.,p.210.
在康德的批判體系中,物自身的概念有著兩重意蘊:其一是作為表象的根據,其二是作為道德實踐的指導。(事實上,這也是柏拉圖式理念的雙重意義。在《論尼采之言:“上帝死了”》一文中,海德格爾認為“上帝”是指柏拉圖式感性—非感性的二分法中的非感性的理念,并且把這個二分法界定為歐洲形而上學傳統的基本結構。)作為表象的根據,物自身是思想所確立的邏輯可能性。它尚非現實的,因為物自身是不可認識的。然而,作為實踐的指導,物自身則在道德決斷中獲得現實性。“但是,要賦予這樣一個概念以客觀有效性(實在的可能性,因為前面那種可能性僅僅是邏輯的可能性),就要求某種更多的東西。但這種更多的東西恰好不需要在理論的知識來源中尋找,它也可能存在于實踐的知識來源之中。”④KrV B XXVI n.
然而,純粹理性在實踐意圖中的擴展并不擴展思辨知識的范圍。也就是說,雖然道德實踐可以達到物自身的理想領域,但不能擴展知識。這是康德所謂“限制知識,為信念留出地盤”的道德含義。建構性—范導性的劃分則在存在論的層面刻畫了思想的這一狀況:理性之范導性應用使得實踐遵循理想,就好像理念世界存在似的;但是,這些理念本身并沒有客體和實在性,它們僅僅是為指導行動而設置的理論可能性。康德對此明確寫道:“……因此,純粹理論理性必須把上述知識的增長僅僅歸功于它的純粹實踐能力,而對它來說,所有那些理念都是超驗的,都沒有客體。在純粹實踐能力這里,它們都成為內在的和建構性的,因為它們都是使純粹實踐理性的必要客體(至善)成為現實的那種可能性的根據,除此之外,它們就是超驗的,是思辨理性的純然范導性原則,這些原則責成思辨理性的事情,并不是超出經驗之外去假定一個新的客體,而僅僅是使它在經驗中的運用接近完備。”①V 135.(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基于上述初步分析,建構性—范導性是涉及康德如何理解理念、本體、物自身等超驗領域的一對重要劃分。一方面,他避免獨斷論,為此拒絕理念之實在并否認一個與現實世界相平行的理念世界;另一方面,他也避免懷疑論,為此保留理念之理想,并且承認理念在知識與價值中的指引作用。簡要地說,在這對劃分里,康德的基本觀點可概述為:“X存在”并非“X有意義”的必要條件。具體地說,它涉及康德對形而上學批判、道德實踐、自然科學等不同語境中的問題。接下來我們依次考 察。
三、理念之批判
對于康德而言,理念既有其積極的意義,又是形而上學批判的標的。就積極的意義而言,理念是啟迪,它能夠指引科學研究和道德實踐。就批判而言,理念誘惑著理性逾越經驗的界限,乃至進入無條件和無限的物自身的領域之中。康德借用建構性與范導性之劃分來維持這兩者之間的平衡:理念是范導性的,而非建構性 的。
理念是科學研究與道德實踐中的啟迪。康德寫道:“以這樣的方式,理念真正說來只是一個啟迪性的概念,而不是一個明示性的概念,它所說明的不是一個對象有什么性狀,而是我們應當如何在它的引導下去尋找一般經驗的對象的性狀和聯結。”②KrV B 699.就其理論應用而言,理念是自然研究中的范本,它激勵人們去具體地驗證對自然的整體性、合規律性、合目的性等假設。“就像理念提供規則一樣,理想在這樣的場合也可以用做摹本無一例外的規定的原型……”③KrV B 597.就其實踐應用而言,理念是純粹德性的原型。“德行以及伴隨它的人類智慧,在其完全的純粹性上,就是 理念。”④Ibid.
作為啟迪,理念是有意義的,但這并不意味著理念存在。用通俗的話來說,理念是作為“就好像”而有啟迪意義的:它促進人們的自然研究與道德實踐就好像它們存在似的。理念并非實體,因為理念是越界的,而我們無法認識其實存。但它可以作為范導性原則。康德寫道:“理念對于我們的理論認識能力來說是越界的,但在這方面卻絕不是無用的或者可以缺少的,而是用做范導性的原則……”⑤V 167.(Kritik der Urteilskraft)康德:《判斷力批判》,李秋零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頁。
康德用建構性—范導性之劃分明確強化這一點。“據此我斷言:先驗理念絕不具有建構性的應用,以至于某些對象的概念會由此被給予,而且如果人們這樣來理解它們,它們就純然是玄想的(辯證的)概念。與此相反,它們具有一種杰出的、對于我們來說不可或缺的必然的范導性應用,也就是說,使知性指向一個目標,知性的一切規則的方向都參照這一目標而匯聚于一點,盡管這個點只是一個理念(focus imaginarius),知性的概念實際上并不是從它出發的,因為它完全處在可能經驗的界限外面,盡管如此,它仍然被用來給知性概念帶來一種與最大的擴展相伴的最大統一。”①KrV B 672.
在建構性與范導性之間的混淆構成了傳統形而上學的先驗幻相。根據艾美里克斯(Karl Ameriks)的詮釋,在傳統形而上學里,其思維模式的特點是尋求無條件者的理念,它源于條件序列之完備性的訴求。但是,它的謬誤在于把“主觀的必然性”當作物自身的“客觀的必然性”②KrV B 353.。實際上,康德把物自身的規定性等同為無條件者,并且無條件的主體的理念具體化為三個理念,即靈魂、宇宙、上帝。對于第三個理念,艾美里克斯寫道:“……思想之無條件起源的觀念轉變為了‘一切存在者之存在’的理念,即上帝。”③Karl Ameriks,“The Critique of Metaphysics:Kant and Traditional Ontology”,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ant,edited by Paul Guy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p.249—279.
具體而言,康德的形而上學批判指向三個理念:靈魂、宇宙和上帝。靈魂的概念是一個關于理智對顯象具有統一性的范導性概念的圖型,從而只是好像現實的存在者。“實體的那種單純性等應當只是這種范導性原則的圖型,不是被預設得好像它是靈魂屬性的現實根據似的。”④KrV B 711.作為范導性概念,靈魂是表象之統一性,“把一切規定視為在一個唯一的主體之中的,把一切力量盡可能地視為從一個唯一的基本力量派生的,把一切變遷視為屬于同一個持久的存在者的各種狀態的,并且把空間中的一切顯象表現為完全有別于思維的行動的”⑤KrV B 710.。但是,靈魂只是“好像是一個實在的存在者”⑥KrV B 712.,而非現實的實體。換言之,當靈魂從作為統一性的能力轉變為了單一實體,這就構成了一種誤讀,其實質是把范導性原則替換為建構性原 則。
理性的第二個范導性概念是世界。它是一個具有完備性的理念,但是這種完備性并非經驗所給予,也無法在經驗中完全實現。作為一個整體的世界是范導性的原則,它設定世界作為完備的一些序列。但是,這并非現實的,或者說“不是仿佛建構性地設定這樣一些序列的一個現實的總體性”⑦KrV B 713.。
理性的第三個范導性概念是上帝,“作為一切宇宙論序列的唯一的和極為充足的原因”①KrV B 713.。它是認識論上的假定。人們據此把世界看作一個合規律的、合目的的、有著充足原因的整體。但是,“在這一理念之下沒有隱藏著任何其針對可能經驗的應用的建構性原則”②Ibid.。也就是說,它的意義并不蘊含著存在。人們只是按照“就好像它存在”的方式來思考世界作為一個合理的整體。康德寫道:“僅僅依據理性概念的那種最高的形式統一性,是事物的合目的的統一性,而且理性的思辨旨趣使得有必要如此看待世界上的一切安排,就好像它出自一個至高無上的理性的意圖似的”③Ibid.,以及“就好像這個世界作為最高的理智按照最智慧的意圖是一切事物的原因似的,來達到最高的系統統一性”④KrV B 716.。就這個范導性概念的作用而言,它在自然研究中激勵理性去探索目的和原因。“……我們有一種目的論聯結的系統統一性的范導性原則,但我們并不事先規定這種聯結,而只可以在對這種聯結的期待中按照普遍的規律追尋自然機械論的聯結。”⑤KrV B 719.
根據蓋伊(Paul Guyer)與伍德(Allen Wood),如果人們把“先驗辯證論”的結論看作完全否定性的,那么這就是一種誤讀。“在辯證論之附錄里,康德開始有限地恢復傳統形而上學的理念,為此論證:理性的各種理念在自然科學的活動中有著重要的功能,如果它們被范導性地(regulatively)理解……”⑥Paul Guyer,Allen Wood,“Introduction”,in Kant,Critique of Pure Reas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18.這意味著:理性的理念不再被用于證明形而上學實體之存在,而是被看作理性在探索和形成知識過程中指示“目的與方向”(goals and directions)的路標。于是,在范導性的應用下,“靈魂”的理念指向對統一心理學的追求;“宇宙”的理念指向對科學研究領域的擴張;“上帝”的理念則指向世界在成因上是理性的,從而使人在經驗知識中力圖最大化秩序與連續性。不僅如此,“先驗方法論”還表明:理念之范導性應用有助于增強道德的根 基。
四、先驗辯證論的兩面
從上述回顧可以看出,建構性—范導性起著批判傳統形而上學的作用。但是,它又在范導性的原則里部分地保留了這種形而上學的傾向的合理性。可以說,在康德的批判里,形而上學的合理性被保存為理性之范導性,而其謬誤則歸咎于建構性。在此,我們將詳加論 述。
康德借助范導性概念部分地保留形而上學的合理性,因為它是一種源于理性本身的傾向。康德明確指出:“凡是在我們的力量的本性中有其根據的東西,都必定是合目的的,并且與我們的力量的正確應用一致,只要我們能夠防止某種濫用,并找到它們的真正方向。”①KrV B 670—671.在語境里,先驗理念一方面是理性越界所造成的幻相,另一方面則在理性本身之中有其合理性的根源。換言之,幻相并非源自理性本身,而只是歸咎于理性的誤 用。
在先驗幻相上,理性之誤用的本質是建構性與范導性能力之間的顛倒和混淆。康德進一步指出:“所以,一開始似乎僅僅向我們許諾把知識擴展到經驗的一切界限之外的純粹理性,如果我們正確地理解它,所包含的就無非是范導性的原則……但如果人們誤解了它們,把它們視為超驗知識的建構性原則,就通過一種雖然燦爛奪目但卻騙人的幻相而造成臆信和自負的知識,但由此也造成永恒的矛盾和爭執。”②KrV B 729—730.這會造成兩類錯誤:其一,理性之怠惰,即人們把作為行動原則的理想轉化為作為實體原則的理念,從而消除了理性之于行動的激勵作用。“由人們不僅范導性地,而且(這是與一個理念的本性相悖的)建構性地使用一個最高的存在者的理念所產生的第一個錯誤就是怠惰的理性(ignava ratio)。”③KrV B 717.其二,“理性之顛倒”(perverse ratio),即理性“預設了本來應當證明的東西”,乃至陷入循環論證。④KrV B 720—721.比如,自然之整體的概念是一個激勵人們在具體的經驗研究中去逐個驗證其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理想,但是當它被當作建構性原則乃至實體化為自然的形而上學屬性,那么這就是把有待證明的結果當作了現成的理由。正如康德所言:“……這樣一種系統的統一性的原則也是客觀的,但卻以不確定的方式是客觀的[principium vagum(不確定的原則)];不是作為建構性的原則,使人就它的直接對象而言規定某種東西,而是作為純然范導性的原則和準則。”⑤KrV B 708.要言之,在自然的統一性上,當它是范導性,它是合理的;當它是建構性,它是荒謬 的。
從建構性到范導性的轉換為二律背反提供了和解。以第四組二律背反(關于第一原因)為例,范導性原則意味著:一方面,感官世界是經驗而有條件的,并且對原因的回溯不會止步于任何一個經驗的部分,乃至把它當作絕對獨立自主的;另一方面,這并不否認“整個序列可能依據某個理知的存在者(einem intelligibelen Wesen) (這個理知的存在者因此而沒有任何經驗性的條件,毋寧說包含著所有這些顯象的可能性的根據)”⑥KrV B 589—590.。這里涉及康德關于“經驗性的性質”(empirischen Charakter)與“理知的性質”(intelligibelen Charakter)之間的界別:前者是指在感官世界中的主體是自然序列中的一個環節,處在廣泛的聯系之中;后者是指主體本身有著獨立于一切感性條件或獨立于表象的部分,它被稱作自在之物自身。①KrV B 567.
當代康德詮釋者亦特別強調先驗辯證論的上述兩面。艾美里克斯指出,康德對傳統形而上學的批判集中于《純粹理性批判》的先驗辯證論:“辯證論的要義在于揭露理性心理學、理性宇宙論、理性神學的具體謬誤,而對形而上學的批判和對反思與理性之運作的一般討論則導向了終結的原則:理論理性的一切超越單純內在時空領域(a merely immanent spatiotemporal field)的主張都應當被放棄。”②Karl Ameriks,“The Critique of Metaphysics:Kant and Traditional Ontology”,p.249.但是,康德的批判又認為傳統形而上學是一種根植于理性之中的普遍思維模式,它是“自然而不可避免的幻相”③KrV B 355.。蓋伊與伍德則認為,康德的先驗辯證論有兩個意圖:其一是揭示傳統形而上學之失敗,即思辨理性在嘗試逾越經驗之界限時注定陷入謬誤;其二是展示形而上學的問題意識本身或者說它的吸引力卻有著在理性之中的根源。就后者而言,當人們對理性的形而上學傾向善加引導利用,則它會有助于科學與道德。這個觀念構成了康德在科學和道德領域中對理性作范導性應用的理論基礎。接下來,我們將具體考察這兩方 面。
五、自然科學視閾里的建構性—范導性
范導性是康德科學哲學中的一個關鍵概念。從先驗辯證論可見,理性之超驗應用在本質上是把范導性原則替換為了建構性原則,乃至把作為行動原則的理想轉變為了作為實體的理念。然而,當理性得到恰當的應用,那么它還是可以作為理想而繼續充當啟迪。正如康德所言:“就這些原則而言值得注意且我們也唯一探討的是:它們看起來是先驗的,而且雖然它們所包含的是供理性的經驗性應用遵循的純然理念,理性的經驗性應用只能仿佛是漸近線狀地,也就是說僅僅接近地遵循它們,永遠也達不到它們,但它們作為先天綜合命題還是有客觀的,但不確定的有效性,并且充當可能經驗的規則,也實際上在加工經驗時被用做啟迪性的原理而取得很大的成功,但人們畢竟不能完成對它們的一種先驗的演繹,如上面所證明,這在理念方面任何時候都是不可能的。”④KrV B 691.
它為理性在經驗領域里提供了理想,并且體現為經驗之統一性。康德寫道:“……按照這樣一種原則在自然中尋找秩序的那種方法,以及把自然中的這樣一種秩序——雖然在何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尚不確定——在根本上視為有根有據的那種準則,當然是理性的一條合法的和杰出的范導性原則,但它作為這樣一條原則卻比經驗或者觀察能夠與它比肩行走的遠得多,它畢竟沒有規定某種東西,而是給理性指明了達到系統的統一性的道路。”①KrV B 696.自然的統一性是范導性的,而非建構性的,這意味著:“……如果嚴格地做出判斷,它們并不具有由此得出作為假設被假定的普遍規則的真理性的性質……”②KrV B 675.它并非關于自然的結論,而是理 想。
對于自然的統一性理想首先體現為主體的認知能力上的統一性,即理性為知性在自然領域中的各種應用提供統一的指導。它細分為同類性、特殊性、連續性等三類原則。康德寫道:“因此,理性為知性準備了行動領域:第一,通過在較高的屬下面雜多的東西具有同類性的原則;第二,通過在較低的種下面同類的東西具有差異性的原理;而為了完成系統的統一性,它還附加上第三,一切概念有親和性的規律,這條規律要求通過差異的逐步增加而從一個種連續地過渡到另一個種。我們可以把它們稱為形式的同類性、特殊性和連續性的原則(die Principien der Homogenit?t,der Specification und der Continuit?t)。”③KrV B 686.自然之連續性的秩序是源于“理性的一條合法的和杰出的范導性原則”,它并不現實地對自然本身做出規定,而是為自然研究指出一條尋求系統性和統一性的道路。④KrV B 696.
與主體的統一性相應的是客體的統一性,即作為整體的世界與自然。康德的“世界”概念是指表象在數學上的整體性;而“自然”則是表象在力學上的整體性。⑤它們構成了先驗宇宙論的兩個方面。前者引出了世界之邊界與可分性問題,構成了第一和第二組二律背反;而后者則引出了因果關系的類型與第一原因的問題,構成了第三和第四組二律背反。在先驗宇宙論中,建構性原則把理性活動當作現成給予的實體,比如,把對原因序列的追溯轉變為第一原因;范導性原則排除了這種實體化的傾向,而強調理性活動之過程性。“它不能說客體是什么,而是說應當如何著手進行經驗性的回溯以便達到客體的完備概念。”⑥KrV B 538.并且,這個完備的概念是永遠不可及的,或者說回溯的序列是“一個永遠不能完備的綜合”⑦Ibid.、“一種無限的回溯”⑧KrV B 540.。從而,宇宙論的總體性原理是把對序列之極大值的追求當作“應負有的任務”,而非“給予”的東西。⑨KrV B 536.
客體的統一性具體體現為目的論。它并不屬于客體,而是作為研究客體的范導性原則,從而 “就好像它是一條客觀的原則那樣”①V 404.(Kritik der Urteilskraft)。對于康德而言,目的論是“與人類知性相適合地作為范導性原則來引導對世界上的事物的評判”②V 416.(Kritik der Urteilskraft)。自然的目的論是內在目的論,即“自然的一個有機產品就是在其中一切都是目的并且交互地也是手段的那種產品。在它里面,沒有任何東西是白費的、無目的的,或者應歸于一種盲目的自然機械作用的”③V 375.(Kritik der Urteilskraft)。這種目的是人對自然事件所作的判斷。不過,這種判斷又是以先天原則為基礎的,因而并非主觀任性,而有著主體間的客觀性。這種原則存在于作為范導性而非建構性原則的自然理念之中,它被康德稱作“評判有機存在者的內在合目的性的準則”④V 376.(Kritik der Urteilskraft)。
因而,在康德視閾里,目的論或自然物體的合目的性,并非屬于自然本身的客觀規定,而是在自然理想指導下的判斷。更具體地說,目的論是一個關于自然的假設,它在研究中有著啟迪的作用,而它的有效性則取決于經驗的具體求證。康德指出:“……我們有一種目的論聯結的系統統一性的范導性原則,但我們并不事先規定這種聯結,而只可以在對這種聯結的期待中按照普遍的規律追尋自然機械論的聯結。”⑤這意味著自然目的并非建構性的概念,它不屬于自然本身。“……因為自然目的的概念在其客觀實在性上是根本不能通過理性來證明的(也就是說,對于規定性的判斷力來說它并非是建構性的,而只是對于反思性的判斷力來說是范導性的)。”⑥V 369.(Kritik der Urteilskraft)換言之,自然的目的只有通過理性的范導性應用才能界定。他寫道:“所以一個事物,作為就自身而言的自然目的,其概念并不是知性或者理性的任何建構性概念,但畢竟是一個對反思性判斷力來說的范導性概念……”⑦V 375.(Kritik der Urteilskraft)
當代學者對康德的自然觀與科學哲學中的范導性原則也有著廣泛的討論。蓋伊認為,對于康德而言,自然科學之體系性是范導性而非建構性的。“雖然,在語義形式上,他認定體系性的原則必定是先驗原則,而非僅僅是邏輯原則,但是康德同樣堅持認為它是范導性的,而非建構性的。”⑧Paul Guyer,“Kant on the Systematicity of Nature:Two Puzzles”,History of Philosophy Quarterly,Vol.20. No.3. 2003,p.288.并且,“該原則在內容上是先驗的,但在效力上是范導性的”⑨Ibid.,p.289.。這意味著,人們只是在研究過程中把自然當作就好像是有體系性的,從而把為自然提供完整而徹底的解釋樹立為目標,而不是把體系性當作自然本身的必然結構,乃至把研究目標誤認為結 論。
瓦滕貝格(Thomas E. Wartenberg)指出,范導性使得康德的科學更側重經驗,而非先天的建構。在科學活動里,理性有三個功能:同類性(genera),建立一條普遍法則以統攝各類經驗的法則;差異性(specification),以具體的觀察為普遍法則尋找細分的差異;親和性(affinity),認為在同類概念中的差異是有著漸變連續性的。它們是建構科學知識的三個原則,并且都屬于理性的范導性應用。“這三條原則——同類性(genera)、差異性(specification)、親和性(affinity)——綜合地構成了康德對自然知識所追求的體系結構的刻畫。綜合起來,它們具體展現了所謂‘完全而充分的科學知識’的理念。它堪稱理念,因為它用三根主軸在知識中設定了一種完備性,足以刻畫理想的科學研究之結果。”①Thomas E. Wartenberg,“Reason and the Practice of Science”,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ant,edited by Paul Guy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241.在實際的科學活動里,它們具體化為各種科學實驗。雖然康德在認識論上刻畫了知識的先天性側面,但是他的科學觀仍然注重經驗和實驗。對康德而言,科學是“一項持續地自我修正的事業,在其中經驗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②Ibid.,p.248.。
麥克納爾迪(Michael Bennett McNulty)借助康德的范導性原則拓展出一種“觀念型”(ideational)的自然法則,以解釋那些不適用于因果必然性的非物理法則。康德時代的化學法則(比如波義耳定律)奠基于元素的理念,而化學家通過實驗把各種現象還原為元素及其組合。雖然元素的理念本身超越于經驗的可能性,但是它們又是為滿足理性的理論目的而必要的預設。這些預設是范導性的。麥克納爾迪寫道:“根據康德,對理性的范導性(regulative)應用(它主要見于先驗辯證論之附錄)本質上包含著對各種原理提出假設和測試,而這些原理又統一著經驗發現的各種規律性(regularities)。當人們提出一條原理,它最大限度地統一著這些規律性,并且它本身并非具有嚴格普遍和必然性的更高原則的衍生物。源自該原則的規律性帶著必然性,并且由此成為法則。”③Michael Bennett McNulty,“Rehabilitating the Regulative Use of Reason:Kant on Empirical and Chemical Laws”,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54,2015,pp.1—10.在自然科學中,理性的范導性應用包含著提出假說和實驗。理性的目的也是范導性的,亦即,在科學的認知中尋求統一和完整的解 釋。
六、道德視閾里的建構性—范導性
作為理性的理想,范導性原則也有著道德實踐的意義,具體表現為:至善、根本惡、自由意志與歷 史。
在康德的道德學說中,至善的概念關聯于他對上帝概念的認識論批判。他在認識論層面上否定關于上帝存在的任何一種證明,即宇宙論證明、目的論證明、本體論證明。盡管如此,與先驗辯證論對理性之超驗傾向表現出雙重態度一脈相承,康德也同意上帝的概念源自人類理性的自然需求。這種需求既是思辨的,即為自然在整體上預設一個理智的原因,也是實踐的,即作為道德動機的基 礎。
康德的上帝概念是范導性的而非建構性的理念。康德通過對本體論證明的批判否定了本體論證明為此概念所賦予的實存,而這標志著它作為建構性理念的瓦解。伍德認為,康德的上帝概念源自理性所尋求的無條件的整體的理念。在道德哲學里,它對應著至善的概念。康德指出“至善”的概念有兩個義項:幸福或自然的善,德性或道德的善。在理想狀態下,完善的德行匹配于應得的幸福。但是,這種匹配是沒有保證的,尤其因為它們各自隸屬兩套因果秩序。上帝的概念是確保兩者一致的公設,它維護著人們對道德的基本信 念。
康德的道德神學實際上把關于存在的信念轉變為了關于行動的希望,即奉行道德法則,就好像上帝存在一樣。在《實踐理性批判》里康德把“上帝存在”當作一條“公設”(postulate),即“在實踐上有用的假定”。①V 11—12.(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對此,伍德指出:“也許這種用法表明康德意識到他的實踐論證,并不會實際產生信念,并且表明(至少暗示)它們導向某種較弱的東西。如果‘公設’‘假定’‘預設’等暗指缺乏信念,那么‘公設’‘上帝存在’就在某種意義上相當于希望上帝存在,或者說仿佛相信上帝存在那樣去行動。”②Allen Wood,“Rational Theology,Moral Faith,and Religion”,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ant,edited by Paul Guy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p.394—416.
然而,為什么康德的道德觀需要這樣一個“就好像”呢?這與他的人性論中的根本惡概念相關,并且它本身也是一個范導性原則。科勒(Markus Kohl)認為,康德關于人性之根本惡的觀念是范導性的,它意味著人在道德上的不完善狀態和偏離理性的傾向。然而,如果根本惡是一個事實陳述,那么它就放縱了道德獨斷論,在對人類整體的本性作斷言時越過了知識的界限。不僅如此,它也矛盾于作為道德條件的意志自由的公設。但是,把它當作范導性的原則卻可以避免上述問題。雖然我們無法認識人類在整體上究竟是善是惡,但是當道德主體預設在自身之中有著作為障礙的惡,這會有助于促進道德進步和培育德性。科勒寫道:“問題的關鍵在于,在我們對‘我們是惡的’這一命題的承認里有一種道德興趣,它源于我們追求道德完善的客觀義務,并且在道德禁欲主義的語境里它把一種范導性的指令奠基于我們的惡的本性之中,即,去追求道德完善。”③Markus Kohl,“Radical Evil As A Regulative Idea”,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Vol.55,No.4,2017,p.665.
實踐理性的第三個范導性原則是自由。自由的概念不是建構性的。它并非關于世界的形而上學斷言,也不是基于觀察的事實陳述。作為概念,自由只是一種可能性,并且這種可能性有益于道德。人并不能認識自由,即“不能憑借思辨理性(更不能憑借經驗性的觀察)認識我的靈魂,從而也不能認識作為一個我將感官世界的效果歸因于它的存在物的屬性的自由”,但是“畢竟可以思維自由”,從而為道德學說保留地盤。①KrV B XXVIII—XXIX.基于上述兩點,它是一個范導性的理 念。
除了《純粹理性批判》,康德在《實踐理性批判》和《判斷力批判》中也反復強調這點。“……就該存在者的一切行動都是顯象而言把它們視為物理上有條件的,同時卻又就這個行動著的存在者是一個知性存在者而言把這些行動的因果性視為物理上無條件的,并如此使自由的概念成為理性的范導性原則,這并不自相矛盾。”②V 48.(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以及,“……只要我們能夠根據我們的理性的性狀去設想它,畢竟是被用做一條普遍的范導性原則,這條原則不是客觀地規定作為因果性形式的自由的性狀,而是確切地說按照那個理念使這些行動的規則對每個人都成為命令,其有效性并不亞于假如做出那種規定的話”③V 404.(Kritik der Urteilskraft)。
在道德實踐領域,范導性原則與建構性原則之間的劃分又有著統一性。康德指出,當我們遵循理性之范導性原則而實踐時,那么實踐本身就把理想建構為理念。在人的道德行動中,道德理念進入實存。他寫道:“但是,如果問題在于實踐的東西,那么,這樣一種(對于明智和智慧來說的)范導性原則,即把某種按照我們認識能力的性狀只能被我們以某種方式設想為可能的東西當作目的,根據它來行動,就同時是建構性的……”④V 457—458.(Kritik der Urteilskraft)
最后,作為人類實踐之整體,康德的歷史概念同樣也是范導性的。他試圖從總體的視角研究歷史,但普遍歷史的理念是范導性的。在范導性的原則下,總體的歷史概念并非把所有具體的經驗實踐納入一條因果鏈之中,乃至為未來提供預測。相反,它引入了對歷史的理性主義信念:人類的歷史在總體上呈現出特定的秩序與合目的性。然而,歷史的合目的性只是范導性的,而不是建構性的。面對當代歷史哲學對宏大敘事的解構,康德的范導性原則卻能為總體的歷史觀留出空間。克萊因戈爾德(Pauline Kleingeld)認為,康德在理性的范導性運用里提出了人類歷史作為整體的理念,而這個歷史概念既有深闊的意蘊,又“在認識論地位上是謙虛而容錯的”。“他試圖拓展這樣一種范導性的理念,即,人類歷史如何可能被視作人類理性能力之逐漸發展的過程。并且,他希望歷史學家的確可以把這個模型當作撰寫‘普遍歷史’的指引理念。”⑤Pauline Kleingeld,“Kant on Historiography and the Use of Regulative Ideas”,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39,2008,pp.523—528.
七、結論:重讀康德,重估理性
康德哲學業已引發了兩百余年的爭論,它關切著對于人類自主性和理性的評價。正如皮平所言:“康德的名字就是自主性。”①Robert Pippin,Modernism as a Philosophical Problem:On the Dissatisfaction of European Culture, New York:Blackwell,1999,p.12.海德格爾對“上帝之死”的詮釋指向歐洲形而上學傳統的破產,即上帝的概念在哲學上不是一個宗教名稱,而是理念的代名詞;它的死亡意味著超感官世界不再是表象的根據,也不再為實踐提供指引。海德格爾把它最終引向對理性本身的批判:“直到我們理解了數世紀以來備受稱頌的理性恰是思想的最頑固的敵人,直到此前,思想不會開始。”②Martin Heidegger,Off the Beaten Track, translated by Julian Young,Kennith Hayn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199.當海德格爾以上帝之死來探討理性之死,黑格爾則把它引向哲學之死。這個通常被歸于尼采的議題源自黑格爾的《信仰與知識》:“純粹的概念或無限是那淹沒一切存在的虛無的深淵,而它必定有著無限的痛苦,這痛苦曾經在形態上和情感上僅僅是歷史的,它是新近時代的宗教所依賴的情感:上帝自身死了(Gott selbst ist tot)……”③Hegel,“Glauben und Wissen oder Reflexionsphilosophie der Subjektivit?t in der Vollst?ndigkeit ihrer Formen als Kantische,Jacobische und Fichtesche Philosophie”,in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Werke 2, Main:Suhrkamp,1986,p.432.
在《信仰與知識》里,“上帝之死”的實質是“哲學之死”(Tod der Philosophie),而它源自康德的先驗辯證論。蓋伊指出,黑格爾把康德哲學界定為“主觀觀念論”(subjective idealism),并且黑格爾的不滿在于:康德式的客觀性是關于事物向主體的顯現在主體間的一致性,而不是屬于物自身。④Paul Guyer,“Absolute Idealism and the Rejection of Kantian Dualism”,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German Idealism,edited by Karl Amerik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p.37—56.在兩者的語境里,物自身即理念世界。在黑格爾看來,在康德關于現象與本體二分法下,理念之彼岸性構成了一個理性不可觸碰的領域,宣告信仰高于理性,宣告理性本身不能觸及世界的真 相。
然而,從范導性與建構性的劃分,我們可以看出,這個評斷對于康德是不公正的。在建構性原則失敗后,理性之范導性的原則繼續承擔著表象之根基(作為物自身)與實踐之指引(作為理想)的雙重作用。可以說,在康德的建構性—范導性之劃分里留存著一種現代的希望:理性是不死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