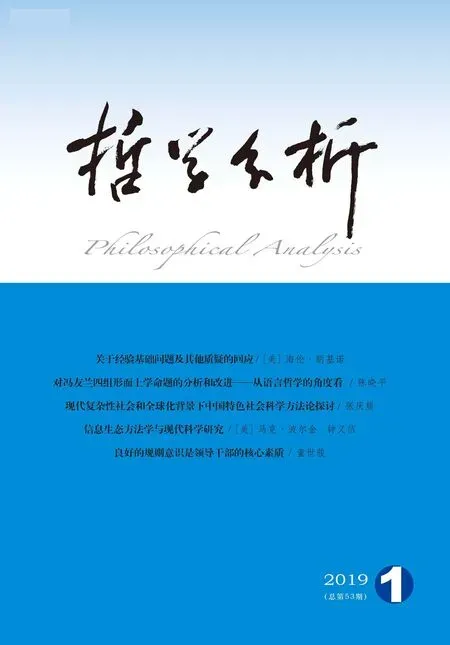關于經驗基礎問題及其他質疑的回應
[美]海倫·朗基諾/文王不凡/譯
經驗主義的哲學觀點包含了兩種不同的主張:一種關于意義,另一種關于知識的基礎。我追隨巴斯·范·弗拉森(Bas van Fraassen),成為關于知識的經驗主義者,而不是關于意義的經驗主義者。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在那篇著名的文章《理論不是什么》①Hilary Putnam,“What Theories are Not”,in Logic,Method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edited Ernest Nagel,Patrick Suppes and Alfred Tarski,Stanford,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 pp.240—252.中,把關于意義的經驗主義擱置了下來。經驗主義,作為一種關于知識的議題,討論的是我們關于世界斷言的根據:經驗。問題是經驗是如何成為基礎的?
當考慮個體知識時,經驗經常被等同于知覺,經驗如何提供基礎的問題也經常被等同于知覺如何提供基礎的問題。但是在科學中,為任何斷言,無論是知識還是合理性,提供基礎的經驗必須是公開的。因而被理解為觀察的經驗在觀察報告中是可交流的。這就是為什么初出茅廬的科學家首先要學的一件事是堅持做實驗筆記。筆記中包含實驗結果,它們是為研究者提出的假設和推測提供依據的觀察報告的來源。但真是如此嗎?邏輯經驗主義者在他們的實證分析中對這一基礎進行了考察。他們的希望是把實證解讀為一種關于觀察報告和假設之間的形式關系。
不充分決定性問題阻礙了他們的努力。①參見海倫·朗基諾:《重新認識證據和不完全決定性》,戴潘譯,載《哲學分析》2015年第6期。——譯者我們用以描述觀察的語言和用來表達假說的語言之間的邏輯鴻溝意味著沒有什么形式關系能夠被建立。相反,需要背景假設來建立觀察數據和假說之間的證據相關性。這就是語境經驗主義的語境。這當然也引發了一個問題:任何背景假設都能做到嗎?如果能的話,那又是什么在阻止科學陷入武斷和一廂情愿的想法呢?對這個問題的解答需要把視角從個人轉向社會,并看到使背景假設可見且可用于批評性審查——修改、拒絕和采納——的話語互動。這是批評的語境經驗主義的批評部分。開展這些話語互動的共同體必須滿足特定的條件,從而使這些話語互動在認識上或認知上是有效的(“可轉變的”)。我提出了四個這樣的條件:公開的話語場所、對批評有吸收和回應、有效規范話語的公共標準和學術權威(適中的)平等性。
我感謝作者們對這些觀點給予了認真的關注,我將逐一對他們進行回應。黃翔、孟強和彼特·穆爾塞普(Peeter Müürsepp)都涉及了批評的語境經驗主義的哲學議題。孟強從科學的社會研究的角度提出了一種評論;黃翔為批評的語境經驗主義提供了一種辯護,他認為認知科學中的生成主義觀點是批評的語境經驗主義在科學中的一種實現;彼特·穆爾塞普討論了批評的語境經驗主義和雷恩·魏霍蒙(Rein Vilhomenn)的實踐實在論之間的關系,以及與尼古拉斯·麥克斯韋(Nicholas Maxwell)的目標導向的經驗主義(Aim Oriented Empiricism)之間的關系。
回應孟強
孟強在展示科學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從田野帶回的經驗研究中所獲得的教訓時,很好地總結了批判的語境經驗主義的許多要點。然而,他仍然不相信批判的語境經驗主義的規范性維度增加了我們對科學作為一種活動或實踐的理解。我們可以說,他對語境部分感到滿意,但對批評部分并不盡贊同。對于孟教授,我主要回應兩點。
首先是一個小問題。我并不同意我關于 “理性—社會”二分的特征描述對科學的社會研究不公平。我的主張是,哲學的理性化者和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把理性和社會性視為相互排斥的。雖然最近來自科學的社會研究工作并沒有那么極端,但早期的工作確實顯示出一種二分法的態度。在科學的社會研究中往往會出現不同的立場。強綱領和愛丁堡學派非常明確地拒絕理性或認知的考慮會決定科學爭論的結果。爭論是被政治而非被理性決定的。這是夏平和謝弗的結論,也是麥肯齊(Mackenzie),有時也是平齊(Pinch)和柯林斯的觀點。但是微觀社會學、實驗室研究、綱領也聲稱在解釋特定的科學事件時沒有必要使用認知過程。拉圖爾在《科學在行動》中說,如果我們只是遵循周圍的科學家,那么我們就不會發現自己在講述我們所目睹的事情時會訴諸理性或認知的概念。皮克林(Pickling)雖然在《建構夸克》一書中對粒子物理學中的特殊事件的描述是無可挑剔的,但他也堅持認為,那表明非認知因素在夸克理論的發展中發揮了一種決定性作用。①Andrew Pickering,Constructing Quarks,Chicago,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我在《知識的命運》一書中的論點是,這種二分法的產生是由于對社會和理性的貧乏認識。我在那本書里的目的是要展示社會性可以是理性的,理性也可以是社會性的。但為了打破這種二分法,這兩個概念都需要擴展。
孟強教授的另一個挑戰是質疑規范是否必要。如哲學家們似乎認為,科學的社會研究中的“怎么都行”(anything goes)是不符合實際的。他們有關于成功的標準。成功就是對他人的說服。辯護是科學家利用不同的資源去說服別人。我認為至少存在兩個理由來拒絕這種反駁。第一,科學家不只是試圖說服別人,而是要發現某些關于世界的東西。此外,科學的消費者——公眾、決策者——經常面臨相互矛盾的主張。批評的語境經驗主義規范的要點是不允許某些資源,例如權力,作為正當的理由。對于規范的滿足(如果它們是正確的規范的話)保證了局外人的主張是可信的。然而,我發現真理這個概念對科學而言太過狹隘了,我確實認為某種形式的語義上的成功是有目的的。我把它稱之為(對內容或意向對象的)構型(conformation)。
第二,批判的語境經驗主義規范不是憑空產生的哲學發明,而是來源于科學的自我形象。這種自我形象是開放的、批判的和自我修正的。關于這種自我形象和科學本身的堅持,批評的語境經驗主義規范是要努力把其中隨之而來的標準明確化。使它們明確的關鍵在于能夠說出科學或從事科學研究的科學家什么時候無法實現他們自己的理想。
因此,我不相信規范在幫助我們理解科學實踐方面沒有作用。
回應黃翔
黃教授為批判的語境經驗主義做了辯護,認為它與當前認知科學中的一種思想——生成主義(enactivism)——有關。因為他非常清楚地解釋了這一思想的宗旨,所以我將不再重復,但還是要利用他所說的來擴大我對孟教授關于規范的評論。黃教授說:“社會規范和價值能被理解為一種資源,它們由來自不同背景的科學家所設計、建構、應用和修改,但他們想要通過參與到設計等活動中來開展交流,因此,通過服從它們,他們使自己有資格成為負責任的和能勝任的人。”科學關乎公共知識,也就是,能被分享的知識/表征。
共同體及其成員與他們的認知問題和解決這些問題的資源共同構成了他們自己。這就導致了知識的概念是動態的,而不是靜態的;一個將被認識的世界和其他認知者參與其中的持續性事業。我認為這是生成主義和批判的語境經驗主義的共同特征,前者是從認知科學中發展而來的一般進路,后者主要是為思考科學探究而發展起來的。我對這種趨同感到高興。
回應彼特·穆爾塞普
穆爾塞普教授讓我們注意到愛沙尼亞哲學家雷恩·魏霍蒙的思想:實踐實在論。我所理解的實踐實在論意味著研究者與主體事件之間的物質關系,因此真實世界是通過那些物質的相互作用來揭示的。因為研究者與主體事件的互動本身就是價值驅動的,或者至少是基于主觀的,所以科學所知的世界也是充滿價值的。
批判的語境經驗主義和實踐實在論都拒絕“上帝之眼”的可能性。我同意批評的語境經驗主義與實在論兼容,但它是與多元實在論兼容。由此我的意思是說,我們接觸主體的方式可能涉及不同的方面,它們會產生同樣恰當的(部分的)理解。這些可能或者也不可能合并為一個連貫的整體。“因循守舊”的規范性概念就是為了捕捉這種實在論。
然而我不能完全理解穆瑟普文本中的許多觀點,但我確實想表達一些擔憂。首先,實踐實在論的實在論者到底是關于什么的?穆爾塞普堅持認為,實驗室里的研究人員實際上是在研究她的材料,但是,這個被構造、被凈化的世界與實驗室外混亂的世界有什么關系呢?其次,麥克斯韋和我看待形而上學假設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麥克斯韋似乎把這樣一組特定的假設視為明顯內在于科學實踐中,且對科學實踐產生影響的。對批判的語境經驗主義來說,那些影響各種科學努力的形而上學本身就要服從批評性的考察。這是討論他關于促進證據相關性判斷的假設的關鍵。但要說任何給定的假設都有形而上學的維度,那只是討論的開始,而不是結束,也不是對非充分決定性問題的解決。按照批判的語境經驗主義,形而上學的觀點被接受,它本身必須是批評性互動的結果。正是這種對互動中的形而上學和規范性維度的基礎的堅持,才使得批評的語境經驗主義有別于麥克斯韋的目標導向的經驗主義,或許也有別于魏霍蒙和穆爾塞普的實踐實在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