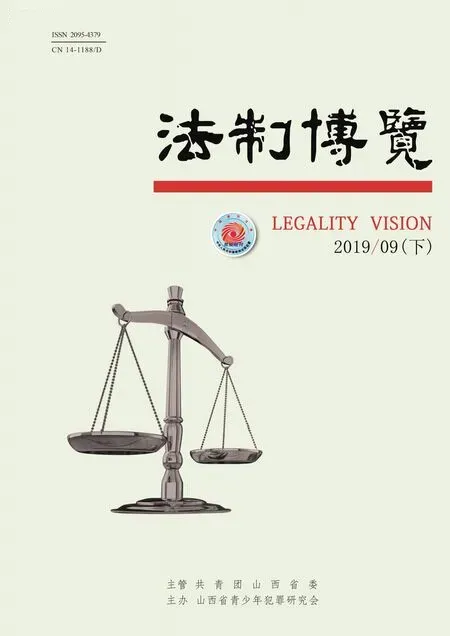論排除合理懷疑
鄧乃浩
貴州民族大學,貴州 貴陽 550025
一、排除合理懷疑的含義
首先從字面上來看,合理懷疑對于某一事物或事件不是完全的確信,存在一定的質疑、假設。并且這樣的懷疑又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一種合理的質疑。合理在普通文義上來說是以普通人的日常經驗,正常思維方式為標準的存在。從法律上來說,排除合理懷疑是西方國家對案件證明標準的一種表述,但是這種證明標準自產生后就一直存在爭議,沒有一個固定的解釋。較早運用這一術語的國家一般都不對其含義進行具體的規定,而直接去從字面理解,認為其本身既是一個術語,同時也是對其本身最好的一個解釋。有學者認為只要辯方破除了控方的證據鏈,那么辯方提出的懷疑就是合理的。按照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的解釋:排除合理懷疑是指“對于事實的認定,已沒有符合常理的、有根據的懷疑,實際上達到確信的程度。”
二、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序進步性
(一)首先是價值觀念的轉變
在我國傳統的職權主義影響下,國家機關調查案件,抓捕犯罪分子目的主要是為了打擊犯罪,懲罰犯罪分子。司法機關往往是代表國家、代表正義,而犯罪實施者往往代表罪惡,在這樣的觀念影響下,即使我國有人權保護,犯罪實施者人權保護的對象之外。在整個司法過程中雖然有某些地方是違反法律規定的,或者程序存在一些瑕疵,忽視犯罪嫌疑人的人權保障,但是往往也能夠被民眾所容忍接受。自從我國憲法明確規定尊重和保障人權,刑訴法也隨即跟上步伐,進行了這方面的修改。把保障人權引入到刑訴法的規范中,在辦案的規程中注重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權,把懲治犯罪和保障人權相互獨立,并行不悖。
(二)刑事訴訟法律觀的轉變,證明標準由追求客觀真實轉向法律真實
以前刑事訴訟法中證明標準是追求客觀真實,即完全客觀的還原真實狀況,不帶有任何的主觀推斷。所有認識都來自于客觀真實的存在,注重辦案人員對過去事實的真實還原,這對于還原案件真實,防止冤假錯案,提升司法公信力是非常有利的。但是我們不能忽視一個重要的問題,案件存在時效性,不盡快偵辦就會導致證據的毀損滅失。并且具有緊迫性,需要有一定的效率去完成案件的偵辦及審理。所以原有的證明標準就顯得很不恰當。其次,我國逐步由職權主義向兼具當事人主義轉變,庭審逐漸轉為控辯雙方的相互對抗。在各種影響下“案件事實清楚”的證明標準已經不能再作為司法人員的強制標準,而“犯罪事實清楚”的標準不僅表明了對于謹偵慎判的態度,又能符合法律的基本狀況。就是說在辦案過程中要注意程序的要求,即證據達到一定的標準,即可做出相應的結論,否則就要排除該證據或者做出無罪認定。法律真實側重程序正義,形式合理,強調對于法律規則的重視及使用,最終作為審判定罪的依據,而不是去客觀還原事實。這一變化表明了我國在還原真實的同時也逐步注意合法性,重視訴訟程序的重要,更符合刑事訴訟活動的要求。
三、排除合理懷疑的定位
根據我國新舊刑訴法的規定對比,首先應當明確的是,我國的證明標準并沒有發生變化,依然是證據確實、充分。新刑訴法只是在后邊加上了需要排除合理懷疑。不難看出,前后規定并非是并列的同等級別的證明標準,后者只是前者的一個衡量標準,也就是說只有對證據及事實的認定達到了排除合理的懷疑,才達到了確實充分的程度,所以說排除合理懷疑是認定證據確實充分的一個必要條件,為其提供可操作性。
四、排除合理懷疑的適用
(一)適用范圍方面,針對所有的刑事案件
民法和刑法由于立法目的、保護客體不同,違法后果不同,所以有不同的證明標準。在刑法調整的對象當中,也并不是全都具有一樣嚴重性,那么對于嚴重的和輕微的犯罪行為,需不需要像民刑法那樣區別對待呢?我認為是不需要區別對待的,因為自從憲法確立了保護人權之后,刑訴法也引進了這一制度,表明了對人權的重視,所以無論涉及的是輕罪還是重罪,刑法懲罰犯罪的目的不會變,刑罰的嚴厲性不會變,所以既然要查清事實,就要在所有案件中運用這一標準進行認定。另外是全案每個細節都適用這一標準,還是對于那些足以影響案件定性的事實才需要?我認為若每個細節都要使用這么嚴格的高標準,那么勢必會影響到案件的進度、結案的效率,無法達到刑法的目的。所以對于那些無關緊要的,不足以影響案件定論的證據,就不需要大動干戈的去費時費力。
(二)適用階段方面,貫穿刑事訴訟始終
首先從刑訴法的立法目的來看,刑事訴訟法是為了刑事訴訟活動能夠正常運行而制定的用來約束司法機關行為的工具,它不僅約束審判機關按照法律規定進行,同時也同樣的標準去約束偵察機關以及公訴機關,即刑事訴訟法是貫穿刑事訴訟的全過程的,從偵查機關開始立案偵查起就要按照該法的規定進行。從條文的字面表達來看,并沒有明確說是在審判階段需要運用這一標準,而是在一個普通的條文當中,那么也就是約束刑訴法面向的所有主體適用。所以對于犯罪行為的這一認定標準也是適用于所有的階段,而不是單單規定在審判階段的。
五、司法實踐中如何把握這一證明標準
(一)提高對證據的要求
排除合理懷疑的主要依據是證據,案件事實也是通過證據進行還原的。首先在證據的搜集過程中,搜集證據的手段要合法,屬于正常的偵查程序獲得的合法證據才能在定案中適用,而通過刑訊逼供等違法方法搜集的證據根本就不能作為證據使用。其次,對于證據的質和量也要有所要求,首先證據要具有三性,合法搜集,并且都要經過法庭的當庭質證,還要足以形成一個完整的證據鏈,這是質的要求。另一方面,在取證的過程中,不僅要有嫌疑人有罪的證據加重情節的證據,還有要可能無罪或者罪輕的證據,保證起訴,定罪,量刑過程中都有足夠的證據去進行論證。
(二)提高陪審員的作用
以前的庭審當中,主要是法官去認定事實,適用法律。即使有些案件有人民陪審員一起審判,但是陪審員大多是走個過場,不僅在法律適用上沒有發表意見,甚至在事實和證據的認定中也未發揮作用。既然該標準是從英美法系國家引進,那么他們的審判模式也是可以借鑒的。我們可以借此強化人民陪審員在審判中的作用,對于事實的認定,可以交給陪審員主持,法官輔助,這其實和我國設置陪審員的初衷是不相違背的。陪審員本來就不是專業法律人,可能來自各行各業,所以從陪審員一般人的視角去看待證據和事實,可能幫助法官開拓一下思維,避免以以前相似案件產生先入為主的判斷,這樣也是對被告人權利保護的另一層保障。
(三)文書公開心證過程
在西方國家,一般法官如何認定犯罪事實的心證過程是不公開的,完全屬于法官裁判的自由。但是我國畢竟國情不一樣,法制狀況不一樣,我國長期運用的是客觀事實的認定標準,對于排除合理懷疑還不太健全,所以為了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最大程度的避免枉法裁判,應該在文書當中把心證的過程表述出來,一方面法官在文書中表述這一過程的同時也會進行進一步的思考與反思,檢驗一下合理性,另一方面有據可考,方便對錯案的追究,這也是符合我國現在的終身追責制度要求的。
六、結論
我國刑事訴訟中引入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一方面是對訴訟法的完善,同時也是對傳統訴訟的一種挑戰,新的標準在我國是運用的過程中肯定會出現一些問題,但是無疑大方向是好的,所以還需要立法者與司法者以及法律學者共同的努力去完善,更好的造福人民,體現法律的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