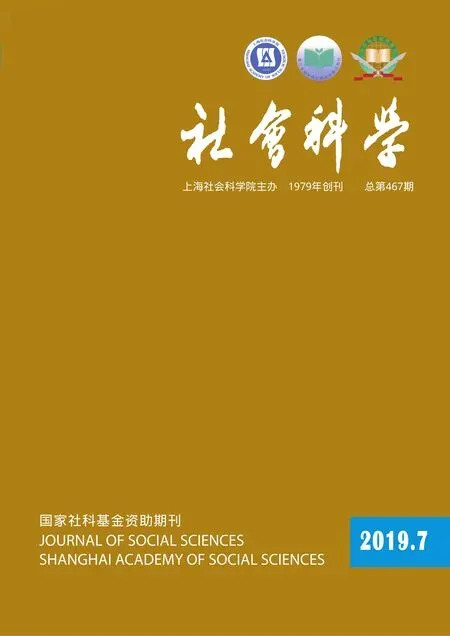百年新詩“辨體”實踐反思
趙黎明
在新文學運動之初,胡適發起“詩體大解放”運動,摒棄千年詩歌成規,給詩歌文體帶來了空前危機:《文學改良芻議》提出“不講對仗”等,傳統詩詞格律的各種規訓被掃地以盡;《談新詩》更進一步,“有什么題目,做什么詩;詩該怎樣做,就怎樣做”[注]胡適:《談新詩》,載《胡適文存》(一),黃山書社1996年版,第126-127頁。,詩歌一夜之間回到了史前期。舊派詩人當然無法接受,新派詩人也屢生疑竇,“是不是有一種東西叫做新詩”[注]廢名:《新詩問答》,參見《新詩講稿》,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7頁。成為大家共同的疑問。人們不斷追問:沒有格律的分行文字算不算詩歌?即使存在一種“新詩”文類,那么其是否也應遵循詩之為詩的規范?等等。早期白話詩人制造的這些“元問題”,被一代又一代詩論家傳遞下去,成為新詩文體史上頗富張力的焦點議題。
單從年齒上看,新詩誕生已有百年,看起來已經長大成人,實際上其“身份焦慮”一直未有化解,卞之琳的一句話反映了這種狀態,他說“新詩雖然誕生了60年,在現代中國文學的一個門類占統治地位也有半世紀之久,可是不少人仍然目之為謬種,不承認它為正宗”[注]卞之琳:《今日新詩面臨的藝術問題》,載《卞之琳文集》(中),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88頁。,其實就在今天,這種“謬種”陰影難說全部散去。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這跟新詩的身份認同有關,因此,中國新詩壇持續不斷的“辨體”實踐,本質上是新詩文體合法性確認活動的一部分。
在傳統詩學系統內,辨體是被置于所有詩學活動首要位置的,“蓋詩之有體,尚矣。不辯體,不足與言詩”[注][明]夏樹芳:《詩源辯體序》,載《詩源辯體》,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440頁。。古典語境中的詩歌“辨體”,不僅體現在別文類、考源流、識正變等文體功能方面,更主要體現在典范追求、傳統認同等價值取向方面。本文所說的“辨體”,跟傳統的“辨體”,既有相通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相同的是“體”的內涵大致一樣,都指詩歌文體、文類、形式等元素;只是外延有所縮小,專指與散文、音樂、舊詩相區分的文體特征。因此,本文的辨體主要是指通過新詩與其他文體的比較,析出其主導性文體規范的話語活動。
一、詩文之辨
詩文之辨是辨體傳統的重要內容。關于詩文差異,劉勰的觀點反映了辨體詩學比較普遍的認識,“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注]周振甫:《文心雕龍今譯》,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85頁。。文筆之分的根據在于韻律節奏的有無,歷代文體家基本延續了這一觀點。“詩與諸經同名而體異。蓋兼比興,協音律,言志厲俗,乃其所尚”[注][明]李東陽:《鏡川先生詩集序》,載《明詩話全編》(2),鳳凰出版社1997年版,第1664頁。。詩與文是迥然不同的兩種文體,“詩與文異體,不可相兼”[注][明]黃廷鵠:《詩冶序》,載《明詩話全編》(7),鳳凰出版社1997年版,第7699頁。,二者不可相混,“詩與文判然不相入”[注][明]胡應麟:《詩藪內編》,載《明詩話全編》(5),鳳凰出版社1997年版,第5447頁。。因此,詩歌必須遵守詩體規則,不能“亂體”,“若歌吟詠嘆,流通動蕩之用,則存乎聲,而高下長短之節,亦截乎不可亂”[注][明]李東陽:《春雨堂稿序》,載《明詩話全編》(2),鳳凰出版社1997年版,第1670頁。。具有古典傾向的詩人篤信,詩之有韻,古今無所變,“大抵有韻者為詩,無韻者為文。《尚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云云,可見詩必有韻,方能傳達情緒;若無韻亦能傳達情緒,則亦不必稱之為詩”[注]章太炎:《章太炎的國學講演錄》,平民印務局1924年版,第72頁。。可見,在古典詩學語境里,“音節”的有無乃是能否成詩的關鍵所在。
新詩就是在詩與文的文體論難中誕生的。1915年,留美時期胡適的幾句打油詩,何以招致梅光迪如坐針刺般的“不以為然”?癥結就在傳統文體規范里。梅光迪說,“詩文截然兩途,詩之文字(poetic diction)與文之文字(prose diction),自古以來(無論中西)已分道而馳…一言以蔽之,吾國求詩界革命,當于詩中求之,與文無涉也。若移文之文字于詩,即謂之革命,即詩界革命不成問題矣”[注]梅光迪:《梅光迪文錄》,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頁。。梅氏此處所謂“文字”問題,并不單指白話之能否入詩問題,也不單指格律存廢問題,而是指詩文邊界能否消弭、融合問題。在梅氏眼里,胡適“作詩如作文”的做派,就是對傳統文體規范的大不敬。實際上,胡適的“詩體大解放”正是“從文的形式”角度切入的。在《談新詩》一文中,他強調指出,“新文學的語言是白話的,新文學的文體是自由的,不拘格律的”[注]胡適:《談新詩》,載《胡適文存》(一),黃山書社1996年版,第123頁。,在他那里,打通詩文界閾,建立“自由的”“白話的”詩體,不僅僅是一般的格律改良,而是建立新詩的立足點問題。
圍繞詩文之別這個“元問題”,現代各派詩論家進行過持久的爭辯。爭辯之時,具有傳統傾向的文論家,多傾向于 “格律說”,認為格律是詩文區分的主要標志。如胡先骕就強調,“詩之有聲調格律音韻。古今中外。莫不皆然。詩之所以異于文者。亦以聲調格律音韻故”[注]胡先骕:《胡先骕文存》(上卷),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27頁。。他認為,格律乃是中外詩歌的普遍文體標志。吳宓也堅持,“惟詩與文既相對而言……詩者,以切摯高妙之筆,具有音律之文,表示思想感情者也”[注]吳宓:《詩學總論》,載《吳宓詩話》,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62頁。。在吳宓關于詩的定義中,“音律”是一個核心要素,也是作為詩歌區別于散文的形式特征。不惟學衡派如此,新文學陣營里的“古典派”,也將格律作為詩文之別的文體要素。聞一多說,“詩有四大原素:幻象、感情、音節、繪藻”。在他心中,音節在詩歌四要素中所處的地位,要遠比其他因素為重,“余之所謂形式者,form也,而形式之最要部分為音節”[注]聞一多:《致吳景超》,載《聞一多全集》(10),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5頁。。朱光潛也服膺“新格律論”,認為詩歌與散文不同的地方在于韻之有無。他對詩有一個定義,詩是“具有音律的純文學”,據他自己稱,“這個定義把具有音律而非純文學的陳腐作品以及是純文學而不具音律的散文作品都丟開,只收在形式和實質兩方面都不愧為詩的作品,這是一個最尋常的也是最精確的定義”[注]朱光潛:《詩與散文》,載《朱光潛全集》(3),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10頁。。就詩與散文的關系而言,朱光潛多次強調“聲音節奏”之于詩文區別的特別意義,“文字意義所不能表現的情調常可以用聲音節奏表現出來。詩和散文如果有區別,那分別就基于這個事實。散文敘述事理,大體上借助于文字意義已經很夠;它自然也有它的聲音節奏,但是無須規律化或音樂化,散文到現出規律化或音樂化時,它的情趣的成分就逐漸超出理智的成分,這就是說,它逐漸侵入詩的領域。詩詠嘆情趣,大體上單靠文字意義不夠,必須從聲音節奏上表現出來。詩要盡量地利用音樂性來補文字意義的不足,七律、商籟之類模型是發揮文字音樂性的一種工具”[注]朱光潛:《給一位寫新詩的青年朋友》,載《朱光潛全集》(3),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70頁。。聯系起來看,他所說的“音樂性”其實就是詩歌的押韻、平仄、對仗等音律節奏,這些“固定模型”“從整齊中求變化,從束縛中求自由,變化的方式于是層出不窮”[注]朱光潛:《給一位寫新詩的青年朋友》,載《朱光潛全集》(3),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70頁。,因而使詩歌具有無窮的藝術韻味;但散文沒有固定模型做基礎,音節變來變去還只是“散”,因而缺乏詩歌那種一詠三嘆的藝術效果。
傳統派崇尚格律,自由派也認同“格律”,不過格律內涵另有所指,格律意識也稍為淡化。如梁宗岱援引西方文體知識,對詩文進行過一番甄別:“在散文里,意義—字義,句法,文法和邏輯—可以說是唯我獨尊,而聲音是附庸。在詩里卻相反。組成中國詩底行駛的主要元素,我們知道,是平仄,雙聲,疊韻,節奏和韻,還有那由幾個字底音色義組成的意象。意義對于詩的作用不過是給這些元素一個極表面的連貫而已。在任何文字底詩學里,句法之倒置,主詞動詞之刪略,虛字系詞之減削,都成為不可缺少的規律。這都足以證明二者之不可得兼的時候,寧可犧牲意義來遷就聲音……如果散文底發展全仗著邏輯的連鎖,一首詩底進行大部分靠聲音底相喚”[注]梁宗岱:《論直覺與表現》,載《詩與真續編》,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版,第234-235頁。。在這個象征主義詩人眼里,詩的文字也好,散文的文字也罷,不外由顏色、聲音和意義三元素構成;這些元素在詩文中表現和作用的不同,決定了詩歌與散文文體屬性的相異。在此三元素中,顏色在散文里無關緊要,在詩里也處輔助地位,因此可以擱置不表;剩下的只有聲音和意義,二者畸輕畸重,決定了何者為詩何者為文。他認為,散文的本體在意義,而詩的本體在聲音,意義和聲音是決定詩文文體的關鍵因素。而在另外一些自由詩人如艾青那里,詩歌音節已經降為一種漸趨于無的說話節奏了,“詩必須有韻律,這種韻律,在‘自由詩’里,偏重于整首詩內在的旋律和節奏;而在‘格律詩’里,則偏重于音節和韻腳”[注]艾青:《自由詩與格律詩問題》,載《詩論》,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116頁。。
總之,不論新舊格律派,還是各種自由詩派,盡管各家對“格律”的理解各不相同,所持標準也寬嚴各異,但在節奏乃詩文之分的文體標志這一點上,大家似乎有比較一致的認識。
二、詩樂之辨
在古典詩學系統里,詩樂一體是一個毋容置疑的常識。“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從這一古老信條出發,古典詩論家大多相信詩樂不分家,且時間越古遠,聯系程度越是緊密,“三代以前,詩即是樂,樂即是詩”[注][清]李調元:《雨村詩話》,載《清詩話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517頁。。他們堅信詩歌的本源來自音樂,“原詩之起,皆因于樂,是故《三百篇》即樂經也”[注][清]黃宗羲:《樂府廣序序》,載《中國歷代文論選》(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4頁。。當然,他們也不否認,詩與樂分途發展的事實。沈德潛曾這樣描述二者分化過程,“詩三百篇,可以被諸管弦,皆古樂章也。漢時詩樂始分,乃立樂府,安世房中歌,系唐山夫人所制,而清調、平調、瑟調,皆其遺音,此南與風之變也。朝會道路所用,謂之鼓吹曲;軍中馬上所用,謂之橫吹曲,此雅之變也。武帝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與司馬相如諸人略定律呂,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此頌之變也。漢以后因之,而節奏漸失”[注][清]沈德潛:《說詩晬語》,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197-198頁。。需要指出,對于詩樂初為一體,爾后分途的認知,現代詩壇是當作“歷史事實”加以承繼的。當然,從這個“歷史事實”,人們讀出的意味不同,對新詩的啟示也就不同。
朱光潛是對詩歌有過系統研究的美學家,他對詩的定義是“具有音律的純文學”,在這個定義中音樂性顯然居于突出位置。為了確認音樂性之于詩歌的作用,他首先從詩歌和音樂起源方面進行了說明。他相信遠古時代的詩樂舞,不過是三位一體“混合的群眾的藝術”[注]朱光潛:《詩與散文》,載《朱光潛全集》(3),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27 頁。,在這個混合藝術中,聲音、姿態、意義,三種元素互為應和、相互闡明,而節奏是其中的“共同命脈”;后來,三種藝術分途發展,各取側重,但詩應和樂舞的痕跡仍無可抹滅。他還發現各種藝術之中,同為時間藝術的詩歌和音樂的關系也最為親近,原因在于“節奏在時間綿延中最易見出”,并且“詩與樂所用的媒介有一部分是相同的。音樂只用聲音,詩用語言,聲音也是語言的一個重要成分。聲音在音樂中借節奏與音調的‘和諧’而顯其功用”[注]朱光潛:《詩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81頁。。對于《樂記》中那段人們熟悉的文字,“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情動于中,故形于聲。聲成文,謂之音”,他這樣加注解釋,“我們可以說,詩之有音節,由于表現感情時有嗟嘆舞蹈之必要。嗟嘆與舞蹈徘徊往復的神情譜到文字上去,所以有節奏”[注]朱光潛:《詩的實質與形式》,載《朱光潛全集》(8),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88頁。。他還遍引世界各地不同時期著名詩論以為旁證,并進而總結原因說,詩之所以必有音樂,從本源上看是源于情感的自然節奏,是情感熱烈時的必然呼聲。
當然,他也多次強調,堅持詩樂親緣關系,并不意味要將二者混為一談。首先,他認為二者早已分途發展,只是保留了使用“聲音”這一共同點。他更認識到,即便使用“聲音”,二者的使用方式和意義價值也大為不同,“語言的節奏是直率的,常傾向變化;音樂的節奏是回旋的,常傾向整齊;語言的節奏沒有規律,音樂的節奏有規律;語言的節奏是自然的,音樂的節奏是形式化的”[注]朱光潛:《詩與散文》,載《朱光潛全集》(3),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22頁。。他專門分析了詩的音樂性與樂的音樂性的不同,認為前者主要含有三大要素,一是有規律的音節(即平仄),二是有規律的章句,三是有規律的收聲(即韻)。盡管反對“把詩變成音樂”,“離開意義而去專講聲音”[注]朱光潛:《詩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頁。的做法,但從整體取向上看,他還是要求詩歌(包括新詩)有一個大致格律。他曾有一句經濟的表達,“詩有固定的音律,是一個傳統的信條”[注]朱光潛:《詩與散文》,載《朱光潛全集》(3),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12頁。,雖然沒有說明適用對象,但從其前后一貫的論述來看,這句話應該是把新詩包括在內的。
林庚也以“樂詩”論為基礎建構新格律論大廈。他認為詩歌節奏就是語言的“飛躍性”,其來源正是歌舞樂的原始基因,它“有規律的隔著一定距離而一次次的出現”,帶來的是“舞蹈中鼓板”的效應,這種“均勻的節奏感”對于詩歌而言是必不可少的[注]林庚:《關于新詩形式的問題和建議》,載《林庚文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18-219頁。。他還繪聲繪色地描述了節奏產生的情景,“接觸到這樣的節奏就不禁會感染到它的力量而想要跳躍起來;因此它在詩歌上也就有利于語言的飛躍。它的有規律的均勻的起伏,仿佛大海的波浪、人身的脈搏,第一個節拍出現之后就會預期第二個節拍的出現,這預期之感具有一種極為自然的魅力。這預期之感使得下一個詩行的出現,仿佛是在跳板上,欲罷不能,自然也就有利于語言的飛躍”[注]林庚:《關于新詩形式的問題和建議》,載《林庚文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18-219頁。。他將節奏的這種作用比作“欲擒故縱”:分了行不免要停一下,這便是“擒”;可是雖然停止卻還要再繼續下去,這便是“縱”。在他那里,“擒”就是“節”,“縱”便是“奏”,節奏就是由人為的語言動能而造成的跳動飛躍趨勢。“‘節’的本義是‘止’是‘制’,‘奏’字的本義是‘進’是‘走’;我們明明是要‘進’要‘走’,卻偏偏要‘制止’一下;這樣便產生一種自然的趨勢,那便是非跳不可!”[注]林庚:《詩的語言》,載《新詩格律與語言的詩化》,經濟日報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頁。在他看來,漢字的“五七言”傳統形式,是這種節奏類型的最佳形式,是“支配了二千年來的詩壇及民間的文藝形式”[注]林庚:《新詩的“建行”問題》,載《新詩格律與語言的詩化》,經濟日報出版社2000年版,第44頁。,是未來新詩節奏的最佳樣板。這個節奏建設方案,跟學衡派的胡先骕前后呼應,胡氏就曾把“加一字不能,減一字也不能”的“四言五言七言”,定為“中國語中最適宜之句法也”[注]胡先骕:《胡先骕文存》(上卷),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頁。。
梁實秋立論也是從詩樂原始關系開始的。他首先從中外詩歌史上尋找詩樂同源的證據。他說,“‘詩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漢時古詩歌謠成為樂府。自唐以后詩一方面隨著音樂變遷而為詞曲,一方面就宣告獨立而與音樂分離。西洋文學也是有同樣的經過,所謂‘抒情詩’本是有lyre伴著歌唱的,‘史詩’‘ 浪漫故事’也是由‘行吟詩人’口頭傳播的,戲劇的詩是含有大量的歌舞的”[注]梁實秋:《文學的美》,載《梁實秋文集》(1),廈門鷺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501-502頁。;又說,“我們的《詩經》,也完全與音樂有關……但是以后文學與音樂就漸漸分家各自獨立發展了。這是一種自然的趨勢,在各國皆然,由混合的‘舞蹈音樂詩歌’而分途各自發展”[注]梁實秋:《文學講話》,載《梁實秋文集》(1),廈門鷺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581頁。。
詩樂同源,復又分途,分手之后,各自如何發展?梁實秋判斷音樂將向偏于聲音方向進化,詩歌將向偏于文字方向成長;走到一定程度,詩中的音樂必將成為一種無足輕重的附加成分,“詩,注重的是內容,其音樂的成分已不重要。并且,老實說,詩既不譜入歌曲,其中所含音樂成分很有限的。所謂平仄,所謂疾徐,所謂高低,所謂音韻,變化固然多端,然而這亦只是文字在可能范圍內加以美化而已”[注]梁實秋:《詩的將來》,載《梁實秋文集》(1),廈門鷺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441頁。。他堅持認為,文字自文字,聲音自聲音,詩歌文字無論如何不能變成樂譜上的符號;詩歌以文字為工具,而為這個工具的屬性所限,其所能含有的音樂成分必然十分有限。
梁實秋認為,既然詩中的音樂性是有限的,那么詩歌就不必再以追求音樂美作為主要職志,“文學里的音樂美是很有限度的,因為文字根本的不是一個完美的表現音樂美的工具”[注]梁實秋:《文學的美》,載《梁實秋文集》(1),廈門鷺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501頁。。因此,盡管他不反對詩的音樂性,甚至提倡“文字上的音樂性上要盡力推敲”,但是對于過于倚重音樂性的做法,他是保持警惕態度的,他說,“詩的工具是文字,詩的目的是抒寫情感,音樂在詩里的地位只是一種裝飾品,只是工具使用的一種技巧,不是太重要的因素。我們寧可為了顧全內容而犧牲一點音樂性,不能只求文字的聲調鏗鏘,反而犧牲了內容的恰當”[注]梁實秋:《文學講話》,載《梁實秋文集》(1),廈門鷺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581頁。。在他看來,相對于詩歌“內容”而言,音樂性畢竟是一個裝飾性的東西,前者是本,后者是末,切不可本末倒置。據此,他得出結論,詩歌尤其是新詩,不能再走倚重音樂性的老路,而應另求新途,尋找與“內容”相適應的形式。
總起來看,帶有古典趣味的新詩論家追溯詩樂關系,主要目的是想從詩樂舞一體的原始遺跡中,提煉出節奏這一共同元素以為詩歌的文體基因,從而為新詩格律建構提供歷史依據。當然,他們也都同時覺察到了詩樂舞加速分化的趨勢,不同程度體認到了新詩不能再走倚重音樂性的老路,這種覺悟為重新認識詩歌文體發展規律、重新建構新詩節奏鋪平了道路。
三、新舊之辨
新詩是在對舊詩否定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因而其誕生后遇到的第一個疑問就是如何與舊詩相區別。一般的認識是,舊詩采用文言,新詩采用白話,然問題也接踵而至——屬于“舊詩”范疇的元白詩歌,言語就是老嫗能解的“大白話”,因而籠統的文白不足以分新舊,新舊的區別另有所在。區分的關鍵在哪里呢?在于節奏類型的不同。新詩草創時期,不少人抓住了這一要害。康白情指出,“新詩所以別于舊詩而言,舊詩大體遵格律,拘音韻,講雕琢,尚典雅。新詩所以反之,自由成章而沒有一定的格律,切自然的音節而不必拘音韻,貴質樸而不講雕琢,以白話入行而不尚典雅。新詩破除一切桎梏人性底陳套,只求無悖于詩底精神罷了”[注]康白情:《新詩底我見》,《少年中國》1卷9期,1920年3月15日。。稍后,葉公超也指出,新詩與舊詩的區別關鍵在“節奏”的不同,舊詩則完全是一種立足于文言的樂譜式節奏,新詩堅持的是一種基于口語的“說話的節奏”,“新詩的節奏是根據各種說話的語調里產生的,舊詩的節奏是根據一種樂譜式的文字的排比作成的。新詩是為說的,讀的,舊詩乃是為吟的,哼的……新詩的節奏根本不是歌唱的,而是說話的”[注]葉公超:《論新詩》,載《新月懷舊》,學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56頁。。陳夢家也強調,“所謂新舊詩,在形式上的區分是:舊詩的語言是‘文言’,有定句和一定的押韻法;新詩的語言是現代‘口語’,沒有定句和一定的押韻法”[注]陳夢家:《談后追記》,載《夢甲寶存文》,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151頁。。何其芳隨后指出,“格律詩和自由詩的主要區別……就在于格律詩的節奏是以很有規律的音節上的單位來造成的,自由詩卻不然”[注]何其芳:《關于現代格律詩》,載《何其芳文集》(5),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7頁。。可見,節奏類型的不同決定詩的新舊,是新詩人都比較認可的觀點。
不過,也有不太認可格律有新舊之分這種說法的,林庚就是一個顯例。在林庚的詩學視野里,中國詩歌語言是一個連續不斷的整體,它經歷了從四言到五七言,乃至九、十、十一言的歷史演變,遵循著從“自由”走向“格律”的歷史規律。與一般詩分新舊觀點不同,他認為新舊之間交集大于分歧,而這種交集的名稱就叫“形式”,“‘詩’原只是一種特殊形式的語言,詩如果沒有形式,詩就是散文、哲學、論說,或其他什么,反正不是詩。”[注]林庚:《再論新詩的形式》,載《新詩格律與語言的詩化》,經濟日報出版社2000年版,第39頁。在他看來,漢語詩歌的共同元素,并非常人所認為的雙聲、疊韻以及平仄對仗,這些不過是語言上的“講究”和裝飾,“對于詩歌形式來說,這種講求是附加的而不是決定性的;對于繁榮詩壇來說,其作用也從來只是從旁的而不是主要的。”[注]林庚:《再談新詩的“建行”問題》,載《新詩格律與語言的詩化》,經濟日報出版社2000年版,第82頁。甚至連詩歌的形式都談不上,“它并非詩的形式,也不足以代替詩的形式”。[注]林庚:《再論新詩的形式》,載《新詩格律與語言的詩化》,經濟日報出版社2000年版,第39-40頁。那么到底什么是詩的“形式”?什么又是詩的“普遍形式”呢?他認為,“詩的形式的真正的命意,在于在一切語言形式上獲取最普遍的形式”。[注]林庚:《再論新詩的形式》,載《新詩格律與語言的詩化》,經濟日報出版社2000年版,第39-40頁。這里要分兩個層次、兩道程序:一個是特殊形式,如幾言、詞牌、曲牌等;一個是普遍形式,它是對特殊形式的再一次萃取。對于這種“普遍形式”,他有過幾次理論總結。據他自述,經過從1935到1950年的十五年“摸索、創作、體會”,“我所得到關于建立詩行的理論不過兩條,一是‘節奏音組’的決定性,二是‘半逗律’的普遍性。”[注]林庚:《從自由詩到九言詩(代序)》,載《新詩格律與語言的詩化》,經濟日報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頁。在他的邏輯里,不管是新詩還是舊詩,都遵循著一種稱作“普遍形式”的規律,如此,他不僅為“舊格律”留下了地盤,也為新詩節奏預留了“半逗律”的空間。
對音節類型認識的差異,也決定了新詩節奏建設路徑的不同。堅持新詩新節奏的詩人認為,新詩就應該建立不同于傳統格律的“自然的音節”或“說話的節奏”。卞之琳曾以徐志摩詩歌為例描述了這種節奏的主要特色:
徐志摩的詩創作,一般說來,最大的藝術特色,是富于音樂性(節奏感以至旋律感),又不同于音樂(歌)而基于活的語言,主要是口語(不一定靠土白)。它們既不是直接為了唱的(那還需要經過音樂家譜曲處理),也不是像舊詩一樣為了哼的(所謂“吟”的,那也不等于有音樂修養的“徒唱”),也不是未來像演戲一樣在舞臺上吼的,而是為了用自然的說話調子來念的(比日常說話稍突出節奏的鮮明性)。這是像話劇、新體小說一樣從西方“拿來”的文學形式,也是在內容拓展以外,新文學之所以為“新”,白話新詩之所以為“新”的基本特點[注]卞之琳:《<徐志摩選集>序》,載《卞之琳文集》(中),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17頁。。
基于活的口語,富有說話節奏,不為哼唱而用于念,卞之琳總結的徐詩節奏特點未必完全符合實際,但從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他的新詩節奏愿景。在另一場合,他更詳細地說明了這種設想:“循現代漢語說話的自然規律,以契合意組的音組作為詩行的節奏單位,接近而超出舊平仄粘對律,做參差均衡的適當調節,既容暢通的多向渠道,又具回旋的廣闊天地,我們的‘新詩’有希望重新成為言志載道的美學利器”,希望這種新的形式能做到“音隨意轉,意以音顯,運行自如,進一步達到自由”[注]卞之琳:《重探參差均衡律》,載《卞之琳文集》(中),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75頁。。
四、“辨體”到底應該辨什么
通過上述梳理可知,不論詩文之辨,還是詩樂之辨,抑或新舊之辨,辨鋒所向都指向了格律,格律問題因而新詩文體建構的焦點,格律儼然成為新詩文體的“主導性”規范。那么,格律能否堪當新詩文體的第一標簽?對于新詩建構而言,還有沒有比格律更為重要的東西?這些問題需要進一步澄清。
第一,新詩辨體首先需要辨析的是有無詩性,而不是作為表征的形式。廢名曾經把這種詩性描述為“詩的內容”;南社詩人胡懷琛也提出過“詩的原理”說,“能合乎原理的無論新舊都好,不合乎原理的無論新舊都不好”[注]胡懷琛:《詩的作法》,世界書局1931年版,第12頁。。這里,所謂“詩的內容”“詩的原理”,跟現在所謂“詩性”有些接近。何謂“詩性”?用形式主義的術語來解釋,就是言語之非實用、非交流、自我指涉的隱喻性。首先,與日常語言不同,詩語是對語言常規的偏離,是對日常語言的扭曲、變形;其次,“詩的材料不是語言,也不是激情,而是詞”[注][前蘇聯]日爾蒙斯基:《詩學的任務》,載《俄國形式主義文論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217頁。。也就是說,單純的情感不是詩,用于實用、交流的語言也不是詩,詩是以話語為目的的語詞本身,“純以話語為目的,為說話本身而集中注意力于話語”[注][俄]雅各布森:《語言學與詩學》,載《結構-符號文藝學》,文化藝術出版社1994年版,第181頁。。最后,詩性語言形成,是一種對應原則的轉移,即“把對應原則從選擇軸心反射到組合軸心”[注][俄]雅各布森:《語言學與詩學》,載《結構-符號文藝學》,文化藝術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頁。。按照索緒爾語言理論,任何言語的形成都“選擇”與“組合”的結果,通俗講,我們說出每一句話都是一個“選詞-造句”的過程,“選詞”對應于縱組合、“造句”對應于橫組合;前者在若干聯想物中選擇合適的對象,其原理與隱喻(意象的相似類比)相同;后者是語詞的空間排列,方式與轉喻(相鄰事物的替代或相繼)相似。詩性言語的形成就是把“對應原則”從選擇軸投射到組合軸,從而造成詩歌文本連續不斷的意義流動。經由“選擇”與“組合”而形成的“詩性”,并不是一個單一元素,而是一種包容性的存在,它既含有情感這一“物質性”的原質,又有“有意味”的形式外殼,同時還需“以話語為目的”的表現性,它是一個多元渾成的復合結構。對新詩文體而言,追求“詩性”可能比講究格律來得更為關鍵。
第二,確定新詩文體“主導”規范,需要考慮新詩文體發展實際。決定某種文體屬性的,并不是單一因素,而是一種因素集群,在這些復合性因素中,總有一種因子起支配或決定作用,這個具有支配作用的東西,在形式主義詩學那里叫做“主導性”規范,“它支配、決定和變更其余部分。正是主導保證了結構的完整性”[注][俄]羅曼·雅各布森:《主導》,載趙毅衡編《符號學文學論文集》,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第8頁。。我認為,對中國詩歌而言,人們推崇格律,將格律視為詩歌文體的決定性規范,說到底還是一個傳統觀念因襲問題,跟詩歌文體發展實際有相當大出入。人們談論格律,談來談去無非是說不能忽視詩的“音樂性”遺傳。不錯,它是詩歌的原始基因,可是這基因一直在發生著變異也是事實,因此,不能死守這一原始孑遺,使之成為妨礙新詩生長的符咒。劉夢葦曾指出,詩樂結合有利有弊,詩歌太過接近音樂,明顯是弊大于利,其中一個重要文體損失是使詩“失去了自己底尊嚴與獨立的精神”,“中國詩到了詞,音韻上算是大有出息……但是,可惜得很,詞他太溺愛音樂了,太嬖寵音樂了,故犧牲了自己底一切去迎合女王,失去了自己底尊嚴與獨立的精神”[注]劉夢葦:《論詩底音韻》(上),《古城周刊》1927年1月第2期。。因而,他認為新詩應該吸取歷史教訓,取長補短,發展出獨立的藝術文體。“新詩承詞曲之后,理應存詞曲之長而去其短,以求進步;從較不自由進到自由,不,從較不藝術求進步到藝術”[注]劉夢葦:《論詩底音韻》(上),《古城周刊》1927年1月第2期。。在他眼里,對于詩歌的“音樂性”歷史遺產,需要采取審慎揚棄的態度;尤其不能把過去詩歌的原始性留存,強行移植、嫁接到未來的文體——新詩生命之中。這些認識應該說是非常有見地的。
第三,辨體需要正視文體混合發展趨勢。一個無法忽視的基本事實是,詩歌發展到今天,已經呈現出亙古未有的復雜局面。古今糾纏,中外相雜,分化組合,無法分辨。環顧當今詩壇,詩歌分蘗遍地開花,令人眼花繚亂:有從樂舞中剝離的,有從“歌”中分化的,詩之內部也蘗出相異的數支。更有甚者,又呈現“逆生長”態勢:詩與樂舞再結合,詩與歌再合體,甚至與其他文體雜交,衍出新的文體。因此,現今詩壇成了一種詩的“合唱團”:有配樂的詩,有裸聲的詩,有高歌的詩,有低詠的詩,有大聲讀的詩,也有默默看的詩。眾聲喧嘩,群響畢至,現有的文體知識已難招架復雜局面。
單就白話新詩主脈來看,變化也令人咂舌,素以聲音見長的漢詩,如今似有一種走向“無聲”的趨勢。當然,這股清流主指現代詩一派。如今的一些現代詩,已與“聲音”漸行漸遠,幾乎成了專供閱讀與靜思的品種。“詩最初是‘歌唱’,隨后是‘吟誦’的,到現代差不多快成為‘閱讀’的了”[注]梁實秋:《文學的美》,載《梁實秋文集》(1),廈門鷺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501-502頁。。為了說明這個問題,這里可以舉一個極端的例子。“一面鏡子在任何一間屋里/被虛擬的手執著,代表精神的/古典形式。光潔的鏡面/經過一些高貴的事物,又移開/石頭的主題被手寫出來/成為最顯著的物象。迫使鏡子/退回到最初的非美學狀態/……”(周倫佑《鏡中的石頭》)這類詩是充分“消音”了,不僅見不到“平仄韻腳”,甚至連“說話的節奏”也喪失殆盡,它把聲音能量轉化成了意象的理性組接。詩體變異必也引起了解詩方式的變化。對于此類制作,詩意的獲取,顯然不能求諸傳統的“讀”和“誦”,而必須另求現代的“想”和“思”了。這也說明現代漢詩已經走到另外一條道上了,單以“音節”為文體標簽的傳統做派已難奏效,中國新詩文體建構必須另找新的途徑和方法。
第四,新詩辨體須要注意文字型與語言型文學的分野。百年新詩史上,不少辨體者特別是具有古典傾向的詩論家,懷著歷史悲情指責新詩丟棄了舊格律,堅信“五七言”乃是漢詩最恰當的民族形式,并試圖重新建立一種漢詩的“普遍形式”[注]參看趙黎明《“文”與中國古典“新詩”派的價值取向》,《南京師大學報》2016年第5期。。應該說,這種情感是可以理解的,種種努力也是值得尊敬的。然而,我們也不能不指出,他們其實忽略了一個最基本的變化,即中國詩歌雖然同用漢文書寫,但語言形態已發生結構性改變,由過去的“文字型”詩歌變成了“語言型”詩歌。郭紹虞曾劃分“文字型文學”范圍說,“以前的文學,不論駢文古文,總之都是文字型的文學,不過程度深淺而已。現在的白話文學,才是真的語言型的文學”[注]郭紹虞:《語義學與文學》,載《照隅室語言文字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44-345頁,。。這種“文字型”詩歌要求,文字簡潔,足可以一當十;節奏鮮明,要求聲調鏗鏘;文字對仗,追求空間上的對稱效應。因為每一個字不僅自己要有獨立的秉性,所以每個單字都是“圣”,具有無可替代的功能,“在中國的詩歌傳統中,人們很自然地把構成五言絕句的二十個字比喻為二十‘圣’(sages)。”[注][法]程抱一:《中國詩畫語言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頁。很多古典詩論家所堅持的其實就是這種古典形態的單字詩,批評新詩和建構新詩的標準也是這種文字詩的標準,梁實秋的話就比較典型,“要解決新詩的形式格律的問題,大概不能不顧到中國文字的特性。中國文字是單音字。天然的宜于對仗,而對仗即是一種美;中國的文字講究平仄,而平仄即是中國文字的節奏之基本原則。”[注]梁實秋:《文學講話》,載《梁實秋文集》(1),廈門鷺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585頁。總之,說到底是他們并未認識到,中國文學已經發生“由音樂到文學的革命性改變”;更未認識到中國詩歌也已經發生“由‘文’到‘語’的大翻身”[注]龔鵬程:《文化符號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3頁。。因此其辨體實踐,往往充斥著悲情的錯亂、標準的錯位,并不能給中國新詩文體建構開出切合實際的藥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