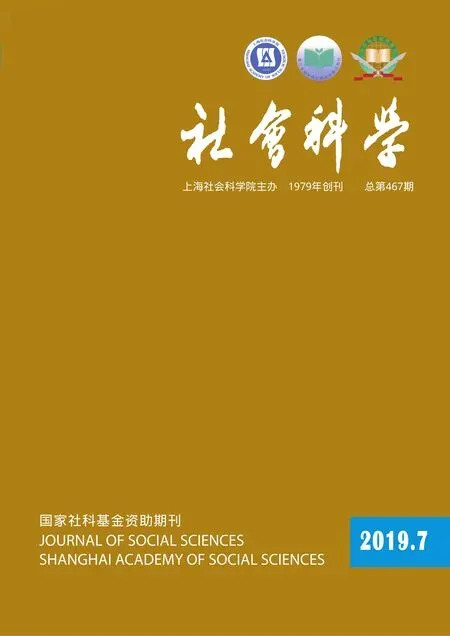何為善:儒家生生倫理學的解讀*
楊澤波
人類發展如此之久,追求的極致目標無非是善、真、美而已。倫理學追求善,知識論追求真,美學追求美。自我從事儒學研究以來,即將與善相關的因素劃分為智性、仁性、欲性三個部分,堅持三分法。近年來在建構儒家生生倫理學的過程中,又對這種方法進行了系統的梳理,使之成為這門新學說的核心標志。有了這種新方法,便可以對何為善這個古老話題,做出自己的界定和說明了。
一、欲性之肯定
雖說求善是人的目的,但在此之前,人必須能夠依靠物質條件存活在這個世界上。在儒家生生倫理學系統中,這方面的內容即為物質利欲,簡稱物欲,與物欲相關的因素叫做欲性。
儒家生生倫理學不否認物欲。“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的說法雖出自《管子》,但儒家同樣認同。孔子十分重視義利問題,首創義利之辨,但他對物欲并不持敵對態度,不走極端。孟子也一樣,他不是苦行僧,有飯食不吃,有車輛不坐,有隨從不要。義利問題的關鍵是看是否合道:合道,利再大亦不為過;不合道,利再小亦不能受。儒家不僅不否定物欲的作用,而且不將物欲等同為惡。恰如荀子所說,好色、好聲、好味、欲食、欲暖、欲息,是人的自然欲望,本身并不為惡,只有順其發展,爭奪生而辭讓亡,殘賊生而忠信亡,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這個不好的結果才為惡。在先秦儒家義利之辨之中,不管是孔子,還是孟子、荀子,都不否定物欲。沒有物質層面的生存,其他都說不上。[注]這并不是說人要是貧窮的,就可以不講道德。貧窮沒有一個絕對的值,即使物質條件十分貧乏,仍然不能放棄對于善的追求。民諺“屈死不告官,餓死不當賊”中的后半句,非常形象地表達了這個道理,體現了高超的生活智慧。這與以“替天行道”為口號的農民起義并不矛盾。農民起義主要是基于政治方面的考量。而政治意義的農民起義,從根本上說,也離不開道德的訴求。
盡管儒家不否認物欲,但不以此為重,更加看重的是義,是道德,始終堅持道德的理想主義。既肯定利,又看重義,如何把握兩者的關系,是一門大學問。先秦儒家是從人禽之分的角度來討論這種義利關系的。人禽之分意義的義利之辨本質上屬于價值選擇關系。價值選擇關系的要義有二:第一,在一般情況下,義與利并不矛盾,可以兼得,既可以要利,又可以要義,既可以要魚,又可以要熊掌;第二,在特殊情況下,二者又會發生矛盾,不可兼得,這時必須選擇價值更高的義,放棄價值較低的利,如果這樣做了,就成就了善,做了好人,反之,就不能成就善,就淪為了小人。牢牢把握人禽之分義利之辨的價值選擇關系,是準確理解儒家相關思想的關鍵。對這個問題的理解有缺陷,將人禽之分義利之辨的價值選擇關系理解為絕對對立關系,最終導致“存天理、滅人欲”等說法的出現,是宋明理學的一個重大失誤。
儒家歷史上對于物欲的肯定,一般不超出上述范圍。對今天而言,這個范圍明顯過窄了,除此之外,還應該關注法權問題。孟子與齊宣王對話時雖然講過“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認識到有了固定的產業,百姓思想才能穩定,百姓思想穩定了,社會才能太平,但沒有將其上升到法權的高度。這方面黑格爾的看法更有啟發性。黑格爾非常重視法的問題,法中的一個重要內容便是權利。每個人都有權利將其意志變成物,受此影響,物不再是自在自為的,而是屬于自己的,亦即自己對物有所有權。這一思想告訴我們,單純講物欲還不行,要成為政治主體,還必須將其上升到法權的高度。雖然這個話題嚴格說來屬于政治哲學范疇,但在倫理學中也需要引起足夠的關注。
二、仁性合于倫理是一種善
求善這個命題本身就意味著善有自己的準則,否則求善就沒有了依據,成為了不可能。因此,人們往往認為,求善必須首先制定善的準則,善的行為即是行為者通過學習掌握這些準則,從而對這些準則的服從。
但現實生活并非如此。自孔子創立仁的學說后,仁便成為了道德的根據,能否成德成善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看能否按照仁的要求而行。后來,孟子進一步創立了性善論,提出了“四心”的說法,將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并列,分別與仁義禮智相對,特別強調“四心”不是由外面取得來的,而是原本就有的,即所謂“我固有之”。無論是孔子的仁,還是孟子的良心,都屬于仁性的范疇。仁性的根本特點是內在。按照孟子所言,是非的標準不在外面,就在自己的心中,不需要他人告知,自己心知肚明,當惻隱時自知惻隱,當羞惡時自知羞惡,當恭敬時自知恭敬,當是非時自知是非。
人何以有仁性是一個重大學術問題。依據儒家生生倫理學,這當從兩個方面分析。首先,人作為一個有生命的物來到這個世界,原本就帶有一種生長傾向。這種傾向對人后來成德成善有著基礎性的作用,不僅使人可以成為自己那個類中的一員而非其他,而且只要順著這個傾向發展,遵循既有的行為規范,自己的那個類便可以得到有效的綿延。因此,人來到這個世界上原本就有規則,雖然這些規則還只是自然性而非社會性的,嚴格說來還不能以善相稱,但它畢竟為后來善的發展打下了根基。其次,隨著時間的發展,人們生存于社會生活中的各種因素,如社會風俗、文化傳統等,都會對內心產生影響。我們不能想象一個人完全脫離社會而生存成長,也不能想象這種社會生活不會對內心產生一定的影響。與此同時,人的智性有了一定的發展之后,也要利用它來思考道德問題,這種思考同樣會在內心留下一些痕跡。社會生活和智性思維對內心的這種雙重影響,會使人的內心形成一種東西,這就是倫理心境。生長傾向和倫理心境不能截然兩分,在實際生活中前者一定會發展成為后者,而后者也一定要以前者為基礎。包含生長傾向的倫理心境是其廣義,反之則是其狹義。
生長傾向和倫理心境是兩個不同的來源。前者是人來到這個世界的那個瞬間就具有的,后者則是人在社會生活和智性思維中逐漸形成的。生長傾向和倫理心境不僅來源不同,性質也不同。前者是先天的,即天生就有的,后者是后天的,即后天養成的。盡管有此區別,但它們又有一致性,都是先在的,具有先在性。了解生長傾向和倫理心境的先在性,是消除他人對我相關說法諸多質疑的關鍵環節。有人提出,我以倫理心境解說仁性,是一種經驗主義的做法,與儒家傳統不合,因為儒家論道德從來都持先天的立場,認為道德根據是“我固有之”,是“天之所與我者”。要消除這種誤解,必須明白狹義的倫理心境只是我詮釋仁性的一個步驟,除此之外,我還講一個生長傾向,生長傾向是天生的,對這個問題的證明不能訴諸于經驗。當然,狹義的倫理心境是后天的,但應當了解后天也可以轉變為先在。由社會生活和智性思維形成的倫理心境當然是后天的,但它在處理倫理道德問題之前早已存在了。這種“早已存在”,就是先在。而這種“先在”,根據我的理解,其實就相當于西方哲學講的先驗。人們對西方哲學這個概念的理解往往過于神秘化了,好像根本不能追問其來源似的。然而,如果上面的梳理沒有根本性過失的話,我們不僅對先驗有了與學界不同的理解,而且可以化解學界對我以倫理心境解說仁性的批評。[注]楊澤波:《經驗抑或先驗:儒家生生倫理學的一個自我辯護》,《社會科學戰線》2019年第2期。
具有先在性的倫理心境平時處在隱默狀態,這種情況就是學界現在常常講的“隱默之知”。隱默之知是生活中常常可以見到的一種現象。為此我曾舉過開車的例子:一個人用了很大的氣力學會了開車,這種技能熟練到一定程度之后,便在自己身上隱藏了起來,在不開車的時候,甚至忘記了自己有這個本領。但隱默之知不會永遠隱藏自己,一旦遇到相應的情況,就會顯現自身。恰如一個人多年沒開車了,當重新接觸一輛車后,又可以很自然地啟動上路,該轉彎時轉彎,該加速時加速,該剎車時剎車。倫理心境也是如此。平時沒有遇到道德問題,我們并不知道自己有倫理心境。可一旦遇到道德問題,它又會自己冒出來,告訴我們什么為是,什么為非,什么當做,什么不當做。熊十力以“當下呈現”講良知之所以是一個了不起的命題,值得高度重視,原因就在這里。
儒家這一思想有著重要的哲學價值,它告訴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具備一定思維能力的人,其成德成善的過程并不是從制定和學習新的準則開始的,而是始于發現和遵從自己內在的是非之心。[注]我提出這個說法,不是要否定學習對于成德的重要性。哪怕通過最簡單的社會觀察,也會明了,兒童遇事如何去做,總是要學習的,總是要大人教的。但對具有一定思維能力的成人而言,則不是這樣。這些“成人”遇事時內心早已有了是非的標準,不需要“臨陣磨槍”式的學習,只要發現并遵從內心的這些標準就可以了。但這里所說的“具備一定思維能力”很難給出一個年齡的標準。在這個問題過于較真,一定計較是多少歲,并沒有多少實際的意義。人們在從事道德行為,做出道德選擇之前,頭腦并不是空的,不是一張白紙,上面早就有了東西。這種東西就是建立在生長傾向基礎之上的倫理心境,就是仁性。倫理心境最奇妙之處在于,它雖然是后天的,但又具有先在性。這種先在性是實實在在的,包含著豐富的內容,就一般情況而言,可以直接判定何者為是,何者為非。善的生活不是從抽象原則,而是從自己的內心,從仁性出發的。孟子性善論最重要的價值或許只有從這個角度才能看得真切。
為了加深對仁性這一特點的理解,我們不妨將其與功利論做一個簡單的比較。功利論是西方道德哲學的一個重要分支,代表人物是邊沁。邊沁把趨樂避苦作為其理論的基礎。在他看來,趨樂避苦是人的本性。快樂有量的差異,如強度有大小,持續有長久,感受有遠近,人們可以依此選擇最大的快樂。如果一種行為帶來的快樂占優勢,它就是道德的、善的,反之就是不道德的、惡的。如果一種行為帶來的完全是快樂而沒有痛苦,它就是最大的幸福。大多數人都去爭取這種最大的幸福,也就達到了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這一理論后來為密爾所繼承。密爾同樣將快樂看做最重要的原則,但與邊沁不同,他認為快樂不僅有量的差異,也有質的不同。人不能只是追求肉體享受,還必須追求更高級的精神快樂,做一個不滿足的人比做一個滿足的豬更有意義。更為重要的是,密爾強調,功利論所追求的不僅是行為者自己的幸福,也包含一切與此相關人的幸福,甚至認為為別人而犧牲自己換取的幸福才是最高的幸福。由于密爾的努力,“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成了功利論的最高準則。在功利論系統中,凡是符合這一準則的,就是善,反之,就不能稱為善。儒家仁性學說完全不是這樣,它并不關心建構新的準則,而是強調這個準則自己原本就有,就在自己的心里。一個將善的準則置于外部,一個將善的準則置于內心,依據前者善是一個外在的對象,求善必須遵從外在的準則,依據后者善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求善必須反求諸己,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思路。
即使與德性論相比,孟子思想的特點也十分突出。近年來,德性論傳統開始回歸。德性論的重要特征是不以行為為中心,而以行為者為中心,關注的重點不是我應該怎么做,而是我應該成為什么樣的人,特別強調不能將學說的重點和希望置于某些行為指南或道德規則的法典化,應該將其落實在人的德性上。但德性論并非完全不關注準則。赫斯特豪斯即將這一準則作過這樣的表述:“一個行為是正確的,當且僅當,它是一個有美德的行為者在這種環境中將會采取的典型行為。”[注][新西蘭]羅莎琳德·赫斯特豪斯:《美德倫理學》,李義天譯,譯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54頁。德性論關注的是行為者個人的德性,儒家仁性系統同樣關心個人的德性,就此而言,二者有一定的相近性。但必須清楚看到,儒家仁性系統不僅講德性,而且進一步強調這個德性不是空的,里面有豐富的內容,有具體的標準。這些內容和標準就是良心,就是本心,就是道德本體。求善必須從這個本體出發,否則一切都將淪為空談。這些內容,德性論是不大關注的,至少不像儒家仁性系統這樣重視。
綜上所述,根據孔子仁的學說和孟子良心的學說,善的生活不是從制定和學習某些行為準則開始,而是從發現自己的內心開始的,通過內求找到自己的仁性是求善的第一步。仁性的一個重要來源是社會生活和智性思維,由仁性成就的善,本質上說即是對既有社會生活規則的服從。此前我曾撰文對倫理和道德這兩個概念進行了區分,指出倫理偏重于人倫之理,指人際關系中既有的行為規范,道德則偏重于人與道的關系,指由道中所得的那個部分。[注]楊澤波:《三分法理論效應三則》,《復旦學報》2019年第5期。按照這種劃分,這種遵從仁性而成的善即為倫理之善。
三、智性成就道德是另一種善
依據仁性行事,可以達成倫理之善,但這并不是善的全部。因為仁性是倫理心境,倫理心境來自社會生活和智性思維對內心的影響,所以由仁性而成的善只是對既有社會規范的服從,這一性質決定了其自身一定有其缺陷。
我在其他文章中對這個問題有過專門分析[注]楊澤波:《“存在先于本質”還是“本質先于存在”?——儒家生生倫理學對存在主義核心命題的批評》,《道德與文明》2018年第6期。,指出仁性隱含的缺陷首先表現為仁性失當。所謂仁性失當,是指仁性本身不夠合理,其正確性有待討論的一種情況。這種情況主要是就狹義的倫理心境而言的。倫理心境的一個重要來源是社會生活。如果社會生活沒有問題,倫理心境一般而言也是健康的。但如果社會生活存在問題,作為其結晶物的倫理心境很可能也存在問題。仁性隱含的缺陷還表現為仁性保守。這里所說的保守首先是指社會習俗的保守,其次是指倫理心境的保守。倫理心境來自于社會生活,社會生活中的一個重要內容是社會習俗。社會習俗盡管總體上與社會生活保持同步,但又有某種惰性的力量,一般又落后于社會生活。因為倫理心境要受到社會習俗的影響,而社會習俗本身有惰性的力量,所以倫理心境一般也跟不上社會生活的步伐。即使社會習俗完全可以與社會生活同步,作為其結晶物的倫理心境一經形成,同樣具有一定的惰性,其變化發展一般又落后于社會習俗。這兩個因素合在一起共同決定了,倫理心境從其產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經包含了容易趨于保守的種子。除此之外,仁性隱含的缺陷更表現為仁性遮蔽。仁性遮蔽是我特別重視的一種現象,特指由于受到外部影響,仁性有所扭曲,產生變形,受到掩蓋的一種情況。這種現象在當前情況下特別值得警惕。由于強大的國家機器可以運用輿論宣傳自己的主張,受其影響,人們很容易被“洗腦”,使倫理心境發生變形,人像沒有腦子一樣,跟著別人做出錯誤的決定。如果社會環境恢復正常,仁性仍然可以發出光亮,但仁性遮蔽所造成的巨大危害,絕對不可小視。仁性失當、仁性保守、仁性遮蔽這些問題具體表現各有差異,但原因沒有不同,都是對仁性缺乏真正的了解,這就是我說的“仁性無知”。仁性無知不是不能體驗到仁性,而是指對仁性缺乏理論層面的真正了解。
由此可知,由仁性而成的倫理之善只是對既有社會行為規范的遵從,只是實然,還不是應然。如何從實然進至應然,是一個必須認真面對的問題。既然仁性有這些不足,而其根源皆在仁性無知,依據三分法,要解決這些問題,一個有效的辦法就是動用智性,對仁性來一個再認識。因此,求善不能只講仁性,只滿足于倫理,還必須再往前走一步,求助于智性。在儒家生生倫理學系統中,仁性與倫理相應,智性與道德相應,這種由智性決定的善即為道德之善。智性之所以可以成就道德,是因為它有認知的功能。智性既可以外識,了解社會發展和道德生活有關的道理,又可以內識,對倫理心境進行深入的理論分析。外識和內識都不可缺,但內識更為重要。[注]楊澤波:《儒家生生倫理學中智性的雙重功能》,《華東師范大學學報》2019年第1期。這不僅是因為外識必須借道于內識,沒有內識不可能有好的外識,更因為內識涉及對內心的觀察,涉及對倫理心境的體悟,相對講也更為困難和復雜。因此,智性在道德之善中擔當的角色絕對不可或缺。換言之,以倫理心境為依據也可以成善,但它還不是人生的最終目的。要實現人生的最終目的,必須再上升一步,從這種狀態中解脫出來,啟動智性對自己的道德根據多問幾個為什么,比如人為什么有仁性?仁性為什么會對人提出要求?這些要求是不是合理?一言以蔽之,我們不僅要知道仁性告知我們應該怎樣去做,更要知道仁性為什么要這樣告知,其合理性在哪里。
這一思路通過康德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我們知道,康德建構其道德學說的進程較為特殊。康德注意到在社會生活中存在著一種普通的倫理理性,這種倫理理性十分管用,即使不教給人們新東西,人們也知道如何去做。但非常可惜,這種普通倫理理性還有很多不足,容易出問題,特別是面對較為復雜的情況時容易不知所措,陷入“自然辯證法”,甚至將非道德的行為視為道德的。為此必須對其進行哲學反思,將其加以抽象提高,上升到哲學的層面,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將我們上面追求道德之善的思路,與康德從普通倫理理性中抉發道德法則的進程相比,不難看出,二者有一定的相似性:它們都尊重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的倫理理性,但又不滿足于此,希望進一步將其抽象提升,使之上升到道德的層面,成為真正的哲學,真正的形上學。但儒家生生倫理學不是康德哲學的簡單重復。康德的努力還較為含混,缺乏方法論的基礎,以至于學界很長時間不大了解康德的致思路線,這種情況只是到了近些年才有了根本性的改觀[注]近年來,李明輝、鄧安慶在這方面貢獻尤多。詳見李明輝:《康德倫理學與孟子道德思考之重建》,(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4年版,第二章“道德思考中的隱默面向”,第四章“康德的道德思考”;鄧安慶《啟蒙倫理與現代社會的公序良俗——德國古典哲學的道德事業之重審》,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二章“康德哲學的實踐哲學轉向與啟蒙倫理的義理闡明”。,儒家生生倫理學則直接將這一思路置于三分法的框架之內,分別與仁性和智性掛鉤,不僅倫理和道德的劃分有了更為扎實的根基,心學與理學的關系也因此變得明朗起來,更易于理解和處理。
啟動智性追求道德之善,需要有勇敢精神。在一般情況下,動用智性對仁性加以內識以達成道德之善后,倫理之善和道德之善,其表現形式可能并沒有明顯的變化,不隨地吐痰還是不隨地吐痰,不亂穿馬路還是不亂馬路,有序排隊還是有序排隊,但因為有了智性的加入,其性質已經有了本質性的變更,不再屬于倫理,而是具有了道德的性質,成為了道德之善。但在特殊情況下,智性必須對仁性加以修正調整,此時需要有一種大無畏的精神。比如,“二戰”時期,身處戰爭前線的日本侵略者,絕大多數受到戰爭宣傳機器的影響,處于瘋狂狀態,這個時候就需要有人站出來,保持清醒的頭腦,對這種現象進行反思。這種人越多,戰爭對人類文明造成的損害就越小。但這種勇敢是要付出代價的,一些人很可能會因此犧牲自己的生命。又如,在文化大革命中,當大多數人跟著形勢走,爭當“造反派”,捍衛革命路線,做出瘋狂舉動,以為這樣做就是革命行為的時候,同樣需要有一些人站出來,以大無畏的反潮流精神,對這種現象進行深入的分析,保持理智的頭腦,甘當“保皇派”、“逍遙派”,甚至是“反動派”。這樣的人越多,社會偏向錯誤方向的可能就越小。但這個時候能挺起脊梁的,只是極少數,也只有這極少數人才能成為民族的脊梁。現在回想起來,在那個荒唐的年代我們犯了那么多的錯誤,固然有政治方面的因素,但人們盲目崇拜,丟失自我,缺少獨立思想與勇敢精神,也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原因。
近代以來,隨著社會的發展,宗教的力量遠不如前,但它對人們的生活方式仍然有著重要的影響。信奉宗教的人,會按照自己宗教的教條行事。但信眾很少能夠對這些教條加以根本性的反思,只是因信稱義,將其視為不可懷疑,不可動搖的真理。因為世界上有不同的宗教,這些宗教原本就存在著矛盾,有的還相當嚴重,一旦這些教條受到某些力量利用,必然發生沖突。這是文明沖突成為當今社會第一等問題的深層原因。要解決這個問題,一個有效的辦法,便是動用智性對自己的宗教信仰來一個徹底的反思。一旦如此,我們就會明白,宗教只不過是一套極為精致誘人的說法而已。信眾可以以信仰的方式相信它,但如果將其視為無可動搖,不能質疑的真理,就大錯特錯了。誤將信仰當作真理,信仰與真理嚴重錯位,是造成當今文明沖突的重要原因。要化解文明沖突,必須首先了解和接受這個道理,有英雄人物挺身站出來,對自己的信仰系統加以再認識,以至于對其進行變革,否則以宗教矛盾為中樞的文明沖突沒有破解的任何希望。
啟動智性追求道德之善,還需要謹慎態度。一方面,這是因為,社會生活十分復雜,常常會出現一些矛盾的局面,即使啟動了智性,也很難一下子給出一個明確的、大家都認可的答案。倫理學界常常爭議的一些兩難選擇,都屬于這種情況。另一方面,更為復雜的是,如果動用智性發現仁性有缺陷從而必須對其加以調整的話,很可能會破壞原有的道德規范。這種調整是否合理,能否有好的社會效果,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不是簡單啟動智性就可以萬事大吉的。如果考慮不周,隨意而行,很可能給社會發展帶來不利的影響。
這時儒家經權智慧的價值就顯現出來了。在儒學歷史上,成功運用經權的案例很多。《孟子》中的兩則材料特別有代表性。一是“援之以手”: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權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注]《孟子·離婁上》第十七章。
按照禮的規定,男女相接,手不可相互接觸。但如果嫂嫂掉到水里了,也可以伸手相救,否則便是豺狼之道。男女授受不親為經,嫂嫂落水伸手相援是權。
二是“不告而娶”: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注]《孟子·萬章上》第二章。
按照禮的要求,娶妻必須稟告父母,但是舜的父母不好,如果稟告了,就不能娶妻,不娶妻則沒有后代,廢人之大倫,所以舜可以“不告而娶”。娶妻必告父母是經,舜不告而娶是權。
《孟子》中的這兩則材料說明儒家對于行權有嚴格的要求,不僅要求必須出于好的動機,而且必須充分考慮到行動的后果。以這兩個案例來說,“援之以手”不是出于邪惡之意,而是救人之命,“不告而娶”不是為了滿足自己一時的利欲,而是不廢人之大倫。為了更好地學習儒家經權智慧,我認為需要提出一個新的概念,這就是“第二良心”。儒家生生倫理學將良心分為兩種,即:“第一良心”和“第二良心”。前者是在孟子意義上使用的。孟子所說的良心是天生的,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后者不是天生的,特指行為者運用智性能力,做出選擇時的善良意志,包含好的動機和充分考慮后果這兩項具體內容。雖然“第二良心”與“第一良心”性質不同,但二者并非完全沒有關系。“第二良心”來源于“第一良心”,因為人的行權之所以有好的動機并充分考慮其后果,是受“第一良心”影響的結果。沒有“第一良心”,單靠智性無法做到這一點,智性本身是不能決定方向的。
儒家生生倫理學重提古老的經權智慧,強調“第二良心”的重要,意在告訴人們,在追求道德之善的過程中,不僅要有勇敢精神,同樣要有謹慎態度。勇敢精神和謹慎態度是一物之兩面。勇敢精神是說一旦發現仁性蘊含著不足,容易流向弊端,必須加以調整,這種做法在特殊情況下有很大的風險,必須有自我犧牲的精神。謹慎態度是說在啟動智性的過程中,不能膽大妄為,要有一種敬畏的心態,戰戰兢兢,如覆薄冰,時刻想到智性選擇也可能出問題,為社會帶來不好的影響。我將二者區分開來,特別凸顯后一個方面之重要,意在說明,這很可能是現代社會出現重重混亂的重要原因。充分看到智性的局限,懂得必須慎用智性,是一門必須補上的哲學必修課。
四、仁性之倫理與智性之道德的統一是完滿之善
前面分別談了倫理之善和道德之善,這種區分的根據全在仁性與智性的不同。倫理之善的基礎是仁性。仁性是倫理心境,來自于社會生活的影響和智性思維的內化。倫理心境一經形成便存于內心,處于隱默狀態,遇事又會表現自己,告訴人們如何去做。在一般情況下,只要聽從它的要求,就可以完成具體的善行。因此,倫理之善是遵從社會既有規范的善。儒家心學一系的意義全在于此。但仁性并不足夠,因為仁性自身也有缺陷,如果對其缺乏真正的認識,很可能出現失當、保守,甚至遮蔽的問題,為各種弊端所困。因此,不能止步于倫理,還需要進一步將其發展為道德,追求道德之善。道德之善的基礎是智性。智性雖然不能離開仁性,但不滿足于此,要求對其加以再認識,檢查其來源,考察其性質,分辨其特點,直至在特殊情況下對其加以調整改動。由此達成的即是道德之善。因此,道德之善是通過智性對仁性再認識后,運用自由意志自覺選擇的善。倫理之善和道德之善不可能完全分開。善的生活,當始于倫理,止于道德。將倫理與道德有機結合起來,才能夠成為完滿之善。
將善劃分為倫理之善和道德之善,有助于對海德格爾關于追求“本真”存在的思想做出新的說明。“本真”存在是海德格爾追求的目標,這本身沒有問題,但他沒有三分法,沒有把倫理和道德區分開來,思想并不完備。儒家生生倫理學不同,在這個新的系統中,仁性屬于倫理,本質上屬于“常人”的范疇。“常人”雖然不是“本真”的存在,但自身也有價值,對此首先應該抱敬畏的態度。現實生活中出現的很多問題,不是“常人”有失本真,而是“常人”沒有做好,沒有達到“常人”的高度。當然,“常人”畢竟不是人生最終的目的,還必須啟用智性,對仁性進行再認識,乃至于必要時對其加以調整和改動,從“常人”態度中超脫出來,追求“本真”的存在,將倫理上升到道德。這一步工作并非一般想象的那般簡單,只要善于籌劃,勇于決斷,就可以萬事大吉了。由倫理上升到道德是一項極為復雜的工作,必須十分慎重。如果智性不受任何限制,膽大妄為,隨意而行,表面看是追求“本真”的存在,很可能是行一己之利,逞一時之快,實際得到的很可能是另一種形態的“假我”甚至“俗我”,給社會造成不好的影響。
至此,我們便可以對何為善這個古老的話題做出我們的回答了。善的生活需要對物欲有一個基本的肯定。人要活得有意義,首先要保證能夠在物質層面上生存。沒有物質層面的生存,道德難免成為一句空話。在現實生活中,善起始于仁性。人自來到世間便具有一種生長傾向,更為重要的是,人作為在世的存在,一定會受社會生活和智性思維的影響,這就決定了社會生活一般的道德標準作為一種結晶物早就保留在了內心,這就是仁性。有了仁性就有了是非的標準,遵循這種標準,不受小體物欲的干擾,就達成了倫理之善。但這還只是“常人”之善,只是實然,還要進一步追求道德之善。道德之善的要點是運用智性對仁性加以再認識。通過這種再認識,不僅可以對仁性有充分的了解,不再陷入仁性無知之中,避免失當、保守、遮蔽等問題,更可以發現仁性本身的不合理之處,主動進行調整甚至改造,使其歸為合理。總之,倫理歸屬于仁性;道德歸屬于智性。倫理是實然,是“常人”之善,是合于人倫之理的善;道德是應然,是“本真”的善,是得于道的善。心學屬于倫理,經過詮釋的理學屬于道德。倫理是有缺陷的、未完成的道德;道德是沒有缺陷的、完善的倫理。求善必須兼顧這兩個方面,次第而行,以仁性之倫理之善為起點,不斷前行,直至智性之道德之善而后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