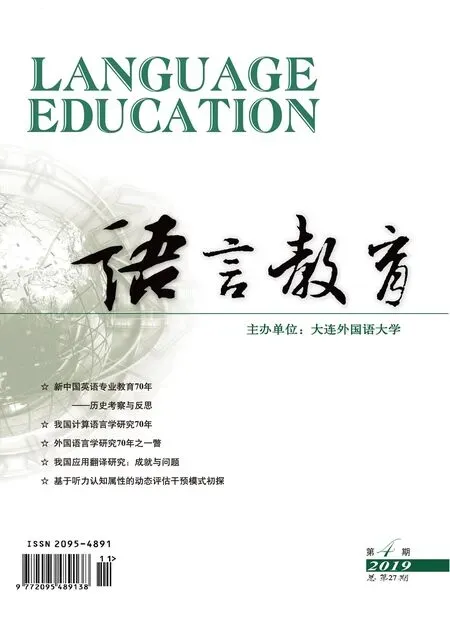外國語言學研究70年之一瞥
王 寅
(四川外國語大學語言哲學研究中心,重慶)
1.百年一瞥
石安石(1998: 683)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普通語言學”一文中將中國的20世紀百年的語言學研究歷史分為三個時期:
① 1920s至1940s的啟蒙時期
② 1950s至1960s中的起步時期
③ 1970s至今的進展時期
他所說的后兩個時期正是新中國成立70年來的語言學研究簡史,本文主要關心“國外語言學(主要是英語語言學)”在我國引介和發展的基本概況。若要將這個問題談透,條分細縷般地梳理清楚,若再配以較為豐富的數據調查,將所出版的專著和論文加以分類論述,保守一點說,恐怕也需要十幾乃至幾十本書才能完成這浩瀚的“工程”。本文只能提綱挈領地簡略述及,重點放在1978年改革開放后該學科的發展概況,且以“語言學的三場革命”為線索做一綱要性梳理,故謂之“一瞥”,僅供參考,難免掛一漏萬,敬請原諒。
在解放初期的十幾年中,我國的外國語言學研究主要以學習前蘇聯的理論為主,斯基與卡婭們在這個領域唱著主角,主要引介了馬爾等的語言學說;斯大林(1950)所發表的“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在我國語言學界也產生了很大影響,這正好迎合了時代的要求。語言學這門新興學科也得益于此,它作為一門學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在高等院校中的語言文學系普遍開設了語言學導論類的必修課,出版了幾十本語言學教材和專著。這一時期也譯介了部分西方語言學家(如梅耶、薩丕爾等)的論著。
我國真正迎來語言理論研究的春天是在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在四個現代化浪潮的帶動下,語言學界出現了一片繁榮景象。首先是1979年之后開始招收研究生和派遣公費留學生,全國范圍內出現了學習外語的熱潮。特別是英語教師,從來沒有如此深刻地感受到自己的使命感和受歡迎度。除此之外,還出現了如下熱潮:
① 一批外語界的學者出國留學,開始接觸到國外的語言學前沿理論;
② 國外最新語言理論不斷被引介到國內,國內學者如饑似渴般吸取;
③ 很多高校開始引進外教,使國外的很多嶄新的語言觀現身于國內;
④ 開始引進原版教材,論文、譯作、論文集、專著紛紛亮相于學界;
⑤ 外語類的期刊在這個時期得到蓬勃發展,涌現出十幾家核心期刊。
回顧我國70年來語言理論的發展簡史,前近20年主要學習和研究前蘇聯語言學界的專著和教材;因歷史原因經歷了10年的中斷;后40年呈現出一片“百花齊放”的景象,各種西方(特別是英美、歐洲大陸等)的語言理論紛至沓來,大有令人眼花繚亂、應接不暇之感,確實有一種讓人“迎頭趕上”的感覺。這一階段的研究又大致分為兩個階段:
①1979 至1999的20年期間,以引介西方理論為主,稍有評論和己見;
② 2000至2019的20年期間,在前20年吸收的基礎上注重繼承與創新。
在第一階段國人主要學習索緒爾、喬姆斯基、韓禮德、雷科夫、約翰遜等的論著,很多語言學理論流派和外語教學法紛紛亮相國內。正如姚小平(2001)所指出的,20世紀下半葉的語言學,領域越分越細,分支越來越多,邊緣學科不斷拓展。除主流學派之外,還有許多邊緣學科紛至沓來,如社會語言學、心理語言學、神經語言學、歷史語言學、方言學、應用語言學(包括詞典編纂、語言調查、外語教學法……)等等。在這個時期引介國外理論的主要貢獻者首推胡壯麟先生,他介紹了十幾位國外著名學者及其成果,如:特納女士(Turner)、赫德遜(Hudson)、韓禮德(Halliday)、哈斯(Haas)、康拉德(Conrad)、切夫(Chafe)、派克(Pike)、巴赫金(Bakhtin)、巴赫曼(Bachman)、吉旺(Givon)、理查茲(Richasrds)、雷迪(Reddy)等等。
現筆者以“20世紀三場語言學革命”為綱簡要梳理百多年來全世界語言學主要流派的發展簡史以及對我國語言學界的影響,本文只能是掛一漏萬地簡要抓綱。
2.三場語言學革命
2.1 概要
羅賓斯(Robins, 1967:103)在A Short History of Linguistics(《語言學簡史》)中指出“哲學是語言學的搖籃”,即每個時代的哲學理論產生了對應的語言學流派。他以其為主要依據,根據各個不同時期的西方哲學理論來梳理對應的語言學理論及其發展簡史①這對于我們來說,倘若缺乏西方哲學知識,閱讀和理解這本書是比較困難的,即使看了,也很難看透。。他在書中主要論述了6種西方語言學派:
① 前4世紀至18世紀:傳統語文學
② 19世紀百年間: 歷史比較語言學
③ 20世紀前60年:結構主義語言學
④ 20世紀中葉后: 轉換生成語言學
⑤ 20世紀中葉后:“系統”功能語言學
⑥ 20世紀末至今: 認知語言學
這六大語言流派中有四者發生在20世紀,由于(系統功能)語言學和認知語言學同屬一大陣營,與形式主義的轉換生成語言學相對立,據此我們擬將這四大流派歸結為三場語言學革命。

圖1
由于特定的歷史原因,我國解放初期的近二十年里主要譯介前蘇聯的語言學理論,少有引介歐美語言學家的成果,后來又因文化大革命的緣故而中斷了這一研究。因此,我國自20世紀70年代才開始全面了解西方語言學界的這三場革命。從上圖可見,這三場革命所涉及的研究內容在逐步向前遞增,不斷走向深入:索緒爾僅關注“語言”本身這個先驗性系統,筆者將其概括為“關門打語言”;喬姆斯基向前走了一步,關注“語言與心智”之間的關系,聚焦“關門打句法”,認為語言轉換生成自心智中的先天性普遍語法;認知語言學強調語言源自對“現實”的互動體驗和認知加工,與功能語言學一樣強調語言研究當持“開門觀”,批判索氏的語言先驗論和喬氏的語言天賦觀。
2.2 索緒爾的結構主義語言學革命
19世紀主要流行“歷史比較語言學”,將語言置于社會、歷史、文化的大背景下研究,通過語言之間的對比建構了語言的類型學(三大類型)和譜系學(十大語系),許多學者從歷時角度對印歐語系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比對。而索緒爾(Saussure,1916)一反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傳統,將語言從眾多因素中脫離出來,切斷了它與社會,與人之間的聯系,實施了語言研究的內指論轉向。他在“關門觀”的統攝下,認為語言本身就是一個先驗的、自治的系統(又可稱為“結構、形式”),可用“關系”做出統一的描寫。筆者(2014, 264)曾以下圖闡明了索緒爾結構主義語言學(Structuralist Linguistics)哥白尼革命意義之所在:

圖 2
索氏在對語言交際系統進行了一連串的二元切分之后,還采用了“留一棄一”策略,將自己的研究聚焦于:語言、內部、共時、形式,而拋棄了備受歷史比較語言學所青睞的言語、外部、歷時、實體。切下這四刀之后,語言之門越關越緊,直至將其結構主義學的研究聚焦于“形式”上,這就與西方哲學中的根基“形而上學”完全吻合。索氏所說的“形式”,大致相當于“系統、結構、關系”。據此,他分別從符內和符間關系加以論述,根據前者分出了“能指vs所指”,根據后者分出了“橫組合vs縱聚合”,這兩種關系都可通過語言的內部系統加以論述,而無涉語言之外的世界。因此能指和所指分別指“音響形象”和“概念”,而不是符號本身和所指對象,橫組合和縱聚合也只存在于語言系統的內部,這就構成了索氏結構主義語言學研究的基本架構,從而革了19世紀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命。
索緒爾的“結構主義”原則曾對許多學科(人類學、社會學、哲學、心理學、生物學、邏輯學、文學、音樂、美學、歷史、民俗學、建筑學、醫學、數學、教育學、宗教學等)產生了重大影響,一時間“關門”之風刮遍幾乎所有人文學科和部分自然學科,也正是由于他的這一研究方法,使得語言學成為一門領先的學科(伍鐵平,1994)。基于這一基本原理所發展出來的結構主義語義學,也采取“關門打語義”的方法,分析語義系統內部的各種語義場(同義場、反義場、上下義場等)。喬姆斯基依據“關門打句法”的策略,建構了他的轉換生成語法。韓禮德基于“系統”,在功能語言學的理論框架中增添了“關門打語篇”的研究方法,即僅依靠文本中所出現的連接詞語來解釋語篇連貫的規律。
索緒爾的語言觀從20世紀30—40年代開始傳入了我國,很多學者基于此討論了中國的文法革新;時至50—60年代學界基于此討論了“語言和言語”。在我國70—80年代,語言學界首先談到的外國語言學理論就是索緒爾的結構主義,高名凱在20世紀60年代就基本翻譯好足本的《普通語言學教程》,經葉蜚聲、岑麒祥兩位先生的多次校訂,于1980年由商務印書館正式出版,后一版再版,成為語言學者入行的敲門磚。人們開始對這位現代語言學之父有了更全面的認識和深刻的了解,是凡從事國外語言學(也包括中國語言學)研究的人,都是從他的這本名著開始自己的學術生涯。
在這期間,還有很多學者都論述過索緒爾理論在中國的發展情況,讀者可參閱趙蓉暉(2005)主編的《索緒爾研究在中國》、錢冠連、王寅(2015)主編的紀念索緒爾逝世100周年專輯《語言哲學研究(第三輯)》,以及王寅(2013a, b, c)專題論述了索氏哥白尼革命意義之所在。
2.3 喬姆斯基的TG革命
20世紀中葉喬姆斯基(Chomsky, 1957)出版了著名的Syntactic Structures(《句法結構》),創建了“轉換生成語言學”(Transformational-Generative Linguistics)。認為語言學理論不能僅局限于分析語言系統,描寫語言結構和成分,這充其量來說僅是在做“表面”文章,而語言學家必須回答“語言來自何處”這一核心問題,從而開啟了對索緒爾結構主義革命的又一場革命。
他基于笛卡爾的天賦論,從句法角度回答了這個問題,認為人們在心智中生來就嵌入一個“Universal Grammar(普遍語法)”(與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即LAD同義),這就是他所說的“黑匣子”(Black Box)。普遍語法可基于三個短語結構(S → NP + VP;NP → Det + Noun;VP→ V + NP),用樹形圖來解釋。這三個短語結構就相當于數學公式 (x + y)2= x2+ 2xy +y2,任何數字代進去,這個公式都可成立;同樣,任何符合條件的單詞代進上述三個短語結構,它們都可成立,從而可通過數學中形式演算的方法生成可被接受的句子,喬氏以此來解釋句法的心智成因,且還實現了科學主義的夢想(這與喬氏原本就是一位數學家有關),將人文研究的最后一個堡壘語言學納入到了形式化的研究陣營之中(而邏輯學、心理學等早已運用上了形式化的研究方法),從而創立了語言學研究的形式主義陣營。
喬姆斯基不再聚焦于描寫語言系統本身,而大力倡導從心智(大致相當于“認知”①這里僅說“大致相當于”,但在本質上有較大差別。喬姆斯基所說的“心智”具有天賦性,且還強調對現實的客觀反應;而認知語言學所說的“認知”強調體驗性,突出人的主觀能動性。)角度來探討語言的起源,從而開啟了語言研究的認知時代,因此喬氏也自認為自己是一位“認知語言學家”。但學界今天所說的“認知語言學”主要源自雷科夫和約翰遜(Lakoff & Johnson,1980, 1999)、藍納格(Langacker, 1987)、泰勒(Taylor)、德爾文(Dirven)等所建立起來的、以批判喬氏為目標的一種語言學理論。
國內自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介紹喬姆斯基的語言理論,很多學者還嘗試用TG理論解釋漢語的生成動因,一時間關于喬氏理論的各種研討喬氏已成為我國語言學界必談之人,以致于有些期刊的主編宣稱,若不采用形式化、數據統計的方法撰寫論文就不予發表。
筆者曾將轉換生成語言學的主要特征概括如下:
(1) 天賦性; (2)普遍性; (3)自治性;
(4) 模塊性; (5)句法性; (6)形式化而系統功能語言學和認知語言學與其背道而馳。
2. 4 (系統)功能學派之濫觴
索緒爾強調“關門”之策略一直受到很多學者的質疑,認為語言研究當奉行“開門”之道。弗斯于20世紀30年代深受社會學家馬林諾夫斯基(Malinowski)的影響創立了倫敦學派,反思了結構主義(包括描寫主義等)之不足,認為語言研究不能僅局限于結構,而必須關注語義,不能關門,而必須開門,強調語境的重要性。他的學生韓禮德(Halliday)傳承了弗斯的這一觀點,將索氏的“系統”觀念嫁接進來,提出了“系統功能語言學”(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重點論述了語言的三大元功能及其應用,為全世界語言研究開辟了一個與喬氏完全不同的方向,他的很多觀點受到認知語言學家的支持和青睞。
有的學者認為功能語言學包括認知語言學,有的學者認為認知語言學包括功能語言學,但不管怎么說,這兩個學派具有較大的互補性(王寅,2007:33),可劃歸同一陣營。據此戴浩一(1989)認為可將這兩個學派結合起來,建立一個“認知功能語言學”學派。
喬氏僅研究語言能力(語言生成自何處)而不關心語言運用,語用學家們提出了與TG不同的研究方向,主要論述語言在社會交際中的實際運用,探析語句與情景之間的關系,這與功能語言學密切相關。姚小平(2001)指出語用學發端于馬林諾夫斯基和弗斯,它深受功能語言學的影響,因此語用學可被視為其下的一個分支。
我國學者胡壯麟先生率一批留澳學者(赴澳大利亞師從韓禮德)于20世紀80—90年代將系統功能語言學全面引入我國,且于20世紀末成立了中國系統功能語言學研究會,吸引了國內高校一大批教師和研究生,為我國的外國語言學的理論研究和教學實踐做出了重要貢獻。
2. 5 認知語言學的又一場革命
學界一般認定1975年為認知語言學的發端年,這年夏天雷科夫(Lakoff, 1987)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聽了四位學者的講座(Kay關于顏色范疇的研究;Rosch的原型范疇論;Talmy關于空間概念關系的論述;Fillmore的框架理論),他深受啟發,決定與喬氏分道揚鑣,不再沿著轉換生成語言學的框架來研究生成語義學,公開打出了“認知語義學”的旗號,這可視為“認知語言學”(Cognitive Linguistics,下文簡稱CL)的先聲(參見他于1987出版的Women,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一書第17章)。此后他與約翰遜在1980年合作出版了Metaphors We Live By一書,轟動學界。Langacker于1987和1991分別出版了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er(上下卷)。德國語言學家Dirven于1989年春在Duisburg(杜伊斯堡)組織了第一屆認知語言學專題研討會,且成立了國際認知語言學協會(ICLA),創辦了Cognitive Linguistics期刊(每年四期)。德國的Mouton de Gruyter出版了Cognitive Linguistics Research和Applications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系列叢書,現前者已出版到第63卷,后者已出版到第43卷。這些觀點、專著、出版物和活動奠定了CL的理論基礎,吹響了全面進軍CL的號角。
CL基于喬氏理論的6大特征(參見上文),針鋒相對地提出了如下觀點:
(1)體驗觀; (2)差異觀; (3)依存觀;
(4)整體觀; (5)構式觀; (6)非形式化堅決認為人類的語言能力中包含先天因素,但絕非完全依賴于天賦能力,而主要是在后天通過人與現實世界的互動體驗而習得的;跨語言中不存在什么普遍語法,各語言有各自的特征,分屬不同語系的語言差異很大;語言和句法絕非自治的,而是緊密依附于其他諸如感知、對比、歸納等認知能力,與我們正常的吃喝拉撒正常活動不可分離;語言中的各層次(音位、語義、句法等)互相交融為一體,不可被切分為不同模塊進行單獨研究;語言研究中就只設一個單位“構式”,語言就是由它構成的;語言主要屬于人文學科,不能依賴形式化作出分析(我們需要數據,但不能僅依賴它)。
中國學者自20世紀末引介CL以來,在這一領域就開始有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出版了如下論著:
《認知語言學與漢語名詞短語》,張敏(1998)
《語言的認知研究和計算分析》,袁毓林(1998)《論語言符號像似性》,王寅(1999)《認知語用學概論》,熊學亮(1999)等等。
21世紀的頭20年里,我國學者在CL、系統功能語言學、語用學、語義學、文體學、修辭學等領域不斷發聲,各類研究論文和專著層出不窮,如雨后春筍般地成長,特別是逐步成為學界前沿的CL,本世紀初至今我國在這一領域的研究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大好景象,從零星介紹進入局部綜述,從消化吸收走向專題研究,從單語分析走向漢外對比,從理性思辨走向實踐運用,且結合認知科學、人工智能,使得CL得到長足的發展,一躍成為當前語言學界的前沿學科。
趙永峰還于2007、2008、2009、2010寫出了這四年的英語語言學的學科發展報告,以較為詳實的數據說明了我國當年外國語言學,特別是CL在我國的研究狀況。
2. 6 國外CL的本土化:體認語言學
川外認知團隊通過近年來的反復思考和深入研究,發現了體驗哲學和CL存在如下一些問題:
(1)雷科夫和約翰遜的哲學視野較為狹窄,只看到后現代的解構派,而不知道還有建設性后現代。他們(Lakoff & Johnson, 1999: 5)說:There is no poststructuralist person—no completely decentered subject for whom all meaning is arbitrary,totally relative, and purely historically contingent,unconstrained by body and brain. (不存在什么后結構主義(屬于后現代——譯者注)之人,沒有完全去中心的主體,它們認為所有意義都是任意的,完全是相對的,具有純粹的歷史偶然性,不受身體和大腦所制約。)
他們也對馬克思的辯證唯物論缺乏了解,未能充分認識到馬克思主義和后現代哲學中的“人本觀”。
(2)他們還保留了現代哲學中的“理性觀”,試圖通過體驗哲學重建理性(這一做法有點像哈貝馬斯企圖通過“交往行動”來重構理性)。Goldberg 所論斷的“構式一元論”也與后現代哲學所倡導的多元化不相吻合。
(3)他們試圖將體驗哲學和CL視為唯一正確的理論,可包打天下。而體認語言學持“象豹觀”(參見下文),認為我們不可能認清語言這只大象的全部,各個學派都是基于某一角度論述了語言之象的一個部分;我們只能在有限的人生中識得語言之豹的某一兩個斑點。
(4)他們所確定的學科術語很不周全,只有“認”而沒有“體”,在批判索、喬二氏的唯心論時,未能充分認識到唯物論的解釋力。很可惜在英語詞匯中沒有“體認”這一詞組,而漢語有,①參見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第1288頁。可譯成英語的“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下文簡稱ECL)。
為彌補其不足,川外認知團隊據此提出了將國外CL本土化的設想,擬將CL修補為ECL。后者基于前者,既長于斯,也高于斯,我們在《外國語文》2014年第6期上發表了題為“后現代哲學視野下的體認語言學”的文章,主要強調了語言研究中的唯物論和人本觀,大力倡導在后現代思潮中掌握和理解體認觀的基本原則(王寅,2013d),以能更清楚地闡明ECL的哲學立場,批判索、喬二氏語言理論中的唯心論和非人本的哲學基礎。我們認為,CL、ECL、(系統)功能語言學同為一大家族,它們與“形式主義”形成對立,是對索氏和喬氏兩場革命的又一場革命。
我們還基于后現代哲學在ECL中提出了“象豹論”,認為人類只能認清事物的某一或某些特性,而不可能識得其全部。國人常將成語“盲人摸象”和“窺斑見豹”視為貶義詞,以批評片面性,主張看問題要全面,這是無可非議的。但這兩個成語本身可另有新解:人們不可能在有限時空中摸遍整個大象,也不可能一下子見到豹子身上的全部斑點。我們永遠走在研究和探索的路途之中,只能是基于某一角度來論述語言這只大象,見到語言之部分斑點,而不可能認清它的全部真面目。因此后現代哲學主張為“盲人摸象”平反,為“窺斑見豹”申冤,為“偏見”申張,這兩個故事本身其實蘊含著符合事實的正確認識。宋代蘇東坡所說的“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那么人們會問在哪兒能識得廬山真面目呢?其實,就是不在此山中也識不得廬山真面目,不管在哪兒都識不得廬山真面目。我們永遠走在通向真理的路途之中。這也與老子所說的“道可道,非常道”基本觀點相吻合,這個“大道”是永遠說不出,道不明的,充其量人們只能說出其中的部分內容,所說出來的那個“道”只能是“小道”,這就是我們所說的“Metonymies We Live By”,本文題目“一瞥”與此也相吻合。
發生在20世紀的這三場語言學革命也充分說明,學者們只能在特定的年代里對語言持某種特定的認識,提出某特定的理論,離全面認識語言還很遙遠,或許可悲觀地說,我們永遠識不得語言的全真面目,包打天下的語言理論是不存在的。隨著時代的進步,知識的更新,視野的開新”之心態。
3. 結語
本文扼要梳理了新中國成立70年來的外國語言學的簡史,概述了20世紀發生在國外的三場語言學革命及其對我國相關研究的影響。隨著西方哲學研究在20世紀60年代出現了后現代主義的第四轉向,很多學者跳出了基于邏輯實證主義(分析哲學也屬其中)的窠臼,走出了遠離人文性的科學主義和形式化之陰影,既擺脫了索氏劃分“語言 vs 言語”且只鎖定前者的“關門派”之進路,也跳出了喬氏僅關注語言能力,用形式化方法研究句法的束縛,大力倡導從“生活世界”和“人本精神”的角度來研究哲學、認識語言。在此形勢的驅使下,(系統)功能語言學和CL應運而生,強調從社會、交際、情景、現實等生活世界的經驗角度來論述語言,密切關注語言在實際情景中的交際功能和認知機制,反思了索氏的先驗觀語言論和喬氏的天賦觀語言論,批判了他們無視人本因素、實際用法之誤導,開辟了語言研究的全新視野。但事物總是一分為二的,體驗哲學和CL也有自身的缺點,我們擬將其本土化為ECL,認為人類的心智、概念、語言等都是來自于“體”和“認”,使得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和人本觀重返語言研究的殿堂,很多后現代哲學的觀點也進入到語言學的研究領地,從而使得語言研究的面貌煥然一新。
根據“象豹論”我們認為,體驗哲學不可能是唯一正確的理論,后現代哲學也會被其他理論所替代,CL不可能包打天下,ECL也有被超越的一天,學術研究永遠是“長江后浪推前浪”,生命不止,探索不息。“山外青山樓外樓”、“吾將上下而求索”才是硬道理,科學研究的迷人之處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