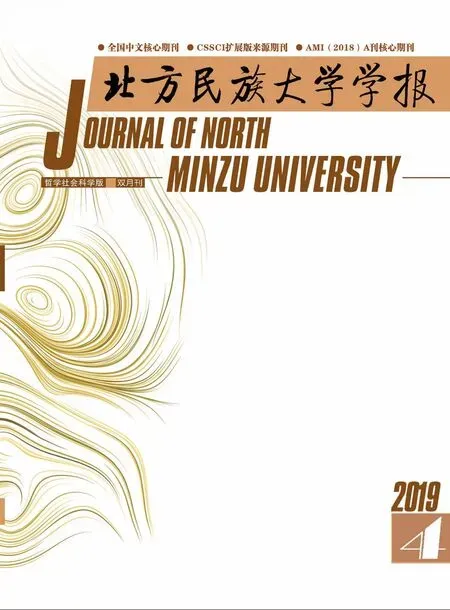鄉村女性的人生困局
——論馬金蓮小說中的女性生存狀態
海曉紅
(北方民族大學 學報編輯部,寧夏 銀川 750021)
“歷史上的中國,女性喪失了自我、喪失了自己的歷史、自己的文化和基本品格,處于歷史邊緣而沉淪于歷史地表。1949年‘男女平等’、‘婦女解放’的新思想讓大多數中國婦女走出了家庭,卻也在這一過程中,逐漸失去了作為女人的‘女性’,一步步演化為‘男人’,強調‘男女都一樣’,顛覆了性別歧視,讓女性與男性擁有了同等地位,但同時也否定了女性作為一個獨立的性別群體的存在。”[1]1978年以來,這一趨勢逐漸發生變化,城市女性開始探索屬于自己的精神空間和發展路徑,而對于鄉村女性,這條路還很漫長。在廣大農村,尤其是偏僻地區,女性仍舊被束縛于家庭,在舊式的軌道上中規中矩地扮演著家庭婦女的角色。寧夏女作家馬金蓮的文學創作較好地描摹了西部鄉村女性的生存狀態。作為一位長期生活于西北農村地區的作家,馬金蓮以獨特的視角講述了一系列關于鄉村女性的故事,閱讀其文字,可以深切地感觸到作者溫情的目光、隱忍的態度中觀照的鄉村女性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本文從村落遭際和城市想象等維度切入研究對象,從社會學角度闡釋馬金蓮小說創作中鄉村女性的生存狀態,以期為新時代背景下鄉土文學批評提供一些啟示,為鄉村女性的發展提供思路。
一、問題的提出
目前,學界對于馬金蓮創作的研究大多圍繞鄉土、底層、死亡、信仰、“80后”等關鍵詞展開,這些成果又多圍繞兩條學術理路展開:一是結合作家生平經歷,圍繞創作主題、美學特征、地域文化、族群文化等展開論述;二是以其他“80后”作家或相同題材創作者為參照,討論馬金蓮創作的獨特性。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有以下幾個。
一是從地域文化角度考察作家鄉村經驗、精神信仰、底層立場和文化觀念的養成。難能可貴的是,學者們在分析馬金蓮小說創作特點的基礎上,也指出了其創作中存在的問題,即具有懷舊色彩的鄉土書寫與嚴峻的社會現實之間存在無法磨合的矛盾,這種矛盾使其創作囿于詩意家園的消失和消失的不可抗拒性之間的惶惑、無奈中[2]。
二是將馬金蓮的小說創作放置在新時期以來的底層文學視域中進行考察,認為馬金蓮創作的底層性具有異質性的一面。有學者就指出,主流的底層文學將寫作重心放置于挖掘底層的現實苦痛,借助物質生活的困窘為底層伸張正義,與此不同的是,馬金蓮以抒情筆調詩意地描摹底層生活,與物質生活的貧窮相比,艱難歲月里的那份詩意才是其作品彰顯的核心[3]。
三是將其與其他“80后”作家加以對比,認為與大多數“80后”作家將創作重心落在商業文化的漩渦里不同,馬金蓮的創作扎根于土地,從日常生活倫理出發,彰顯了具有普世價值的人間光輝,用溫情的筆觸書寫了一個善良淳樸的鄉土世界[4]。
四是以欲望化寫作為參照,認為馬金蓮的創作是“根源于愛的鄉土童謠”。她以獨特的生命意識,用平實的語言書寫了寧夏西海固山區人們的家長里短、農事更替、婚喪嫁娶,在瑣碎的文字中隱含著自己的情感積淀、生命體驗,彰顯出對于生命的悲憫情懷[5][6]。
總體來說,關于馬金蓮創作的研究成果討論最多的是其主題中的苦難意識,從女性角度切入其創作的成果也有一些,但大多數屬于輕描淡寫類,目前,尚未見到全面探究其作品中女性生存狀態的相關研究成果。另外,縱觀馬金蓮的作品,女性在其中占有很大篇幅,且是其小說中不可或缺的關鍵形象之一,女性角色已經成為其小說構思的支撐所在,而鄉村女性的遭遇、困惑、品質客觀上彰顯了傳統文化背景下普通鄉村女性的生存狀態,對這類女性形象的全面考察,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一方面,對鄉村女性生存狀態的探究不僅是對作家創作研究的拓展和深化,也是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對鄉村女性深入了解、進而使其成為反觀現代鄉村女性生存現狀的一面鏡子。另一方面,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女性群體的發展進步對于推動家庭、鄉村乃至社會的發展進步具有重要的意義。與此同時,從文學意義上看,馬金蓮筆下的女性勤勞卻隱忍、頑強卻安于當下、心懷憂慮卻不挑戰陋習、期待愛情卻停滯不前、向往自由卻選擇留守,這一群體矛盾性格的文學呈現客觀上表現出這樣一種精神風景,即對于家以及家的承載地——鄉村由深情而至絕望或希冀有所改觀的心理軌跡,她們的遭際及現實生存狀況從側面表征著我國西部鄉村幾代女性勤勞保守的生存狀態。
二、鄉村女性的村落遭際
“村落既是一個空間單元,又是一個社會單元。”[7](3)在村落中,鄉村女性經歷著棲居、立足、安身和立命的不同人生階段,“婦女做女兒時,依托父親而獲得在父姓家族、村落‘棲居’的資格,獲得歸屬和生命的體驗;出嫁之后,依托丈夫在夫姓村落‘立足’,從而獲得夫姓家族、村落的安全感和歸屬感,并依托丈夫體驗自身的存在意義;亡夫之后,兒子便是婦女的依靠,是婦女安全感和歸屬感的來源,并且所有的農村婦女只有完成傳宗接代、依托兒子才能在夫姓家族、村落‘安身’,以之為最終歸屬;等到婦女年老,兒孫繞膝,完成了畢生任務,也就實現了人生的‘立命’,并在兒孫為她準備的體面的葬禮上完成最后的歸屬。”[8](30)因此,客觀上,鄉村女性的生命軌跡是清晰的,她們按照“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傳統理念過日子,這是一條看似清晰的人生道路。但是,從另一角度看,主體性之于她們,是一個模糊甚或不存在的概念;人生之于她們,意味著長大、結婚、生育、離世,她們是一個為了活著而不懈勞作的群體。《長河》中的“我”對人生的想象僅止于村莊女子的生命軌跡:像每個村莊里的女子一樣,長大、成熟、變老,“等這副身軀老成了一把干柴才會離開世界。這是每一個身體健康的人要走的路,除非半途遭遇不測,才能將這一常規打亂”[9](19)。所謂自己想要的生活,是一件遙遠的事情。由此,我們看到馬金蓮筆下不同年齡段的鄉村女性都在隨父棲居、隨夫立足,終而在鄉村安身、立命的軌道上經年不變。
首先,鄉村女性在隨夫棲居中安身度命。在《長河》中,伴隨著四季流轉的是個體生命的無常,這其中,女性的命運常常與男人相關,比如伊哈媳婦,她嫁給伊哈時,是一個“臉色粗紅”的女人,隨著伊哈“口喚”,伊哈媳婦改嫁了。令村民們深感意外的是,她居然改嫁到了川道里一戶家境還不錯的人家,于是,村莊里的女人開始感嘆伊哈媳婦有福氣,苦盡甘來,然而當伊哈媳婦再次出現在村莊里時,只帶給孩子幾個饅頭就匆匆離去了,“之后女人們議論說看她那笨笨的吃力樣兒,八成有身子了”[9](10~11)。這里,女人的存在映襯著一個男人之于家庭的重要性,而她的離去,客觀上表征著川道里另一個男人的存在,以及她為其傳宗接代的事實。小說中,沒有正面出現的男人是一個真正的存在,而正面出現的鄉村女人卻是為了烘托男人的權威,以及女人所扮演的勞作、生育的角色。在《繡鴛鴦》中,爺爺的罵聲不絕于耳,每當天氣干冷、刮西北風時,他就喜歡罵人,“罵奶奶是個邋遢婆娘,炕席上落有灰土!罵我父親火燒得不旺;罵牲口圈里那頭黑驢肚子不爭氣,老是下驢駒子,連一個騾子駒兒也不下,配種時明明用的是兒馬嘛,還花了錢呢;罵小叔叔放羊不經心,滿山洼趕著羊群胡逛呢,游蕩一天羊的肚子不還癟癟的嗎?罵這鬼天氣,好好兒的刮啥風,害得他的老沙眼又犯了……”[10](3)這里,爺爺是家庭威嚴的表征,無論他怎樣“罵”,奶奶都選擇無聲地順從,奶奶和其他人的隱忍無度,使得爺爺更加任性。這里,男人的權威無限擴張,而女性在逼仄的空間里隱忍度日。
其次,在家庭及村落的無形壓力中默泣。關于這一點,集中地表現在馬金蓮一系列以死亡為主題的小說中。在馬金蓮看來,活著或者死亡,都只是無盡生命長河中的一瞬。于是,生命無常便是鄉村女性經常需要修煉的人生功課。面對親人的離世,鄉村女性通常的做法是,在葬禮上失聲痛哭,而在日常生活中,她們選擇默泣。在《長河》中,面對唯一的兒子的離世,“馬云會的女人哭暈了”[9](17)。在《賽麥的院子》中,男嬰的降生和離世是賽麥母親命運的福音,也是她的最大苦痛。男嬰的降生和離世在改變家庭氛圍的同時,也改變了賽麥母親的命運,他的離開之時即是母親的大悲之際,從此,“母親的哭聲像夜半游蕩的孤魂,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悄然響起”,面對來自家庭和村落的無形壓力,“母親極力想撕破這張要命的令人窒息的巨網”[9](65~66)。葬禮上的痛哭及其他失態行為都是在世者,尤其是母親大痛大悲的表現,而日常生活里對于痛苦的消解方式則是暗夜里一個人的默泣。無疑,痛苦的雙重表達方式客觀上呈現了鄉村女性身心俱疲的現實處境,而“令人窒息的網”不只是男嬰離世的悲痛,更包含著曾經經受的壓力以及接下來還必須面對的各種困境。
再次,在傳宗接代的“自然使命”中負重前行。在農村,血緣的傳遞是通過男性后裔完成的,生兒子意味著祖宗牌位前的香火永不間斷,香火不斷就意味著這一宗族能夠傳宗接代[11](65),女性并不在血脈傳遞的序列中,因而,在家里的位置并不明確[8](47)。因此,當賽麥母親生下一個又一個女孩時,賽麥爺爺的神情是萎靡的,顯出“受了挫折的樣子”,對于別人眼里“懂事”“惹人疼愛”的賽麥姊妹們,爺爺表現出冷淡、不屑的態度,在“不過是幾個毛頭女子”的話語中,有著明顯的蔑視輕賤。如果爺爺的冷淡是出于接續香火層面的考慮,那么,賽麥父親的表現則多了幾分復雜的意味。面對“生不出兒子”的境況,他選擇“拍拍屁股”出走。在賽麥的世界里,父親是一個好吃懶做、不顧家小、一無是處的男人,但就是這樣一個男人,母親義無反顧且毫無悔意地跟隨著。在《馬蘭花開》中,馬蘭的父親也是類似的男性形象,賭博成性、惡習滿身、毫無責任感等是其典型特征。由此,我們看到,馬金蓮筆下的鄉村婚姻生活中,女性極少表達自己的主觀意愿,男性承擔的責任是模糊的,而其權力似乎是無處不在的。
最后,在婆婆及其他女性的圍觀中隱忍度日。在傳統家庭中,婆婆是一個特殊的人群,“是在男人的權力下討生活,逐步取得了局部的權力和地位,然后擺出一副‘統治者’的姿態,幫助男人實現女人的統治,她們是男性的同謀和共犯”[12]。在《馬蘭花開》中,婆婆對于馬蘭和嫂子是一種無形勝有形的力量,她所在的每一個角落都充滿了對兒媳婦的掌控,而兒媳婦們則在她的掌控下生兒育女、伺候老人,稍有不妥,婆婆便會通過各種形式進行“教訓”。如果說婆婆常態化的教訓已經使兒媳婦們產生了心理疲勞,那么,家庭之外熟人社會里女性同伴的圍觀則在無形中給予鄉村女性致命的“嘲笑”。面對賽麥母親又生一女兒的現實,本家二奶奶顯得分外興奮,在賽麥家出出進進無數次,喜形于色,她的兒媳婦們生的都是兒子,于是,她似乎有了“笑話”別人的理由,在她看來,應該一一休了她們,“世上女人多的是”。由于沒有生育男孩,賽麥的母親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壓力,夜里,她翻來覆去,感嘆命運悲苦[9](48)。而在周圍人眼中,賽麥的母親就是一個“笑話”,理由則是她生出了七個女兒,也沒有生出兒子[9](48~49)。由此,生男生女不只是傳宗接代層面的事情,也關乎家庭的面子,不光女人臉上“不好看”,“覺得矮人一截”,其公公婆婆也會覺得“低人一等”[9](49~50)。于是,鄉村女性理所當然地成了被議論的對象。對于鄉村女性而言,她們一邊自責,一邊充滿了無力感;而對于長輩,他們的一舉一動都顯示出生男孩的渴求以及由于未能生男孩的某種苛責和無法言說的糾結。
三、鄉村女性的城市想象
成長于農村的馬金蓮對鄉野生活有著天然的親切感,她的大多數作品取材于一個名為扇子灣的地方,留守農村、心向城市是其筆下大多數鄉村女性的生存狀態。比之于孫慧芬筆下鄉村女性強烈的“出走”愿望,馬金蓮筆下的鄉村女性更加保守,城市之于她們,僅是一種抽象的存在,城市在別處,它始終與想象同行。也正因為此,以城市想象為參照,鄉土文化對于女性的深層影響和城鄉二元結構中鄉村女性的困惑、矛盾在馬金蓮的小說創作中得到了突出表現。
首先,在馬金蓮的小說中,城市想象意味著小家庭的團圓。它不同于大多數鄉土文學作品中的城市想象,即一個全新的世界、一種完全不同于鄉村的生活方式、一種截然不同的命運,“尤其是在廣大鄉村女性的想象中,進城意味著命運的轉折和嶄新生活方式”[13]。在馬金蓮筆下,城市表征著一種家庭生活方式,即一家團圓的幸福日子。“向城而生”的女人大多是已婚女性,她們之所以“向城而生”,主要是因為那里有她們的丈夫,這種特殊的牽掛和依賴成為她們想象城市的重要基點。在鄉村女性心目中,比之于窮困的現實生活,分居兩地更加難以忍受。一方面,分居意味著“守活寡”。《大拇指和小拇尕》《馬蘭花開》《鮮花與蛇》等作品都在傳遞一個信息:那些留守鄉土的女性在日復一日的勞作后經歷著巨大的寂寞和孤苦,農閑時節或農忙休息時段,她們的心里滿載著對丈夫的思念。另一方面,分居意味著缺乏妥靠貼心的男性平衡婆媳、妯娌關系。在傳統的鄉村社會中,婆媳、妯娌關系對鄉村女性的日常生活具有重要影響,她們是鄉村女性日常生活是否愉悅的關鍵影響因素。在馬金蓮筆下,婆婆表征著規矩,她掌握著支配兒媳婦的權力。因此,馬蘭們一面按照婆婆的要求、暗示或示范行事,一面在心底暗暗做著自己的打算。妯娌關系的好壞直接影響到鄉村女性在大家庭中的地位,而地位的高低不僅受其原生家庭財富、丈夫地位高低等因素的影響,同時也是其自身能力的顯示。但也有例外,比如《馬蘭花開》中,馬蘭的娘家并不富裕,父親是個賭徒,母親帶著弟弟妹妹過著窮苦日子,馬蘭對家務一竅不通,但是她有文化,且個性溫順,因此,頗得婆婆喜歡,也是其嫂子心事的傾聽者,由此,她得以在婆家安穩度日,但是日子久了,也會有一些的矛盾浮出水面,這時,丈夫就會成為撫平她心理褶皺的“熨斗”,但是丈夫隔三岔五外出打工,馬蘭不得不為此不時地調整自己的姿態,以適應婆媳及妯娌關系的變化。
其次,金錢是城市想象的重要構成之一。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使得金錢成為影響鄉村超穩定文化結構的關鍵因素。《大拇指和小拇尕》講述了一個疼痛的故事:哈蛋一年中的多數時間都在外打工,家里的重擔自然而然地落到了哈蛋媳婦的身上。雖然男人每月都會寄錢回來,但是終究只能滿足日常花銷而已。面對日益增多的掙錢機會,哈蛋媳婦終于耐不住寂寞,想出去掙錢,可是孩子無人照看,她先后帶著孩子外出干活兒、將孩子鎖在家里或放在窖里,然而不幸降臨了,孩子在經歷了暴曬、電擊等災難之后,最終,蛇鉆進了孩子的嘴里,悲劇發生了,悲劇留給人們的不只是孩子離世的苦痛,更有新時代農村女性無力也無法邁出家庭的現實矛盾,以及金錢給人帶來的傷痛。《富漢》講述了王牛子家靠挖煤發家的故事,在該作品中,所謂“富漢”,如同王牛子手里的氣球,膨脹起來,無人能及,憋下去時,僅看到王牛子哇哇大哭的嘴巴。如同學者所指出的,鄉村文化的脆弱之處在于,“一條項鏈、一方頭巾,這些看似無關緊要的細節卻奏響了鄉村文明崩潰的序曲,冷卻了傳統價值倫理的脈脈溫情”[14],金錢之于鄉村文明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再次,城市之于鄉村女性,僅止于守望,她們始終未能走出長久生活的安全區——鄉村。誠然,“在中國當代發展的情景下,農村成為她們想要掙脫和逃離的生死場,而不是希望的田野、希望的‘空間’”[15],然而,馬金蓮筆下的鄉村女性始終留守在鄉村,這與其說是保守、膽怯,不如說是對自身責任的認知使然。在《鮮花與蛇》中,懷孕的阿舍期盼著外出打工的丈夫爾薩的歸來,當每日的期待變成一個又一個豪言壯語之后的“匆匆離去”時,阿舍只能以鄉民不屑的某些年輕媳婦的抉擇安慰自己。作者描述道,也有一些“不安分”的年輕媳婦不愿意留守,希望跟隨丈夫外出打工,這樣不僅能夠專心“拉扯娃娃”,“給男人做飯”,也能掙到一份工資,“好歹一家人是團圓的”[9](193)。而事實上,阿舍之所以安于現狀,不是她不想走出鄉村,而是她對自身所處位置進行判斷后做出的選擇。關于這一點,有學者提出了學理性的解釋:“女人心中的宿命觀念、男權意識、依附品質使女人放棄了自己把握命運的權力,女人把自己當作花瓶、擺設、勞動工具……起著滋潤男性的作用。長期的非主體感,使女人愈來愈模糊了自我認識、愈來愈認同罪劣觀念、是應該在苦役式生存與依附中贖罪的對象”[16]。因此,在阿舍的心里,照顧公婆、種地、生育等事務是其理所當然的責任。同樣,《馬蘭花開》中的馬蘭借助于自己不屑的外力(嫂子)試圖出走,終而在家庭責任、丈夫的說服、公公婆婆的威懾等多種力量的合謀中“出走失敗”。《鮮花與蛇》中的阿舍也是如此,她老老實實地在鄉村留守,可是她何嘗不想出去呢?作者如是寫道:“她的內心是渴望出去的,一來和丈夫早晚守在一起,二來見見外頭的大世面”[9](193)。傳統文化和文化慣習的共同影響,使鄉村女性將心底真實的渴望深藏,她們本能地行使著家庭女性的角色。于是,“出走”被擱置,“希望”流產,留守成為她們余生的常態。在這個意義上,馬金蓮筆下的鄉村就是生活本身,其地域環境、文化生態等共同制約著鄉村女性的日常生活。
四、余 論
鄉村女性的文化是直面現實的文化,無論面對多大困境,她們選擇的初衷始終是最根本、最直接的生存問題,而較少考慮精神層面的因素。因而,更多的時候,我們看到馬金蓮筆下的鄉村女性忙著耕作、忙著生孩子、忙著伺候老小,她們的姓名被隱沒或忽略,人們理所當然地稱呼她們為“某某的女人”或者“某某媳婦”,她們的生命之重主要表現為鄉野日常生活的消磨、樸素平庸日子里的寂寞、生“兒”不能的焦慮,以及鄉村文化制約而不自知的煩悶。她們的人生之旅是從父家向夫家位移的過程,她們的行為舉止是鄉村戒律的傳聲筒。鄉村之于她們,是難以走出的安全區;城市之于他們,則意味著一種全然不同的生存方式。然而,在她們的生命哲學里,“出走”意味著“被說”,固守則意味著貧窮、孤獨、無趣,但是她們寧愿在貧窮里掙扎,也不愿或無法走出鄉村。究其原因,大多緣于文化水平對其個性和命運的影響、傳統鄉村倫理觀念的束縛、鄉村女性的主動依附和被迫依附[17],以及主要活動于社會場域,缺乏自我成長的獨立空間,使其對自身發展缺乏規劃。
馬金蓮的文學創作忠實記錄了現代化背景下處于鄉土一隅的女性生存狀態,其創作能夠直面鄉村女性的生存困境,對這一群體生存狀態的書寫豐富、豐盈了當代文學的女性形象圖譜,而且,其創作提供了一種想象鄉土的視角和方式,即以女性視角審視靜默無聲的鄉村,以女性的隱忍彰顯鄉村發展現狀。作為女性作家,馬金蓮天然具備的細膩、善感、體察入微等能力,使其作品往往顯現出較多的柔軟、細膩和溫潤,同時,其細膩敏銳的感知和捕捉能力,為女性在與整個世界的堅硬對抗中提供了堅韌溫婉的立足點[18]。但是其在女性生存狀態書寫中的不足也是較為明顯的,比如,女性日常生活的平面化書寫,對鄉村女性文化心理的種種痼疾等缺乏必要的批判,而往往包含著烏托邦的想象。如同陳曉明所指出的,就當今女性作家僅有的“女性意識”而言,主要是在個人經驗范圍內的自省意識,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個人話語的副產品,因而,多少具有“女性意識”的作品難免生活面狹窄,無力與現實對話[19](90)。這是后新時期女性小說普遍存在的問題,馬金蓮的作品也同樣存在。我們相信,以馬金蓮的文學天賦和勤奮,一定會在未來的創作中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