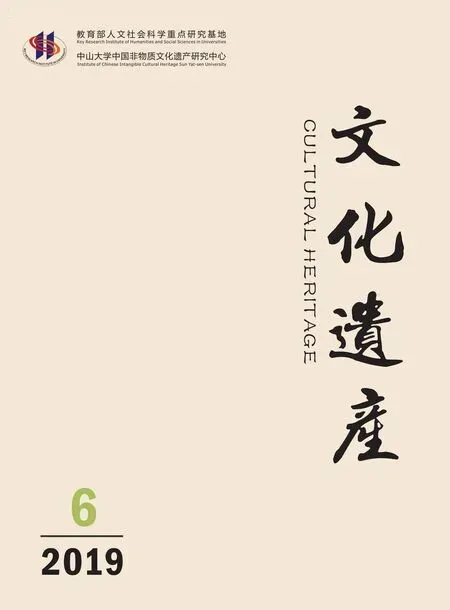回歸·彌合·傳承:新耕讀傳統中的家園遺產*
彭兆榮
引 言
“耕讀傳統”是中華民族農耕文明中重要的文化遺產;今天,我國的許多地方,特別是廣大鄉鎮,紛紛以其為資源、為名義、為主題進行各種各樣的設計規劃活動。學術界也出現了不少專題討論;然而,卻鮮見對這一重要的文化遺產進行梳理、辨析、厘晰,當然也就難以“文化自覺”的態度,實事求是的方式進行繼承,開發上自然也會出現一些問題,特別是絕對化傾向。
事實上,在耕讀傳統這一文化遺產中存著多種相互“撕裂”的因素,這些因素不獨與歷史傳統有關,亦與中國村落政治,特別是宗法制度有關。所以,我們在繼承和發揚這一傳統時,“回歸”——回歸這一傳統的本真和本相;“彌合”——根據新時代的需要進行辨析和改造;“傳承”——在此基礎上進行創新性繼承和發展。只有做好這些工作,才能更好地發揚這一文化傳統。
回歸:農耕傳統中的文化基因
不言而喻,“耕讀”作為農耕文明的一種文化表述和圖景,生動地反映了鄉土歷史的實情和實景。“讀”的歧義少,與今日的意思起伏不大。《說文解字》釋:“讀,誦書也。從言賣聲。”“耕”者,文字分類為“田族”;由“耒”(農具)與“井(田)”組合而成。(1)谷衍奎:《漢字源流字典》,北京:語文出版社2010年,第977頁。《說文解字》釋:“耕,犂也。從耒,井聲。一曰古者井田。”(2)(漢)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第93頁。對于這一說法,有些學者持謹慎有態度,許倬云說“中國古代有無井田確切性質,至今是紛挐難決的問題,自從《孟子》提起井田制度的構想以后,學者一直在努力彌縫各種相互抵觸的敘述。”(3)許倬云:《求古編》,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第123頁。這也反映在對“耕”的闡釋上;日本學者白川靜認為,“耕”的正字為“畊”;而學術界認為“耕”等于“耒”加“井田”的假設未能得到證實。由于缺乏古代原始字形資料,目前無法確知“耕”與“畊”的構成原委。(4)[日]白川靜:《常用字解》,蘇冰譯,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年,第138頁。“耕”字在甲骨文中未見,從目前的文字資料看,始見于篆文。不過,無論“耕”的最原始的本義是什么意思,都不妨礙對這一個字的意會語義:耕作、耕種、耕田。從其造字字形看,已經進入到了牛耕的時代,即農耕文明已經進入到了用牛替代人耕于木耒的時代。
“耕”與“耒”關系密切。作為古老的農耕文明,農具不可或缺。從現存的文字資料看,在古老的214個象形字中,“耒”即在其列,它在甲骨文中就是犁具形象,《說文·耒部》:“耒,手耕曲木也”(5)(漢)許慎:《說文解字》,第93頁。,說明最早的犁具系由人來完成的,后來由“犁”(牛)替代。(6)[美]魯道夫·P·霍梅爾:《手藝中國:中國手工業調查圖錄(1921-1930)》,戴吾三等譯,北京: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45頁。這樣的判斷是有根據的。《周易·系辭傳》有“神農氏斫木為耜,揉木為耒。”(7)《周易》,楊天才等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607頁。初,耜、耒皆為人力,至叔均才開始以牛耕耘;《山海經·大荒經》曰:“叔均始作牛耕。”(8)袁珂:《山海經校注》,北京:北京聯合出版社2014年,第331頁。在農具的演變史中,“耒”顯然是一個重要的階段性農具。陳夢家根據殷商卜辭的材料提出這樣的觀點,即卜辭和金文中都沒有“耕”字,古以耒耕。可證殷商卜辭中的耒耕為人耕。(9)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540頁。張光直認為耒很可能是商人最基本的翻土耕田工具,即帶長柄的工具。學者們認為那是一種協同性耕作的工具。(10)張光直:《商文明》,北京:三聯書店2013年,第244-247頁。古籍中二者可單獨使用,亦有連用的。對其考據,近人又已發展出了若干新假設。(11)許倬云:《兩周農作技術》,載《求古編》,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第125頁。
《齊民要術》卷第一便對農具做了“詞與物”的考釋:
《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遂耕而種之。作陶,冶斤斧,為耒耜、鋤、耨,以墾草莽,然后五谷興,助百果藏實。”
《世本》曰:“倕作耒耜,”“倕,神農之臣也。”
《呂氏春秋》曰:“耜博六寸。”
《爾雅》曰:“斪謂之定。”犍為舍人曰:“斪,鋤也,名定。”
《纂文》曰:“養苗之道,鋤不如耨,耨不如鏟。鏟柄長二尺,刃廣二寸,以刬地除草。”



中國傳統的農耕文明,是天時與物候的合作;在農具方面也有反映。“耒耜”即為范,其形制得天象之啟示。徐中舒在《耒耜考》中認為:
甲骨文及銅器之方……象耒的形制,尤為完備,故方當訓為一番土謂之坺,初無方圓之意。方之象耒,上短橫象柄首橫木,下長橫即是所蹈履處,旁兩短畫或即飾文……古者秉耒而耕,刺土曰推,起土曰方,方或借伐發、墢未建造等字為之。
許進雄評述:“方為耒形之說為一般人所接受,旁與方的不同,從字形看在于有無一塊橫而長的東西。文字的創造,對于抽象的意義,除了用音的假借外,就是以有關的事物來表示。旁有四旁、旁邊之意,其意義與犁耒的形制或操作有關的,除了犁壁以外,沒有其他更恰當的東西了。”(14)許進雄:《甲骨文所表現的牛耕》,載《許進雄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322頁。“方”與“耒”的“象形”闡釋是否中允,筆者在此不作評述,但是,“方圓”原本是天地的最早的經驗認知,因此,對耒的另一種解釋亦頗為有趣,丁山認為,耒之形貌酷似天象“大辰圖”,民間稱為“犁頭星。”天空的大辰本是后稷布置用以啟發農人工作的。農人一見這耒形的“大辰”當黎明之前正現于天空午位,就是一年工作的開始,謂之“農祥”。(15)《爾雅·釋天》:“天駟,房也。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史記·天官書》:“東宮,蒼龍,房,心。心為明堂,曰天駟。尾為九子,曰君臣。”參見丁山《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考》,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第26-28頁。
中國自古講究“天時地利人和”。所謂“天時”,指以“天”為“時節”依據,并與地候相和。故“(時)辰”有天辰和地辰,二者相輔相成。天辰是星象,地辰是農具、蟄蟲。而“大辰星”即以“辰”命之,可知其之重要。其主春時、農時。《說文》:“晨,房星,為民田時者。”“辰者,農之時也。故房星為辰,田候也。”(16)(漢)許慎:《說文解字》,第141、311頁。有的學者認為,辰如龍象。而如果錯失農時,便為大錯;亦即恥辱,《說文》釋之:“辱,恥辱也,從寸在辰下。失農時,于封疆上戮之也。”(17)(漢)許慎:《說文解字》,第311頁。辱從辰,辰為農時,誤失農耕季節,即觀天象的失誤,將影響一年的生計,所以把失職者殺掉。(18)鄭重:《中國古文明探源》,上海:東方出版社2016年,第260-261頁。
如果上述考述得以成立,那么,古代的耒、耜、犁等重要農具不僅存在著一個由人力向畜力發展的演化軌跡,還透露出了“天時-地利-物候”之間的具象性關系。當我們重審“耕犁形具-大辰星象-龍的形象”之間的關系時,我們似乎有了驀然醒悟的感覺。僅從農具所契合的“天時、地利、人和”的精神中,人們更為真切地看到了具象性的“耕”中的復合性文化因子。
彌合:耕讀傳統中被撕裂的因素
毫無疑義,“耕讀”作為中華文明的農耕傳統,學界皆有共識。然而,對于“耕讀傳統”的產生及原型,學術界有不同的看法,李存山認為:“中華民族的先民在伏羲和神農之世, 就已從漁獵生產逐漸進化到了農業文明。在堯、舜時期, 就已經有了崇尚人倫道德的價值取向;至遲在夏、商、周三代, 中國就已經有了以‘明人倫’為宗旨的學校教育。農業文明加上以‘明人倫’為主的學校教育, 就是中華民族和中國文化的耕讀傳統。”(20)李存山:《中華民族的耕讀傳統及其現代意義》,《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17年第1期。多數學者認為“耕讀體系”肇源于春秋百家爭鳴時期,至漢文帝時期創建成“耕讀型”國家,此后的歷代王朝沿襲其為治國方略,漸漸發展,尤以唐朝、宋朝為興盛,至清末逐漸沒落。這就是說,中華民族的耕讀文化傳承了兩千多年,并成為傳統士人立命之本。(21)參見梁媛《文化傳承視野下的新耕讀教育模式論》;文豐安《新耕讀文化的現實困境及發展途徑》,《重慶社會科學》2017年第8期。筆者對此說并非不同意,只是認為很不充分。我們相信,中國的“耕讀史”可以從中國的文字文獻中找到相應的表述和記述,卻難以這些文字表述為終極依據。很多因素要到農耕中去尋找。
在我國,麥作文明和稻作文明的起源問題有不同的說法,隨著新的考古材料不斷被發掘出土,使得最終的定論難以確定。較近的材料:1992年,中美兩國的農業科學家在江西調研,“美方于1996及1998年已發表兩次報告,證實長江中游是世界栽培稻及稻作農業的搖籃,江西萬年仙人洞等遺址的居民距今一萬六千年前已以采集的野生稻為主要糧食,至晚距今九千年前被動定居的稻作農業業已開始。”(22)何炳棣:《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1頁。最近在媒體上又報湖南有了考古新發現,據說可將稻作文明前推至14000-18000年,未見最后證實。無論我們采用哪一種數據,都遠比文字記載的“耕讀傳統”起始時間早得多,如果我們將“讀”推往“前讀書時代”即,將其視為“學習”“知識”,而不只是以“文字”為媒介的“讀”(誦書),結論就要遠推到史前,即葉舒憲教授所主張的以多重考據為證的“大傳統”。(23)參見葉舒憲主編《重述神話中國》,上海:上海交通大學2018年。
此外,作為一種特殊的、以農耕文明為背景的、中國特色的農業遺產,并演化成為人們最為普遍的一種生活生活場景和狀態:“耕讀并舉”“半耕半讀”“耕讀傳家”等。必然包含了更為廣闊的領域,比如,亦可將“耕讀”延伸到不同的階層、生業等,如《孟子》曰:“士之仕,猶農夫之耕也,”故“不耕不可。”(24)(北朝)賈思勰:《齊民要術》,繆啟愉等譯注,第35頁。由是可知,無論“耕讀”關系如何,它都已經成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的、復合性文化遺產。對于這一份遺產,今天,大多數人們以囫圇的方式解之、續之,或作“文化資源”,或作“文化符號”,或作“文化品牌”,而不作歷史的分析和深度的考釋。竊以為皆不可取。以歷史的演化線索觀之,我國的“耕讀傳統”既具有政治道德倫理、知識融匯的“立基”之功德教化作用,又表現出等級分化、尊士卑農的“撕裂”矛盾與悖論。以下幾個是需要特別厘清的點和面:
1.總體上說,中華文明在類型上屬農耕文明。其特點是:以土為重,以農為本。“社稷”乃國家之相。農耕者重“土”;“社”為濃縮。“社”者,古人以土地滋育萬物,立社祭祀。“社”在譜系上的神圣性,亦與“英雄祖先”相配合。古代“后土為社”“禹勞天下而死為社”等說法。“社”故神圣祭祀和祭祀場所,也演化成公眾聚會的地方。《詩經》中也有西周時用糧食、犧牲祭社祈求甘雨和豐收的篇章。春秋時代遇到日食、水災亦祭祀于社。這些故事皆表明中國以農耕為本。換言之,“耕讀傳統”以“社稷”為“家國天下”之本位。然而,“農本/農貧”的情狀一直存在著,一個發達的農耕養育了貧窮的農民。即使到了今天,“扶貧”的主體對象仍然是農民。西方甚至有學者這樣形容中國的一些地方的農業和農民的窘境:
有些地區農村人口的境況,就像一個人長久地站在齊脖的河水中,只要涌來一陣細浪,就會陷入滅頂之災。(25)引自[美]詹姆斯·C·斯科特《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程立顯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3年,第1頁。
2.農本、農正(政)傳統表明中國的政治體制生長在“土地”之上,等級制度也因之建立;農民則一直處在社會的底層,迄今未能徹底改觀。“讀”與“勞心”相屬,“耕”與“勞力”相依,即“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章句上》),“耕讀”恰好在二者之間建構出了“勞心/勞力”二元對峙的社會等級價值圖景,并反映在了“王制”中。《禮記·王制》云: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上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26)《禮記·王制》,張樹國點注,青島:青島出版社2009年,第54-55頁。
3.社會等級差距也體現在鄉土社會的治理問題上。我國歷代鄉村治理,多以“自治”為主,官家的治理,多以貢賦為主要目的,這種關系反映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剝削/被剝削”實況,并貫徹在了保甲制度中。即使到了清代,國家基層組織體系的主要形式是保甲和里甲組成:
清廷實行保甲政策,遍于全國,始于順治,初為總甲制,繼為里甲制,皆十戶一甲,十甲一總,城中曰坊,近城曰廂,在鄉曰里,康熙四十七年申令十戶立一牌頭,十牌立一甲頭,十甲立一保長。
保甲雖然起源早,但直到清朝才正式采行。一些歷史學家認為,保甲的雛形始于《周禮》,但真正做為地方行政的控制系統,到清朝才算完備。(27)參見蕭公權《中國鄉村——19世紀的帝國控制》,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年,第38頁。無論是保甲還是里甲,事實上都以“田土”為依據。需要辨析的是,古代國家的基層管制和管理體系與帝國官僚體制有著本質的不同,由于國家需要通過稅賦、納貢等方式從農民那兒獲取,對三農的掌控自然在任何朝代都存在。然而,對于廣大“鄉野”,國家的掌管是有限的。換言之,官家以貢賦為主要目的管理,往往將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擠壓到了極其艱難的境地。
4.耕讀傳統也反映在知識體制中的巨大背離。在廣大的鄉土社會里,“讀”皆為“四書五經”,讀書以考取功名為家族榮耀,藉此流芳百世。所讀經學罕見與提高農民生活、提升農業效率、改善農村環境為內容者。換言之,耕讀傳統中的“體/用”分離嚴重。筆者近期率隊前往江西省泰和縣蜀口洲村落調研,參觀了歐陽宗祠,觀覽了《歐陽家族譜》,曰:
蜀江歐陽氏文獻史籍記載甚矣。歐陽氏宗人族裔蕃衍昌盛,分布祖國海內外難以悉計,而且忠孝節義,理學奕世,光岳正氣,流芳千古。蜀江宗祠古風長存。“五經科第”“朝天八龍”“二十一進士”“父子進士”“兄弟尚書”“鳴陽三鳳”“奕世翰林”,名匾高懸,豐碑林立,與日星同輝,和天地共存,充分顯示蜀江歐陽氏的輝煌歷史。(28)彪彤二宗合修歐陽氏宗譜理事紡委會撰《歐陽氏宗譜》第一本,2004年,第18-19頁。
一個普通的鄉村,歷史上出了那么多經國濟世之才,令人尊敬、景仰,卻罕見科舉精英們以知識、技能、田功、增產等回報桑梓。也就是說,他們的確是國家的棟梁之材,在宗族內除了光宗耀祖外,他們所“讀”的書,所學的知識,基本上與“耕”無關。
5.眾所周知,在傳統的鄉土社會里,真正的村落是自治的。只要是一個社會群體單位,就有秩序,有秩序就需要維持,維持秩序需要治理;我們無妨將“耕讀傳統”視為一種維持鄉土社會秩序的力量。“統治如果是指社會秩序的維持的,我們很難想象一個社會的秩序可以不必靠什么力量就可以維持”;而“鄉土社會秩序的維持,在很多方面和現代社會秩序的維持是不相同的”。費孝通先生將鄉土社會的治理方式稱為“無治而治”,即“禮治秩序”。“禮和法在不相同的地方呈現和凸顯維持規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國家的權力來推行的,而禮卻不需要這有形的權力機構來維持。維持禮這種規范是傳統。”(29)費孝通:《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48-50頁。這樣,“禮制/法制”構成了“同意權力”與“橫暴權力”之間相應差異。(30)費孝通:《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第59-60頁。雖然國家統治中也突出禮制,卻與鄉土社會有天壤之別。
以“耕讀傳統”論,“讀”者,儒家禮教之大義,禮治鄉里,乃“讀”之最大福澤。只是,鄉土社會的治理,非全靠“禮治”可以通行,“鄉土知識、民間智慧”同樣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事實上,“村莊所具有的作為一個村莊的道德穩固性,事實上最終基于其保護和養育村民的能力。只要村莊成員資格在緊急情況下是重要的,鄉村規范和習慣的‘小傳統’就博得廣泛接受。”(31)[美]詹姆斯·C·斯科特:《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程立顯等譯,第55頁。所以,維持村落的道德穩固性至為重要,村落的道德穩固性又靠“小傳統”的支撐;村落的“小傳統”能夠長久的持續下去,又需要有相應的村落自治。因此,以“讀”之“禮”傳家,有作用,卻有限。至少,農夫的生計、生產和生活與“讀”的關系甚遠。
傳承:新耕讀傳統中的家園遺產
毫無疑義,當我們把中華民族農耕文明背景下的“耕讀傳統”視為一份重要的、祖先留給我們的、必須繼承,而且必須傳承好的文化遺產,以配合當今的發展變化,使之成為一種“新耕讀傳統”,就必須對傳統耕讀傳統的產生的土壤、本質特征、存續方式、演變情況等有所了解,有所分析,進而揚棄,以留取“精華”,去其“糟粕”。這也是我們這一代(學)人的責任和使命。
在“耕讀傳統”中,宗族的一個最重要的社會群體單位,表明大家不是外人,是同祖同宗的“族人”。“族”基本上的是一個地緣群體,有的學者認為,“族”是一種社會組織,擁有一個共同的祖先。對于同一個宗族群體而言,“宗族的最大功能,是使人知道自己的來源,知道自己與別人的關系,知道人與人之間的輩分,這就是道德。”(32)錢杭、謝維揚:《傳統與轉型:江西泰和農村宗族形態——一項社會人類不學的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5年,第28頁。在傳統的村落政治中,宗族給鄉村帶來了一種特殊的,無可替代的凝聚力,這是其他因素所無法提供的,雖然近代以降,宗族重建會在鄉村的傳統結構中增加某些新的成分,但絕不會從根本上改變現在的秩序性質。(33)錢杭、謝維揚:《傳統與轉型:江西泰和農村宗族形態——一項社會人類不學的研究》,第30頁。根本原因是:中國的鄉土村落,特別是漢族村落,從“開基”(開創)到延續、繁衍,其根本的動力機制就來自于宗族。我國傳統村落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以姓氏命名村落。換言之,血緣、親緣與地緣構成了事實上的“家園共同體”,這也是“耕讀傳統”中的基本和基礎因素。
“家園共同體”的范疇和范圍的“邊界”關系,確立了多重關系的認同機制。宗族與鄉村之間的關系密切而簡單,鄉村里占大多數的農業人口,流動性不強,血緣紐帶保持得緊密。鄉村的繁榮與強大的宗族組織之間有形成了個榮辱與共的關系體。當然,維持和維系這個關系體的最重要因素是經濟。經濟發展不達到一定程度,鄉村就不能形成,任何規模的宗族也不能維持。(34)蕭公權:《中國鄉村——19世紀的帝國控制》,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年,第383-391頁。比如在廣東的鳳凰村,宗族是一個單系的親屬群體,除了一些來做生意的外姓人之外,村里所有的人都是同一宗族的成員。一個男子一旦成為宗族成員就會永遠都是(實際上,有人因觸犯族規而被逐出族)。鳳凰村是一個父系的宗族,通過男性來追溯世系,因此也是單系繼嗣的群體。一個人一旦出生在一個宗族,就是離村遠走他鄉,也脫離不了宗族。(35)[美]丹尼爾·哈里森·葛學溥:《華南的鄉村生活——廣東鳳凰要的家族主義社會學研究》,周大鳴譯,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6年,第117頁。總體上說,在中國的漢族鄉村,鄉土社會與族化制度形成了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家園共同體”,而在鄉村所形成的“耕讀傳統”也很自然地屬于“家園遺產”的常規化活動。
歸納族化功能的特點,可以表述為:(1)族化是村落家族使家族成員增加認同和向心力的必要活動;(2)族化也是村落家族為獲取生存資源保證家庭整體性所必須的活動;(3)族化有“宗教”、禮教、耕教與文教四種形式。前兩者基本上合二為一,繼續存在,后兩者逐漸由社會體制所取代,盡管程度不高,但已超出村落家族所能達到的極限;(4)族化的核心價值是以孝為主的宗族秩序觀念,族化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使家族內部秩序能夠綿延;(5)族化活動呈現出兩種趨勢,有些地方弱化了,有些地方強化了;總體上弱化了,局部上強化了。(36)王滬寧:《當代中國村落家族文化——對中國社會現代化的一項探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8頁。耕讀傳統,——無論是從性質上,還是功能上,都是鄉土社會宗族主導下的一種生存和延續方式。
即便到了當代,“兩委”落到了村落基層,宗族勢力早已衰弱,但仍然無法改變宗族這樣一個人群構造的事實。而鄉村的秩序、道德、倫理、教育、社會活動等大都離不開祭祖、編修族譜、宗祠、鄉村公共事務、與相鄰村落建立關系等,古代還有自衛防御等功能。王滬寧認為,我國目前村落家族的情況,從結構到功能的總體方面,在當今的情勢下,如何保持家族文化的延續,保證族員的情感認同與向心力。當前,村落家族文化正處在歷史的演變之中,它已經脫離了村落家族文化原型的某些基質,向著現代社會的基質演進。在現代中國,村落家族文化呈現為雙重的運動:一方面,村落家族文化受歷史運動總趨勢的推動,逐步走向消解;另一方面,現代中國社會的某些因素,當代社會經濟條件的某些因素,又可產生強化村落家族文化的客觀和主觀愿望。(37)王滬寧:《當代中國村落家族文化——對中國社會現代化的一項探索》,第147頁。
鄉土社會的宗族勢力并不僅體現在“鄉治”的秩序和管理上,在宗族文化方面更為具體而充分。每個古村都會見到祠堂、宗族宗譜,這些都是普通百姓生活的真實記載與展現。儒家文化正是通過宗族文化漸漸滲透到每個村民思想中的,鄉規民約、家規家訓都教導人們禮義廉恥四維,仁義禮智信五常。(38)王維、耿欣:《耕讀文化與古村落空間意象的功能表達》,《山東社會科學》2013年第7期。這一切也都會反映和體現在“讀”(鄉學、教育)——教化和教育體系之中。古代的“鄉學”主要是一種私墅性的教育,隨著時代的推移,“鄉學”逐漸變得多樣,形成一個集官方、民間和個人多種復雜因素的概念。在清代,鄉學包括書院、社學和義學三種類型。對學生進行系統教育,由清政府建立或經過其批準的各類學校,可以分為兩大類:“官學”(官辦學校)和“學校”(非官辦學校)。義學(慈善學校)和社學(鄉村或大眾學校)。書院起源于唐朝時期。(39)蕭公權:《中國鄉村——19世紀的帝國控制》,第278-279頁。
值得一提的是“義學”,義學也稱“義塾”,是指中國舊時靠官款、地方公款或地租設立的。義學的招生對象多為貧寒子弟,免費上學,大多教學是啟蒙性的知識。與“社學”有相似之處。二者的概念邊界在不同的時期、地方,于不同的人在認知定義上不盡相同,不管社學和義學之間到底有什么區別,它們的基本目的實質上是相同的:盡可能把更多的人置于儒學思想的范疇內,尤其是對于那些地方精英和領袖。蕭公權先生為我們提供了清代一些地方“鄉學”的情況:在河南一個縣合計有超過120多所社學。在廣東清遠縣,由鄉人集資創辦了21所社學。規模較大的宗族,有時也創辦鄉學。其中一個著名的例子發生在廣東花縣平山墟,江姓、梁姓、劉姓和危姓等宗族(其成員在該村總人口8000人中占絕對多數,)聯合創辦了聯云社學。紳士們也對創辦社學表現出深厚的興趣。(40)蕭公權:《中國鄉村——19世紀的帝國控制》,第284頁。翻開中國近代教育史,特別是由“私”而“公”的演變中,無數的精英個體參與了這一教育轉型;他們憑借著無不與“宗族-鄉學”情結有涉。
如上所述,傳統的耕讀傳統有一個弊病,即“耕”與“讀”的契合力弱。在傳統的耕讀形制中,“讀”的是圣賢書,農書不在其列。“讀”的目標是“仕途”,是宗族榮耀,罕見“讀”農業方面的書,鮮見與“耕”發生關系。因此也頻繁出現在某一個村落出了“大官”,宗族因此長時期地“顯耀”、“顯貴”,家族驟然就不一樣了。可是,農業生產卻一直保持原樣。這是耕讀傳統的巨大悖論。今天,黨中央制定了偉大的“鄉村振興戰略”,我們也將地面對這種歷史的悖論。遺憾的是,我們在許多方面仍然延續著這一種“價值的悖論”。以高等教育為例,我國的綜合性大學沒有“農科”,農業知識被歸入到“專業院校”這是難以理解的;其他的專業學科可以,農科則不行。中國是“農本”國家,以“社稷”為先,何以“綜合性知識體系”中沒有“農科”?究其原因,亦與傳統的“耕讀分離”有關,——這種分離也衍生出了經久性的“讀(尊)/耕(卑)”社會價值。不諱言,這種社會價值觀迄今未有根本改變。
鑒于諸上,筆者對“新耕讀傳統”作為范式及要素羅列于次:第一,在“耕讀傳統”基礎上的繼承與創新;尤其是“天時-地利-人和”的價值觀,以“生態優先”為原則保護好鄉土社會的文化遺產。第二,將“讀”與“新三農”相結合,除了尊重、體恤、扶持“三農”外,還包括“知識引入”,使農業產生新的生存、生產的持續性能力,特別要建立農業產業化機制,新的知識與技術必須加力引導。第三,在揚棄的基礎上,保留和傳承具有中華農耕文明特點與特色的“禮”的文化景觀。中國素有“禮儀之邦”之稱,而“禮制社教”的最基層落實是廣大鄉村。中國在任何時候,都不能淪為“無禮之邦”。第四,“力”的發軔。在甲骨文里,“力”寫成或,“乃原始農具之耒形,殆以耒耕作須有力,故引申為力氣之力。”(41)徐中舒主編:《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2016年,第1478頁。今之力量,故以農業、農耕為基礎,向更加廣闊的領域拓展發力,形成新的、創新性、符合現代社會的“力道形制”。第五,發揚耕讀傳統中“義”(仁義、公理、慈善、義舉等)的精神,(42)央視《記住鄉愁第二季》第十一集記錄了浙江省金華市鄭宅鎮的東明村的耕讀傳統中的“尚義”精神,值得借鑒。特別在經濟和商業社會里,“義”不獨有“勇”,還有“仁”“慈”“德”等——“尚義精神”。“精準扶貧”何妨視為義舉,只是我們要強調的是,“義”除了國家行為外,更需要體現和實踐于民間。第六,突出耕讀傳統中“宗族-家族”家園遺產,并注入新的內涵:既保持鄉村中的傳統格局,又在“家園遺產”中注入、加入“家園-家國”的新價值、新內容和新取向,提升愛國愛家的價值觀。
結 語
中國是一個以農耕傳統為基礎的“社稷”國家,在這樣的國家,“三農”是終極的說明和證明。如果我們說中國富強,而農民還掙扎在社會底層,這個說法就難以成立。“鄉村振興戰略”從根本上說,就是“三農”的狀況全面改善,水平全面提升;而要做到這些,數千年形成的“耕讀傳統”就必須做到回歸、彌合和傳承的綜合層面上。習近平主席說:“中國要強,農業必須強;中國要美,農村必須美;中國要富,農民必須富。”(43)201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安徽鳳陽縣小崗村主持召開農村改革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竊以為,是為鄉村振興戰略的根本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