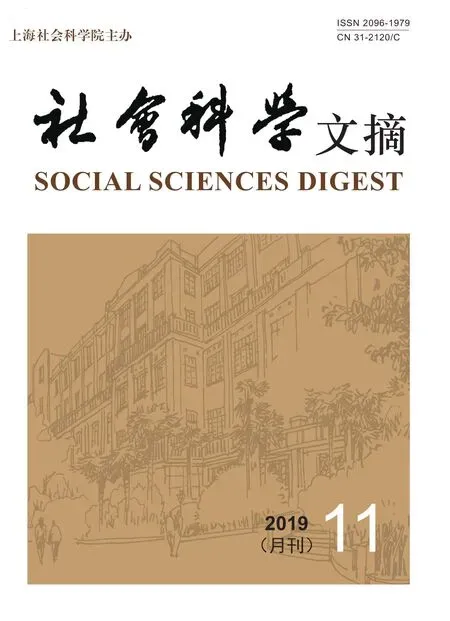資產階級與種族視野:普魯斯特的猶太意識與階級身份
文/張亙
普魯斯特的宏篇敘事以其里程碑的地位和意義指示和引導了法國文學批評的未來走向,他也許是法語作家里被研究最多的人,類似于英語里的莎士比亞。一邊是稀有和卓爾不群的寫作維度,一邊是密集多產不遺余力的評論闡釋,如同所有躋身最偉大作者行列的作家一樣,普魯斯特的創(chuàng)作深度讓批評的動力永遠有著可持續(xù)性推進的空間,同時也很少留下未被涉足的地域。猶太情結是研究人士著墨頗多的界域,同時也是普魯斯特的主體意識和對真相的提問方式,是敘事者針對于主體所進行的觀察和檢驗。批評者對于資產階級這一概念的分析,少數(shù)馬克思主義批評家曾經提到過,例如本雅明,但是將其與種族視野相比較的研究要鮮見得多。筆者試圖探討的是如何將“資產階級”和“種族視野”這兩個批評術語連接,從未曾有過的進路來理解《追憶逝水年華》文本中糾結多面的種族意識,將文學話語同社會、經濟、政治環(huán)境結合加以考察,希冀合理闡釋作者有關猶太身份的敘事、表象和指涉體系,抽取出種族身份與主體階級屬性的關聯(lián),探求資產階級的背景是如何訴諸普魯斯特的種族經驗和政治旨趣。
資產階級身份與書寫
普魯斯特的書寫是否可以被定位為資產階級書寫?瓦爾特·本雅明在普魯斯特的鴻篇巨制里“看到的不僅是‘非意愿記憶’作為一種文學實驗如何使個人生活得到拯救,更是資產階級時代及其私生活如何在一種比這種生活本身更致密、更專注、更綿延不絕的形式中暴露出這個時代自己無法認識的‘頹敗歷史的具體性’”。從本雅明的視角,當普魯斯特的書寫是資產階級書寫時,意味著三個層面:第一,敘事者在描述資本主義時代所特有的生活;第二,敘事者不一定是在維護自己所生活的政體或是制度,他有可能是在鞭撻資本主義社會的世俗日常;第三,“病殃殃的闊少”本身屬于資產階級,雖然本雅明并未點明,但很難想象一個抨擊資本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寫作能被定位為資產階級寫作。
我們首先將目光投向普魯斯特的現(xiàn)實身份。《追憶逝水年華》的作者出生在巴黎的十六區(qū),這是以資產階級屬性和生活方式而聞名的城區(qū)。直至今日,巴黎十六區(qū)在法蘭西國民的集體想象力中仍然是富人區(qū)的象征。普魯斯特的父親是一名醫(yī)學教師,母親讓娜·威爾(Jeanne Weil)則是富有的投資家之女。小普魯斯特就讀的中學是著名的孔多塞高中(Lycée Condorcet),這所創(chuàng)立于1803年的中學是巴黎的四大歷史名校之一,也是巴黎排名最高的中學之一。在整個19世紀,孔多塞中學一直是資產階級家庭所眷顧的名校,孱弱的普魯斯特雖然病體多磨,卻是學校的優(yōu)等生。他的高等教育在著名的巴黎政治學院完成。他是有著私人司機和秘書的上流社會人士。
資產階級作者和資產階級敘事者的同一身份如同雙重封印,然而,探討《追憶逝水年華》的階級屬性,我們也可以思考書寫本身的特質。普魯斯特的創(chuàng)作癥狀從某個角度上講是可以寫進小資產階級病歷的:“多愁善感,抑郁寡歡,溫情主義,動不動就傷感,在回憶之中打發(fā)日子。這顯然是一種多情而纖弱的性格。”但是,從本質上來說,小資產階級話語批評是誕生于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內部的文學范疇,它有的放矢,射向的更多是在陣營之內擾亂文學秩序的革命意志薄弱分子,批判的是他們的騎墻位置和模糊的階級訴求。《追憶逝水年華》的敘事在階級話語的層面上表現(xiàn)出許多曖昧的景致,它不是類似楊沫的《青春之歌》或是王蒙的《戀愛的季節(jié)》那樣是囿于階級對壘大時代下的多舛命運,馬塞爾本人從社會財富和地位而言肯定也不是“小資產階級”這一術語能夠包容的。
《發(fā)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是本雅明的力作之一,與這位“20世紀最偉大、最淵博的文學批評家之一”談到普魯斯特時一樣,資本主義同樣是這部向波德萊爾致敬著作里的關鍵詞。波德萊爾是本雅明“寵愛的詩人”,與普魯斯特的生存狀況迥然有別的是,波德萊爾的生活有時拮據(jù),他不是一直都能夠無所顧忌地揮霍和花天酒地,雖然他似乎從來沒有節(jié)儉度日的打算。《惡之花》的作者曾經被歸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而被考察。“為反抗而反抗,為革命而革命,這是一種將革命非政治化、非道德化或者說將政治審美化的態(tài)度,它與波德萊爾在二月革命時期主張‘為藝術而藝術’的原則如出一轍,本雅明由此發(fā)現(xiàn)了在詩人那里政治和藝術的同一。”19世紀資本主義上升期的小資產階級與20世紀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的小資產階級有著一以貫之的地方,他們是始終追逐浪漫和耽于幻想的。波德萊爾在1848年加入搶劫商店的人群,興奮地呼吸著暴動的氛圍,在騷亂中找到亂世英雄的感覺。作為波西米亞文人,他在文字里制造幻象,現(xiàn)實的秩序在詩歌里解體,迷亂、曖昧和蠱惑是字里行間涌動的漩流。
從《在斯萬家那邊》伊始,“這位斯萬先生,作為斯萬老先生的兒子,完全‘有資格’受到‘上層資產階級的淑女名媛們’的款待……他為自己穿了一身夜禮服而連連致歉……他方才是同一位王妃‘共進晚餐’的”。“我”所生活的圈子是人物努力認識的現(xiàn)實,人物與他的圈子一起凌駕于社會結構的上端,《在少女身旁》里的大使、外交官、構成職能生活部分的晚宴、固有的優(yōu)雅生活如同水晶燈的璀璨光華,照耀著社交沙龍來往人群的格調和談吐。這已經不再是用小資產階級或是中產階級的詞匯能夠厘定的世界。大資產階級掌握著財富和社會的經濟命脈,高坐在金字塔分層結構的云端俯視眾生。在封建社會,資產階級是介于貴族和下層勞苦大眾之間的社會構成,而在19世紀末期和20世紀初葉,普魯斯特所躋身的大資產階級在一定意義上已經成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新貴,他們追求儀式感,鐘愛繁文縟節(jié),喜歡曲折多解和隱晦雙關,在普魯斯特的句法里,我們能夠重新發(fā)現(xiàn)17世紀貴族在拼寫和詞匯上的某些矯揉造作的風格。
政治旨趣與猶太情結
《讓·桑德伊》是普魯斯特從未完成的自傳體敘事,年輕的普魯斯特在書中為法庭上的被告站臺。在《讓·桑德伊》里,敘事者既感謝那些幫助猶太人“理解”反猶主義的人,也感謝那些幫助德雷福斯支持者“理解”判定左拉有罪的陪審團的人。這樣的人其實也就是后來《追憶逝水年華》里的敘事者,是普魯斯特的主體自身。
究竟德雷福斯事件的真相為何?作為歷史后來人的我們似乎已經有了答案,但是,位于那個時代沖突錯綜復雜交匯點上的普魯斯特并不明了,他支持猶太軍官并不意味著他堅信被告的清白。不了解《追憶似水年華》的眾多人物面對這一世紀性審判的多樣化立場,就不會明了敘事者在《讓·桑德伊》整整三章隱藏在字里行間的矛盾心理和逡巡猶疑。不了解普魯斯特的猶太身份背景和他對母親的復雜情感,也許就無法體察猶太教、同性戀和亂倫主題在文本里相互纏繞的顯影歷程。在《德雷福斯事件的真相》一章,普魯斯特指出,整個事件極其錯綜難解,是間諜戰(zhàn)和反間諜戰(zhàn)的交錯角力。“無論法國人如何貪婪地渴求,他們永遠不會解開謎團。”《我控訴》的審慎分析和理據(jù)陳述里涌動的反叛精神和抗爭激情來自左拉的堅信、對真相的把握和積極參與的決心;普魯斯特行文出現(xiàn)的長句繾綣、復數(shù)主語在單一語句里的并置,就如同傳奇小說借助時代跨度和人物繁雜維系讀者懸念,既是觀點的呈現(xiàn),也是視角的多變,既是事件的講述,也是真相的延異。這樣的語句風格傾向于排除決斷和堅毅的宣言,傾向于讓讀者在人物立場的變化和復調中鳥瞰全局和管窺謎團,政治的答案不會透徹地顯形,永遠如皮影戲或是走馬燈一般幻變。
普魯斯特在一定意義上是個神秘主義者,這也許是猶太人血管里所流淌的文化基因使然。理性的局限和意識的不可捕捉并非同一版本的不同年份。普魯斯特所發(fā)掘的是意識的廣袤疆域,是意識那難以探測的縱深,是意識的多變和自我拯救的可能性。的確,在探尋自我救贖的回溯之路上,普魯斯特所求助的更多是非理性的記憶,是在某一個時刻不由自主涌現(xiàn)或是——套用薩特的話來說,意識的迸發(fā)——所迸發(fā)出的過往印跡。普魯斯特的非理性過往也許正是他矛盾政治立場的解釋之一,種族身份的意識不斷在時間的川流中泛起漣漪,但是由于資產階級的惰性氣體而波瀾不驚。當政治和種族相遇在回憶的交叉路口,兩者的模棱和徘徊在相互傳染。
如果說生活與作品之間的距離感是普魯斯特代表作的主題之一,在整部長河著作里,作者總是樂于將自己的矛盾性呈獻給讀者。于是,作為猶太人和德雷福斯支持者的普魯斯特同時又每天閱讀反猶報紙,并從中尋找到美學快感。作者和敘事者雖然是兩分,我們還是可以說敘事中的人物是一個憂郁善感的猶太人,他是生活中現(xiàn)實的某種復現(xiàn)。作品里敘事話語的結構顯然是為了讓敘事者從形式上獲得超然脫離的地位,于是,有關猶太人的話語或者是由猶太人,或者是由反猶份子發(fā)出,敘事者本人并不表明立場。敘事者面對種族問題的態(tài)度和《讓·桑德依》異曲同工,這是作者有意的模糊化處理,給讀者的閱讀結果可能是造成情感的不適或是判斷的不確定性。整部《追憶逝水年華》包含許多反猶元素,這些絕不是可以用諷刺來解釋的,失去價值判斷參照的讀者在閱讀上會失去安全感。
階級身份與種族意識
普魯斯特的意識形態(tài)和他的世界觀是有可能背道而馳的,他的意識形態(tài)有著正統(tǒng)、保守甚至是反動的一面,而他的世界觀卻能夠讓他在書寫中娓娓道來地言說資本主義世紀的華燈初上之下所拖曳的平庸、膚淺與俗陋。在物化的世紀之交,在金錢和商品交換主導一切的實用生活里,自我受到物質的威脅,個人被孤獨感所籠罩,“每個讓我們痛苦的人,我們都可以把他與一個神相連接,他只是神的碎片似反射,是神的最后階段,對于神(觀念)的沉思會立刻讓我們在遭受痛苦之后感受歡樂”。希望在想象中和社會之外尋找自我所喪失的部分,或是重整已經碎裂的自我。當人的生活方式已經被大規(guī)模的工業(yè)化進程所沖擊,即使生活在別墅和莊園的深宅之中,也無從躲避和幸免,人不可避免地被卷入異化時代的洪流,人成為了在自己家園里迷失的陌生人,“于是,一股新的光芒在我的內里生成,比這種光芒更耀眼的也許是讓我發(fā)現(xiàn)藝術作品是唯一找回逝去時間方式的光芒。我明白了,所有這些文學作品的素材就是我過往的生活……”普魯斯特的精神結構使得敘事者“對那陰晦的白天和必將如期來臨的明日愁眉不展”,他“戰(zhàn)栗顫抖,專注于自我內在所發(fā)生的奇妙感覺”,唯有這種快感才能讓生活的變遷、災難和短暫如過眼云煙,才能泰然處之。
批評家可以從感傷心理與低迷精神的視角將普魯斯特闡述為資產階級文化的旁觀者與破解者,這并不是普魯斯特的定性,它顯現(xiàn)的是《追憶逝水年華》文本的龐大和復雜多面。當批評轉向另一個視域,即普魯斯特的意識形態(tài),首先,普魯斯特終其一生都執(zhí)著于維護軍隊的秩序捍衛(wèi)者地位:“身著便裝的軍人如同裝扮成凡人的神。”敘事者也是貴族社會和上流沙龍的常客與欣賞者:“在某個祖上參加過十字軍東征的人的沙龍里感到愉悅,這是虛榮。智力與此毫無相關。但是,某個人祖父的名字是阿爾弗雷德·維尼或是夏多布里昂,或者(對于我的確是無法抵擋的誘惑,我承認)他家族的徽章位于亞米安圣母大教堂的大玫瑰之中,參與他的沙龍感到愉悅,這可是智力原罪開始的地方。”在整部巨幅敘事的經緯縱橫之中,普魯斯特的回憶與思緒再現(xiàn)的可能是上流沙龍和發(fā)達資產階級的頹敗,但是這種頹敗不能遮掩敘事者的自尊和自傲。密致細微的文字鋪滿連續(xù)綿延的頁面,密不透風的話語從敘事者筆下徐徐不斷地流出,敘事者的從容淡定散發(fā)出造物主駕馭人物和放眼文本的氣勢,很難說這是一位抨擊人士在痛苦彷徨中的冷眼旁觀。
馬克思曾經這樣批評他那個時代的德國哲學,“既然他們僅僅反對這個世界的詞句,那么他們就絕對不是反對現(xiàn)實的現(xiàn)存世界”。德國哲學的批判是一種沒有離開哲學領域的抽象的思想批判,在他們看來,現(xiàn)實世界的統(tǒng)治者是宗教、觀念、思想和概念,一切都是意識的產物,因此,敵人是意識,需要與之斗爭的是意識這個無所不在的對手。于是,詞句反對詞句的斗爭在青年黑格爾派那里沒有觸及現(xiàn)實世界。馬克思的剖析也許過于犀利,有可能下刀失之偏頗,但是,他的意識形態(tài)批評讓我們在現(xiàn)實和想象之間憑借政治的敏感性嗅到可疑的差異。
在普魯斯特的世界里,在《追憶似水年華》所流淌的話語長河里,就像馬拉美所說的,文學當然是“虛構”“光榮的謊言”和“真正的人類創(chuàng)造”,敘事者正當合理合法地在用語句來重構世界。這是一個想象的世界么?的確是。耽于溯流回游的普魯斯特在沉思中神飛,追憶流逝在時間隧道里的碎片拼圖。在想象中捕捉記憶片段的敘事者將現(xiàn)實世界中的種族元素重新排列組合,猶太意識的體驗、苦痛、記憶、遺忘和壓抑在階級意識的現(xiàn)實制約和功利性謀劃下走樣和變形。這是一個現(xiàn)實作用于想象的世界。借用馬克思針砭德國哲學的模式,如果說“普魯斯特社會批判的爆炸力量”讓“布爾喬亞在笑聲中土崩瓦解”,這仍然是詞句反對詞句的敘事。
身為猶太后裔的普魯斯特在歷史境況和集體經驗的背景下選擇以曖昧的方式創(chuàng)造性地表述種族沖突,從階級關系和政治經濟學的角度解釋,這是因為大資產階級或是貴族屬性始終是普魯斯特作品的社會學主題。“普魯斯特對那些進入貴族圈子所必須具備的訓練從不厭倦……奧爾特加·伊·加塞特第一個提醒我們注意普魯斯特筆下人物的植物性存在方式。這些人物都深深地植根于各自的社會生態(tài)環(huán)境,隨著貴族趣味這顆太陽的位置的移動而移動……并同各自命運的叢林糾纏在一起而不能自拔。”所謂的貴族生活并不是指普魯斯特對中世紀的時光戀棧,雖然在貢布雷的教堂、雕像和彩窗似乎呈現(xiàn)出一個想象的中世紀景色。貴族生活更多意味的是一個生活層次,是只有大資產階級或是克萊爾芒-托萊爾公主、圣西門公爵這樣的人能夠共享的階層、生活圈和品味。敘事者的階層身份讓他的種族話語和政治旨趣在文學表述中的落點發(fā)生變異,畢竟普魯斯特屬于利益既得者的集團,他在集體記憶中的受迫害者意識不可避免地會被中和與沖淡。
跨越兩個世紀的普魯斯特因為他的里程碑式巨作而地位卓然。因為他的精神探索,他與喬伊斯、弗洛伊德這些名字一起成為20世紀初時代思想的典型代表。我們對作者種族話語的定位并不意味著褒貶的價值判斷,在種族語境里的普魯斯特,更多地是作為歷史和階層的產物留在詩意、優(yōu)雅和具有獨特法蘭西氣質的話語里。我們沒有理由以階級理論和政治迫切性來給出普魯斯特的立場坐標,卻可以借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來組合起一個種族、階級和詮釋的批評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