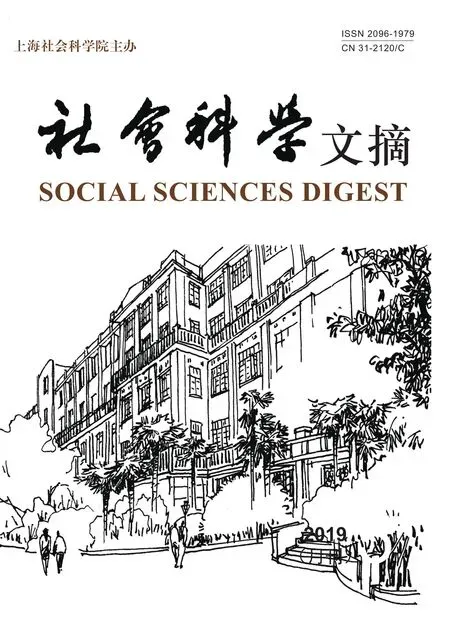孫犁與莫言:從認同走向疏離
孫犁與莫言都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不可忽視的存在。孫犁早在戰爭年代便已獲得文學盛名;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他相繼創作了一批有影響力的小說;改革開放后,他盡管不再著力于小說創作,但仍繼續關注當代文壇,尤其關注文學新人的文學創作。當文學新人莫言剛走上創作之路時,他的小說便得到了孫犁的賞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孫犁對莫言的早期創作予以關注之后,便很少再論及莫言的文學創作;同樣,莫言對孫犁也鮮有評說。實際上,孫犁與莫言之間的交往猶如兩顆彗星,在最初的交匯過后,便轉瞬即逝,除了給我們留下簡短的幾行文字之外,幾乎已被淹沒在浩瀚的文學星空中。那么,孫犁與莫言何以會從認同走向疏離?在其認同與疏離的背后,隱含著怎樣的文學發展內在規律?其對當下的文學創作又有什么啟示?
一
在通向文學圣殿的道路上,作家的起步階段至關重要。在此階段,對莫言文學創作具有重要影響的人物是不能不提及的,那就是蟄居天津的現代作家孫犁。在莫言的小說尚未在文壇上引起反響的時候,孫犁讀到《民間音樂》后充分肯定了莫言小說的文學價值。這極大地提升了莫言及其作品的知名度和美譽度,對莫言走上更為廣闊的文學道路起到了重要作用。
孫犁對莫言小說《民間音樂》的評論大約寫于1984年3月。在此期間,孫犁以《讀小說札記》為題評述了數位作家的作品以及文壇上的一些現象。在該組札記中,孫犁從8個方面對作家作品及一些文學現象進行了評述。第一篇就莫言的《民間音樂》展開評述。第二篇是就李杭育的《沙灶遺風》的評述。第三篇是對當時文壇評獎現象的評說。第四篇是對關鴻的《哦,神奇的指揮棒》的評述。第五篇是對汪曾祺的《故里三陳》的評述。第六篇是對古華的《“九十九堆”禮俗》、李杭育的《沙灶遺風》以及張賢亮的《綠化樹》所作的評述。第七篇評述了張賢亮的中篇小說《綠化樹》。第八篇對鐵凝的《沒有紐扣的紅襯衫》作了評述。在結尾處,孫犁特別標示出了本組札記為“1984年4月14日寫訖”。
在評述小說《民間音樂》時,盡管孫犁沒有刻意凸顯莫言小說的超人之處,但我們還是不能否認這組評述之于莫言文學創作及其人生道路的作用及意義。當時,莫言的文學創作才剛開始起步。在孫犁同時評述的幾個作家中,就當時的文壇地位而言,莫言顯然無法和汪曾祺、張賢亮等已經成名的作家相提并論,甚至也無法與同齡作家李杭育、鐵凝等并駕齊驅。但是,當莫言的短篇小說被孫犁置于同一個文本中進行評述時,便意味著被評述者似乎在伯仲之間了。
20世紀80年代初,文學已經迎來了春天,其重要標志便是文學期刊或復刊、或創刊,這對文學的發展和繁榮起到了積極作用。當然,緣于文學期刊主辦單位的不同,文學期刊存在著極大的差異,最顯著的是級別較低的文學期刊影響力較低。如果沒有《小說月報》等影響力較大的文學選刊選載、沒有參與全國性的小說評獎、沒有得到知名的文學評論家的舉薦,那些刊發在一般文學期刊上的小說便很難引起較大的社會反響。值得欣慰的是,在《蓮池》這個地方文學期刊上刊發了5篇小說之后,莫言便如破土而出的幼苗,相繼獲得了“春雨”的滋潤和“民間”的沃土。這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其短篇小說《售棉大路》被《小說月報》轉載,這恰似久旱的“春苗”獲得了“春雨”的滋潤;二是其短篇小說《民間音樂》獲得了在全國享有盛譽的老作家孫犁的贊許,這猶如“春苗”終于植根于“沃土”。然而,讓人稍感遺憾的是,莫言的小說雖被《小說月報》轉載,但并沒有馬上產生較大反響,這恰似“春雨”的滋潤需要一個“細無聲”的過程;不過,《讀小說札記》借助孫犁的文學盛名以及《天津日報》這一更為大眾化的傳播平臺,而為更多的讀者所熟知,莫言自然也借助這一平臺為更多的讀者所知曉。實際情況也的確如此。當莫言要敲開對其人生具有轉折意義的命運大門——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時,他的小說《民間音樂》獲得了當時文學系主任徐懷中的青睞。從徐懷中在全系會議上特別提及孫犁評價這一事情來看,孫犁的賞識對徐懷中的認同無疑起到了強化作用。這種認同,對莫言的文學主體性的確立及其文學創作來說,所產生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
孫犁與莫言的交集如彗星一樣,在浩瀚的文學星空
中一閃即過。據考察,當莫言開始真正走上文壇并逐漸產生了廣泛影響之后,孫犁對莫言的作品卻鮮有評述。在20世紀80年代,莫言創作出《紅高粱》等引起廣泛影響的小說,孫犁對此不會不知曉;在90年代,莫言創作出《豐乳肥臀》等一系列具有較大社會爭議的長篇小說,孫犁對此也應該有所耳聞。但是,此后的孫犁猶如隱居在世外的修煉者,對這一系列曾經引起文壇波瀾的文學事件保持了一種沉默的態度,對莫言其人其文保持了疏離的文化姿態。這說明,孫犁與莫言在藝術追求和審美趣味上顯然已經相去甚遠。具體來說,孫犁對莫言《紅高粱》以及之后的文學創作所體現出來的那種思想及其激情可能并不是非常認同。這也許與孫犁的性格和文學理念有關。孫犁作為一個性情淡泊的作家,對莫言所建構的高密東北鄉文學世界中的“魚龍混雜”現象恐怕難以接受。他們之間的“代際文化”差異日漸明顯。莫言依循《紅高粱》所開創的創作道路越走越遠。作為對文學新人呵護有加的老作家孫犁,盡管并不見得會認同莫言的文學道路,但他也不會以文學前輩的身份來規訓莫言的文學探索之路。與那些動輒以自己的文學理念來規訓莫言的批評家和文學家相比,這一點恰是孫犁值得我們敬重之處。
二
在莫言還是一個寂寂無名的文學新人時,孫犁以其獨立的文學立場和審美眼光發現了其短篇小說《民間音樂》的獨特文學價值,并對其進行了專門評述,成為莫言小說獨到文學價值的最早發現者和闡釋者,這與那種跟風式的文學評論有天壤之別。那么,孫犁為什么會對刊發在一個“小刊”上的“小人物”的短篇小說進行評述呢?換言之,孫犁為什么會對莫言的小說特別賞識呢?
其一,莫言對社會“小人物”生存狀態的邊緣書寫,促成了孫犁對異質文學的認同。孫犁與那些同時代的作家大不一樣。當那些一同參加革命的作家相聚北京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的政治文化中心時,孫犁依然偏于一隅,遠離政治文化中心,似乎是中國當代文學的“多余人”。與此對應,孫犁對那種標語口號式的寫作范式極其反感,這主要緣于孫犁本人的獨立文學立場和美學追求,以及其獨立的思想堅守。孫犁對莫言小說《民間音樂》的評述便體現了這一點。在《民間音樂》這篇小說中,莫言塑造的形象并不是20世紀80年代初期一般文學作品所追捧的英雄人物,更沒有什么深刻的社會內涵。在這個時期,莫言的這種邊緣化書寫顯然不甚符合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要求。但是,這種文學書寫引起了孫犁的關注,甚至還使孫犁覺得這篇小說“寫得不錯”。
其二,莫言對農村題材情感的詩意書寫,撥動了孫犁的情感之弦。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文學主潮中,現實主義占據主流,與此相對應,作家注重現實主義的寫實原則,突出文學觀照和反映現實生活的能力,具體到農村題材的文學作品,則表現為作家注重對大轉折時代下農村社會矛盾的書寫。這固然強化了文學對現實的干預力度,但文學對自身的審美性追求則顯得不夠,文學對生活的詩意書寫往往就無從談起。值得肯定的是,莫言在創作起步階段的美學追求,與文學主潮所呈現出來的美學特點有所不同,他關注的是農村社會身處邊緣地帶的“小人物”。這些“小人物”既難以承載起什么主旨深遠的宏大主題,也無涉波瀾壯闊的時代風云。由此,孫犁認為莫言所寫的這個“事情”“不甚典型”是有根據的。實際上,像莫言所寫的這個“事情”,在一些苛刻的批評家那里也許會被視為“不甚靠譜”。那么,對這樣一個有可能被人們視為“不甚靠譜”的“事情”,孫犁為什么還“覺得寫得不錯”呢?這恐怕與莫言小說的詩意書寫有著密切聯系。孫犁更看重的是莫言所營造的獨特的“小說的氣氛”。實際上,孫犁所謂的“小說的氣氛”便是小說所體現出來的美學特色。在孫犁看來,這部作品“基本上還是現實主義的”。那么,我們由此可以斷定,在孫犁所強調的“現實主義”之外,還應該有其他的“主義”。也許,莫言的這部小說打動孫犁的恰是“現實主義”之外的那種“主義”,而這種“主義”集中地體現在“小瞎子”這一人物形象上,他給人“有些飄飄欲仙的空靈之感”。其實,除了“小瞎子”這個形象給人一種飄飄欲仙的空靈之感外,花茉莉這一形象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莫言在《民間音樂》這篇小說中表現出來的“空靈之感”,恰好喚起了孫犁蟄伏已久的情感,由此產生了某種共鳴。莫言在小說《民間音樂》中對情感的詩化書寫,遠離了對“性”的展示,展現的是一種朦朧的詩意情感,這種久違的詩意情感能夠撥動孫犁的情感之弦也便是再自然不過的了。
其三,莫言對文學陰柔之美的追求,激活了孫犁既有的對陰柔之美的審美趣味。在《春夜雨霏霏》這一短篇小說中,莫言塑造了一名在“春夜”里輾轉反側難以入眠的新婚的女性形象。她獨守空房,思念著戍邊守島的丈夫,而打著窗欞的“細雨”,恰似剪不斷理還亂的情思。在《民間音樂》中,雖然莫言不像在《春夜雨霏霏》中那樣刻意表現人物形象的情感世界,但二者的美學風格是一脈相承的,只不過是淡化了人物的情思,增加了一層“虛無縹緲”的“空靈氛圍”。但就整體而言,《民間音樂》所顯示出來的美學風格是一種陰柔之美的美學風范。孫犁作為一位具有鮮明美學追求的作家,其審美趣味指向的也是陰柔之美。孫犁對莫言的短篇小說《民間音樂》的認可,在某種意義上說,正與他對陰柔之美的美學風格的偏愛有關。
孫犁之所以關注莫言這樣的文學新人,除了以上我們所論及的三個重要原因之外,還與孫犁特別看重文學傳承有關。應該說,孫犁在20世紀80年代對文學新人,尤其是那些與自己有著某種相似文學趣味的文學新人特別關注,這既有利于文學新人的健康成長,也有利于文學的代際傳承和良性發展。
三
孫犁對莫言早期文學創作的贊賞,理應激起莫言對孫犁的感念之情。但實際情況是,莫言并沒有專門寫有關孫犁的文章,即便是在其文章中偶有涉及,也或是片言只語,或是因為在講座時被專門問及此事而發表評說。
莫言在一些訪談中曾公開談及孫犁,具有代表性的是在獲獎多年之后的一次文學講座上。莫言充分肯定了孫犁小說的價值,尤其是凸顯了孫犁對賈平凹以及自己的深刻影響。當然,這種影響更多地體現在“文風”方面,莫言早期的一些作品模仿過“孫犁的風格”。莫言還肯定了孫犁的文學成就及地位,他認為:“至今還是沒有一個作家可以替代孫犁的。他對細節的關注,尤其他對年輕女孩的那種微妙心理的把握,我覺得是我們這一代作家望塵莫及的。”正是基于這樣的認知,莫言相信:“像孫犁這樣的一些經典作家的經典作品會經常地被重讀的,即便現在我們好像感覺沒人在讀,但實際上還是有人在讀,我們感覺現在沒有人讀,說不定過不了多久會重新有人讀。起碼在大學的課堂上,在學到文學史的時候,孫犁是永遠繞不過去的一個巨大的存在。”這番話表明,在莫言心中,孫犁依然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其他人無法替代的“這一個”;而孫犁作為一個男性作家,其對年輕女孩微妙心理的把握及其表現能力,更是一般作家無法企及的。在莫言內心深處,他推崇的孫犁與其說是文學上的孫犁,還不如說是道德上的孫犁。從莫言對孫犁的推崇來看,他尤其凸顯了孫犁作為文人所顯現出來的那種高潔的品格、出世的風范。從莫言的片言只語來看,孫犁留給莫言的是“大儒”和“大隱”這兩大影像。
其實,莫言后來在文學創作上不僅走出了有意識地模仿孫犁的階段,而且已經把眼光投向了西方文學。在此過程中,福克納等西方作家的文學作品給莫言的文學創作帶來了深刻的啟迪,使其醒悟到文學創作要創造出屬于自己的天地。本來,莫言不僅是一位在新時期男性作家中情感較為細膩的作家,而且是一位對情感有著詩化表現的作家。如果循著這條文學創作道路走下去,莫言成為中國情感“唯美主義”的作家也不是沒有可能。但莫言并沒有循著這條道路走下去,相反,他走上了與“唯美主義”截然不同的文學道路,以至于有些批評家質疑莫言在文學世界中過多地展現了“惡”的東西。
正是緣于觀念的變化,莫言建構起來的文學王國開始顯示出莫言的鮮明烙印。事實上,莫言正是循著自己的這一感悟路徑走出了創作原點,走進自己生于斯長于斯的高密東北鄉,并著手建構起一個屬于自己所獨有且深深打上了自身精神情感烙印、帶有鮮明個性的“高密東北鄉”文學王國。莫言正是在閱讀西方文學作品的過程中,把西方文學建構的“核心技術”——建構一個屬于自己的文學王國——視為文學創作的圭臬,從而真正地開啟了獨立自主的文學創作之旅。在文學創作中,浮現在莫言腦海中的是他自己感受到的生活。莫言的文學世界已經找到了建構的堅實基石——一個為莫言所熟知和獨有、同時也區別于孫犁的“荷花淀”的“高密東北鄉”。
當莫言有意識地建構起自己的文學王國之后,自然與孫犁建構的“荷花淀”越來越遠,由此表現出來的審美趣味與孫犁的審美趣味也越來越遠。在此情形下,莫言和孫犁已經不再屬于“同一個時代”的作家,他們分屬于不同的時代。從這樣的意義上說,孫犁對莫言“高密東北鄉”這個文學王國的影響已經不再是文學技法及美學風格上的,而僅體現在“荷花淀”這個文學地標之上。反過來看,莫言對孫犁鮮有提及是因為他已經走出了孫犁的文學疆域——莫言建構的“高密東北鄉”也許是一個讓孫犁感到難以理喻的文學王國。
總的來看,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人物。莫言作為一代文學新人要像前輩作家一樣,成為彪炳史冊的文學巨人,就必須既要繼承前人的優秀文學傳統,又要創造新的文學精神,而且要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努力超越前人。實際上,莫言所建構起來的“高密東北鄉”,不僅區別于孫犁的“荷花淀”,而且區別于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莫言以開疆拓土的氣勢,建構起了一個屬于自己的文學王國,確立起了自我的文學主體性。這意味著莫言不僅與孫犁漸行漸遠,而且還與中國現代作家漸行漸遠。當孫犁與諸多中國現代作家漸行漸遠之時,也許表明了莫言及莫言的同時代人的文學時代已漸行漸近。20世紀中國文學的代際更替便在這種歷史嬗變中悄然展開。然而,歷史的發展總是循著辯證之否定的規律綿延向前的,當莫言建構起來的“高密東北鄉”日漸成為學界矚目的焦點之時,也就意味著超越“高密東北鄉”的新時代文學之春天已經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