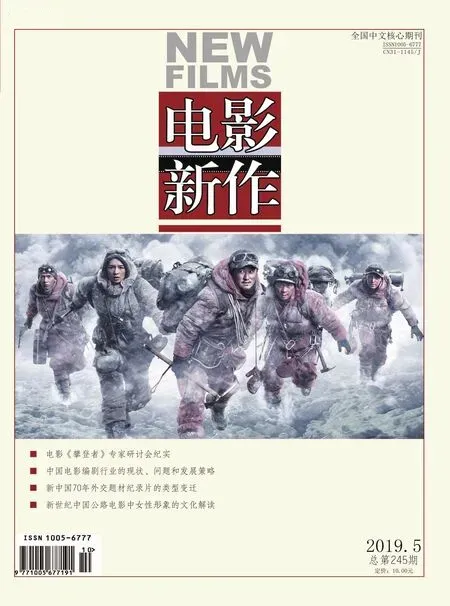論電影的表意體系及表意機制
姚汝勇
著名的系統功能語言學家韓禮德曾經指出,“除了語言外還有許多其他表意方式。語言,從其相當模糊和不確定的意義上來講,可能是一種最重要、最全面、最概括的符號系統。很難確切地說是怎樣的,但在任何文化中,在語言之外確實還有許多其他表意方式,包括藝術形式,如繪畫、雕刻、音樂、舞蹈等,和其他沒有歸在藝術中的文化行為方式,如交流方式、衣著方式、家庭結構等,它們都是這個文化中意義的承載者。”電影作為一種藝術形式,也是“語言”之外的表意方式。不過,電影是科技的產物,其表意材料由于科技的參與而呈現出精確性、直接性和連續性,這與傳統的藝術形式或語言大不相同。具體來講,逼真、連貫的視覺(默片)或視聽形象(有聲電影)構成了電影表意的材料體系。表意時,創作者以觀影者的視聽經驗為基礎來配置視覺或視聽形象,即摹擬觀影者的視聽感知經驗。
一、科技生產形象并參與表意
傳統的藝術形式,如文學、戲劇、繪畫等,基本都是自然形成的,到現在我們也無法斷言它們起源于何時。而且,它們的發展是循序漸進的,其規律是人們在長期的使用中慢慢形成的。然而,電影與之不同,它是被發明出來的,是現代科技的產物。
1.機器生產表意的形象
發明家或科學家給我們提供的是一系列記錄與還放活動形象的機器:攝影機、放映機、錄音機等等。這一系列的機器本身就是科技的產物,它們的成熟與完善經歷了相當漫長的過程:攝影機是在連續照相成熟后出現的,放映機則在馬耳他式十字架齒輪發明后成熟,而可以錄制電子信號的錄音設備在20世紀20年代末期才投入使用……大英百科全書電影史部分指出,電影的史前史幾乎和電影的歷史一樣,確實如此。不過,這些機器并非冷冰冰的機械設備,它們是能夠激起人的某種心理活動的工具:機械設備的間歇性運動,使感光材料可以通過葉子遮擋板和抓鉤的動作進行曝光或還放,重要的是,這種機械運動刺激觀影者產生了一種心理活動——在靜止的物體間看到了運動,或者說,在沒有連續位移的地方,看到了連續的運動。即“似動”(apparent movement)。換言之,銀幕上并沒有“運動”,出現的僅僅是一格一格靜止的略有區別的畫面,但觀影者因為機器間歇性運動機制的激發,卻“看”到了“電影”。對此,德國著名的電影理論家雨果·明斯特伯格強調說,電影“不存在于膠片上,甚至不存在于銀幕上,而只是存在于把它實現的人的思想之中。”20世紀10年代,機械復制的電影是否具有藝術資格是大家爭論的焦點。明斯特伯格的研究從科學和美學兩個方面給出了回答:電影不是簡單的機械復制品,它是觀影者參與“創造”的藝術。也就是說,機器不但生產影像,而且激發觀影者對影像的感知。
2.機器參與電影的表意
電影本身也是科技的產物。科技讓觀影者“看”到了電影,同時,科技也參與到電影的表意之中,甚至影響到了電影的美學形態。因為“電影較其他任何藝術形式更受工藝學的制約,音樂、舞蹈、圖畫、油畫、雕刻、詩歌,甚至建筑學的原始的和基本的形式或者不需要材料,或者是可以信手拈來的材料,但是電影攝影沒有經過苦心的設計發明和精確制造的設備,就不可能出現。電影的歷史就是它的手段的發明史。”拍攝影片時,如果攝影師要塑造一個視覺形象,他就要隨時考慮光照、鏡頭的光圈和曝光的時間等,而這些參數又取決于他使用什么型號的膠片的感光特性,如果換一種型號的膠片,他又得重新考慮調整其他參數。此外,早期電影因為膠片的感光性能較差,演員需要重彩化妝才能正確曝光。不過,當高溫快速膠片(如5247或5297)出現后,重彩化妝就不能再用了,因為膠片的高分辨率會把油彩和粉、發網甚至影片的布紋都拍下來。20世紀30年代末期,制片廠為拍彩色電影專門發明了亮度更高的燈,這些燈搭配上快速膠片和較小的光圈,使畫面的景深大為拓展,這造就了奧遜·威爾斯為代表的一個時代的深焦風格。錄音技術,如20世紀70年代出現的多聲道降噪及信號增益系統,大大增加了聲音的表現幅度——視聽表現的相對平衡的理念開始被創作者關注和應用。可以說,科技上的每一次進步都為電影的創作及其美學的轉向提供了新的可能。相比之下,不論紙、筆或印刷術發展到多么先進的水平,它們都沒有直接參與到文學的創作中來,更沒有影響文學的創作規律,它們改變的僅僅是文學的生產以及傳播的速度和范圍,真正影響文學創作的是“語言”。此外,鋼琴和制造電影的設備一樣,都是半自動化的機器,但是鋼琴并沒有影響音樂的創作規律,它只是改變了一部完成的音樂作品的演奏方式,它創造了由一個人單獨演奏復雜的多聲部音樂的可能,沒有鋼琴,音樂依然可以創作出來,音樂會照樣舉行。不過,沒有一系列的科技產品,電影就不復存在了。
二、逼真、連貫的形象結構體系
科技參與電影的創作,其實就是科技不斷釋放電影表意材料潛力的過程。具體來講,制造電影的機器的發明是一種仿生學,它摹仿的是人的眼睛和耳朵的主要結構特點:透鏡和微音器(只是不盡相同,它們沒有人的眼和耳那樣完善和靈敏)。對此,愛因漢姆認為:“就繪畫來說,從現實到畫面的途徑是從畫家的眼睛和神經系統,經過畫家的手,最后還要經過畫筆才能在畫布上留下痕跡。這個過程不像照相的過程那么機械,因為照相的過程是:物體反射的光線由一套透鏡所吸收,然后被投射到感光板上,引起化學變化。”“照相”的過程就是機械記錄的過程,即直接對真實的生活或搬演的生活進行半自動化的、精確的四維記錄:一維——線;二維——平面;三維——立體;四維——時間。聲音進入電影后,有學者認為它是第五維。“五維”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光波和聲波,即視覺和聽覺。視聽的“五維”記錄,直接、具體、連貫,可以準確全面地傳達物理現實的信息。
1.逼真性:視聽形象表意的基礎
機器記錄下來的事物,比如一只貓,其大小、體態、毛色等都是具體的,就是“這一只”,不多也不少,既不抽象也不概括。形象的精確、具體、直接是電影表意材料的基本性質。這與“語言”有所不同。銀幕上的貓,用語言學的說法,是“貓”的音響形式(能指)及其概念(所指)的合一,或者,能指和所指是短路的。實際上,銀幕上貓的視聽影像就是“所指”本身,與“能指”還沒有任何關系。貓的影像首先還不是一種“能指”,它還不具備抽象、概括、任意且能指稱它以外的某事或某物的功能,它就是它自己。這與“真正”的“符號”大為不同:符號本身首先就是指稱它以外的某事或某物的結果,它因此而生,換言之,符號本身已經是一個最小的含義單位了,而且,經由社會的約定,它與含義之間的關系穩定、通用。然而,銀幕上的貓的形象是否可以做“能指”,能夠指什么,這取決于電影制作者如何在鏡頭中或鏡頭之間來安置它。不同的情境、創作者不同的選擇和處理,貓的影像可能會與柔順、溫暖的含義建立聯系,也可能指向兇惡、不祥等含義,當然,也可能與任何其他的含義都無關,它就是它自己。按照符號學的規矩,“所指”就是指稱物,如果指稱物又指稱其他的事物,就比較荒謬了。對于電影來講,如果我們將貓的視聽影像本身認定為“能指”,不過,這個“能指”指稱的不一定就是社會本來約定給它的那個“所指”,而是另外的并不確定的什么,這無疑是反符號學的。銀幕上的視聽影像并不需要語言符號那樣的表意流程,“說話者發出的聲音在聽話者的心靈產生一個音響圖像(形式),從而激發音響形式和指稱對象(即符號所指物)之間的聯系……”電影的表意材料是直接具體的,或者說,是可聽或可見的,不需要轉述。
此外,機器記錄的精確性和具體性也取消了視聽形象這一表意材料的修飾語,“貓”在鏡頭中非常具體,無須再用形容詞或借喻隱諷的手段來描寫它。至于是黑貓還是白貓,白如雪還是別的什么,則需要機位、角度、燈光、化妝、布景甚至剪輯、錄音等表達手段來呈現。其實,就是電影創作者對事與物進行特殊的選擇:從無數的貓中做出選擇,再用無數種拍攝方式把選中的那只貓拍攝下來。進而言之,電影創作者對視聽形象的操控在于其展示或陳述的能力,即便再抽象的事物,比如思想、情感等,他也必須通過具體的影像呈現出來,他無需甚至不應該把自己的結論直接用語言轉述給觀影者:這是一只毛白如雪的波斯貓。因為,所有的觀影者看到都是同一只貓,而且貓的視聽形象直接訴諸他的視聽感官或記憶中的表象,貓就在銀幕上,黑還是白、白如雪還是什么,結論應該由觀影者給出。從表意的角度看,電影的材料走向了逼真性,或者說,逼真性是電影表意的基礎,即膠片上曝光后的影像與鏡頭視野內的一切物體的反射光的關系都是直接的,哪怕是現實生活中不存在的事物,只要設計者制造出來,機器照樣對其進行精確的“五維”記錄,即所謂“攝影機不撒謊”(錄音機同樣如此)。至于假定性或藝術性,那是逼真性的延伸——如果機位選得不合適或光的方向不對,甚至錄音稍不準確,呈現在銀幕上的白貓就可能會變成灰貓甚至根本就不像貓。藝術,這時恐怕就要放一放了。因此,電影的表意,從信息傳播的角度看,基本是一個由具象(觀影者先看到銀幕上精確具體的形象)到抽象(得出某種抽象的結論)的過程。
在性質上,這與符號作材料的語言恰恰相反:面對“貓”這個文字符號,閱讀者首先“看”到的是抽象的符號本身,與它相勾連的形象并不在現場,它需要讀者首先習得該符號,然后再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在腦海里進行各自的構想:有人可能會想到去年朋友送的那只白色的波斯貓,而有人則可能想到剛剛在路旁看到的那只灰色的流浪貓……“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意即于此。顯然,這是一個從抽象到具象的過程。當然,“具象”的程度如何,對于語言來講,則取決于解釋、說明或描寫的能力。比如,“貓”“一只貓”“一只白貓”“一只毛白如雪的貓”“一只毛白如雪的溫順的波斯貓”……語言的表意存在無限的“想象”空間,這得益于符號形式與含義之間的巨大差異,或者說,能指與所指之間的任意性是語言表意的威力所在,“在文學中,這種能指與所指之間的關系就是藝術的中心……事實上,詩歌的美在很大程度上正在于此:在于聲音與含義之間的對舞之中。”按此邏輯,電影的巨大力量恰恰在于機器的記錄直接取消了所謂的能指和所指之間的距離,它就是它,我們無需做任何努力去辨認它。或者說,觀影者不需要經過專門的學習就可以欣賞電影,更不需要具備什么相應的電影智力:嬰兒在發展說話機能之前好幾個月就能理解電影的畫面,甚至貓也看電視。所以,麥茨也說,“一部電影是很難加以解釋的,因為它太容易理解了。”
2.連貫性:視聽形象表意的結構
機器記錄下的視聽形象是連續的或運動的。1936年,英國紀錄片大師約翰·格里爾遜格指出,電影的美學是在空間中通過光波和聲波來捕捉時間流逝的美。捕捉即記錄,流逝即運動。記錄運動或許源于人類的一種原始的心理:保存生活或降伏時間,類似于巴贊所講的“木乃伊情意結”。文學可以保存生活,不過,由于語言符號系統的抽象、概括和任意性,文學記錄下的生活要靠讀者的想象和聯想才能還原;繪畫和照相也可以保存生活,但它們是對生活中某一個瞬間的凝固,是靜態的;電影可以保存生活,它通過機器的記錄與還放,不僅保證了“生活”的精確具體,還保證了“活生生”的狀態。“活生生”,意味著時間和空間的變化。不過,與每個瞬間只能表現一個空間點的線性進行的時間藝術相比,電影的空間是立體的;與一個瞬間表現一個同時性的面的空間藝術相比,它獲得了時間,即運動。
具體來講,電影的時空有些類似于生活里的感覺:連貫。其實,它是一個相對的關系:空間通過時間體現出來,是時間化的空間。同時,時間又通過空間來體現,是空間化的時間。電影的相對的時空可有各種不同的組合形式:空間的跳躍造成時間的省略;空間的重復造成時間的延長;時間的放慢造成空間的省略;時間的加速則造成空間的放大。顯然,電影是一個比較特殊的相對時空結構體:空間上,具有多信息共時性的特點,它可以在一個“面”上同時呈現人、物或事,而且,信息具有等值性,無需“停下來”對此空間中的存在另費筆墨進行描寫。同時,電影的時間是連續的而且有最小的時值(一般是二十四分之一秒一格),創作者可以通過控制時間從而設計出精確的節奏以支配和感染觀影者,而作為一個不能中斷的流程來講,也必須要有節奏,否則就是死的。更為重要的,電影空間的呈現是在二十四分之一秒一個畫格的基礎上進行的。于是,和靜態的語言符號系統需要審視不同,電影相對時空的運動使得觀影的時間和音樂作品一樣,稍縱即逝,必須一氣呵成,才能獲得一個整體的深淺不一的印象。此外,電影相對的時空結構體,是通過機器記錄下來的流動的視聽形象體現出來的。換言之,相對的時空是結構,流動的影像是體現結構的材料。這樣,電影便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表意體系:光,有自己的系統——點、線、面、縱深等,它們形成一個視覺系統。聲,也有自己的系統——距離遠近、音量大小、反射、衍射、音色、音高、共振等,即聽覺系統。聲畫結合生成的相互影像——對位或合一,又構成一個視聽系統。時間,實時和省略,構成了時間系統。空間,連貫與非連貫以及畫內與畫外,形成空間系統。時空結合則形成一個相對的時空系統,即時空統一或時空不統一。視聽系統,是表意材料的系統;相對的時空系統,是結構系統。視聽系統和相對的時空系統結合起來,就構成了電影這個母系統。電影的表意,就是創作者對這個系統的資源進行選擇、裝配的過程。
三、摹擬視聽感知經驗的表意機制
電影的機械記錄使視聽形象與現實的表層有著極其親密的關系,即直接性。當然,隨著技術的發展,電影也可以借助強大的電腦技術制作出幾乎可以亂真的視聽形象,不過,電腦制作出的影像無論多么逼真,效果多么強大,它也只是電影記錄本性下的一種輔助的手段:電腦技術本身是一種再現的媒介或藝術形式,其實質是還是一種“繪畫”,只不過,電腦技術提供了比傳統意義上的人手及畫筆更為復雜有效的工具而已。如果一部影片完全是由電腦“畫”出來的,恐怕再逼真它也只能稱為“動畫”——題材和觀察者之間的直接性被取消了,它更傾向于一種“憑空”的創造。換言之,如果抽掉機器記錄這個根本,電影也就失去了其存在論意義上的價值,也就不能稱之為電影了。
1.摹擬人的視聽感知經驗
“影片這一與真實的表層的親密關系,再結合著它那時空運動的極大自由,使它較任何其他媒介更接近于我們的帶隨意性的生活經驗。……電影制作者可以運用他手中所掌握的靈活手段使他的作品近似于現實的實際織體。此外,他無需提高效果來傳遞信息,因為他可以依靠觀眾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那種感受力(sensibilities)來打動觀眾。”⑧“感受力”,即觀影者在生活中所積累的看或聽的經驗,即視聽感知經驗。電影沒有現成的語匯可以使用,也缺乏一套普遍通用的結構規則,其表意的機制是:通過機器記錄下來的流動的視聽形象摹擬觀影者生活里看或聽的經驗。或者說,電影的含義是根據人的視聽感知經驗在影片放映的流程中體現出來的。
舉例來講,將一只貓激怒,然后把它發怒的表情以及用爪子不斷打向攝影機的動作拍下來,在銀幕上呈現時,許多觀影者會嚇一跳,有的甚至尖叫并做出躲閃的動作。實際上,“貓”只是銀幕上的視聽影像,它與觀影者并不處在一個時空之中,也沒有對其造成任何的實際傷害,但觀影者卻會產生和生活里幾乎完全一樣的反應,有的甚至比生活里的反應還要激烈。原因在于,生活中我們對外界光和聲的刺激做出某種反應,依靠的是從嬰兒時期就開始積累的視聽感知經驗,即存儲在記憶中的有關事與物的表象。電影的表意材料逼真、連貫,它直接訴諸觀影者記憶中的表象,這使其不由自主地將銀幕上流動的視聽形象“認同”為某個現象或事件的“真實”發生的過程。進而言之,電影比其他任何藝術形式更能給我們一種“直接”體驗的幻覺。而且,暗下來的影院、帶有催眠性質的銀幕、連續不斷的視覺形象和聲音,以及把觀影者淹沒在其中的大批無名的觀眾……整個的情境都會讓觀影者暫時喪失自我意識,完全沉浸在銀幕上的事件之中。電影的這種接受機制恰恰是電影表意的路徑。對此,制作者需要熟知并能富有彈性地利用觀影者看或聽的經驗來傳情達意。具體來講,電影表意者要動用生活的表層本身——確確實實的光影記錄的視覺形象和精確復制的聲音,此外,還要藝術地根據表層的內容進行挑選,通過細致的選擇和安排,形成一個符合觀影者視聽經驗的思想感情的結構或表意體系。比如影片《雁南飛》中的一場戲:薇拉要去送她的未婚夫去參軍,可是龐大的坦克車隊擋住了她。時間來不及了,她想穿過車隊趕去未婚夫家里。結果,在一個大遠景中,薇拉被夾在了兩列坦克車隊中間,進退不得,這時的薇拉顯得弱小而無助。這是戰爭和人的關系。影片創作者通過流動的視聽形象創造了一種情境,它讓觀影者好像“看”到了生活里的一種關系:戰爭機器冷漠無情,它將親近的人隔離開來。
2.現實的表層調動視聽感知經驗
可以說,電影與日常生活的表層具有天然的親近性,而且創作者也正是利用這種普通的表層來構成任何的情境和故事——抒情的或戲劇性的、歷史的或現代的。比如,美國的一部教學短片《蝴蝶》(長十分鐘),其主題是生態平衡遭到破壞。影片開始,一片美麗的自然景色:森林、花草和鳥鳴。其中,出現了一只蝴蝶,它在花草中自由地飛翔。此時,影片使用了許多鏡頭來表現那只蝴蝶的舞姿,形成了各種優美的韻律。不過,周圍的自然環境卻在不知不覺中發生變化:自然景色越來越少,樹木也變得稀疏。飛了很長一段時間,那只蝴蝶才遇見一棵樹,之后,樹變成了電線桿,過了一會兒,線桿也沒有了,蝴蝶開始在摩天大樓中飛。接著,蝴蝶飛進了一座大廈的大門里。一時,攝影機似乎找不到那只蝴蝶了,之后,它也趕忙進了大樓,拐進一個走廊,一個門一個門地找。最后,攝影機終于在一個門口看見了那只蝴蝶:它停在房間的一面墻上,攝影機推上去,原來那是一只釘在墻上的蝴蝶標本。整部短片沒有使用任何語言(解說或字幕)。不過,觀影者不但能看懂而且還可以根據其生活經驗為自然景色前后的對比以及蝴蝶前后的變化賦予含義:環境惡化,吞噬生命。由此,電影要通過摹擬精煉地表現一個事件或講一個故事,在基本的生理——心理效應的基礎上,還要從視聽思維的角度去模擬人的主觀思維活動——這是一個逆向的過程,即把客觀世界攝取的素材變成觀影者內在的思維活動。或者說,在記錄的基礎上,把外部事件從視聽感知的角度加以塑造,直到調整到符合觀影者的主觀的思維活動為止。只有這樣,觀影者在情感或理性上才會對銀幕上視聽形象構建的織體形成共鳴。
簡言之,電影制作者通過逼真、連貫的視聽形象作為表意的材料,這種材料的組織往往基于觀影者的社會認知和心理認識——這種感知大多是非文字的(nonverbal),而且常常以一些外觀上無意義的提示或征兆作為依據。因此,電影的表意和感知并不局限于受過教育或有天分的人,“我們全靠這類感知來認識他人并且對于那些微妙細膩的跡象——如語氣的微妙變化、躲閃的目光——非常的心領神會。但是這種微妙的感受是很難為其他藝術所使用的,因為作為它的基礎的這種親近性和總體經驗是文學和戲劇所不能提供的,因為它們依靠文字;這也是視覺藝術所無法提供的,因為它們依靠畫面。只有影片所造成的經驗具有足夠的親近和總體性來使我們在生活中所運用的感知程序起作用。”
結語
美國電影理論家詹·莫納柯考察了人類藝術演進的路線。他認為,迄今為止有三類藝術形式:一是演出的藝術。它發生于實時,比如話劇、歌劇、芭蕾舞等。演出的藝術形式,其媒材以假定為本,講求表演,演員是核心。二是再現的藝術。它依靠媒材既定的編碼和語言規程,把題材的信息轉達給觀察者,比如繪畫和文學。再現的藝術形式使現象的“再創造”成為可能,然而它們都要求使用復雜的語言系統(繪畫幾乎像小說一樣依靠語言,比如,在充分理解一幅日本畫之前,必須學會它的“語言”),而且,那些語言由個人掌握,因此選擇的因素——過去和現在——在再現藝術中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而這,也是其美學的源泉。三是記錄的藝術。它的媒材提供了一條題材與觀察者之間更為直接的途徑。比如電影。機器記錄并還放的流動的視聽形象可以準確生動地表意但并不需要語言那樣一套穩定通用的符號系統,它有自己獨特的表意體系和表意機制。從本質來說,電影比再現的藝術形式直接得多。而且,從歷史來看,紀錄媒介的發明就像七千年前文字的發明一樣重要,因為照相、電影和錄音總合起來,完全轉變了我們的歷史透視,它第一次使人類學會了用記錄機器來生產表意材料,依靠機器的記錄——組合——放映來產生藝術效果和美學感染力。
【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