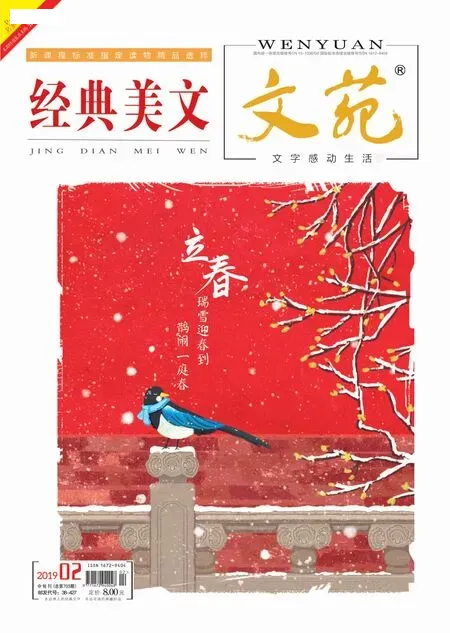舌尖上的汪氏父子
2019-11-15 08:42:10文/王干
文苑
2019年4期
文/王 干
汪朗是汪曾祺先生的大公子,資深媒體人,燒一勺子好菜,寫一手好散文。我和他的交往可追敘到25年前。那時候汪曾祺老先生住在蒲黃榆,我被借調到《文藝報》工作,周末節假日隔三岔五地到老頭家蹭飯。蹭飯是一個原因,更重要的是,汪曾祺先生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偶像,我是汪先生的追隨者、模仿者、研究者。能和自己的偶像一起進餐,是最幸福的事了,精神上的享受也是最高級別的。
汪曾祺先生在文壇的美食大名,跟他的廚藝有關。據汪朗統計,除了汪先生的家人,我是嘗汪先生的廚藝最多的人。因為吃多了,總結老頭的美食經大約有三:一是量小。汪先生請人吃飯,菜的品種很少,但很精,不湊乎。量也不多,基本夠吃,或不夠吃。這和他的作品相似,精練,味兒卻不一般。二是雜。這可能與汪先生的閱歷有關,年輕時國家動蕩四處漂流,口味自然雜了,不像很多的江浙作家只愛淮揚菜。我第一次吃雞樅,就是1986年在他家里,炸醬面拌油雞樅,味道仙絕。直到現在,我拿云南這種獨特菌類招待人,很多北京人、很多作家不知雞樅為何物。三愛嘗試,他喜歡做一些新花樣的菜。仙游前十幾天,他還用剩余的羊油燒麻豆腐招待我,說:“合味,下酒。”
因為周末汪朗帶媳婦孩子看老爺子,我們就認識了。汪朗一來,汪先生就不下廚了,說汪朗會做。老頭便和我海闊天空地聊天,我開始是聆聽,時間長了,也話多起來。汪朗則在廚房里忙這忙那,到十二點就吆喝一聲:“開飯了。……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