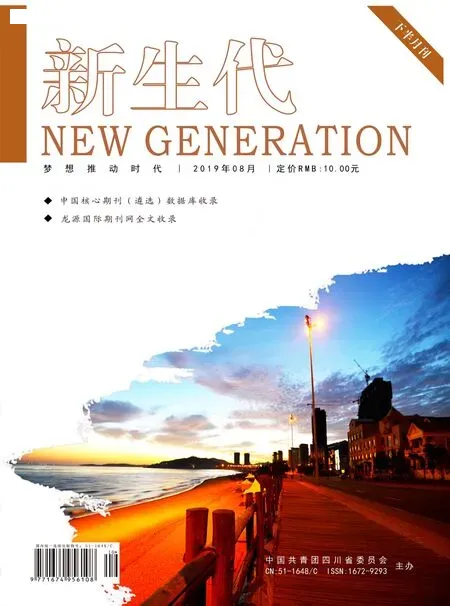民族自決權的主體范圍研究
李洋洋 河北大學 河北保定 071000
民族自決權的重要性在二戰后達到頂峰,通過發揮其對民族獨立和民族解放的推動作用,使得越來越多的國家對民族自決權持支持、贊同的積極態度.但隨著時代的發展變革,民族自決權這把雙刃劍,一方面仍是主權、人權和人民的基本自由保障之基礎,另一方面因其主體范圍的不確定性具有被濫用的可能,給國際社會形勢帶來了負面影響.
一、民族自決權的概念明晰
我國王英津學者提出了學科劃分來界定民族自決權,而本文所討論的就是學科劃分中的國際法意義上的民族自決權.對于民族自決權的概念存在狹義與廣義兩種觀點,二者的區別主要體現在民族自決權主體及內容兩方面.狹義概念將民族自決權的主體限制在深受殖民壓迫的人民及外國占領奴役下的人民范圍內,且這兩種主體僅在涉及自身未來發展和政治地位這兩方面可以取得民族獨立的權利;而廣義概念將主體擴大至所有民族和人民,且他們所享有的民族自決權既包括基本的事務自行處理權,也包括自主決定其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如何發展的權利,并且這些權利不受外國社會和其他勢力的干涉.不論是從狹義概念或是廣義概念,我們都可以得出民族自決權是特定主體所享有的自己處理基本事務,自主決定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自由發展的一項集體人權.
二、民族自決權的理論發展
民族自決權的理論內涵既來源于歐洲的思想啟蒙也被社會主義思想充實著.十八世紀的美國獨立戰爭與法國大革命真正將民族自決思想從理論的紙上談兵變為了實際的金戈鐵馬.美國《獨立宣言》中的宣告是民族自決權早期較為明確的表述,而在法國大革命中的"三民口號"更是直接表明了法蘭西對于民族自決權的正面態度.與資本主義相對陣營的馬克思、恩格斯也提出了具有社會主義特色的民族自決理論.其后,列寧繼承了馬克思對于民族自決的肯定與支持,連續多次發表著作,并從無產階級角度將民族自決權定義為"民族自決權就是民族脫離異族集體的國家分離,就是組織獨立的民族國家",同時他指出民族自決權不可以隨意濫用,應當在具備這兩個先決條件的情況下,民族自決權才是正當合理適用,其一是事實存在殖民統治,其二時在若為多民族國家,其內部應存在民族壓迫;除此之外無限度的分離并非民族自決的初衷,民族自決的本質是建立在無壓迫、無殖民基礎上的民族團結和諧,這一點筆者認為是民族自決的精髓所在.
三、民族自決權的主體范圍界定
民族自決權中權利主體范圍到底應該如何界定是當前國際法尚存爭議的話題,到底適用主體應該是人民還是國家,學者們各執一詞.有的學者認為行使民族自決權的主體應當是以共同的發展文化背景為基礎,具有相同或相類似的習俗及思考方式,所形成的聚集體,或者說是狹義的民族.這里面就涉及到多民族國家內單獨的人數相對較少的民族是否也可以擁有民族自決權.國內外的主流觀點還是認為,一個國家內部的少數民族群體不應當擁有民族自決權.我國認為民族自決權主體僅包括處于殖民統治之下、正在爭取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的民族;處在外國軍事侵略和占領下的民族;主權國家的全體人民這三種.但是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民族自決權的主體范圍被確定為"所有民族",我國在這一問題上進行了條約保留.我國的做法是否恰當合理,學界也是議論紛紛,筆者贊同張磊學者的觀點,我國所進行的適當保留在沒有違背公約的根本目的情況下,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一方面在民族自決權產生到形成到早期發展的進程中,其主體范圍常被描述為"在外國奴役和殖民統治下的被壓迫民族或人民自由決定自己命運、擺脫殖民統治、建立民族獨立國家的權利";另一方面對于具有法律效力的條文解釋,我們不能僅拘泥于它的表面文義,尤其是對于這種具有歷史延續性的條文,除了普遍的文義解釋外還應當結合其產生背景,兩種方法綜合運用才能更為準確得出其含義.從公約創制的歷史背景來看,它屬于反殖民運動浪潮下的產物,如果將"所有民族"放在該情境下,筆者認為應當是特指被外國奴役、殖民壓迫的民族和人民,而并非是全部民族這一擴大含義.但國際法對于是否可以擴大到所有民族這一問題態度曖昧.科索沃獨立事件后,作為聯合國司法機構的國際法院就此事件給出的結論為科索沃宣布獨立的行為方式沒有違反任何國際法規則,這種說法既沒有承認民族自決權可以擴大到所有民族,也沒有說明不可以擴大到所有民族,僅是就該行為是否違法進行了界定,實質上并沒有解決問題.這也讓民族自決權這一初衷美好的權利存在被濫用的可能性,甚至淪為某些強國分裂其他國家的手段.
國際法確立民族自決原則不是給予任何民族隨意使用民族自決權的機會,更不能成為某些強國施行霸權主義及不良分子分裂國家的合理外衣.在未來發展進程中,我們對民族自決權的內涵進行更新與補充的同時也要加強對其使用條件的限制,尤其應當明確民族自決權的主體范圍,如此才能使民族自決權在新時代煥發出勃勃生機.
- 新生代的其它文章
- ">乘"微"破浪——略談小學語文教學中微課資源的運用
- ">論"手機依賴癥"對大學生人際關系的影響——以滁州市大學生為例
- 爭當師德標兵 加強師德建設——藥學口腔系黨支部主題年度活動
- 中國共產黨革命精神的內涵及其傳承
- 試析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的實踐觀
- 政府部門間電子政務信息共享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