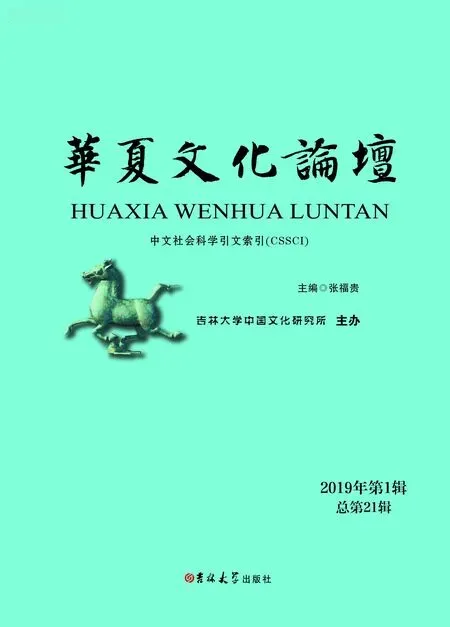新聞專業(yè)主義的文化政治
盛 陽
一、引 言
新聞專業(yè)主義是當(dāng)代中國新聞學(xué)研究的重要命題。在現(xiàn)代通信技術(shù)升級改造、信息生產(chǎn)與傳播方式不斷發(fā)展的轉(zhuǎn)型過程中,傳統(tǒng)新聞業(yè)在技術(shù)、政治、倫理和正當(dāng)性層面也受到諸多挑戰(zhàn)。在這些不確定條件下,新聞專業(yè)主義既被用于充當(dāng)鞏固行業(yè)合法性的理論武器,這一概念自身也持續(xù)遭到解構(gòu)和挑戰(zhàn)。作為不斷延伸和拓展的知識范疇,新聞專業(yè)主義內(nèi)部不乏客觀性、中立平衡等重要的價值理念,但是,如果將專業(yè)主義視為整合新聞實踐及其價值判斷的基本前提,作為標(biāo)尺存在的專業(yè)主義本身就已經(jīng)高度“意識形態(tài)化”。
事實上,新聞專業(yè)主義是歷史性的話語構(gòu)造。根據(jù)哈克特和趙月枝對新聞客觀性的觀念史研究,在19世紀(jì)的北美,正是商業(yè)報刊對勞工報刊民主話語的吸納,客觀上奠定了新聞專業(yè)主義的基石,造就了工人階級報刊的迅速退化。在20世紀(jì)后期的西方社會,新自由主義進(jìn)一步推動了新聞專業(yè)主義理念的發(fā)展。在新自由主義思潮和政策安排下,新聞專業(yè)主義不斷擴(kuò)張,發(fā)展出了一套完整的概念體系。如果類比丹·席勒(Dan Schiller)對傳播技術(shù)政治性的論述,新聞專業(yè)主義不是天然存在的哲學(xué)概念,而是保守性的政治力量:新聞專業(yè)主義的出現(xiàn),“正是打破社會力量平衡的激進(jìn)改革的結(jié)果,而不是原因”。
本文將從社會結(jié)構(gòu)和文化思潮切入,對新聞專業(yè)主義的文化政治展開分析。首先,本文從新聞與文化政治的角度,系統(tǒng)梳理新自由主義的思想內(nèi)涵。作為當(dāng)代新聞專業(yè)主義的思想背景和歷史語境,新自由主義的行動訴求和政治原則,為理解新聞專業(yè)主義的文化政治及其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意涵提供了結(jié)構(gòu)性框架。其次,本文從媒介技術(shù)變革的歷史與當(dāng)代語境,分析新聞專業(yè)主義的實踐訴求與現(xiàn)實困境。最后,本文從中國語境出發(fā),批判性地分析新聞專業(yè)主義的歷史意義及其局限。
二、流動的學(xué)說:新自由主義知識考古
作為現(xiàn)代經(jīng)濟(jì)學(xué)理論的分支,新自由主義的論述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紀(jì)20年代。作為對社會主義理念及其制度的批評,新自由主義在米塞斯、哈耶克等小范圍的經(jīng)濟(jì)學(xué)家內(nèi)部傳播。這一思潮最初秉持的理念是,“不必對人類需求進(jìn)行探求,只需用科學(xué)規(guī)劃的方式把握住買主偏好”。作為理論設(shè)計,新自由主義以新古典經(jīng)濟(jì)學(xué)為核心,簡要來說就是把經(jīng)濟(jì)從政治中剝離,用私有產(chǎn)權(quán)、自由市場、程序正義等手段替代高度組織化的經(jīng)濟(jì)生產(chǎn)模式和實質(zhì)正義,批判國家干預(yù)和福利政策。
新自由主義不是通約式的公理,也從沒有在現(xiàn)實政治中獲得徹底執(zhí)行,是一種“不完整”的歷史和政治實踐。作為實用主義的政策設(shè)計,新自由主義被國家政府部分提取并選擇性執(zhí)行。在執(zhí)行過程中,它被認(rèn)定為強(qiáng)有力的反社會主義理論資源,這里的社會主義既包括世界體系中的社會主義國家制度,也包括西方資本主義內(nèi)部的社會主義元素。因此新自由主義是一項激進(jìn)的政治議程。
需要?dú)v史性地理解新自由主義的政治威懾力。在理論誕生的最初,它并沒有進(jìn)入西方的主流政治議程,卻通過單向度的知識輸送、政策引導(dǎo)、技術(shù)支持、輿論宣傳等多種方式,參與到20世紀(jì)80年代的蘇聯(lián)解體、拉美軍事政變等一系列社會變革中。世界范圍內(nèi)的廣泛試驗幫助新自由主義完成了政治資本的原始積累,使得它通過“理論旅行”的方式從“試驗場”再度回到歐美政治舞臺中心,成為里根—撒切爾時代執(zhí)政的主導(dǎo)資源。
在世界范圍內(nèi)的后社會主義國家,新自由主義理論落實為實現(xiàn)資本主義現(xiàn)代化的建構(gòu)性目標(biāo),其中包括在行政體系、經(jīng)營管理、財務(wù)審計等宏觀制度層面去組織化的改造;也包括微觀層面,對于去技能化的、競爭型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塑造。哲學(xué)層面用個人主義、普遍主義理念替代全球結(jié)構(gòu)性不平等條件下激發(fā)的集體主義、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技術(shù)層面,新自由主義政策通過對生產(chǎn)率、比較優(yōu)勢、法制程序等經(jīng)濟(jì)、政策、法律指標(biāo)的強(qiáng)調(diào),替代管理自主、技術(shù)主權(quán)、階級政治等實質(zhì)正義過程。新自由主義表現(xiàn)為有著強(qiáng)烈政治對手——發(fā)生在被外部化的內(nèi)部和被內(nèi)部化的外部的,想象的或?qū)嶓w的激進(jìn)主義。
可以借助政治社會學(xué)進(jìn)一步理解新自由主義。哈佛大學(xué)批判法學(xué)家昂格爾(Roberto Unger)對政治有廣義、狹義兩種區(qū)分。在他看來,政治可以被狹義解釋為“政府機(jī)構(gòu)及其權(quán)力配置”。一般而言,這是西方自由主義政治學(xué)對政治的傳統(tǒng)定義,進(jìn)而通過政治科學(xué)公理化、量化研究和概率論等對社會政治的不確定性進(jìn)行開放分析。另一方面,政治也可以被廣義地解釋為“統(tǒng)領(lǐng)于社會生活、個人生活所有方面的組織形式和交往方式”。在他看來,應(yīng)當(dāng)更多地從廣義方面來理解政治。從這個角度看,新自由主義視野中的政治體現(xiàn)為雙重性:政治首先被框定在狹義的行政范疇中,再寄希望于國家政策的進(jìn)入、推動和落實,用政治進(jìn)入的方式反政治。換句話說,新自由主義將國家的意義全部擠壓在狹義政治的密閉空間,再用廣義化政治行動的方式,發(fā)動對國家政治的反叛。
新自由主義政治議程在抹去國家政權(quán)豐富意義的同時,又以要求國家推動市場化的方式拓展了政治權(quán)力的邊界。在新聞實踐中對應(yīng)著新聞專業(yè)主義的要求。這種廣義化政治不是人民民主意義上的政治實踐,而是被資本和權(quán)力捆綁住的政治議程,也就是去政治化的政治過程。
三、新自由主義思潮中的新聞專業(yè)主義
切換到傳媒行業(yè),新自由主義主要表現(xiàn)為“去規(guī)制化”的政策手段,即通過降低媒體準(zhǔn)入門檻、開放市場準(zhǔn)入權(quán)利,讓多樣化資本進(jìn)入原來封閉、壟斷的媒體行業(yè),從而改變原有公共服務(wù)的壟斷格局。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國《1996年電信法案》(Telecommunications Act of 1996
)。從全球范圍看,這演變?yōu)橐粓觥皻v史上無與倫比的資產(chǎn)集體轉(zhuǎn)讓”:“從1988年智利電信運(yùn)營私有化開始到2005年,不少于80個欠發(fā)達(dá)國家進(jìn)行了網(wǎng)絡(luò)私有化”,巨大的資本密集型行業(yè)對私人投資的開放,將美國“曾經(jīng)最大的工會化雇主變成了股票交易量最大的商業(yè)公司”。根據(jù)北京大學(xué)吳靖教授的分析,電信法案的發(fā)布,直接導(dǎo)致了20世紀(jì)90年代末期、21世紀(jì)初期出現(xiàn)的大量媒體兼并。這一兼并過程不僅在資本規(guī)模方面越來越大,內(nèi)部更出現(xiàn)了跨行業(yè)的資本整合。而原本基于公共服務(wù)的考慮,媒體不能一家獨(dú)大,例如雖然電視行業(yè)存在壟斷,但它的另一面是廣播或其他媒體渠道對電視行業(yè)的競爭。憑借政策推動和資本執(zhí)行,新自由主義被注入美國媒體專業(yè)主義的觀念體系中。
有學(xué)者認(rèn)為,新聞專業(yè)主義進(jìn)入公共服務(wù)的正當(dāng)性,建立在“新聞媒體不應(yīng)當(dāng)被賦予過多的角色期待”的行業(yè)定位,以及“制約公共生活的真正障礙來自體制結(jié)構(gòu)”的雙重認(rèn)知條件中。“中立”的新聞專業(yè)主義被積極調(diào)動,改造被體制束縛的公共服務(wù)體系。相反的觀點認(rèn)為,新聞專業(yè)主義不是客觀中立、價值無涉的觀念,它恰恰建立在對新自由主義體制結(jié)構(gòu)的認(rèn)同上:“新聞專業(yè)的意識形態(tài)及其實踐”反映了新自由主義反意識形態(tài)、“后政治”(post-political)的意識形態(tài)話語。
更為重要的是,新聞場本身就是公地(commons)的一部分,內(nèi)在于社會關(guān)系中,因此“新聞專業(yè)主義進(jìn)入公共服務(wù)”這一議題牽涉到誰是新聞傳播的主體這一問題。如果承認(rèn)新聞事業(yè)本身是社會建設(shè)的一部分,中國的新聞事業(yè)是與人民民主專政在主體性方面高度統(tǒng)一的,那么新聞專業(yè)主義試圖“進(jìn)入”公共服務(wù)的議題則至少包括了兩層含義:第一,新聞專業(yè)主義首先要割斷新聞事業(yè)與國家制度的聯(lián)系,即新聞“離開”公共服務(wù);第二,在完成行業(yè)獨(dú)立、資本化運(yùn)作改造之后,再重新“進(jìn)入”公共服務(wù)市場,瓜分馬克思主義新聞學(xué)及其文化領(lǐng)導(dǎo)權(quán)。所以真正需要討論的不是新聞專業(yè)主義如何走進(jìn)、參與公共領(lǐng)域,而是公共性如何在新聞報道中得到體現(xiàn),“無論用哪種最前沿的理論或最新潮的視角來看,‘走基層'報道的實質(zhì)都是讓新聞報道回歸其‘人民性'和‘公共性'的主體,讓普通民眾成為新聞生產(chǎn)和傳播的主體”。這再次說明,新自由主義并不能僅僅從市場原教旨主義、極端消費(fèi)主義以及絕對個人主義的形而上學(xué)層面去理解。
事實上,對于新聞專業(yè)主義的辨析,無法脫離開傳媒資本運(yùn)作等權(quán)力體系和社會政治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新聞專業(yè)主義在西方傳媒機(jī)構(gòu)中的展開,自有其政治經(jīng)濟(jì)土壤和社會文化語境。與新自由主義相同,新聞專業(yè)主義只是自由主義的烏托邦想象,從來沒有完整地得到執(zhí)行。以西方媒體中大量存在的“恐怖主義”宣傳報道為例。西方思想界已有對《紐約時報》、CNN新聞臺等主流媒體的深刻反思。《美國的恐怖主義成癮癥》(America
's Addiction to Terrorism
)一書就指出,對“恐怖主義”的混用,恰恰是造成社會和思想失序的根源。事實上,如果媒體配合當(dāng)權(quán)政府,對當(dāng)代中東、伊斯蘭等復(fù)雜問題一概貼上“恐怖主義”的標(biāo)簽,仿佛只要把社會矛盾的原因全部歸咎于惡的“恐怖主義”,就可以停止追問、停止思考,一切就得到了合理解釋。這種思想的懶惰造成了對其中蘊(yùn)含的階級分化、貧富差距等全球性議題的視而不見。進(jìn)一步說,新聞界的思想快餐和眼球經(jīng)濟(jì)只是專業(yè)媒體缺陷的表象,更重要的是,那些把持信息和思想生產(chǎn)權(quán),同時以客觀中立為標(biāo)榜的資本化媒體——它們客觀中立性的前提是承認(rèn)資本主義制度的合法性——直接抹去了對社會問題進(jìn)行嚴(yán)肅辯論、分析和思考的公共空間。實際上,專業(yè)性只是西方媒體報道在操作層面的規(guī)范,而這種專業(yè)性的行業(yè)規(guī)范不是專業(yè)主義所斷言的去政治化的、排他性的絕對主義。進(jìn)一步說,專業(yè)性理念本身就有自己的前提預(yù)設(shè)和政策主張,即它是在特定的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土壤中生長的,因此主要是對這一制度的默認(rèn)和維護(hù),并通過信息傳播、改造資源配置的方式保持和推動這一制度的運(yùn)轉(zhuǎn),是一種保守性的政治力量。這并不匹配社會主義中國的文化政治語境。
理論上,新聞專業(yè)主義可以理解為在新聞生產(chǎn)環(huán)節(jié)中對生產(chǎn)過程、工作倫理的規(guī)范化要求。但若我們僅僅從本質(zhì)主義層面對其進(jìn)行辨認(rèn),那么我們對它的認(rèn)識就基本止步于“真實、客觀、平衡、全面等天然正確的理念”。然而新聞專業(yè)主義運(yùn)動是在新聞倫理和政治社會學(xué)范疇內(nèi)展開的一項政治改造運(yùn)動。它通過對麥克切斯尼(Robert McChesney)所言的“美國新聞史的黑暗時代”(the Dark Ages of American journalism)的批判,建立自身的合法性。因此,我們需要在動態(tài)的政治關(guān)系和更開闊的社會空間中論述這一過程。它至少包括四個方面:
第一,在西方傳統(tǒng)媒體中,新聞專業(yè)主義首先將存在著勞資對立的行業(yè)群體抽象為一個整體的“新聞人”,忽略了作為勞動過程的新聞生產(chǎn)內(nèi)部的雇傭關(guān)系和勞資關(guān)系,抹去了政治經(jīng)濟(jì)分析的空間;
第二,專業(yè)主義將廣義上的新聞生產(chǎn)裁定為編輯部內(nèi)部的專業(yè)化職業(yè)生產(chǎn)。編輯部行業(yè)門檻和自我隔離,切斷了與制版、印刷、分發(fā)等傳播產(chǎn)業(yè)鏈之間的聯(lián)系(在新聞生產(chǎn)的數(shù)字化時代,傳播產(chǎn)業(yè)鏈延展至全球范圍),理論上拒絕了整體性分析的可能;
第三,法權(quán)層面,新聞專業(yè)主義對使用權(quán)的強(qiáng)調(diào),以及對所有權(quán)轉(zhuǎn)移問題的遮蔽,催生了新聞領(lǐng)域內(nèi)的雇傭勞工職業(yè)群體。“從階級撤退”的勞動分工方案,使得文化政治與階級意識形態(tài)的辯證分析變得不可能;
第四,全球金融資本主義、世界勞動分工體系與全球市場的形成,以及西方中心主義的全球史觀、意識形態(tài)的形成,共同培育了階級情感與國際主義意識模糊的西方中產(chǎn)階級群體,這一群體在供給側(cè)孕育了作為職業(yè)群體的新聞從業(yè)者,在需求側(cè)再生產(chǎn)了意識形態(tài)模糊的都市消費(fèi)主義群體。
問題是,在西方大眾媒體議程中,很少能看到對這一全球性問題的思考,而中國都市媒體除了對傳播消費(fèi)過程——例如點擊率、收視率、票房、移動通信和新媒體終端銷售狀況等——給予關(guān)注,媒體視野中的中國南方生產(chǎn)線以及產(chǎn)業(yè)工人幾乎都被納入國家與市場對立的分析框架中。用沃勒斯坦世界體系理論解讀,這與西方媒體處在全球傳播生產(chǎn)體系相對優(yōu)渥的核心地帶,中國媒體處在亞核心地帶,因而處在各自特定的政治經(jīng)濟(jì)視野密切相關(guān)。西方媒體看到的非洲,不是在后殖民主義時代依舊受到西方資本主義盤剝的、苦難深重的不平等地區(qū),也不是日復(fù)一日將通信產(chǎn)品原材料運(yùn)輸?shù)饺蚰戏竭M(jìn)行再生產(chǎn)的產(chǎn)業(yè)鏈底層,這個具有全球意義的跨國勞資問題被翻譯為文明等級與文明沖突問題。
四、媒介變革視野中的新聞專業(yè)主義
傳播技術(shù)的發(fā)展再次將新聞專業(yè)主義推上議程。在新媒體研究中,一個重要的議題是如何看待新技術(shù)對新聞業(yè)的影響。主流邏輯是,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通過人工智能、云計算、平臺媒體等科技手段,在國家產(chǎn)業(yè)政策傾斜條件下,將信息傳播的產(chǎn)業(yè)化不斷納入互聯(lián)網(wǎng)產(chǎn)業(yè)內(nèi)部。傳統(tǒng)新聞業(yè)不得不被動地展開新媒體技術(shù)轉(zhuǎn)軌,否則將遭遇無情的行業(yè)洗牌。這被廣泛解讀為技術(shù)問題:技術(shù)發(fā)展對傳媒業(yè)來說不是令人欣喜的文明進(jìn)步,而是一個“生存還是毀滅”的生死存亡問題。不僅如此,技術(shù)變革和普及還帶來了“后真相”的道德恐慌,堅守專業(yè)主義則是這一邏輯下的必然產(chǎn)物。
如果單從技術(shù)發(fā)展史來看,技術(shù)升級本身只意味著技術(shù)間的迭代,是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其進(jìn)步性在于提高了傳播生產(chǎn)力。那么,新媒體技術(shù)的發(fā)展何以造成媒體行業(yè)內(nèi)部恐慌,甚至在現(xiàn)實層面造成了實踐轉(zhuǎn)型和大規(guī)模的失業(yè)問題?為回答這一問題,我們可以首先回到《資本論》。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馬克思就生動地講述了百年前的歐洲“人機(jī)大戰(zhàn)”斗爭史:在1758年,英國首先制成了水力剪毛機(jī),但是它隨后就被10萬名失業(yè)者焚毀;19世紀(jì)初期,蒸汽織機(jī)的應(yīng)用又造成英國規(guī)模浩大的工人破壞運(yùn)動,即著名的魯?shù)逻\(yùn)動(Luddite Movement)。在那里,新技術(shù)的發(fā)明對掌握舊技術(shù)的工人來說不意味著生產(chǎn)方式的提高,而是勞動機(jī)會的替代。工人與技術(shù)之間不是相互促進(jìn)的關(guān)系,而是相互排斥的關(guān)系。
馬克思從“勞資關(guān)系”展開人機(jī)斗爭史的分析:“資本家和雇傭工人之間的斗爭是同資本關(guān)系本身一起開始的……在采用機(jī)器以后,工人才開始反對勞動資料本身,即反對資本的物質(zhì)存在方式”。他特別指出兩點:第一,工人反抗機(jī)器和技術(shù)是不理智的,工人學(xué)會區(qū)別開機(jī)器和機(jī)器的資本主義應(yīng)用,從而把攻擊的矛頭從物質(zhì)生產(chǎn)資料本身轉(zhuǎn)向它的社會使用形式,是“需要時間和經(jīng)驗的”;第二,工場手工業(yè)內(nèi)部為工資進(jìn)行的經(jīng)濟(jì)斗爭,是以這一生產(chǎn)關(guān)系本身為前提的,因而是不徹底的,“根本不反對它的存在”。根據(jù)馬克思的判斷,與資本捆綁的技術(shù)發(fā)展,只能帶動新興資本對原有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的挑戰(zhàn),在現(xiàn)實生活中表現(xiàn)為對原有市場結(jié)構(gòu)、資源配置、勞動分工等多方位的沖擊。因此,技術(shù)的發(fā)展才會一方面表現(xiàn)為現(xiàn)代文明的進(jìn)步、新的勞動分工的形成,另一方面同時表現(xiàn)為對部分勞動機(jī)會的摧毀。
數(shù)字平臺技術(shù)對市場化傳媒業(yè)的改造也是如此。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個體的斗爭,比如斯諾登對美國新聞業(yè)和秘密政治的揭露、反對知識私有化的“著佐權(quán)”(Copyleft)運(yùn)動、政治權(quán)力對網(wǎng)絡(luò)知識共享倡議者的壓迫,以及《點共產(chǎn)主義宣言》(The dotCommunist Manifesto
)、《開放存取游擊隊宣言》(Guerilla Open Access Manifesto
)等數(shù)字媒體工人革命綱領(lǐng)等等,它們都是21世紀(jì)的魯?shù)逻\(yùn)動。另一方面,技術(shù)政治史敘事也廣泛存在于最普遍的日常條件中:資本主義商業(yè)競爭的條件下,技術(shù)對人的牽引,迫使部分傳統(tǒng)媒體人離職,或轉(zhuǎn)型為以互聯(lián)網(wǎng)為生產(chǎn)資料的網(wǎng)絡(luò)自媒體。與此同時,政治蛻化為權(quán)力控制,最直觀的表現(xiàn)是互聯(lián)網(wǎng)媒體平臺的刪帖現(xiàn)象(例如左翼言論也常常被暴力刪除)。在宏觀層面,媒介融合也可以被理解為新聞生產(chǎn)方式、勞動分工方式對數(shù)字技術(shù)——技術(shù)發(fā)展本身由資本帶動——的妥協(xié)。
在這一意義上,如果依舊用新聞專業(yè)主義的道德放大鏡考察傳媒業(yè)困境,只能造成對困境根本原因的視而不見。更為重要的是,在中國條件下發(fā)生的新聞專業(yè)主義運(yùn)動中,行業(yè)獨(dú)立、經(jīng)營自主、資本化恰恰成為其首要訴求,因此新聞專業(yè)主義甚至都不是根除中國商業(yè)新聞業(yè)困境的配方,而恰恰是癥候本身。用斯邁思(Dallas Smythe)的話說:“真正需要承當(dāng)責(zé)任的,恰恰在社會組織和政策內(nèi)部——西方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而)幻想通過‘技術(shù)'治愈西方社會病,就如同奢望天上掉餡餅”。
在此我們不妨?xí)诚耄挥袕馁Y本化的新聞業(yè)內(nèi)部的生產(chǎn)關(guān)系和勞動方式等問題切入,重新闡述聯(lián)合化生產(chǎn)、技術(shù)主權(quán)、管理主權(quán)、剩余資料分配等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問題,從結(jié)構(gòu)層面對這一系列危機(jī)進(jìn)行反思,才能真正理解傳媒業(yè)困境。這是因為,新聞行業(yè)危機(jī)是以新自由主義危機(jī)為內(nèi)核的表象;新自由主義和新聞專業(yè)主義不是問題的答案,而是問題本身。
五、小 結(jié)
如果認(rèn)為新聞專業(yè)主義的根本要求在于通過變更產(chǎn)權(quán)關(guān)系的方式,改變生產(chǎn)力和生產(chǎn)關(guān)系,它固然起到過一定積極作用。但是,新時代中國的主要矛盾已經(jīng)從“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zhì)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chǎn)”轉(zhuǎn)化到“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fā)展”之間;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不僅在于物質(zhì)文化生活,更在于“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huán)境”等各個方面。這恰恰提醒了當(dāng)代的中國新聞實踐,在改進(jìn)傳播生產(chǎn)力與生產(chǎn)關(guān)系之外,必須重新挖掘“公平、正義”平等政治的落實方式,重新思考黨群與新聞事業(yè)的辯證關(guān)系,重新探討新聞實踐如何全面切入社會建設(shè)的歷史進(jìn)程。
如果把新聞學(xué)作為參與社會歷史進(jìn)程的進(jìn)步力量,必須重新思考新聞傳播的文化領(lǐng)導(dǎo)權(quán)問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聞發(fā)展進(jìn)程中,群眾辦報思想、人民通訊員制度、農(nóng)村電影放映隊到當(dāng)代的打工春晚、新工人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等都是文化領(lǐng)導(dǎo)權(quán)具體的體現(xiàn)。堅持新聞媒體的社會主義性質(zhì),不是在國家權(quán)力/市場的二元論框架中對國家制度的排除,而是廣泛吸納政策制定者、新聞工作者、城鄉(xiāng)群眾,共同參與到傳播制度設(shè)計和新聞書寫。因此,如果說新聞專業(yè)主義是西方資本主義新聞實踐在新自由主義思潮中的內(nèi)卷化,是知識分子對資本主義結(jié)構(gòu)內(nèi)部的批判,而不是對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批判,那么在中國語境中,新聞專業(yè)主義無法擔(dān)當(dāng)指導(dǎo)新聞實踐的行動綱領(lǐng),對新聞業(yè)的構(gòu)想應(yīng)該置于更為開放和建設(shè)性的歷史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