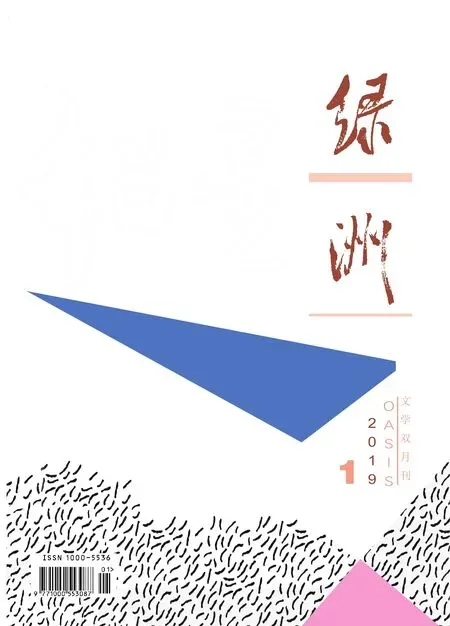天空并不遙遠
梁積林
扎斯停了車,拉起了手剎。他把車載播放器里的音樂調到了歌曲《鴻雁》上。他搖下車窗,又往大里開了開音量。他趴在車窗,向天空仰望,一只鷹盤旋著,突然一個俯沖,落在了對面山腰的一根石柱上。他拿上副駕駛位上的相機下了車。他又一個腿子跨上車,把播放器的音量開到了最大。隨著被音樂震顫了的車身,他的身子也顫栗了一下。他倚著車邊停了停,閉上眼睛,隨音樂哼了幾聲。他覺得釋放了點什么,或者還有別的。他舒了口氣,下了車,但沒有關車門,這樣音樂傳出的聲音大,在整個峽谷里回蕩,對他是一種陪伴,也是激越。
他打開了相機蓋,向著石柱上的鷹對好了焦距。他迷眼按下快門,石柱和鷹定格在了鏡框里,像一幅巖畫。
《鴻雁》依然唱著,已近尾聲。一股水一樣的東西在他的身體里漫過了某個節點。
云層很低,一些聲音像是峽谷里的風與云層摩擦出來的。要下雨嗎?他看了看鷹,鷹在振翅。他吼了一聲,鷹騰空而起。鷹在他的頭頂盤旋了幾圈后,折身翻過了東山梁去。
他又用特制相機上的望遠鏡對準了石柱和石柱后面的巖壁,拉近了焦距,沒有發現什么,但他還是從車的后備箱里拿了本子,去石柱那兒看看。
扎斯走下路基,過了沙河,爬上了對岸的沙坡。石叢中,他鞠著身子,在每一塊黑巖石上尋找著他所需要的東西。然后,他站在了石柱前,挓挲起雙臂,做了個飛翔的姿勢。他走到石柱側,向石柱后的夾縫里看了一陣。他放下相機和本子,從很窄的夾縫里穿過去,到了石柱的后面。他看到了奇跡。石柱后背上是一幅很大的巖畫。畫面左上方有兩個呈仰臥顛倒狀交媾的人形,右側是四只似乎受驚嚇而奔跑的北山羊;右上方,有幾個圓圈連綴在一起的紡錘體圖案,仿佛一個變形了的葵花頭;但他細細一琢磨,發現那個圖案更像一個女人的陰部。他明白了,這是古人渴望繁衍生息的圖騰。扎斯興奮不已,這和他在龍首山中找到的巖畫都不同,那些不是北山羊,就是駝隊,更多的是射獵圖。而這幅獨具匠心且很有意味。
扎斯從夾縫里鉆了出去,取了相機和本子。他把本子從夾縫里扔了進去,右手提著相機,側身又從夾縫里鉆了進去。石柱后面的空間稍大些,但也艱難,他幾乎扭曲著身子,睡倒了,才拍了幾張巖畫的照片。他又在本子上把那幅巖畫臨摹了下來,在圖下寫道:龍首山巖畫33號。他思謀了一陣,給畫起名為:交媾圖。他又依依不舍地端詳了一會兒巖畫,并用右手食指沿畫跡游走了一遍。他抬頭,從窄縫里看了眼云層厚重得幾乎要墜下來的天空,那只鷹又掠過了頭頂。他把本子扔出了夾縫,才像先前一樣的姿勢,提著相機,從夾縫里鉆出。
他回到了車里,放好相機。音樂已響到了別處,是一首他也很喜歡的搖滾《招招手》,正唱到:你不嫌我丑,見面招招手,山高呀路遠就一樣地走;我不嫌你黑,黑的像個鬼,舉起杯呀還就嘴對嘴,喝它個前腿碰后腿。他長得黑,長年累月跋山越嶺,餐風宿露曬黑的。DD喜歡他的黑,總是在他面前唱這首歌里的這幾句。DD,他想。他從副駕駛座上,拿起了一本影集。他翻開影集,DD依然向他笑著。“我不嫌你黑,”DD在他的耳邊唱著,貼近他的耳朵說了句什么,只有他們能明白的一句話,讓他身子抽搐了一下,心猛地刺疼。不對,是他的左小腿的腿肚上被什么扎了一下的錐疼。他下意識地抬起了左腿,同時帶起了一些什么,很笨重。他佝下頭,伸下右手去。他看到一條蛇吸附在他的腿上。他一把捏住了蛇的七寸,一甩手,把蛇扔出了車外。
他感到身體上突然開了一道風門,冷風直往里面灌。毒性在侵襲,不能怠慢。他卷起褲腿,小腿已紅腫起來,傷處開始變的黑紫。他咬緊牙關,用雙手擠壓傷處,但沒有擠出什么來。他知道,得用嘴吸,可自己又夠不著。他挪下車,從后備箱里找出了一截搭帳篷用的繩子。他脫了褲子,用繩子狠勁地在大腿根扎了一道箍兒。
他看到后備箱里折疊好的篷布,搭帳篷休息?他想了想,但他立馬搖搖頭。不行,得盡快把蛇毒吸出來,或者其他治療,不然會毀了他的腿子,他想到了截肢,或者更嚴重的后果,那他就再也不能到山里探秘巖畫了。要是DD在,DD,DD,DD隨同他進過幾次山,后來退縮了。
扎斯關好后備箱,進到了車里。他拿出手機,撥號呼救,但是沒有信號。自救的辦法只能是前行,山里有牧民,說不定不遠的某處就有一頂牧人的帳篷。他的左腿已經疼得踩不動離合器,他把全身的重量都放在了左腿上,才踩下了離合。他打著車,慢慢起了步。
播放器里的音樂又返回到了《鴻雁》,他沒有關,也沒有調小音量。他開著車,DD就坐在副駕駛座上,一路給他唱著《鴻雁》。DD唱完《鴻雁》唱《招招手》……
路很窄,扎斯得忍疼小心駕駛。天黑下來了,加上疼痛的分心,路有些漫漶,他開了車燈。
一股冷風,從車窗刮進了幾滴雨星。他停了車,把手伸出窗外,天的確下雨了。一道閃電劃過,像是誰揮著鞭子,急急趕著雨來了。緊接著,一聲滾石般的雷鳴,雨像開了閘門般地,潑開了。扎斯狠狠地按了幾下喇叭,停了停,他又用雙手壓得緊緊地按了一聲長號。
他停了下來,側耳聆聽著,閉了會眼睛。
他掛上了檔,繼續前行。
只走了一截,他又停了下來。車在打滑。在這條只能通過一輛車那么寬的路上,稍不留意,就會翻下溝去,何況打滑,何況他的身子在一陣陣地發冷打顫。
他拉起手剎,熄了車,開了車內燈。
扎斯拿出了手機。他翻了幾下,按出的是DD的號,無法接通,是他的手機依然沒有信號。而那邊呢?DD,他想。
這次進山,DD說有事沒有送他。他進山的第三天,DD給他打電話,說她換手機了,還換了別的,然后就掛斷了。他反打過去,那邊的手機已關機。
“換了別的。別的什么?”扎斯囁嚅了一句,抽了抽臉上的肌肉,把手機裝進了上衣口袋里。他拿起影集,看了看DD的笑臉,“鴻雁,北歸還,帶上我的思念……天空有多遙遠。”他的心被什么咬嚙了一下,滑身哆嗦了起來。左腿的疼又一次向全身蔓延。
又一聲雷鳴。一道閃電延伸到了車前頭的石崖上,接通了他和天空的距離。
天空并不遙遠。
他不能這樣等下去,這樣等,就等于等死。
扎斯點著左腳,掂量著下了車。他試著向前挪了挪,盡管疼,但能走。他吃力地走了幾步,又返回了車上。他開了車前燈,可以用來照明。他看了看本子上的巖畫圖,又拿起影集,摸了摸DD的臉,再次下了車。
路很滑,扎斯只能扶著路內側的巖壁才能前行。他每抬一次左腳都很吃力,滿臉都是雨水混雜著汗水,幾乎把眼睛都迷住了。他停了下來,一只手搬著一塊凸出的石頭,用另一只手抹了一把臉。眼里澀澀的,他擠了幾下眼皮,才能睜開眼睛。
先一段,路面上有石子,還可將就行走。接下來,是一段光溜溜的土路,一挪腳,就向外滑。車燈已很遠了,顯得模模糊糊。他蹲下身子,脫了鞋。他站起身,扶著巖壁,用腳尖摳著地面,一寸一寸往前移。
但他還是跌倒了,緊接著,滑下了路面。他攥住了路邊上的一墩馬蓮,墜在了石壁上。他雙手攥緊馬蓮,鎮定了一下自己。他長年累月在野外跋山涉水,身體里蓄有力氣。他鼓住氣,一努勁,做了個引體向上。他趴在了路邊上。但是再往上爬時,路面上沒有可抓的東西,吃不上勁,他上不去。他一只手死死握緊馬蓮,用另一只手在路面上摸著。他摸到了露出地面的一個石尖。他用指頭在石尖四周摳著。他已挖出了一個能扳住石尖的小坑,但還不能握得太緊。
他想到隨身帶的腰刀,拔了出來。他用刀子幾下就在石尖四周剁了一圈深坑。他把刀子狠狠地扎進地面。他左手握著刀柄,吃住勁,讓右手從馬蓮上騰了出來,扳住了石尖。他雙臂一用力,猛一縱身,上到了路面。
扎斯索性沒有站起,而是直接爬著前行,反而快點。只是左腿已經麻木,吃不上力,像是身后拖著個重物,在匍匐。
雨小了。不知走了多遠,早沒了車燈的照耀。滿山谷都是他的喘息聲。
扎斯扶著石壁,坐了起來。
休息并沒有給他帶來好處。疲憊使他的身子一下松弛了下來,一會兒,連睜開眼睛的力氣都沒了。
他咬了咬嘴唇,又狠狠地咬了幾下牙,像是嚼了嚼了黑夜的硬度。
他趴下身子,不是先前的屈俯前行,他已沒了那么多能力,而是平展展地趴在地面上,一下一下地蠕動。
他沒有意識到前面是個急彎。他摸到了幾株灌木和一些草,以為出了峽谷,到了草地上。他抓住灌木,猛一挺身子,猝不及防,一頭栽下了路去。
DD在喊他,推了他一把。一聲驚雷。緊接著的瓢潑大雨,像一個人在他的臉上潑了一盆水,使他一個激靈。他驚慌失措,不知身在何處。他揉了揉眼睛,動著麻木了的腿。左腿動不了,他才回過神來,他明白了自己的處境。
扎斯額頭很疼。他摸了摸疼處,有一道傷口。他想找什么貼上。但是口袋里只有一疊衛生紙,已被水浸成了泥團。他往手心里吐了一口唾液,據說能消炎,抹在了上面。
他挪了挪身子,想繼續前行。但衣服上滿是泥水,像是背著多重的東西,根本就動不了身。他把衣服全脫光了,只留下背心和褲頭。
好在,他坐著的地方真的是一片草地,而不是沙河,那樣的話,他光著身子怎么爬行。他趴了下來,向前挪了一截。他借著微弱的光氣,看到了模模糊糊的山形。前面很開闊,他出峽谷了。
雖然是草地,但是是上坡,一爬一滑,也很費勁。
雨小了,只有零零星星的雨滴偶爾落在臉上。他停了下來,聽著山谷的寂靜,他聽到了一些更顯寂靜的聲音。他屏住了呼吸,聽得更真切了,是狗叫聲,忽高忽低。
他急急爬行,越往前爬,狗叫聲越清晰。有節奏的吠聲,鼓點一樣,像是給他鼓勁、督行。
扎斯的肚皮上肯定被什么劃傷了,鉆心的疼,但他一努勁,就把這些小疼給忽略了。他終于爬上了坡頂。他看到了遠處的一星光亮。
狗叫的更厲害了,可以說是兇猛,還有牛的噴鼻聲。他只在坡頂上稍喘了口氣,就向下滑開了。在半坡里,他墜著一墩灌木坐了起來。他看到一柱手電光向他照了過來,還聽到了一聲吆喝。他趕緊呼應了一聲,但因為自身的疲乏和饑餓,聲音很微弱,那邊未必能聽到。
他開始用屁股滑行。隨著手電光的晃動,他看到一個身影向他移了過來。他看到了坡下面有一群牛,牛的眼睛像小火苗一樣,撲騰著。
扎斯滑到坡底時,那個身影也離他不遠了。
“誰?”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干啥的?”
“我。”扎斯拼出了所有的力氣。“救命。”扎斯猛地站了起來。但他忽地又跌倒了。他的左腿麻木,一點知覺都沒有,失去了支撐力。由于暴發的太猛,近乎揮霍,一下掏空了身體里所有的能量。
那人掐疼了他的人中,他的生命氣息又回來了。他長長地呼了一口氣。
“咋了?”那女的手電光照在他身上,又挪開了,“咋成這樣了?”
他張張眼皮,又疲憊地閉上了。
“遇到啥了?”那女人說,聲音遲疑。但她馬上往起里扶他。
“蛇。”他說,“被蛇咬了。”
扎斯順著女人的攙扶站了起來。
女的從腋窩里挾住他,拉過他的左手搭在了她的肩上,用右手裹著他向帳篷走去。
那女的把他放在了地鋪上,他看到他的左腿腫得像水里浸泡過的椽子。一個女孩從被窩里探過頭來。“誰?阿媽?”女孩怯生生地問。
“別管,好好睡覺。”女人說。女孩向后縮了縮,但眼睛一直向他瞅著。女人抬起他的左腿,找見了傷口。
傷口在腿肚子上,在下面。女人扳著身子,讓他趴在了地鋪上。女人拿了一只鞋,用袖口擦了擦鞋底,在傷處猛拍了幾下,他疼得直出聲。
“男人!”女人語氣很重地說。他感覺到了她的輕蔑。他咬住了枕頭的一角,堵住了嘴。女人在用嘴吸他的傷處,他像是又被蛇咬了一下似的,抽了抽身子。
女人“噗”地吐了一口:“別動。”
“別!”他說。他想翻起身來。
女人在他的屁股上拍了一把:“別動。”
女人又連續在他的傷處吸了幾次。
“時間太長了。”女人嘆息著說。“得找醫生。”女人說。“你一定很餓了吧。”女人把他扶著坐了起來,背后墊了一床被子。
他看清了女人的臉,雖然皮膚黑,但眉清目秀,像吉克雋逸。
女人捅了捅火爐,在上面搭了把茶壺。接著,女人又折身從墻角的木桌上拿過一只碗。女人提起茶壺,向碗里倒了些什么。
“餓壞了吧。”女人說,把碗遞給了他。“先喝些涼的,壓壓饑。”
是奶茶。他幾乎沒換氣,就喝完了多半碗奶茶,肚子里像空山回音,很重地響了一聲。女孩“撲哧”笑出了聲。
“我叫烏云。”女人說。女孩叫哈斯,烏云說。
烏云等著奶壺滾了后,給他做了幾個糌粑,又倒了一碗熱奶茶放在了他的旁邊。在這當兒,他給烏云講了他的工作,和他遇險的經過。烏云一直皺著眉頭聽著。有一陣子,扎斯看到烏云的眼里在神往什么,更像是迷惘。
“怎么?”扎斯說。他不知道他這句話的來由,他不明白要說什么。他望望烏云,又看了看眼神專注的哈斯。
“沒什么。”烏云說。她隨手套上了一件衣服。“你把這些都吃了。”她說,“我得去找醫生。”
“這么遲了?”扎斯說,“再說,我覺得好多了。”
“不行,”烏云搖搖頭,“毒還沒有完全排掉。”出門時,烏云又回過頭來說:“難受了難受,腿上的繩箍先不要解開。”
“阿媽?”哈斯坐了起來。
“待著。”烏云說。
一會兒,聽著一陣馬蹄聲急速地馳過了帳篷門口。狗叫聲像河水一樣,一直在不停地潺潺流淌。
“那是你媽媽?”扎斯問哈斯。
哈斯點點頭。
“爸爸呢?”
哈斯搖搖頭。
扎斯吃完后,疲憊,使他不一會就迷糊了過去。
醫生在扎斯的傷處,用一個吸附器,狠吸了幾次。醫生又給他打了一針,解開了繩箍。扎斯覺得輕松了許多。
醫生放下了一些針劑和一個針管。“一天打上兩針,把這些針都打完,應該就好了。”醫生說。“這段時間不要走動太多。”醫生給扎斯說,望著烏云,更像是給烏云安頓。
醫生在扎斯的頭上包扎了幾圈繃帶。“好了,我該回去了。”
醫生出門時,扎斯覺得應該給醫生就診費的。“稍等。”他說。醫生回過頭來。可他一摸身上,幾乎是裸體。“我的東西都在車上。”他說,“我好了后,去給你。”他說。“醫藥費。”他說。“還有,太謝謝你,你們了。”
“別管這些了。”烏云說,眼里是責怪的體慰,“好好養傷吧。”
“聽烏云的,”醫生說,“好好養傷。朋友,真是萬幸……”醫生停了下,望著烏云,把剩下的話咽了回去。
“這,”烏云像是被什么卡了一下,咳了一聲,才又流暢了。“等會,我立馬就做好了,吃過早飯了再回。很快,不耽誤你多少時間。”
“不了,我回去剛好趕上上班。”醫生說,出帳篷門。扎斯看到天光已大亮。
送走醫生,烏云返回帳篷。“我去擠奶,擠完奶,把牛放到山坡上,就回來做飯。”烏云說,提了奶桶,走了出去。哈斯已穿好了衣服,隨阿媽走了。
扎斯也想掙扎著起來,可坐起身,才明白自己是裸體,怎么示人,又躺了下來,偎進了被子里。
扎斯閉上了眼睛,DD給他喂飯。他感冒了,DD一口一口地給他喂著,直到他睡著。
扎斯太累了。烏云把飯做好,才叫醒了他。
“手抓羊肉,羊湯。多吃上些,養身子。”烏云說。
看著扎斯吃開了,烏云急急地吃了些,就站起了身。
“鑰匙?”烏云說,把手伸向扎斯。
“什么?”扎斯說。
“車鑰匙。”
扎斯恍惚了一下說:“就在車上。”
烏云一笑。“我也是糊涂了,你光著身子來,那來鑰匙。”烏云揶揄了一句。“即使不在車上也早丟路上了。”烏云揉了下鼻子說,“你吃過了,睡著,緩著。我給你往回弄車去。”
“你?”扎斯說。
“是啊。”烏云說。
扎斯還是不放心。“那條路,又窄又滑,不好開。”他懷疑地問,“你會開車?”
“原來有過一輛,后來賣了。”烏云說,眼神里有一些很抽象的東西一閃而過,像是大草坡上,一只老鷹的掠影,倏忽就不見了。“那條路我能不知道,常來常往的。”烏云說,“再說了,天早晴了。天一晴就把路面晾干了。”
扎斯想說,給我找件衣服吧,我和你一起去。一想,一個女人家,看得出來家里沒有男人,哪里給他找男人衣服去。但他還是試探著說了。“有男人衣服嗎?給我找件穿上。我和你一起去。”
“有。”烏云說,轉過身,從一個木箱子里翻出了一套衣服,猶豫一下,很規整地遞給了扎斯。“穿上吧。”烏云聲音很輕地說,帶有曖昧,似乎還有別的情緒。“但你不能去,去了傷著,反而累贅。”
烏云取下掛在墻上的馬鞭。“哈斯,你好好陪著叔叔待著。我去去就來。”烏云搭起門簾,一股強光猛地涌進了帳篷。
吃過后,扎斯穿上了那套衣服,幾乎是嶄新的,也挺合身。扎斯站起身,試了幾下,但不能走,左腿使不上勁。他向帳篷里各處瞅了瞅,沒個可拄的東西。“哈斯,來讓叔叔扶著你。”他示意哈斯走到了他的左邊。
他把手搭在了小哈斯的肩上,趁了點力,向前走了幾步,又扶著帳篷邊,出了帳篷。天晴得萬里無云。草地上,濕氣蒸騰,整個河溝像是一個大蒸鍋。空氣中彌漫著牛糞的味道。扎斯放開帳篷邊,想繼續前走,但沒走兩步,就趔趔趄趄的,幾乎跌倒。他前傾身子,扶住了扯帳篷的桿子,才把自己穩住。
哈斯很懂事地,從帳篷里搬出了兩個小凳子,讓扎斯坐下。她并排坐在了旁邊。
“哈斯,你爸爸呢?”扎斯又想到了那個疑問。
哈斯還是搖搖頭。
“你幾歲了?”
“六歲。”
牛場邊的狗突然很狂地叫起來。
“媽媽。”哈斯興奮地喊了一聲。
扎斯朝著哈斯出聲的方向一看,一匹馬從草坡上飛奔了下來。
“媽媽。”哈斯站了起來。扎斯也站了起來。
烏云在帳篷前吁住了馬,跳下馬,從馬上抱下一堆濕衣服。
“你的。”她說,把衣服堆在了扎斯面前。“趕緊掏掏口袋里,有什么東西都掏凈了,我給你洗去。”她又從懷里拿出個什么遞向扎斯。“這個,是你的吧?”
扎斯接過去。是他的手表。表鏈斷了,啥時候丟的,他都不知道。是DD給他買的。扎斯望向烏云,想說句什么感激的話。但烏云望向了別處。狗不叫了,一塊潔白的云掛在對面的山尖上,一飄一飄的。
烏云從帳篷里拿出了一個臉盆,把扎斯的衣服盛在里面,去了牛場那邊的河邊。
“車呢?”扎斯想。但他沒問。他覺得這是一種不信任。
烏云端著一臉盆洗好的衣服回到帳篷前,把衣服掛在了晾衣繩上。
“我得去趟旗上。”烏云說,“車沒電了。”
扎斯醒悟過來,車燈著了一晚上,能有電嗎?咋能開回來?他咋早沒想到。
扎斯拿起掏在地上的手機,掄著胳膊甩了幾下,飛出了好多水珠,直到手機沒水了才停下來。他試著開機,按了幾次開機鍵,都沒有動靜。是燒壞了?還是沒電了?
應該充上電試試。扎斯在手機上比劃著,問旁邊的哈斯,可以充電嗎?哈斯明白:“行呢,能行。阿媽的手機也經常充電。”她知道充電的地方。“帳篷里有插座。”哈斯很情愿地要接過手機。可是,還需要東西呀。扎斯想到了,充電器在車上,他做了個無奈的動作。
“沒有充電器。”扎斯說。收回了手機。
哈斯第一次在陌生人面前笑了,伸了伸舌頭。一只鳥落在了面前,她用手去抓,小鳥飛了起來。她一停下,小鳥又落下來,面對她“唧唧”地叫著,像是向她示威。她又追了過去,一直追到了老遠。
“不要跑遠了。”扎斯喊。
哈斯應了一聲,蹲下了身子。
這時,他聽到一只小鳥在他身后的什么地方“唧唧戛,唧唧戛”,很歡實地叫著。是剛才哈斯追了的那只嗎?他磨轉身子四處尋找。帳篷南面的太陽能極板上,有一只彩色的鳥兒。旁邊是一個電視接收器。是它,是它高昂著頭在那兒抑揚頓挫呢。就像DD在給他有模有樣地唱著《鴻雁》。他注目著,鳥兒沒有飛走的意思。他想叫過哈斯來看。可是先前蹲了的地方沒有哈斯。四處也沒有。他急了,硬掙著站起來。
“哈斯,哈斯。”他喊。
哈斯沒應聲,狗卻叫了起來。
他站不久,左腿吃不上力,人在搖晃。他拿起凳子,前挪了幾步,又坐了下來。
“哈斯,哈斯。”
哈斯卻從哪兒轉回來,站在了他身后。她用手蒙上了他的眼睛,“咯咯咯”地笑呢。笑完了,很快地竄到他前面。“看。”她說,“好看嗎?”扎斯看到哈斯的頭上插著兩朵馬蓮花,努著嘴,做著怪像。他也笑了,說:“好看,漂亮。”看來哈斯在他這個陌生人面前終于放開了,不再拘謹。他又想起了那個問題。
“哈斯,給我說說你爸爸。你爸爸呢?去哪了?”
哈斯還是搖搖頭。臉上換成了疑惑的表情,好像那個詞與她沒任何相干,或者說她就不懂那個詞是什么意思。
“你沒見過爸爸嗎?哈斯。”
哈斯還是搖頭。
“你媽媽也沒說過爸爸?”扎斯說。
“沒有。”哈斯說,搖著頭,似乎更疑惑了。
“像我,”扎斯說,“像我一樣的男人。爸爸。”
哈斯頭一彎,思考著。然后她擰緊了眉頭,又放松下來,像是一下子豁然開朗了。哈斯突然捏住扎斯的鼻子。“那你就是爸爸。”她說,取下頭上的馬蓮花,插在了扎斯的頭上。
興許是活動得久了,扎斯覺得左腿脹疼,陽光也更強了,曬得他直淌虛汗。他有些支撐不住了。他一只手按住凳子,趁上勁,站了起來。他示意哈斯,讓他扶著她去帳篷。但哈斯拽著他的手和衣角,又把他拉住坐了下來。“等等。”哈斯說,向帳篷后面跑去。一會兒,哈斯拿來一根木棍,遞給了扎斯。扎斯明白了哈斯的意思,小丫頭挺機靈的,得刮目相看。他接過木棍,撫了撫哈斯的頭,把自己早已取下來,握在手中的馬蓮花插在了哈斯頭上。
有拐杖方便多了。哈斯走在前面,倒行著,笑盈盈地看看扎斯一拐一拐地進了帳篷。
扎斯上了地鋪,拿出了手機搗鼓著。沒啥結果,他長嘆了一聲,放下手機。
哈斯好像很理解扎斯的那一聲嘆息,忙打開了電視,并把遙控器遞給了扎斯。
扎斯接過后,哈斯笑了一下,向帳篷外跑了。
扎斯拿著遙控器翻了一遍,臺很少,沒有他想看的考古頻道。內蒙古頻道倒是有,但這個時段沒有他想看的,是個娛樂節目。又向下翻了幾個頻道,他停住了。畫面上是一片荒原,這引起了他的興趣;接著,畫面轉到了一座山峰上,頂上是一塊巨大的巖石,很圓;然后鏡頭拉向了一輛自行車,確切地說,是一輛非常漂亮的山地車;畫面急轉直下,落到了一個山體的裂縫里;鏡頭突然停在了一個點上:是一個人和一塊石頭,在裂縫的半截處。他明白了,這個他看過,是美國電影《172小時》。此刻,拉斯頓正在用一塊石頭,往斷里砸他的手臂。他的手臂被一塊石頭夾在了山縫里,他想了許多辦法,他堅持了很久了,絕望中,他必須以這種方式才能逃離災難。“哐哐哐”的砸擊聲,像砸在扎斯的身上。
如果沒有碰到烏云,他想,時間久了,他的左腿就會壞死,就會蔓延到整個身體。他咬緊了牙。他想,如果真是那樣,他有沒有決心弄斷自己的左腿……
一陣車的轟鳴,越來越響,到了帳篷前,戛然停了。幾個人下了車,嚷嚷著向帳篷門走來。扎斯往起里坐了坐身子,注視著門口。
先進來的是哈斯,跟著是兩個男人,烏云在后面謙讓著。
是他們幫了他的忙,扎斯知道,是他們把他的車弄回來的。兩個男人進門后和他打招呼,他趕緊點頭致謝。哈斯看著電視上那個致殘自己的人,抖了一下身子,像是受了驚嚇,急忙跑到了媽媽身邊;烏云用手一撥她,她抽身到了扎斯旁,貼在了他的身上。
烏云在忙著往地中央擺桌子,然后端過了一盤早晨做下的手抓羊肉。烏云又在爐子上搭上了奶茶壺。那兩個男人圍著桌子坐定后,烏云又盛了一盤羊肉,放在了扎斯旁。
“吃吧,都不要客氣了。”烏云說,“大中午的,都餓了。”
其中一個男人拿起一塊羊肉,對著扎斯舉了舉,說:“吃。一起。”
烏云在桌子上擺好酒杯,用一只錫壺往酒杯里倒酒。倒完后,烏云站起身,走到扎斯旁,也給他遞了一杯酒。
“給你介紹一下,扎斯。他倆是旗上汽車維修部的師傅。是他倆開車拉上電瓶,到你車那兒,才把你的車打著,開到這來的。”烏云說。
扎斯忙說:“太謝謝了!”
男人說:“不要客氣。萬幸,萬幸。誰都會有難處。你脫險才是最應該敬的。來,互敬互敬。”一起舉杯喝了。
烏云給那兩個男人添上了酒,又過來給扎斯倒。扎斯把酒杯往懷里一收,說,“我有傷,不能多喝吧。”
那個男人“哈哈”一笑。“酒能消毒,多喝有好處,喝吧,兄弟。”
烏云也笑臉認同。
“喝吧,兄弟,喝上幾杯了,我們馬上要回旗上去。”那兩個男人說。
扎斯把酒杯伸向了烏云。
“邊吃邊喝。”烏云說。她也端起了酒杯。“敬你們。”
哈斯已經不吃了,洗了手在聽他們說話。他們不說話的時候,她拿起了扎斯的手機翻來復去地看。她像是突然想起了先前的事情,想起了給手機充電的事。
她說:“媽媽,給手機充電。”她指了指扎斯說:“爸爸的。”
烏云先是一愣:“什么爸爸。”接著,她就反應過來了,臉一紅:“胡說呢。哪有爸爸。那是叔叔。”
“爸爸。”哈斯執意地說。
那兩個人也明白過來,“哈哈哈”地笑個不停。
扎斯拽拽哈斯說:“哈斯,我說的爸爸是……是問你的爸爸呢,可是……”他覺得一時也解釋不清,就不再說了。他轉向烏云說:“我的手機充電器在車里的包里。”
烏云起身去拿。
“給,車鑰匙。一個男人說。又說,“怎么忘了,把車給熄了。你順便把車打著,讓多著會兒,把電充起來。電跑光了,不充的話,過陣子又打不著了,還得我們再來。”
烏云把那兩個修理工送走后,又給扎斯打了一針。扎斯讓她從插座上拿過他的手機。扎斯按著開機鍵,手機仍舊沒有反應。扎斯很沮喪地把手機扔到了一邊。“看來,是徹底壞了,”他說,呆呆地坐在了那兒,看烏云收拾屋子。他突然抹了一把臉,又有了表情。
“你的。”他說,“烏云,你的。”
“什么?”
“你的手機。”扎斯說。
烏云停下了手中的活,從長袍的懷里掏出了手機,在手上掂了掂。扎斯看到烏云的手機是那種簡單功能的超長待機款。“怎么?”烏云說,把手機扔在了扎斯偎著的被子上。
“用你的手機打個電話。能打出去嗎?”扎斯說,拿起了手機,琢磨著。“我是說這兒有信號嗎?”他說。
“可以的。”烏云說,“但得上到后面的山頂上。”她佝著身子,把桌子上的骨頭往一個盤子里撿。“這里沒信號,得上那兒才行。”烏云說,端著盛滿骨頭的盤子出了帳篷門。
“非得打嗎?”烏云拿著空盤回到帳篷后,望著扎斯說。
“得打。”說這話時,扎斯沒有什么深刻的語調,只是淡淡的,他怕帶上過于強制的意味。但他心里是急的。
“那行。”烏云抹完了桌子,“那現在就去。”
盡管烏云沒再問更多的話,好像一切都是應該的。但扎斯不那么想,他覺得這是一種為難。
“要不就算了。”他說,“腿子這樣,怎么上山?”
“有事就不要推托。”烏云說。“有我呢。”烏云又說。
扎斯猶疑了一下。“也沒什么要緊事。”停了下來,他又說,“就是,昨天一直在山谷里,沒信號,沒有打通過電話。得給單位說行蹤,這是每次出來時,單位的要求。另外,家里只有阿爸一個人,我每天都得給他報個平安,不然他會擔心的。”扎斯長出了一口氣。
“這還不要緊?”說完,烏云連忙脫了長袍,套了一件運動衫。“走吧。”她說,過去扶扎斯。
扎斯做了個要強的動作,說:“我能行。”但烏云已從胳膊上牽起了他。她牽著扎斯一直出了門。哈斯在后面喊了一聲:“爸爸。”兩人回過頭去,看到哈斯手里拿著那根木棍。兩個人都笑了。哈斯也笑。烏云說,“這丫丫能了。”接過了木棍。很明顯,她在“爸爸”那個詞上有過異樣的表情,想說什么,但她立馬就放過了。倒是扎斯有些臉紅,像先前在帳篷里時那樣,不知道怎么解釋,也放棄了。他拿住烏云手里的木棍。“這個挺好的。”他說,拄著木棍前走了兩步,“我能行。”他說。說這話時,他的心勁在上升。
沒走幾步,他就覺得費勁了。走在旁邊的烏云看出來了,上前,扔了扎斯手中的木棍,把肩膀頂在了他的腋窩里,幾乎是掮著她,向前走去。哈斯在另一邊,手里拿著撿起的木棍。
走到半山腰里,單靠右腳著地的扎斯,腿太酸了,臉上已是大汗淋淋。他都這樣了,支撐他半個身子的烏云肯定也夠嗆。
“緩緩吧。”他說。
“這兒。”哈斯跑向前面,指著一塊石頭說。
烏云攙著扎斯坐在了石頭上。望望山腳,又看了看山頂,似乎在測著剩下的距離。哈斯蹲在地上喘了幾口氣,起身去捉一只“吱吱”響的螞蚱。
“扎斯。”烏云說了一句,但又不知道說什么,停了下來。
扎斯等著,望著烏云。他低下了頭,又抬起頭來。“烏云,你怎么知道我叫扎斯。我記得我一直沒給你說過我的名字。”他說。
烏云身子顫了一下。是顫了一下,扎斯看到了那個變化。烏云捋了一下頭發,沒說什么,帶著一種神往的表情看向了遠處。
一只旱獺停在了他們前面,抬起前腿,“呱呱呱”地叫了幾聲竄上了山頂。
“走吧。”烏云說,轉過身,拽住扎斯的雙臂,把他背了起來。
“這咋行?”扎斯掙扎著說。
“行呢——”烏云說,往上掂了掂扎斯。“這樣快些。”她說。她換了手,抓緊了扎斯的雙腿。扎斯不能亂動了,不然讓烏云更吃力,他雙手抱在了烏云的脖子上,很輕地。但一會兒,他不得不用上點力氣。
中途,扎斯要烏云把他放下來,他自己再走會兒。烏云沒停,她一口氣把他背上了山頂。
三個人并排坐在了山頂。哈斯把那根棍子遞到了扎斯手里。
“這代價也太大了,打一個電話。”扎斯沉悶了一陣說,“不打了。”他有些氣惱。
烏云像是沒有聽明白,直愣愣地望著扎斯。
“這算什么?”她說。她也氣惱了。她把手機塞到了扎斯的手里。“打。”她狠勁地說。
扎斯看了眼烏云。她的臉上有一種不可違拗的東西。扎斯按上了一個電話號碼,但不通,什么反應都沒有。他搖了搖頭。“不通。”他說。他先按上的是阿爸的號碼。
烏云說:“不急,這個地方信號也不太強,時有時無。你多打幾下興許就通了。會有那么一次的。”她站了起來,看著扎斯按上了重撥。
但還是沒有反應。扎斯連按了幾次都一樣,沒一絲動靜。“不行。”他說。
“我試試。”烏云躬下身,接過了手機。“得走著試,不定哪個點上就通了。”她說。她重撥上號碼,來回在山頂上走著。哈斯也站了起來,跟在媽媽后面來來回回地走。烏云反復撥著那個號。一直向北,走到山沿上時,手機通了。但她能聽到那邊說話,那邊卻聽不到她說話,她使勁說著,那邊卻總是說你說話呀。她趕緊掛斷,又重新打過去,又不通了。其間,那邊往回撥過來,通了一次,烏云慌忙接上。那邊“喂”了一聲,她也“喂”了一聲。“你是DD呀。”那邊說。她說什么,猶疑了一下,她剛說,“我是……”她喊道,“扎斯,通了。”手機“吱吱”地響起了怪聲,然后就斷了。再按,就一直不通了。扎斯已拄著棍子站在了她旁邊。
烏云看著他,無奈地聳聳肩,發愁地皺了下鼻子。“這個地方有時信號好,有時干脆就沒有,這個,說不來。”她說,把手機給了扎斯,讓他再打。她看著扎斯打過了幾次依然不通。她停了停,像是在思索。她說,“那個山尖上倒是信號非常好,我打過幾次都通,清晰的很。可是,”她指了指北面的一個山頂,“遠著呢,走上去,得一個多小時。”她停下來,像是在決斷,她接上說,“要不我開上車,拉你到旗上打去。”
“那怎么行。”扎斯連忙說,否定地擺了擺手。“就這夠折騰你了。”他說,“我明天一早就出山。”
“那可不行,你得把傷養好了的。”她說,“醫生說那些針打完你才能好。我得聽醫生的。醫生說,你腿沒好,絕對不能讓你走長路,即使坐車也不行。剛才我說的去旗上,都是不可能的。那也是我急了隨口一說。”聽那架式,要繼續說下去,但她突然停了。她接上又興奮地說了一句。“還有個辦法。”她說。
“什么辦法?”扎斯說。
“發短信。”她說。
“連電話都打不通,短信能發出去嗎?”扎斯不相信地笑了笑。
“你等等。”烏云說;又對哈斯說,“哈斯,你和——”她笑了笑說,“你們在這等會,我一會就來。我用過。”
她說著向山下跑去。
哈斯喊了一聲:“媽媽。”但沒有回音,又轉向扎斯說:“爸爸。”
扎斯無可奈何地笑笑,說,“你的爸爸。”
哈斯像學生跟著老師念生字似的說:“你的爸爸。”
這是一種無法辯駁的執拗。扎斯撫了撫哈斯的頭,兩個人同時笑開了。
一會兒,烏云肩上扛著件皮襖上來了。她沒有停下休息,還在大口地喘氣,就選了個地方,把皮襖拉展鋪開。她“呼哧呼哧”地說,“你寫短信,把短信寫好,我們就開始發。”她一屁股坐在了皮襖上。
“寫好了。”扎斯捏著手機說。“發送了。”
手機“嘟嚕”了一聲,顯示“發送失敗。”
“不對,”烏云說,“你寫好了給我。”烏云站了起來。“你得給我。”她說。“你那樣可不行。”她笑得不行。
扎斯把手機遞給了烏云。烏云接過手機,止住了笑,按了重復發送,猛地把手機向空中扔去。三個人眼巴巴瞅著手機在空中回旋了一下,落在了皮襖上。烏云拿起來,一看,還是發送失敗。她重復發送了一次,又向空中拋去,這次拋得更高。手機再次落地皮襖上時,烏云已迫不及待了。她拿起一看,一下跳了老高。“成功了。”她說。她興奮地說:“發送成功了。”
“真的?”扎斯說。
哈斯也跟上說,“真的?”
烏云把手機給了扎斯。“你看。”她說。“還有給誰發的,你寫上。”
“你太神了。”扎斯說,“怎么想出這么個辦法?”他說,又寫好了下一個。
烏云照舊扔了幾次,把另一個短信也發成功了。
扎斯看著手機。
他拿著手機鼓搗了好一會兒,才遲疑地說:“還有一個,不知道發不發。”
“發呀,怎么不發?”烏云說,“有需要發的就發,不要讓人家為你著急。”
其實他早寫好了短信,只是在那兒糾結著。他把手機給了烏云。烏云只擲了一次,就發送成功了。
烏云坐在了皮襖上。扎斯和哈斯也跟著坐了下來。
“等著收回信。”烏云說。
“不收了。”扎斯說。
“他們回嗎?”烏云問。
“收到的話,肯定會回。”扎斯說。
“那就收呀,怎么不收?”烏云說,“收到了你心里也踏實。”她說,“稍等會。”
烏云站起身,向空中拋了幾次手機。她把手機給了扎斯。
“都收到了。”她說。“手機響了三次短信音,收到了三個短信。你發出的三個短信都回信了。”她說,“你看。”
扎斯前兩個是發給阿爸和一個同事的,后一個是發給DD的。他打開收到的回信一看,一個是阿爸的,一個是同事的,另一個是天氣預報。
“下山吧。”烏云說,揮了一下,“得攬牛去了。”
扎斯向烏云笑了笑,也許是自己苦笑了一下。“下山。”他說。他看到夕陽像一塊燒紅的鐵,鉆進了云里。
四天過去了,扎斯已經能不拄“拐杖”行走了。其間的幾天里,他們每天下午上到山頂上發一次短信。
第五天早晨,烏云擠過牛奶,把牛群吆到山坳。回帳篷做上飯吃過,烏云忙出忙進忙完后,給哈斯換上了嶄新的衣服,也讓扎斯換上了自己的那套行裝。這幾天,扎斯一直穿著烏云給他的那套男人的衣服。烏云把那套男人衣服疊得整整齊齊放進了木箱里。她也換上了一件新長袍。
烏云又包好一包酥油和一包牛肉干,裝進了一個袋子里,又把袋子裝進了一個背包里。烏云出了帳篷,把背包放進了車里,打著車,返身進了帳篷。
“走,上旗上去。”她說。
“有事嗎?”扎斯問。扎斯另有打算。他猶疑了一下說:“我還想,今天可以回了。”他甩了甩自己的左腿:“你看,好好的了。”
“不行,這可不行。”烏云被這話給提醒了,光忙了準備去旗上的事,扎斯還有一天的針沒打呢。“得把針打完。”她說。取了針給扎斯打了。
“給你散散心,順便看看他們。”烏云說。
“看誰?”扎斯問,“你的父母親?”他說,“我去不合適吧。”扎斯想到了別處,想到關鍵時候,哈斯叫他“爸爸”。
烏云低了頭,做了個祈禱的動作。“不是,他們在幾年前就相繼去世了。”她說,臉上出現了另一個意思。“去看看鐵彬他們。對了,就是那兩個維修工。你也知道,當時你給他們付錢,他們不要。說是又沒有修什么,只是幫了個忙。”她說。“給他們帶了些東西。”烏云說。
“就那些。”扎斯說。
烏云點了點頭。
烏云牽了一把他:“上車吧。那邊去,我開車。”
“我能開。”扎斯想從烏云手里拿鑰匙。
“不行,今天你還是病號。”烏云說著先上了駕駛位。
哈斯在他們說話時,早上了車,在副駕駛位上坐著。扎斯拉開車門,一看,想到后面坐去。但他看到哈斯向他伸著手,又改變了主意。他上車抱起了哈斯。哈斯往他身上緊緊一貼。“爸爸”哈斯說。車子震顫了一下,起步了。
到了旗上,把車停好后,烏云讓扎斯和哈斯在停車場旁邊的一排椅子上坐著,讓他們稍等,她去去就來。
一會兒,烏云手里拿著一個白盒子從一個拐角處走了過來。
“給我。”烏云說,站在扎斯面前伸出手。
“什么?”扎斯說。
“你的手機呀。”扎斯看到烏云的另一只手里拿著個手機包裝盒。他算是明白了。“怎么能讓你——”但他還是從口袋里掏出了自己的手機。“我還打算抽個空子修修去呢。”他說。
烏云已經拆開了包裝盒,拿出了新手機。烏云接過了扎斯手里的手機,取出卡,安進了新手機里。“算了,不修了,用這個吧。”烏云說,遞給了他。
“這?”扎斯說。
“別說了。”烏云說,“快給家里打電話吧。”她說,“老用我的,他們會把我當成誰了。”烏云說。
還真讓烏云給說著了。正說著,烏云的手機響了。烏云接了起來。“是DD嗎?”烏云知道是扎斯的阿爸,她“哦”了一聲,趕緊掛了。她說,“是你阿爸。”他向扎斯說,“用你的手機打過去。”
扎斯給阿爸回了電話,又給單位打了一個。停了停,他按上了DD的號,但那個號永遠是空號了。扎斯捏了捏手機,裝進了口袋。他像擺脫什么似的向空中甩了一下手。“哈斯。”他說。他把那塊舊手機遞給了哈斯,讓她當玩具玩去。去年他同時買了這樣的兩部手機,一黑一白,白的DD拿著。
扎斯看著烏云走到了車前,取出她的背包,把手機包裝盒裝進了包里,同時掏出了裝酥油和牛肉干的袋子。
一進修理鋪,烏云就喊:“師傅,師傅。”但沒人應。扎斯向四面瞅著也沒人。“咋沒人?”烏云說,大聲喊了一聲,“鐵彬。”聽到什么地方有響動。一會兒,從一輛車底下鉆出個人來。正是鐵彬。“來了呀,烏云,你們。”他拍了拍身上的土,“哈斯。”他說。他轉向站在不遠處的扎斯說,“傷好了嗎?扎斯兄弟。”
“好了,好了。”扎斯說,“非常非常感謝你們。”
“謝什么呀。”他說,抽出了一根煙給扎斯遞。
扎斯擺了擺手。
“這個。”烏云掂了掂手里的袋子,“放哪?”
“什么?”鐵彬說。
“沒什么,你說放哪?”烏云往上提了提袋子。
“別,別放,好像送禮似的,真沒勁。”鐵彬說,瞪了烏云一眼。
“誰給你送禮,想得美。自家做的酥油。”烏云也還了一眼說。“拿著。”烏云直接把袋子杵到了鐵彬的懷里,他不得不接。
“還是不行。”鐵彬抱著袋子,換了一下手,提在了手里。“要是吃上癮咋辦?”鐵彬嘻哈著說,沒了剛才的嚴肅勁兒。
“好啊,自己來取呀。”烏云就勢說。
“只怕有人不愿意。”他把目光扎在了扎斯身上。
“誰?”烏云挑了挑眼瞼。“誰?”她笑著說。
鐵彬又看了看扎斯,肯定是想起了那天在帳篷里的情景。他摸著哈斯的頭,“這是誰呀?”他問哈斯,他指的是扎斯。
“爸爸。”哈斯很快地說。
鐵彬目地性地笑著。
扎斯臉黑紅黑紅地敲了敲了旁邊一輛車的引擎蓋。“這車不錯,越野性能好。”他說,像是沒聽見剛才鐵彬的用意和哈斯說的。
“怎么就你一個人,別的人呢。”烏云趁機轉了話題。
鐵彬不笑了。“出外勤了。”他說。“紅寺湖那段的公路上出了事故,到那修車去了。”鐵彬說,又說,“進辦公室,我給你們泡茶喝。”
“不了,我們到別處轉轉去。”烏云說。
“好吧,轉會兒再過來也行,下午他們來了,請你們一起吃燒烤。”鐵彬說。
“再說吧。”烏云說,“看時間。”
他們先去了一個超市,給哈斯買了些零食。然后,烏云領著他們轉過幾個小巷子,停在了一個叫“紅·其其格”的精品店門前。
原來,那家店的主人就叫紅·其其格。店里沒別人,一進門,烏云沖著正在串一副手鏈的女店主喊了一聲“紅,紅姐”。那個女人抬頭一看,就叫開了:“烏云呀,總算想起姐來了。”說著,兩個人又是牽手又是擁抱的,親熱的不行,把扎斯和孩子都忘在一邊了。
扎斯看到她們興奮的樣子,臉上也溢出了莫名的微笑。他想說什么,動了動嘴唇,但收回了原想的調侃。他不想打擾她們的那股訴說勁兒。他牽著哈斯的手,坐在了柜臺外的一個圓凳上,透過玻璃看那些五光十色的手鏈和掛件,并一一指給哈斯看。
“這個,像個蝴蝶。”哈斯指著一個掛件說。
這時,紅像是才注意到他們。
“哈斯呀。”過來抱起了哈斯,“幾天沒見長這么大了。哈斯真好。”她說,又對烏云說,“怕是一個多月沒見了,上次還是旗慶的時候,你們來的。”
“就是。”烏云說,“一個多月了。”
“自己瞅,瞅上哪個,阿姨送給你。”紅說。“這個嗎?”紅指著那個蝴蝶掛件說。
紅把哈斯放在了扎斯的腿上,取了那個掛件,要給哈斯戴,讓烏云擋住了。“不用,不用,不能太慣孩子,再這樣,我可就不來看你這個姐姐了。”烏云說,“上次給的,都還沒正經戴過,一直在她的小包里放著。孩子還小,大了你咋給了給去。你就是置嫁妝我也樂意。”烏云說,笑了起來,她被自己說的話給惹笑了。
“那還用說。”紅說,“早就說好的,哈斯是我的孩子,那嫁妝肯定得我給置辦。”說著,紅愣怔了一下。“這位是?”她說,望著扎斯,又望向烏云。
“忘了給你介紹,過路的。”烏云說。“找巖畫的,受傷了,在我們那住了幾天。”烏云說,覺得沒說明白,又說,“養傷呢。”
紅拍了一把烏云。“你就胡謅吧。”紅說。
烏云有些急了。“真的,咋能哄姐姐。”烏云說,“可不能胡說,讓人家聽了多不好意思。還以為——”烏云說,覷了一眼扎斯。
紅沒有讓烏云說完,就截住了。“好了,好了,不胡說了。”
烏云忙打岔兒:“姐姐最近生意好吧。”
紅從里間屋子里拿出三瓶飲料,一一打開,讓他們喝。但她又接上說:“說真的,烏云,你不打算再找嗎?”壓低了聲音,“上次見的那個,怎么樣?我給你介紹的。就是左旗的那個巴特爾。”
“咋又轉到這個話上了。”烏云紅著臉說,像是惱了。
“好,好,好,不說這個了。”紅說。
停了一會兒,她們又說起了別的。
扎斯趴在柜臺上看著,一直聽著她們說的話。幾次,他都想說,但他沒說。那些話牽扯到了他,他怕添進去更亂了。他把注意力轉向了柜臺里飾品,一件一件地打量。
“爸爸。”哈斯突然指著靠墻的貨架上的一個玩具,拽了拽扎斯的胳膊。“小牛。”哈斯說。
紅的耳尖,猛地就笑開了。“你看這人。哈斯都叫上了還裝。叫的啥,你聽見了吧?還瞞你紅姐。”
“哪里?”烏云忙解釋,但又覺得解釋不清,只好作罷。“孩子那是胡叫呢。”
這時,進來了一個買貨的,趁機,烏云說還到別處轉轉,告辭出來。
出了店,烏云并沒有顯出生氣,抱起哈斯說,“這丫頭,你咋總是胡叫?”望了望扎斯。但哈斯沒改她的認定,又叫了聲:“爸爸。”
扎斯接過了哈斯,抱在了懷里。“沒事,孩子嘛,咋叫了叫吧,只要她高興。回吧,烏云。”
“還早呢,要不我們找個飯館,吃了再回。”烏云說。烏云又說,“找個火鍋店吃去,哈斯最愛吃火鍋了。”
扎斯想了想,拿定了一個主意。他說,“去超市,把菜和料買上,回去了我們自己做上吃,我做。幾天了都是你伺候著,讓你們也嘗嘗我的手藝。不比火鍋店里的差。”
“你?”烏云說,“你行嗎?”烏云好奇地說。
“沒問題。”扎斯說。接著用做廣告的口氣說:“保管你吃了還想吃。”
他們在附近一家超市買好了東西,提著去停車場。
把東西放到車上后,扎斯上了車,又要下車。
“你們在車上稍等會兒。我有個小事。”他說。
“你有什么事?”烏云說,“這個地方你又不認識人。”
“剛才路過看到一把腰刀挺好,我想買上。”扎斯說。
“你有腰刀呀。丟在草里,我給你找到了。”烏云說,“你以為沒有找見?”她跳下車,從后備箱里拿了出來。
“這個?”扎斯看著刀,眼里有異樣的東西,感激,或者什么。但他停了停說,“這把舊了,我想買把新的。”
“那我和你去。”烏云說。
“哈斯一個人咋行。你陪著她。孩子溜了一天夠累的了,不能再跟上去。你陪著他休息一會兒。”扎斯從后備箱背上背包走了。
扎斯不到半小時就來了。
“這把刀還真不錯。”烏云看了看,遞回給了扎斯,打著了車。
半路上,鐵彬打來電話。烏云說他們已經回了。
扎斯忙著做火鍋。哈斯在地鋪上入迷地玩著一只小牛的玩具。
烏云把牛吆到圈攤后,回到了帳篷,天已黑透了。沒有月亮,只有狗叫聲,在遠處,一下一下地閃爍。
烏云看到哈斯手里的東西,問是哪來的。哈斯頭都沒抬,說:“爸爸。”
“你——”烏云看了一眼扎斯,沒再說什么。她洗了手,往地桌上擺起碗盞。
“我知道孩子喜歡那個。”扎斯悄悄說。
“你就嬌慣吧。”烏云說。
扎斯沒有接茬口。扎斯說,“開飯了。哈斯,過來吃火鍋了。”
哈斯抱著小牛玩具,吃飯時,也不放下。連媽媽往過里接,她都不給。她是抱著那只玩具小牛睡著的。
吃過收拾停當后,烏云沒有把地桌搬走。她拿過了兩個酒杯和一錫壺酒。她倒好了酒,給坐在桌子對面的扎斯遞了一杯,自己也端了一杯。
“你明天就要走了。”她說,碰了碰扎斯的酒杯,一飲而盡。
他接過酒壺,又斟滿了個兩只杯子。
“是啊,”他說,“如果不是遇見你——”他說。他沒有碰杯,一口喝干了自己的,看著烏云。
“別說那個。”烏云說,也干了自己的。“說說你。”她說。
“我,”他說,“我有什么好說的,不就在這兒嘛。”
烏云動了動身子。“DD是誰?”她說。她說,“你阿爸在電話里說的。”
“這個,還是不說了吧。”扎斯像是在掙脫什么撕扯,往上挺了挺身子。
烏云不再追問。但扎斯卻說了起來。
“一個過往。”他說,“她也是我們肅南人,我是在QQ上認識她的。她叫當然,她的網名是DD。她主動加的我。她說她知道我是搞巖畫的,他喜歡我長在野外的生活。后來,我們就見面了。我進山找巖畫,她每次都陪著。兩個人方便了許多。后來,她突然不跟我進山了,她說太累,她還要在家里干些別的。對了,她是寫網絡小說的。但不是那樣。”他端起酒杯,呷了一口,又猛地喝盡,長出了一口氣。“不是那樣,”他說,“后來,我發現她和一個文化傳媒公司的老板來往密切。但我沒有干涉,我覺得她有她的生活,我得尊重她的生活。起先,她也坦誠,那個老板給她買的鐲子,她戴在手上,也給我說。那個老板知道她喜歡看書,就投其所好,拼命給她買書,她也拿給我看。她常到我們家去,她和我的阿爸也熟。我都三十幾了,阿爸催促我們結婚,她也同意,把日子定在了今年十一。后來,阿爸再催,她總是敷衍。再后來,她很少去我們家了,就連我從山里回去,她也推托有事,不和我見面,最多閃個面就走了。我忍著,裝做什么也沒有發生,我一直等著她的回歸。”他不說了。
他一個不抽煙的人,卻從口袋里掏出了一盒。他抽出一支點著,又給烏云遞了一支。烏云擺擺手,但馬上又接了過去。她讓扎斯給她點上,吸了一口。她說,“后來呢?”
“后來,”他說,“就這次了。我剛進山時,她給我打了一個電話,她說她換了手機,是別人給買的,還換了別的。然后,她的那個手機號就不通了。她的手機和我的,是我同時買的兩個,一白一黑,她拿白的,我拿黑的,號都是連著的。”扎斯又接上了一支煙。“可是,”他自嘲了一下,“沒有可是了。”他說,“后來的,你都知道。”
“也許……”烏云說。
扎斯輕輕搖搖頭。
烏云站起來,走出了帳篷。扎斯看著烏云走出帳篷,又走了進來。他看到有一種東西在她的身體里突然強烈起來。
“你真的認不出我來了嗎?扎斯?”她說。“扎斯。”她說。
扎斯愣怔著,看烏云臉上的表情。
“我是其其格,烏云·其其格。”烏云說,“那時,你們不叫我烏云,大家都叫我其其格,叫我格格。”她坐了下來,喝了一口酒,又平靜了下來。
“格格,你是格格。”扎斯在記憶深處搜尋著,又盯著烏云的臉看。“格格。”他說。
烏云又站了起來。她在那個盛衣服的木箱里,翻著什么。她找到了。她拿出一個很厚的本子,放在了桌上。
扎斯剛要拿起,烏云把手按在了上面。“先別。”她說,“等說完了再看。”她看著扎斯。“記得蒙合嗎?布仁蒙合?”她說。
“記得,怎么能不記得?”扎斯說,“我們是大學同學。我們挺要好的。”扎斯停了停,像在踅摸什么,眼睛一閃一閃的。“可是,他大學畢業后,考上了公務員。我們通過幾次電話。后來,他的手機換號了,或者怎么,反正打不通了,就再沒聯系。也許他給我打過電話,但不會通的,因為,我也換號了,單位統一換的。”
“是的,”烏云說,“我知道你們挺要好的。還記得嗎?”烏云說。
“啥?”扎斯說。
“你們上大學時,有次野外實習,到我們這兒來,一班同學分散在各個牧區。你們幾個就住在我們家里。”烏云說,“那時,我阿爸阿媽都還健在。你們是四個人:扎斯、蒙合、達隆還有辛巴。”
扎斯重重地點著頭。“對,格格,就是那個人人喜歡的格格。”扎斯在烏云的臉上找到了過去的那個格格。他笑了:“沒變,就是黑多了。”
烏云也笑。“你不是也從一個白面書生變成了一個又黑又壯的黑熊。”說完了又覺得不貼切。“不對,這像是在損人。應該是……”她屏住聲息;她在想個好詞。
“像啥都行,別糾正了。”扎斯也笑。
但烏云不笑了。“只要你不生氣就行,反正我也想不出個更好的說法。”烏云說。她嚴肅了起來,或者神往。
“你們在我家待了有半個月,對吧?”烏云說。
扎斯說:“是半個月。白天我們出去勘察,晚上就在你們家住。你們家給我們四人單獨扎了頂帳篷。可是,我們總是在你們帳篷里待得很遲了,才回去睡。聽你阿爸講了許多東西,還喝酒。記得你阿爸還讓我們把離的近的同學招集來,給我們開了一次篝火晚會。那次,差不多都醉了。”
“你記得很清呀。”烏云被觸動了,她說,“就是那次,”她停住了。“就是那次,布仁偷偷親了我。”她接上說。“這個布仁。”像是布仁就在旁邊,她嗔了他一下。
“這小子夠賊的呀。”扎斯說,“我們可沒發現,他也從來沒說過。”
“問題在后面。”烏云說。
“怎么?”扎斯很吃驚,他懷疑到了別處,比如他讓她懷上了孩子。他想到了哈斯,可是,不對,顯然時間和哈斯的年齡相差很大。“那么?”他說。
“你們回校后,沒幾天,他就又偷偷來了一次。”烏云說。
“這,他可一點都沒透露過。”扎斯說。
“那天阿爸阿媽都不在,去旗上購物去了。我正在看他走時給我留下的一本書。我初中畢業就不再上學了,受你們的啟發,我想多學些東西。我在帳篷外的草地上坐著,他突然就走到了我的跟前。他抱住了我,把我都嚇著了。他說他沒有別的意思,就是回來告訴我,他要娶我,讓我等著他。他讓我向他保證,在他娶我之前不要嫁給別人。他說他愛我,除了我,他可以什么都不要。他說我要不保證的話,他就不回學校去了,留下來和我一起放牧。我答應了他,我和他跪在太陽下發了誓。”烏云說著,長長地吁了一口氣。
扎斯點著頭,又在各自的杯里倒上了酒。他端起來喝了。烏云也端了起來。她喝了一半,又把酒杯放在了桌上。
“他是左旗人。”烏云說。
“這個我知道。”扎斯說。
“但他考的是我們右旗的公務員。他畢業回來就給我說了,考到右旗的目的是離我近些。他考上了,分到了稅務局。但那不是他想要的。和你一樣,他喜歡的專業是勘察巖畫。我鼓勵他先把班上著,還有別的可能,想辦法,興許有調到博物館什么單位的可能。就是你現在上班的那種地方。”
扎斯點著頭,沒有說話。他又給自己倒了點酒。
“調工作,你知道的。他這人不會去求人,更不會走動什么的。但他工作認真,領導看中了他,不久就提拔他當了副局長。”
“這小子,官運亨通呀。”扎斯咧咧嘴,“好事嘛。”
“可是,讓你當,你當嗎?不是你的專業。”烏云說。
“這個,”扎斯吭了吭,“這個恐怕不行。”他說。
“所以嘛,他就急了,回來和我商量。那時,我們已結婚了。他說他不干了,回來和我放駱駝,正好安心勘察巖畫。他說他寧可放棄別的,也不能放棄他的專業。我們家那時有駱駝群有牛群。現在駱駝群還在,是哥哥嫂子在曼德拉山中放著。”烏云說。“另一個山,離這兒很遠。”
“你們結婚后,他沒想把你搬到旗上去嗎?”扎斯不解地問。
“有過,但我不愿意。我喜歡放牧。”烏云說。“我當時一聽,覺得還真委屈了他。我真的很疼愛他,更支持他的事業,這一點,與你們實習時,給我種下的印象有很大的關系。于是,我就說,回來就回來吧,這么大的牧場還養活不了一個你。他就打了報告,辭了工作回來了。后來,阿爸去世時,把駝群分給了哥哥,把牛群分給了我們。嫂子是曼德拉的人,說那里更適應養駱駝,就搬遷上去了那兒。”
“壯舉啊。”扎斯說,把酒杯拿在手里,捏了好一會兒,猛地喝了。他明白了一切。“可是,”他說,“他人呢?”他說,“他人呢,究竟發生了什么變故?”
烏云沒有回答他。她繼續接上說:
“他每天把牛吆到山坡上后,就到山里面去找巖畫。他拿著個本子,在上面寫寫畫畫,到晚上,講給我看。他還在每幅巖畫后面配上了詩。”烏云說。“就這個。”烏云把本子推給了扎斯。
“我們結婚后好幾年了沒有孩子,后來才有了哈斯。可是,哈斯生下來不久,他就出事了。”烏云聲音哽咽,停了下來。
扎斯翻著本子,好多地方都被水洇壞了。
烏云接過了扎斯手里的本子,翻到了后面。
“就是這幅。”她說。烏云指著最后一幅畫說,“就是這幅巖畫,讓他出的事。”她說。
扎斯吃了一驚,那幅畫正是他剛剛發現的“交媾圖”。畫得細致,配有說明文字,還配有一首小詩。他起的名字是:“圖騰”。
“這幅畫在一個石柱的夾縫里,他就是在研究這幅畫時,天突然下起了暴雨,突然的洪水,把他堵在了夾縫里。”烏云說,“找到他時,他在那個夾縫里趴著,這個本子在懷里的衣服里緊緊裹著。”她咳了一聲,捂了下嘴。“我們的圈攤原來并不在這兒,在另一個溝里。他是在這里出的事,不知道為啥,我就搬到了這里,扎了攤子。”
“哦,是這樣啊。”扎斯說。他想嘆息,又覺得輕浮。他閉上眼睛沉默著。
“這個,我一直沒給哈斯說過,所以,”烏云又說,“哈斯并不知道爸爸是什么。從小就不知道爸爸這個概念,直到你給她說了。”
扎斯撫著本子,撫著那幅畫。他想說什么,又說不出什么。但他還是說了。“這個,我能帶上看嗎?”里面有許多他沒有發現的巖畫,他要帶著他復查。他說,“我會還回來的。”
“對你有用,你就用吧。”烏云說,“還不還的,對我有啥。”
扎斯一頁頁翻著畫冊,許多他沒有發現的巖畫,讓他震驚。每一幅畫都配有一首詩。每一首都配得那么精準,這是他完全沒有想到的一種創舉。
他坐不住了。他滿滿地喝了一口酒,走出了帳篷。烏云也跟了出去。
“爸爸。”是哈斯。是哈斯在夢中叫了一聲。
他轉過了身,猛地就抱住了烏云。他說格格。他還說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