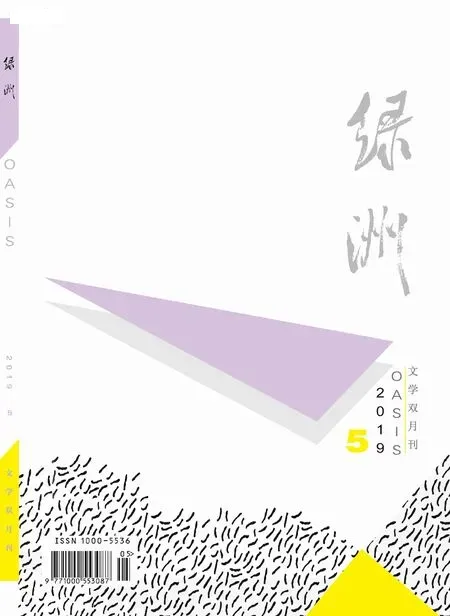云端下的氈房
黃水成
一
“咚”的一聲,遇上強對流了。忽上忽下,飛機像一葉小舟在浪尖上出沒,這種失重感令人十分不舒服。淺睡中的我一下被顛醒過來。
人是脆弱的,特別是在飛機上,失去大地的支撐,總讓人感到不踏實。而長途飛行能干什么呢,除了吃還是睡,睡,讓累人的旅途顯得短暫一些。然而,遇上強對流讓人一下睡意全無,每個人的神經都揪得緊緊的。
我拉開舷窗望去,窗外一片白茫茫的世界,原來我們正在雪山上空掠過。年齡或者歲月總會隔開一些重要的東西,在懸浮顆粒物難以抵達的萬米高空之上,天空藍得有些不像話,那童年深秋才能望到的景象,原來都躲在云層之上。
云是山造的浪。飛機下方氣流沖擊著連綿的山脈,山頂上云朵洶涌澎湃,和積雪互相映襯,以致模糊了對遠處山巒的辨識,那片純白的世界到底是云還是雪。
這白色我并不陌生,我在江南見過多場積雪。但我驚異腳底的世界,這些起伏的山,每一座山頭都被刀削斧劈一般。是什么力量,能把山打磨得如此棱角分明?在雪的映襯下,遠遠望去,銳利無比。我貼著舷窗向下張望,每座山峰都延伸出無數個山頭,每座山脊都有分明的際線,看似無序,卻縱橫相連,就像一片溶解的葉子,只剩下筋骨,脈絡清晰的映在眼底。
有人告訴我腳下是祁連山。突然倒吸一口冷氣,東西橫亙兩千里、南北縱橫八百里的祁連山脈,此時竟在腳下。不要說眼睛難以丈量,就連想象也難有一個隱約的輪廓,難怪氣流在此都要翻上筋斗。西北這座最重要的分水嶺,一生能看上幾回,何況在它上空掠過,我把臉摁扁在舷窗上朝下方觀看,此時,我看清腳下大片山脊,以及漫長的天際線,看到日落天邊的寥廓,才真切感受到這個星球經度與緯度的遼闊。
白雪皚皚,放眼望去,看不見丁點綠色,腳下的每一座山頭是那么的傲岸、蒼凉,但它們看上去是那么的壯美,好像一旦站住了,就是一副傲然屹立的身骨,不要說常年風雪,就是刀削斧劈也大義凜然。除了白就是灰黑,它們,仿佛都是筋骨畢露的漢子雄赳赳,這里的山像極某個地方的人,可以不水靈,甚至粗糙,但個性鮮明,有棱有角,站住了,就是一個令人膜拜的姿勢。這和南方的群山是多么的不同啊!南方的群山多婀娜多嫵媚,但蔥郁之下卻少了一份大義凜然的風骨,祁連山,顛覆了我對山的認識。
二
飛機一直在顛簸,翼尖處抖得厲害,鋼鐵與氣流持續對抗,人類前進的翅膀,在祁連山上空彎出一道美麗的弧度。
越過群山之巔,山峰如浪峰般徐徐退去。舷窗外的氣流逐漸平息下來,飛機又恢復平穩的姿態。此時,前方是大片開闊的丘陵地貌,在積雪覆蓋下,灰白相間,像大面積的皴染,把這片隆起的高原清晰而立體地呈現出來。
不一會兒,山峰和雪景幾乎同時隱去,云層也不見了,陽光直直地傾瀉下來。不再顛簸,很快又來了困意,正想拉上舷窗,突然,我看見了一片“海”。感覺有陣風,正掠過那粼粼的水面,斑紋狀的浪一波連著一波,齊齊向山岸邊涌去,海風吹拂,碧波浩渺,遠處的雪山一下成了漫長的海岸。
怎么可能?西北哪來的海?
仔細辯認才看清,竟是一片沙漠。高原地貌帶來太多的視覺沖擊,群山腹地竟出現沙漠,讓人一時不知所措。不禁想起之前飛機掠過陜北時所看到的溝壑縱橫的高原地貌,那缺少綠色覆蓋的土地,成了失守的國土,風雨日夜沖刷那裸露土層,紛紛脫落,輾轉,漂泊,漂染了一條大河的顏色。那流浪的黃土,改變的何止是一條大河的方向,還有世代萬千生靈的命運。
腳下這片沙漠,應該是氣流長年沖刷加上雨雪剝蝕而留下的泥沙,在群山的包圍中,氣流經不住座座高山的阻攔,終于在開闊的群山腹地停下疲憊的腳步,被裹挾的泥沙也就此落下腳跟。缺少大河的幫助,它們沖積在一起,最終形成一片片小沙漠。
看到這片沙漠,讓我對這片土地又多了一層敬意。大自然的殘酷廝殺分秒不停地上演,蒼凉或者風骨,這背后都有著沉重的分量。只有經過殘酷的摔打,才能練就強勁的筋骨。電視畫面見到的高原生物總是那么彪悍,不要說狼和雪豹,就連巖羊都強悍無比,那奮起的蹄,還有那高高舉起的大角,能讓峭壁上的雪花飛抖。
此時,我無法分辨狼和雪豹的蹤跡,眼睛死死地盯著腳下這片沙漠走神。我見過沙漠,一望無際的沙海,就像一個凝固洋面,每個起伏的沙丘都是凝固的波浪。然而,只要下一陣強風襲來,它便再翻出新的面孔,沙漠總在不經意間更新自己,永不疲倦。
每一座沙漠都是一片遠逝的海。恍惚間,覺得它就是一片海,起碼,它曾經是海。從過去到現在都是。從海水換成了沙子,從蔚藍變成金黃,從柔軟變成了堅硬,這片土地上的生命需要重新面對,堅硬地面對,在另一個形態上重新演繹物競天擇的故事。想到這些,忽然覺得幾千里的祁連山,更加偉岸蒼然。
又一串激烈的顫抖,飛機落地了。帶著一身凜凜寒氣回到堅實的地面,遠去的祁連山卻像一塊蒼然礪石立在心頭,神圣,高潔。
三
落地的翌日,魯院同學李健便邀我們進山,到牧區轉轉,這是來新疆前他早就謀劃好的事。出發前,他在電話中三言兩語地說了幾個地方,去牧區是其中一個重點。
這位新疆漢子話不多,但只要說出來他勢在必行。
天灰蒙蒙的,好像要下雪的樣子。一行八人,同學約好友幫忙,兩部車來接我們進山。
同學說,新疆的文化精粹其實不在畫冊里,更不在舞臺上,新疆的文化精粹流淌在一代代民間藝人血液里,在世襲的民俗中,在冬不拉的彈挑中,在牧人的鞭子上,在篝火旁的長袖里,新疆的故事在白花花的胡子上凝起霜花,代代相傳。同學話中的新疆風情,在大家心里鼓起大大的風帆,一路伴隨北風前行。
同學好友的家在米東區柏楊河哈薩克族牧區。車子一直朝烏魯木齊的東邊前進,歷經幾次寒流的洗劫,沿街的白楊和白蠟樹一片金黃。越來越近,剛到郊區,便遠遠望見起伏的山巒,以及遠處高聳的雪山。缺少林木的阻擋,眼前起伏的丘陵露出寬闊的脊背,這樣一丘連著一丘,一直向著遠方延綿起伏,這片隆起的高原再次展開它遼闊的畫卷。
這遼闊的畫卷上,卻不見成群牛羊,只有零星的幾只羊或馬在山梁上自由地吃草。入冬了,草木枯黃而稀疏的山岡,似乎敞開了胸懷準備迎接嚴冬的風雪,這里很快將變成一片白色世界,它,絕不是越冬的理想場地。成群的牛羊應該在更遙遠的大山深處,那茂密的林區才應該是它們越冬的牧場。
沿著柏楊河山谷前行,翻過幾道山梁,很快到了同學朋友的哈薩克牧區定居點的家。一下車,熱情的女主人便迫不及待地招呼大家朝院子后面的山上跑。站在山梁上,她一指遠處的雪山說,瞧,那便是天山東段著名的博格達峰,天山天池也在那邊,女主人說我們來得不是時候,且天色太晚,錯過了新疆最美的季節,也錯過了途中忽必烈的敖包和丘處機的喇嘛廟,還錯過了三千多年前的塞人巖畫……
女主人的指尖瞬間流出一幅幅美麗的圖畫,順著她指尖徐徐展開的,有空間的緯度還有時間的長度,她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間。細究起來,新疆這廣闊的土地,我幾輩子也看不完,而我總覺得作為一個匆忙的過客,能站在這片熱土上看一眼,再吹一陣山風,便什么都值了。
站在這片開闊的山梁上眺望四周,我再次想到了海,只有海的遼闊才可比擬眼前這片無際的丘陵。盡管世界上還有很多無邊的大平原,但那缺少起伏的平面,反而讓人沒有縱深感,它不能完美地把這種大而遠的空間立體地呈現出來。
我們太缺少自然的撫摸了,快節奏的現代生活,讓人終日陷在犬牙交錯的鬧市中,神經繃得緊緊的,目光一刻也清閑不下來。每次在電腦前待到眼花時,總會對著旁邊那盆綠蘿看上一會,讓眼睛重新聚焦。眼前這無邊的風景于我是一種奢侈,同伴們都回去了,我卻留在原地貪婪地張望,眼睛終于沒有任何阻擋了,盡可縱目馳騁,讓目光盡情舒張,終日疲憊的神經一下松弛下來。
此時,真有一股策馬揚鞭的沖動,順著這一道道山梁一直往前沖去,沖向時光深處那無邊無際的草場,然后坐在空曠的山梁上,當一個安然自在的牧人,這一刻,恍若一個被塵世遺忘的自然人。
四
暮色漸濃,野風生硬撲到臉上感到有些疼。我有些不舍地朝山下走去,遠遠便聞到一股羊肉的香味。其實剛來時便聞到了,只是沒在意。這時我看到架在院子外的那口大鍋,爐里還煨著柴火,鍋里不斷地冒著熱氣。
雖沒見到氈房,但眼前成片房子中,清一色的白,每個院落都保留一間圓形、穹頂氈房風格的房子,它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過去,在這片聚居的營地,我想象著它過去的樣子。
一進屋,女主人領著大家在穿羊肉串。同學說,今天主人家宰殺了一只羊,用水煮全羊招待大家,男主人和孩子已經忙乎一整天了。羊可是大牲畜,更是草原人家賴以生存的命根。全羊,歷來是牧民招待貴客的最高禮儀。我們何德何能受此盛情,竟以最高禮儀招待我們這幫初來乍到的南方人,頓覺得有些愧受。女主人不斷地和我們拉家常,仿佛早已認識,如闊別重逢的親人。她的每一句話都飽含溫度,讓我們毫無生疏之感。或許在新疆人的觀念中,朋友的朋友依然是朋友,他們,壓根沒有我們南方人那些彎彎繞,他們即便對登門投宿的人,主人都會拿出最好的食品招待,我們開始領教了新疆人的熱情與胸懷。
我們所在的是哈薩克族定居點,主人以哈薩克族風情接待我們,她選擇那間“氈房”招待晚宴。這“氈房”其實是主人的臥室,一張暖炕占去房間的三分之二,再擺上一張桌,顯得緊湊而溫暖。土豆絲、鹵蛋、大盤雞、羊肉串陸續登場,大盆大盆的煮全羊緊跟著一一端上來,鮮香四溢,熏得一桌的人不自在。經常對電視上大塊吃肉、大碗喝酒的情景流口水,試想,那人生該有多豪邁,哪敢想有朝一日,我也在這樣的情景里大快朵頤。
我仔細看了盤中的大餐,羊頭、腸、肝、肺、肚……都擺在桌面,地地道道的一只全羊。主人交給同學一把小刀,同學很謹慎地接過刀子,瞬間一臉莊嚴地對著羊頭橫豎劃了幾刀,并象征性地從羊頭剔下幾塊肉分給大家,晚餐就正式開始了。
南方人講究清淡,怕膻腥。最讓大家欣喜的是,煮了一天的羊肉非常鮮滑、爽口,竟一點也不腥膩。主人告訴大家,什么訣竅都沒有,什么料都沒加,就是純水煮,最后放點鹽,純正的哈薩克族的手抓羊肉。在家燉羊肉時,除了姜、蔥外還要加上許多佐料來除膻,這樣做其實早已失去羊肉的鮮味了。前些年恰好從內蒙回來時參加一個派對,主人用烤全羊熱情招待大家,皮脆肉嫩,看得出廚師沒少費功夫。但拿起羊肉時,卻聞到一股煙熏的焦味,和內蒙的全羊完全兩樣,才知道閩南人做不出地道的草原風味。不是廚藝不精到,而是每個地方的物產都有獨特印記,那是泥土的記憶,永遠不被篡改。
閩南話是幸存下來的古漢語方言之一,它保留了上古的古音古韻。有意思的是,閩南話里,“人”字發音正好和當下普通話的“狼”字同音。如今,我們這幫閩南人到了草原上,眼前羊肉鮮美,大家左右開弓,腮幫鼓鼓的,大口大口地吞咽,一個個真像餓極了的“狼”。我看同學和女主人也和大家一塊吃羊肉,卻吃得一臉虔誠,不分肥瘦,也不管是肝、腸、肚、肺,只要是盤中的食物,他們都吃得津津有味,他們把每一塊骨頭上的肉都剔得丁點不剩,然后把骨頭齊整地碼在跟前。主人說,吃過的全羊,把全部的骨頭拼起來,就該是一只羊的骸骨,只有這樣才算是吃盡了。
在這里,一枝一葉都歷經歲月,生命充滿傳奇和艱辛。其實,大地上的任何一種食物都得到尊重。看著眼前成堆的并未剔盡的骨頭,頓覺羞愧,相比他們,我們就是一幫無知而粗俗的食客,終日挑肥揀瘦,缺少禮儀不說,我們對食物缺少虔誠,更談不上對這土地上所有生靈的一份尊重。“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其實傳統文化中不乏這種自律,這缺失的背后,我看見巨大的信仰空白。由饑而飽,由貧到富,從面黃饑瘦到油頭肥耳,我們似乎忘記了過去的饑餓,我們不再珍視土地上的一草一木,我們背叛了土地,我們只是食客。
那天,同學和主人原本還約好一對說唱的民間藝人,誰知他們剛好出遠門了。主人和一位叫安子的好友臨時客串,酒酣肉飽之際,她倆為大家跳起哈薩克族的舞蹈,舞姿曼妙,迎面如吹來一股草原之風。
五
臨走前,熱情的女主人再次挽留大家小坐片刻。這時我才注意到主人的家居裝飾特別簡樸,紅柜、樹根、花束、干麥,簡單點綴的背后,透出主人崇尚自然的內在文化氣息。我對石頭有著天然的感情,最引我注意的是書架上各色石頭。
女主人說,新疆是石頭的天堂,石頭太多了,和田玉、戈壁石、觀賞石……只要到了野外,俯拾皆是。架子上的石頭就是她從各地拾來的寶貝,其中幾顆是從她家院子旁那條柏楊河淘來的石頭。
臨走前,女主人執意要贈我一顆石頭,著實嚇我一跳。每顆石頭都歷經地質年代的漫長孕育,又歷經千萬年風霜雨雪盤剝,它們是宇宙的精靈,是修行的佛。對于愛石之人,每顆石頭都是隔世的一段未盡情緣,一個個惜石如命。她不僅要贈我,還要贈同伴們每人一顆石頭,這豪舉再次讓我們震驚,大家不敢奪人所愛,都不敢答應。
世間絕無雷同的兩粒沙子,何況是石頭。我仔細打量書架上的石頭,形態各異,姿態萬千。我從架子上眾多石頭中,一眼看中那顆小青石。它其實并不顯眼,吸引我的是那兩條很特別的白色紋路,一上一下,如盤龍出海,如彩練當空,如白云出岫,我說不出它具體像什么,拿在手中直愣愣朝它發呆。女主人走過來了,她說,看,它們多像長江和黃河。仔細端詳,還真像兩條大河圖形,但它似乎更像什么,一時覺得眼熟卻又說不出來。
我既不藏石,更不玩石,雖拾過幾塊石頭,但都是隨手從路邊撿來的無心之作,只是覺得有緣,遇上了就帶回來,絕無把玩之意。眼前這顆小青石,剛照面卻被它一下黏住了,難以說清其中滋味。女主人說它是柏楊河里拾回來的石頭,只要我看中,她堅持要贈我當個念想,突然有一種奪寶的感覺。她卻說,不是奪,是換一個主人在陪伴它。
世上每顆石頭都具有靈性。回到賓館,我拿出小青石細細把玩,越看越覺得眼熟,似曾相識卻一時難以記起,它像某個熟悉景象印在腦海中一般。我愛不釋手地把玩著,那兩道白色紋路像一道靈光,把我引入夢中,千里祁連山一片清澈,幾朵祥云盤繞峰間,晚霞中,一片蒼茫。夢醒了,我才明白,這塊小青石上的紋路多像祁連山上的云彩,它和我夢中的景致完全一樣,如今卻被凝固在這塊石頭上,心中一陣欣喜。
好石頭都是養出來的,越養越溫潤,越盤越剔透。我把它揣在口袋里,一有空閑就把玩它。回來后,我把它放在每天工作的電腦前,在勞累的間隙不斷地盤摩它,看到它就想到那里的山水,那里的人。我帶走的何止是朋友的情誼,那是她家鄉柏楊河的古老結晶,還有祁連山上的神秘圖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