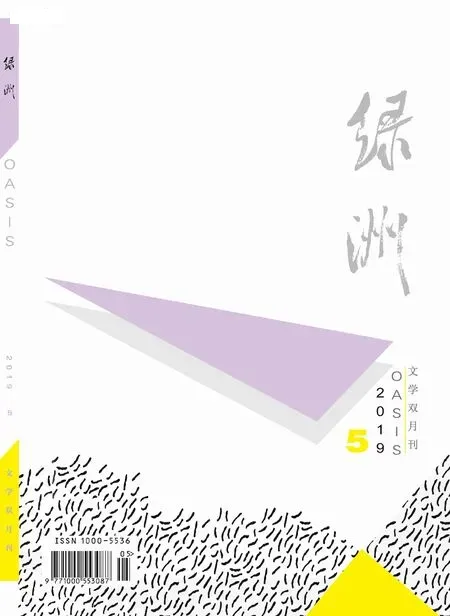“流動”的學校
吳新平
高中畢業(yè)40年了,我的中小學生活,是跟隨父母所在的工作單位在遷徙中度過的。當年,父母所在單位新疆軍區(qū)生產(chǎn)建設兵團工三師23團是一支建筑工程部隊,在南疆浩瀚的戈壁灘上走南闖北,承接工程,學校隨著連隊“流動”四方。
1969年春天,我們連隊工一隊正在南疆澤普縣修建東岸大渠。有一天,兩位具有初中文化的女同志挨家挨戶去登記適齡孩子,原來她們是連隊里挑選出來的老師。太高興了!我們連隊準備辦學校了。到了我家,我還不足7歲,老師說,連隊孩子不多,可以入學。登記我的名字時,父親想了想,說:“叫吳新平吧。”母親說不好聽,去掉“新”字,單名叫“平”就行了。父親是志愿軍轉業(yè)干部,他說:“我們奮斗的目標是為了新的和平,還是叫新平吧。”就這樣,“吳新平”成了我的學名,我的小學生活開始了。
大約讀了一年,連隊合并,我們被合并到工三隊。由于有新任務,連隊的男職工搬到了巴楚縣農(nóng)三師53團去施工,一時沒有搬走的家屬們被合并到工二隊,我又到了工二隊小學上學。在這里,由于我學習及各方面表現(xiàn)突出,我居然還成為學校“三結合”領導班子成員。所謂“三結合”,就是學校領導、家長和學生共同管理學校。一個二年級的孩子懂什么呢?只不過是當時文化大革命那種政治形勢的一個需要罷了。在工二隊小學讀了兩年,我們便搬到巴楚縣農(nóng)三師53團,在15連住下了。這個連隊小學一共有十幾個孩子,各年級都有,一年級學生有十幾個,可以組成一個班。另外我們6個孩子中分別有3個四年級、1個三年級和2個二年級,于是就讓三年級的孩子留級到二年級,我們6個人分成2個班在一間教室里開展復式教學。老師給二年級上課時,我們四年級的做作業(yè);給四年級上課時,二年級做作業(yè)。我們就一位老師,名叫謝經(jīng)式,語文、算術、美術、體育……什么課都是他一人教。
這位謝老師是山東人,在上海第二醫(yī)科大學讀大二時被錯劃為“右派”,后來“發(fā)配”到我們連隊改造。他有極好的古代漢語功底,非常喜歡孩子,熱愛教書育人的事業(yè)。學校僅有一排房子,三間是教室,一間是老師宿舍。他帶著我們學生去割沙漠紅柳,給校園筑起籬笆圍墻,又請連隊的木工做了一個秋千,還用土塊搭了乒乓球臺,一個像模像樣的連隊小學校誕生了。在當時,引來了其他連隊多少雙孩子們羨慕的眼光啊!每天下課后,他都帶領我們開展體育、文藝等課外活動。吃過晚飯,他給我們講《水滸傳》,講《三國演義》。即使到今天,他生病了躺在床上,我們圍在他的床邊聽他講故事講古詩文的情景依然歷歷在目。
當時物質奇缺,一塊掛在墻上的鐵皮就是我們的黑板,課前課后我們要到處去撿土疙瘩當粉筆用,但是我們的眼界被打開了。謝老師請連隊里有特長的北京、上海知青到學校,有的教我們唱《三弦》、唱京劇、排文藝節(jié)目,有的教我們打乒乓、蕩秋千、下象棋,校園成了當時連隊繁重枯燥的勞動后最輕松、最有文化氣息的聚集地。孩子們吃過飯就想去學校,職工們勞動之余也愿意去學校,那里有人讀書,有人排練節(jié)目,有人打乒乓球,有人打羽毛球,有人蕩秋千,有人下軍旗、跳棋和象棋……多么生動豐富的生活場景。至今想起,我仍覺得心有余熱。我們小孩子排好節(jié)目后會到勞動工地去為大人演出,我們唱的《三弦》還被選到團部去演出,非常受歡迎。這樣的小學生活雖然只持續(xù)了一年多,卻給我留下了最豐富最深刻最美好的記憶。
是的,我們又搬家了。國家要建設南疆鐵路,兵團組建鐵路工程局,把原工三師23團抽調到阿拉溝。按慣例男職工先去打前站,家屬們集中到53團團部等待隨后搬遷。于是我在53團團部學校上了五年級的下學期。在這里我見到了人生當中的第一次魔術表演,農(nóng)三師文工團來學校慰問演出,魔術師在舞臺上變出鴿子,變出錢,簡直太神奇了!
男職工在阿拉溝蓋好半干打壘的房子后,我們就跟著搬到阿拉溝。可是到了9月1日,學校沒有蓋好,直到10月中旬,我們才開學。我的初中一年級就是在阿拉溝開始的。
印象最深的是數(shù)學老師,她是我們的班主任,是一位上海知青,人長得十分漂亮,課也講得好。只是剛上初中的男同學十分調皮,常常搞出各種惡作劇。他們會在老師進教室前,把掃帚放在虛掩的門上,老師一推門,掃帚正好掉在老師身上,引來他們哄堂大笑。男孩子不愛學習,滿肚子的壞主意,把課堂攪得上不下去,常常看見老師忍住委屈的淚水,繼續(xù)為我們上課。不過,更多的記憶是老師帶我們去爬山,給我們講外面的世界,講很多的格言警句。她教育我們不要做語言的巨人,行動的矮子,這個比喻多么形象,一下就深深刻在我的腦海里。
可能是考慮到建筑工地經(jīng)常搬遷,團里決定建一個基地,把家屬和學校固定在基地。地址選在焉耆四十里城農(nóng)二師27團一個叫炮臺的地方。初二的時候,我們就搬到基地學校了。這個學校距離我們父母工作的阿拉溝600余公里,當時的交通條件很落后,坐汽車需要一天的時間。我們這群十三四歲的孩子,就這樣離開父母開始了住校的獨立生活。
在焉耆基地學校的宿舍是葦拱房,就是用椽子先搭成類似窯洞的半圓形,然后用蘆葦扎成的長長的葦把子挨個緊密地搭在椽子上,再在葦把子上糊上泥巴,就成了一個窯洞式的葦拱房。我們一到學校,老師就組織我們打土塊、砌火墻。火墻是北方的一種取暖設施,它由爐灶、火墻體和煙囪三部分構成。火墻體是用土塊砌成的空心曲回煙道,墻內可砌成豎洞、橫洞、獨洞、花洞等多種形式的煙道。熱煙氣通過火墻體向屋內散熱。煙囪是火墻的排煙通道,必須有足夠的高度,火墻的爐灶可以做飯。打火墻可是個技術活,爐灶、火墻和煙囪設計合理,爐火熊熊,屋內熱氣騰騰。如果設計不好,火墻燒不熱,還滿房子倒煙。這時才發(fā)現(xiàn)男同學是多么能干,他們也只有十三四歲,不僅能打出標準的土塊,還能砌成十分像樣的火墻。十三四歲的孩子,既要管好自己的生活如洗衣服等,還要幫助學校的食堂做事。食堂需要的煤炭都是我們一車車卸下來,食堂冬儲的大白菜,也是我們一棵棵卸下車,再一棵棵碼好。那時我是學生會主席,樣樣要帶頭。送煤車、送白菜的車半夜三更到,我立即起床招呼同學們卸車。卸完了,腰都快直不起來了。
但令人欣慰的是,和以前我們隨著建設部隊搬來搬去,沒有固定的學校,從來沒有按時開學相比,真是天壤之別了。現(xiàn)在學校有了固定校址,每學期都能按時開學,學校還組織了形式多樣的文體活動。最難忘的是我們的迎新年聯(lián)歡會和全校運動會。學校老師大都是上海、溫州知青,個個多才多藝,他們教我們唱歌、跳舞、排小品。逢年過節(jié),老師帶著我們用彩紙裝扮教室,做迎新年黑板報,班班都開聯(lián)歡會,擊鼓傳花,師生同樂,笑聲滿堂,十分開心。
我們也有了自己的土操場,開運動會之前,團里派了宣傳科的同志專門為我們畫宣傳畫。開幕式上,國旗隊、會標、彩旗隊、裁判員、運動員依次入場,我們邁著正步走過主席臺,無比興奮。運動會三天,操場上熱鬧非凡,加油聲、吶喊聲此起彼伏,同學們龍騰虎躍,你追我趕,創(chuàng)造了很多驚人紀錄。后來我們曾派代表隊參加了焉耆縣的中學生運動會,我們學校運動隊的成績遙遙領先。每每想起上個世紀70年代的這場運動會,我都覺得十分感動。我們的老師以他們在大上海的標準,在新疆邊遠偏僻的學校認認真真指導學生參加體育運動,讓健康、青春、激情、競技扎根在孩子們心底。它在我心里沒有任何缺憾,是屬于我們那一代人的“奧運會”。
1977年,國家恢復了高考。團里把平反了的“右派”選派到學校做老師。我們的數(shù)學老師是北京大學數(shù)學系的,物理老師是清華大學水利系的,化學老師是北京鋼鐵學院的,他們都是在上大學時被錯劃為“右派”的。雖然大學沒有畢業(yè),但他們的基本功扎實,特別是他們的教學態(tài)度令我們終身難忘,受益一生。在那個交通不便,信息閉塞的年代,我們除了教科書,什么復習資料也沒有。老師們千方百計地通過自己在內地大城市的同學、家人,找來復習資料,刻鋼板用油墨印刷,手工裝訂一本本復習資料送給我們每一個同學。有的老師因為刻鋼板把手磨出厚厚的老繭,有的老師裝訂時把手扎出血,卻不曾有半句怨言,只想著讓我們學到更多知識。
我們學校1978年有了第一屆高中畢業(yè)生,當年考取了2個本科大學生。我是1979年高中畢業(yè)的,當時我們12人參加高考,5人考取了本科院校,黃明奇同學以新疆數(shù)學第一名的成績考取了浙江大學,我和韓玲玲考取了石河子農(nóng)學院,金文同學考取了塔里木農(nóng)墾大學,馬金富同學考取了新疆工學院。
1979年是恢復高考的第三年。這一年,中國高考步入正軌:從這一年開始,高考試卷由1977、1978年各省、自治區(qū)分別出題改由教育部統(tǒng)一命題,并一直延續(xù)到2000年;從這一年開始,高考考生由歷屆生為主向以應屆高中畢業(yè)生為主過渡;從這一年開始,高考時間定為7月7日至9日,并一直延續(xù)到2003年;從這一年開始,高考模式穩(wěn)定在二十年以上,直到新千年。據(jù)馬國川、趙學勤所著《高考年輪》披露,1979年高考,洶涌如潮的報考大軍不亞于前兩屆,全國有近470萬人報考,六百多所高等學校共錄取新生27萬多人,錄取率為5.74%。然而,在我們這樣一個名不見經(jīng)傳的邊遠偏僻建筑單位的子弟學校,高考錄取率竟達到41.6%。這是一個驚人的成績。況且我們其他同學有的考入中專,有的參加工作后通過成人高考繼續(xù)學習,約有三分之一的同學后來也逐步取得大專學歷。雖然我們的學校一直在遷徙流動,但因為有了那些優(yōu)秀的老師,文化依然在荒漠戈壁中流動傳承,所以,我們雖生活在蠻荒之地,卻依然能脫穎而出。
上世紀八十年代,父母所在的單位決定在石河子紅山嘴建立基地,于是又在那里新建了學校。那時我已經(jīng)在石河子農(nóng)學院畢業(yè)留校工作了。有一回,我專程回去看望老師和學校,整整齊齊的校園,分成中學部和小學部,我十分開心,我們團終于有一所固定的、初具規(guī)模的學校了。但是,后來隨著企業(yè)改革的需要和社會的發(fā)展,企業(yè)把學校、醫(yī)院等社會事業(yè)交給了地方政府,學校逐漸萎縮,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不存在了。我們的子弟學校就這樣在“流動”中匯入社會發(fā)展的洪流之中,獲得另一種意義上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