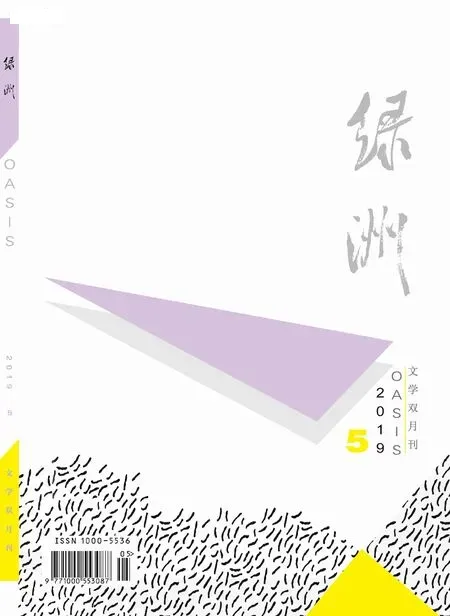祖國(guó)
汪惠仁
永興島
當(dāng)然是從海口出發(fā),飛一個(gè)小時(shí)的樣子,到永興島。飛機(jī)上,身邊坐著的是寧夏作家張學(xué)東。他的眼睛一直看著窗外,很明顯,南海碧波在他的心頭蕩漾。機(jī)艙里另外一些作家,有些來(lái)過(guò),對(duì)南海很熟悉,并且表現(xiàn)出扎實(shí)的初中地理功底,他們?yōu)槲乙灰恢v解正在被飛越的島礁。
上面是美好的藍(lán)天,下面是美好的南海,飛機(jī)渺小,在無(wú)垠的幽藍(lán)里飛行。飛行員一定知道,飛行員一定清晰地知道,在全球定位系統(tǒng)的幫助下,接下來(lái)如何操作,飛機(jī)將準(zhǔn)確降落在何處。我沒(méi)有見識(shí)過(guò)什么大世面,這無(wú)邊的美好,讓我感到虛脫。
沒(méi)有比永興島的機(jī)場(chǎng)更讓人感到親切的機(jī)場(chǎng)了:左邊是層層推進(jìn)的海浪,右邊是島民的生活小區(qū)。在這里得以停留何其幸運(yùn)——那天,飛機(jī)一落地,我就是這么想。可能無(wú)數(shù)人都這么想過(guò),旅人需要驛站,漂泊者需要港灣,迷航的船需要燈塔。從古到今,所有在南海有所經(jīng)歷的人都用直覺(jué)在證明,永興島是寶島。
法國(guó)人,日本人,還有越南人,都曾經(jīng)霸占過(guò)永興島。很多人都知道,日本人從永興島掠走了很多的鳥糞。而現(xiàn)在,永興島,牢牢地把握在我們的手里。漁民在這里做魚干的生意,從針鼻那么大的魚到枕頭那么大的魚,從我們經(jīng)驗(yàn)中的魚到有著怪獸般身形的魚,從透明的魚到顏色奇異妖冶的魚,漁民將它們晾干。每一種魚,在熱帶漁民的嘴里都有自己的小名,漁民們并不按生物學(xué)分類的中的學(xué)名來(lái)稱呼這些五顏六色的魚。
夜幕降臨,西沙賓館里的游客紛紛走出來(lái),這是熱帶島礁上的美妙時(shí)刻,凉風(fēng)習(xí)習(xí),濤聲陣陣,椰樹、羊角樹、美人蕉還有野棉花,在各自的高度,提供著各自的剪影。那些酷愛(ài)以鍛煉身體來(lái)對(duì)抗人生焦慮的朋友,今夜他們遠(yuǎn)離大陸,在南海的島礁上,散步或者奔跑,然后,借著路燈用手機(jī)通過(guò)社交平臺(tái)及時(shí)向世界發(fā)布他們的行走步數(shù)和奔跑里程——就在那天晚上,在島礁的路燈下,一個(gè)老干部沖著我喊,同志,在朋友圈怎么顯示我的位置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顯示此刻我的位置。我也想讓人們知道,我在一個(gè)遙遠(yuǎn)的地方。
石家莊
我和一個(gè)作家說(shuō),石家莊是中國(guó)最好的城市之一。他笑了。我懂他的意思。
我有一個(gè)愛(ài)好,替一些憨厚的城市說(shuō)好話。我并不是通過(guò)做學(xué)問(wèn),來(lái)下一個(gè)判斷曰好。我必須承認(rèn),幾乎就是意氣用事,直覺(jué)告訴我,此地在一線城市之外仍然在持續(xù)提供著獨(dú)立的意義,我就常常會(huì)脫口而出,好地方——夸張一點(diǎn),最好的地方。
在石家莊,得一天空閑,沒(méi)有目的亂逛。無(wú)論哪里,商場(chǎng)我都是不會(huì)去的,高樓的層數(shù)也無(wú)須我來(lái)數(shù),反正它們會(huì)越來(lái)越高。
往郊區(qū)走走吧。往滹沱河邊走走吧。于是就遇到了好些寺廟。我一向不愛(ài)進(jìn)寺廟。我當(dāng)然知道,各地的文旅產(chǎn)業(yè)沖動(dòng)中,寺廟獲得了空前地產(chǎn)與房產(chǎn),但我就是打不起興致進(jìn)去看看。但在石家莊的郊區(qū),在滹沱河的流域,我走進(jìn)了這些寺廟。
柏林禪寺,本是有來(lái)歷的老寺,但四十年前你若來(lái)過(guò),除了一座古塔,你只能看到一片廢墟。凈慧老和尚讓這所寺廟復(fù)活過(guò)來(lái)。在柏林寺的一段長(zhǎng)廊里,我匆匆瀏覽凈慧老和尚修行歷程。在生命的最后時(shí)刻,他顯示了六祖惠能那樣的儀態(tài),其戒其定其慧,總歸于最后一句阿彌陀佛。十幾歲離開故鄉(xiāng)故人,六十多年之后,何處不是老和尚的故鄉(xiāng),何人不是老和尚的故人。正是中午齋飯時(shí)候,風(fēng)里有鐘聲傳來(lái),一行年輕僧人托缽而過(guò)。
隆興寺。我驚詫于它的恢宏,更驚詫于它的完善。如果說(shuō)柏樹為柏林寺塑造了獨(dú)特氣質(zhì),那么,隆興寺的道場(chǎng)氛圍則從隨處可見的古槐中散發(fā)出來(lái)。一千年前,這些槐樹就在這里。一千年后,高速交通把我?guī)У搅诉@里,它們,這些槐樹,仍然活著。我看到,有槐花旋轉(zhuǎn)著飄落,而這一千年里,它年年飄落。這里是好幾個(gè)朝代的皇家寺院,有金之木刻、宋之筑金、唐之碑刻,其間風(fēng)波,槐樹最為知道。
回程路上,又見數(shù)塔。其敦厚穩(wěn)健者,雁塔也,在開元寺。其清秀玲瓏者,澄靈塔,八角九級(jí)密檐樣式,在臨濟(jì)寺,傳塔藏義玄禪師衣缽。此二院,未進(jìn),留他日再訪。
日頭欲落大荒中,滹沱在側(cè),河水滔滔,我是多么地想見識(shí)滹沱河邊當(dāng)年一幕啊——機(jī)鋒凌厲,棒喝峻烈。
四姑娘山
從四姑娘山下來(lái)的時(shí)候,實(shí)在累得走不動(dòng)了,就要了一匹馬來(lái)騎。剛下過(guò)雪,又出了太陽(yáng),原始森林豐厚的腐殖層變得泥濘難行,以至馬數(shù)度趑趄不前。為我牽馬的人很特別。同行的別的牽馬人滿身泥漿,我的牽馬人,她卻那么的特別,連鞋子都是干凈的。她在云杉林間的石頭上跳躍,她有能力選擇出一條潔凈的路。沙棘樹出現(xiàn)了,山勢(shì)慢慢變得平緩。這是一匹愛(ài)清潔的馬啊,它看見了溪流,忍不住要洗去蹄上的泥污。馬奔脫了韁繩。“不要害怕。”牽馬姑娘沖我喊道,“我的馬很溫順的,就是愛(ài)干凈而已。”“知道,和你一樣。”我沖她笑。就這樣邊走邊聊,我知道了更多關(guān)于她的故事。她上過(guò)大學(xué)。后來(lái)父親去世,妹妹年幼,弟弟在一次意外中被馬踢瞎了雙眼。為了母親,她決定退學(xué)。她叫楊興茂。她說(shuō):“父親愛(ài)看書,有好多的漢族朋友。我的名字就是他的漢族朋友給取的。”我說(shuō):“這是個(gè)男孩子的名字啊。”她回答:“我從小就是像男孩子一樣的性格。”事實(shí)上,直到她提醒了很多遍讓我下馬,我才意識(shí)到自己已經(jīng)回到了山下。她并不知道我在想,想她有著給作家們上一課的資格——她沒(méi)有把自己埋藏在靜態(tài)的悲苦之中。“和當(dāng)初相比,你覺(jué)得你走出來(lái)了嗎?”我問(wèn)她。“好多了。眼下我得先幫弟弟完成盲人按摩的學(xué)業(yè)。”不知道她的藏文名字是什么,一定是個(gè)一經(jīng)說(shuō)出便如同天啟的詞吧。
貴州
前段時(shí)間,在讀者反饋意見調(diào)研中,我的同事發(fā)現(xiàn)了一位特別讀者。他是我們的一本長(zhǎng)篇小說(shuō)《海邊春秋》的讀者。
同事給我拿來(lái)了這位特別讀者的點(diǎn)評(píng)本《海邊春秋》。圈圈點(diǎn)點(diǎn),天頭地腳寫滿了心得體會(huì),不同深度、強(qiáng)度與熱度的批語(yǔ),這位特別讀者動(dòng)用了不同的顏色與字體——在激賞的地方,他甚至特別為此刻印加蓋。
后來(lái)我和這位特別讀者見面了,他是高校的老師,正做著下鄉(xiāng)幫扶的干部。關(guān)于農(nóng)村,關(guān)于幫扶,我們聊了很長(zhǎng)時(shí)間。天黑下來(lái),我留他吃晚飯,他說(shuō)不行,還得趕回薊州的山里。
我記住了他的一些話,因?yàn)槭钦嫘脑挘矣涀×恕N覇?wèn)他,有必要下鄉(xiāng)幫扶嗎?他說(shuō),太有必要了,應(yīng)該早做。我問(wèn)他,幫扶以來(lái),對(duì)你自己而言,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他說(shuō),現(xiàn)在每一次回到市里,就覺(jué)得原來(lái)自己為一些事生氣啊想不通啊,都沒(méi)有必要,心太小了,現(xiàn)在的全部注意力就在解決一個(gè)一個(gè)困難上。
四月中旬,我來(lái)到黔東南的大山深處,遇到了更多下鄉(xiāng)的幫扶人士。在市、縣、鄉(xiāng)、村之間,幫扶人士來(lái)回奔波,他們像我先前遇到的那位特別的讀者一樣,熱烈而沉著,疲憊而沒(méi)有怨言。
扶貧,脫貧,要求是一戶也不落下。莽莽青山里藏著這樣了不起的意志。
在雷山的村莊,我看到一張張登記表,記錄著所有貧困人員的姓名、脫貧路徑以及解決進(jìn)度。看著這些登記表,我想起王陽(yáng)明曾經(jīng)給學(xué)生這樣解釋他的知行觀:只在嘴上講孝敬而行為里沒(méi)有孝敬的人,這只能說(shuō)明他既沒(méi)有孝之行也不懂孝之知。同樣,在綜合國(guó)力顯著提升的今天,我們?nèi)绻€在空談對(duì)人民的愛(ài),是過(guò)不去知行合一這道關(guān)口的。必須切實(shí)行動(dòng)起來(lái),只有行動(dòng)起來(lái),在行動(dòng)中培植愛(ài)之“知”,“致良知”的愿景才有可能在知行合一中漸漸實(shí)現(xiàn)。在貴州,在黔東南的莽莽青山里,這支“行”的隊(duì)伍在不斷壯大,覺(jué)醒的貧困戶加入進(jìn)來(lái)了,省市的公職人員加入進(jìn)來(lái)了,縣鄉(xiāng)村三級(jí)專職的幫扶機(jī)構(gòu)與人員加入進(jìn)來(lái)了,在外地獲得良好發(fā)展、現(xiàn)在心懷感恩反哺故鄉(xiāng)的游子加入進(jìn)來(lái)了,剛剛走出大學(xué)校園的青年加入進(jìn)來(lái)了。
還有一些特殊的社會(huì)力量也加入進(jìn)來(lái)了——在臺(tái)江縣一座苗寨的食用菌培育大棚外,我碰到了平安產(chǎn)險(xiǎn)的幾個(gè)業(yè)務(wù)經(jīng)理,毫無(wú)疑問(wèn),他們身上自然也透著金融保險(xiǎn)行業(yè)所給予的工作風(fēng)范,精明高效,操著流利的業(yè)務(wù)“貫口”;但在食用菌散發(fā)的特殊的馨香中,在莽莽青山無(wú)意供出的秀色里,我還是在這幾個(gè)業(yè)務(wù)經(jīng)理的身上感受到了另外氣質(zhì)。在這個(gè)項(xiàng)目上,平安產(chǎn)險(xiǎn)沒(méi)有追求獲利,來(lái)到大山深處,他們只想擔(dān)起一份責(zé)任,擔(dān)起這些厚道的山里人無(wú)法承受的在生產(chǎn)經(jīng)營(yíng)環(huán)節(jié)可能會(huì)出現(xiàn)的種種風(fēng)險(xiǎn)。大棚里培育的食用菌是我之前沒(méi)有見過(guò)的一種,灰色的,像絨花,層層疊疊,很美,叫灰樹花。大棚外面有簡(jiǎn)易的烹調(diào)設(shè)備,客戶是可以品嘗的,但當(dāng)日行程太匆匆,我沒(méi)有來(lái)得及品嘗——我悄悄摘了一小朵,做個(gè)紀(jì)念吧,對(duì)莽莽青山里的人來(lái)說(shuō),對(duì)參與幫扶的社會(huì)力量來(lái)說(shuō),對(duì)我自己來(lái)說(shuō),灰樹花完全可以擁有另一個(gè)名字,覺(jué)悟之花。
二十三年前,在我剛剛進(jìn)入出版行業(yè)做圖書發(fā)行員的時(shí)候,我到過(guò)貴州。你可以想象當(dāng)時(shí)的情景,一個(gè)涉世未深毫無(wú)工作經(jīng)驗(yàn)的長(zhǎng)發(fā)詩(shī)人,一路散發(fā)新出的樣書催收未結(jié)的賬款,所有的書店都在告訴他,這個(gè)春天雨水太大,書被泡壞了,沒(méi)辦法結(jié)賬。就這樣,沒(méi)有錦囊妙計(jì),沒(méi)有任何收獲,我從南京到上海到福州到桂林,最后來(lái)到貴陽(yáng)。記得到貴陽(yáng)是夜里了,疲憊不堪,我拖著裝樣書的大箱子,隨意坐到了一個(gè)夜食攤前。后來(lái)知道,那個(gè)夜里,我吃的是腸旺面。酸、辣,吃出了幻覺(jué),在職場(chǎng)生涯中,這是一碗關(guān)鍵性的面條,它讓我吃出了遵義式的轉(zhuǎn)折感。
二十三年后,我再次來(lái)到貴州。從貴州,我?guī)Щ亓艘欢溆X(jué)悟之花。
秦巴
已經(jīng)有很長(zhǎng)時(shí)間了,我懶得看山看水。
山水,河山,江山,這三個(gè)詞,我也沒(méi)有興趣去厘清它們的來(lái)由與歸宿。
我記得故地的好山水的樣子。并且,我知道,世上有很多的好山水。但我不想在更多的地方拍照留念。見識(shí)過(guò)雍容,領(lǐng)略過(guò)深刻,體會(huì)過(guò)仁慈,這就夠了,再做加法,人生就會(huì)很累——秦嶺、巴山卻讓我看見自己是如此的傲慢。
從西安往南——用此地作家群體的話,就是從長(zhǎng)安往南——時(shí)間并不太長(zhǎng),就進(jìn)入了秦嶺。車子在丙申年秦嶺的秋色里奔馳,終于停在服務(wù)區(qū)。半百的年紀(jì),走在高速公路上,心里總想著快到服務(wù)區(qū)啊快到服務(wù)區(qū)。除了那什么,抽支煙,也都是賦予旅途節(jié)奏感的好手段。海拔已經(jīng)不低了,又正是微雨時(shí)候,煙云在周圍斑斕的林木間游走。
走出洗手間,身體在松弛里打著激靈,我看見服務(wù)區(qū)的空地上聚集了不少人,他們和我一樣,在清凉的空氣里妄圖延續(xù)剛剛獲得的幸福狀態(tài)。一只小狗在人群里來(lái)回穿梭,主人把它洗得很干凈,一身潔白,它似乎也懂得珍惜這片刻的珍貴時(shí)光,它撒著歡,像一只鹿或者一只兔,快上車了,它還在貪戀這泥淖里的溫情,挑逗著主人追趕。
是的,還得接著趕路。我們還要穿過(guò)眼前的一個(gè)隧道,朝著漢中的方向走。
王瀟然用低沉的播音腔莊重地告訴我,穿過(guò)這個(gè)隧道,我們將進(jìn)入另一水系——漢江水系。瀟然兄是老朋友了,他一直是誠(chéng)懇而莊重的。從他那里,我得到的知識(shí),都伴隨著莊重的儀式。比方說(shuō),關(guān)于秦嶺羚牛,他會(huì)說(shuō),這種大型牛科食草動(dòng)物。他一點(diǎn)也不做作,他喜歡追根溯源,他說(shuō),這種大型牛科食草動(dòng)物,在阿爾卑斯山早就絕跡了。
我們要去的,是黎坪。
已經(jīng)是大巴山里的地方了。
若以唐之長(zhǎng)安作為讀書人實(shí)現(xiàn)人生價(jià)值的中心地帶,那么,我們會(huì)發(fā)現(xiàn),長(zhǎng)安到秦嶺終南山是做隱士的合適距離,而從大巴山到長(zhǎng)安——至少,在古人那里,真的可以稱為漫漫長(zhǎng)路了——這樣的距離,恐怕只適合生發(fā)思念了。從長(zhǎng)安到終南山并不遠(yuǎn),仕途不順了,來(lái)此散散心,很方便的。終南山的合適位置,得消息觀政局也不難,窺探心在這里死不了,機(jī)會(huì)來(lái)了,正能量又會(huì)重新爆表。巴山就不一樣了,它真的遠(yuǎn)了,遠(yuǎn)到你必須對(duì)自己的情感刪繁就簡(jiǎn),遠(yuǎn)到你這只蜜蜂只能在這朵花上舞蹈——思念,雖然它苦而無(wú)藥——何當(dāng)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shí)。當(dāng)年蘇東坡到海南,也是這樣啊,有什么辦法呢,說(shuō)其他的還有什么用呢,隔著大海,呆呆望著大陸,思念只能寄托在海天之際,“青山一發(fā)是中原”。
克敬告訴我,現(xiàn)在終南山里還有著萬(wàn)余隱居者。他補(bǔ)充道,高學(xué)歷的居多。
這應(yīng)該是專業(yè)的繪畫人士喜歡的地方。黎坪之風(fēng)物氣候,恰在中國(guó)南北的分界線上,品類殊盛,尤其在這秋天的時(shí)節(jié)。霧靄、流泉在滋養(yǎng)著黎坪的秋山,但即便如此,黎坪又從它的內(nèi)里散發(fā)出不被“南方”定義的氣質(zhì),它的骨力,它的烈度,的確還是北方的。
記得好多年前,到延安去,半道上餓了,穆濤兄帶著我們摸進(jìn)了一戶農(nóng)家(那時(shí)還沒(méi)有農(nóng)家樂(lè)的說(shuō)法),殺了一只羊。我到院子里去看,只是一鍋羊肉加水,大火煮著,現(xiàn)在回憶起來(lái),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我當(dāng)時(shí)比現(xiàn)在更像個(gè)書生,我站在院子里怯怯地問(wèn),難——道——不——烹——調(diào)——了么?滿院子的北方人都給我投來(lái)奇異的目光。
后來(lái)知道,我所謂的烹調(diào),是能毀掉一鍋好肉的,人家的修辭就是為骨力和烈度服務(wù)的。這里仍然是陜西,只不過(guò)黎坪及大巴山讓陜西變得闊大而豐富。在羊肉泡饃、腰鼓、信天游、窯洞、華陰老腔之外,從秦嶺往南,還有更多的陜西。每一種“更多”,巴渝口音、麻辣食譜、漢江水系,我想,這些都是上天賜給陜西的福利。
回到天津,有些時(shí)候了,還經(jīng)常想起黎坪。黎坪的紅葉谷,甚至能入我的夢(mèng)里,霜露繁重,山紅澗碧,爛漫無(wú)涯。
嶺南
西關(guān)
在廣州西關(guān),只是很短的時(shí)間,不算晚餐的話可能不超過(guò)一個(gè)小時(shí)。
所以,我沒(méi)有跟隨導(dǎo)游——雖然那是一個(gè)漂亮的女導(dǎo)游,在之后的行程中,她不再陪同我們卻被我們屢屢談起。
我把這一個(gè)小時(shí)全部用在一處老宅的書房里。
書房在老宅的東南角落,高大而寬敞。透天的半開放的設(shè)計(jì),讓書房連接著院廊。沿院廊的墻角,生長(zhǎng)著青草、翠竹和芭蕉。
這是一個(gè)很大的宅子,我只愿意在它的這間書房里發(fā)呆。我不知道它的來(lái)歷,也不愿多想它在沸騰的生活中今后的去向。
我只是覺(jué)得,在此處,我可以問(wèn)一問(wèn)自己:你是不是也有這樣一個(gè)夢(mèng)?偏安一隅,磚雕的花窗和亮瓦卻不遮蔽天光,而那透天的設(shè)計(jì),本來(lái)就是留給風(fēng)和雨的。
沙灣
這鎮(zhèn)子很安靜,讓我震驚。
干凈的巷子里,釘在墻上的鐵牌標(biāo)注著怪異的名稱。
很多家庭仍然在沿用祖屋,他們用蠔殼來(lái)裝飾自己的庭院。
集市上也不喧鬧,蔬菜和中藥材最是常見。
這些是什么,是吃的么。我指著一大堆樹枝樹皮似乎還有一大堆花瓣問(wèn)攤主。
攤主是個(gè)瘦小的中年男人,但他的嗓音里飽含著精氣。他說(shuō),煲湯!他的普通話沒(méi)有包裹住粵語(yǔ)發(fā)自內(nèi)部的光焰。
我喜歡廣東人說(shuō)普通話時(shí)的那股子“掙扎”的勁頭——我把他們的廣普式的發(fā)音稱為嶺南呼麥。
“大補(bǔ)!”
他見我沒(méi)有買的意思,他用嶺南呼麥強(qiáng)調(diào)道:“大補(bǔ)!”
我沖他笑笑,說(shuō),我一會(huì)兒就喝湯去,我確實(shí)需要大補(bǔ)一下。
陳宅
陳慈黌的宅子。
這無(wú)疑也是深宅大院。經(jīng)年近百,青苔從屋基向上蔓延。大面積的墻皮已經(jīng)剝落。
但它顯然不同于我以前見過(guò)的散落在祖國(guó)各處的老宅。
它不是陰郁而森嚴(yán)的,它至今奇跡般地還在散發(fā)著青春氣息。
它的瓷板,首先引起了我的注意:每一個(gè)房間,每一個(gè)窗臺(tái),每一個(gè)門頭,都鑲嵌著不同樣式的瓷板,所施皆是西洋顏料。這不是傳統(tǒng)土豪的審美趣味。它的趣味里充滿陽(yáng)光。
我承認(rèn),好的陽(yáng)光會(huì)增加我對(duì)這個(gè)老宅的好感。但,另一面,我不得不說(shuō),是這個(gè)宅子,讓我對(duì)陽(yáng)光金子般的質(zhì)地有了深切的體會(huì)。陳宅的一切,仿佛就是為了相互輝映,以回報(bào)陽(yáng)光的照耀。
陳慈黌故居里的陽(yáng)光,是我見過(guò)的最好的陽(yáng)光。
在陳宅的大院子里,我把手機(jī)遞給身邊的朋友,請(qǐng)他給我拍照——我很少有這么明朗的時(shí)刻。
海柳
我僅僅想說(shuō)海柳煙斗。
在參觀南澳島大帥府之后,回賓館的路上,我看到徐貴祥先生叼著海柳煙斗。他是一個(gè)有著威儀的軍人,再叼著煙斗,那是一個(gè)什么陣勢(shì)!
我向來(lái)認(rèn)為,合格的煙民是應(yīng)該武裝到煙斗的。
我不太關(guān)心海柳傳說(shuō)中的藥用價(jià)值,我只喜歡它的枝枝丫丫、它的烏亮、它的幽幽的凉意、它暗藏的金絲紋理以及它微微的壓手的感覺(jué)。海柳是天生的做煙斗的好材料。
但我居然錯(cuò)過(guò)了南澳島的海柳煙斗。離開南澳島的那天清晨,我起得很早,我沿著海岸線看了幾十家海柳店鋪,沒(méi)有一家開門。是啊,在美麗的南澳島,人們貪戀睡眠是再正常不過(guò)的事了。
是劉兆林先生看出了我的心思。他從口袋里拿出了昨晚買來(lái)的海柳煙斗。我說(shuō),這個(gè)比徐先生那個(gè)還要好啊。他說(shuō),那你拿走吧。
天底下還有這樣的好人。
惠山
運(yùn)河
運(yùn)河仍然在使用,它仍然活著。仲春的晨霧彌漫在河面,那顯然不是霾,盡管它阻礙了我的視線,但我仍然能確認(rèn)它是干凈的水汽,我能聞到櫻花的味道。
早晨,在運(yùn)河邊走路的人不多。這是我喜歡的。你要知道,在很多的沿河地帶,在日常里最適合散步和思考的時(shí)段,中國(guó)大媽會(huì)帶著她們的擴(kuò)音設(shè)備播放著《鳳凰傳奇》和《小蘋果》,她們沉浸在某種氣場(chǎng)中不能自拔,她們爭(zhēng)奇斗艷,她們甚至背著腰鼓,她們整齊地打開折扇——聲如裂帛。
但我真的喜歡這個(gè)早晨,這個(gè)安靜的惠山的運(yùn)河邊的早晨。偶爾有大的貨船穿過(guò),鳴笛,霧氣翻滾。黑色的船體移動(dòng)緩慢,緩慢得像民國(guó)的某個(gè)場(chǎng)景。
半日
霧氣散去,上午就往寄暢園走。從入街的牌坊開始,行人的密度猛然變大,我仿佛鉆進(jìn)了一個(gè)由無(wú)錫話編織的口袋。我大致能聽懂他們的實(shí)詞部分,也就是和普通話大概率重疊的那一部分,但這是他們的符號(hào)世界,他們的嘆詞和粘著詞匯如此豐富,如春花爛漫。導(dǎo)游很辛苦,在這條街上,她要不停地照顧我們這些只會(huì)用普通話思考的語(yǔ)言上的旱鴨子,她在兩個(gè)符號(hào)世界里來(lái)回穿梭——她時(shí)而與鄉(xiāng)黨呢噥,時(shí)而又轉(zhuǎn)過(guò)身來(lái)用“祖國(guó)新貌”式的播音體和我們交流。走在這樣的一條街上,我想起了故鄉(xiāng)的方言,雖然那是和普通話關(guān)系親密的江淮官話,但它也有動(dòng)人的富有感染力的細(xì)節(jié),但現(xiàn)在,我?guī)缀跻阉恕?/p>
從運(yùn)河辟有專門的水道與這條街相通。以碼頭為中心,兩岸商戶林立。此外,清末至民國(guó)建成的大戶宗祠一家連著一家。用青磚或者石材筑成的西式洋房不少,更多的,自然還是白墻木穿枋結(jié)構(gòu)的南方民居——這是我記憶里南方的房子。我站在碼頭想象,如果還有石條的街道,還有青苔從下水道爬出,還有迷宮一樣的巷子,如果還有暗綠的池塘,如果池堤上種滿楊柳和香樟……這一條街走下來(lái),我知道,這不是想象,種種假設(shè)都一一在此地呈現(xiàn)。并且,在一個(gè)巷子的拐角,我看見一個(gè)婦人,她從老宅二樓的窗戶探頭張望,她姣好的面容暴露在強(qiáng)烈的陽(yáng)光下,而她身體的其他部分則完全隱沒(méi)在老宅內(nèi)部濃重的黑暗里。
耳得之為聲,目遇之成色。內(nèi)外兼修如蘇子者才有能力隨處體味造物者之無(wú)盡藏,我們沒(méi)有這樣的能力。我們必須要感謝古代的那些園林工程師,他們務(wù)實(shí)地把美分解為一個(gè)又一個(gè)知識(shí)單元教給我們,他們講幽僻的妙處,他們講房舍圍墻與樹藤的搭配,他們講如何把窗戶化成景物的鏡框,他們講如何借用園外遠(yuǎn)山之峰嵐又如何導(dǎo)入溪流以成八音和諧。
寄暢園就是這樣一個(gè)園林美學(xué)的教材。
也許,太奢侈了,走遍寄暢園后,我們還占據(jù)了園子里最宜觀景的亭:耳畔泉聲淙淙,眼前老樹臥波。
這是一個(gè)可以為寄暢園和中國(guó)園林的美學(xué)做總結(jié)的亭子。在我們接觸一個(gè)又一個(gè)美的角落之后,我們坐到這個(gè)亭子里,最應(yīng)該做的,就是靜靜地體會(huì)一下什么樣的內(nèi)在邏輯與氣息把這些角落貫穿起來(lái)。那可能是一種高遠(yuǎn)的自然主義的生活理想:雖為人做,宛自天開。
金先生是這園子的管家,也是這園子里的學(xué)者。我在寄暢園的這半日,主要是聽他的講解。他的嚴(yán)謹(jǐn),他的對(duì)惠山文史的深情,給了我太深的印象。幾乎關(guān)于惠山的知識(shí),只要你問(wèn)得出來(lái),都可以從他那里得到解答,并且是完整得不帶任何臆想臆斷的解答。我在寄暢園的亭子里,喝著太湖翠竹茶,聽金先生講園子里的故事,從秦觀的宋朝一直講到人民的當(dāng)代。這園子原先也只是一簡(jiǎn)樸山居,養(yǎng)個(gè)閑情逸致而已;不想,經(jīng)秦氏家族在漫長(zhǎng)時(shí)光里精心、接力般地維護(hù)和擴(kuò)建,舊家積德,小筑終成美廬。
“乾隆爺太愛(ài)這個(gè)園子了,回北京就仿制了一個(gè)。”金先生的眼睛本來(lái)就大,說(shuō)到此處,他把眼睛睜得更大了。他的手向園子外指去,他說(shuō),“就是那個(gè)碼頭,乾隆爺就是在那兒下的船。”
我見過(guò)不少私家園林,在一個(gè)家族內(nèi)部傳承如此有序的,似乎只有寄暢園。但它依然和其他古典的私家園林一樣,并沒(méi)有逃脫在那個(gè)特定時(shí)刻“斷代”的命運(yùn)。聽著金先生的講述,我恍惚覺(jué)得,我們坐在那里喝茶的亭子并不是在一個(gè)園林里,它向上飄浮,飄浮,它好像落在了一處斷崖上。
這樣的亭子,連同這樣的園子,還幸存在文化的斷崖上。
并且,我們還在這樣的斷崖上,泡茶——用陸羽的時(shí)代就公認(rèn)的天下第二泉來(lái)泡茶。原先我們僅僅知道一騎紅塵里藏著從廣東運(yùn)給楊貴妃吃的荔枝,而現(xiàn)在,我們還知道,在那個(gè)年代,從同樣遙遠(yuǎn)的惠山,吳地的人們把最好的泉水送往長(zhǎng)安。茶之妙味,植物的根性除外,水是頂頂重要的,所謂“山水第一江水其次”,而惠山石泉又是山水中的極品。所以,蘇軾說(shuō)啊,獨(dú)攜天上小團(tuán)月,來(lái)試人間第二泉。
有一個(gè)問(wèn)題,金先生他是否姓金。我不敢肯定,對(duì)一個(gè)學(xué)問(wèn)家,我真的不好意思當(dāng)面追問(wèn)他到底姓什么。我只是聽得他的一個(gè)學(xué)生輩的女同事柔聲地喚了聲,金老師。
另一個(gè)半日
后來(lái)去的是杜鵑園。我養(yǎng)過(guò)杜鵑。在杜鵑園,我卻變成了一個(gè)白癡——在惠山的杜鵑園,我才無(wú)比清晰地看見那個(gè)在天津的屋子里號(hào)稱養(yǎng)過(guò)杜鵑的“我”,除了給杜鵑澆水拍微信照片,我?guī)缀跏且粋€(gè)和杜鵑沒(méi)有內(nèi)在聯(lián)系的人。在這個(gè)春天的杜鵑園,我第一次見識(shí)“萬(wàn)朵互低昂”是怎樣一幅圖景,我第一次見識(shí)“一園紅艷醉坡陀”是怎樣一幅圖景。
生命力在杜鵑園發(fā)出了集體的尖叫。
我和朋友們都似乎體會(huì)到了某種壓迫感,生命力的極度張揚(yáng)有時(shí)會(huì)引起我們極端的情緒。當(dāng)我們回到休息室,我看到幾乎每個(gè)人都癱軟在沙發(fā)上。我們有氣無(wú)力地談?wù)撃莻€(gè)盲人音樂(lè)家,談?wù)撃莻€(gè)圍棋高手,談?wù)摽蓯?ài)的阿福。
南方
很多年來(lái),我認(rèn)為自己已經(jīng)是完全的北方人。在新蒜上市的時(shí)節(jié),我已經(jīng)習(xí)慣一邊咬著新蒜一邊吃著炸醬面或者打鹵面——在我的廚房里,我樂(lè)意做的事情是,細(xì)細(xì)地切那些拌面的配菜。我也習(xí)慣了滄州以北的干枯荒凉的景色。我覺(jué)得,我有點(diǎn)熱愛(ài)北方了,我希望自己不斷地進(jìn)入北方的深處,比如那些草原和戈壁。但是,這僅僅一天的惠山,它讓我身體里的南方再次蘇醒。
惠山是南方,比我的故鄉(xiāng)安徽更像南方,甚至,它比很多緯度更低的地方更像南方。
只有能夠提供“南方意義”的地方才是南方。
太湖
丁酉谷雨,路過(guò)太湖。
沒(méi)有細(xì)看的時(shí)間,我對(duì)司機(jī)說(shuō),就沿著湖邊的公路,兜兜風(fēng)吧。
我們?cè)谔K州的這一側(cè),停停走走。
午后的氣溫升的很快,水汽蒸騰,太湖渺無(wú)邊際,湖中島嶼、峰巒若隔世影像隱約浮在眼前。怪不得皮日休為太湖寫下了那么多詩(shī)。人生如此逼仄,誰(shuí)不稀罕放曠之境?便是俗鄙如我,此刻也希望被一葉扁舟馱著,向那湖心蕩去。
在湖邊,你會(huì)明白,美景廢黜一顆經(jīng)綸之心是多么簡(jiǎn)單的事。陶弘景雖然是南京人,但我總覺(jué)得,他有著這湖邊的精神。他是真心不出山的“山中宰相”,為朋友出幾條治國(guó)主意不難,難在一朝醒悟便不與世交,難在他的注意力真的在這地上的植物那里。所以皮日休們常有一種幻想,在太湖,臥聽舟底濤聲,隨風(fēng)吹向神仙府,在那里,逢著陶弘景。
湖邊的故事不必非得追蹤到春秋戰(zhàn)國(guó)。那天我就把自己當(dāng)作第一個(gè)見識(shí)太湖的人,我用簡(jiǎn)陋的手機(jī)拍了好些照片,直到電池報(bào)警。湖山之怡林泉之致豈是幾張圖片所能載得動(dòng)的?于是干脆又把照片全部刪掉——有五分鐘,我騰空記憶,前世渾沌來(lái)世迷離,就當(dāng)此刻人與湖第一次相對(duì)。傳說(shuō)、戲劇、詩(shī),還有那首腔調(diào)軟糯的“太湖美”,都必須在此刻擱置——這樣,我才會(huì)獨(dú)立蒼茫,然后被太湖的意志吞沒(méi)。
我覺(jué)得一切再明白不過(guò)了。太湖意志,吞沒(méi)了感染了古往今來(lái)的湖邊人。
太湖意志,最終以太湖美學(xué)的面目影響了湖邊的香山營(yíng)造。如果看過(guò)蘇州城里的那些園子,你一定會(huì)生出“此處確與他處不同”的感喟。
這就是蘇工。這就是營(yíng)造之心。
從湖山泉林之境到日常用具之微末,大含細(xì)入,全程營(yíng)造。
吾國(guó)核雕看蘇州,蘇州核雕看舟山。
于是去訪湖邊的舟山村。村中有手工藝者數(shù)百,一個(gè)把營(yíng)造心思凝于果核的村子。
隨意走進(jìn)兩戶人家。
普通游客如果沒(méi)有向?qū)У闹敢茈y走到夏棟的工作室。三間老房子略加修葺,一間陳列、一間操作、一間會(huì)客。在我見過(guò)的核雕藝人里,他是留長(zhǎng)發(fā)的唯一的人。三十六歲,但很顯然,他的眼神有些疲憊。核雕是精細(xì)累人的事情。可能我們知道地?cái)偵嫌写蟀汛蟀蚜畠r(jià)核雕手串——舟山村不是這些產(chǎn)品的生產(chǎn)地,舟山的藝人在堅(jiān)持手工雕刻,并且,他們不放過(guò)對(duì)每一枚果核的質(zhì)量要求。在舟山村,核雕的普通效率是這樣的,一件構(gòu)圖和刀法比較復(fù)雜的核雕,工時(shí)大約在兩周。
這個(gè)年輕的“老藝人”從十六歲開始從事核雕,十八歲那年,他準(zhǔn)備放棄,表姐對(duì)他說(shuō):“其實(shí)你刻得蠻好的來(lái)。”這一聲鼓勵(lì),讓他一直刻到現(xiàn)在。
夏棟的核雕工作臺(tái)上,擺滿了各種雕刀,刀柄被磨得烏亮,為了增強(qiáng)拿捏的控制感,一些雕刀的柄上纏著細(xì)密的麻繩。二十年的雕刻生涯一晃而過(guò)。
夏棟說(shuō),佛頭啊觀音啊彌勒啊,其實(shí)我不愿意將他們做成手串的,在手里捏呀捏的,我總以為這不恭敬。
帥道富的工作室靠近村口。他見到我的時(shí)候,略微有點(diǎn)緊張——以為拉廣告的來(lái)了,他喃喃問(wèn)道,怎么收費(fèi)?我說(shuō),就是聊聊天。
于是我們都松弛下來(lái),這是碧螺春的好時(shí)節(jié),邊喝邊聊。
道富是江西人,二十多年前招工入的核雕行。現(xiàn)在雖已經(jīng)名列大師譜系,道富處世的謹(jǐn)慎還是讓人一眼便可識(shí)出。
畢竟是異鄉(xiāng)人。
開始很難,在上海擺地?cái)偅钡绞昵安庞X(jué)得有奔頭。他說(shuō)。
道富講:“我經(jīng)歷過(guò)核雕無(wú)人問(wèn)津的時(shí)候,正是在這樣的時(shí)候,我看到舟山村的老藝人還在雕刻,每完成一件,他們就把這一件默默地放進(jìn)柜子里。這是讓我感動(dòng)的地方,我現(xiàn)在也成為他們中的一員。”
生意經(jīng)的盡頭就不是生意經(jīng)了。交換價(jià)值之外還有另一種價(jià)值。
歸途又路過(guò)太湖。
這一次是故意路過(guò),通往高鐵站的路有很多,我愿意帶著營(yíng)造的心意,再次路過(guò)這個(gè)大湖。
天津人民公園
十月的假期沒(méi)有出遠(yuǎn)門,但總得轉(zhuǎn)轉(zhuǎn)吧,我去了人民公園。我來(lái)天津三十年了,第一次到人民公園。人民公園的灰色花磚圍墻我并不陌生,常常騎車路過(guò)時(shí)我會(huì)放慢一點(diǎn)腳踏的節(jié)奏,看看從墻頭逸出身來(lái)的植物,或者聽聽?wèi)騽∑庇褌兊跎ぷ拥募庖簟?/p>
從公園大門進(jìn)去,才幾步,就想笑出聲來(lái)。
記起蕭紅回憶魯迅先生說(shuō)公園的那個(gè)片段了,魯迅先生這么說(shuō):“公園的樣子我知道的……一進(jìn)門分做兩條路,一條通左邊,一條通右邊,沿著路種著點(diǎn)柳樹什么的,樹下擺著幾張長(zhǎng)椅子,再遠(yuǎn)一點(diǎn)有個(gè)水池子。”當(dāng)我站在左右兩條路中間試圖選擇行走路線時(shí),真的想笑——事實(shí)上,此時(shí),我向右邊略微張望了一眼,僅僅此一眼,真的就看見了那個(gè)水池子。于是點(diǎn)起一支煙,在樹下擺著的長(zhǎng)椅上坐下,我小聲用紹興口音模仿大先生說(shuō)這段話時(shí)可能的樣子。
笑的原因,乃是因?yàn)檠矍爸安坏叭绱恕保摇肮蝗绱恕薄Uf(shuō)話之難,難在你要說(shuō)的別人已經(jīng)說(shuō)得很好了,而那些明明在那里的事情我們卻無(wú)力道破。
如此,文章若能揭示“如此”,若能指給世人看,我眼里世界是這樣的,已經(jīng)是好文章了;果然如此,則又遞進(jìn)了一層,我們不要誤以為這僅僅是文學(xué)閱讀之接受美學(xué)里的事,它對(duì)言說(shuō)者本身就暗含著要求,它要求:言說(shuō)者既在“如此”的結(jié)構(gòu)之中又在“如此”的結(jié)構(gòu)之外——我想,那才是不用發(fā)出嚎叫聲的真正的解構(gòu)。
不知解構(gòu)者,以為解構(gòu)就是顛覆。知解構(gòu)者,當(dāng)知解構(gòu)亦是為了致良知。
梅州
在梅州的紀(jì)念館里,記錄著葉劍英的不同于一般政治人物的話。即便是面對(duì)需要啟蒙的勞苦大眾或者需要鼓舞的軍隊(duì),葉劍英的話也有著“陌生化”的意味,葉劍英習(xí)慣于用詩(shī)體的語(yǔ)言來(lái)表達(dá)。
葉劍英說(shuō):革命的馬達(dá)在飛轉(zhuǎn),產(chǎn)生出解放人群的熱,幸福的光。
葉劍英說(shuō):戰(zhàn)!團(tuán)結(jié)而堅(jiān)決的戰(zhàn),勝利是我們的。
我對(duì)三十多年前的生活還記憶猶新,還記得葉劍英獻(xiàn)給“科學(xué)的春天”的那幾句押韻的話:攻城不怕堅(jiān),攻書莫為難。科學(xué)有險(xiǎn)阻,苦戰(zhàn)能過(guò)關(guān)。
葉劍英是政治家里的詩(shī)人。毛澤東在給陳毅的信中論及詩(shī),建議關(guān)于律詩(shī),可以向葉劍英請(qǐng)教。在其他場(chǎng)合,毛澤東也表示,葉劍英的詩(shī)律對(duì)精工意趣醇厚。我想,在詩(shī)詞歌賦的手藝上,毛澤東犯不上刻意去恭維一個(gè)人的,他一定是看到了葉劍英身上作為詩(shī)人的某種特質(zhì)。
舊的格律,裝著新的情理,葉劍英的詩(shī),我們似曾相識(shí)——我覺(jué)得,梅州近代以來(lái),可能存在著這樣的隱秘的接力,那把燃燒的火炬,詩(shī)界革命的火炬,幾經(jīng)接力傳到了葉劍英的手中。
這隱秘的接力之發(fā)生,不是偶然的。清末民初,梅州新式教育的發(fā)達(dá),是我們難以想象的。民國(guó)初年,在大部分的中國(guó)鄉(xiāng)村的生活形態(tài)還處于“古代”的情形下,梅州一地,居然擁有六七百座學(xué)校——這一數(shù)字,在一個(gè)外國(guó)人的筆下被描述為“駭人聽聞”。新式教育的這種密度,造就了梅州地域文明開化的高度。一批又一批梅州人接受著新的思維的熏陶,致力于建設(shè)新的生活,而葉劍英,僅僅是他們中的一個(gè)。
他被稱為客家詩(shī)宗,詩(shī)界革命的領(lǐng)袖。
他是那場(chǎng)隱秘接力中最耀眼的明星。
人境廬主人,黃公度。葉劍英手里的那把火炬就是由他點(diǎn)燃。
人境廬,是黃公度給自己設(shè)計(jì)的宅子。宅子并不宏大,連居室?guī)г鹤樱襾?lái)回踱步計(jì)量,長(zhǎng)寬不過(guò)三十步。除了回廊略顯寬闊,之外皆是小樓小亭小閣,花壇及假山也都是極小的。當(dāng)我手扶二樓的欄桿,環(huán)視整個(gè)庭落,所見皆如盆景。亞熱帶的景觀小植物花艷葉肥,肥厚的葉片上包裹著蠟質(zhì),它們一叢一叢地順應(yīng)著一個(gè)晚清知識(shí)分子對(duì)私園的美學(xué)構(gòu)圖。
精巧,愜意,實(shí)用而溫暖。結(jié)廬在人境,步履隨春風(fēng)。他極愛(ài)此廬,他生命的最后的時(shí)光在此度過(guò),他手訂詩(shī)稿,名為《人境廬詩(shī)草》。
他在維新事敗后,回到梅州,回到人境廬,回到中國(guó)文人自己的獨(dú)有話語(yǔ)資源里——這是一種不容易被外力剝奪的資源,只要還有可能,中國(guó)文人愿意把人生的哪怕是一線生機(jī)透露在詩(shī)歌里。只不過(guò),黃公度,分外看重的是“詩(shī)之外有事”,他要將維新運(yùn)動(dòng)在另一個(gè)場(chǎng)域進(jìn)行到底,他寄希望于梅州的后學(xué),他要將舊有的詩(shī)藝點(diǎn)燃,發(fā)出新的光焰,照亮新的眼睛。
精巧、愜意、實(shí)用而溫暖的人境廬里,它的主人卻是不折不扣的不斷進(jìn)取著的狂者。
從黃公度入職文官系統(tǒng)開始,即注重與求新求變的政治人物打交道:何如璋、李鴻章、張之洞以及陳寶箴,更不必說(shuō)康梁等強(qiáng)學(xué)時(shí)務(wù)之中堅(jiān)力量了。
李鴻章認(rèn)為黃公度有霸才。
康南海的回憶應(yīng)當(dāng)是可靠的。強(qiáng)學(xué)會(huì)初創(chuàng),黃公度來(lái)訪,康南海的記憶是,公度昂首加足于膝,縱談天下事。此前公度見張之洞,亦是昂首加足于膝,搖頭大語(yǔ)。
他是睜眼看世界的先驅(qū)。他自負(fù)。他目中無(wú)權(quán)貴。
他從梅州出發(fā),外交生涯讓他的見識(shí)遍及歐美和日本。政治變法主張中飽含著人生體驗(yàn),這是他與那個(gè)時(shí)代普通政治家的大區(qū)別。詩(shī)歌變法主張中飽含著域外觀與心上語(yǔ),這是他與那個(gè)時(shí)代詩(shī)人的大區(qū)別。他用十年時(shí)間,五十萬(wàn)言,寫成《日本國(guó)志》,詳盡考察日本的天文地理工商文教風(fēng)俗及軍政制度沿革,他企圖以此深遠(yuǎn)寄意。極端保守派和洋務(wù)派均忽略了這本國(guó)志的資政價(jià)值——那時(shí),自上至下,即便心懷圖強(qiáng)的官員,他們的興趣,也至多在物質(zhì)現(xiàn)代化這一層徘徊,“體”是決然不可動(dòng)搖的。甲午戰(zhàn)事之后,割地賠款,國(guó)運(yùn)凋敝,于種族迷惘生民疾苦中,有人重新看見《日本國(guó)志》的特別價(jià)值。這個(gè)人是袁昶,他說(shuō),《日本國(guó)志》刊行之延遲,讓中國(guó)多花了2億兩銀子。歷史迫使越來(lái)越多的人,越來(lái)越多的像袁昶一樣敦厚的舊忠臣也加入到了變革的行列,也參與到那場(chǎng)隱秘的接力之中。袁昶不是狂者,他一直小心地踐行著師傅劉熙載的教導(dǎo),“立功立德必須從人情物理做起”。他不滿意利用義和團(tuán)來(lái)滅洋的作法,他提意見,于是,被砍頭。
莊騷兩靈鬼,盤踞肝腸深。詩(shī)界革命是冒險(xiǎn)的,其實(shí)至今我們也無(wú)法對(duì)它做出一個(gè)簡(jiǎn)明的判斷。我們清楚,任何一個(gè)貌似激進(jìn)的舉動(dòng)里亦是包含著復(fù)雜的世界。同樣,致力于生活、國(guó)家現(xiàn)代化的“接力”也是復(fù)雜的,也是“冒險(xiǎn)”的,它的內(nèi)里究竟有多少難以逾越的關(guān)口和困境。黃公度即便是以文為詩(shī),伸縮離合,也只能拓寬些許情理之疆界。正因?yàn)檫@是一場(chǎng)接力,一場(chǎng)隱秘的接力,不是一個(gè)人的馬拉松,黃公度創(chuàng)辦嘉應(yīng)新學(xué)會(huì)議所,讓新學(xué)漸漸成為影響梅州念書人的思想主潮。有多少見過(guò)世面的官員和商人啊,當(dāng)他們?cè)俅位氐矫分菁淳栀Y辦學(xué)。東山中學(xué)就是葉劍英與其師友聯(lián)合創(chuàng)辦的。后來(lái),梅州國(guó)民教育的輻射力越出了廣東越出了華南,像陶行知就于1933年把梅州定為他的教育基地。
這是一場(chǎng)傳承有序的“新學(xué)”接力,從梅州出發(fā),再次回到梅州,再出發(fā)。
參觀人境廬的時(shí)候,我在想,這就是那個(gè)隱秘的接力的出發(fā)地啊。
精巧、愜意、實(shí)用而溫暖的人境廬,那么安靜,它靜靜地和我們發(fā)生著關(guān)聯(liá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