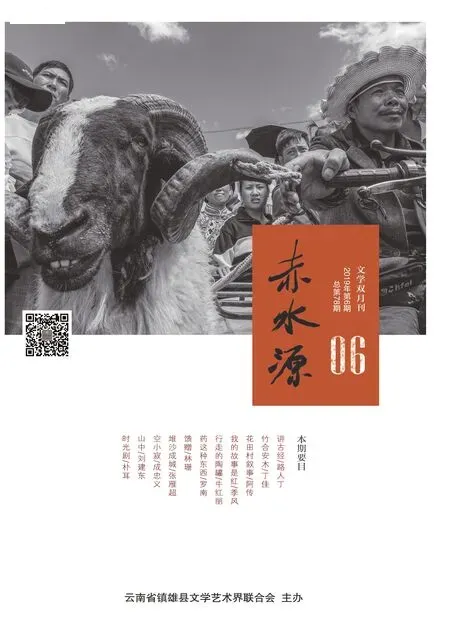山中詩歌
/ 劉建東
山中
獨自去到山中
天涯叫做塵埃
光陰叫做夢
我們的矛,或盾
叫做廢墟。夜幕巨大
天空只有幾顆星星
萬里而來的風
持有出發時的輕盈
野草,漫山亂撞
梨花,留白人間
幾粒鳥鳴,牽在一根線上
我在空山,空山緊貼我的心底
身后的滾滾紅塵,足夠深
足夠黑,足夠白
每一處都是卓別林的默片
恐高
登上烏峰山
我所寄居的地方
街道,樓房就更像蟻穴了
至于人,我甚至
無法用肉眼看到他們
整座城的炊煙都太小了
天空撥開云霧的時候
陽光照射下來
我趕緊蹲下身子
擔心擋住哪怕是一縷
抵達小城的冬日暖陽
那里有我的親人
也有藏在袖口的寒意
握手
高大的墻院越能隱藏
季節的前朝,不可將
背脊交付給它
書生靠窗
一坐就是幾個世紀
槐樹上掛著幾只鳥兒
蹦蹦跳跳的鳴唱
綠,把陽光侵透
一截樹枝伸出手
朝著窗戶靠近
多么美麗的善意
但卻不敢輕舉妄動
突然伸出去的另一只手
必然嚇壞緩緩而來的綠
必須正襟危坐
把隨時準備好的和潤笑容
悄無聲息收好,耐心等待
終于,在五月
盛開的細碎白花,一串串凋敝
就連葉子也收起了綠
在窗外的半空,戛然而止
書生在燈火昏暗的窗旁
一坐就是幾個世紀
場景
晚風中拖扯出
瘸拐身子
塞進冬日黃昏
土狗,外表丑陋
不會搖尾,都是年老
流浪的代稱。人間,車馬
已經足夠繁忙,一個露宿街頭
骯臟的生靈,注定勢單力薄
大雪后,潔白,如童話
沒能熬過冬天,這只傷痕累累
的狗,終于將自己的垂暮
交給了風雪,安靜地蜷縮
在商店的房檐下
鋼筋水泥不斷加固的城市
人來人往,這只狗死去的地方
幾年前也有一個老人
在這里躺下,再已沒起來
樓上的黑洞
清明,傍晚
中年夫妻打開后座的車門
試圖將一個雙眼緊閉
靠在座椅上的老人
攙扶下來。像孩子不舍得離開
大人剛買的新玩具
老人托辭頭疼,十分不愿
神情狡黠而不安
舊樓,樓梯窄而陡
因步伐太快
我差點與正蹣跚上樓
秋風中的一片樹葉
迎面相撞
像黑夜伸出來的一部分
扶著墻,老人趕緊將身子
往背后的黑縮回
幸好腳步帶出來的風
沒將他枯瘦的氣息刮滅
老人獨自住在樓上
很少出門
屋子里也應該有個黑洞
人間四月
梨花、櫻花、桃花……
都是雷,風一吹
就接連爆炸
如果世界只有春天
那么,任意一朵花就不會開得如此認真
必須在俗世中抓住
一些盛開的事物
用做竹杖芒鞋
因為一道光
飛蛾就會傾盡生命
至L
任何一個與晴空萬里相背的標點
都不應該被提起
在三月,在花紅柳綠的春光里
你從遠方趕來,告訴我
一朵桃花盛開的消息
我們塞進電影院的角落
人滿為患,卻又座位虛空
投影,讓故事得以永恒
而我們僅是其中一場過客
不應該在冬天談論悲傷
那么春天的眼淚就不是眼淚
是春雨,是朝露,是青春
盡管青春已是軟弱無力的詞匯
從北方跋涉而來的最后一縷風
帶著疲憊的塵埃,以昂揚的身姿
在南方的艷陽里丟盔棄甲
是的,我們都要奔赴各自的戰場
沒有悲傷和冰涼的漩渦
而列車停下的地方就是終點站
那么,就祝福它經過的地方
春日山花爛漫,秋時碩果累累
畫師
作為一個笨拙的畫師
我勾勒不出風和日麗的生活
也涂抹不去迎風的霜雪
如果大雁只是大雁
沒有南方,沒有歸處
任意一片天空便可安頓
潦草的一生
但我還不能做一個
跌跌撞撞的,酒肉之徒
折戟的刺就是馬革裹尸的將軍
必須傾盡一生
畫一只虎
有刺骨的寒風
和絕望的崖壁
也要有藐視一切的傲骨
和竭盡全力,王者的咆哮
冬
白色適合遙遠的村莊
適合光影堅硬的城市
每條孤獨跋涉的小路
都有雪花相伴
這些紛飛的白
僅剩骨頭
依舊保持決然
各自緊捂小小的呼嘯
飄落在或平,或峭
或高,或低的塵世
堆積,消融,寂靜無聲
我的小小人間
許多人背負行囊
踏在深深淺淺的黃昏
每個冬天
雪,都很盛大
心慌
大雨無邊際
從我出生,一直大到
我隱沒塵埃
滴滴嗒嗒
不能自已的腳步
趕往遠方。遠方仍是雨聲
滴滴嗒嗒
上帝在天上一邊敲響銅鼓
一邊提木偶前行
真擔心某一天他突然厭倦了這游戲
隨手就扔掉幾個
滴滴嗒嗒
樓下的老人剛從這個世界轉身
就有人在雨中吟唱
杜甫的“三別”
和劉希夷的《代悲白頭翁》
其聲嗚嗚,沉如雷
這雨下得我心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