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末元初館閣文人所書楷書石刻書法風格遞變研究
景曉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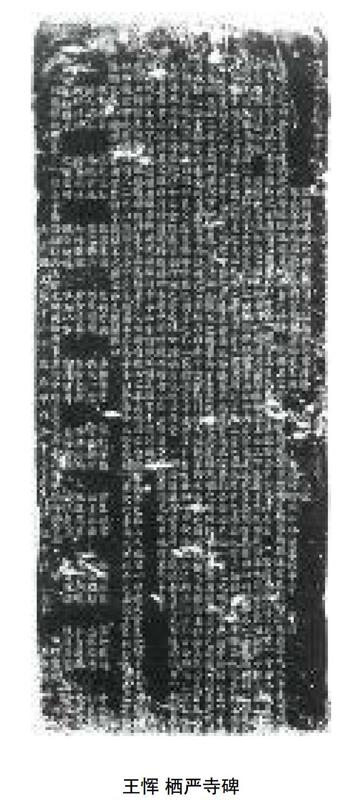
摘要:從金末元初現存的石刻中發現,楷書石刻的書丹人中館閣文人身份的占多數,本文就金末館閣文人書石審美的轉變以及元初楷書石刻風格的變化,進行論述和分析,以勾勒出這一時期石刻的文化價值以及書法史學的意義。
關鍵詞:金末元初;楷書石刻;館閣文人
館閣文人群體一直是書法發展的中堅力量,金末元初館閣文人書法發展是被人忽略的,一方面是因為朝代變更,書法的發展處于低迷,另一方面是留存的書法墨跡有限,因此,金末元初劉存的大量石刻能夠刻客觀地反映出金末元初館閣文人楷書發展的真實面貌。
一、金末館閣文人書石取法審美的轉變
金代中晚期,隨著金章宗完顏璟(1168—1189)從其祖世宗完顏雍(1123—1189)手上繼承皇位時,金朝遷都,政治文化中心南移,金代書法振興,達到全盛時期,金代的館閣文人書家由最初的宋臣或者宋臣之后變為金代本土書家的出現,如仁詢、王庭筠等,這些書家足以代表整個金代館閣文人書家的書學思想。
金代中晚期館閣文人題署的楷書石刻,其書法風格是兩條線并進的,一部分則是繼續延宋書“尚意”風,蘇學盛行,一部分則是晉法宗唐,到了金代晚期,館閣文人書家書石風格由最初的師法法顏真卿發展到對唐代書風的推崇,開始全面對柳公權、褚遂良、虞世南等書家的認可與學習,楷書石刻的書法風格由追求率意轉變為追求法度,當然這兩條線不是絕對的劃分,而是一個取法轉變的過程。
柯昌泗《語石·語石異同評》云:
金碑文體學蘇,書體學顏、米。翁覃溪云:蘇學勝于北……其時正書之學顏者,任南麓(任詢)、趙黃山(趙沨)是也……鹿菴逮至元間,已臻耄耋,書張弘范碑,純是蘇書,不涉米法,當時自不經見。金末石刻風氣又變,學米之行書已稀。傳世碑版,正楷之復近顏柳。
葉氏對于館閣文人書石取法轉變做出闡釋,由之前的崇蘇向崇顏轉變。金初館閣書家承北宋書法,師法米芾、蘇軾、黃庭堅,碑版石刻上也表現的多為蘇、米之風,所謂“蘇學盛于北”,但是隨著金代政治中心的難移,金代晚期楷書石刻的取法發生轉變,也就是葉氏所說“傳世碑版,正楷之復近顏柳”。而這種轉變并不是一揮而就,主要來兩方面,一方面是在朝廷影響下,館閣文人書丹楷書石刻時對顏體的認可。元豐改官制以后由尚書省給牒,禮部頒行符牒,大定四年(1164)《普照院牒》《福祥殘碑》,而石刻書丹人王競(?—1164),字無競,其官至翰林學士承旨、禮部尚書,《金史·王競傳》中:“善草隸書、工大字,梁都宮殿榜題碣競所書”,元好問《王無競題名記》贊其:“無競他書未必便國前人,至于尋丈大字,盤之筆勢,如作小楷,自當為古今第一,殆天機所到,非學能也。”元好問對王競的評價之高,可見其在金代也是能書之人,雖未見其楷書,但是從其所書的楷書石刻中看出其書法風格很明顯師法與顏魯公。另一方面則是金代館閣文人書家對于楷書石刻取法顏、柳書家的學習以及推崇,使得楷書石刻取法顏、柳的書風逐漸興盛。
黨懷英(1134—1211),字世杰,號竹溪。大定十一年(1171)及進士,歷官汝陰縣尹、翰林待制、國子祭酒、翰林學士承旨。金代石刻中的碑額多為篆書,且多出自黨懷英之手,篆書造詣極高,趙秉文在《閑閑老人滏水文集》卷十一《中大夫翰林學士承旨文獻黨公神道碑》中云:“八分自篆籀中來,故公書上軌鍾(繇)、蔡(邕),其下不論也。小楷如虞、褚,亦當為中朝第一。書法以魯公為正,柳誠懸以下不論也。古人名一藝,公獨兼之,亦可謂全矣。”趙氏不僅對其文章頗為稱贊,更認為其篆書是繼李陽冰后第一人,評價甚高,并且對黨懷英正書尤為稱贊。認為其師法顏、柳,這在黨懷英大定十八年(1178)所書《禮部令史題名記》以及大定二十四年(1184)所書石刻《重修天峰寺記》都可表現出來。與黨懷英齊名的還有趙沨(?—1195),字文孺,號黃山,官至禮部郎中。清代孫星衍《寰宇訪碑錄》卷十所收金碑中趙沨所書三方,且由趙沨撰文黨懷英書丹和黨懷英撰文趙沨書丹各一方,而明昌六年趙沨所書楷書石刻《時立愛神道碑》(如圖2—8)的風格可知金代中晚期館閣文人書家之間書風的互相影響,他們的書風這時候已經很少能看到米學、蘇學的影子,可以說是完全師法顏、柳。
趙秉文在評價同時對虞伯施、褚登善正書的認可,曰“秦相、李監之篆,漢、魏之八分,虞、褚、魯公之楷,見者莫不斂而敬。”并且在對別人的教誨表現出他對唐代其他書家的推崇,其曰:“學書當師三代金石、鍾、王、歐、虞、顏、柳,盡得諸人所長,然后卓然自成一家。非有意于專師古人也,亦非有意于專擯古人也”,一定程度上表現趙秉文從對師法顏、柳到對取法唐代其他書家的書學思想轉變。同時,師法唐人的這種思想在其大安二年(1210)所書《圭峰法語石刻》、貞佑四年(1216)所書《李演碑》 、正大四年(1224)《劉從益惠政碑》均可窺探。
金代中晚期館閣文人群體將金代楷書石刻宗法晉唐推到一個高潮。不得不說從金代楷書石刻看,“復古”的萌芽已然初現,這也為元代的“復古”思潮埋下伏筆。
二、元初館閣文人書家以顏、柳為宗,趨于雅正
忽必烈建元中統后,開始設立館閣機構并推行漢法,因此集中了大量以北方為據的漢族館閣文人,而這些館閣文人中有很多善書者,但是僅存于文獻記載,傳世作品并不多見,因此,要窺探元初館閣書家楷書風格面貌,石刻成為了唯一的文獻載體。
元初楷書石刻風格主要是金代書風的延續,金代晚期,館閣文人已經開始尊崇唐代,但楷書石刻的風格是主要以顏真卿為主,對于唐代其他書家取法相對較少,且書風多取開張之勢,縱橫恣肆,并不注重細節的變化。如柯昌泗《語石·語石異同評》中云“其碑文字多猥鄙,書法亦無士氣”。至元初,這種書風稍稍得到改善,館閣文人書家以唐為宗在楷書石刻上完全體現出來,逐漸褪去綿延之氣,點畫開始精細,更加注重學習唐人書法的嚴謹法度,同時其取法不僅僅體現在顏、柳,更是對歐陽詢,虞世南書風的全面學習。
姚樞(1203—1280),字公茂,號雪齋、敬齋。柳城(今遼寧朝陽)人,遷洛陽。太宗(1235)七年,隨楊惟中南下,訪儒道釋醫卜者,后得名儒趙復,得逞朱理學書籍傳至北方。
姚樞書法主要是以草書著稱于世,而其楷書多被忽略。姚樞楷書傳世的只有碑刻并無墨跡流傳,有至元八年(1271)所書《贊皇復縣記》、至元十六年(1279)所書《重建贊皇縣學記》等。《贊皇復縣記》由徒單公履撰文姚樞正書并題額,額為正書,從石刻看其師法顏真卿,結體外拓,點畫遒勁,書風較為率意,未脫金世遺風。時人對于姚樞書法的評價甚高,程鉅夫說道:“學齋名跡不下古人,字畫亦非后來所及”。但是這些評價大都是對姚樞草書的推崇,并不是針對楷書而言,其原因首先在于姚樞草書以唐人為宗,師法山谷道人,未沿襲宋人之風,可謂獨樹一幟,開啟元代草書書風的新篇章,而元代善草書的人并不多,使得其楷書無人問津。其次也是受到碑刻書體的限制,姚樞楷書師法顏魯公,稍顯稚嫩,但所書的《贊皇復縣記》仍不失碑刻的莊嚴之氣。但是無論出于何種原因,姚樞的楷書與草書都師法于唐人,一定程度的體現出了元初楷書石刻的書風取向。
元初館閣文人書石除卻姚樞,還有姚樞之侄姚燧也不可忽略。姚燧(1238—1313),字端甫,號牧庵,洛陽人,至元十七年(1280),有《牧庵文集》。姚燧所書楷書石刻有至元元年(1264)《楊奐神道碑》、至元九年(1272)所書《大名路總管兼府尹張子良神道碑》、至元十三年(1276)所書《重陽祖師先跡碑》。其中《重陽祖師先跡碑》拓本藏于國家圖書館,其師法顏真卿,相比于姚樞,姚燧所書楷書石刻已經脫去金世率性之遺風,點畫精細、遒勁,法度嚴謹,清人對其評價曰:“仿顏平原,秀拔樸厚,大有先正典刑”。
王惲是繼姚樞之后館閣文人的重要領軍人物,其所書楷書石刻書風影響諸多館閣文人書家。王惲(1227—1304),字仲謀,號秋澗,衛州汲縣(今河南衛輝)人。王惲所書楷書石刻共有七通,其中北京圖書館所藏拓本《棲嚴寺碑》(如圖)可見,王惲楷書石刻師法顏魯公,筆力挺拔,開闊雄勁,相比姚樞其師法顏魯公時書風更加成熟,這主要得力于對顏真卿的推崇。例如其題跋中記載:“予嘗謂魯公此筆,用忠義為本,然后以大篆變而為開題,故后之學者,終莫能及”。王惲楷書石刻師法顏真卿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則是王惲對顏真卿大量書帖的收藏,這為其學習顏體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其子王公孺在《王公神道碑銘》中云:
字畫遒婉,以魯公為正。所書卷帖,為世珍玩。
不可否認,王惲對顏真卿的推崇在元初館閣文人中影響是極深的,引起了元初楷書石刻師法顏真卿的熱潮,而這股熱潮一直持續到元代中期。
元初楷書石刻的書風受金末書風影響,主要師法顏、柳,追求“法”的同時,書風趨于雅正,可以說,元代館閣文人所書楷書石刻的書法風格已經開始走向“復古”。因此,南宋以來“書學之弊,無如本朝,作字直記姓名爾。其點畫位置,殆無一毫名世”的書法局面在元代初期得到了全面的改變。
參考文獻:
[1](明)宋濂撰.元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6.
[2](清)葉昌熾撰,王其祎點校.語石[M].中華書局,1998.
[3]北京圖書館金石組.北京圖書館藏歷代石刻拓本匯編·元49卷-50卷[M].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