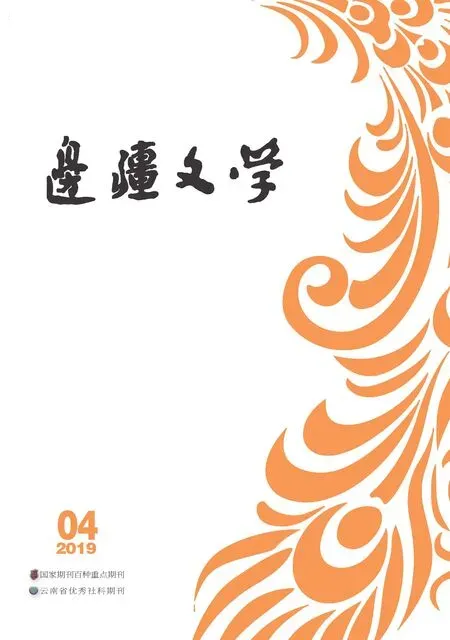江湖遠[散文]
2019-11-12 14:57:22黃立康納西族
邊疆文學
2019年4期
黃立康 納西族
就讓雨只是場雨,不是濃淡墨色/渲染的寺宇,留白的紅塵。
我曾是個喜歡發呆的孩子,被幻想寵壞,江湖,是我的執迷。
未曾想,某年月日,落到信箋上的字,會成為一篇武俠。似是故人來,我寫下第一行:時間如針,我們都是偷針的人。
時間如針,細碎、閃亮,我們貪戀的快樂,是否藏著偷竊的快感,是否都帶著細小難覺的刺痛。但更多時候,時間如磨,沉重、粗糲,磨盤慢慢轉動、碾壓、研磨,將疼痛磨細拉長,將時間磨得緩慢冗長,這酷刑,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
你有沒有覺得難熬的時候,十面埋伏,被時間夾擊?臨睡前怕黑的輾轉、課堂上漂浮的昏沉、熬夜時沉重的燈光,某個死去又活來的瞬間,年少的我虛構生死窺得天道——時間寄生在我們身上,我們以痛供養。瑪格麗特·杜拉斯在《情人》中哀嘆:“我在十八歲的時候就變老了。”是的,十八歲時,我們就已經變老了,甚至更小的時候,我們就已經很老很老了。這是時間的幻術,這是時間帶給我的痛。痛讓人躲,我本能地選擇逃離,幻想是我逃離世界的密道。
我是“罐頭”里的孩子,流水線上成長。我生活的高原小鎮荒蠻閉塞,如果我想認識世界,必須幻想,只能虛構。但我缺少細節,讓虛構顯得真實的細節,我一生都走不出狹窄逼仄的橫斷山脈,無法想象加勒比海盜迷戀的驚濤怪浪,無法虛構銀河艦隊穿越的浩瀚宇宙,無法鋪敘雙槍牛仔馳騁的狂野西部。我只能從小說的只言、電影的掠影中,虛構我秘密的世界。……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中國新聞周刊(2024年18期)2024-06-07 22:40:49
散文詩(青年版)(2022年4期)2022-04-25 23:52:34
都市(2022年1期)2022-03-08 02:23:30
文苑(2020年11期)2021-01-04 01:53:20
意林·全彩Color(2019年8期)2019-09-23 02:12:26
意林·全彩Color(2019年6期)2019-07-24 08:13:46
現代計算機(2016年12期)2016-02-28 18:35:29
發明與創新(2015年25期)2015-02-27 10:39:23
中國衛生(2014年12期)2014-11-12 13:12:38
杭州科技(2014年4期)2014-02-27 15:26: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