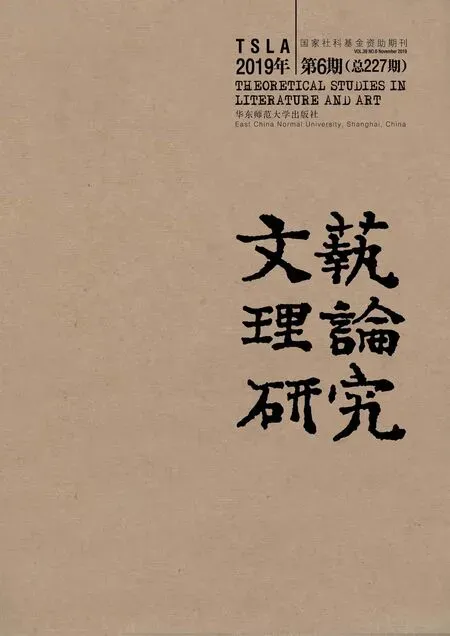重尋文學的友情
——論韋恩·布斯文學倫理思想的當代啟示
范 昀
引論:“后批判”時代的文學研究
2015年,弗吉尼亞大學教授芮塔·菲爾斯基(Rita Felski)出版的專著《批判的局限》(The
Limits
of
Critique
,2015)無疑在學界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彈。在這部作品中,菲爾斯基對當下的文學研究提出嚴厲的批判。她用“批判”(Critique)來指代那種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的批評實踐,指出這種批評理念不再追求傳統批評(criticism)所設定的對文學作品進行解釋與評價的目標,而是體現出一種激烈的好斗性與反叛性;批判意味著一種對主流價值的抗拒與否定。從精神分析、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到后結構主義,這些批評流派都共享了一種“癥候式的解釋”范式,這一范式在很長一段時間主導著當代文學研究:我們需要像對待病人或罪犯那樣審視文學作品,從中發現病情或敵情。新一代的文學研究者普遍采取了一種冷漠的態度來對待文本,以“深入挖掘”(digging down)和“置身事外”(standing back)的方式來探索文本中可能潛藏的意識形態和權力話語,作為代價的是,文學研究已經喪失了回答諸如“人們為何要閱讀文學/觀看戲劇”這類常識性問題。菲爾斯基的看法絕非其一己之見,而是代表了當下左翼學者的集體焦慮與不滿。比如在一篇《當沒有什么是酷》(When Nothing is Cool)的文章中,芝加哥大學教授麗莎·魯迪克(Lisa Ruddick)則直言當代的文學研究不僅使年輕一代學者喪失了從文學閱讀中獲得快樂的能力,甚至還喪失了探詢人生意義的興趣。隨著2017年菲爾斯基編輯的文集《批判與后批判》(Critique
and
Postcritique
,2017)的出版,旨在超越當下批判狀況的“后批判”(postcritique)正式浮出水面。在此意義上,所謂的“后批判”并非一種新的理論潮流,它的出現表達了當代西方學界的有識之士期待文學研究走出“大寫的理論”(THEORY)與批判模式的迫切期待。比如有學者提出用“表層閱讀”(surface reading)來取代之前的“癥候式批評”;或有學者提出告別那些標新立異的學術酷玩,重新去探詢那些“不酷”的,但對生活有意義的事物。總而言之,他們形成了普遍的共識:文學研究者需要改變這種疏離與冷漠的姿態,要以更具感性與溫度的方式去參與批評,以更為開放與包容的視野去探討文學的倫理與社會維度,通過重建與文學之間的友情,使文學研究更好地解釋與參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因此,“后批評”其實并不“后”,它試圖促使文學研究回歸普通讀者的經驗與常識。在為文學研究的未來尋找出路之時,有時過去的歷史往往更具啟示價值。比如早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文學理論家韋恩·布斯(Wayne C.Booth)就對如何將文學研究引入人生做了深入的思考。盡管他所處的寫作語境與今日有所不同,盡管布斯的寫作重點落在如何擺脫“內部研究”的研究范式,克服對文學的去倫理化的形式主義理解,但他同樣對當時日漸興盛的意識形態批評提出嚴厲批評。他指出,不少當代文學學者與其說把書籍當作朋友,不如說更多地把它當成“迷宮式的蛛網”、“語言的牢房”,謎語、密碼,或者說是“一個有待進入的世界,或一件有待分析甚至令人仰慕的對象”(The Essential Wayne Booth157)。通過重啟“友情”這一隱喻,布斯強調了書籍與讀者、作者與讀者以及讀者與讀者之間的重要聯系紐帶,從而為當代文學研究走出偵探式閱讀與癥候式批評提供了重要啟示,為此重新審視布斯的文學倫理思想有其意義所在。
雖然國內學界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就譯介了韋恩·布斯的《小說修辭學》(The
Rhetoric
of
Fiction
),并使其學說在當代文藝領域產生了一時的影響力。但總體而言,對他的介紹和研究都缺乏必要的廣度和深度:迄今為止他的另一部重要作品《我們所交往的朋友:小說倫理學》(The
Company
We
Keep
:An
Ethics
of
Fiction
)尚未得到譯介。此外,在改革開放新時期倡導“文學自主論”的語境中,布斯的作品常常被作為敘事學理論的經典受到關注,而他對倫理問題的關切卻并未得到國內學界的足夠重視。隨著上世紀末后現代等新潮理論的引入,布斯則被喜新厭舊的理論界打入冷宮。近些年隨著西方文學理論與批評的“倫理轉向”(ethical turn),對布斯的關注出現了一定的回暖跡象,學界也開始重視布斯文學思想中的倫理維度,但全面系統的論述還有所缺失,尤其是對布斯文學“共導”思想的公共性維度挖掘不足。基于這一狀況,本文試圖通過呈現布斯對文學倫理的重新定位和對文學友情的獨到見解,來為“后批判”時代文學研究與批評事業的未來尋找有益的出路。一、辯護與定位:布斯對文學倫理的重構
韋恩·布斯對文學倫理的關注,緣于他的一段親身經歷:上世紀六十年代某年秋季學期的開學前,年輕的布斯和他的同事們在討論如何為新生修訂推薦書目時,發生了一件令他們感到出乎意料的事。作為一部經典,許多年來馬克·吐溫的《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一直都在這個目錄中,卻在當時遭到同事保爾·摩西的質疑。這位黑人助理教授氣憤地指出這本小說中充斥著強烈了種族主義,尤其是作者對吉姆的描繪深深地冒犯了他,他坦言沒法拿這樣的作品去教課(The
Company
We
Keep
3)。摩西的這番言論在同事中引發爭議。在當時的美國文學界,強調文學形式的內部研究占據了主流,文學研究被“內部研究”的潮流所主宰。包括年輕布斯在內的絕大多數學者都認為,摩西對文學作品的道德指摘顯得幼稚和業余,這種強烈的道德義憤竟使他喪失了作為職業文學研究者應有的審美判斷力。然而,這一事件卻對布斯的思想產生了很大影響,逐漸使他對自己的立場產生懷疑。當日常經驗不斷提示:人類的生活離不開故事,個體的成長與人格的完善離不開故事的講述與聆聽,這就不可避免地使布斯對那種“封閉的”“自主的”“去人性化”的美學觀念產生質疑:文學怎么可能與大千世界有所隔離,與人類的豐富生活分道揚鑣?即便再純粹的文學,也會對人的生活產生影響。在經歷了一番思想的斗爭與發展之后,布斯認為那位英年早逝同事的想法是合理的,他的質疑讓布斯意識到,“批評性的倫理話語,不僅是合法的,而且對一個正義和理性的社會至關重要”(NussbaumLove
’s
Knowledge
232)。對文學進行倫理層面的評判,不僅在人類的日常生活中稀松平常,而且在文學研究中也有久遠的歷史。布斯通過對文學批評史的考察看到,無論在古代還是近代,批評家對于自己的主要職責存在共識:那就是要對藝術作品的價值做出評判,他們沒有理由用那些類似“有意味的形式”或“美學上的統一”這樣的中性術語去掩飾自己的倫理關切(The
Company
We
Keep
25)。然而在二十世紀,“倫理”和“道德”卻成為文學研究者避之不及的詞匯,無論是以新批評為主導的形式主義年代,還是當下以女性主義、精神分析、性別研究為主導的意識形態,“倫理”都成為了一種默認的禁忌。在《小說修辭學》中,布斯就做過這樣的感嘆:時尚風潮對諸如“好人”或“壞人”的忽視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它導致了人們去輕視在絕大多數文學閱讀中倫理判斷所扮演的角色(The
Rhetoric
of
fiction
131)。在布斯看來,有四個原因導致倫理批評的衰落:一是出于對道德專制與政治審查的反感;二是基于對審美自主性的現代美學理念的捍衛;三是來自于科學主義的挑戰,認為倫理批評不具備客觀的知識性,只是純粹的個人主觀產物;四是來自于文化建構主義的沖擊。這些建構主義的論述都假設文學作品的評價背后都潛藏著“權力”,認為倫理批評不僅是主觀的,而且它代表著由某個階級或團體的意識形態。
不必諱言,上述觀點的確對倫理批評形成了極大的挑戰。因為它們很尖銳地觸及到了傳統倫理批評的短板。尤其是第四種建構主義的論述,迄今依然在學界有很大的市場。針對上述挑戰布斯做了如下回應:
關于政治審查與道德主義的問題,布斯認為批評家并無政治權力去對文學進行政治審查;他所理解的倫理批評要比那種柏拉圖或利維斯式的“道德主義”要寬泛的多,因為后者的批評無法被稱為探詢、研究或者學問,而是具有爭議性、激勵性與“道德主義色彩”(The
Essential
Wayne
Booth
156)。有關審美自主性問題,布斯并不認為我們可以在“審美”或“非審美”、“說教”與“修辭”的作品之間劃出一條絕對的界線。他甚至認為一切文學都具有“說教性”。即便是奧斯卡·王爾德這樣的“唯美主義者”,其審美理念本身也隱含了倫理維度(The
Company
We
Keep
11);此外人們還會在那些致力于“顯示”而不再“講述”的現代主義文學作品中,體會到某種說教。針對科學主義的質疑,布斯認為倫理評價的客觀性不同于科學意義上的客觀性。他認為文學評價的客觀性是一種基于“共導”基礎上的主觀普遍性,關于這點后文會有詳細介紹。針對建構主義的挑戰,布斯反對把尼采等人的觀點進行脫離語境的教條主義運用。在某種情形下,理性可能是某種權力的伎倆,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必然可以與權力意識形態劃等號,“難道為了把倫理批評從教條式的道德主義中解放出來,我就必須轉向支持另一種與之相對的教條?”(The
Company
We
Keep
377)。在為文學倫理辯護的基礎上,布斯試圖重新確立倫理在當代文學研究中的地位,因為我們無法否認文學的這種“改變我們生活的力量,無論善惡”(“Why Ethical”25)。布斯對倫理批評的重新定位并不旨在復辟文學的道德主義傳統,也不愿重新卷入形式主義者與道德主義者之間曠日持久的爭論。他重新定位倫理批評的目的在于:倫理批評需要根據當今時代的特征與文明的價值做出相應的調整,對文學倫理批評的目標、主題以及方法進行重新審視與定位,因為只有這樣文學批評才能重新與人類的現實生活建立起緊密的聯系。倫理批評若要在當代重新實現它的價值,首先需要超越過去僵化的道德主義的局限,這就需要在批評目標上作出兩方面的調整:
一方面,倫理批評需要從過去的“道德審判”轉向“倫理探詢”。倫理問題并不僅僅是狹隘的道德戒律或行為準則,它覆蓋了人生的方方面面。受亞里士多德倫理學的影響,布斯對倫理(ethical)的理解相當寬泛,在他看來,最好的倫理思考往往不是回答“你應該如何”,而是追尋一系列的“美德”(virtues):即值得稱贊的行為舉止的典型習慣。這些美德包含實踐者、自我以及人格所推崇或至少能夠忍受的每一種能力、氣質、力量、素質以及心智習慣。不管是成功駕駛一艘船,還是擲出一塊鐵餅或是養家糊口,都可算做一種美德(The
Essential
Wayne
Booth
222)。這種多元主義的倫理觀,不僅有助于克服柏拉圖式的一元論道德主義,而且也對現代以功利主義和康德主義為代表的倫理學的局限有所修正。更明確地講,布斯試圖將倫理學定位于蘇格拉底的“人應當如何生活”之問。文學意義上的倫理批評并不關注某個故事或作品是否違反了道德準則,而更關心“故事講述者與讀者或聽者在氣質上的遭遇”(The
Company
We
Keep
8)。因此布斯意義上的倫理批評甚至愿意去以同情的方式關注在傳統上看來“不道德”的作品,愿意從生命這一更大的視野去思考文學作品為什么吸引讀者同情第三者、色情狂,認同戀童癖等等,并引導讀者自己去作出理性的判斷。另一方面,布斯還將倫理批評的關注點從對“事后效應”(after-effects)或“結果”(consequence)轉向“作者或讀者在閱讀或聆聽的期間所追求或獲得的體驗質量”(The
Essential
Wayne
Booth
157)。他不是去追問這首詩或這個戲劇是否使我在欣賞完以后成為一個更好的人,而是在于探討在欣賞作品過程中我與作品的關系是怎樣的。比如在傳統道德批評中,批評家會對《德伯家的苔絲》提出這樣一些問題:“苔絲是否為女性提供了一個典范?”。布斯認為倫理批評不該這樣去提問,而應思考“托馬斯·哈代在他的故事中所要你在生活中去渴求、害怕、哀嘆以及希望的東西是否為你,或你的兒女提供了一種好的生活?”(168)。由于人的行為與社會的風尚的變化是由諸多復雜的現實因素構成,衡量一部作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人的行為,在科學上很難得到充分的說明與論證。《浮士德》并不能阻止希特勒的屠猶政策,閱讀大量色情小說與人格墮落之間的聯系也從未得到科學的有效論證。因此與其執著于一個無解的問題,不如轉向更具實質性的問題:“不同于追問這本書,這首詩,這出戲,這部電影或電視劇是否會讓我在明天轉向德性或罪惡,我們現在要問的是,它在今天向我提供了怎樣的友情”(The
Company
We
Keep
169)。二、修辭即倫理:文學友情的表達方式
當布斯把倫理批評的對象從作品的道德后果轉向作品的“友情”時,這就意味著布斯文學倫理學的思考重點在于:文學作品如何來呈現它的“友情”,文學的形式技巧如何與倫理發生關聯,以及讀者又該如何去獲得這份“友情”。
“即便享有所有其他的善,也沒有人愿意過沒有朋友的生活。”(亞里士多德228)深受亞里士多德倫理學的影響,布斯試圖重新激活“友情”作為幸福生活的核心要素。因為“友情”在亞里士多德有關人類幸福的思考中占據核心的地位。但在這個推崇“自我“與”孤獨“的時代,友誼不再得到當代人的重視。對于很多普通人而言,書籍只是工具,是通往成功的階梯,而在過去,有關“書籍的友誼”有關的比喻則到處可尋。
要重新尋找我們與作品之間的友誼,也就意味著重新恢復我們與文學作品之間古老而親密的聯系。我們需要放棄當下學術圈所倡導的“偵探式”的冷冰冰閱讀,回歸到充滿熱忱與情感的閱讀。讀者需要在閱讀文學的過程中,并不是與個別的語詞、結構以及技巧相遇,而是與作品的整體遭遇。這種作品的整體性,并不必然體現創造者的主觀意圖,而是體現于布斯所謂的“隱含作者”(implied author)。布斯創造這一概念來描述讀者在閱讀中感受到的作者形象與聲音,在倫理批評中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讀者/批評家對“隱含作者”的責任。
在布斯看來,“隱含作者”有別于日常生活中的作者。因為在寫作時的作者應該盡可能地超越自身的特殊性,擺脫個體的偏見,把自己看作是“一般人”,如果可能的話,忘掉他的“個人存在”和他的“特定環境”(The
Rhetoric
of
Fiction
70)。布斯的這一概念讓人注意到:作品是一個在進行選擇與評價的人格的產物,而不是現存自我的產物。“隱含作者的感情和判斷,正是偉大小說的構成材料。”(86)讀者對“隱含作者”的理解,其實包含了對一部完成的藝術整體的直覺理解。“無論它的創作者在現實生活中屬于哪個黨派,隱含作者致力于實現的首要價值,是那些通過全部形式所表達出來的東西。”(The
Rhetoric
of
Fiction
73-74)這個隱含作者“有意或無意地選擇了我們閱讀的東西;我們將其視為一個理想的、文學的以及創造出來的替身;他是他自己所有選擇的總和”(74—75)。讀者若要實現成功的倫理閱讀,負責任地呈現“隱含作者”,就需要付出艱辛的努力。倫理批評并非僅僅拿一些既定的抽象原則對作品中的個別細節、人物以及言論作出評判,而是需要通過一句一句(line-by-line)的細讀來獲得關于作品的總體印象。“我必須讓它成為我的一部分,我要像對待朋友一樣,花數小時時間與它相處。”(The
Company
We
Keep
285)只有到這種程度,我才能真正作出倫理評判。若要批評一部作品“感傷”“膚淺”“做作”“頹廢”“布爾喬亞”或者“邏各斯中心”,我就得先在作品中體驗這些(The
Company
We
Keep
285)。盡管布斯認為喬治·布萊等為代表的日內瓦批評在這方面走得有些過頭(讓自己的意識變成作品的意識),但他更反對當時學術潮流所倡導的那種與藝術作品之間保持“審美距離”的做法,因為在當時主流美學理念中,全情投入藝術被視為幼稚之舉,為故事而感傷,為音樂而落淚只是非專業讀者的標志。當下的文學研究總是將“文本”視為一種拒人千里之外的“難題”或“謎語”,人們大概“只有在紙面上除了無意義的語詞之外什么也看不到,才失去了指控其多愁善感的理由”(The
Company
We
Keep
140)。但對文學的閱讀批評不該喪失對作品的全情體驗,甚至反對色情文學的人都不得不承認,若要更好地檢討色情文學的道德危害,也唯有與色情文學的親密接觸才能讓他明白什么是色情。若要爭取來自“隱含作者”的友情,較之于現實生活中作者的經歷與言論,讀者更需重視文學作品本身的修辭。什么是善的,什么是好的,必須放在具體語境中才能得到理解,此時作品的修辭便會產生力量,正是由細節構成的修辭為倫理的探詢提供了豐饒的背景。文學的倫理效果的實現需要作家高超的敘事技巧與修辭能力。真正杰出的作品通常擁有極佳的修辭能力,這種修辭能力既確保了作品的道德內涵,也確保了其對讀者的倫理影響力。在布斯看來,修辭作為小說的技巧,本質上是一種與讀者交流的技術,是一種把小說世界交給讀者的技術。傳統道德批評忽視了藝術的道德存在于“技巧”之中:“整個藝術的道德存在于讓兩個人物,即隱含作者與隱含讀者建立起友情所需要的大量事物之上”(The
Essential
Wayne
Booth
173)。因此,“小說修辭學的終極問題是,決定作者應該為誰寫作”(The
Rhetoric
of
Fiction
396)。布斯對修辭如此重視的原因也正體現在這一倫理層面上。換而言之,“修辭即倫理”是布斯倫理批評的核心思想。布斯對修辭的重視,體現了“芝加哥學派”的文學立場。“芝加哥學派”不同于“新批評”的最大特色在于其對亞里士多德詩學觀念的倚重,尤其是他對“有價值的形式”的重視,在《詩學》中亞里士多德對詩所作出的形式上的規定都是與其對詩的倫理效果的關切聯系在一起的。布斯對修辭的關注也是亞里士多德意義上的,他也因此被稱為“新亞里士多德主義者”。
布斯對修辭的理解非常寬泛,他自己也以修辭學家知名。就亞里士多德的定義而言,修辭即是一門勸說的藝術。它跟形式論批評視野中的“技巧”最大的差異就是它始終關注勸說的對象,也就是與讀者之間的交流。布斯所強調的“修辭”并不是純粹技巧性的,而是具有濃重的倫理內涵。所謂的“小說的修辭學”就是討論作家是如何使用各種技巧和手段來達到介入故事發表評論的目的。那些形式主義者所關注的“象征”“隱喻”“反諷”,在布斯的理解中去除了它們的神秘色彩,成為了“隱含作者”操縱讀者視角的一種手段。
從具體的批評案例來看,比如布斯認為《麥克白》的卓越之處在于莎士比亞能用“一種精心的修辭來控制我們的同情”(The
Rhetoric
of
Fiction
115)。他在描寫麥克白殺害鄧肯的過程中,盡可能避免客觀場面描寫,而是從麥克白的感受去進行側面描寫,這會使得邪惡造成的負面效果得到削弱,從而確保“戲劇主角墮落的每一步都會對他增長的同情所抵消”(The
Essential
Wayne
Booth
30)。與之相反,在另一部劇作《李爾王》中莎士比亞對暴力所進行的客觀冷靜的正面描寫(葛羅斯特被挖眼珠這一幕)則激起了讀者對暴力的憤慨。在那個場景中,作為“隱含作者”的莎士比亞不僅提醒我們要譴責暴力,而且還應該發自內心地體會到我們為什么要這樣做。對暴力的道德譴責無需訴諸“道德上的陳詞濫調”,要通過運用“修辭的倫理”來促使人們進行自覺地道德探究。布斯對奧斯丁《愛瑪》的解讀同樣展示了修辭的倫理之維。在他看來,《愛瑪》這部小說的寫作難度在于,一方面作者需要展示主人公愛瑪的缺點,對其進行道德上的評判,另一方面又不能讓讀者喪失對她的同情。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布斯指出奧斯丁選擇以愛瑪,而不是比她更為優秀的簡·費爾法克斯作為敘述者,讓讀者在很長一段閱讀時間里都是通過愛瑪的雙眼來獲取故事情節。如此一來,不管人物顯露出怎樣的品質,“這種持續不斷的內在視野都會引導讀者期盼這位伴隨著他們一起游歷的人物能夠獲得好運”(The
Essential
Wayne
Booth
37)。即便愛瑪有各種人格缺陷和行動錯誤,但她的內心活動中永遠包含了自責,使得讀者更能以同情的方式去理解愛瑪犯下的錯誤。由此可見,文學修辭的價值并不止于技巧層面,而體現在對價值世界的關注。三、活在“友情”中:文學與人的成長
布斯提示我們:若要真正地獲得文學的友情,我們需要像朋友那樣去對待文學作品;同時我們還需要看到,文學所提供的友情千差萬別,良莠不齊。在這個鼓吹本真與自我的時代,如何贏得最好的友情,實現自我真正的成長,顯得尤為重要。
有關文學所能提供的“友情”,布斯所做的描述非常豐富:有時他會細致地呈現文學的友情:有的“長篇巨制”,有的則“短小精悍”;有的與讀者處于“互惠關系”,有的則與讀者形成不平等的“權力等級”;有的“冷若冰霜”,有的則“平易近人”;有的“引人入勝”,也有的“缺乏魅力”;有的“聯系緊湊”,有的則“毀滅性地斷裂”;有的提供“他者”,有的則讓讀者感到“熟悉”;有的“內涵廣闊”,有的則“意義集中”(The
Company
We
Keep
182-94)等等。有時他也試圖用相對簡化的“真、善、美”來做概括:有的作家可以提供“豐富的想象時刻重構”(如弗吉尼亞·沃爾夫);有的作家則“讓我們首先主動地參與對事物真理的思考”(如托馬斯·曼);有些強調“實踐問題與選擇”(如約翰·班楊);有些則無所不包(如莎士比亞、狄更斯、荷馬)(165)。由此可見,布斯在價值上趨向于多元主義,他對文學作品的各種友情,采取了比較包容的態度。對于如何去評判這些友誼,他有時并不愿意拿出一種絕對的倫理尺度。這點也得到了他本人的確認:比如他對大學時代老師理查德·麥基翁的贊賞就在于后者所倡導的價值多元性;他還從俄國文藝理論家巴赫金那里受到啟示:“復調性”是人類生活不可回避的現實,“我”正是在與他人的共同對話中存在著。在談到對倫理批評的定位時,他明確提出一種系統性的批評多元主義:通過吸收不同的哲學思想與批評理論來更好地理解與包容文學所提供給我們的不同的友誼。因為在他看來,倫理批評的首要敵人是專斷獨行的教條主義,而不是同情包容的多元主義。
盡管布斯并不主張用一種至高的尺度來衡量文學,但這并沒有妨礙他像亞里士多德對“美德之誼”的推崇那樣,對文學友誼的質量作出必要的評判。他十分看重美好的文學友情帶給讀者的積極價值,同時也對文學作品帶來的消極友情提出批評。首先,他對許多流行作品(如《大白鯊》、《低俗小說》等)持批判態度,因為在這些作品在娛樂背后缺失倫理內涵,這些作品中所呈現的暴力場景缺乏“內在的控訴”,使人們“常常為技術手段所操縱,反而會對施暴者報以強烈的同情”(The
Essential
Wayne
Booth
257)。其次,布斯還認為某些作品的曖昧不清也會有損友情的質量。比如他認為很多現代小說為了追求某種非人格化的敘述而付出了相應的代價。比如亨利·詹姆斯的《螺絲在擰緊》中由于敘述意圖上的含混而給讀者帶來了很多困惑;而納博科夫在《洛麗塔》中反諷手法的使用導致作品清晰性的喪失。在布斯看來,正是這種清晰性的喪失,造成了我們生活中道德的含混不清。再者,甚至某些經典作品也會助長自我的封閉與自戀。布斯的這一觀點在他對《一九八四》和《一位青年藝術家畫像》的分析中得到了淋漓盡致地展現。他認為這兩部著名的現代文學經典不但提供不了最好的友情,反倒是迎合與助長這個時代的個人主義與自戀文化。在此問題上他認同萊昂內爾·特里林有關現代文學的看法:當“他人即地獄”成為當代青年文化的主流,當反叛社會與追尋本真成為時代的主旋律時,我們很多的文學經典都被用來為了支持這樣的“社會-自我”之間的二元對立。
因此,最好的友情還是要從培育人格,引導成長的角度來衡量。布斯追隨馬修·阿諾德的文化理想,認為只有以偉大經典為代表的“文化”才能實現人從“一般自我”(general self)到“最好的自我”(best self)的實現。唯有在這些經典中讀者才能遇到最優秀的朋友(“隱含作者”),使自我在與之共處的時光中得到提升:“你的陪伴要勝于我希望在與普通人一起生活中所發現的任何陪伴——包括我自己。畢竟你是精華版,甚至比那個創造你的作家還要優秀”(The
Company
We
Keep
178)。布斯指出,偉大經典作品所提供的友情不僅在于“它們所提供愉悅的廣度、深度與強度,也不僅在于通過證明它們的有用性,實現了對我的承諾,而且在這些時刻,它們最終在無法抗拒的邀請中它們讓我過上了我自己所無法做到的豐富而完整的生活”(223)。他援引桑塔亞那在《三位哲學詩人》(The
Three
Philosophical
poets
)開篇的一段話:擁有偉大文學的唯一好處在于,它們能幫助我們成長(become)。它們本身,作為其作者所創造的豐功偉績,即便在我們這個時代之前就已消亡,也不會喪失它們的真實或偉大。我們既無法帶走也無法增加它們過去的價值與內在的尊貴。就它們是我們的佳肴而非毒藥這點而言,它們只會為我們的思想增加價值與尊嚴……(桑塔亞那1)
布斯提示沉浸于“本真性”文化的我們,對“偽善”(Hypocrisy)需有更為成熟的認識。“偽善”的古典含義是“在舞臺上扮演角色”,在當時并無貶義色彩。它是指在舞臺上或者舞臺下尋找特定的方式,從一種性格變成另一種性格。他指出,“人格”與“偽善”是一對近義詞:演員通過“hypocrisy”來表演人格;作者通過創造人格來扮演角色,讀者則通過再創造來表演角色。簡而言之,“一種特定的人格扮演是我們培養人格的方式”(The
Company
We
Keep
252)。在兩種不同的hypocrisy(upward hypocrisy,downward hypocrisy)中,向上的hypocrisy對于個體的人格發展意義重大,因為這種扮演有助于人格的完善。在他看來,失去所謂自我沒有什么大不了的,關鍵是自我的成長。“如果我能夠分享那些角色,那要比尋找獨一無二的自我更為重要。”(The
Company
We
Keep
259)在接納偉大經典給予我們的友情時,我們非但不會失去自我,而只會實現更好的自我:“當我放棄了這個私人意義上的‘個人’或‘真實自我’時,我并沒有在這種放棄中失去什么”;與之相反,正是在全心投入低扮演其他角色的過程中,我得到了充分的成長,在各種閱讀遭遇中,我找到了“新的自我(selves)。”(259—60)這種自我的更新,即為“可塑性”,這也是布斯為藝術性評價而辯護的核心:“在與比我們優秀的隱含作者的交往過程中,我們受其引導,實際上改進了我們自己的‘欲望模式’”(The
Essential
Wayne
Booth
187)。我們可以在與書為友的過程中得到成長,同樣也可以在與生活中的朋友的對話與交談中變得更好。正是在強調這種“可塑性”的過程中,布斯已經暗示了他的“共導”觀念。這種共導觀念不僅對于個人人格成長與完善意義重大,而且對于民主社會公共生活的構建與促進更具有不容忽視的政治意義。四、我們共同的生活:“共導”實踐與公共生活
布斯對“共導”觀念的創建,源于他對存在于歷史與當代文學批評中普遍存在著的陳舊思維方式的不滿。因為無論是歷史上的道德主義批評,還是當代的各種意識形態批評都帶有濃重的教條主義意味。在他看來,邏輯上的三段論不僅出現在傳統的道德主義批評中,同樣也呈現于當代的意識形態批評之中:
1.任何一部作品中存在著X的話都是壞的。
2.諾曼·梅勒的小說中存在著X。
3.那么,我們就無需細讀梅勒小說的整體結構,也不需要考慮不同的讀者所感受到的不同經驗,就可以認為它在道德上是有害的。(The
Company
We
Keep
54)“所有的批評家都傾向于過度一般化,倫理批評家最容易受到這種誘惑。”(51)如今的意識形態批評表面看似與傳統道德主義水火不容,但其所信奉的“政治正確”與前者幾乎如出一轍。在這種簡單的極端化處理中,他們放棄了在批評世界中更為豐富多元的論證與價值。為此他援引薩繆爾·約翰遜的話指出“在科學事件中可能發生的證明(Demonstration)直接展示它的力量,不必因時間變遷而感到希望或害怕;但暫時性與經驗性的作品[也就是依托于經驗的作品]則必須根據它們與一般與集體意義上的人的能力的相應程度來評價它,因為它是在一段漫長連續的努力中來獲得的”(71)。當我們既不能從一個特定的前提以演繹的邏輯來評價作品,也不能通過對一系列作品案例的歸納來找到批評的原則。當抽象原則無法幫助我們理解藝術價值的微妙與復雜性之時,文學的倫理批評又該如何展開呢?
布斯的答案是“共導”(Coduction)。“共導”是他創造的新詞,他把它同演繹(deduction)和歸納(induction)區分開來。這個詞由co(“一起”)與ducere(“導出、產生”)兩個詞根構成,對持續不斷的對話發出了召喚。它與科學論斷只依賴孤獨個體的理性不同,它需要通過與他人的交流的情形下發生。“我們的共導必然是在與那些我們所信任的他人的共導之間的對話中獲得修正的。”(73)因此,“共導”是一種具有公共性而非私人性的批評實踐,意在指出人們對文學的價值評判是在與他者的交流中走向客觀的。
布斯認為,在我與他人的交流過程中,一個人的看法會以三種方式得到改變:其一,這種改變會使人更富于比較意識;其二,我不再執著于自我的私人經驗。我朋友的意見值得認真對待;其三,我還會對我的個人信念與原則有所調整。(“我總是認為那些十惡不赦的謀殺者形象是非道德的,當我在閱讀麥克白的故事時,我自己的準則是否有所改變?”)。
布斯以自身經歷為例:有一次他與妻子一同觀看電影《紫色》,他在觀看過程中數次流淚,而妻子卻完全沒有。于是他們之間進行了這樣的對話:
布斯妻子:“他們怎么會拍出這樣陳詞濫調的作品來?”
布斯:“你說什么?陳詞濫調?我真的被打動了。”
布斯妻子:“你的意思是你絲毫不厭煩那些顯而易見的公式化情節?”(The
Company
We
Keep
74)“經過這樣的對話,我開始對我的眼淚有了重新審視。而我的妻子也反省自己是否過于冷酷。于是,‘作品自身’通過我們的對話得到了重新演繹與改變。”(The
Company
We
Keep
74)除此之外,在《我們所交往的朋友》中布斯還以極為真誠的態度敘述了他對文學史上三部文學經典態度變化的心路歷程。在他年輕時他曾經是一位拉伯雷的擁躉,但在經歷了女性主義思想的洗禮后,他看到了《巨人傳》在倫理上的缺陷;在對奧斯丁《愛瑪》以及D·H·勞倫斯作品的重讀中,布斯的看法也發生了新的變化。最后他還談到了本文開篇涉及的“馬克·吐溫事件”,在重讀《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的過程中,布斯同情共感地體會到了這位作家在思想上的“膚淺”。盡管他依然喜愛這部經典作品,但這樣的一次“共導”使他從對這部作品“毫無質疑的迷戀”轉向了“永不停止的質疑”(478)。
通過這些例子布斯試圖指出,“共導”本質上并非單一“信息”的獲取,而是相互經驗的建構;不是“獨白”,而是積極的“對話”,是一種與他人分享交流審美經驗的過程。在這一交流過程中,人們會對他人的意見進行思考,并帶著他人的眼光進行重新閱讀,先前的判斷就有可能出現某種程度的改變,倫理批評的客觀性就是建立在這種主體間的交往之中,這種客觀性無疑對良好的公共生活起著潛移默化的推進作用。這種“可塑性處于為藝術性評價辯護的核心位置:‘我’并不是孤軍奮戰;‘我們’共同行事,無休無止地來回爭論”(The
Essential
Wayne
Booth
186)。在此意義上,“共導”體現出它的公共維度與政治價值。因為這種包含著“對話”內涵的“共導”,與西方政治哲學上討論的“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ing)并無二致。在約翰·羅爾斯、阿瑪蒂亞·森等學者的論述中,“公共理性”代表了一種“協商式民主”,即“當公民進行協商時,他們對相關的公共政治問題相互交換意見,并提出支持理由來為其觀點辯護”(阿瑪蒂亞·森302)。公共理性意味著個人在參與公共生活時應該盡可能地保持立場的不偏不倚,這樣才能保障公共理性在民主實踐中與社會正義的目標聯系起來。
這里所說的“公共理性”,絕非某種超然的理智,而是帶有同情共感性質的情感。因此公共理性并非源自于抽象理智的推導與計算,而是融合了情感因素的理性。這不僅得到了休謨、斯密等18世紀啟蒙思想家的確認,而且在當代也得到了愈來愈多思想家的倡導。因此不可否認的是,公共理性與情感之間的緊密聯系,這也使得作為拓展人類情感最重要的文學作品為培養公共理性提供了可能性,而布斯的“共導”恰恰體現了這一可能性。這點也在當代美國哲學家、芝加哥大學教授瑪莎·努斯鮑姆(Martha C.Nussbaum)的《詩性正義》(Poetic
Justice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public
life
)中得到了充分的引申發揮。努斯鮑姆指出,在民主社會的公共生活中,我們每個個體都應去追求一種基于公共利益的道德觀念:“我們所追尋的不僅僅是使得我們自身個體經歷有意義的道德教育觀念,而且還是一種能為他人辯護,并與那些我們希望與之共同生活的他人一起去支持的道德觀念”(84)。她認為布斯的“共導”預設了一種理想的公民理念。因為“共導”是“一種與其說是從個人偏好,不如說是從人類的相互關系出發的合作性的論證。在此,在一段時間的交流過程中來自于朋友的原則、具體的經驗以及建議能夠產生并改進你的判斷”(Love
’s
Knowledge
234)。在此意義上,她認為文學的“共導”有助于塑造一種亞當·斯密意義上的“公正的旁觀者”(judicious spectator)理想。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所塑造的“公正的旁觀者”形象,一方面體現在其作為旁觀者去關注他人的生活,另一方面他的旁觀并不缺乏情感的介入。文學的“共導”恰恰體現在這個意義上,文學“共導”所構建的讀者身份“實際上就是一種對明智的旁觀者身份的藝術建構,它以愉快而自然的方式引導我們進入到一種與好公民與法官完全匹配的態度之中”(Poetic
Justice
75)。她還通過具體的案例實踐對這個觀點進行了有效的論證,有力地論證了文學閱讀/批評對于公共生活的價值,也有效地對布斯的文學倫理學進行了政治哲學以及法學意義上拓展與延伸,開創性地揭示了布斯文學倫理思想深遠的社會與政治內涵。結 語
綜上所述,在當代“后批判”的背景下重審韋恩·布斯的文學倫理思想有其重要價值。首先,布斯對文藝作品倫理維度的重視,符合人類生活的常識并具有強烈的實踐品格。他的倫理批評遠遠超越了傳統狹隘的道德主義,有助于我們更好地通過文學來探詢“人應當如何生活”的倫理學之問。其次,布斯的文學倫理思想重新召回了我們與文學之間的那種自然而原初的友情,尤其是對當代的職業文學研究者而言,這種關系的重新找尋與確立,顯得尤為必要。再者,布斯的文學倫理思想具有強烈的公共性內涵。他的“共導”概念指向了一種超越個體的,實質指向公共理性與協商的理想,從而為文學研究如何為公共生活的貢獻提供了相關有價值啟示。
布斯的思想并非無懈可擊。比如有人認為他的多元主義有滑向相對主義的危險性;但同時又有人認為他在評判文學作品的過程中依然存在著狹隘的道德主義問題,比如理查德·波斯納對他所倡導的倫理批評提出了強烈的質疑。此外在當代后現代反人文主義的潮流中,布斯更是被視為過時落伍的人文主義者而遭到批判。在針對布斯的諸多細節的批評中,筆者認為很多批評是中肯的,布斯的思想確實存在著一些不容回避的內在矛盾。不過,若僅僅因為他是“一位落伍的人文主義者”而對其進行批判,卻并不在理。為此在全文結尾之際筆者想就此多說幾句。
不可否認,自文藝復興以來的“人文主義”確實在當代遭遇挑戰。尤其是上世紀的歷史教訓以及六十年代以來的理論思潮,都對這一現代價值觀形成了挑戰。有人認為人類在二十世紀所經歷的政治浩劫與生態破壞都與這種以人為中心的現代價值密切相關,而以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為代表的理論思潮則致力于消解人文主義所確立的主體性思想;各種意識形態思潮則以階級、性別、種族的名義來消解人文主義所追求的普遍人性論。于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反/后人文主義”在文化層面(尤其在學院中)形成蔚然之風。一位從事人文學科的研究者不相信/不認同人文主義理念,似乎已經成為行內默契。
但平心而論,當代所謂的“后人文主義”常常只是一種學院化的抽象理論游戲與學術時尚,并非確立在對社會現實生活的真誠體認之上。因為每一個生活在現實生活中的人(包括這些學者自身)并不會因為“后人文主義”而拒絕自身得到人文關懷,受到人文教育,渴望過上美好而富于價值的生活。此外,這些理論思潮過于隨意地將“人類中心主義”與“人文主義”混為一談。因為對人性的尊重絕不意味著放縱人性,對人類的自我膨脹缺乏限制。就“人文主義”的原意而言,就是強調“能夠控制自身道德世界的、有教養的人的重要性”(彼得·蓋伊100)。當代文學研究的困境的根源就在于,學者們總是習慣于抽象而教條的大詞與行話,卻對具體的現實生活熟視無睹;習慣于“將孩子與洗澡水一起倒掉”,無法對事物的復雜性做更為細致的辨別。但正如筆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樣:“文學研究若繼續無視社會現實,淪為行話與扯淡的大本營;批評理論若繼續我行我素,回避對公眾閱讀經驗作出有效回應;文學學者們若不能對詩歌與小說有所感動,卻只對反叛與發表倍感興奮的話,那么人文學科必將付出被社會不斷邊緣化的代價。在此處境中,人文學者就必須堅持與捍衛人文主義的立場,需要放棄某種自戀與自負,而以更為有效的方式向社會證明自身研究的價值。它需要清晰地向人們傳達閱讀文學、關心藝術的重要性。它決不能淪為自娛自樂的學術圈游戲,而應努力面向現實世界貢獻貨真價實的思想與智慧,來為人類社會未竟的啟蒙事業盡一份力”。
正是在這點上,韋恩·布斯通過他對文學友情的呼喚淋漓盡致地體現出了他作為人文主義者的清晰度、現實性以及倫理觀,也正是他對個體與社會良好生活的人文關切中,我們才能真正理解布斯文學倫理思想的最終歸宿。我們不僅不應該輕視他,忽略他,甚至貶低他,而更應該通過與他的文學思想的比較與參照,來清醒地看到在消費主義時代當代文學研究在體制化與產業化的過程中所付出的巨大代價。在此意義上布斯一直都是我們的朋友,當代文學研究事業需要他的這份彌足珍貴的友情。
注釋[Notes]
① 參見拙文“打破文學研究象牙塔:‘后批評’概念浮出水面”,《中國社會科學報》2017年12月4日域外版。當時筆者將Critique翻譯成“批評”,而后經過仔細斟酌認為,critique所涵蓋的內容超過文學批評,因此覺得翻譯為“批判”更為妥當。
② Jeffrey J.Williams.“The New Modesty in Literary Criticism.”Jan 5,2015.Sept.10,2016〈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The-New-Modesty-in-Literary/150993/〉.
③ Lisa Ruddick.“When Nothing is Cool.”Point
Magazine
,2015.May 12,2015.May 15,2015.〈https://thepointmag.com/2015/criticism/when-nothing-is-cool〉.④ 自2000年以來,對布斯文學倫理問題的探討逐漸升溫,這不僅體現在《修辭的復興:布斯精粹》的出版(譯林出版社,2009年),而且也體現在新近的研究之中:如程錫麟的“析布思的小說倫理學”,見《四川大學學報》1(2000):64—71;任世芳的“韋恩布斯的修辭倫理批評:從小說修辭學到小說倫理學”,見《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2018):121—26;梁心怡的“自我的重塑:韋恩布斯倫理批評探微”,見《江淮論壇》2(2018):175—79、陳后亮“小說修辭閱讀的倫理批評多元主義——再論韋恩布斯的文學倫理批評”,見《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2016):29—36;炎萍:“文學與朋友—析韋恩布斯的文學倫理批評”《牡丹江師范學院學報》4(2014):56—59;等等。
⑤ 參見Wayne Booth.“Richard McKeon’s Pluralism:The Path between Dogmatism and Relativism.”The
Essential
Wayne
Booth
.Ed.Walter Jost.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6.120-39.⑥ 在為《我們所交往的朋友》所撰寫的書評中,努斯鮑姆尖銳地指出布斯提供了一種令人困惑的多元主義,因為他沒有意識到在價值之間存在著尖銳沖突的可能性:“我認為布斯是在竭盡討好他在文學領域的那些現實或想象中的批評者,急于打消他們的疑慮,說他不是教條主義者,不是古板的邏輯的捍衛者。他沒必要如此遷就”(Love’s Knowledge 243)。對此布斯也做出了回應,他并不認為自己是一位相對主義者,但他還是認為“作為倫理批評家,我們不需要就哪種倫理學原理更加優越達成共識。相反,我們理應即刻放棄決定任何一種優越理論的一切希望”(The Essential Booth 191)。
⑦ 參見Richard Posner.“Against Ethical Criticism.”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21(1997):1-27.⑧ 陳后亮《小說修辭閱讀的倫理批評多元主義——再論韋恩布斯的文學倫理批評》對布斯的自由人文主義立場提出批評。他援引鮑爾(B.Bawer)所評價,認為他的理論“高尚但卻空洞”,認為“布斯和大多數自由人文主義者一樣,聽不到世界的嘈雜聲,也看不到現實生活中的階級、種族和性別問題,對解決這些問題既沒有興趣也無能為力”,見《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2016):29—36。
⑨ 范昀:“打破文學研究象牙塔:‘后批評’概念浮出水面”,《中國社會科學報》2017年12月4日域外版。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廖申白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
Aristotle,Nichomachean
Ethics
.Trans.Liao Shenbai.Beijing:Commercial Press,2004.Booth,Wayne C.The
Company
We
Keep
:The
Ethics
of
Ficti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 - -.The
Essential
Wayne
Booth
.Ed.Walter Jost.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6.- - -.“Why Ethical Criticism Can Never Be Simple.”Mapping
the
Ethical
turn
:A
Reader
in
ethics
,Cul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Eds.Todd F.Davis and Kenneth Womack.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2001.- -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Nussbaum,Martha C..Love
’s
Knowledge
:Essays
on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 -.Poetic
Justice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Public
Life
.Boston:Beacon Press,1995.彼得·蓋伊:《啟蒙時代:現代異教精神的興起》,劉北成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Gay,Peter.Enlightenment
:The
Rise
of
Modern
Paganism
.Trans.Liu Beicheng.Shanghai:Shanghai People’s Press.2015]喬治·桑塔亞那:《詩與哲學:三位哲學詩人盧克萊修、但丁及歌德》,華明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
[Santayana,George.Three
Philosophical
Poets
:Lucretius
,Dante
,and
Goethe
.Trans.Hua Ming.Guilin: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01.]阿瑪蒂亞·森:《正義的理念》,王磊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
[Sen,Amartya.The
Idea
of
Justice
.Trans.Li Lei,et al..Beijing: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