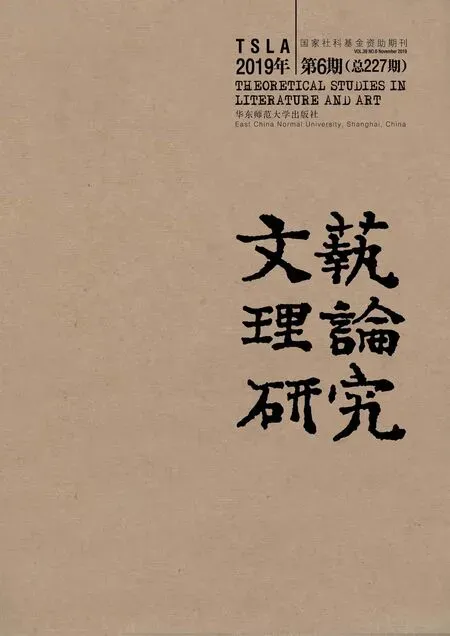雅克·朗西埃論“文學性”
鄭海婷
文學性是一回事,文學又是另一回事。文學性使文學成為一個非等級的藝術和書寫體制,作者在其中論及任何人任何事。相應的,作為歷史性的書寫體制的文學,呈現給文學性的是其他藝術和書寫體制所不能呈現的東西。(Dissenting
Words
193-94)從以上文段,可以發現兩點:第一,文學性關涉到民主和政治性,它不是文學所獨有,可以屬于任何的藝術和書寫體制;第二,文學比文學性多了一個限定詞:歷史性。這與我們認知的“文學性”似乎大相徑庭。
我們知道,自文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關于何為文學性的討論就從未停止過。學界大體上形成兩大陣營,一是主張文學獨立自足的純文學論,把文學性定義為使一部特定的作品成為文學作品的東西,一種獨屬于文學的特性;二是主張文學與社會歷史聯系的馬克思主義觀點,認為文學同樣是社會的產物,置身于社會關系中,并由社會關系所決定,不存在純而又純或者永恒不變的文學特性。朗西埃指出,他對以上兩種文學理論都不感興趣,前者是“文學本質論”,“基于一種難以察覺的語言從屬關系”使文學具體化;后者是歷史相對論,把多個不同的問題糅合在一起。“在任何情況下,作為書寫體制的文學都是對過去作品的重新占有,這就模糊了任何一種建立正統的欣賞和闡釋方法的主張。[……]它將無限期擺蕩在文學本質論與歷史相對論之間。”(“Literature,Politics,Aesthetics”11)
一、什么是文學性
考慮到朗西埃在國內學術界的接受情況,有必要先對“文學性”的法語、英語、漢語的翻譯和使用情況做一個說明。“文學性”是20世紀形式主義—結構主義文論的關鍵詞,最早由羅曼·雅可布遜于1919年提出,用的是俄語literaturnost,他把“文學性”定義為使某件作品成為文學作品的因素。此后這一定義在學界流傳甚廣,影響至今。根據比較文學學者張漢良教授的考察,其法語為littérarité;英語為literariness,也有少數譯作literarity,但學界目前基本上統一用literariness;中譯為“文學性”或“文學特性”。(張漢良20—21,34)朗西埃提及“文學性”,用的法語單詞同樣是littérarité。但是,朗西埃又多次提到,他所說的“文學性”并不是使文學成為文學的那種東西,恰恰相反,文學的根本性危機就來自“文學性”所指涉的詞語的過度及其帶來的文學的民主(Mute
Speech
99)。也就是說,他的“文學性”是要讓文學不成其為文學的,與literariness完全不同。但他在書寫上用的又是同一個詞語,這很容易帶來理解上的混淆。比如,早期英譯者就將其譯為literariness;而漢語學界也一直都在用“文學性”來翻譯朗西埃的相關用語。這種不做區分的術語使用和翻譯給我們的理解造成了障礙,鑒于對“文學性”所作的“面目全非的改造”在朗西埃的文學美學思想中的重要位置,有必要更加慎重地對待朗西埃的“文學性”。從朗西埃作品的英譯本來看,在不同的作品中,我們會碰到兩種英譯literariness和literarity。隨著英語學界對朗西埃譯介的增多,研究也不斷深入,學者們意識到雖然有著同樣的字音和字形,但是朗西埃的“文學性”與學界的流行版本在字義上相差甚遠。為了避免混淆,近年來,學界已達成共識,用當前比較不常用的literarity來翻譯朗西埃的littérarité,以區別于流行版本的literariness。
實際上,在2000年的一個采訪中,朗西埃就被問到了這個問題:兩個字面上一樣的“文學性”,字義卻完全不同,這很容易導致誤解。朗西埃的回答相當直接:
對我來說,如果“文學性”指的是一種特定語言的“所有權”,賦予文本某種“文學的”品質,那“文學性”這個詞就是空的,我的“文學性”與著名的“不及物性”并不一致。[……]我對“文學理論”不太感冒。我所說的“文學性”與“感性的分配”有關。(“Literature,Politics,Aesthetics”8)
“文學性”在朗西埃的著作中出現最早是在1992年出版的專著《歷史之名》。該書中兩處用到“文學性”,表示完全不同的含義。第一處在法文版第108頁,提到“歷史角色的文學性”,關聯到“人是文學動物”(Les
noms
de
l
’histoire
108),這與朗西埃之后對“文學性”的釋義一致,他在另一篇文章解釋了此處“文學性”的定義:“在《歷史之名》中,我建議把‘沉默的文字’的這種可用性(availability)叫做‘文學性’。”(“The Politics of Literature”15)第二處在法文版第153頁,提到要劃出“歷史性與文學性的界線”,其中“歷史性”是歷史特性、歷史本性,“沒有這個界線就沒有場所來書寫歷史”(Les
noms
de
l
’histoire
153)。可見,此處“文學性”相對“歷史性”而言,是文學特性,更接近“使文學之為文學的本質屬性”,而不是“沉默文字的可用性”。《歷史之名》以后,朗西埃有意識地把他所理解的“文學性”與通常意義上的“文學特性”作出區分,極少出現使用“文學特性”的情況了。比如,1995年出版的《歧義:政治與哲學》中,他更加直接地把文學性定位于“詞語的過度”(excès des mots/excess of words),并由此關聯了文學與政治,他寫道:“現代政治動物首先是一種文學動物,處在文學性回圈之中,此文學性解開詞語秩序和決定每個人位置的身體秩序之間的關系。”(Disagrennment
37)“文學性”首先在歷史哲學和政治哲學的研究中出現,這說明了朗西埃的“文學性”并不局限于文學或者某個具體學科領域,而是指向所有的書寫(writing)。與朗西埃把書寫指涉為“自由言談的不受控制的民主”(Philosopher
and
His
Poor
40)相應,文學性指的是這么一種狀態:“寫下來的詞語任意流通,沒有一個合法的體制來規定詞語的發出者和接收者之間的關系。”(“Literature,Politics,Aesthetics”7-8)文學性的核心是詞語的過度,就是詞語對其所表達的既定意義的偏離,以及由此帶來的巨大的不確定性,有可能形成詞語和意義的新的聯結。朗西埃認為這種新關系的創造可以類比于現實社會的組織。統治秩序和政治權力規定了存在方式、做事方式和說話方式之間的對應關系,比如柏拉圖的城邦之內,一定社會地位的人從事一定的工作,他說的話也和其他人不同,哲學家的話是真理,而窮人的話并不具有理性,與真理隔了一層又一層。在朗西埃看來,這種對應關系是權力運作的結果,是可以被改變的。這就是他所謂的感性的分配和再分配。2000年前后,朗西埃把主要精力轉向對文學和美學的研究,多次使用了“文學性”這一術語,一方面不斷將其與“文學”加以區別,另一方面將其與“文學特性”進行區分,在這一過程中,賦予“文學性”越來越多的政治上的重要性。這些著作包括但不限于《詞語的肉身:書寫的政治》(1998年)、《沉默的言語:論文學的矛盾》(1998年)、《美學的政治:感性的分配》(2000年)、《文學的政治》(2006年),等等。
綜上,朗西埃的“文學性”概念要結合“感性分配”來理解(Dissenting
Words
8)。文學性是一種獨特的可感性邏輯,始終致力于推動感性的再分配。用感性分配理論,朗西埃在雙重意義上改造了學界對“文學性”的流行解釋。首先,文學性是某種感性分配的原則。“藝術作品被界定為藝術作品,是因為它屬于某種識別體制,這一識別體制規定了藝術作品中可見性、可說性和可能性的分配。”(Dissenting
Words
232)如果文學性是使文學成其為文學的東西,那么這里核心的問題就是關于什么是文學和什么不是文學的評判標準,某種識別體制,于朗西埃而言,就是某種感性分配的原則。其次,文學性致力于推動感性的再分配。文學性使文學實現感性再分配,產生文學的政治。這一點尤為關鍵。朗西埃不滿足于簡單套用“感性分配”的概念,他的工作重點是在其中引入政治的維度。前文提及,朗西埃把文學性定義為詞語的過度,定義為沉默文字的可用性。在這里,文學性并不僅僅服務于文學,也可以服務于其他藝術門類。落實到文學書寫,文學性指的是“孤兒的文字”在沒有父親相隨的情況下自由流通,從而破壞了既有的藝術再現體制的感性坐標(Dissenting
Words
193-94)。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理解何以“做文學就是做政治”。因為“寫作本身就構成了行動,是一種配置和劃分感性的共享領域的方式”(131)。簡單來說,“文學性是政治和文學聯系的中心”(The
Flesh
of
Words
108)。文學性用“詞語的過度”來瓦解“話語秩序與其社會功能之間的關系”(Dissenting
Words
84)。文學性的詞語過度威脅著治安秩序——朗西埃的兩個重要論斷“人是政治動物,正因為人是文學動物”“做文學就是做政治”都應該從這個角度去理解。二、文學性的悖論
文學性是沉默文字的可用性。“沉默的文字”(mute letter),朗西埃所用到的類似表述還有“沉默的言語”(silent/mute speech)“沉默的石頭”(mute pebbles)“沉默的書寫”(mute writing)“沉默的符號”(mute signs),等等。在他的概念譜系中,這幾個短語在政治指涉上是一樣的,根據不同的上下文會作出不同選用。
朗西埃用“活的詞語”與“沉默的詞語”對舉,指出“文學性就介于這二者之間”(“Literature,Politics,Aesthetics”7-8)。“活的詞語”指的是在共同體內能夠合法散播的詞語,比如教師向弟子傳授知識、神父向信徒布道、將軍向士兵作戰前動員演講,這些話語的發出者、接收者、目的、場合、傳播模式等都有很明確的規定。也就是說,共同體自有一套存在方式、說話方式和做事方式的固定的自然的聯系,形成了再現體制下的等級制度,對應著現實社會生活的感性分配。在此體制內,話語從意義的生產到輸出到接收,意義體系的整條線索都很明晰。“沉默的詞語”則不一樣,它用不受約束的自由游歷來沖擊既定的感性分配。那些不被共同體秩序計算在內的部分,他們說的話不被聽見,比如亞里士多德就認為人與動物的區別就在于人能夠發出有意義的聲音,而動物只能發出無意義的嚎叫,人的聲音是邏各斯,動物的聲音就只是噪音而已。同時,也正因為不被共同體秩序所承認,沉默的詞語就有了脫離秩序四處流浪的特征,過度和越界是其常態,這使得再現體制所確立的美文范式受到了等級體系和意義體系瓦解的雙重沖擊。
首先,沉默的詞語不屬于任何人,是孤兒的言語,沒有一個師長隨行,教導它各種各樣要去遵守的規則,它可以自由游蕩,向四面八方傳播。正如柏拉圖當時將詩人驅逐出理想國的理由,書寫是不受控制的民主。其次,沉默詞語的不受控制還體現在諸多方面。它的發出者是不合法的,不知道什么時候、什么場合應該說話,什么時候、什么場合不應該說話。它同樣不知道最后要到哪里去,被誰接收。因此,沉默的詞語意味著一切確定性關系的中斷,沒有什么是確定的了。就像朗西埃所引用的伏爾泰對高乃依的艷羨之語,高乃依的時代是古典美文秩序的鼎盛時代,比如他在宮廷劇場上演道德教化劇,有明確的受眾、明確的目的。但是到了伏爾泰的時代,文字和書本普及開來,劇場也向大眾開放了,這時,文學的受眾就有可能是任何人,說話的效果也沒有任何保證(《文學的政治》15—16)。意義不再是從一個意志到另一個意志,意義變成了是從一個符號到另一個符號,這中間沒有什么是確定的。“意義變成一種‘沉默’的符號與符號的關系”(“The Politics of Literature”19)。
文學性的悖論就來自沉默言語的這些特性。朗西埃首先明確了一點:“平等的預設”。即任何人、任何物都擁有平等的話語能力或者潛能。那些被認定為“沉默”的話語,不是沒說,也不是不能說,而是沒被聽見。這樣,文學就是要為這些不能自己發聲的存在服務,文學要做的就是去解讀沉默物件上的符號。作家要讓那些不被計算在內的部分發聲,不投入個人的任何好惡情感,只做忠實的記錄員,給他們舞臺,讓他們自己說話,就像福樓拜所做的一樣。朗西埃說,這是文學的另一種政治,即“癥候式閱讀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Literature”21)。一方面,文學的政治性源于沉默詞語的不受約束的播散,它帶來了文學的民主,使再現體制下美文規范的恰切性受到沖擊。另一方面,它所關聯的不確定性,就是藝術解放的核心。藝術不強加某種信息,不規定特定的目標受眾,不用單一的模式來解釋世界,這樣的藝術才是解放的藝術(Dissenting
Words
231-32)。這種不確定性給文學帶來了許多麻煩,比如,沉默詞語的肆意流浪挑戰了文學的邊界,使再現體制的等級制崩潰,原先定義文學的一系列特征也不斷失效。許多不被認可的部分進入了文學,文學和非文學的區分不再明確了。事實上,美學體制下的文學寫作就是在重新審視各種界限,審視治安秩序所界定的可見性、可思性以及可能性的配置(239)。把“沉默的言語”對應到小說創作中,朗西埃經常談到的是福樓拜小說的“石化”(pétrification)文體(《文學的政治》9—15)。福樓拜小說中對細節的癡迷,對行動和人物的人類意指的冷漠態度,對人類生靈和物質事物的同等重視程度,被認為是某種語言石化的形式。
薩特在《什么是文學?》中認為,福樓拜用石化的文體拒絕外部世界,拒絕文學的交際用途,是不及物的書寫,文學在福樓拜的筆下成為貴族式的排外的秘密花園,建立起了自己的象牙塔,因此,福樓拜是反民主的。
有意思的是,福樓拜同時期的保守派評論家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石化文體是福樓拜支持民主的標記。他們的理由有二,一是從寫作方面看,福樓拜筆下所有的詞語一律平等,一切事物都被同等看待,人物、事物,包括描寫的前景和后景之間的區別都被消除了,這是十分民主甚至是民粹主義的;二是從政治態度看,福樓拜主張作家在作品中不透露個人的情感好惡,作品拒絕任何的政治介入,這種針對任何信息的冷漠就是他支持民主的真正標記——我不管你的政治立場如何,你是什么派別都可以,任何人可以是任何派別,民主、反民主或者壓根兒不關心民主,在福樓拜這里是沒差的,這種態度就是一種民主的態度,給予任何政治觀點平等的眼光、平等的可能性——這使福樓拜的小說成為了民主的場域,擺脫了作者意志的人物可以隨意行動。
朗西埃更支持后一種觀點——石化文體是民主的表征。他在保守派評論家的基礎上進一步推進——石化是美學體制對再現體制的顛覆(Mute
Speech
43)。石化文體把風格/筆法(style)作為看待事物的絕對方式,破壞了古典時代的美文規范所確定下來的一整套等級制度,這套等級制度規定了行動要有因有果、描寫什么等級的人用什么文體、在國王的位置上如何才是得體的、什么才是工人和奴隸該做的、什么才是這類人該有的表現、該說的話,諸如此類。石化文體使存在方式、說話方式和做事方式之間的自然聯系斷裂了,從而催生出無數的可能性:任何人有可能做任何事、說任何話。將一種激進平等的民主原則引入小說之中。因此,朗西埃所謂的“文學性”,重要的不是存在方式、說話方式和做事方式之間又有了一套新的聯系,重要的是舊的確定性聯系的斷裂。這樣,詞語就不在舊的回圈之中了,而是在回圈之外任意流傳,流向那不知名的所在,沒有特定的接收者,也沒有發號施令的指揮者。
“文學性”的悖論同樣存在于這種不受約束的自由徜徉之中,文學性侵蝕著文學的權力,失去了任何確定性聯結的文學實際上也走向了自我取消。
三、文學性的流竄與壓制
要么政治,要么文學?文學和政治成為了不相容的東西。——文學性的民主制造的混亂也是19世紀歐洲經典作家們的共同困惑,他們通過文學寫作來表達這一困惑,并試圖尋求答案。這也使得這一階段的小說成為朗西埃多年來一直熱心鉆研的工程。這些經典作家給出的解決辦法是:不能任由文學性不受約束地肆意游蕩,要對其進行適當壓制,文學還必須是文學。至于如何壓制?其中的度怎么把握?這在每個作家的不同作品中有不同的處理方式。“文學是一種不再承認藝術法則的書寫藝術的體制,它的隱含規范必須在文本的細節中尋找。[……]對于巴爾扎克、福樓拜或馬拉美,‘遵循規范’和‘偏離規范’是寫作過程的內在。”(“Literature,Politics,Aesthetics”10)
巴爾扎克的《鄉村教士》中,一個原本不該接觸小說的小鎮姑娘接觸了小說,受小說影響,憧憬浪漫的愛情,后來,她為了愛情背叛了她的丈夫,欲與情人私奔。而深愛著她的那個情人,一個窮小子,為了私奔的費用,搶劫并殺害了一個無辜的老人,最后被處刑而死。這一系列的罪行是由民主的文學性所引發的。在小說的后半部分,就講述了如何去補贖這個罪行。神父給女主人公提供的補贖方案是讓她用金錢去筑壩建渠,從山上引水改道灌溉平原,使小鎮的土壤變得肥沃,農民豐收,人民富足。這是通過銘刻在無聲的土地上的文字來彌補民主的文學性所犯下的罪過。而為了補贖這一罪過,文學性要進行自我壓制:致人犯罪的是文學性,但文學性沒有能力來贖罪。用來贖罪的是工程師建造的堤壩與水渠,是從山上引下的灌溉農田的水流,而不是溫情與夢幻的詞語,或者上帝的圣言。朗西埃寫道:“文學的政治存在著一種只能通過自我壓制才能解決的矛盾。”(“The Politics of Literature”21)
但實際上,在朗西埃看來,巴爾扎克在《鄉村教士》中所提供的只是其中一種解決方式,并且也不見得是最有意思的那種。朗西埃更推崇福樓拜提出的解決方案——文學性犯下的過錯由文學來解決。他的著名論文《為什么要殺死愛瑪·包法利》通篇在談的就是這個問題。在此之前,先談談《布瓦爾與佩庫歇》,這是福樓拜的最后一部小說,小說的大意是兩個碌碌無為的小抄寫員突然在某天獲得了一筆意外之財,于是,他們放棄工作,用這筆錢投身科學事業,一門接一門地研究學問,農業、化學、醫學、天文、地理、文學、歷史、教育、社會學等等,他們用全部的精力和熱情投入科學研究,完全按書本指示行事,不聽任何經驗之語,這使他們的試驗全都失敗了。最后,一事無成的兩位主人公重操舊業,又干起了抄寫員的工作。小說所提出的困難仍然是由文學性引起的——把生活完全交付給書本文字。兩位抄寫員不知道書本知識僅僅是書本知識,不愿意把書本的文字封閉在一個適當的空間之內,要讓它越出書本的空間。一有機會,他們就按照書本上所記錄的規則來經營生活,碰到任何問題都從書本中尋求解決之道,結果是無一例外的失敗。福樓拜給出的解決方案是讓主人公放棄對文字的應用,而只是去復制它們,這是文學對文學性的另一種抑制形式——兜兜轉轉,一切又回到原點,書本的文字仍然待在適當的空間內,小說的情節自我取消了。
《包法利夫人》是一個更好的案例。福樓拜在小說中一方面放縱文學性,給沉默詞語以極大的流竄空間,另一方面,他又用了殺死愛瑪·包法利這種最極端的方式來壓制文學性的民主。我們知道,福樓拜把風格/筆法作為一種徹底看問題的方式,他要讓藝術隱形,作者的意志潛入幕后,一切都為風格服務,作者對句子和情節的各種處理也要干凈利落,不留痕跡。然而,他筆下的愛瑪·包法利在跟他唱反調,愛瑪接觸了不該接觸的浪漫小說之后,要讓藝術在生活中顯形,用藝術來裝點生活。所以,可以在小說中看到兩種沉默的言語。一種是愛瑪·包法利式的,用藝術來裝點生活,讓蠟燭臺、跪凳、服飾珠寶等等沉默之物為她羅曼史式的生活作證。另一種是福樓拜式的,讓沉默之物自己說出他們愿意說的。比如讓小地方的農家女成為小說的主角;比如對各種各樣的靜態細節作事無巨細的描寫,讓陽光、塵土、綠草等等沉默之物都出來說話。福樓拜式的沉默言語“成為無理由事物的純粹強度”,是“從意義王國里解放出來的物體那自由的呼吸”(《文學的政治》34—35)。以上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沉默言語。福樓拜以此在他的藝術和他的人物之間劃下清晰的界線。但是,為了達到這一效果,福樓拜就得更多地讓沉默之物發聲,讓沉默的言語成為小說的日常,最后,我們發現,小說的情節基本是由這些平常生活的沉默串連起來的。文學性的過度使《包法利夫人》成為日常生活的洪流。福樓拜采取的補救方式是用文學總體化(totalized)來整合溢出的細節。
舉例來說。小說第二部第八章著名的農業展覽會的段落,多聲部話語同時發聲,一片嘈雜。參議員在臺上發言,鼓動小鎮農民繼續為國家服務;羅多爾夫在愛瑪耳邊低語,鼓動愛瑪獻身于他。但是,有那么一個時刻,兩位男性的話語在愛瑪這里都是無聲的,她沉浸在自己的感官里,什么話都聽不見,在她被羅多爾夫誘惑的這個瞬間,在她又一次愛上一個男人的瞬間,她聽到了自然界的沉默的言語:她聞到了羅多爾夫胡子上香草和檸檬的氣息,她瞥見了遠處舊驛車行駛揚起的長長煙塵,她的內心像被陣風揚起的沙粒在芳香里起舞,她盡情吸進攀在柱頭上的常春藤的清香氣息,把這些感官都調動完后,愛瑪才透過自己太陽穴的汩汩脈搏聲,聽見了人群中的嘈雜聲響和參議員的單調演講(福樓拜140—41)。這里,沉默的言語喋喋不休,充滿了小說的空間。但是,這種沉默言語的嘈雜喧囂并不是雜亂無章、肆意生長的,它們有共同點。這些微觀的分子式的存在在愛情的名義下實現了總體化,它們共同服務于一種總體性。香味、煙塵、沙粒所形成的復合效果共同寫出了愛瑪對羅多爾夫的愛情。——這樣的總體化是對文學純粹性即“美文”的回歸。體現出福樓拜對民主文學性游歷的收—放力度。——文學以總體化壓制了文學性。
從以上三個案例中,我們發現,引導主人公犯下罪行的是書寫,而不是金錢。這是文學性的罪過。在這些作品的結尾,民主的文學性無一例外都被壓制了。書寫在自然的感性分配體制之外游蕩,流向不知名的所在,但是,為了讓它們被聽見,它們又得向自然體制靠攏,這樣,它們通常總是又回到自然體制之內,成為里面的一環。在文學中,不被計算在內的部分如何從不可見變得可見?沉默的言語如何從不被聽見變得可被聽見?這種“犯罪+贖罪”的模式是其基本的實踐模式。平等“以一種特定的過錯形式”對社會秩序發揮作用:“正是過錯將共同體建構成為一個奠基于沖突之上的共同體”(The
Flesh
of
Words
71)。他們犯下的過錯是被既定的感性體制所認定的過錯,而他們補救的方式就是用既定體制認可的方式,所以,不外乎兩個結果:一個是他們由不可見變得可見,取得被承認的成功;另一個是他們重新回到不可見的位置,重新在體制內隱身起來。但是,事情沒有這么干凈利落,這里仍然有偏差存在,即便補贖了罪過,還是有什么東西改變了。比如銘刻在土地上的溝渠和水流——從無意義的噪音變成了有意義的話語。由于民主的文學性的介入,無分之分犯下了過錯,但是,由于這個過錯,無分之分也從不被看見變得可以被看見了。這就是偏差。這種偏差構成了對既有的感性分配體制的微調和修正,所以,朗西埃說“書寫是話語正當秩序的失衡”(The
Flesh
of
Words
103)。另一方面,通過吸收這些界外之物,文學不斷調整自身,形成新的規范。盡管不斷地在越界,但文學還是有一套規范,并不是說沒有規范了,所以文學還是有其界限。“文學并不是簡單地、完全地遵循文學性的解離所追蹤的那個將身體與政治聯系在一起的路徑。相反,文學總是傾向于建立自己的政治或元政治。”(Dissenting
Words
194)文學的政治需要書寫的不受控制的民主;而政治的文學又要求文學仍然是文學,不論如何重組感性經驗,最終都是要讓其變得可見,這就不能過分跳出美文的框架。美學體制下的文學就在二者的緊張關系中活動,交出一份份文學的答卷。從這里我們就能知道,朗西埃為什么說“文學性是一回事,文學又是另一回事”。文學是文學,需要民主的文學性為其注入創新的活力;而文學性則屬于所有的書寫體制,它是所有的沉默文字的可用性。“平等只是以一種在個別情況下可資銘刻的形式、一種與處于治安秩序核心之平等的爭議和確認有關的形式,來提供政治現實。”(《歧義》65)文學要提供的就是這種個別情況。巴爾扎克《鄉村教士》的第三章曾經被指責為完全多余。一方面,作家采取了倒敘的方式,案件很快就發生了,然后是破案的過程。以偵探小說的視角來看,或者從故事情節的完整性來說,小說的最后一章確實多余,因為謎底在第二章就已經揭開了。另一方面,從巴爾扎克的初衷來看,他就是要以鄉村神父為主人公,寫一位教士用上帝的言語感化人心、改變鄉村的故事,這也不需要描寫韋蘿妮克死亡的第三章。那第三章留著干什么呢?朗西埃分析認為第三章才是最值得稱道的地方。前兩章寫了罪行發生的前因后果以及偵查的經過、改造鄉村的事跡。第三章寫了主人公的心路歷程,她的懺悔和死亡。這使小說在神父用圣言感化人心的線索之外,多出了另一條線索,專屬于韋蘿妮克的故事,不是神父的功績而是她本人如何去贖罪的故事,文學性的“犯罪+贖罪”的鏈條在這里才得以完全。因此,恰恰是第三章才最充分地體現出巴爾扎克對當時社會上由民主所帶來的混亂的思考。這并不是無關緊要的。我們發現,雖然巴爾扎克是保皇派、福樓拜是漠然派,但作家的政治立場似乎并無關系,恰恰是這些保持了探索精神的作家給予文學的政治最大的實驗空間。反而是那些要用文學傳遞政治觀點的作家,最后只能鎩羽而歸:他們一開始就有了明確的答案,沒有困惑,文學的政治也就少了演武之地。無論什么時候,文學創作都是一個探尋答案的過程,這種探尋與民主的不確定性相互生發,使文學性的悖論成為文學的生產性矛盾。
朗西埃把平等的預設導入對文學之政治的討論,他對“文學性”的重構拒絕了排他性的文學定義,著重指出任何人都有能力打破生活的假面,重新創造與歷史的聯系。這是一個徹底的激進民主派。但是,朗西埃的“政治”并不是沒有限制的。就文學來說,文學的政治是偶然的。即便主人公們最后仍然無法逃脫被體制收編的命運,只要他們曾經在體制之外游蕩并沖擊體制,曾經政治過,就夠了。因為他們已經以他們的曇花一現改變了共同的風景。朗西埃說,政治只是偶然的,它不會一直發生;關鍵是,文學制造了無分之分的現身場域。從這個角度看,朗西埃的文學政治理論是對資本主義現行代議制民主體系的增補和修正。這位激進美學旗手的底色是改良主義的。
朗西埃論述的矛盾之處遠不止這一點。回到本文開頭所引朗西埃對文學和文學性的區別定義,“歷史”成為一個關鍵字眼。但也正是“歷史”讓朗西埃的文學和文學性概念陷入自我論證的循環。一方面,如果文學的政治是偶然的,那就等于“剝離了政治的任何具體的歷史銜接關系”(Rockhill203);另一方面,如果朗西埃對文學的定義“歷史性的書寫體制”能夠成立,那就不存在脫離歷史的文學政治。朗西埃對“文學性”的定義也存在同樣的困難——“沉默文字的可用性”,可用性如果要成立,就不能脫離具體的歷史語境;這就反駁了文學政治之偶然性。而如果文學政治之偶然性是不成立的,那朗西埃的整套論證基礎就全部失效了。
朗西埃在不同場合就外界對他的批評做出過回應。他并不否認其論述中存在武斷和自相矛盾。但是,他強調這種矛盾性論述必須被更好地理解。他希望讀者把關注點放在文學的發現上。如他所言,文學是一種可能性體制,實現了再現詩學的美文范式所明確的規范言語與不合規的沉默言語之間不可能的調和。通過文學,無限的可能性空間被打開了。這種向不可能的敞開使文學不斷地超越自身。什么是文學?什么是文學性?朗西埃回答說,文學性并不是要去定義什么是文學,而是要使文學不斷地突破現狀,自我超越。“文學的概念永遠是不準確的。因為明確的概念意味著異議空間的關閉。”朗西埃堅持了他的樂觀主義:對無限可能性敞開的文學總歸意味著希望,指向更美好的未來(Dissenting
Words
198-99;Mute
Speech
172)。注釋[Notes]
① 因此,我們可以發現,埃里森·蘿絲在《朗西埃:關鍵概念》一書的相關章節中對朗西埃使用“文學性”的歷史考證由于僅以英譯本為資料,用literarity來檢索,追溯就并不可靠。參見《朗西埃:關鍵概念》,讓-菲利普·德蘭蒂編,李三達譯(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8),第171頁。
② “感性分配”是朗西埃使用的一個專門術語。法語原文為le partage du sensible,英譯為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就字面意思來看,sensible在法語里指“可感覺的、能感受的、感性的”;partage則同時具有“分割、分配、分享、瓜分”的意思;不論取哪一個意義都不能完全言盡其義。目前漢語學界較為通行的譯法“感性分配”是參照英譯選取其較為中性的表述。就術語的具體含義來看,“感性分配”指的是“一套統治感知秩序的隱性法則,在一個共同體中,通過預先建立內在的感知方式來分配參與的位置和形式。因此,感性的分配產生了一個基于固定視野的不證自明的感知體制,這一體制形塑了什么是可見、不可見,可說、不可說,可思、不可思,可做、不可做”。并且,每個時代的藝術實踐與政治共享著同一套感性分配的邏輯。參閱Gabriel Rockhill.“Glossary of Technical Terms.” in Jacques Rancière.The
Politics
of
Aesthetic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
.Trans.Gabriel Rockhill (London,New York:Continuum,2011),85.③ 這種風格同樣可見于雨果《巴黎圣母院》和左拉的自然主義小說。可參照左拉的自述:“在我們的作品中,泉水開始歌唱,橡樹開始相互交談,巖石猶如被正午的酷暑所征服的女人一樣發出嘆息和悸動。葉子上有交響樂,青草也被賦予角色,成為光與氣味的詩歌。[……]我們渴望擴張人性的范圍,甚至使其滲透進鋪就道路的石塊里。”(Mute
Speech
185)在朗西埃,“石化”有使沉默之物發聲和使有聲之人沉默這兩個面向。④ 朗西埃對雨果《巴黎圣母院》的分析可作參考:“小說在諸如大教堂的石頭等等這些沉默的物體上銘刻下意義,賦予它們具現認識的力量。雄辯的石頭取代了再現體制下話語的修辭組織和行為的模仿布置,形成了一種新的表達方式。《巴黎圣母院》通過對事物的活化,以及相應的對人類行為和語言的石化,顛覆了以往的詩學體制。這是一首巨型的‘獻給石頭的散文詩’,它也體現了作為一種虛構類型的小說的興起,也就是說,小說是一種打破了一般原則的體裁,它消除了再現主體/主題與再現方式之間的層級關聯。”參閱Alison James.“Mute Speech.”Understanding
Ranci
ère
,Understanding
Modernism
.Ed.Patrick M.Bray.New York:Bloomsbury Academic,2018.251.⑤ 《鄉村教士》1839年在《新聞報》上分三章連載:第一章“基督教的關懷”(現第二、三章),第二章“韋蘿妮克”(現第一、四章),第三章“踏入墳墓的韋蘿妮克”(現第五章)。1845年收入“人間喜劇”時巴爾扎克將全書章節結構做了前后調整和重新劃分,分為五章,現中譯本采用的是調整過后的分章。但朗西埃的討論基本上采用的是《新聞報》連載的三章版本(見《詞語的肉身》第二章《巴爾扎克與書的島嶼》)。本文循朗西埃,采用三章版本進行分析。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Battista,Emiliano,ed.Dissenting
Words
:Interviews
with
Jacques
Ranci
ère
.Trans.Emiliano Battista.New York:Bloomsbury Academic,2017.古斯塔夫·福樓拜:《包法利夫人》,周克希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7年。
[Flaubert,Gustave.Madame
Bovary
.Trans.Zhou Kexi.Shanghai: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2017.]雅克·朗西埃:《歧義:政治與哲學》,劉紀蕙等譯。臺北:麥田出版社,2011年。
[Rancière,Jacques.Disagreement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Trans.Joyce C.H.Liu,et al..Taipei:Rye Field Publishing Co.,2011.]——:《文學的政治》,張新木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
[- - -.The
Politics
of
Literature
.Trans.Zhang Xinmu.Nanjing:Nanjing University Press,2014.]Rancière,Jacques.Disagreement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Trans.Julie Rose.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8.- - -.Les
noms
de
l
’histoire
.Paris:Editions du Seuil,1992.- - -.Mute
Speech
:Literature
,Critical
Theory
,and
Politics
.Trans.James Swens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1.- - -.The
Flesh
of
Words
.Trans.Charlotte Mandell.Palo Alto: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 -.The
Philosopher
and
His
Poor
.Trans.Andrew Parker.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4.- - -.“The Politics of Literature.”Substance
33.1(2004):10-24.Rancière,Jacques,Solange Guenoun,James H.Kavanagh,and Roxanne Lapidus.“Literature,Politics,Aesthetics:Approaches to Democratic Disagreement.”Substance
29.2(2000):3-24.Rockhill,Gabriel.“The Politics of Aesthetics:Political History and the Hermeneutics of Art.”Jacques
Ranci
ère
:History
,Politics
,Aesthetics
.Eds.Gabriel Rockhill and Philip Watts.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9.195-215.張漢良:“‘文學性’與比較詩學”,《中國比較文學》1(2012):19—34。
[Zhang,Hanliang.“Literaturnost and Comparative Poetics.”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1(2012):1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