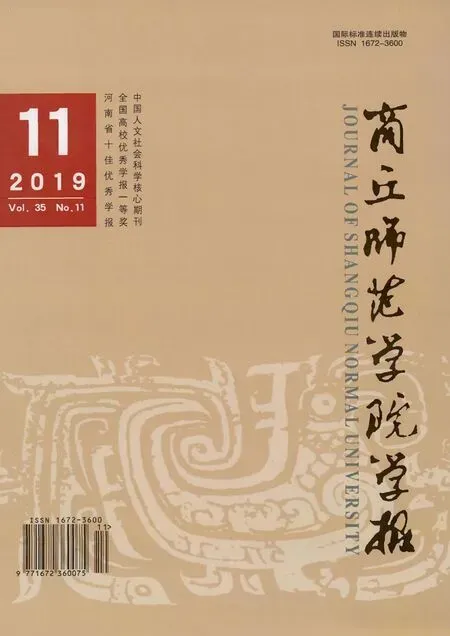盛名之下:傅勤家和她的《中國道教史》
韓 吉 紹
(山東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山東 濟南 250100)
在民國學術界中,道教研究是一個很不受待見的冷門領域。受西學大潮影響,當時大多數學人都認為道教完全是荒誕迷信、封建余孽,對社會有百害而無一利,早該徹底革除,哪還有什么研究價值。像魯迅先生所謂“中國根柢全在道教”,胡適先生所謂“整部《道藏》就是完全賊贓”,就是那個時代主流觀念的代表性標簽。然而在如此嚴酷的思想環境中,道教研究竟在夾縫中生發,并取得不俗的成就,出現像“三陳”(陳寅恪、陳垣、陳國符)這樣的大家,不能不令人驚奇。近些年來,隨著民國風在知識界和學術界勁吹,早期道教研究作品也趁勢引起越來越廣泛的關注。不過令人意外的是,關注度最高、最走紅的既不是陳寅恪“孤明先發”之論,也不是陳國符“考鏡道藏源流之作”,而是兩部即便是專業學者閱讀起來也不輕松(并非因為內容深奧)的特殊著作:一部是學者兼文學家許地山寫了一半的《道教史》,一部是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傅勤家編撰的《中國道教史》。這里要討論的正是后者。

圖一

圖二
傅勤家著《中國道教史》于1937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見圖一),它與商務印書館1934年出版的許地山《道教史(上)》是民國時期道教通史的兩種代表性著作。這兩種書在新世紀中同時得到廣大讀者異常青睞,多達十余家出版社爭相印行,甚至被列為“領導干部讀經典”系列,受眾面完全超越了專業范疇,作為學術著作可謂火爆。數年前,它們又同時入選商務印書館“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2017年,進一步被篩選進入該套叢書120年紀念版(見圖二)。不過,令我十分困惑不解的是,對于《中國道教史》這樣有市場有地位的“明星”著作,學術界中長期見不到應有的客觀學術評價,對作者傅勤家的情況更是一無所知。大概是為了彌補這樣的缺憾,商務印書館120年紀念版特意約寫了一篇書評,題名《中國學者的第一部完整的〈中國道教史〉——讀傅勤家〈中國道教史〉》。可是這篇書評不僅沒有解決上述兩個問題,反而造成進一步的混亂。為正本清源,我認為有必要再加以分析討論。
一、傅勤家其人
1933年,商務印書館王云五主編的《萬有文庫》推出一冊《道教史概論》,署名傅勤家。該書雖然是國內第一部道教通史類著作,但內容過于簡略,出版后在學術界沒有產生什么影響。1937年,商務印書館王云五和傅緯平(即傅運森)主編的《中國文化史叢書》又推出一冊《中國道教史》,作者同為傅勤家。根據書中介紹得知,該書原來是此前《道教史概論》的增補本,篇幅增加數倍。但傅勤家究竟為何人,兩本書中都沒有只言片語介紹,以致時過境遷后,今天成為一大謎團。到目前為止,我只見到兩種有關傅勤家身份的討論:一種是網絡帖子,認為傅勤家是傅運森的筆名;另一種是商務印書館版的書評,推測傅勤家與傅代言為同一人。遺憾的是,這兩種推測都是錯誤的。
先從傅運森說起吧。傅運森(1872—1953),字緯平,湖南寧鄉人,活躍在民國時期,是一位歷史學家、教育家和出版家。1909年,受張元濟聘請進入商務印書館工作。1936年,與王云五一起推出《中國文化史叢書》,《中國道教史》為叢書第二輯所出。傅運森與傅勤家的關系固然可疑,但他們實非同一人。在《中國道教史》出版前的1936年,商務印書館出了兩種傅勤家的譯作,一是英國Charles Bell著《西藏志》,一是日本白鳥庫吉著《康居粟特考》。據《西藏志》書末介紹,該書原由董之學譯出,出版過程中遭“一·二八”兵火,書稿后半部焚毀,“因托傅勤家女士續譯,即自第十三章末頁起,迄于第二十七章,皆傅女士續譯者”。傅勤家既為女士,自然不可能為傅運森。
傅運森有一個兒子叫傅彥長(1891—1961),其平生日記部分保存下來,現收藏在上海市圖書館。近年,該館歷史文獻中心張偉先生將這些日記作了整理,自2015年開始分期刊登在《現代中文學刊》雜志上。閱讀這些日記后得知,傅勤家實為傅彥長之妹(另有一妹名傅明家)。至于傅勤家的年齡及職業,1932年9月14日的日記有一條重要記錄:“勤妹語予,她今日第一次拿到她自己工作出來的錢,一共二十五元。”[1]檢索民國資料,《申報》1932年8月7日號刊登的上海市教育局第六屆小學教員登記及格人員名單,其中有“傅勤家”之名。而當時上海市的教師工資水平,根據1933年的資料統計,市立初等學校(包括幼稚園和小學)教師月薪從5元到100元不等,其中以20-60元的人數最多,占83%[2]52。結合這三則材料,可以斷定《申報》上的小學教員傅勤家即《中國道教史》作者傅勤家,也即傅運森的女兒,她于1932年八、九月間開始參加工作,當值青春年華。1934年,傅勤家發表《石先生的國文課》一文,描述了小學生上課時頑皮嬉鬧的場景,正是其教學工作的生動反映[3]174-177。
傅運森精通英文和日文,傅彥長也曾長期游歷日、美,那么傅勤家的外語水平如何呢?Charles Bell《西藏志》和白鳥庫吉《康居粟特考》原作均為英文,此外傅勤家還翻譯過T.B.Macaulay著《腓特烈大王》(商務印書館1938年出版),可見她精通英文。又她在《康居粟特考》譯者序中說,該文另有日文版發表,但她沒有找到日文雜志,所以翻譯時未能作對照。由此來看,傅勤家還能閱讀日文,下文我們會看到,她的這項能力在《中國道教史》中有充分展現。
二、《中國道教史》其書
要客觀評價傅勤家的《中國道教史》,首先需要了解一部日本著作。1926年11月,商務印書館王云五主編的《國學小叢書》推出日本道教研究先驅小柳司氣太的《道教概說》(1930年王云五主編的《萬有文庫》再版)一冊,譯者是后來成為漢奸的陳彬龢。巧合的是,1927年11月,中華書局也推出該書的漢譯本,譯者是傅代言。據書中序言介紹,傅氏先是將譯稿郵寄給友人蔣維喬(1873—1958,近代著名教育家、哲學家、佛學家),再由蔣氏刪訂,改名為《道教源流》。查閱《蔣維喬日記》(中華書局2014年版),蔣氏于1926年8月26日閱讀完譯稿,9月9日開始修改,10月25日改畢,26日撰成序言。從時間上來判斷,這兩個譯本應是各自獨立進行的(內容也顯示如此)。《道教概說》篇幅不長,是日本初期道教通史研究的代表作,其翻譯引進對國內道教研究起到了較大促進作用。
《道教概說》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在那里工作的傅運森應當知曉。傅彥長在1927年11月23日的日記中記錄了一段很突兀的文字,強調道教的教理綱要應該先看魏伯陽的《周易參同契》與葛洪的《抱樸子》[4]。經核對,原來他是抄錄自《道教概說》而非《道教源流》。我沒有找到傅勤家何時開始關注道教的證據,但肯定與家庭影響不無關系,因為她在1933年的《道教史概論》中使用了其父傅運森的知識[5]。不過,《道教史概論》中沒有發現小柳司氣太著作的明顯影響。傅勤家對小柳氏以及其他日本學者研究成果的大量引用,見于后出的《中國道教史》。
與過于單薄的《道教史概論》相比,《中國道教史》作了較多增補和調整,全書包含二十章,第一章緒言,第二章外人對于道教史之分期,第三章諸書所述道教之起源,第四章道之名義與其演變,第五章道教以前之信仰,第六章道教之形成,第七章道教之神,第八章道教之方術,第九章道教之修養,第十章道教之規律,第十一章道佛二教之互相利用,第十二章道佛二教之相排,第十三章唐宋兩朝之道教,第十四章道教之流傳海外,第十五章道教經典之編纂與焚毀,第十六章道教之分派,第十七章明清時代之道教,第十八章現在之道藏與輯要,第十九章宮觀及道徒,第二十章結論。總體而言,其結構更趨完整,內容也較前豐富,從而使其成為一部相對比較完整的道教通史,其實也是民國唯一一部像樣的道教通史。從這層意義上說,傅勤家和她的《中國道教史》在學術史上毫無疑問都應該占有一席之地。不過,一部學術作品要成為真正的名著,進而成為經典,應該具備一些基本特點。如果是開創性之作,應有奠基之功;如果是綜合性之作,應有集大成之力。無論哪一種經典,歸根到底,都應該具備極高的學術水準。用這個標準來衡量民國的道教研究作品,陳寅恪的《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系》《陶淵明的思想與魏晉清談之關系》等系列論文,陳國符的《道藏源流考》等,都可以無爭議地入選,但傅勤家的《中國道教史》則很遺憾不應歸入此列。為什么這樣講,我們需要對《中國道教史》有全面認識。
首先審其學術傳承。在《中國道教史》之前,國內其實已有多種重要道教史研究論著問世,像陳銘珪的《長春道教源流》(1921—1922)、許地山的《道家思想與道教》(1927)和《道教史》(上)、陳寅恪的《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系》(1933)等。對這些專業水平較高的成果,傅勤家在書中沒有明顯吸收,她似乎不大了解國內學術界的最新發展情況。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她大量引述了日本學界的研究成果。在《中國道教史》較《道教史概論》新增的六章中,有一半來自日本研究,其余擴寫章節中也有引述內容。具體而言,她援引最多的是小柳司氣太的作品,包括《道教概說》《〈后漢書·襄楷傳〉之〈太平清領書〉與〈太平經〉之關系》《論道教與真言密教之關系》(《論道教真言密教之關系及修驗道》)等。其他還有妻木直良《道教之研究》、常盤大定《道教發達史概說》、三品彰英《新羅花郎制度考》、狩野直喜《支那學文藪》等多種。不過顯而易見的是,這些引述都是直接搬運過來作為書中一章或一節,沒有繼承性或發揚性的研究。這表明,傅勤家無論在學理上還是在技術規范上都沒有表現出應有的專業水準。另外,盡管傅勤家聲稱這些引述都是自譯,但實際上至少有兩種采用了他譯:一是小柳司氣太的《道教概說》,使用了中華書局和商務印書館兩種譯本;二是三品彰英的《新羅花郎制度考》,使用了其父傅運森的譯文。
其次查其資料來源。傅勤家對道教研究有一種可貴的責任感,這一點超過了很多同時代的學者。她在書末寫道:“道教實中國固有之宗教,剖析而分明之,豈非學者之責哉?”不過限于觀念和視野,沒有證據表明她注意到當時國內對道教文獻研究的重要進展[如劉師培《讀道藏記》(1911)、劉咸炘《道教征略》(1924)、王國維《長春真人西游記校注》(1926)、曲繼皋《道藏考略》(1933)、湯用彤《讀太平經書所見》(1935)等]。由此導致她對《道藏》的史料價值嚴重認識不足,撰寫道教史竟然說“道藏之書雖多,要皆空虛誕妄,等于無物,無從采擇”。觀其書中所用原始資料,可知其言非虛,道經使用的確不多,而且還有不少缺乏代表性,甚至使用不恰當。例如,她多次引明代胡應麟的筆記資料《少室山房筆叢》中的二手甚至多手記載來陳述道教歷史,使用當時雜志上的通俗文章《瓊崖風俗志》介紹武當派道教等,諸如此類的輕率行為,書中俯拾皆是。

圖三
第三總其寫作特點。與小柳氏和許地山的著作相比,傅氏《中國道教史》最大的寫作特點是論少引多,全書從頭到尾都在堆砌資料,有時候到了不堪卒讀的程度。這種寫作方式和她對日本研究采用“拿來主義”的做法完全一致,經常造成相關問題沒有深入討論,或者不加辨別,或者缺乏見解的現象。1939年《圖書季刊》新1卷第3期刊登了一篇《中國道教史》的書評(見圖三),作者對傅勤家的這種寫作方式進行了嚴厲批評,說她采用日人著作有時不加辨別刪汰,以直引為能,浪費篇幅,使讀者目眩頭痛;對道教資料則直抄原書,洋洋不休,冗長可厭。最后給出這樣一句總評:“斥是書為雜抄,不為過苛也。”由此可見,對《中國道教史》的缺點當時讀者即有清醒認識。
最后看其學術影響。從學術著作的發行量和受眾范圍來看,《中國道教史》是一本不折不扣的暢銷書,甚至遠遠超過改革開放后出現的兩部道教通史代表作。不過這與真正的學術影響力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以經典之作陳國符《道藏源流考》為例,該書考證極具功底,用著名語言學家羅常培先生的話說:“于三洞四輔之淵源,歷代道書目錄、唐宋金元明道藏之纂修,鏤版及各處道藏之異同,均能究源探本,括舉無遺。其功力之勤,蒐討之富,實前此所未睹也。”[6]3自其問世以來,一直是道教及道藏研究的必備參考書,至今仍然難以逾越。反觀《中國道教史》,現在它流傳雖然如此廣泛,但學術界鮮有引用者,無論是書中結論還是所用資料,大部分早已時過境遷,不合時宜。
讀罷上述文字,想必不難理解我的困惑所在。令人玩味的是,這樣的學術作品,這樣的市場現象,在今天并不鮮見,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的呢?不管怎樣,我想,起碼對這部書還是塵歸塵,土歸土,還其歷史本來面目為好罷。
(感謝成都中醫藥大學王家葵先生和四川大學周冶先生為本文寫作提供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