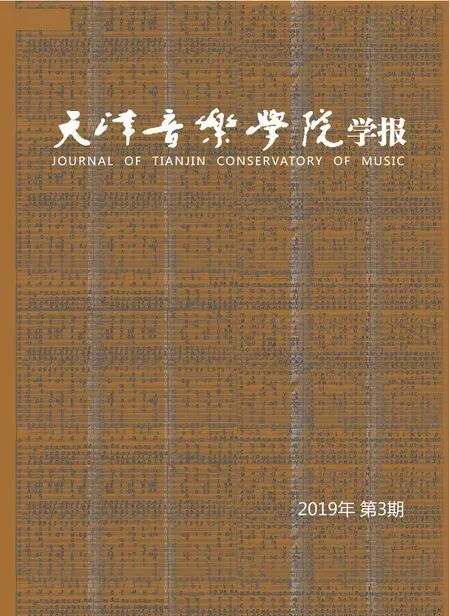一勾勾戲唱腔源流考
李德敬
一勾勾是流行于山東德州的臨邑、齊河、夏津縣以及聊城、東平等地的一種地方小戲,因每句句尾都有個向上七度或八度以假聲演唱的勾腔而得名。一勾勾大約在19 世紀中葉發展成為戲曲,也被稱為“四音( 戲) ”“四根弦”“河西柳”等。
一勾勾進入到學者研究視野是近十幾年的事,以被列入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為時間節點,陸續有十余篇論文發表。這些文章的研究角度有這樣幾類,一是對其歷史、現狀以及音樂情況作整體式介紹,二是研究其藝術特色,三是研究當下的傳承問題,四是著眼于唱腔旋律與方言的關系,五是關注其伴奏樂器及演唱發聲。從這些已有成果看,尚未有從音樂形態的角度對其劇種音樂做深入研究者,包括其音樂來源、“聲腔”歸屬等問題。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編纂的《戲曲集成》《戲曲志》等集成志書,雖有對一勾勾劇種歷史和音樂的概括性介紹,但失之籠統,一些說法也缺乏論證,如《中國戲曲志·山東卷》認為“一勾勾音樂吸收借鑒了當地姊妹曲種、劇種和民間演唱的音樂素材。”但并未進一步指出吸收了什么曲種、劇種和民間演唱的曲調。由于其音樂源流問題未搞清楚,一勾勾在山東戲曲的分類中,暫被歸為“歌舞—戲曲”類,與梆子腔系統、弦索系統、肘鼓子系統并列。但是這種分類法的問題是顯而易見的,“歌舞—戲曲”表明的是戲曲形成的一種來路,梆子腔系統、弦索系統等則是聲腔的系統,二者不是一個分類角度,也就無法并列。除了一勾勾之外,在山東的戲曲中,被歸為“歌舞—戲曲”類還有二夾弦、四平調、王皮戲等。另外還有“說唱—戲曲”類,也存在同樣的問題。我們把目光投向全國,除了四大聲腔劇種外,為數眾多的地方戲很多由于音樂源流和歸屬問題尚未理清,也只得暫被歸為“說唱類”“歌舞類”中,可見,這是一個帶有普遍意義的問題。要解決這一全局性的問題,非是一蹴而就的,需從個案做起,對每一個劇種的音樂進行分別研究,然后對它們進行比較,最后再進行歸類。本文擬對一勾勾唱腔音樂的源流做一考察,以期對于戲曲音樂的分類問題做一點基礎性工作。
一、一勾勾劇種淵源
一勾勾唱腔音樂常以其劇種來路為依據,目前主要有三種說法: 高唐鼓子秧歌說、1《中國戲曲音樂集成·山東卷》編輯委員會:《中國戲曲音樂集成·山東卷( 上) 》,中國ISBN 中心1996 年版,第357 頁。花鼓丁香說2《中國戲曲志·山東卷》編輯委員會:《中國戲曲志·山東卷》,中國ISBN 中心1994 年版,第116 頁。和兩夾弦戲淵源說。3李趙璧、紀根垠:《山東地方戲曲劇種史料匯編》,山東教育出版社1983 年版,第368 頁。這三種說法中,“高唐鼓子秧歌”,根據《集成·山東卷》的描述“腰挎花鼓、雙手持鼓槌、身穿彩衣、上妝,進行行街、圈場演唱”,與山東花鼓( 聊城花鼓) 的表演形式完全一致,實為聊城花鼓,而且花鼓本來也有“花鼓秧歌”的別稱; 花鼓丁香,是山東花鼓中的南路( 因主要演《休丁香》而得名) ,流行于菏澤、濟寧地區,據說聊城花鼓就是由花鼓丁香傳播到聊城而形成;至于兩夾弦戲,是由南路花鼓直接發展而成,其形成時間,與一勾勾接近,都在1850 年左右,從形成戲曲時間看,這兩個劇種之間不存在傳播的關系,應是各自由花鼓發展演變而來。
那么,一勾勾的唱腔音樂與山東花鼓有多大程度上的聯系? 又受到哪些民間音調的影響?當筆者將一勾勾與花鼓的曲調進行對照時,直觀的感受是二者似乎不太像,經過反復聆聽和試唱,又發現存在某些內在的聯系,再將一勾勾與魯西北的民歌小調進行比較,則比較容易發現一些直接的聯系。鑒于一勾勾為板腔體結構體式,筆者將其主腔與山東花鼓和魯西北一帶的民歌音樂分別做一比較,從中總結與它們的聯系與差別。由于聊城花鼓從《中國民間歌曲集成·山東卷》中收錄的六首譜例看,都是四句式民歌,還未發展到說唱階段,按照戲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太可能直接由民歌發展而成。接下來,筆者將主要分析南路花鼓的特點。
二、一勾勾與山東花鼓音樂的比較
已有研究表明,山東花鼓系由安徽花鼓流入山東發展而來,時間不晚于清初,山東花鼓最初由一人演唱,后發展到載歌載舞的男女對唱,并以其為主要形式,所唱由四句民歌發展到八句子、十二句直至幾十到上百句的“段子”,進入到說唱音樂階段。
一勾勾主腔無曲調名,亦無男女腔之分,早期統稱“平唱”,是一種無板無眼的唱腔,后逐漸發展出[原板][散板][垛子板]等,建立專業劇團后,又創作出[慢板][流水][搖板]等。4來自對原臨邑一勾勾劇團伴奏人員馬殿發、作曲于汝朝、演員龍傳英等人的采訪。早期旦角由男演員扮演,唱腔較為簡樸,出現女演員后,較之前變得婉轉、抒情,并且起始音音高有所提高。山東花鼓唱腔只有很簡單的板式,如散板、平調一眼板、無眼板類直板等,男女腔亦無明顯區別。為了確保研究結果的有效性,文中所選一勾勾譜例均是筆者根據田野調查中采錄的民間藝人演唱記譜,而非經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音樂工作者創作改編過的唱腔,力求更接近劇種音樂原始面貌。
(一)一勾勾主腔音樂分析
譜例1. 一勾勾戲《李香蓮賣畫》李香蓮[旦]唱“平唱”5筆者根據1986 年禹城縣楊官營村一勾勾業余藝人張丁里演唱錄音記譜。



表1. 譜例1 唱腔形態分析
譜例2. 一勾勾戲《王小趕腳》二姑娘(男旦)[平唱]6筆者根據高唐縣四弦莊戶劇團馬希岐在2015 年山東省地方戲曲票友演出大賽頒獎晚會上的演唱視頻記譜。

對表1、表2 兩個表格的分析結果做一統計,我們可以發現女腔[平唱]特點如下:
①上下句結構。上句落“仄”,下句落“平”,上句落“2”或“1”音,下句一律落“1”;每句字數從八字至十五字不等,忽略襯字仍不等長,基本都是變化句式。

表2. 譜例2 唱腔形態分析
②上句落“re”或“do”,下句均落“do”,宮調式。音階多用變宮音“si”,清角“fa”次之。調式為七聲清樂宮或加變宮的六聲宮調式。
③每個樂句( 包括腔節) 都是板起板落。
④上( 句) “斷”下( 句) “連”的腔句結構特點。從譜例中提供的共計12 句唱腔看,有四對上下句(8 句) 呈現出上句兩截腔下句單節腔的上斷下連的結構特點。
⑤從旋法上看,每句句尾都有一個向上七度(3 -2) 的大跳,成為一勾勾的標志性特征。
⑥旋律骨干音,“do-re-mi”和“re-si -la”均為12 次,“la -do -re”為2 次,( 譜中依出現順序分別用II、III 和I 標出。譜例3 和譜例4 亦如此標記。)
(二) 山東花鼓音樂特點分析
以兩個一眼板[平調]為例。
譜例3. 山東花鼓《貨郎段》貨郎(生)唱[平調]7《中國曲藝音樂集成·山東卷》編輯委員會: 《中國曲藝音樂集成·山東卷》,中國ISBN 中心1998 年版,第799 頁。8花鼓唱腔無固定調高,為方便與一勾勾比較,以G 調記譜。譜例4 亦同。


表3. 譜例3 唱腔形態分析

?
譜例4. 花鼓八句子 女腔《九盡新春楊花開》9《中國曲藝志·山東卷》編輯委員會:《中國曲藝音樂志·山東卷》(上),中國ISBN 中心2002 年版,第287 頁。



表4. 譜例4 唱腔形態分析

?
據以上兩圖表,這兩段花鼓唱腔特征如下:
①結構為上下句,字數大多為七字句基礎上的擴充;
②旋律上句落于“la”或“do”,下句基本都落于“do”,七聲清樂宮調式;
③樂句開頭大量使用切分節奏,造成多在閃板或眼上起,風格比較活潑;
④除倒數第二句之外,句間和句內無過門,而且下句與( 下一個段式的) 上句以一個“連門子”10所謂“連門子”是下句尾部的旋律配以上句開頭的詞。相連,造成句與句之間、段與段之間連綿不斷的效果。
⑤旋法上多用級進及三四度音程,少用七八度大跳。
⑥多用“la-do-re”“mi -re -do”“re -si -la”骨干音,尤其是“la -do -re”和“mi -re -do”,在譜例3、譜例4 中各出現9 次和11 次。
(三) 一勾勾與花鼓音樂異同的比較
從以上對一勾勾和花鼓各自兩種板式的音樂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二者的相似之處:上下句結構,變化句式為主,骨干音多用“la-do-re”“re-si-la”和“mi-re-do”,調式都是宮調式,六聲大多加變宮,七聲則加變宮和清角。不同之處在于:一勾勾句間和句內有過門,句尾有“mi -re”七度大跳音程,板起板落,花鼓腔則句間無過門,句尾將一勾勾的“mi -re”七度跳進變為級進,閃板( 或眼) 起板落。應該說,二者在音樂材料上的共性不少,之所以聽起來不太像,主要是外在表現形態的差異,如標志性句尾甩腔的有無,節奏的穩健和活潑,唱腔的頓挫感和黏連性,等等。變造成化的原因主要是戲曲的主腔需是那種擅長敘事具有較強可塑性和表現力的曲調,單純的歌唱性曲調表現力太過單一。而促成這一變化的因素則是境內成熟板腔體大劇種如京劇、河北梆子、山東梆子的影響。經過了這樣的改造,一勾勾初步具有戲曲的程式化、敘事性特征,而花鼓還停留在載歌載舞的歌唱階段。
三、一勾勾唱腔與魯西北民歌的比較
一勾勾男腔的典型特點是曲調平直,常常由相鄰兩個音的重復構成,如同數唱。這樣的曲調在花鼓中并不多見,筆者發現,在魯西北商河、惠民、樂陵、臨邑一帶的秧歌調中,大量應用了這種旋法。如“打岔”( 也稱“搖葫蘆”) ,是商河樂陵秧歌中的一種小場演唱,所唱有《大觀燈》《饞老婆吃狗》《鴛鴦嫁老雕》等,曲調大同小異,特點是大量應用“sol、la”兩音,有的樂句旋律甚至完全以“sol、la”兩個音的交替構成。下面將一勾勾男腔與“打岔”旋律作一對比:
譜例5. 一勾勾《烏龍院》中“張文遠”唱段與“打岔”《盼郎》

可以看出,這兩段旋律如出一轍,秧歌調只是在第二句結束處出現了個經過性的“mi”,一勾勾唱腔第二句下行引入“re”和“do”,二者均具有平直如話的敘述性特點。
一勾勾男腔還可舉一例:
譜例6. 一勾勾《宋江殺惜》宋江(須生)唱[三板]11《中國戲曲音樂集成·山東卷》編輯委員會: 《中國戲曲音樂集成·山東卷》,中國ISBN 中心1996 年版,第362 頁。

這段旋律以“la-sol”開頭,并以這兩個音的交替貫穿整個唱段,偶爾出現“mi -do”六度跳進,配以有板無眼的“流水”板式,整體具有很強的語言性。
魯西北的秧歌調代表著這一帶小調的整體特點,即念誦性的音調。我們不妨推測,一勾勾男腔的這種曲調很有可能吸收自魯西北地區的秧歌調。
四、對一勾勾唱腔的“終極探源”
以上是針對曲譜文本所做的分析。但是筆者在田野調查中發現,藝人在實際演唱時曲調具有很大的靈活性,或者說不確定性。如,剛才所舉《王小趕腳》二姑娘唱段“六月里三伏好熱的天”這一句,既可以唱成“mi-do-re-mi-re-mi-re -do -do”,也可以唱成“re -si -la -re -sol-mi-re-do”,還可以唱成“do -la -do -la -sol -do”,另外《夜宿花亭》高文舉唱“高文舉來”幾個字,也有“mi-sol-mi-( 高) mi-re-do”和“la-sol-la-re-do”等不同的唱法。除了下句的落音和句尾的甩腔以及上句的腔節結構,其他都是可變的。而有意思的是,不管怎樣唱,都不影響一勾勾劇種音樂的風格,藝人和觀眾也都認可是一勾勾而不是別的戲。
對于這個現象,原臨邑縣一勾勾劇團作曲于汝朝曾告訴筆者“‘mi-do-re-mi’和‘re-sila-re’是一樣的,老藝人不識譜,在學唱過程中會不自覺發生變化。”“劇團在初期每次排戲,安排唱腔時只需確定每個唱段的板式,是[平唱]或者是[慢板],具體怎么唱由個人去發揮,因此每個人唱出來的[平唱]或者[慢板]都不一樣。”他還向筆者講起這樣一件事:1957 年,興隆鎮一勾勾劇團到濟南振成舞臺演出,連臺本戲《五女興唐傳》連演三天后,觀眾要求繼續演下去,但是戲已結束,誰都不知道“第四本”該怎么演,這時導演把演員叫到一起,把內容大概一說,分配下角色,晚上便開戲了,伴奏和演員竟配合默契順利完成了演出。事后問起演員是怎么唱的,卻都說“不知道”。伴奏也一樣,“一勾勾的伴奏樂器笛子和板胡不完全跟著旋律走,而是順著‘溜’,也不知怎么拉的,反正下次拉還會。一勾勾也叫‘河西柳’,這個‘柳’實際是‘溜’。”12來自筆者對于汝朝的采訪。時間是2013 年3 月10 日,地點在濟南于汝朝家中。無獨有偶,同樣源于山東花鼓的柳琴戲,除了句尾固定的拉腔和一些花腔唱法,其他地方的曲調也具有很大的靈活性,藝人的說法是“想怎么唱就怎么唱”,因而也被稱“怡心調”。甚至于上世紀50 年代,曾有北京的專家到柳琴劇團進行記譜,但是由于其唱腔過于自由,始終處于捉摸不定的狀態,這位專家花了兩個月時間居然沒有成功記下柳琴戲的唱腔曲調。13孔培培:《魂里拉腔——從拉魂腔到柳琴戲的傳承與變遷》,中國藝術研究院2007 年博士論文,第80 頁。來自田野的發現令我們無法滿足于僅依靠分析曲譜所得出的結論,我們不禁深思:造成一勾勾戲唱腔多變又不失劇種風格的終極因素究竟是什么? 筆者認為是——語言。
眾所周知,漢語語言與音樂關系密切,語言對音樂有著決定性影響,主要體現在旋律線、節奏、音色等方面,尤其是旋律線,這在戲曲中有突出的體現。“依字行腔”“腔隨字轉”是戲曲創腔的一個普遍規律。從某種程度上說,各種地方戲的形成,其實就是方言影響下的唱腔曲調確立的過程。筆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比較一勾勾戲唱腔與魯西北方言字調的關系14李德敬:《臨邑方言字調對一勾勾唱腔旋律的影響》,《齊魯藝苑》2015 年第1 期,第23—27 頁。,通過量化統計,二者一致的比率高達86%! 無論是逐字比對還是看語調的整體起伏,一勾勾唱腔曲調可以說就是當地語言的音樂化。
從字調與旋律關系角度看,前面所舉“六月里三伏好熱的天”和“高文舉來”兩句詞無論是配以哪種旋律,它們的走向與方言中的字調幾乎都是完全一致的,都是符合創腔原則的。因戲曲與民歌或歌舞音樂的最大不同在于它的功能首先是敘事,所以對唱詞意義的準確交代就成為演唱者和編曲者的首要追求,只要讓人聽明白,至于它是“mi -do-re-mi”還是“re -si -la -re”“do -la -do-do-la-mi-do”,并沒有實質性區別。一勾勾吸取了花鼓的骨干音來作為其音樂的“基因”,而具體的旋律旋法則依方言來安排,這正是遵循“敘事為要”的原則。這樣一來,前面的各種現象都有了解釋:演員在演唱時無需現學每一個劇目的板式唱腔,只需在已掌握的曲調基礎上,再結合具體唱詞的方言念法,將其“唱”出來就可以了,因而都能隨口唱,唱的還不一樣,關鍵觀眾還都認可,就是所依據的方言在起作用;唱幕表戲,大家都能即興創腔且配合默契,也是因為方言;而北京專家花兩個月也沒記出來的譜,也是因為方言字調所能配唱的具體曲調形式是多種多樣的。
還可提供一個事實為證,原臨邑一勾勾劇團的龍傳英曾對筆者談到,她的老師民間藝人焦連坤“唱得跟說似的,沒調兒!”但是觀眾卻很喜歡,因為“一聽就懂!”除了唱詞語言通俗外,旋律貼近語言聲調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至此,對于一勾勾戲的唱腔源流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一勾勾唱腔的確脫胎于山東花鼓,吸收其“la-do-re”“re-si-la”“mi-re-do”和“do -la -sol”骨干音,通過將“mi -re -do”變為“mi-( 高) re-do”,節奏上變閃板起為板起,去掉樂句之間的“連門子”,加入絲弦樂器過門,與純歌唱的花鼓發生了質的改變,具有了戲曲的某些程式化特征。同時,男腔吸收了魯西、北地區秧歌調的“la、sol”兩音交替的旋法來發展旋律;花鼓音樂對于一勾勾來說具有深層的隱形的影響,秧歌調則具有表層直接的影響。而對一勾勾唱腔起到終極作用的則是語言。
還有一個問題,一勾勾標志性的句尾翻高七度甩腔唱法來源于哪里呢? 筆者查閱山東境內的民歌,發現有兩種民歌有句尾翻高七、八度甩腔這一唱法,一種是魯南蒼山花鼓調( 花鼓最初所唱的民歌小調) ,另一種是前文提到的魯北秧歌調“打岔”。一南一北,一個是一勾勾的源起地,一個是形成發展之地,到底哪一個影響了一勾勾的這一特點? 在沒有確切證據出現之前,我們只能說或許是蒼山花鼓調已經埋下了這一特點的種子,抑或是二者皆有作用。不過,與一勾勾同源于花鼓的柳琴戲、茂腔、柳腔,也都保留有句尾翻高七度或八度甩腔的唱法,這又似乎指向了花鼓。這一問題留待以后進一步的研究。
余 論
從對一勾勾戲腔源的探究過程中,筆者的感受是:民間小戲的唱腔是異常活躍而易變的,我們在對其唱腔源流的分析不能只根據曲譜,曲譜是一次性、凝固的,只能說明某一次的演唱是這樣的,我們需要把不同的演唱版本放在一起,綜合考量,才能對其腔源問題作出一個相對合理的解釋。
從對一勾勾與花鼓音樂的比較中,我們可以看到由花鼓發展到戲曲,并無一支共同的曲調在維系,這是與聲腔類劇種的不同之處,聲腔類劇種是以某個曲調為核心構建劇種的唱腔體系,并通過傳播到各地形成聲腔體系,一勾勾唱腔則還未在語言基礎上實現旋律的自由和升華,尚未有一個音樂性強、性格鮮明、風格突出、辨識度高的曲調出現,也就無法在這樣一個曲調之上構建不同板式的曲調群。由此,我們說一勾勾尚無構成聲腔的可能。推而論之,與其同屬花鼓類戲曲的二夾弦、四平調以及其他“歌舞類”小戲,其聲腔問題也應大抵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