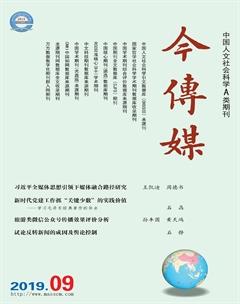淺論魯迅小說中的死亡描寫及其意義
摘?要:死亡主題是文學創作中無法忽視的部分之一。在魯迅的小說集中,尤其是《吶喊》《彷徨》這兩部小說,其關于死亡的描寫不可勝數。本文將通過簡略分析三類魯迅小說中的典型人物之死,領略魯迅小說中死亡意象蘊含的獨特的文學價值和審美意象,探尋魯迅小說中的死亡主題所表現的反諷意蘊,解讀魯迅先生在死亡背后賦予的“生”的希望和啟蒙意義。
關鍵詞:魯迅;小說;死亡描寫;啟蒙意義
中圖分類號:I2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8122(2019)09-0152-04
魯迅無疑是一位功力深厚的語言大師。他善于運用文字表現不同的氛圍,形成不同的風格,表達不同的內涵。因此,其小說人物的死亡現象千差萬別,獨具特色,具有研究價值。在為數不多的小說中,有一系列各種人物的不同死亡方式,有民主革命斗士無謂的犧牲、有貧苦百姓為生計所困之死、有知識分子不為社會包容之死……總而言之,他們都是封建制度和封建禮教的“犧牲品”。魯迅對死亡的描寫是作品意蘊寄托的手段之一,隱藏在文字下面的內容才是作者真正要表達的本意。本文選取了一些典型個例,將不同種類的死亡分類整理,進行更深一步地研究。
一、魯迅小說中的死亡描寫對象
(一)民主革命斗士之死
在魯迅的數十篇小說中,塑造了許多先驅者和革命斗士的形象。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藥》中勇敢獻身的民主革命斗士夏瑜。他生在一個舊勢力掌權的封建家庭,卻依然義無反顧地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這其中的艱難是可想而知的。他心中抱著救國救民的偉大理想,懷著一腔熱血干革命,最終卻被夏三爺為了“二十五兩雪白的銀子”出賣,落得入獄處死的下場。夏瑜將生死置之度外,哪怕在牢里,他還堅持呼喊著“這大清的天下是我們大家的”[1]。然而他的犧牲沒有換來一個人的響應,英雄事跡也淪落為群眾們的飯后談資。他被稱為“賤骨頭”,被人們無情嘲笑,連他的母親也無法理解兒子的作為,只是傷心;他的血并沒有染紅人民的愛國之心,反而為一些貪婪的劊子手提供了一次詐騙無知群眾的機會;他英勇就義的時刻沒有人為他流淚,卻給了無聊的看客鑒賞殺人盛舉的機會。
群眾對犧牲者的不理解,是革命斗士們最為痛心的。由于先驅者與落后者之間存在著思想上的鴻溝,這種無法逾越的距離讓“犧牲”變得一文不值。犧牲者希望用自己的死換來民眾的覺醒,成為他們脫離愚昧的一劑良藥,華小栓吃了帶夏瑜血的饅頭依然死了,恰恰證明這種犧牲是無謂的、虛無的,只是給愚昧民眾打了一劑“假藥”。魯迅對于像夏瑜這樣的革命斗士之死表現出深深的同情與痛惜,他在《墳》中寫道:“我們無權去勸誘人做犧牲,也無權阻止人做犧牲。況且世上也盡有樂于受苦的人物”[2]。
(二)貧苦群眾之死
在魯迅的小說中,還有一類不可忽視的人——生活貧苦,命運悲慘的勞苦大眾。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祝福》中的祥林嫂。祥林嫂從一開始到死前的樣貌和心理變化基本上全面展現了她悲慘的一生。初來魯鎮時她剛喪夫成為寡婦,從婆婆家逃出來,干活利索,兩頰泛紅,生活艱辛卻算得上溫飽,日子也有奔頭。緊接著婆婆把她抓回去賣給賀老六,她先是為了貞潔,“出格”地以死相爭,最后還是迫于男性的蠻力屈從了他。而這段殘忍的婚姻并沒有澆滅她生的希望,與丈夫的這個孩子可以說是她生存下去的全部指望,精神上的唯一寄托,是她在這個冰冷世界中感到溫暖和真情最后的地方。所以阿毛的慘死徹底摧毀了祥林嫂的精神世界,她變得健忘糊涂,在捐門檻上花掉了全部積蓄,最終獨自死在熱鬧的街頭。
魯迅筆下的悲劇小說之所以觸人心弦,就是因為他能完美地把握人物身上最后一點珍貴的東西,當人物徹底失去它時,才是真正的悲劇。對于祥林嫂而言,命運對她太不公平。年紀輕輕就背上了“寡婦”這個不祥的頭銜,這對于當時的女性來說一輩子都將生活在別人的冷嘲熱諷中,接受陌生人的冷眼;失去孩子又讓初為人母的她雪上加霜,徹底成為一個沒有表情的“木偶人”。這一切都不是她的過錯,她只是生錯了時候,成為封建禮教和思想的犧牲品。她的死被作者有意淡化了,沒有人知道她是如何死的,因為本身也沒有人關心,這樣更加凸顯了祥林嫂之死的悲劇性,乃至其整個人生的悲劇性,這種悲劇性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更具有普遍性。她的死沒有換來任何人的同情,卻換來了魯四老爺認為不吉祥的理由。
同樣的,阿Q成為了辛亥革命用來殺一儆百的犧牲品,他的冤死卻落得個“槍斃不如殺頭這般好看”;孔乙己為生計所迫,做過一些小偷小摸的勾當,但從他還賬,喜歡小孩來看,這個人物也沒那么糟糕,他的生命在那個等級制度森嚴的社會下顯得那么渺小;陳世成和孔乙己一樣,也是被科舉毀了的人,他短暫的一生全無光彩,只有枯燥的考試,人生也沒了奔頭。魯迅通過對這些貧苦百姓的描述,再現了當時社會的真實情況,表現出封建禮教思想依然是壓在群眾頭上的大山,革命并沒有真正深入底層。
(三)孩子之死
魯迅小說的很大一部分由孩子構成。他喜歡孩子,把拯救社會的重任交付在孩子身上,希望他們不要被這個骯臟的世界玷污,永遠純潔可愛。從《狂人日記》的“救救孩子吧”,到《故鄉》的“他們應該有新的生活,為我們所從未經過的”[1]。從這些語言描寫中,可以看出魯迅十分重視孩子的成長,這也使得他小說中關于孩子的死更加值得研究。
或許是由于自己的身世,孤兒寡母的模式在魯迅的小說中十分常見。《明天》中的寶兒和單四嫂子與《祝福》中的阿毛和祥林嫂就是典型個例。孩子的死亡對于母親的傷害遠遠比對小孩本身要大的多,尤其是對于單身母親,孩子就是她們在這世上僅存的溫暖,有時候她們對小孩的需要大過了孩子對自己的需要,可以說她們是為孩子而活。
單四嫂子為了給寶兒看病,一個人不辭辛苦,努力紡線維持生計,整日東奔西走尋求良方,最終寶兒還是沒能從庸醫的手下活命。單四嫂子的精神還算堅強,文中說“但單四嫂子雖然粗笨,卻知道還魂是不能有的事”[1],她賣了自己所有值錢的東西厚葬了寶兒,隨著棺材一起被埋入土中的是她的明天。祥林嫂失去阿毛的同時也失去了理智,剛開始跟別人講述不幸遭遇時還會收到一些同情,后來收到的只剩下厭煩。夏瑜的血沒能治好華小栓的病,卻造成了兩位母親失去孩子的痛苦。多么諷刺的現實,孩子的死引出的是沉重的社會矛盾,審視孩子的死就是審視社會的現狀,讓人認識到中國人民受到封建迷信的毒害之深、而應真正地“救救孩子”。
二、小說中死亡描寫的意義
生死在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中都是一個恒久的命題。凡是想要創作出寫人、寫世界的宏大作品,必然離不開對生死問題的理解。魯迅先生對死亡的描寫體現了其個人對死亡的認知,這讓他的小說意蘊更加深厚。
(一)推翻舊生命觀,塑造新生命觀
魯迅深受進化論的影響,他認為生而為人,不能渾渾噩噩地活,糊里糊涂地死,應重視生命的價值,活的精彩而有意義。在《死》一文中說中國人的“生死久已被人們隨意處置,認為無足輕重,所以自己也看得隨隨便便,不像歐洲人那樣認真了”[3]。的確,在封建時代,人們對生死的態度是矛盾的。一方面看重生死,重視人的降生和去世的儀式化;另一方面又看輕生命,祖祖輩輩傳下來的畸形生命觀一直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封建社會等級制度森嚴,上層賦予下層權力的同時似乎也有權決定他們的生死。“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這種觀點在百姓的頭腦中根深蒂固。所以傳統的生命觀認為“人生而有別”,對下層民眾的生死從不放在心上,而可怕的是他們自身也認同這種生命觀,自己看輕自己的生命,如草芥螻蟻一般生存。受到佛教的影響,人們為了降低對死亡的恐懼,則將希望寄托在看不見摸不著的“下一世”,今生行善積德便會讓來世活得順利一些。這種認知說到底是生命的轉化觀,人們不清楚人死了之后會怎么樣,于是有了來世之說,也就是生命的另一種存在方式。傳說女娃死后成了精衛;梁祝死后化蝶續緣;關羽、諸葛死后成為神靈,這些生命的轉換讓普通民眾對死亡逆來順受,以至于麻木妥協。
對阿Q臨死前的一段描寫就是舊生命觀最標準的體現。“他一急,兩眼發黑,耳朵里喤的一聲,似乎發昏了。然而他又沒有全發昏,有時雖然著急,有時卻也泰然;他的意思之間,似乎覺得人生天地之間,大約本來有時也未免要殺頭的。”“過了二十年又是一個……”[1]阿Q在百忙中,“無師自通”地說出半句從來不說的話。面對死亡,他本能地感到害怕,卻因為這種生命觀又勇敢起來,說出這句口號。“二十年后還是一條好漢”不是阿Q偶然想到的,而是千千萬萬底層民眾在困難時刻拿來安慰自己的口號。
同理,祥林嫂在喪失生的欲望變成“木偶人”后,見了“我”,第一反應就是詢問“一個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沒有魂靈的?”,問這問題時,“她那沒有精采的眼睛忽然發光了”,這表明祥林嫂在生死間猶豫時,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死后的問題,不去關注后半生的生活,而是拿它與死后的生活對比,擇優選擇。之后也問到“那么,死掉的一家人,都能見面的?”[4]這才是她想問的最終問題。由于對阿毛的深切思念,她想到了以終結自己生命的方式見到兒子,可憐又可悲。
從這兩個人物身上,我們可以看出傳統封建的生命觀對百姓的影響之深,也表現出魯迅對舊生命觀的態度,他為弱者輕易失去生命感到惋惜,因此要樹立一個嶄新的生命觀。首先,要從正視死亡開始,將死亡放在單獨的生命個體上,不以人的意志而轉移,不與所謂的陰間地獄相通,這樣一來,死亡對于每個個體而言都具有了終極意義;其次,再談重視生命的意義,每個人都要實現自己作為人類的價值。受進化論影響,他認為“生命的路是進步的,總是沿著無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不了的。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著跳著,跨過了滅亡的人們向前進。人類總不會寂寞,因為生命是進步的,是樂天的”[5]。某種意義上,魯迅首先提出了這種健康向上的新生命觀,引導人們向前走,積極樂觀地生活。
魯迅小說通過描寫舊式生命觀的潰敗,體現這種嶄新的生命觀,“死而后生,向死而生”說的就是這種不畏死亡的健康生活態度。從此,中國現代文化有了直面死亡的勇氣。
(二)自我意識的覺醒
魯迅文學造詣深厚,筆下的人物不會單薄地死去,一定要在讀者心中留下點什么。他之所以把許多人物逼到死亡的角落,就是要讓他們發出一些其他人發不出的聲音,想一些其他人想不到的事情。自我意識的產生讓人物意識到自己作為獨立個體的存在是異于他人的,短暫的理智是文章最有價值、最引人深思的部分。在這個“吃人”的社會,自己的死亡并不能改變什么,只有群體的覺醒才能撼動這個世界,這也是魯迅想要通過他的筆傳達出來的思想。
由魯迅小說的死亡主題帶來的自我意識覺醒主要分三種類型,分別是恐懼意識、懷疑意識和毀滅意識。
一是恐懼意識。阿Q在面對死亡時,首先是慌亂,后來又泰然了,甚至擁有了一股豪氣,想要唱一曲;在聽到“豺狼的嚎叫”一般的歡呼聲后,“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風似的在腦里一回旋”,想到了四年前遇到的那只餓狼,眼神凌厲,“似乎遠遠的來穿透了他的皮肉”。為什么在走向法場的時候想到了狼呢?文中說,“而這回他又看見從來沒有見過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鈍又鋒利,不但已經嚼了他的話,并且還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東西,永是不遠不近的跟他走。這些眼睛們似乎連成一氣,已經在那里撕咬他的靈魂”[4]。吃人的狼和麻木的看客讓阿Q聯想到一起,對這種恐怖的“吃人”現象表現出深深的恐懼,一直激蕩到他的內心。這種對于周圍情況的真實認知雖然只有一瞬間,但來自心底的顫動還是激發出他的自我意識,在生命即將毀滅的時刻才清醒地認知了這個社會,這是由死亡帶來的。
二是懷疑意識。《藥》的最后,夏四奶奶與華大媽都來給自己的兒子上墳,夏瑜葬在路的左邊——埋葬死刑犯的這邊,華小栓葬在路的右邊——埋葬窮人的這邊。夏四奶奶先是感到羞愧,后來看到墳冢上的花圈時,終于喚醒了內心的密語,大聲說道:“瑜兒,他們都冤枉了你……可憐他們坑了你,他們將來總有報應,天都知道”[1]。這些話來自一位深深愛著自己兒子的母親,她不懂革命,不懂兒子的追求,甚至話語中還夾雜著封建迷信的觀念,但是這顯然是對社會不公的一種強烈控訴,對執法結果的深刻懷疑,她堅信自己的兒子是無罪的,這是懷疑強權,懷疑社會的一種自我意識。
還有祥林嫂對“我”問的關于魂靈和地獄的問題,也可以看做是她對人的存在產生的一種懷疑。文中的“我”也發現了她的懷疑,“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卻疑惑了,——或者不如說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無[4]”。這種矛盾的想法反映了祥林嫂面對死亡的猶豫抉擇。從某種角度看,她似乎是在與深層次的自己對話,以求得死后就能見到阿毛的安慰,這樣來看,祥林嫂的自我覺醒是對于另一個世界的困惑。
三是毀滅意識。這里的毀滅意識指的是自我意識的毀滅,即自我的放縱與沉淪,其代表人物是魏連殳和狂人。狂人一開始擁有著罕見的歷史批判意識,他清醒地認識到這是個“吃人的社會”,而周圍的環境不允許他一直成為狂人,他的拼命呼吁和挽救在吃人的浪潮面前顯得單薄無力,因此他的逝去是必然的、可悲的。狂人向“正常人”的轉變也是他自我意識的毀滅,歷史批判意識的毀滅。魏連殳本來是個“異類”,全山村中只有他一個外出游學,后來也迫于生計成為了自己不愿成為的人,用自己的方式“報復”社會,到去世什么也沒有留下,只留下了一抹“冰冷的微笑”。他的報復行為是對社會的個人病態反抗,促成了自我意識的毀滅和人格的沉淪。
在魯迅的小說中,我們發現人在被逼入死亡絕境時,麻木愚昧的人也會產生自我意識;而本來有自我意識的先覺者,也可能因為舊勢力壓迫走上毀滅的道路。
三、結?語
死亡母題在魯迅小說中的廣泛應用主要是為了開發民智而創作的啟蒙作品。由于封建禮教、封建主義的存在,人的生命意識薄弱,喚醒人“生”的價值,是魯迅寫“死”的意義所在。關于魯迅小說中的死亡意識,還存在許多有價值的地方,包括魯迅的生平對筆下人物命運的影響,和死亡意識影響的其他方面,值得我們繼續深入研究。
參考文獻:
[1]?魯迅.吶喊[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
[2]?魯迅.墳[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
[3]?吳中杰.吳中杰評點魯迅雜文[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
[4]?魯迅.彷徨[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
[5]?魯迅.生命的路[N].新青年,1919-11-01.
[6]?魯迅.魯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責任編輯:武典]
收稿日期: 2019-08-10
作者簡介:閆亦凡,女,西北大學文學院漢語言文學專業,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