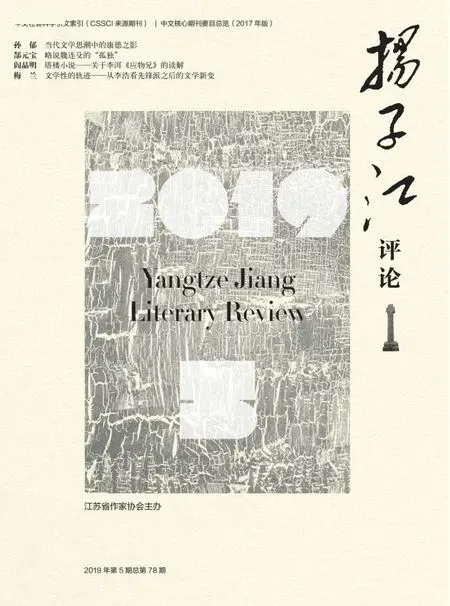文學性的軌跡
——從李浩看先鋒派之后的文學新變
梅 蘭
文學性,往往被看作是在中與西、文學與政治的框架內一個隸屬于80年代啟蒙主義思想和自由主義文學的概念,在文學性的反思中,當代文學史研究往往以純文學和左翼文學作為此消彼長的文學現象;對于文學史研究來說,這無可厚非,但對于文學批評而言,有必要明確,文學性本身并不是一個封閉的隸屬于自由主義的形式概念,從語言技法、敘事技巧、文本結構、作者表達、讀者接受、體裁、話語、文化環境等各個方面,20世紀以來的文學研究者都曾努力區分文學和人類其他語言活動,可以說文學性就是對文學活動本身的形而上與科學性追問。正如50、60、70后甚至80、90后中國作家作品的社會歷史語境并非毫無相通之處,純文學的中/西、文學/政治的歷史框架也適用于左翼文學,20世紀中國文學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的轉變,同屬于啟蒙主義的激進主義思潮,從服務于個人主義理想,到服務于社會進步、民族國家,純文學和左翼文學都在同一個歷史語境中,對左翼文學的文學性的研究角度、概念、方法很多來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純文學研究。事實上,圍繞左翼文學的文學史反思比純文學研究更依賴西方后結構主義,比如說激烈抨擊學術的體制化和二元對立思維方式,揭示某些文學的意識形態合謀現象等。這充分說明,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文學性研究促進了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的左翼文學研究,純文學甚至是先鋒文學與左翼文學的差異實際上在縮小而不是擴大。文學史的壓抑與回歸、批判與清理固然必要,擺脫對西方理論的依賴,從當代文學的傳統與發展中辨識和思考當代文學與文學秩序、社會語境之間的關系,構建當代文學的藝術譜系,更值得期待。
李浩生于1971年,但與其說他和70后作家有相似之處,還不如說他和西方文學經典的距離更近,他不僅以“純文學”“精英文學”“先鋒派”自居,也撰寫了不少評論文章闡明他的觀點和立場,這毫無疑問會引來側目和批評,畢竟先鋒派本身都撤退和轉向了。現在的一般看法是:語境決定了當年先鋒派的意義。正如左翼文學被重新從文學經典角度審視,80年代的先鋒派被放在當時的政治文化語境中批評,當年的文學先鋒被診斷為精神創傷應激反應:“中國先鋒小說中的后現代主義可以被定義為蘊涵在主流話語之中的對政治文化現代性的心理反作用”。在經過精神分析和文化研究訓練之后,文學研究者的成熟標志看來是,在一切文學作品中讀出政治和心理問題,而在一切非文學中讀出文學。毫不奇怪,對李浩的批評中也包含了他對先鋒精神和純文學不合時宜的堅持,同時,當一個作家無法歸于當下某種文學現象或現實主義標簽下時,對他的批評也幾乎無從展開。從這個角度來看,李浩是一個讓人陌生的當代作家,他兼長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兒童文學、詩歌、文學批評諸種文體,問題在于他的小說無法呼應當下的文學風尚,缺乏可以辨識出社會現實價值的重要題材、主題、人物和情節,人們能夠發現他寫實功底扎實,癡迷先鋒文學,但除此以外似乎再無他解。
在一個偏離當下文學風尚的作家身上,人們其實可以發現同時代作家的一些新變。事實上,在戲劇化敘述者、虛構與現實的融合、轉敘與世界性等方面,李浩以及先鋒派之后的當代文學呈現出某些新的藝術特點;本文即從文學性建構的角度總結先鋒派以來的文學新變,或者說當下的中國文學如何處理虛構與現實/歷史語境的關系。
一、戲劇化敘述者
戲劇化敘述者是韋恩·布斯提出的概念,指把敘述者完全戲劇化,賦予敘述者人格特征,把敘述者變成和他們所講述的人物同樣生動的人物,換句話說就是“在或多或少的細節上以‘我’為特征的敘述者”,與之相對的是非戲劇化敘述者或隱性敘述者。戲劇化敘述者在小說中可以是作為人物的第一人稱敘述者,也可以是作為“意識中心”的第三人稱敘述者。戲劇化敘述者實際上展開的是人格化講述,因此和全知的、客觀的展示形成對比。
李浩的小說常常有著一個饒舌的敘述者,長篇小說《如歸旅店》《鏡子里的父親》都采用了戲劇化的第一人稱敘事,尤其《鏡子里的父親》,第一人稱“我”和魔鏡的對話及講述構成了小說最突出的敘事特點;中短篇小說也是如此,大量出現第一人稱敘述人,《驅趕說書人》開場是“現在,該說書人上場了。且慢——我們先壓住呼吸、聲音”,《變形魔法師》的開頭則是“他從哪里來?我不知道”,其他如《他人的江湖》《夸夸其談的人》《跌落在我們村莊的神仙》《消失在鏡子后面的妻子》《郵差》《在路上》《村長的自行車》《哥哥的賽跑》《記憶的拓片(三題)》《一把好刀》《雨水連綿》《父親的沙漏》《碎玻璃》《失敗之書》,等等,也都是第一人稱敘事。一般來說,采用第一人稱敘事,作家有敘事和題材上的方便,比如說“我”的敘述極其自然,李浩的小說又大多圍繞爺爺、父親、母親、妻子、哥哥、姐姐等——這些家庭關系和人物當然也是虛構的。這些特點同樣出現在20世紀80年代的先鋒派作家身上,蘇童的“我的楓楊樹故鄉”“我們香椿樹街”系列是成功的范例。蘇童、余華、格非等的小說都有不少第一人稱敘事,但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的先鋒派作家不管是使用第三人稱敘事,還是第一人稱敘事,其敘事風格追求的大多是客觀和疏離感。而李浩的小說有一個高度戲劇化的講述人,他既是故事的人物之一,也講述故事,發表評價,提問并回答,制作表格,抒發感情,回憶往事、爭辯或想象……最突出的即是《鏡子里的父親》。
《鏡子里的父親》一開頭就幾乎全盤托出了父親的一生,重要場景如電影鏡頭般閃過,這種預敘以及其后對父親一生各階段的重點描述說明,“我”的講述重點并不是父親平庸的一生,“我”的苦惱在于如何敘述,如何將個人與歷史的邂逅中發生的出生、表演、規訓、饑餓、傷痛、抵抗、羞辱、幻想、死亡、革命、憤怒、麻木、沉寂、新生等講述出來。但是,完全不同于中國傳統白話小說的全知第三人稱講述,小說有著一個夸張、自戀、溫情、嘲諷、嚴厲、順從、妥協等融為一體的講述者;同時,《鏡子里的父親》號稱是百科全書式的小說,充滿了各種現代及后現代主義技法,比如元小說敘述、拼貼、問卷、插敘、鑲嵌體裁、魔幻、象征、空白、取消標點……應該說,第一人稱講述最大程度上為小說的敘事實驗提供了戲劇化舞臺,但是這看起來也讓小說變成了一個敘述技法競技場。
高度戲劇性的敘述者或者說自我意識的敘述者,當然可以追溯到先鋒派的馬原,但是更為明顯的是,李浩的長篇小說借鑒了《午夜之子》的敘述方式,把后者的敘述者薩利姆和帕德瑪,換成了“我”和魔鏡;如同《午夜之子》中薩利姆和帕德瑪經常討論小說本身的人物、情節等,“我”和魔鏡的對話也貫穿全文,是整部小說的敘述支架。當然,李浩對《鏡子里的父親》的敘述人做了調整,他的每一章都變換著敘述角度,用“我”的話來說,就是選取不同的鏡子或者幾面鏡子來講述某一章,而魔鏡有時幫助負責講述某個故事的鏡子,描述一些難以抵達的場景,有時幫助“我”返回敘述時間之前的某個時間,有時則因不滿“我”講述的故事太過憂郁,親自上陣講述。在魔鏡的選取上,李浩不能不說受到了博爾赫斯的影響,鏡子和水晶球,都是無限增殖的隱喻,有著難以取代的神秘意蘊,但李浩小說里無所不知的魔鏡就是另一個“我”,有著相似的耽于各種文學文本的愛好和強烈的敘述欲望,對“我”的敘述起著監督、幫助、評價作用。李浩在小說里對其它鏡子的運用,主要是從電影鏡頭角度,發揮了形形色色的鏡子的媒介功能,小說因此可以像攝像鏡頭般表現場景、人物和事件。比如,
還是交給鏡子……再調一個角度,45度斜角,向一個遠處:無棣,慶云,德州,然后濟南,不,不是那個方向……如果進行追蹤,你得不斷調整鏡子的角度才能捕捉到他——七百四十里地之外,那時,他在去往唐山和灤縣的路上。
到這里,突然卡殼,鏡子里散落著大片大片的雪花和墨點,就像、就像一段放舊受潮的膠片電影,落到銀幕上所剩的那些。
人格化講述在當代小說中并不偶見,但很少有作家像李浩這樣把它發展到如此汪洋恣肆的地步,魔鏡也好,鏡子也罷,都不過是“我”的虛構工具,這種將戲劇化講述、魔法與影視鏡頭結合起來的敘述方法,使講述人的能力無限擴大,能在多維時空維度上自由虛構。
講述的人格化是劃分傳統中國白話小說與現代中國小說的一個重要標志。傳統白話小說地位的改變以及小說作者的文人化,從根本上奠定了現代中國小說的敘事模式,而人格化的講述者即第一人稱敘事無疑是“五四”小說最突出的敘事特點。中國傳統的白話小說是第三人稱敘事,其全知視角、重視情節、連串敘述、詩文夾雜、預敘等程式化的非人格化敘述,皆來自說書人和看官之間的擬書場語境。在陳平原看來,中國古代白話小說自宋元到晚清700多年在敘事方式上的停滯,“應主要歸因于說書藝人考慮‘說—聽’這一傳播方式和聽眾欣賞趣味而建立起來的特殊表現技巧,在書面形式小說中的長期滯留”。而趙毅衡指出,這是因為白話小說有長達400多年的改寫期,“在此期間,不管是作者還是改寫者,對白話小說作品都不擁有全部著作權。由于敘述主體沒有權威性來源,敘述者就不得不取得類似口頭敘述者的權威性。在口頭敘述藝術中作者主體幾乎不在考慮之列,同樣,程式化的擬口頭敘述格局也可以使著作權成為不必考慮的問題,任意改寫就理由十足”。由于文類地位的低下,傳統白話小說的作者實際上恥于署上真名,而程序化的說書人角色也限定了敘述者的形象、功能和講述方式。隨著晚清報刊的繁榮和西洋小說的影響,晚清小說中的這種擬書場敘事格局已出現松動,比如韓南描述的晚清小說如何以人格化敘事者等打破了傳統白話小說的第三人稱全知敘事。五四運動徹底改變了小說的地位,“五四”作家由此取得了在小說中表現自我的權力,中國現代文學出現了普實克所說的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特點,“五四”小說從此革新了傳統白話小說的敘述格局,確定了中國現代小說的敘事特點。比如狂人、阿Q這樣的戲劇化的敘述者,即是《狂人日記》《阿Q正傳》在敘事上讓人印象深刻的新變。
如果說傳統白話小說敘述者身份的程式化主要源于文類地位的低下,白話小說因此對歷史敘事和詩文多有摹仿及借鑒,敘事技巧的發展受到制約,那么現代中國小說自“五四”時期后,從20世紀30年代到70年代末,則更多受到民族國家危機和政治需求影響,革命文學、文學大眾化、民族形式、為群眾服務等爭論、討論、講座,指向文學家的文學觀念轉變和個人思想改造,在敘事模式上傾向于向俗文學學習,圍繞戲劇化的敘述者的敘事模式探索從此止步。
比題材、人物、情節等更為穩定的敘事要素是敘事形式,中國傳統白話小說不使用人格化敘述者,以說書人身份出現的敘述者地位卑微,小說摹仿史傳敘事模式,有著難以擺脫的說教功能,這些敘事特點也有潛移默化的效果。當代作家里面,受到中國傳統文化和白話小說影響最明顯的莫過于賈平凹,在他的十幾部長篇小說中,第三人稱敘事充裕有余,第一人稱敘事則顯得捉襟見肘,常流露出說教傾向,比如《土門》《秦腔》《高興》《極花》等。因為中國傳統白話小說里作為說書人的講述者,往往是非人格的社會秩序的代言人,這對賈平凹的影響也許體現為其小說里稍顯稚弱的第一人稱敘述者。比如《極花》里被拐賣到圪梁村的胡蝶受到老老爺的開解與教導,從而認同了自己被拐賣的命運;《土門》里的梅梅則發現了仁厚村神醫云林爺的變化。
我靜靜地立在屋里,看著他,我忽然覺得云林爺的渾身在發光,繼而則通體透明,……那透明的體內紅色的液體在循環流動,使身子的四周的光芒由紅到白,由白到黃。我簡直驚呆了,我無法描述這若虛若幻的光芒,但我卻有說不出的愉悅和溫暖,竟感動得淚水嘩嘩啦啦地流下來。
這種說教傾向與不加節制的自我情緒的宣泄并行,在20世紀80年代是頗為常見的,很多第一人稱敘述者仍是流行話語的代言人,并不能體現敘述者的人格和異質性,他們忠實于隱含集體作者的意志,不放過任何抒情和教化的機會。先鋒派作家所面對的正是類似的戲劇化敘述者,先鋒派的敘述實驗因此是對這種敘述模式的反撥,他們客觀冷靜甚至冷漠地講述各種暴力、色情、亂倫等逾越道德的故事,不僅改變了當代中國小說教誨化的敘事模式,而且創造了和主流敘事不同的個人敘述者形象,先鋒小說的異質性敘述者所展現的敘事空間,對當代文學的發展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長篇小說的繁榮意義重大。
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當代文學出現了大量異質性的戲劇化敘述者,比如余華《活著》《許三觀賣血記》、阿來《塵埃落定》、畢飛宇《玉米》《玉秀》《玉秧》、劉震云《一句頂一萬句》、金宇澄《繁花》、蘇童《黃雀記》、徐則臣《耶路撒冷》、吳亮《朝霞》、李修文《山河袈裟》等,這些小說或散文有著第一人稱或第三人稱的意識中心,隱含作者充分展現出一個個高度個體性的敘述者,他們以新的方式處理個人和種族、歷史、日常、思想等的關系,這些獨立而異質的戲劇性敘述者保證了小說對歷史、現實有著獨特的理解。這些作品中,《繁花》的講述風格看似接近中國傳統白話小說的說書人,但實際上是對市民口語的雅化和文人化。20世紀90年代王小波當代文人化的戲劇性敘述者“王二”,是當代文學史上迄今為止最為獨特的敘述者,因王二的“我”對本民族的文化、觀念、事端保持了足夠的審美距離。王小波的小說《黃金時代》《革命時期的愛情》中“我”的瀟灑自如也最接近李浩小說的人格化敘述,只是王小波的“我”偏重于審視現實思想意識的問題和荒誕性,智性的評論比比皆是,故事和人物倒在其次,而李浩的戲劇化敘述者更關心敘述本身的奇特效果,比如有關敘述方式的選擇、爭吵、協商、評價,敘述與故事的短路。敘述或者說虛構的疆域本身才是李浩關注的對象。
二、虛構與現實的融合
虛構在李浩的小說里居于核心地位,這不僅是說他如同一般小說家一樣,充分發揮虛構的能力構建小說的情節人物等,而且說他在小說中思考虛構的邊界與可能,虛構擺脫了工具地位,成為小說真正的主人公。 這當然不是一個新話題,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的先鋒派就曾以大膽的虛構聞名,馬原曾直接以“虛構”為小說名稱,80年代的先鋒派對抗和解構的是當時的主流宏大敘事,先鋒派的反現實性、非邏輯性、暴力/色情、戲仿、開放式結構相對應的是主流敘事的現實性、邏輯性、教化性、嚴肅性、整體性等特點。1989年余華在《虛偽的作品》一文中,將虛偽或者說虛構與日常生活經驗、精神與常識相對立,對常識的懷疑是余華思考真實的起點,但是李浩及一些當代作家所癡迷的虛構,則是和現實、物質、世界性、跨文化等結合在一起,李浩在小說中所發現的不再是想象或虛構的反現實性,而是虛構與現實的交融。在李浩小說里,虛構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學習能力,也是面對現實的隱藏、掩飾、揭示、抗爭,它常常和恥感為鄰,也帶來出路和生機,它就是小說,也是現實以及人本身。從這個角度來看,現實以及其中的人充滿了虛構的邏輯性、趣味性。現實和虛構的融合,才是李浩小說的真正主題。
李浩寫的最好的是一批中短篇小說,如《失敗之書》《那桿長槍》《碎玻璃》《消失在鏡子后面的妻子》《郵差》《告密者札記》《將軍的部隊》《閃亮的瓦片》《蹲在雞舍里的父親》《父親的籠子》《哥哥的賽跑》《變形魔術師》《驅趕說書人》等,這些小說毫無疑問有著鮮明的思想,有些主題非常明確,但又很耐讀,因為在每一個尖銳的主題下,都有著重重疊疊的日常生活場景和現實的邏輯性。相比較當年的先鋒派以及同時代的當代作家,李浩小說如果說有著所謂的先鋒性,其語境也是當代小說本身,而不是社會歷史語境,這決定了他小說獨特的藝術氣質。他的小說身后是小說的當代傳統,體現在對現實的虛構性的感悟,以及對虛構的現實性、世界性的掌控能力。在越來越關注古典傳統的當下中國文壇,李浩的小說其實在強調文學的另一種不可忽視的傳統,即小說的當代傳統及其展現的虛構與現實的交融。
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這兩種風格構成了李浩的寫作姿態。李浩具有70后作家的隱忍和苦澀,即便是他最張揚的文字里,也有著沉重的底色,他的另一極端是囂張的后現代主義拼貼,人物名稱、情節甚至大段文字都來自其他文學作品。李浩是小說的當代傳統孕育出來的作家,他的小說因此有著不同的關注焦點。李浩擅長書寫的主人公都飽受折磨,《被噩夢追趕的人》的肖德宇不得不在夢中一次次回到塌方的礦井面對自己死去的弟弟;《哥哥的賽跑》的中學賽跑冠軍哥哥在患得患失的巨大壓力下,逃離了比賽現場,他所有的訓練成果最終都淋漓盡致地體現在了逃離的速度和激情上;《如歸旅店》里父親一個人于亂世中苦苦支撐著日益破敗的如歸旅店……李浩在眾多中短篇小說里描摹了一個與恥辱相伴一生的“父親”,他漫長而恥辱的自殺旅程、被禁錮的家庭生活、稍縱即逝的詩人生涯、與時間的對視和無奈,等等。在一次次的書寫中,“父親”成為一個當代失敗者形象,他在一切已知的理想和安慰中,都掙斷了靈魂的線繩。《失敗之書》幾乎是一部當代“變形記”,失敗深入骨髓如影隨形,小說描繪的不僅是一種失敗的心理狀態或病態人格,也是哥哥作為一個失敗者是如何一點點摧毀掉家庭的父子、母子、兄妹之情的。血親間牢固的倫理關系其實非常脆弱,它們的不斷糾結沉淪,讓人看到了家庭與個人天然的對立。失敗的與其說是哥哥,還不如說是他所破壞掉的倫理和家庭。在所有李浩關注的題材中,家庭和失敗都聯系在一起,這毫無疑問是當代人的困惑疑問,而不是傳統中國文化的當代延續。李浩筆下的這些人物在心理上的能量遠遠超過他們的行動能力,他們常常被心理陰影壓抑變形,到處碰壁,偶爾的行動也是點到為止,更多的時候只是一種抗議的姿態。這些人物甚至不能說屬于本民族社會歷史及文化傳統,他們更像是20世紀以來當代人幽暗的心理鏡像。
李浩的主人公有著奇特的邏輯,他們或者從虛構中進入現實,或者從現實中步入虛構,現實和虛構的界限在李浩的小說中是不存在的。《鏡子里的父親》講述的是一個普通的鄉村教師“我的父親”的一生,雖然不管是眾多的敘述技法,還是耳熟能詳的1948年生人必然經歷到的土改、反右、大躍進、饑餓與死亡、文革、改革開放,都并未超出人們已知的范圍,但小說描摹出了一個“我”縈繞于心的父親的精神史,沒有人像“我”一樣曾那么近距離地體驗、觀察、審視、評價父親的精神世界,雖然這個世界和當代重大的歷史變故幾乎都是擦肩而過。李浩用高度戲劇化、人格化的磕磕絆絆的講述,構造了一般的歷史敘事會舍棄掉的以父親的感受為核心的個人精神史——所謂不可見的歷史,這部40萬字的長篇小說因此成為可見的、分析式的一個農村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成長、消亡史。李浩的小說看起來符合歷史敘事的模式,也容易被納入中國當代鄉土歷史敘事中加以審視;但是這也許是個誤會,《鏡子里的父親》的父親和李浩的中篇小說《告密者》中的虛構人物西吉斯蒙德·馬庫斯幾乎是同一個主人公。他們都是復數的各種身份疊加的個體,在虛構/真實之間彷徨于無地。如同西吉斯蒙德·馬庫斯,父親同樣有著參與歷史的激情與熱情,同樣曾“被烈焰燒灼”,他的一生同樣也是伴隨著撒謊/隱瞞或者說虛構的一生。李浩的《鏡子里的父親》是以虛構的眼光解剖了“父親”作為人的一生,“父親”身上交融著伴隨新中國成長的那代人的精神圖譜,它的激昂、痛苦、迷惘或沉寂在虛構中色彩斑斕,但“父親”卻在這個過程中越來越形象模糊,逐漸變成了一個鏡子里的多重的人,變成了讓他自己都陌生的他人,一個虛構的人。虛構因此在李浩的小說里是一種形而上的思考,自我在辨認中發現,他者才是自我的本質,這一錯認才是人的根本特點。李浩的小說擁有一個帶有濃厚精神分析色彩的后結構主義式的自我形象:現實中的人其實是虛構和想象的產物。
李浩的小說不僅從一個人的一生看到了人的虛構性,而且在歷史和思維中都發現了虛構的基因。比如《鏡子里的父親》里,大躍進對于普通農民如爺爺奶奶一家來說,是一種需要學習的虛構能力,需要在大隊長劉珂、高強和眾小隊長的啟發、鼓勵、誘導中,習慣成自然;面對反右的一整套詞匯,“我的爺爺”得在全家人的幫助下才約略掌握,隨之而來的是,
他先是把自己在炕上的位置由中間調整到了左邊,并按照我們家里各人的性格、習慣,劃分出左中右,姑姑和二伯,還有我的奶奶被劃到了右側。他把所有自己的物品,喜歡的物品,都歸放到左邊,我們家的偏房也空出了一半兒,柴草都堆放于左側……
思想一旦及物,就顯示出其濃厚的虛構性。學習一分為二的辯證法思維,更是讓爺爺走火入魔,一早出來尋找爺爺的父親和二伯,依次看到了梨樹上被切掉右邊一半兒的梨、半只青蛙、半個甜瓜、半個蘑菇、半個石菌、半個紅蘑……三只被劈成一半的黑蟬。小說此處虛構的模式也許來自卡爾維諾的《分成兩半的子爵》,但是思想經驗卻是中國的,虛構成為認識現實的方法,雖然荒誕,卻準確有效。《鏡子里的父親》因此也是學習和發現之書,在中國經驗上演練所有作者喜愛的虛構方式,照亮或者說發現那些普遍性的東西,用新的轉喻方式重新學習一遍歷史,賦予它們新的色彩、聲音、味道和內涵;在人類學意義上研究父親的一生,而不僅僅是1948年出生的一個中國農村知識分子的人生,真實的父親可能一生屈辱而沉寂,虛構的父親則折射出人類共通的情感與邊界。
即使是在最具虛構性的小說里,李浩也顯示了對虛構的現實性、物質性的深刻認識和掌控能力,比如《消失在鏡子后面的妻子》《郵差》《父親的籠子》這些挑戰常識的小說。消失在鏡子后面的妻子、為死神送信的郵差、困在畫出來的籠子里的父親,這些都不是問題,問題在于所有的隨之而來的真實變故,它們強大的現實邏輯讓讀者不得不接受小說的核心,那就是虛構的合理性。李浩是一位非常耐心和純粹的小說家,他的小說有著手工藝品的嚴謹設計和豐富細節,最抽象的東西也被物質化,比如死神的信是暗黃色的薄薄信封,“悲傷是黑色的,所謂悲傷,就是夜晚,河岸,個人,缺少哪怕一點點的微光”,“二伯的時間一秒一秒,均勻,并且直線。我父親的時間大大不同,它跑動,彎曲,略略發粘”,“他把自己的委屈、憤怒、病痛和怨毒都編織在里面,橫的壓住豎的,豎的插入橫的,它們相互交織、勾連,一點點顯出模樣”……其最難以回避的訴求是,虛構是完全合理合法的。
在李浩的小說里,虛構是對過去的學習、現實的發現和未來的預言,它讓時間可視、空間折疊,它包容萬象顧盼生姿,虛構就是文學實踐本身。無獨有偶,當代不少作家的小說,也出現了這種虛構與現實的悖反書寫,其轉喻性特點,帶來了當代中國小說的想象力和世界性。
三、轉敘與世界性
轉敘即是敘述轉喻。轉喻是一種修辭手法,常與隱喻相對,“表示某一概念的術語A被用做表示另一概念的術語B的一種修辭,使概念A與原因和結果、包含者和被包含者、部分與整體相互關聯”。在熱奈特看來,轉喻可以被用作修辭格,但是當作者變成自己所描述的對象,就是說當轉喻進入敘述層面,就會發現它的異常突出的虛構性特點,作品往往出現多個敘述層面之間的轉換,轉喻就從一種修辭手法變成了敘述上的轉敘,即越界敘述。李浩小說的轉敘手法非常突出,敘述者常常自由轉換于不同的敘述空間,從現實到虛構,或者從虛構到現實,小說的敘述層次因此豐富飽滿。《鏡子里的父親》貫穿了作者轉敘的跨界行為,頻頻進出故事層,它最大的特點是突出敘述者的作用,強化小說的虛構性和闡釋功能,闡釋帶來了敘述者的另一種聲音,和小說的故事空間構成了張力。
在小說的越界敘述上,20世紀80年代的先鋒派小說顯然更為抽象、含混、虛無,比如蘇童《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南方的墮落》《罌粟之家》等以作者轉敘破壞了傳統現實主義小說的真實性想象,格非《褐色鳥群》的自述垂直轉敘體現了不可靠的敘事人造成的故事空間的翻轉或不穩定性。《錦瑟》的述說橫向轉敘,則以相同故事層的多個情境間的跨界敘述連綴起一個頭尾相接的循環敘事,這些轉敘指向的都是意義的消解或破壞,蘇童大量中短篇小說如《園藝》《群眾來信》《燒傷》《肉聯廠的春天》《傘》等的述說橫向轉敘,主要是嘲弄、調侃常識、小市民、理想等,相比之下,新世紀以來的當代作家更為注意轉敘的想象力和世界性。
李浩《記憶的拓片(三題)》的“九月的一個晚上”這樣開始,
九月的一個晚上,就像書上寫的那樣,樹梢上掛著一枚冰冷的月亮。就像書上寫的那樣,一只鳥從一顆樹上飛走,在閃著白光的地上投下了影子。晚上的田野也像書上已經寫過的,包括村子、通向村子的路,包括那些匆匆的行人。這樣說吧,從表面上看,九月的那個晚上都已經被書寫過了,它沒有什么新鮮的、特別的,它是九月的,一個晚上。
應該說,這是最符合李浩小說氣質的一段轉敘,在小說的空間之外,是其他小說的世界,或者說虛構的世界,那里才是小說空間的鏡像和來源;同時,李浩強烈認同虛構的現實性,小說的故事嵌套在一個虛構之書中,毫無違和之感。其實無論是李浩筆下失蹤在鏡子里的妻子、能變幻為各種動物的魔法師、夢中復活的弟弟、為死神送信的郵差,還是韓少功探討符號過度侵蝕現實之象的《暗示》,描述不同時代的現實之間,現實與虛構之間的斷裂、拼貼的《余燼》《山上的聲音》《第四十三頁》等,都飽含對現實的真實性的深深懷疑。不同于后現代主義的價值顛覆和意義虛空,或者鮑德里亞所謂媒體時代的擬像世界,符號及其生產對現實的改造等西方理論,中國當代文學的轉敘對虛構的物質性書寫的前提,是對現實的虛構性的深刻體會。


對于地方性和世界性問題,阿來有自己的看法,他說:


人類學家阿爾君·阿帕杜萊在《消散的現代性:全球化的文化維度》中指出,傳統的以國族為核心的地方性、本土化的想象共同體及其生產,將越來越困難;大眾遷移、電子大眾媒介和流離共同領域的出現,使得主體身份的生產日益全球化和去國土化。在這個過程中,想象已突破藝術與日常、幻想與行動、個體與群體的區分,成為日常生活的情感共同體的社會實踐力量。



【注釋】
①參見賀桂梅:《“純文學”的知識譜系與意識形態——“文學性”問題在80年代的發生》,《山東社會科學》2007年第2期。
②參見周小儀:《文學性》,《外國文學》2003年第5期。
③楊小濱:《中國后現代:先鋒小說中的精神創傷與反諷》,上海三聯書店2013年版,第261頁。
④?[美]普林斯:《敘述學詞典》,喬國強、李孝弟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54頁,第123頁。
⑤講述(telling)和展示(showing)是小說敘事的基本方法,《敘述學詞典》解釋說,二者“同為距離DISTANCE的兩種調控敘述信息的基本類型……講述是一種模式,與展示相比較,其特點是對情境與事件進行更多的敘述者調節和更少的細節表現。”[美]普林斯:《敘述學詞典》,喬國強、李孝弟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227頁。
⑥李浩:《驅趕說書人》,《變形魔術師》,安徽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第49頁。
⑦李浩:《變形魔術師》,《變形魔術師》,安徽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第1頁。
⑧⑨????李浩:《鏡子里的父親》,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22頁,242頁,60頁,243頁,46頁,150頁。
⑩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60頁。
?趙毅衡:《苦惱的敘述者》,四川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28頁。
?參見[美]韓南:《“小說界革命”前的敘事者聲口》,《中國近代小說的興起》,徐俠譯,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28頁。
?賈平凹:《土門》,漓江出版社2013年版,第179頁。
?參見約翰·皮耶:《轉敘》,熱拉爾·熱奈特著,《轉喻:從修辭格到虛構》,吳康茹譯,漓江出版社2013年版,第175頁。
?李浩:《記憶的拓片(三題)》,《變形魔術師》,第187-18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