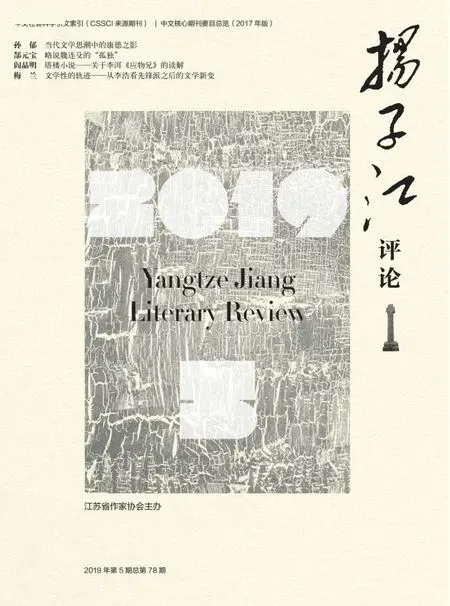城市、建筑與懷舊敘事的悖反
——讀王安憶《考工記》
劉陽揚
在20世紀90年代的那股“懷舊”熱潮中,上海成為了承載人們懷舊想象的極佳處所。隨著張愛玲小說的廣泛傳播,小說里那些帶著舊時代氣息的人物、服裝、飾物以及生活方式激起了大眾強烈的興趣。飯店、咖啡館、歌舞廳等消費場所,開始興起一種“1930”年代的裝潢風格,旗袍、黑白照片、留聲機、月份牌等小物件構成的“風花雪月”和“小資情調”一時成為想象上海的時髦方式。1995年,王安憶的《長恨歌》發表在《鐘山》雜志上,2000年前后,《長恨歌》獲得了茅盾文學獎在內的多項獎項,小說迅速走紅,并開始受到海內外評論者的重視,被視為“海派”的又一力作。雖然,王安憶本人否認《長恨歌》與懷舊的對應關系,她認為小說最多給懷舊提供資料,虛構的成分更大,但作品依然憑借著老上海的時光風物,收獲了一大批大眾讀者。
在中國現代文學的書寫中,上海一直是現代性的象征,百年來,文學中的上海開始擁有了一些特質,包括幻想、欲望、流動、頹廢等等,這些特質組合成為一個光怪陸離、變幻莫測的都市形象。事實上,歷史上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有著多重面貌,除了“懷舊”氛圍中十里洋場的上海,還有弄堂里的上海、工廠里的上海,以及變動、混亂、革命的上海。
王安憶的《考工記》再次全面書寫上海,從讀者所熟悉的弄堂、街道和建筑出發,借助陳書玉的命運遭際,以清晰的歷史線索勾勒城市的世事變遷。按照陳思和的解釋,《長恨歌》里呈現的“懷舊”風貌實際上更多的是一種反諷,諷刺的正是當時上海的整體氛圍。而在《考工記》里,王安憶不再為“懷舊”提供資料,轉而表現上海可能被忽略的另外一些側面。
一、觀察上海的視角:從高空到地面
《長恨歌》一開始,敘述者就說明了全書展現上海的方式,即“站在一個制高點看上海”。這種全景式的觀察方式,讓上海的全貌盡收眼底,同時,也表明了敘述者冷靜、審慎的敘述態度。不過,在《考工記》的開頭,王安憶卻并沒有采用《長恨歌》中的鳥瞰視角,而是讓我們跟隨陳書玉抬起頭來:“抬頭望,分明是上海的天空,鱗次櫛比的天際線,一層層圍攏”。跟隨陳書玉的目光,在上海的暮色中,以老宅為中心,上海的街景、人物和故事也如卷軸一般逐漸展開。
文學中對城市的觀察和體驗,常常采用兩種方式。其一是鳥瞰式的,站在一個高點向下俯瞰,看到的是城市的整體概貌。例如在《長恨歌》中,通過“鴿子”的視角,上海在各色各樣、頗為壯觀的弄堂中浮現出來。另一種觀察城市的方式,則從地面展開,跟隨故事里人物的眼睛,快速地略過城市的層層街景,從而獲取一些瑣碎的、零亂的城市信息。正如《考工記》里,陳書玉返回老宅的途中,電車路軌、路燈、瓦礫、老鼠、廢墟紛紛出現,城市的一致性被打破,碎片化的體驗則洶涌而來。如果加以比較就會發現,鳥瞰式的視角相對靜止,關注的是都市的整體特質,而地面式的視角則是變動甚至混亂的,城市的不連續性和破碎性才是關注的重點。
米歇爾·德·塞托在《日常生活實踐》中反思了這種全景式地觀察城市的方式:“全景式城市是一個‘理論上’的模擬品(也就是說視覺上的),總而言之是一幅畫。這幅畫存在的先決條件就在于對實際的遺忘和不了解”。塞托認為,為了獲得城市的“全景”,觀察者不得不通過局外人式的旁觀方式,將自己排除于日常事務之外。然而,這種“全景式”的圖像,來自于觀察者的投射,可能是不可靠的。并且,由于和日常生活拉開了距離,全景式的城市往往具有一種陌生感,隔絕了紛繁復雜的日常信息。塞托進一步談到,觀察城市的最佳視角可能并不在空中,而在“下面”,觀察者需要跟隨城市中的行走者的步伐,以動態的視角獲得另一種城市體驗。這是因為,“城市平凡生活的實踐者生活在‘下面’(down),生活在被條條門檻擋住了視野的‘下面’。這種生活的基本形式在于,他們是步行者。他們的身體依循著城市‘文章’的粗細筆畫而行走”。行走者動態的目光構成了觀察城市的地面視角,從地面的角度觀察城市,城市不再是一副縮小的圖畫,而成為一個由無數碎片構成的錯綜復雜的迷宮,等待著探索和挑戰。凱文·林奇也提到,“我們并不是城市景象的單純觀察者,而本身是它的一部分,與其他的東西處在一個舞臺上”,而人們感受城市的方式,也是“斷斷續續的,零打碎敲的,還常與其他有興趣的東西相混淆”。《考工記》里的上海,正是行走者們眼中變動的上海,在地面視角中,上海的“現代”特質,即變化、流動、混亂和不確定,被更好地展現出來。
《考工記》里流動變化的觀察上海的方式,似乎暗合了本雅明筆下的巴黎體驗,游蕩者終日在街道漫游,在某種程度上承擔了城市偵探的角色:“他具有與大城市節奏相合拍的各種反應。他能抓住稍縱即逝的東西”。在《單行道》里,本雅明再次表述了以地面視角觀察城市的優點:“坐飛機的人只看到道路如何在地面景象中延伸,如何隨著周圍地形的伸展而伸展,而只有走在這條路上的人才能感覺到道路所擁有的掌控力,才能感覺到它是如何從對飛行員來說只是一馬平川的景觀中憑借每一次轉彎呼喚出了遠近、視點、光線和全景圖,就像指揮官在前線呼喚自己的士兵一樣”。同樣,在《考工記》里,作者引導讀者通過地面視角捕捉城市的細節,形成了對城市的感性認知。
二、建筑:理解歷史的一種方式
老宅在《考工記》的敘述中占據重要的地位,小說的開頭就是陳書玉“歷經周折,回到南市的老宅”。老宅與上海一道見證了時代的風云變遷,陳書玉則親歷了上海民國后期的繁華與頹唐,戰爭帶來的經濟凋敝,以及時代更迭之后的種種磨難。正如小說中寫的:“這上海實在是個奇異的地方,一方面,處在歷史的風口浪尖,……另一方面呢,又在柴米油鹽尋常道里。”盡管夜間尖嘯的警笛總會驚醒夢中的都市人,但是百姓在循規蹈矩的日常生活中竟能生出天然的穩健與平和:“百姓的日子,似乎有恒常的性質,像水一樣,無論從誰家岸邊過,都一徑向前去,這里斷了,那里又續上。”上海或許就是這樣一種矛盾的所在,而致使其在時代變化中屹立不倒的,或許正是流水般的恒定與尋常。
是否要修繕老宅,如何修繕以及何時修繕成為小說敘述的一條線索。王安憶頗費筆墨地描寫了老宅的細節:榫卯木質結構、門頭的磚雕、屋脊的釉陶、天井的青磚,這些華美繁復的細節一登場就鎮住了從事木器生意的大虞。老宅外觀、布局和裝飾都呈現出高超的設計水準與精湛的技藝,小說名為《考工記》的一重含義也隨之浮出水面。老宅隨著時間日漸破敗,然而每當老宅面臨著修繕的需要時,總會被一再推遲。在第三章中,陳書玉主動向政府交出老宅,成為瓶蓋廠后的老宅日漸頹唐,仿佛一座“廢園”。到了第四章,房子已經漏水多日,兩個“集后處”派來的工匠總算修復了屋頂的碎瓦。從此往后,盡管陳書玉從未打消修整老宅的念頭,但修房計劃還是失敗了,房子塌了大半,搖搖欲墜。王安憶安排的這個“修房”的懸念貫穿全書,同時也設置了種種障礙,達到“延宕”的藝術效果。
未完成的修房,在表現故事本身悲劇性的同時,也暗含了對“懷舊”本身的懷疑。渴望以“修復”的方式來留住或者重現歷史,本身就是不可靠的行為。如果回到世紀之交上海的“懷舊”語境,就能發現,以二三十年代的傳奇故事為無形資產的修復和重建的行為并不少見。由石庫門建筑舊區為基礎改建而成的商業中心“上海新天地”就是“修舊如舊”的成功案例。“新天地”的外部保留了舊時的磚墻外表,內部卻按照新的消費習慣設計成了飯店、咖啡廳、酒吧等各種娛樂場所,在獲得商業上的巨大成功的同時,也成為上海的一張旅游名片。但在《考工記》里,同樣擁有歷史故事和商業價值的老宅卻未能修復成功,最終只豎起了一座刻著“煮書亭”的石碑,仿佛一座墓碑,紀念著一個時代的逝去。
帕克在《城市社會學》里提出:“城市絕非簡單的物質現象,絕非簡單的人工構筑物,城市已同其居民們的各種重要活動密切地聯系在一起,它是自然的產物,而尤其是人類屬性的產物”。由此看來,《考工記》里的上海和老宅,也已經超越了磚瓦建筑的外形,成為寄托人類情感的建筑。不僅如此,主人公陳書玉對老宅感情也隨著時代的前進發生著變化。
40年代,陳書玉剛剛回到老宅,感到的是溫暖與熨帖,宅內水般的月光和細語般的蟲鳴隔絕了戰火,顯得平和而寧靜。陳書玉也突然發現了老宅的美:“宛如海水中的礁石,或者礁石上的燈塔,孤立其中,煢煢孑立。始料未及地,一陣心驚襲來,他感到了危險。就在這同時,他看出老宅的美。”老宅的美麗伴隨著危險,在萬象更新的時期,更顯得不合時宜:“廳堂的高、大、深,本是威嚴和莊重,但時代是奔騰活躍,一派明朗,于是就襯托出晦暗。”當老宅再一次將外界世界隔絕在外的時候,陳書玉的想法開始發生改變,他“仿佛站在晝和夜的分界線上,兩重天地既近又遠,咫尺天涯。那一邊有故舊,這一邊是新知,他在中間,哪邊也擺不脫,舍不下,滿心悵惘”。陳書玉終于決定投身新社會,在大煉鋼鐵時期他捐出了鐵鍋、銅爐等器物,甚至拆掉了西側的鐵門。鐵門的拆除使老宅幾乎成為公共場所:“七八日時間宅子是敞著的,也沒有太大的擔憂,因這些日子,全社會都敞開著,你的就是我的,我的也是他的,也讓人放心。”桑內特在《肉體與石頭》中分析了人的活動與城市的發展建立之間的互動關系,他認為,人類文化曾經對城市構造產生過相當的影響,但是現代城市理念則在逐漸剝奪人對身體的自然感受,同時也禁錮了人類的活動和思想。在分析伯里克利時代的雅典時,他提到,雅典公民愿意在他人面前裸露自己的身體,正如敞開給全體公民的神廟一樣,代表了文明與強大:“裸體似乎已經成了雅典人的標志:城市是一個人們可以快樂地暴露的地方,而不像野蠻人那樣只是漫無目的地漫游在世界上,沒有石頭的保護”。似乎總是獨立在時間與空間之外的老宅,此時的全面敞開,意味著它與它的主人陳書玉離開了孤單的獨居生活,開始與社會產生接觸。可惜老宅的敞開并未讓它煥發生機,宅子的陰冷、家人的算計、鄰里的侵蝕與無處不在的危機感讓陳書玉產生了遠離老宅的心理,他決心將老宅交給政府。瓶蓋廠的建造雖給老宅注入了人氣,但老宅的頹勢也無可抵擋。到了新世紀,由于兄弟間的財產紛爭和修繕計劃的無限制拖沓,老宅終于無可避免地走向倒塌的命運。
小說中,如何處置老宅,一直有一條大家默認的原則,即“順其自然”。無論是“弟弟”、大虞還是陳書玉本人,都“順其自然”地處理老宅,在該交公時交公,該修繕時努力修繕,然而,這樣的“順其自然”卻讓老宅全面地頹敗下去。陳書玉多次思考“自然”的含義,他掙扎過,也一再地認為“自然”其實很不自然,但他最終選擇了逃避和妥協,告訴自己,“自然”“似乎真的就是被遺忘”。桑內特在分析現代都市紐約的時候,發現了現代城市理念所帶來的人的心靈的麻木狀態:“現代都市,個人主義在發展,而個人在城市里則逐漸沉默了。街道、咖啡館、百貨公司、鐵路、巴士以及地鐵,都成了受人關注的場所而非談話的地方。在現代城市里,陌生人之間的言語連結難以維系,城市里的個人這時看到身旁的場景所產生的同情心,也會因此變得短促——就像對于生活上的一張快照一樣”。人的冷漠和麻木,造成了現代建筑物的單調和呆板,攜帶著歷史文化痕跡的老宅來到現代,再也無法與人類的文化活動相互感知,只能“被遺忘”,成為冰冷的遺跡。
三、“非典型”的都市形象
與《長恨歌》相比,《考工記》的傳奇性、人物的“典型性”和“象征性”都有所減弱。《長恨歌》里的王琦瑤具有上海弄堂的女兒的共性,與其說是一個具體的文學形象,不如說是象征著上海幾十年社會文化變遷的藝術符號。王琦瑤抓住了四十年代末期上海最后的繁華,獲得了一時的富足,同時也被腐朽墮落的生活方式所俘虜。承載了上海四十年的城市變遷,王琦瑤的故事滿足了普通市民關于金錢的虛妄幻想,王琦瑤的死亡也徹底擊碎了關于都市繁華的“懷舊”之夢。
《考工記》雖然同樣有明晰的歷史線索,但是陳書玉似乎并不是一個“典型”的時代形象,他的行為方式和身世命運總會稍稍偏離讀者的閱讀期待。作為一名上海“小開”,陳書玉本應不學無術,花天酒地,至少應該像《活著》里的福貴一樣頑劣不肖。但是,陳書玉紈绔風流的外表之下,卻有“一顆赤子之心”,為人也“相當實在”。他一心從教,勤勤懇懇,甚至義務為學生補習;他從不沉迷風月,一把年紀還是童男子,以至于終身未娶。雖然與父母親戚之間的關系非常冷漠,陳書玉卻也沒有放棄做子女的義務,按月給父母支付生活費。這樣的生活方式,實在不符合讀者關于上海“小開”的認知。陳書玉的名字想必來自“書中自有顏如玉”,那棟老宅也被稱為“煮書亭”,可惜,陳書玉讀書不能算多,更是不近女色,他的一生與飽含美好祝愿的名字相去甚遠。
1949年以后,王安憶為陳書玉設計的人生路線也與時代的“典型”無法吻合。如果說福貴以一人之身擔負了時代的“典型”苦難,陳書玉則一次次與苦難擦身而過。當生計無望時,“弟弟”介紹了教師的工作;反右時期,因為早早交出了老宅,陳書玉幸運地錯過了政治斗爭;饑荒年代,得到遠在香港的朱朱夫婦接濟,陳書玉反而體重見長;即使到了文革時期,經歷了一次例行的抄家之后,陳書玉又逃過一劫。時代的苦難似乎總也沒有在陳書玉身上停留,他仿佛生活在時代夾縫中的“中間人”,沒有大喜大悲,茍且偷生卻又曖昧不明。
在大時代里,陳書玉是幸運的,但這幸運中也有著不安與恐懼:“因是個曖昧不明的人,合法與不合法的夾縫里,所以能夠安然無恙,全憑借某一個忽略。等到形勢反轉,正負交換場地,兩股力量一升一降,本該放心,慶幸沒有卷入是非,可是不然,更惶恐了,因這一輪的斗爭更像沖他來的。無產和有產,革命和保守,進步和落后,左和右,他哪一邊都不屬,又哪一邊都屬,就看怎么解釋。”王安憶曾在創作談中提到,自己的寫作策略是四個不要:“一,不要特殊環境特殊人物;二,不要材料太多;三,不要語言的風格化;四,不要獨特性”。《考工記》里的陳書玉,就不屬于特殊環境中的特殊人物,正是這種“曖昧”,他的生命沒有大起大落,沒有無法承受的苦難,也缺乏動人心魄的幸福。不過,他的“幸運”背后,是無所依靠的彷徨與無奈,明明有顯赫的家世,陳書玉卻仿佛孑然一身,先人無處找尋,家人涼薄無情,容身之處也破敗倒塌。
這種無依無靠的生活方式,反而異常符合現代人的生活常態,故里褪色,家人遠離,留在身邊的僅是三五好友,盡管有些迷茫慌張,依然能夠獲得堅實可感的生活。而一旦不愿安于現狀,想要追索過去的精神線索,往往無計可施,空懷落寞。
除了陳書玉的形象與王琦瑤有所差異,《考工記》里也出現了一些在《長恨歌》里曾經出現的物象,這些物象的含義也發生了細微的變化。《長恨歌》為鴿子設置了專門的一節,開篇就說“鴿子是這城市的精靈”,并且故事整體上從鴿子的俯瞰視角展開。《長恨歌》里的鴿子充滿靈性,看遍了城市的秘密,與被束縛的人類相比,鴿子的身體和心靈都享受著自由。鴿子雖然傲慢,卻是“人類真正的朋友,不是結黨營私的那種,而是了解的,同情的,體恤和愛的”,是人類喜愛的神性生物。然而,在《考工記》里,鴿子的形象開始發生變化,它們不再高高在上,而是落入凡間,人們對鴿子的態度也變得厭惡且不耐煩。老宅遭到鄰居的蠶食,東墻外建造了一間鴿棚,“鴿子屎滿地皆是,腥臭不堪”。陳書玉喂過鴿子,鴿群毫不猶豫地飛落在他的腳邊:“他有意放一點飯粒,引它們啄食,一眨眼工夫,米粒全無。”要知道,《長恨歌》里的鴿子,可是“從來不在弄堂底流連,它們從不會停在陽臺、窗畔和天井,去諂媚地接近人類。它們總是凌空而起,將這城市的屋頂踩在腳下”。落在地上的鴿子,只能留下令人厭惡的垃圾,它們脫下了神性的外衣,也似乎再也無法讀懂城市的故事。
在《長恨歌》里,麻雀是一個負面形象,用來襯托精靈一般的鴿子,是弄堂的常客,是媚俗的,小肚雞腸且缺乏智慧。但在《考工記》里,麻雀與陳書玉的相遇卻充滿了靈動:“看見有麻雀停在窗臺上,然后飛走,尾翼掃在玻璃上,嗖的一下子,那禽類明顯長了力氣。他呢,生出閑心。”和落在地上的鴿子不同,忽而飛走的麻雀此時卻顯得可愛而富有生氣。不僅如此,麻雀還引發了陳書玉的智慧,當他為年久失修的老宅擔憂時,“看見底下幾何形的鋼架之間,進來一只麻雀,左沖右突,最后站在—根橫梁,正對著他。人和鳥對視有幾秒鐘時間,各自走開了。在這幾秒鐘里,他產生一個主意,讓瓶蓋廠負責維修。”
兩種鳥類形象的細微變化,在某種程度上表現出王安憶寫作心態的改變。《長恨歌》里,無論是人物還是動物,都有著些許“傳奇化”的痕跡,他們的身上被賦予了太多東西,時代的氣息、歷史的變遷或是城市的故事,這也是造成小說給人“懷舊”之感的原因。而在《考工記》里,刻意為之的痕跡漸漸變淡,人物、動物或是建筑,開始以一種更加自然而從容的方式出現,小說對都市生活各個方面的表達也更加真切可感。上海的城市形象,也逐漸從“懷舊”的氛圍中解脫出來。
四、清晰的時間與缺席的女性

比起《長恨歌》,《考工記》的時間卻清晰可感,陳書玉明白老宅在新時代里的格格不入,總是想辦法讓自己和老宅跟上時代的步伐。祖父的房間里也有一口鐘,這口鐘沒有停擺,也沒有變慢,而總是“上足發條”。陳書玉雖帶有舊時代“遺少”的印記,卻不僅沒有被時間所圍困,還借助修理鐘表重啟停滯的時間。他修好的鐘表“每天上滿發條,調準時間,嘀嗒走著,到正點還會當地敲起來,幾點鐘響幾下”。與王琦瑤的日夜顛倒不同,陳書玉的時間清晰可感,從不停止。他務實、勤勞,甚至放棄了愛與欲望的體驗,清醒而冷靜地投入日常的生活體驗。

《考工記》無論是建筑構造、城市形象,還是人物的生活方式,都與王安憶之前小說中的上海有所區別。在情節的走向上,王安憶看似一直在延宕讀者的期待,其實卻提供了更加符合現實邏輯的結局。小說摘下了“懷舊”的濾鏡,呈現一個日常、現實且現代化的都市形象,并順著歷史的線索,描繪了“非典型”普通市民的生活經歷,為讀者提供了新的理解上海的資源。
【注釋】
①王德威:《記憶的城市,虛構的城市Ⅰ:海派文學,又見傳人》,《現代中國小說十講》,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②王安憶:《〈長恨歌〉,不是懷舊》,《王安憶說》,湖南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頁。
③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名篇十五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79頁。

⑤王安憶:《考工記》,《花城》2018年第5期。本文對《考工記》原文的引用都出自該文,不再一一注釋。
⑥⑦[法]米歇爾·德·塞托:《日常生活實踐 1.實踐的藝術》,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69頁、169頁。
⑧[美]凱文·林奇:《城市的印象》,項秉仁譯,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1990年版,第1頁。
⑨[德]本雅明:《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張旭東,魏文生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版,第64頁。
⑩[德]本雅明:《單行道》,王涌譯,譯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頁。
?指設置一些障礙性的主題單元以阻止某個計劃的實現。[法]帕維斯:《戲劇藝術辭典》,上海書店出版社2014年版,第305頁。
?[美]帕克等:《城市社會學》,宋俊嶺、吳建華、王登斌譯,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頁。
??[美]理查德·桑內特:《肉體與石頭》,黃煜文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頁、363頁。
?王安憶:《自述》,吳義勤主編,王志華、胡健玲編選:《王安憶研究資料》山東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第69-70頁。
?Burton pike,The Image of The City in Modern Literature,LeGates,Richard T.,and Frederic Stout,eds.The city reader.Routledge,1996.p243.
?張英進:《中國現代文學與電影中的城市:空間時間與性別構成》,秦立彥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6-18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