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木行
李曉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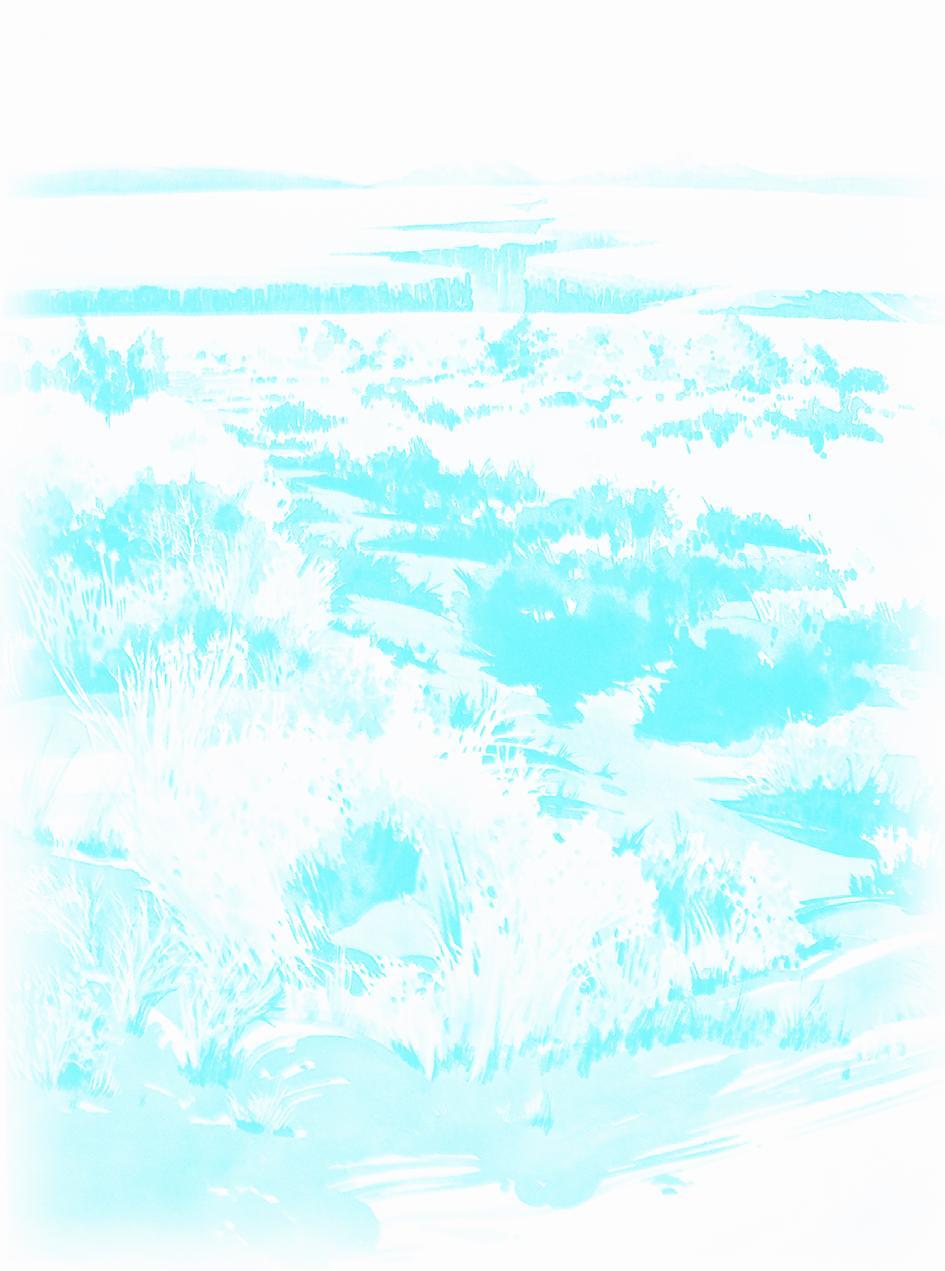
執著追求并且從中得到最大快樂的人,才是成功的人。
——梭羅
草之語
我生來對草木充滿了親切感,每當到了陌生的地方看到陌生的樹木和草,都要停駐仔細打量,看看有沒有與我的生命相通的氣息。我熟悉草,甚至熟悉草木的情緒,知道不同的季節對于草木意味著什么,尤其是白茫茫的冬天與蕭殺的秋天,草木以各種姿態呈現它們的堅強。
草有草的生長周期,人有人的生命歷程。平時,人們太容易忽略小草。草和百姓相似,都屬默默無聞一類。在人和草木的交往中,有的人認為草不會開花。其實,草本植物中除較低等的蕨類植物和苔蘚植物外,大多數的草都會開花結果,只不過它們的花果太不起眼,就像大街行走的普通人,平常的衣服,平常的步履,平常的表情,根本無法知道他們有過怎樣不同尋常的經歷。如果你是一個有心人,跟著一個人進行跟蹤采訪,都會發現每個人都有自己不同尋常的東西。我也是一個普通人,父母為我選了上大學的專業——師范類大學的英語系,畢業后當一名普通的英語教師。如今我已經從教師崗位上退休了,但我教的學生中有兩個不一般,一個當了萬億企業的老總,一個當了學校校長,他們說,李老師,你給我們說過的印象最深的一句話是“做人可以沒有權勢,但是不可沒有格局。”我都忘記什么時候說過這樣的話,可是他們已經由一棵小草長成了大樹。
一位老師能教了幾個出息的學生,是緣分。人和草的相遇也是需要緣分,我上初一時,父親常常帶我到貴定縣關力堡村去寫生。我趴在關力堡表叔的窗戶往外看,立即看見了窗外草地的花蝴蝶,馬上就跑進草地。在草地,我把辮子打開,綠色的風便和我的長發一起飄揚。在我的體悟里,草和人是一樣有呼吸的,只不過很多人忽視草的呼吸。草有自己的語言,或者可以稱作“草語”。草們會和同類說話,甚至可以用肢體動作表達思想情感,只是人類聽不懂它們在表達什么。我的家鄉黔南有一個縣叫三都縣,深山有一種草叫風流草,只要聽到人唱歌,它就會跳舞;風流草見到姑娘穿得漂亮,也會搖搖擺擺地跳舞,只是對那些邋遢的男人,無動于衷。草還會吹奏樂曲的,尤其是夜晚,草叢里彌漫著草們好聽的奏鳴曲。在草叢,我相信只需把手伸過去,就可以接住夜空里的螢火蟲,它們不僅發亮,還像鈴鐺和鐘表一樣會唱歌。
我是一個自然主義者,上大學時候,我讀到梭羅的《瓦爾登湖》就快樂得發瘋,感到美國的梭羅是草木的知音,當然也是我的知音。梭羅徜徉于大自然,他說“一個湖是風景中最美的,最有表情的姿容。它是大地的眼睛;望著它的人可以測出他自己天性的深淺。湖所產生的湖邊的樹木是睫毛一樣的鑲邊,而四周森林蓊郁的群山和山岸是它的濃密突出的眉毛。”貴州多山,我也常常一個人爬上某一座山頭,靜靜地體察大自然:天空的云彩像是一條金魚的圖像,云彩的周圍還有飛來飛去的白鷺,山坡上的草啊,鳥啊,它們都是人類的朋友。天空的云彩在一早一晚會發紅,像是火燒一般,而小草不會,小草的一生,或者是綠的,或者是黃的,綠的時候是活著的,黃的時候是枯萎了。對于生死,草們比人類要坦然得多。
草的夢
很久以來,我期待在某個夕陽款款而來的時候,有小草腳步聲從長廊響起,穿越一個又一個門,走到我駐足城市的那個鋼筋水泥的門牌號,走上19樓……這個時候我仿佛通靈,感到關力堡的草木又在呼喚我了。
于是乘車來到了關力堡,貴定縣的關力堡離我所在都勻并不遠,不到一個小時車程。表叔的房子就在公路邊,我把車停表叔大門口,登上小三層樓的最高一層,看到房子后面的一大片草甸子,這是經過鎮政府聯系搭橋,專門為城市美化而種植的草皮。在草甸子里,我能看到在大片的枯黃中間,居然夾著令人心動的小小的綠。草地的東面是公路,公路的前面是綠山,黔南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冬天,即使在隆冬季節,山坡仍然綠黃交加。田野里的田埂并不那么筆直,田梗邊會有垛起來的圓圓的稻草垛,一層層圍著木柱,中間高,四周低,雨水可以順著草葉流下來。
草對于關力堡是過客,正好似人活在世界上都是匆匆過客。秋天結束的時候,會看到一部分草皮被卡車運走了,這時草甸子就不完整了,有草的地方是綠的,沒有草的地方是黃的,而且地皮凹低。因而我盼望夜晚早早到來,夜幕會掩蓋住一切。夜晚來了,關力堡寨子四周的山線逐漸模糊,山是深色的,天空是淺色,可謂山天一色。大自然安靜了,人的大腦就活躍了起來。寂靜不是絕對的,夏天和秋天可以依稀聽見鳥鳴或是蟲語。深夜,草葉會發出聲波,仔細聆聽,聲波里有長句,有短句……這是草們自己的語言符號。星子們在天際閃著光,天空開著無數扇門。小河邊的小樹林更暗了,除了大人打著手電筒走過去,小孩子絕不敢過去的。人們對眼睛看得見的黑暗有恐懼之心,而對心底中的黑暗卻麻木不仁。
關力堡的草坪里藏著各種會唱歌的蟲,草和蟲類都有自己的生活,我雖然不是草,也不是蟲,但是我可以藏匿在它們身邊,做一個隱身者。草和蟲子,還有它們身邊的樹木好像并不反對我的隱身,它們只管自己以自己的方式安置自己。草們的生命雖然不像人能活幾十年,但是在自己的生命周期內照樣活得精彩。在草甸子,我還看見了黑白相間的小鳥,比麻雀小,能發出尖細玲瓏的叫聲(我稱呼它為靈鳥)。在貴州這個地方,沒有北方的嚴寒,即使在冬天草們也不會干枯,只會發黃,在黃兮兮的大片的草叢中間,還會夾雜一些嫩綠的小草,它們急切地翹盼春天的到來。我注意到草很公平,年輕的草不會歧視年老的草。我喜歡這片草地,喝醉一般和草們無距離交流,沒有官腔,也沒有空話和套話。草甸子上草的身形如此纖小,使得我對它們就多了憐愛。我發現草也有自己的秘密,只是人類不知道而已。
表叔的孫子是一個快樂陽光的小家伙,每次我到關力堡,總是纏著我講故事。我曾和小家伙淌過小河,捉泥鰍,我倆捉了三條黏糊糊的家伙,放進小水桶,往回走,路上向我講了一個女孩的事:女孩在東安小學上學,三年級。她媽媽在廣州打工,跟一個男人跑了。她爸爸去了廣州,再也沒回來。一天晚上,女孩一定做夢看到自己的爸爸媽媽,她起床喊著爸爸媽媽往河邊跑,奶奶跟在女孩的后面,沒有跟上……第二天早上,人們發現女孩躺在小河,從上游的小東寨漂到新安寨鎮的關力堡……從此以后,在關力堡走夜路就有了莫名的恐懼。
草木寂靜
一次次抵達關力堡,一次次登上表叔小樓打開窗戶……又看到那片可以寄存靈魂的草地了。雖然是冬天,貴州的冬天不算太冷,草地大部分已經干黃,尚有一部分綠的小草和蔬菜。我看著小草,小草們也看我。白天的關力堡是安靜的,夜晚到來后更加豐富多彩。我感到自己像梭羅一樣喜歡夜晚的孤獨感,梭羅在瓦爾登湖邊生活的時候,曾這樣描寫過心境:“大部分時間內,我覺得寂寞是有益于健康的。有了伴兒,即使是最好的伴兒,不久也要厭倦,弄得很糟糕。我愛孤獨。我沒有碰到比寂寞更好的同伴了。”是的,平常我們在人群中有說有笑,實際上有時候不是發自內心,而是應酬,應酬得久了,就會產生虛假,虛假的笑容,虛假的奉承,虛假的生活……真的是糟糕透了。
我喜歡夜晚到來時那種堪稱完美的安靜。比如在關力堡的草坪上,剛才我還低頭看手機,猛抬頭看到大地上的光線已經走丟了,真的沒有想到,這些在白日里生龍活虎的山頭,怎么一閉眼就睡著了?關力堡的夜晚是我所熟悉的,晚八點以后,星星會落到草叢捉迷藏,你可著勁去跑,也不會驚跑它們。星星們還會笑嘻嘻地藏在窗下,說“我們偏不走!”夏天或者秋日,只要打開窗,就會聽到野蟲藏在草棵之下唱歌,窗外還有蝴蝶,蟋蟀,還有能飛得很遠的蚱蜢。三十幾米外有一溜樹木,樹葉大多掉了,但是枝丫依然很密,小鳥藏在里面,人看不見它,只能聽見它好聽的叫聲。
位于云貴高原上的貴州,山是主角,山之間的平地并不多,無論是稻谷,還是小草,可著勁長,長到山根,就長不動了。山坡的主角是灌木,即使是有小草,小草也被灌木掩蓋住了。山的上面是天空,山腳的下面是一條小河,沉靜而神秘。水中剪影般地出現交錯迷亂的樹影和為枝條所分割的藍色天空,形成一幅天然的抽象畫。這一大片草地的四周是山,東西北三面的山像大饅頭,獨有南山呈馬鞍型。山底的小河無名而寧靜,清凌凌的水里漂動綠瑩瑩的水草,是生長在水下的草。天空的白云在不遠的小河水中閃爍而過,然后蹤跡全無。農民在小河邊種蝴蝶蘭,春天的時候,蝴蝶蘭就像一只只蝴蝶翩翩起舞。如果把臉藏在花辨后面望月……月亮只剩下半牙時,最迷人。在月夜可以和一只小狗在田野上奔跑,心砰砰地跳。可以說,無論時光怎樣流逝,草木的眼神一直淡定,迷人,而自己作為塵世中一顆粒子,卻越來越小,感到時間是一頂扎不牢的一帳篷,只要一陣風就能把它吹跑。
我的家鄉不缺乏草木,但多年前年云貴高原遇到大旱,春天的山頭和土地不是綠的,而是黃的,對于已經習慣青山綠水的貴州人,焦灼到了極點……我才知道,有些草即便沒有實用價值,至少可以綠,用綠去滋潤期待健康和幸福的人們。在鄉下,你會遇見了一棵樹,我問它信仰什么?樹木告訴你說,信仰時間。一個人活著,存在的依據是什么?我以為坐在草地可以大悟。人們總是容易短視,只看重自己的物質需要,看不到其它植物和物種的存在。人們發狠的時候會說,“我要像踩斷一棵小草一般整死你!”豈不知小草在地球的生命要比人類更加久長呢。草還喜歡和別的植物做朋友,比如說野菜,草從不會干涉野菜長在草叢。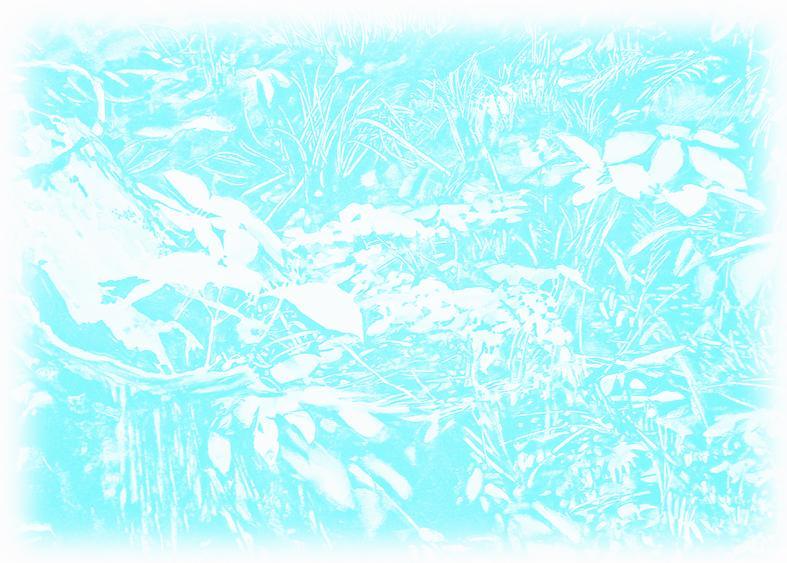
在草地,有時候我的思緒很遠,會想到一些哲學家的名字,從中國的孔子、孟子,到外國的蘇格拉底、康德等,感到他們的思想成長可能與他們所在地的一片草地有關。有了草的生長,就有了思想的孳生地,美國的梭羅并不是哲學家,但是他熱愛大自然,崇拜東方哲學,才有了他的《瓦爾登湖》。人類的三大哲學基本問題之一,就是人生的意義是什么?人們對這個問題見仁見智,在人類爭論不休的時候,草和樹木已經靜靜地回答了這個問題,只不過人類并沒有草木悟性好,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