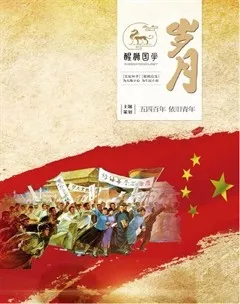啟蒙新思想,古豈能拘牽
楊雪瑾



人們思想的改變從不是一蹴而就的,文學的改變也是如此。從晚清起就開始醞釀的“言文合一”的語言變革,在新文化運動中積蓄力量,為文學革命提供了動力和契機,又借著“五四”運動的大勢,將這場驚天動地的變革推向高潮……從1917年1月《新青年》第2卷第5號發表胡適《文學改良芻議》,到1927年冬后期創造社活動提倡革命文學運動,這短短的十年對于文屆不啻于海嘯地震般的震撼。在這場震動中,不僅僅有零余者的哀嘆,更有鐵屋中的吶喊,像在黑暗中尋覓光明一樣,找尋中國文學的未來出路。
1915年陳獨秀創辦《青年雜志》,次年改稱《新青年》,舉起“民主”和“科學”兩面旗幟,猛烈抨擊封建主義舊文化,提倡新文化。1917年2月,在《新青年》發表的《文學革命論》中,陳獨秀提出了著名的三大主義,把文學的形式與內容聯系起來,也就是我們現在熟知的“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國民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雖然仍然不夠全面,但是也反映了“五四”文學革命運動民主啟蒙精神的一個重要方面。
語言表達模式的變革是文體變革的先聲,與思想觀念的更新密切相關。,改變文學的外顯形式成為了和舊文學相區分的當務之急。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并在“文學革命”的口號下,提倡新文學,也成為了當時的先鋒知識分子所奮斗的目標。1916年時《新青年》編輯部還只有胡適的詩文使用白話,留下了諸如“兩只黃蝴蝶”之類的實驗之作。到了1918年1月《新青年》編輯部改組,全部改用白話。這是當年最早的一份白話雜志。由于《新青年》同仁采取凌厲的攻勢,將廢除文言與反對封建專制制度,批判孔孟之道結合了起來,將推行白話與推行民主科學精神結合了起來。
之所以在短短兩年間就取得如此卓有成效的效果,就不得不提胡適在1916年10月發表的著名文章——《文學改良芻議》,此文以別開生面的“文學八事說”吸引了文屆目光,并引發了大討論。陳獨秀提出新的文體分類學說,認為應將應用之文與文學之文徹底分家,得到了《新青年》同仁的一致贊同。經錢玄同、劉半農的進一步論證補充,總結為“文章區別于文學,正是在實用與不實用上劃清界線”。不過甚為可惜的是,五四運動一過,對應用文體的研究突然沉寂,傳統的雜文學觀念又占住了人們的頭腦。本來纏繞不清的文章現象,由于復雜的社會生活又造出了眾多的新文體,從而變得更加難解難分了。
總體而言,“五四”時期所誕生的現代文學,是在中國社會內部發生歷史性變化的條件下,廣泛接受外國文學影響而形成的新的文學。它不僅用現代語言表現現代科學民主思想,而且在藝術形式與表現手法上都對傳統文學進行了革新,建立了話劇、新詩、現代小說、雜文、散文詩、報告文學等新的文學體裁,在敘述角度、抒情方式、描寫手段及結構組成上,都有新的創造,具有現代化的特點,從而與世界文學潮流相一致,成為真正現代意義上的文學。“五四”文學革命由倡導白話文開始,就體現了文學必須能為最廣大的群眾所接受的歷史要求。文學革命的先驅者并提出了“國民文學”、“平民文學”的口號,以表現普通人民生活、改造民族性格和社會人生為文學的根本任務。在創作實踐上,出現了中國文學史上從未有過的徹底反封建的新的主題和人物:普通農民與下層人民,以及具有民主傾向的新式知識分子,取代封建舊文學中常見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成為文學的主人公,展示了“批判封建舊道德、舊傳統、舊制度”、“表現下層人民的不幸”、“改造國民性”與“爭取個性解放”等全新的主題。
經受了“五四”的洗禮,文屆也煥發了屬于自己的獨特時代風貌,以理性精神的張揚、感傷的時代標志、突出的個性追求、多樣的創作形式為特征,勢不可擋地開拓了現代文學的新紀元。隨后的幾十年中,魯迅、巴金、朱自清、徐志摩、林徽因、張恨水、冰心、張愛玲、胡適、丁玲等等依次在文壇進發光和熱,這些活躍在中國二三四十年代舞臺上的最優秀的人們,當你讀了他們偉大真摯的作品,才了解那個時代的人們一如我所生活與熱愛的時代一樣,也有著自己的喜怒哀樂,也有著至純至真的幸福與快樂,有著“惟其是脆嫩”的憂郁與愁思,有著生生不息的鐵血與奮斗。那些歷史是這些人的歷史,是他們筆下的人物的歷史,是所有他們生命拓展的歷史。正是他們滿負艱辛地走到了今天,才有了今日之中國。
從“五四”的文學革命到今天,盡管時代已經不同,文學的審美追求也有了很大的改變,但是中國現代文學繼承和發展確實從“五四”以來所提倡的優秀傳統。魯迅先生曾經預言:“人國既建,乃始雄厲無前,屹然獨見于天下。”當代文學只有時刻不忘“創造這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的使命,才是對“五四”精神最好的繼承。
編輯/徐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