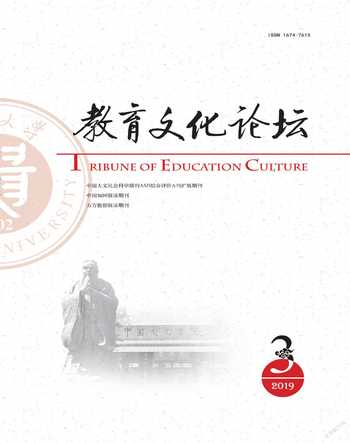西南儺戲藝術膜拜價值與展示價值研究
胡李柱
摘 要:儺戲作為一種原始的藝術形態,隨著當下經濟、技術發展,越來越呈現出傳承與發展疲態。為何會出現這樣的狀況,目前學術界研究較少。本文從本雅明的“靈韻”“膜拜價值”與“展示價值”這幾個概念出發,研究儺戲作為一種有“靈韻”的藝術在當下的存在狀態,對儺戲的膜拜價值與展示價值進行分析。并將儺戲藝術的傳承與發展放在別現代視域下,從觀眾角度出發,分析觀眾的評價如何使得儺戲藝術中膜拜價值與展示價值的裂變。同時,技術媒介變遷對藝術的影響,使得儺戲展示價值與膜拜價值裂變的程度進一步被放大,而且儺戲藝術的展示價值最終超過其膜拜價值而獲得藝術自律。
關鍵詞:儺戲;本雅明;膜拜價值;展示價值;靈韻
中圖分類號:G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7615(2019)03-0062-05
DOI:10.15958/j.cnki.jywhlt.2019.03.011
Abstract: As an original art form, the Nuo Opera has been increasingly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rrent economy and technology, the reason for which has less researched at present. Based on Benjamin’s concepts of “Aura”, “worship value” and “exhibition valu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esent existence of the art as a kind of “Aura”, and the worship value of the opera, and by putting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rt of the opera in allomodern perspective and through the audience angle, discusses how the audience comments would influence the fission of worship and exhibition value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influence of technological media changes on art causes the magnifying effect of value and the fission of worship value and that the exhibition value of the art of the opera will eventually replace the value of worship and obtain the art’s autonomy.
Key words:Nuo Opera; Benjamin; worship value; exhibition value; aura
一、作為“靈韻”藝術的儺戲
本雅明在《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中曾經提到“靈韻”這一概念,“靈韻”概念提出的語境是文藝復興以后,隨著技術的發展,藝術作品所具有的的獨一無二的“神秘性”。本雅明在談到藝術最初產生時與宗教禮儀的關系時說:“最早的藝術起源于某種禮儀—起初是巫術禮儀,后來是宗教禮儀。藝術作品那種具有韻味的存在方式從來不能完全與它的禮儀功能分開。換言之,真正的藝術作品所具有的獨一無二的價值根植于禮儀中,藝術作品在禮儀中獲得了其原始的、最初的價值。”[1]藝術作品在早期與巫術不是截然分開的,甚至可以說是藝術作品在早期對于巫術與宗教有一定的寄生性。我們在儺戲中可以窺見一斑,在西南地區不同種類的儺戲中有著不同的表現形式。如,在德江儺堂戲中,戲劇表演處于一種附屬于儀式的地位,演戲的目的為取悅于神靈而獲得福佑;又如地戲中的封箱儀式,但這已經處于一種較晚的形式,對巫術宗教的依賴性已經弱化許多。
儺戲作為一種原始藝術形式,我們可以看出其對巫術、宗教的依賴性。“從藝術與宗教的歷史發展來考察,我們會發現舉行任何宗教儀式都需要一定的表現形式、表現工具和程序,而早期藝術的各種形式,諸如歌、舞、詩、繪畫、雕塑等等,就是這種最恰當的表現形式、手段或工具。”[2]首先,舞蹈、音樂、服飾、繪畫等各類藝術形式在儺儀式中的功能看,都是為整個巫術儀式的完成服務,帶有一定的實用性。如,繪畫藝術在穿青人五顯壇的表現,各類神祇案畫的繪制,功曹、山魈、水魈、二郎等神祇人物案子。這些繪畫,在本質上是一種由早期圖騰崇拜的演變而來,賦予人格化的表現。在早期的藝術形式中也有相類似的實用,如人類早期在巖壁上的畫作,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原始人類對獵物的祈求,并由此演化而成的巫術、圖騰崇拜。畫師在對這些神祇的創作中,表達出的崇拜情感是高于創作時的藝術審美的。又如,法冠、法袍所承載的刺繡藝術,在被手工生成出來并使用之后,它原有的使用價值與審美價值在巫儺儀式中被淡化了,成為一種展示給信眾具有一種神秘性的特殊存在物。信眾與這些物品之間有一個距離感,而由這個距離感自然而產生一種神秘感。這些又如書法藝術在儀式中的唱書、祖公的牌位、告書、符中的運用。文字作為書法承載體的藝術性在此是被忽視的,帶有一定的實用目的。如唱書被作為一種唱誦的記憶工具,牌位上的文字作為記錄祖師的載體被賦予了祖師的靈魂,告書與符咒上的書法作品被用作與神祇交流的工具。舞蹈,如舞蹈的步法,七星步、罡步作為一種娛神的姿態出現,滿足神對于人的規定性。手訣,作為一種神性存在方式,在儺儀式上可以產生神性的影響力,而到了儺戲表演中,它本身成為一種可具有觀賞性的手指表演動作。簡單來說,我們在諸如神話題材的電視劇中所看到的各種手訣,在戲劇演出過程中靈性的部分是退隱的,只作為一種神性力量的表現形式。在儺儀式中,這也是一種給信眾觀看的帶有靈韻的形式,在儀式中這種靈性成分與表演成分處于一種含混。以上種種,都反映出了在巫儺儀式中各類藝術處在附庸的地位上,其作為一種工具的功用性是大于藝術的審美性的。藝術作品在此時是帶有“靈韻”的,富含神秘性與神圣性,并處在一種藝術與巫術的含混狀態。
其次,藝術作品與儺的含混狀態。在前文,我們說到藝術作品在儺儀式中處在一個附庸地位,而缺乏一種藝術自覺。在整個儀式過程中,藝術作品的膜拜價值與展示價值處在一個雜糅狀態,無法區分。如儺公儺母的泥塑或者石雕,可以看做一種藝術作品的同時也是作為被信仰的對象。作為藝術作品時,觀眾在觀察時是帶有大眾的審美眼光進行美感的評判,雖然審美從本質上是一種個人化的,但不可否認大眾審美對于個人審美的強烈影響。作為被信仰的神靈時,信眾帶有一定的個人化的膜拜情感。再者,儺信仰藝術性表達的必然。作為被信仰的對象,其必然具有一定的神秘力量或神秘要素,正如所說的,在被手工生產出來,帶有神秘性。具體如下:首先,要使超自然的本質成為群體膜拜的對象,就得以具體的感性印象的形式。在儺戲藝術中,表現為常常在一定的膜拜對象物通過泥塑、木雕等藝術形式展示出來,使得崇拜者可以直觀地看到對應的膜拜對象,這個時候抽象的神靈變得具體化、具象化和感性化。第二,舉行宗教儀式時,對神的召喚和乞求則成為最本質的方面。原始洞穴壁畫,尤其舞蹈、詩歌是激發宗教情感的載體,在這些激發宗教情感的載體中,藝術從一開始便帶有了“神性”或“靈韻”,儺戲在表演過程中,唱儺歌、跳儺舞等實質上就是一種激發儺信仰的載體,以此來召喚出神靈降福,如撮泰吉中的舞蹈、慶壇中的舞步等。作為信仰群體的大眾,大多數人的知識水平有限,如何讓這些神秘力量被理解、被信仰也成為儺戲藝人所思考的問題。談到理解方式,最直觀的就是視覺藝術,其次是聽覺、嗅覺。這也解釋了為何儺儀式中有如此多的特技表演,從本質上說這些儺技基本上都是以視覺方式呈現,對信眾有一個征服作用,使其相信背后的神秘力量的存在。儺戲藝術,除了視覺上的呈現,還有聽覺上的補充,將神祇的故事演述出來,使信眾更易理解。其中不乏“諢詞”“亂語”,以博得信眾的一笑,也是其信仰價值面向信眾的敞開。正是這種敞開,使得儺戲呈現一種生活化的表達方式。如五顯壇中,土地買肉等情節的展現。除此之外,儺戲中還有一些世俗人物的出現,如歪嘴秦僮的形象,就是一個世俗小人物,擁有著丑陋的長相,卻時常語出驚人、逗樂調笑,又如陽戲中的安安等。這些世俗人物的出現,拉近了表演者與觀眾的關系,使得戲劇更具觀賞性。同時,也由原先表演神的故事慢慢走向表演人的故事。這一點在陽戲壇上表現明顯,陽戲中有三圣信仰,即“川主”“土主”“藥王”,這其實已經逐漸由對神的信仰走向對被神化的人的信仰,越來越走向生活化。儺戲的藝術性與審美性,在這一敞開的過程中逐漸凸顯。
然而,在作為有“靈韻”的儺戲藝術還未脫離原始形態而存在時,已經面臨著危機。
二、別現代視域下儺戲膜拜價值與展示價值的裂變
別現代是由王建疆提出,旨在指出中國目前社會狀態所具有的不同于其他國家的現代性特征。中國當下由于經濟、文化發展不均衡帶來的一個前現代、現代、后現代歷史的、地理的交織狀態。而正是這個論述,給我們對儺戲藝術的研究帶來了很重要的啟示意義。別現代狀況下,人與人之間的知識水平、審美鑒賞力都是具有明顯差異的。也由于一定的地理時空所產生的觀念發展水平的不同,導致對儺戲藝術的評價呈現一種多樣化。究其本質,還是主要由儺戲觀者的多樣化造成的。儺戲的觀者主要有以下幾種:信眾、非信仰的大眾及其他。這些人也呈現出參與者與觀者的雙重身份,由此帶來了一種儺戲的膜拜價值與展示價值的“裂變”。
費爾巴哈曾經指出:“純粹的藝術感,看見古代神像,只當看見了一件藝術品而已,但異教徒的宗教直感則把這件藝術作品,這個神像本身,看作實在的、活的實體,他們服伺它就像服伺他們所敬愛的一個活人一般。”[3]費爾巴哈的這段論述為我們正確認識原始藝術提供了參照,同時也表明原始藝術畢竟是宗教禮儀的副產品和工具,觀眾的不同,也帶來了不同的審美趣味和價值觀。我們可以看到,在陽戲中為信仰而雕刻的三圣公對于信眾的意義與對于非信眾的意義顯然是不同的。對于信眾而言,所有的儀式的作品都具有崇高意義,不容褻瀆與質疑,看中的是藝術所模仿的神秘性;對于非信眾而言,所有的儀式都是一場“表演”,所有使用的道具都是有一定審美價值與展示價值的藝術品。其作為原始狀態的儺戲,在內核上由觀者的不同而導致了膜拜價值與展示價值的分化。對于本雅明來說,這是由于演出的機械重復,在這里也得以展現出它的力量,促進膜拜價值與展示價值的分裂。
信眾與非信眾在別現代語境下相互轉化的可能。別現代帶了更多的是前現代、現代與后現代的碰撞與摩擦。在這種碰撞中,必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在一定條件下有轉化的可能性。別現代不僅是一個社會狀況,更是一個個體狀況。因為人的思想的復雜性,人的思想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有一個變化發展的過程,個體的思想中也必然包含著前現代、現代、后現代諸多思想。縱使當下科學、理性思想較為普及,但人們在面對不可解釋的事物時也是無能為力,最終上升到宗教神學,以獲得精神救贖。這便為信眾與非信眾的相互轉化提供了一個可能。但我們所發現的,更多的是信眾向非信眾的轉化居多。如,在進行儺儀式時,將其作為一種商業行為進行操作過程中,主人家往往帶有一種圖熱鬧的心理舉辦相關法師活動亦或者因為上一輩的信仰而不得不做的“偽信仰”。在湘西地區的陽戲中最為明顯,呈現出一種完全商業化的表演。信仰與戲劇完全分離,儺儀式主要由專門的儺法師負責,而演劇則由專業化的劇團演出,作為儺儀式過程中無聊時的消遣活動。且在此,法師不扮演任何儺戲角色,只充當一種靈性的代言人,與世俗是脫離的狀態,戲劇演出者也不能學習任何關于儺儀式的知識,兩者完全分化,在一場還愿儀式中各司其職,達到藝術與巫術宗教的各自獨立。在田野調查中,越來越多的壇班出現斷代,無人繼承,信仰基礎越來越薄弱,而作為展示成分的戲劇自身為了發展,必然從中脫離出來。由此可見,這種儺信仰呈現出一種逐步消亡的狀態。同時,儺戲在這里便起到一定的承接與緩和二者關系的作用。儺戲的觀者,在此時是無需有信仰,是誰都可以看得懂的,是一種神祇的具體展示,信眾在此時也處在被非信眾淹沒的狀態。膜拜價值在這時被展示價值所擠壓。隨著非信仰群體的觀者的增多,信仰群體的地位越來越被壓縮。儺戲藝術的展示價值由于非信仰觀者的數目增加,這種膜拜價值與展示價值的裂變加劇,儺戲藝術的“靈韻”也逐漸消亡。儺戲藝術的膜拜價值與展示價值的鴻溝也逐漸擴大,分裂已在所難免。
觀者的評價作為一種審美再創造活動對兩種價值分裂的助力。由于技術的發展,現代或后現代文化隨處可見,觀者的審美品位也在逐漸提升。觀眾接觸到的藝術形式越來越多,對儺戲這種傳統形態的戲劇形式也會形成一定的審美評價。從本質上來說,這些評價是一種審美再創造活動。在審美的過程中,這種評價會促進儺戲藝術原始形態的轉變。由作者中心、劇本中心轉變為觀眾中心、演員中心,而儺戲藝術目前正面臨著這一種轉變。觀眾的評價對于儺戲的發展是有著深遠影響的,儺戲藝人有時候必須按照觀眾的喜好演出相關劇目。如,觀眾喜愛地戲中的楊家將戲,演員也必須演,觀眾想觀看儺技,特技演員也必須表演。例如,在儺文化藝術節中,觀眾在面對精彩刺激的上刀梯、開紅山、口吞紅鐵時,表現出一種激動的情狀。這給表演者帶來一種反向的刺激,使得他們在以后的演出中會更多考慮此類表演,以獲得觀眾認可。而原先儺戲中較為原始的成分,因為理解的困難,逐漸被拋棄,靈性成分逐漸缺失。這類緊張刺激的表演,原先的靈韻價值是祈福禳災,在商業化演出中,這種功能退居后方,取而代之的是其展示價值。我們可以看出,從一定程度上演員沒有了主動選擇的余地,因為在經濟社會,這與演員的收入息息相關。這種觀眾的評價對于儺戲藝術膜拜價值與展示價值的裂變,也有一定的助力。
除此之外,部分地區的陽戲在社會經濟的推動下,出現以經濟價值衡量戲劇的現象。如湄潭地區,按照主人家的意愿商量演戲的場次與時間,并依此進行結算。在遵義道真的中國儺城,也出現一批陽戲藝人,進行商業化的表演活動,以此來謀生。此時,儺戲的膜拜價值在這一系列的商業活動中被沖淡,其展示價值在商業演出的過程中被抬高。有其在演出過程中,面對的觀眾群體主要是游客,游客注重更多的是其展示價值的一面。且這種商業演出是每天都進行的,在重復的演出中,其展示價值進一步被放大,而膜拜價值被消解。另有部分有一定文化藝術的民間藝人,對原生態的儺戲進行改造,在音樂中加入板腔,并根據原有的劇本進行藝術再創作,使得其更具有觀賞性,其展示價值也在這一改造的過程中加速從膜拜價值中分裂。
三、媒介技術跨越性發展帶來的機遇與問題
在本雅明那里,媒介還停留在機械復制時代的傳統媒介。麥克盧漢曾認為:“任何媒介或技術的‘訊息’,是由它引入的人間事物的尺度變化、速度變化和模式變化。”[4]隨著新電子媒介的發展,由原先單向度的傳播逐漸演變成多向度的具有交互性的信息互換。而這些變化又為儺戲這種原始形態的藝術帶來怎樣的影響呢?
首先,所有藝術在這個時代都面臨同一個問題,“快文化”帶來的沉淀不足,藝術作品的經典性受到的消解,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說的那樣,“商品、物質產品的生產,要花費一定量的勞動和勞動時間。一切藝術和科學的產品,書籍、繪畫、雕塑等等,只要它們表現為物,就都包括在物質產品中”[5]。在這種物質化的過程中,神圣的意味即告消解,也就是本雅明的現代藝術理論中所說的“韻味”的消失。對于儺戲藝術而言,其藝術作品所具有的“靈韻”隨著其獨一無二的在場狀態顯得彌足珍貴。從它的演出場域出發,在當下主要的演出場域還是在民間,雖然同一班子演出的劇目有一定的程序化,但對于儺信仰本身而言,是獨一無二的,其膜拜價值在特定的在場狀態下是高于展示價值的。而真確性的藝術就是靠著它所散發的“韻味”或“光暈”來確定其神圣地位的。只不過到了后工業化時代,新電子媒介的發展,同一儀式在網上被傳播,出現了大量的電子化的復制品,藝術的光暈逐漸暗淡了。因為隨著大量復制品的出現,“真品”取代了“膺品”,而人們對“真品”的觀念也隨著能接受而逐漸轉變過來,因而正是這種復制品驅散了原真藝術品的“韻味”。
其次,儺戲藝術,在紛繁復雜的社會文化中,尤其是新電子媒介帶來的大眾文化中,處在弱勢地位,這種傳統的藝術所具有的神圣感、本真性、距離感發展到最后,日益遠離了大眾接受,不得不走向凋零和消逝,被反和諧的現代藝術所代替,所以出現了本雅明所謂的藝術的“裂變”時代。“裂變”的結果便是展示價值最終取代膜拜價值,發展出一套完善的藝術形式,實現了藝術的自律。如,在貴陽花溪舉辦的儺文化藝術節。各個儺戲班子的展演活動,受眾群體眾多,但大多數都是帶有審美消費意味前去觀看,品位其別樣的原始藝術性。較少有真正信仰與膜拜者。而儺文化要發展,也必須要依托儺戲、儺技為代表的具有展示價值的藝術獲得當今語境下的一席之地。作為一種文化產業,想要走得更遠,也必然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對其膜拜價值進行適當的拋棄。如,去進行商業演出或文化交流,需要盡力展現自身所具有的藝術意義。
最后,互聯網等新媒體平臺所帶來的便利性,為文化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很重要的虛擬場域。這個場域提供了展現儺戲自我意義與價值的同時,放大了審美再創造的效應,加深了觀眾的評價對儺戲發展的影響。其具有極強的交互性,儺戲藝術的廣泛傳播帶來了觀眾群體的急劇增長,觀眾評價的效應也增加。儺戲演出的形態也需要以觀眾為中心,不斷改變,最終實現膜拜價值與展示價值的徹底剝離。
四、結語
隨著技術的發展,以儺戲為代表的原始藝術形式在當下的發展過程中,呈現出“靈韻”的消失與膜拜價值與展示價值的分裂。而這種分裂在所難免,又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在西南地區,我們可以明顯看見原始藝術正如本雅明所論的那樣,處于消失的邊緣,可見其思想的深刻性。同時,我們也可以借助西方已經發生過的藝術變遷來反思自身,做到保護與發展的同步。儺戲的展示價值終將超過其膜拜價值,而獲得藝術的自律,儺戲藝術正在逐步走向自律,終將脫離宗教與巫術而獲得自身的藝術形式。
參考文獻:
[1] 本雅明.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M].倫敦:哈佛貝拉納普大學出版社,2008:27-31.
[2] 張文杰.藝術裂變時代的美學[D].上海:復旦大學,2009.
[3] 費爾巴哈.費爾巴哈哲學著作選集:下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684-685.
[4] 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3-4.
[5]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64-165.
(責任編輯:趙廣示)
——鄉村儺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