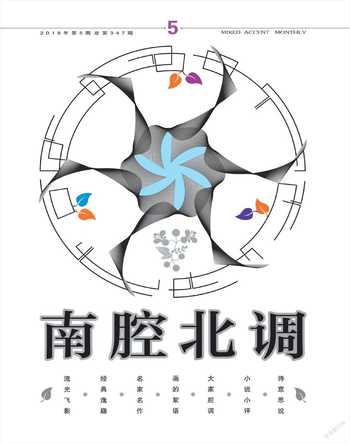當代中國版《東京物語》
趙振杰
“子女們長大之后,總歸會漸漸遠離父母的,畢竟大家都是要以自己的生活為重的。”
“如果是這樣,那父母與子女的關系就太冷漠了。”
“不錯,但每個人漸漸都會變成這樣的。”
“生活難道總會這樣讓人失望嗎?”
“是啊,不如意的事太多了。”
用電影《東京物語》中的這段對白,來概括羅偉章中篇小說《倒影》(《人民文學》2019年第1期)的主題,或許再合適不過了。伴隨著現代化進程的逐步加快,中國的家庭日益單元化、分子化,幾世同堂的傳統大家族變得越來越罕見,《東京物語》中所呈現的親緣關系,正在成為中國家庭的普遍現狀;而與此同時,在婚育政策、醫療條件、生活水平、思想觀念等多方面因素的合作用力下,中國已提前進入老齡化社會。當父母步入耄耋之年,誰來贍養?當老人患病住院時,誰來陪護?這些已然成為當前每一個中國家庭必須面對的棘手難題。《倒影》所傳達和表現的,正是在這種時代癥候和社會語境下產生的倫理危機與生存困境。
小說以醫院為據點,以“父親的病”為導火索,采用定向爆破的敘事方式,將子女們的內心世界逐一炸裂,從得知父親住院時的張皇失措,到病房陪護時的手忙腳亂,從選擇放棄治療時的迫不得已,到問訊父親去世時的追悔莫及,各種復雜微妙的情緒交織在一起,如銀瓶乍破一般,被和盤托出。父親突發腦溢血,正在醫院緊急搶救。當“我”得知消息時,正在酒桌上與縣城里的幾個朋友推杯換盞。在大姐夫的再三催促下,“我”只好極為尷尬地起身告辭,趕赴醫院。病床上的父親正在急促顫抖,一名護士熟練地向父親體內插著各種管子,兄弟在一旁不停地喊著“爸爸,爸爸”。不知過了多久,父親終于平靜下來,兄弟問我:“三哥,你渴不渴?”這時“我”才覺得整個身體像被擰干,于是摸出零錢,讓他去買水。望著兄弟早已被汗水浸透的衣服,“我”不禁感嘆道,他竟然手頭如此拮據,連買瓶水的錢都不舍得花。第二天早上,大哥、二哥也來到醫院。探視過后,兩人紛紛表示父親生還的希望或許不大,不如果斷放棄治療。隨后趕到的大姐夫聲稱,自己可以動用醫院關系安排車輛把父親接回家。而“我”和兄弟卻堅決不同意。為了打消大家的顧慮,“我”主動提出愿意支付全部住院費,但話一出口,便心生悔意,畢竟“我”不過是一名省城的小公務員,工資微薄,還要供給一家人的開銷,能拿出手的積蓄也相當有限。片刻沉默之后,大姐夫打破僵局,他說:“即便如此,也應提早考慮后事,萬一老人有個山高水長,不至于手忙腳亂。”才按下葫蘆又浮起瓢,住院問題剛達成一致,喪葬問題又出現分歧——父親此前一直與兄弟同住,但兄弟是個倒插門女婿,靈堂肯定不能設在兄弟家;而大哥家的房子又十分緊張,實在無法承接葬禮;唯有二哥家里尚有空房,可是二哥平日里與父親關系并不融洽,所以不愿騰房設靈。局面再度陷入僵持。又是大姐夫從中斡旋調和,才終于達成妥協——靈堂設在二哥家,大哥負責買黑漆,請匠人,置辦父親的大料。
就在大家緊鑼密鼓籌備后事之時,醫院突然傳來消息,父親奇跡般地醒了過來。父親病情好轉原本是件好事,然而對于兒女們而言,卻意味著“大家都白折騰了一場”——大哥抱怨辛苦漆好的大料派不上用場了;二哥二嫂因騰房問題而大吵一架;在外打工的大嫂、二姐和幺妹也在為是否退掉回家奔喪的車票而苦惱。用大姐的話講:“父親的不配合,將家里徹底搞亂了。”更糟糕的是,蘇醒后的父親變得神志不清,精神恍惚,很不識趣地叫嚷著:“我要活到一百歲,哪個敢叫老子不活到一百歲!”沒過多久,又再度陷入昏迷。醫生診斷父親的病將進入了一個“靜水期”。當“我”問及父親是否還有指望時,醫生只是微笑言道:“理論上,只要還有一口氣,就有希望。”意思就是說:“不至于絕望,但也看不到任何希望。”無奈之下,兄弟幾人只好再次召開緊急會議,商討下一步怎么辦。大哥默不作聲,只是埋頭抽煙。二哥開門見山:“看樣子父親就是不死也癱。丑話說在前頭,如果爸爸變成植物人了,反正我是不會接手的。”然后對著兄弟說:“你要是愿意管,我沒有意見,但是你考慮過你媳婦愿意在家里養著一個活死人嗎?”兄弟欲言又止,只能做出一副又氣又恨的模樣。“我”沉思半晌后,輕聲嘆道:“算了,還是送爸爸回去吧!”話一出口,似乎所有人都輕松了許多。辦完出院手續,“我”獨自一人坐在醫院大廳的長椅上黯然神傷,不知過了多久,大哥電話打來,說“爸爸老了”……
《倒影》以看似平淡如水、波瀾不驚的敘事筆觸,講述了兒女們在醫院陪護患病父親的經過,將一場世俗無比的相遇凝練到對生死、道德、人性的感慨與叩問,把故事講述得沉郁頓挫又讓人唏噓不已,到結尾時只感覺心中尚有千言萬語卻又不知從何說起。從總體敘述風格以及作品的現實指向性層面上講,羅偉章的《倒影》與電影《東京物語》確乎存在著某些同質異構意義上的家族相似性,然而,就敘事基調和情感溫度而言,《倒影》卻要比《東京物語》凜冽、凄涼得多。與《東京物語》自始至終溫情脈脈不同,《倒影》的質地更加堅硬,質感更為粗糲,更能凸顯出當下中國現實語境中的在地感和殘酷性。此外,在矛盾沖突的設置上,《倒影》也要比《東京物語》更加直接與強烈。在《東京物語》中,母親從病危到去世只不過幾天的時間,而《倒影》所要集中呈現的恰恰是老人病而未亡的時間段中子女們承受的“相同的悲痛”,以及各自面臨的“不同的難處”。從這個意義上講,《倒影》更像是在《東京物語》的空白處展開的假設與續寫。常言道,久病床前無孝子。小說中的人物,既是父親的子女們,同時也在生活中分別扮演著父親、母親、丈夫、妻子、領導、下屬等不同的角色。每一種角色都意味著一份沉甸甸的責任與義務。如何化解各種角色之間的沖突與矛盾,讓每個人都焦頭爛額、力不從心。面對“沒有絕望,也看不到希望”的父親,放棄治療似乎成為兒女們于心不忍卻又無可奈何的唯一的也是最好的選擇。畢竟“大家都要以自己的生活為重”,畢竟生活中“不如意的事太多”。或許,我們可以殘忍地進一步假設,如若沒有選擇放棄治療,接下來又將發生什么。癱瘓在床的父親勢必成為子女們生活當中的負擔與累贅,在無休止的贍養與陪護過程中,他們的孝心與耐心將被一點點地蠶食殆盡,父子之間、夫妻之間、兄弟之間、上下級之間的矛盾也會層出不窮、愈演愈烈。可以想見,時間長了,兒女們的矛頭遲早還是會指向“老而不死”的父親身上,于是電影《喜喪》便會成為這一假設的必然性結局——老人像瘟神一般,被子女們推來搡去,最終在羊圈中孤獨死去。這是每一個中國家庭都不想看到的,但又是無時無刻不在反復上演的現實悲劇。
當然,《倒影》并非僅僅是一出家庭倫理劇。作者羅偉章在講述家長里短、人情冷暖的同時,也在“醫院”這個特殊場域中思考、詮釋著另一個頗具形而上意味的沉重命題,即人在“異托邦世界”中發生的畸變與異化。“異托邦”(Heterotopias)是法國著名哲學家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在上世紀60年代所思考、介紹的一個重要命題。在福柯看來,異托邦與烏托邦既有著某種聯系,也存在著明顯的差異。烏托邦是一個沒有場所的想象空間,而異托邦則是現實生活中權力者和全體社會成員出于某種需要而建構出的一種異質性空間。它既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實體,也不是子虛烏有的幻象,而是一種混合了社會實踐與意識形態的“間性存在”。用福柯于1967年在建筑研究會上一個題為“另類空間”的講演中的話講,異托邦就如同一面鏡子:“正是從鏡子開始,我發現自己并不在我所在的地方,因為我在那邊看到了自己。從這個可以說由鏡子另一端的虛擬的空間深處投向我的目光開始,我回到了自己這里,開始把目光投向我自己,并在我身處的地方重新構成自己;鏡子像異托邦一樣發揮作用,因為當我照鏡子時,鏡子使我所占據的地方既絕對真實,同圍繞該地方的整個空間接觸,同時又絕對不真實,因為為了使自己被感覺到,它必須通過這個虛擬的、在那邊的空間點。”而醫院就是異托邦的典型代表,福柯將其與學校、兵營、監獄、精神病院、墓地等一同定義為“危機異托邦的異托邦形式”。人們把所謂正常社會里所不愿意看到的、需要重新整理、治療、訓練的因素、成員、分子放在這個特定的空間中。老人、病人作為一種危機、一種偏離,就需要放置到作為“危機異托邦”存在的醫院之中,因為“在我們這個社會中,閑暇是一種慣例,而游手好閑則意味著一種偏離。”
在《倒影》中,羅偉章通過“我”在陪護父親期間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將醫院的異托邦屬性展露無遺——醫院大廳電子顯示屏上滾動著的關于脾切除、胃切除、膽囊切除、子宮切除的血紅字幕,重癥監護室內以爺爺口吻訓斥爺爺的年輕小伙,沒病裝病滿世界找人扯閑篇拉家常的老婆婆,身患胰腺癌卻打扮成健康人模樣到處溜達的瘦高個兒,以及以診斷能力作為象征資本在患者家屬面前狂刷存在感的康醫生,還有那位恪守南丁格爾誓言對所有患者一視同仁的“機械天使”程護士……這些都令“我”莫名地產生一種幻覺,仿佛“一切如同在夢境中一般”。小說結尾處這樣描述:“辦完父親的出院手續,我心想是不是應該跟醫務人員道個別。正猶豫著,康醫生迎面走來,我還未及開口,他就一陣風從我身邊飄過,仿佛我們從未相識過一樣……而護士辦公室和各個病房都沒有程護士的影子,只是在走廊墻上的護士欄中貼著她的照片。湊過去看,并不是我熟悉的那個時刻面帶微笑的程護士,卻像個一本正經的中年婦人。”此刻,“我”才如夢初醒,若有所失地自言自語道:“這家醫院,一下子空了,與我再沒有任何關系了。”由此可見,醫院作為一種危機異托邦的存在形態,對人性與情感的型塑與規訓已經到了令人發指的程度。
此外,小說題目《倒影》也頗值得玩味一番。從情節上看,由于題目與內文并不構成直接對應聯系,且對于故事本身也未起到綜括性作用,讀者于是會很自然地聯想到題目可能具備的隱喻功能。在我看來,這種隱喻功能或許有二:一是便于傳遞作者內心深處那份融合著悵惘、悔恨、自責、迷失、無奈等多種情緒的復雜心境。小說在最后一句寫道:“大哥說‘爸爸老了’。——爸爸老了快滿十年了。”從中我們可以得知,作者是以追憶性的敘事視角來回顧那段在醫院中陪護父親的短暫而艱難時光。從這個意義上講,前面的整個故事都可以視為最后一句話的“倒影”。我們完全可以在腦海中構筑這樣一幅畫面:敘述者站在時間的湖畔,望著水中由記憶組成的倒影,兀自言道:假如上蒼再給一次機會,我是否有足夠的勇氣改變曾經的選擇?又是否有足夠的勇氣承受改變帶來的后果?這個哈姆雷特式的疑問不僅僅是“我”的捫心自問,也是向每一個讀者發出的追問。二是在于建構一個連接敘述者與讀者、個體與世界、虛構與真實的無聲傳感器。透過“倒影”,我們不僅能夠看到故事中各色人等的不幸遭際,同時也折射出社會大背景下每個現代人普遍面臨的生存危機與道德困境。由此,我不禁再次聯想到《東京物語》。導演小津安二郎在處理人物對話時,有意識地打破“第四面墻”,讓演員們刻意直視鏡頭說話,從而為觀眾營造一種“被注視”的錯覺。羅偉章將小說命名為《倒影》,亦能產生異曲同工的藝術效果。他借助“倒影”一詞,將讀者代入到文本故事之中,進而迫使讀者在“你若是‘我’,又當如何抉擇”這個噬心命題面前進退維谷,無言以對。從這個意義上看,《倒影》不啻為當代中國版的《東京物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