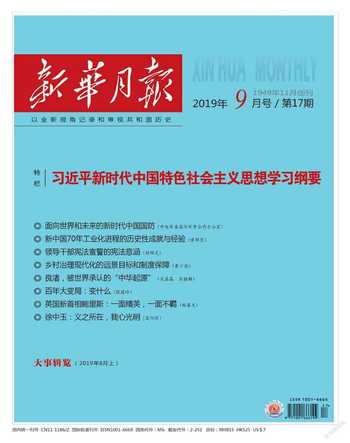百年大變局:變什么
張蘊嶺
最近,關于“百年大變局”的談話、文章、新聞報道突然多起來。我查了一下,中國領導人談這個話題是2017年12月28日,習近平在駐外使節工作會議上提出:“放眼世界,我們面對的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最近這個話題熱起來,可能與各界重視有關,也與世界大事頻出有關。
按國人的思維方式,“百年”不是一個嚴格的時間界定,而是指著眼于長遠看問題,比如,“百年大計”“百年樹人”“百年和好”,等等。百年大變局的核心是“變”,大變局則意味著是性質、結構、影響發生巨變。百年大變局既指世界,也指中國。就世界而言,變的是格局、秩序、體系;就中國而言,變的是實力、地位、影響力。
就百年的時間聚焦而言,研究者所持的視角多樣。我本人認為是指上個世紀與這個世紀的百年之間變化的比較,溫故知新,這個時間區間還包含新千年的轉變。有的則從更長遠的視角觀察,如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以來的400年之變,還有的主要著眼于新中國成立后的變化,等等。視角不同,分析的重點不同,得出的結論也不盡相同,但是,有一點是一致的,就是我們所處的時代正經歷歷史性的巨大變化,因此,分析和認識這些巨大變化時緊密聯系中國之變,具有重要的意義。
在諸多大變局中,世界力量大格局變化引人注目。在我看來,認識世界力量格局有三種方法:一是世界經濟大格局變化,由于經濟格局是其他力量格局的基礎,這方面的變化影響深遠;二是國家力量格局,特別是大國力量格局的變化,鑒于大國對地區和世界的格局與發展非同一般,這方面之變影響巨大;三是從思想文化視角觀察,思想文化的集中體現往往代表著文明的取向,這方面的變化影響深遠。
從世界經濟大格局的角度來分析,最大的變化是發達國家群體力量與發展中國家群體力量對比的巨大變化。自歐洲開啟工業化以后,世界力量重心逐步向西方轉移,西方國家率先進入工業化、現代化進程,成為發達國家群體,并且長期占據世界經濟格局中的主導地位。
如今,世界變了,發展中國家群體的力量有了大幅度提升,按經濟總量(GDP)計算,已是“半壁江山”,按購買力平價(PPP)計算,已經超過發達國家群體。這個變化大趨勢還在繼續,預計到本世紀中期,發展中國家群體經濟總量就會大大超過發達國家群體。
這是一個大格局的變化,而且隨著發展中國家群體力量的上升,他們在發展方式、利益訴求、制度體系,以及思想文化等諸多方面的影響力還將會大大提升。
當然,在當今和未來的世界,簡單地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完全分開并不科學,一則,各國都加入了一個共處的國際體系,經濟全球化把各國的發展緊密聯系在一起;二則,發展中國家群體也會發生結構變化,有的會成為發達國家。不過,從總體格局看,這樣的區分還是有意義的。盡管崛起的發展中國家群體作為利益相關者,會維護體系的基本穩定,但也會推動其調整、改革,讓體系與規則能更好地體現他們的利益訴求并成為可發揮作用的空間與平臺。鑒于此,調整與改革是一個共同參與的進程,不是非此即彼的零和游戲。當然,進程并非暢通無阻,定會有博弈,有沖突,甚至會有激烈的沖撞。
就發達國家群體而言,盡管在相當長時間里還會在資本、科技等方面保持優勢,但也面臨諸如人口規模縮減、“后老齡化”“鐵銹地帶”等諸多嚴峻問題的挑戰。在以往相當長的時間內,發達國家群體是世界經濟的中心,這包括經濟的增長、投資、科技和消費,但今后情況會大不一樣。
我們看到,在過去的一個時期,發展中國家群體已經成為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動力源。特別是中國,成為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主動力,對年度增量的貢獻甚至達到了1/3。盡管近年來中國經濟的增速放緩,但是由于總量大了,即便保持中速增長,其拉動力仍然很大。在中國之后,還有其他一些人口規模大、發展潛力強的國家,如印度、印尼等。從消費市場看,以往重心在發達國家群體,今后,由于發展中國家群體擁有巨大的人口規模,且“中產階級”的規模不斷擴大,世界消費市場的增長會越來越由其拉動。由于發展中國家群體作為世界消費市場的作用會不斷提升,由此,也會改變以往生產靠發展中國家、消費靠發達國家的不平衡格局。這種結構轉變必然會帶來一系列的大調整與大變革。
對于百年大變局,人們特別關注的是權勢(power)的變化,或者說是轉移。權勢,英文是power,蘊含的主要詞義是力量、影響力,用在個人表明強勢,用在國家意味著強大。
讓我們從個人的角度觀察權勢的轉移。權勢主要以財富為基礎,自從工業化以來,財富向個人集中的趨勢就越來越明顯。在新的大變局中,財富向個人集聚體現出新的特征:其一,快速向那些抓住新機遇的少數精英集聚;其二,在新興領域集聚的速度最快、規模最大;其三,集聚超越國家,在世界范圍進行。其結果,少數人擁有的財富數額越來越大,富可敵國,且在新興領域,如網絡、知識產權、大數據等方面擁有掌控地位,雇員達幾十萬,甚至數百萬之眾,分布在許多國家。
據統計,2018年,全球26位最富的人所擁有的財富為38億貧窮人的一倍,億萬富豪每天增加的財富多達25億美元。在美國,0.1%的富豪擁有美國25%的財富,1%的富豪擁有40%的財富,比如,亞馬遜老總貝索斯所擁有的財富高達1120億美元。就世界范圍而言,目前1%的人掌控了50%的財富,預計到2030年,這個比例會提升到65%。
值得注意的是,在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體,財富積累向個人集聚的速度最快。2018年,在全球新增的億萬富豪中,多數在新興經濟體,1/2在中國。不過,與傳統的財富集聚不同,其突出的特點是,絕大多數新富豪的財富增長并不是靠繼承,不是靠強奪,而是靠抓住新機遇,靠技術創新。比如,在中國新增的富豪中,97%靠白手起家,1/3靠創新,而且,就年齡結構來看,大多為年輕人。
財富向少數人傾斜,由國家向個人傾斜,在此情況下,會出現這樣的現象:一國財富總量的增加并不必然帶來公民財富的普遍增加,在富豪財富積累加速的情況下,很多人的財富卻會縮水,并可能會滑落到下層。另一方面,本來強勢的政府會因新技術,特別是網絡、大數據、智能化的快速發展而變得“失能”,對增量財富的再分配能力下降。技術積累比勞動積累更快,比爾·蓋茨早就提出,政府應該對機器人征稅,也有人提出應該對所有能帶來增值的“非人勞動者”征稅。
在此情況下,社會權勢的結構出現大的變化,一則,少數人對社會生活產生越來越大的導向力,對政治與政策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力;二則,作為社會穩定基石的所謂中產階級人群地位動搖,影響力下降;三則,被排擠到社會底層的人群走向“民粹主義”,極端勢力上升。而那些掌控巨額財富的富豪通過“國際化”的方式(免稅島、多國護照等),成為不受政府管理的“超級人”,他們運籌帷幄,進退有方。而普通民眾出于對現行社會政治的不滿,往往采取“非理性”的選擇,讓極具個性的“政治黑馬”上位,比如,從未有過從政經驗的商人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靠出演反腐人物的演員澤連斯基當選烏克蘭總統,等等。
新科技革命導致經濟運行方式、就業結構、生活方式等發生重大與快速的變化,越來越多的工作會被智能機器人替代。新的變局勢不可擋,盡管對其帶來的后果還有待進一步觀察,但有些已經初露端倪。比如,大數據成為經濟、社會的重要基礎構成,擁有者的權勢掌控力與影響力可以變得超乎尋常,由此推動經濟、政治、社會、思想、文化等的巨大變革。
如果僅順著這種思維去分析,未來的世界將是非常可怕的。新時代似乎需要有新的思維方式與認知。比如,有人認為,盡管未來財富趨于集中,但財富擁有的方式與含義發生巨大變化,財富大多是存在于股市、債市的“虛擬資產”,是數字化的“社會資本”,依托社會的支撐,在很大程度上說,是一種“個人財富的社會化”。如果失去社會支持,大量財富可能會“頃刻化為烏有”。傳統工業化創造的是集聚化的社會結構,而新變局創造的是離散化的社會結構,在此情況下,少數富豪并不能掌控多樣、離散與變換的“公民社會”。有人認為,新經濟創造的是一種“協作網絡”,依賴開放、創新、互動與分享。故此,新時代的財富集聚特性與以往有著巨大的差別。
盡管如此,新變局所帶來的挑戰仍是嚴峻的。比如,傳統的就業方式發生轉變,對大多數人而言,是如何不被新的發展所拋棄,如何能夠分享新發展的成果。對于政府而言,是如何建立適應新變局的政策與管理方式,如何找到解決財富積累兩極(財富擁有者和社會公眾)化問題的“兩全其美”的新政策。
談到百年大變局,總是要回答未來是什么,其實這個問題很難回答,或者說,現在很難說清楚。為此,我曾引述別人的一個說法,把未來稱之為“一個沒有答案的世界”,而正是因為沒有答案,人們都在尋求答案。
冷戰結束后,兩份答案曾引起爭論,一是福山的“歷史的終結”,二是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福山認為,鑒于蘇聯垮臺,世界會從此走向西方自由民主道路。此論斷也許對助長美國在世界各地賣力推行其所謂自由民主制度,甚至為此不惜發動戰爭起到了一定作用。世界實際的發展現實卻不支持這個答案,福山本人也認為,自己的論斷錯了。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根據是,冷戰結束了,意識形態不再重要,需要一種新的思維來理解世界政治,這就是未來引起沖突的是文化,即文明。他的這個說法好像至今還有市場。
就在前不久,美國國務院規劃司主任斯金納(Kiron Skinner)放言,美國與中國之爭“是一種完全不同文明和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斗爭”,這將是美國首次應對“一個非白人的強大競爭對手”。此言一出,立即引起了軒然大波,遭致廣泛的批評。斯金納是美國的高官,負責政策制定,她好像不是說著玩的,背后定有故事。正如《華盛頓郵報》刊文所指出的,美國可能正在策劃一場“文明沖突”。
其實,亨廷頓并非堅持必定會有文明沖突。在他后來寫的專著《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指出,文明的沖突是對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礎上的國際秩序才是防止世界大戰的最可靠保障。的確,把當今和未來的世界變局歸結為文明沖突,既不正確,也很危險。百年大變局,變的領域很多,諸如力量格局、國際秩序格局、發展范式、氣候變化、社會文化等。這些是大局之變,還有中局、小局之變。這么復雜的變化,怎能用文明沖突而概之呢!
就力量(power)變局而言,結構也很復雜。比如,既包括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力量對比之變,又有大國力量對比之變。總的趨勢是,發展中國家力量大幅度上升,會超過發達國家,美國霸權衰落,非西方大國上位。據預測,按經濟總量衡量,到本世紀中期,前三位綜合實力大國是中國、美國和印度。沒有不變的格局,力量對比變化是一個大趨勢。面對變局,理性的選擇是適應性應對,而不是對抗。在當代,后起者爭霸,或守成者守霸,都可能難以如愿,而斗起來更是兩敗俱傷。
在力量變局中,還有“第三者”的因素不能忽視,即越來越有影響的“非國家力量行為體”,如大公司集團,它們都是“富可敵國”,其業務、財富和人員遍布世界;跨國商業網絡,它們超越國界,甚至運行于云空間;非政府組織,它們擁有雄厚的資金支持和龐大的聯系網絡;還有極具影響力和破壞力的極端恐怖組織網絡集團,等等。在許多情況下,它們的影響力和作用甚至超過單個國家,包括大國。它們有著不同的行為方式,比如大公司集團,往往通過市場行為導向影響政策,或者通過利益關系影響政府決策;跨國商業網絡,可以通過其“內部系統”形成巨大的影響力,甚至推出“準規則”;非政府組織,可以通過有影響力的游說或者社會輿論,生成巨大的影響力;還有極端勢力集團,利用網絡進行聯絡,進行恐怖活動,等等。這種“非傳統國際格局”體現為復雜的非傳統特征,其作用甚至很難透察。特別是在全球化、網絡化的時代,它們的隱形存在與非常規活動常常難以應對。
總之,大變局下的世界,可能將是一種多中心、多力量、多角色的復雜格局。由此,文化,或者說是文明,也會是多樣性并存與相互影響的。特別值得指出的是,文明有其自身的內涵基礎和生存方式。比如,盡管近代西方實力占上風,對國際關系和國際秩序起到了導向的作用,西方文明也因此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傳播與擴張,但是,西方文明并未獲得獨霸地位,并沒能消滅,或者替代其他文明的存在與發展。
今年5月份,中國組織召開了亞洲文明對話會議,亞洲全部47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的1300多名代表與會,會議的主調是文明的交流互鑒,強調的是文明多元、多向格局下的相互尊重。中國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之前還提出過構建和諧世界,二者的旨意是一致和清晰的,就是要推動不同文明的兼收并蓄,反對文明對立和沖突。
百年大變局,一個理想的未來,可能不再是霸權主導的世界,不再是單方力量主導的世界,不再有文明的沖突……也許,在經歷過無數災難后,人類有了新的文明覺醒。然而,回到現實,那個理想的世界似乎仍很遙遠。
(綜合《世界知識》2019年第8、10、12期。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山東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