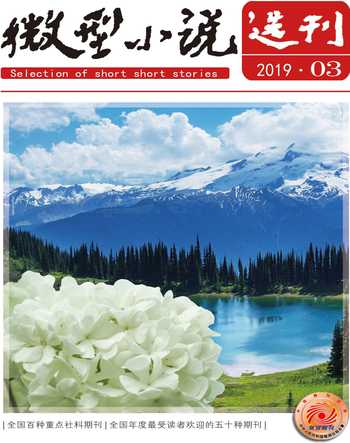槐花淡淡香
劉建超
我走在回家的路上,母親來電話說,她做了槐花包子,回來吃。
我出生在山區的一個偏僻的小村莊,家境不富裕。我小時候記憶最深的就是總覺得肚子不飽。我們村子小,沒有學校,上學要到五里外的一個大村子學校。每天早上去學校,母親都會在我的書包里放兩個黃面窩窩,一小塊自家腌制的咸蘿卜。中午下課,在班主任的屋里倒一杯白開水,就著咸菜吃掉黃面窩窩,打著飽嗝還是覺得肚子不飽,應該是缺少油腥的緣故吧。
我家的前院,有兩棵木桶般粗的槐樹,四月的季節里槐樹長滿了綠葉,在輕輕的春風里,靜悄悄地結出一串串潔白如雪玲瓏剔透的槐花。那一簇簇一簇簇雪白雪白的花朵綻放在枝頭,把枝頭壓得微微下垂,隨風搖曳,滿院都是槐花淡淡的清香。槐花盛開的季節,是我最快樂的日子,餓了,渴了,捋一把槐花塞進嘴里,清爽香甜口舌生津。我走到哪里都把兜兜里裝滿槐花,自己吃分給小伙伴們吃。
母親手巧,能把槐花做出許多種吃法。她把剛摘下新鮮的槐花,用井水淘洗干凈,控干水分,把槐花撒上鹽,加入黃面雪攪拌,放在大鍋的篦子上蒸。剛出鍋的蒸槐花,淋上幾滴香油,蘸著蒜汁,每次我都把肚子撐得圓圓的。我最喜歡吃的還是母親做的槐花包子。把槐花在開水中焯一下,放在簸籮里晾干。家里來客人了,母親把封在缸里的槐花取出一些,用熱水泡開,拌進蔥姜末,澆點芝麻油,剁一把封在大油里的油渣,蒸出的包子那個香啊,直撓你的心窩子。
我去鎮里讀中學,每到學校有活動,要帶飯,母親就會給我包槐花包子。雖然槐花包子在我家就是最好的飯食,可是在鎮里的同學中真不算什么美食。看著同學們吃著面包蛋糕肉炒飯,我總是有點自卑,吃飯一個人躲在安靜的地方。母親知道了我的想法,對我說,娃啊,不管吃的是啥,只要吃飽肚子,只要是咱自己勞動掙的,吃啥都不丟人。班里的馬蘭蘭家在鎮上,看到我一個人吃飯,就端著鋁飯盒說,偷偷吃什么好東西啊,我都聞到香味了。我說,我媽包的槐花包子,貧民百姓家哪有啥好吃的。她故作驚喜地說,我就愛吃槐花包包了,我用兩個餅餅換你一個包包。她不由分說,把兩個肉火燒塞在我手里,拿走了我的一個菜包子,咬一口,說,真香。一直到高中畢業,只要有活動,馬蘭蘭就會用她帶的好吃的換我一個槐花包子。我把事情和母親說了,母親慈祥地笑著說,那是女孩心疼你,你得念人家的好。
我真的得念人家馬蘭蘭的好。我考上中國政法大學,馬蘭蘭沒有考上大學,她父親給她安排進了電業局。馬蘭蘭用她的第一月工資,給我買了一大堆書寄到了學校。我告訴她,學校圖書館書很多。她說,學校的書得還,看了還得做筆記,需要什么書,我寄給你。她說,你不要有什么負擔,你是鎮中唯一一個考到北京的大學生,你是鎮里的驕傲。大學畢業后,我回到了老街。馬蘭蘭召集高中同學聚會,馬蘭蘭已經從單位辭職,直接拉起了一個公司,經營得風生水起。
幾年后,我得到提拔。那天,我把父母接到老街一家酒店,點了一桌酒菜。我清楚地記得母親看到一桌子酒菜吃驚的表情,母親說,老天啊,這得花多少錢?我寬慰母親說,媽,您隨便吃,這桌菜不花咱的錢,我簽個單,公家報。
吃公家的錢?我看到母親拿筷子的手都在顫抖,筷子始終都沒有伸向一只盤子。父親掏出身上帶的所有錢,塞到我手里。
母親說,娃啊,不管吃的是啥,只要吃飽肚子,只要是咱自己勞動掙的,吃啥都不丟人。你這頓飯,爸媽吃不下去啊。
父親打開帶來的包袱,說,你媽臨來還專門蒸了槐花包子,說娃愛吃。
我的淚水忍不住就留下來,我抓起一只槐花包子,大口地嚼著,說,媽,娃愛吃,娃愛吃。娃錯了,娃再也不做錯事了。
馬蘭蘭找到我,說要投標一個項目。公司近幾年經營困難,這個標的對公司非常重要,希望利用我的影響給各個方面打打招呼,還將厚厚的活動經費拍到我桌子上。
我什么都沒說,只是靜靜地給她講了我請母親進城吃飯的往事。馬蘭蘭哭了,默默地收起錢走了。
我走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了大門口站立著的母親,一頭白發如盛開的槐花,我聞到了槐花淡淡的香甜。
母親讓我回家吃槐花包子,我剛剛當選了市紀委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