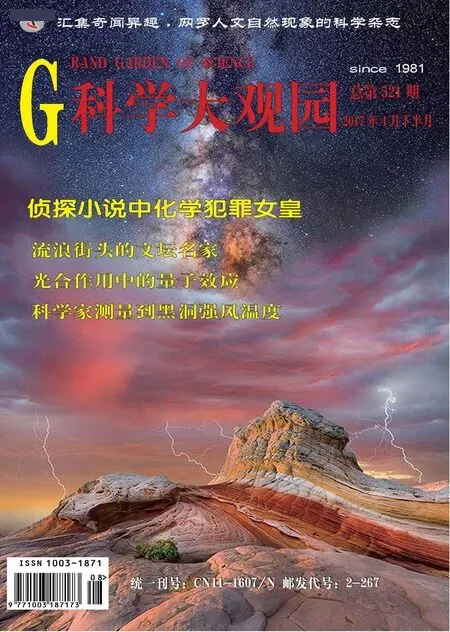女性裸露
出現女性裸露鏡頭,就是“迎合直男”嗎?近期走紅的網飛(Netflix)系列動畫短片《愛,死亡和機器人》 (網友昵稱“愛死機”),正在因這個問題而引發爭論。
許多人認為“女性主義”是“愛死機”的亮點,但這也成為它引發爭議的地方。片中有多處女性角色裸露身體的場景,有網友認為這是“消費女性身體”、“迎合直男”;國外也有影評人指出“愛死機”帶有性別歧視的色彩。反對派則認為,將女性身體裸露等同于羞恥,是把所有女性看為潛在的性對象,這才是對于女性的真正歧視。
這種對于身體裸露與女性主義的爭論并不新鮮。比如2017年,著名影星艾瑪·沃森(Emma Watson)的性感寫真就引發了不小的爭議,批評者認為拍攝裸露乳房的照片與她“女性主義者”的身份不符;也有許多人為沃森辯護,稱這些批評的聲音顯示了平權之路道阻且長。
自第二波女性主義興起,身體開始成為焦點后,各種觀點在此交織碰撞;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關于女性身體的爭議未見平息之勢,女性的身體,仍然是戰場。女性的“裸體呈現”,在觀念上發生了怎樣的變遷?當女性用裸露來爭取權益,這些“壞女孩兒”該如何應對“裸體羞恥者”發出的“淺薄女性主義”質疑?
看與被看和視覺快感
觀看女性身體的視覺習慣,是被塑造的。
1975年,英國女性主義電影理論家勞拉·穆爾維(Laura Mulvey)發表雜文《視覺快感與敘事電影》(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這篇文章使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提出經典好萊塢電影的“窺淫癖”(scopophilia),即在電影中,女性角色是一種“奇觀”,接受攝像機后面的人、電影中的男性角色和觀眾的共同凝視;而這種凝視,是異性戀的、男性化的目光。自此,“男性凝視”(Male Gaze)作為一個完整的概念,被女性主義媒介分析沿用至今。
在好萊塢電影典型的敘事方式中,“男性凝視”投射到了風格化的女性身體上,女性的身體被編碼為強烈的視覺與色情符號,女性的在場只為滿足“男性凝視”,男性通過這種“窺淫癖”滿足性欲,獲得視覺快感。比如希區柯克的電影《迷魂記》(Vertigo),女主角瑪倫的身體呈現,就能看到“男性凝視”的影子。
電影男主角斯考蒂·費古森警官,因于高處失足受傷辭職,當上了私家偵探。他接受了一位朋友的委托跟蹤朋友的妻子瑪倫,在這一過程中,斯考蒂對她產生了深深的迷戀;殊不知,斯考蒂已經落入了陰謀之中——瑪倫已被朋友謀殺,男主角愛上的是假扮者朱蒂,朋友想利用他為自己制造不在場證明。
《迷魂記》絕大多數敘事,都是通過男主角斯考蒂的視角展開的,展示女主角的鏡頭就是斯考蒂的眼睛,他看到什么,觀眾就看到什么;而“跟蹤”這一情節,將“窺淫”合法化,“瑪倫”時刻處于斯考蒂的觀賞之中;特別地,“瑪倫”還經常處于門框、車窗、陰影之中,她被塑造成一件藝術品,而不是具有主體性的人;而對于朱蒂,斯考蒂將她作為“瑪倫”的替代品,要求她打扮成“瑪倫”的樣子,是赤裸的“戀物”。正如穆爾維說:“希區柯克的電影時常以‘窺淫癖’和‘戀物癖’(fetishism)為主題,并在兩者之間搖擺。”
“男性凝視”作為女性主義媒介分析的奠基理論,被廣泛應用于影視作品、廣告、藝術品等各種媒介的批評之中,盡管穆爾維的理論具有一定時代局限性,但在今天,我們仍然可以在看電影、看劇、看廣告時發現,男性凝視的目光無處不在。
藝術,挑戰“男性凝視”
其實,在穆爾維正式提出“男性凝視”之前,這種女性主義的分析思路已經被一些研究應用。約翰·伯格(John Berger)在《觀看之道》(Ways of Seeing)中通過分析歐洲裸像藝術中的女性形象,提出女性是一種被觀看的景觀,女性通過男性的目光來關注自己:“男人渴望女人,女人希望自己被人渴望,男人注視女人,女人注意自己被別人觀察。”這一論斷深刻地揭示了性別權力之間的不平等。
藝術史家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曾提出,裸體(nakedness)只是脫光衣服,裸像(nude)則是一種藝術形式。克拉克認為,藝術裸像不存在男性性欲。
但是,伯格的觀點與克拉克正好相反。“成為裸像則是要讓人觀看自己裸露的身體,并非自主。裸露的身體要成為裸像,必先被當成一件觀看的對象。”也就是說,裸像并不具有主體性,女性的裸像依據男性的觀看方式塑造,她的裸露并非自我情感的呈現,而是為了被觀看。比如,歐洲古典主義繪畫中的女性從沒有體毛,因為體毛是性欲、精力和激情的象征,在男權社會中,這是男性自我期待的特質,并不屬于女性。伯格因此提出,裸體,才是恢復自我之道。
時間進入60年代,西方第二波女性主義浪潮興起,藝術界自然不會缺席,女藝術家們意圖顛覆男性主導的權力關系,女性主義藝術應運而生。60—80年代是當代藝術的迸發期,也是女性主義藝術的輝煌年代,很多女性藝術家通過對于身體裸露的顛覆性創作,挑戰男性凝視,表達對于男性權力壓迫的反抗。
美國藝術家漢娜·維爾克(Hannah Wilke)以自己的身體作為材料,在1974 年到1982年期間進行了一系列創作,完成了《急救——傷疤系列》(S.O.S. —Starification Object Series)。在這一系列的作品中,維爾克上身裸露,擺出各種姿勢,她的身體上粘有女性生殖器模樣的口香糖,暗示了女性的愉悅;但它遠看又像是一個小小的傷疤,暗示了女性的痛苦。
另一位知名度極高的女性主義藝術的代表人物朱迪·芝加哥(Judy Chicago),在80年代初發起了一項名為“生育計劃”(Birth Project)的藝術項目。芝加哥之所以發起這個項目,是因為她發現在漫長的藝術史上,關于婦女生育的圖像少之又少。在男性凝視之下,生育的女性往往缺乏性吸引力,但生育是許多女性生命中的重要體驗。在這幅名為《大地誕生》(Earth Birth)的作品中,柔和的藍色曲線勾勒了一個全裸的分娩婦女的身體,她的乳房和子宮都散發著金色的光芒。
繪畫、雕塑、行為藝術、自拍……通過女藝術家們的不斷努力,越來越多的女性主義藝術進入了公共空間。在一定程度上,女性主義藝術都是以女性身體或藝術家自己的身體作為創作原型,從男性凝視下的被觀看轉變為自我的主動觀看,從而建構女性的主體意識。這些在一些人眼中可能“驚世駭俗”的作品,代表的是女性從心底發出的吶喊。
“壞女孩”走上街頭
在《裸體政治:裸體,政治行為和身體修辭》(Naked Politics:Nudity, Political Action, and the Rhetoric of the Body)一書中,作者Brett Lunceford考察了身體裸露與政治性運動的關系。從女性主義者通過裸體游行反抗性別暴力、環保主義者進行裸騎抗議石油依賴,再到女大學生們用裸露上身的照片支持總統候選人,這些訴求并沒有相似之處,但是行動者們共同認定,脫去衣服、裸露身體,可以獲得更好的結果。Lunceford提出,身體裸露已經成為一種政治話語與修辭,即使聲音消匿,身體也仍在發聲。
2008年,三個年輕的女孩在烏克蘭成立了當代最知名的激進女性主義組織Femen。Femen在拉丁語中就是大腿的意思。她們吸引了許多志同道合的女孩,走上街頭,反對烏克蘭泛濫的賣淫產業、反對宗教制度、反對獨裁、支持同性戀……裸露的胸部是她們的標簽,也是她們的武器。對于Femen來說,暴露胸部曾是引起關注的手段和策略,后來則成為她們的自我表達——女性應當自主決定將身體作為欲望的對象,或者抗議的工具。
一位Femen組織的成員在接受采訪時說:所有男女平等和女性權利的議題都和身體有關,比如墮胎、醫學輔助生育、穆斯林頭巾和賣淫等。
“身體是輿論場和戰場,因此,女性主義運動應該重回身體……我們重新成為自己身體的主人。”
與Femen行動相似的,還有在2011年發源于加拿大的“蕩婦游行”(SlutWalk)。當年,一位多倫多警官建議“女性應當避免穿得像蕩婦一樣”,從而預防性侵犯。這一言論激起女性主義的憤怒,從多倫多開始,“蕩婦游行”在許多國家和地區展開,在一些城市還成為固定的年度活動。
參加“蕩婦游行”的女性穿著暴露的服飾,超短裙、露胸裝、吊帶襪……身體的裸露帶有一種破壞性的力量:絕不向男性挑逗的目光妥協。同時,在許多現場集會與互聯網上,許多強奸受害者勇敢地站出來,談論她們的經歷和感受。這種“我可以騷,你不能擾”的話語,也被中國公眾所熟悉。
2012年,上海地鐵一官方微博發出一張穿著透視裝女性的背影,配文“穿成這樣,不被騷擾才怪。姑娘,請自重啊”。一時間,社交媒體上爭議不斷,有人在上海地鐵中發起了一場“我可以騷,你不能擾”的行為藝術,并受到了許多聲援。
激進的Femen幾乎關心所有具有爭議的性別議題,她們的行為也注定會受到公眾的非議和當局的壓制;“蕩婦游行”的價值觀和執行方法一直具有爭議,批評的聲音從未停止;如果在今天搜索“我可以騷,你不能擾”,討論仍然沒有停止,反對的聲音也從未間斷。
當“壞女孩”( Rebellious girls)走上街頭,當她們掀起自己的上衣,在吸引關注之余,裸露的身體究竟意味著什么?如果帶著玩味和滿足的男性目光從未離開她們裸露的胸部和大腿,她們的行為又該如何評價?當反對的聲音稱她們為“淺薄的女性主義”時,“壞女孩”又該如何應對?

以上問題可能永遠沒有答案,因為關于女性裸露身體的爭議,注定不會停止。
永恒的身體戰場
在當代的流行文化中,女性裸露的身體和性感的外表,似乎又與文化產業與資本產生了糾纏。當麥當娜在舞臺上做盡挑逗之熱舞,當卡戴珊的性感照片一次又一次出現在雜志封面,80年代末期女性主義者們對于色情作品的辯論似乎早已沒有了意義。裸露身體的政治意義被當代商業文化消解,“男性凝視”成為“資本凝視”,資本壓迫在女性身體的重構之上。關于性別的戰爭永遠都會出現新的矛盾,女性的身體,是永恒的戰場。
然而,可以確定的是,女性的身體不應當與男性的欲望相聯系,女性的身體屬于自己,而不是男性潛在的性對象。也許“男性凝視”永遠無法消除,但在女性身體的重構之中,女性的主體性是確定且唯一的標準,女性可以賦予自己裸露的身體無限多的意義,這些意義,與羞恥無關。
一個真正的女性主義者(無論男女),應該是什么模樣?這個問題可以有千萬種回答,但是,真正的女性主義者,不應該給女性設限,無論是裸露身體,還是其他。正如《女性主義者不穿粉色衣服(以及其他謊言)》[Feminists Don’t Wear Pink (and other lies)]所說:“穿粉色衣服、超短裙、刮腿毛、喜歡男孩,都不妨礙我成為一個女性主義者。”
回到文章的開頭,對于《愛,死亡和機器人》中女性角色身體裸露的擔憂,似乎并沒有必要。如果將身體裸露等同于迎合直男,這不正是以“男性凝視”的目光去審視女性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