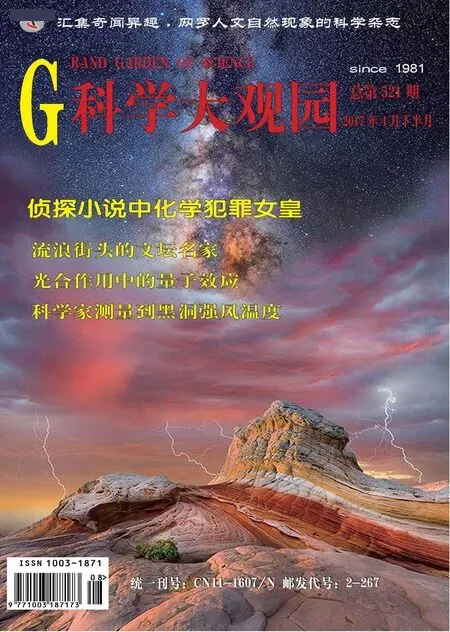比爾·蓋茨
在世界的每個地方,人們都比過去更長壽。一個人到80多歲還能活得很好已不再是稀罕事。人類的壽命比以前更長,這應該是一件開心事才對。但如果長壽不能使人開心,那會發生什么?
你活的時間越長,就越可能出現慢性病的情況。你罹患關節炎、帕金森病或其他降低你生活質量的非傳染性疾病的風險逐年遞增。不過在所有威脅到我們晚年生活的疾病中,有一種對社會的危害尤為嚴重,那就是阿爾茨海默癥。
你如果活到80多歲,就會有接近50%的可能性得這種病。在美國,阿爾茨海默癥是十大死亡原因之一,卻是其中唯一沒有有效治療手段的死因,每年的發病率都在增加。隨著美國在“嬰兒潮”時期出生的一代人步入老年,這種趨勢將會繼續擴大。這意味著有更多的家庭將眼睜睜地看著他們親人的認知能力減退,然后慢慢地消失。盡管疾病負擔越來越重,科學家們還是沒能弄清到底是什么原因導致了阿爾茨海默癥,以及如何才能阻止這種疾病破壞大腦。
我最初對阿爾茨海默癥產生興趣是由于它對家庭和醫療系統造成的負擔——既是情感上的負擔,又是經濟上的負擔。這種病的經濟負擔更容易量化。比起沒有神經退行性疾病的老年人,患阿爾茨海默癥或其他形式癡呆癥的病人,每年在自費醫療項目上要多花5倍的錢。與許多患慢性病的人不同,阿爾茨海默癥患者既要支付長期護理的費用,又要負擔直接的醫療開支。如果你在六七十歲得了這種病,你在接下來幾十年里可能需要昂貴的護理。

這些開支是發達國家增長最快的醫療負擔之一。根據阿爾茨海默癥協會提供的數據,美國人在2017年將花費2590億美元看護那些患阿爾茨海默癥及其他癡呆癥的病人。如果沒有重大突破,在未來幾年甚至幾十年里,這些支出還將繼續擠壓財政預算。這些問題是世界各國政府都需要考慮的,包括那些中低收入國家——那里的國民預期壽命也在接近全球平均水平,患癡呆癥的人數正不斷增加。
想要把阿爾茨海默癥造成的人力成本轉化為數字,這實在是難上加難。這是一種可怕的疾病,它摧毀的不僅是得病的人,而且包括所有愛他們的人。我對此深有感觸,因為我的家族中就有人得過阿爾茨海默癥。眼睜睜地看著你愛的人掙扎著被這種病奪走心智你卻對此無能為力,我知道那有多痛苦,感覺像是在經歷你曾經認識的那個人一點點死去的過程。
家庭背景并不是我對阿爾茨海默癥產生興趣的唯一原因。但個人經歷確實讓我明白,當你或你愛的人患上這種疾病時有多絕望。我們已經看到科學創新的力量,它把像艾滋病毒這樣曾經不可一世的殺手,轉變成為可以通過服藥被控制住的慢性疾病。我相信我們對阿爾茨海默癥也能做到這一點(或者做得更好)。
過去一年,我花了大量時間研究這種疾病和迄今為止取得的進展。在這個領域里,人們正在開展許多了不起的工作,目的是推遲阿爾茨海默癥的發病時間和減少它對認知能力的影響。從研究人員、學者、投資人和業內專家等各方聽到的信息使我信心滿滿,只要可以在5個領域取得進展,我們基本上就能改變阿爾茨海默癥的發展方向。
我們需要更深入地了解阿爾茨海默癥是如何發生的。大腦是一個復雜的器官,由于病人在世的時候很難對大腦進行研究,我們對它如何隨著年齡老化,以及阿爾茨海默癥如何破壞了這個過程知之甚少。我們對大腦狀況的認識大部分來自尸體解剖,所以只能看到阿爾茨海默癥末期的表現,而無法解開其長久以來的謎團。例如,我們無法完全理解為什么非洲裔美國人或拉丁美洲人要比白人更容易患阿爾茨海默癥。如果想要取得進展,我們就需要更好地了解這種病的深層次原因和生物學原理。
我們需要更早地檢查及診斷阿爾茨海默癥。由于最終確診阿爾茨海默癥的唯一方法是通過死亡后的尸檢,我們很難在病程早期就準確地識別出這種疾病。雖然有認知測試這種方法,但結果往往變動很大。如果你前一晚沒睡好,這可能會影響你的結果。如果有一種像驗血一樣更加可靠、價格可負擔和容易獲得的診斷方法,我們就能更容易地了解阿爾茨海默癥的進展和追蹤新藥物起作用的方式。
我們需要更多對抗疾病的方法。一種阿爾茨海默癥藥物可能通過不同的方式預防疾病或減緩疾病發展。截至目前,大部分的藥物試驗都瞄準了β-淀粉樣蛋白和Tau蛋白,這是兩種造成大腦斑塊和纏結的蛋白。我希望這些方法能夠成功,但萬一它們不成功,我們需要為科學家們提供些不一樣的、不那么主流的想法。一個更加多樣化的新藥產品線將有助于提高發現突破性解決方案的機會。
我們需要讓人們更容易地參與臨床試驗。創新的步伐有多快,部分取決于我們能多快地進行臨床試驗。由于我們對阿爾茨海默癥了解不多,也沒有一種可靠的診斷方法,很難找到處于病程早期且愿意參與臨床試驗的合適人選。招募到足夠的患者可能需要數年的時間。如果可以找到一種方法來預先選定參與者并創建有效的注冊體系,我們就可以更快地開展新的試驗。
我們需要更好地利用數據。每當制藥公司或實驗室進行一項研究時,他們都會收集大量信息。我們應該用一種通用的格式來編譯這些數據,以便更好地了解阿爾茨海默癥如何發病、發病情況怎樣受性別和年齡影響,以及遺傳基因如何對患病幾率造成影響。這將使研究人員更容易尋找模式和發現治療的新途徑。

如果我們在以上這些領域都能取得進步,我想我們就能開發出一種干預措施,從而極大地減小阿爾茨海默癥的影響。我們有理由對前景保持樂觀:我們對大腦和阿爾茨海默癥的了解正在突飛猛進地發展。我們已經取得了一些成果,但還需要做得更多。我想要支持有才華的人從事這項工作。作為第一步,我向癡呆癥發現基金(Dementia Discovery Fund)投資了5000萬美元,這是一個致力于增加臨床藥物種類和發現治療新目標的私募基金。大型制藥公司中的大多數還在繼續尋求β-淀粉樣蛋白和Tau蛋白治療方法。癡呆癥發現基金是制藥公司的有益補充,它支持一些初創公司去探索不那么主流的方法治療癡呆癥。我所做的這筆投資是以個人的名義,而不是通過基金會。要想實現阿爾茨海默癥首次被成功治愈,這或許要等1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而且最開始的治療也一定會非常昂貴。等到那天來臨的時候,我們的基金會可能會考慮如何把它推廣到貧困國家。
不過在開始考慮各種做法之前,我們還是需要先實現許多科學突破。所有正在研發過程中的新工具和新理論都讓我相信,我們正處在一個阿爾茨海默癥研發事業的轉折點。現在正是加快進步的時候,從而避免讓阿爾茨海默癥造成的巨大損失沖擊到那些無法負擔高昂醫藥費的國家。在那些國家,阿爾茨海默癥流行對財政預算的影響,足以導致整個醫療系統破產。
這是一個可以大幅提高人類生存質量的前沿領域。人類壽命越來越長是一個奇跡,但只有更長的預期壽命是不夠的。人們應該享受自己的晚年生活,為了實現這一點我們要在阿爾茨海默癥方面取得突破。我很激動能加入對抗這一疾病的戰斗,同時迫不及待地想要看看接下來會發生什么。
如果不能用一種簡單的方法來診斷阿爾茨海默癥,我們該如何消滅它?這真的是一個雞和蛋的問題。找到阿爾茨海默癥的治療方法需要大量新藥的臨床試驗,但如果不能在發病初期發現這些患者,從而測試治療方法是否能發揮作用,就很難招募到合適的試驗參與者。
目前,診斷這種疾病的最佳方法是脊椎穿刺或腦部掃描。問題在于前者具有侵入性,后者價格昂貴。許多病人在開始出現認知能力下降的跡象之后才進行這些測試,而此時病情可能已經相當嚴重了。找到一個可靠、價格可負擔和好用的診斷方法對于消滅阿爾茨海默癥的重要性,再怎么強調都不為過。
好消息是,多虧過去幾年里取得的重大突破,這個目標終于變得觸手可及。科學家們正在推進新的診斷方法:從簡單的血液測試到語音分析,這些方法就好像科幻小說里寫的一樣。我們已經接近攻克雞和蛋問題的臨界點了。
這就是我投資診斷法加速器的原因——我去年夏天宣布與阿爾茨海默癥藥物發現基金會(ADDF)一起投資了這個新的基金,旨在加快現有的研究進展。
就在不久前,我們還沒有除了認知評估之外的阿爾茨海默癥診斷方法。第一次突破出現在20世紀90年代末和21世紀初,那時大腦成像——如PET(正電子發射斷層掃描技術)和MRI(磁共振造影)——使我們能夠看到患者大腦的生物學變化。
隨后在2006年出現了脊椎穿刺。一個由瑞典科學家奧斯卡·漢森(Oskar Hansson)、亨里克·塞特伯格(Henrik Zetterberg)和卡伊·布蘭納(Kaj Blennow)組成的團隊,證明了觀察腦脊髓液(在大腦和脊髓中發現的液體)可以預測哪些人會患上阿爾茨海默癥。他們的發現為研究人員提供了一個可使用的工具,利用這個工具,他們能夠更明智地決定應該找哪些人參加臨床試驗。不過這個辦法并不完美,問問那些做過脊椎穿刺的人是否愿意再經歷一次這個過程就知道了。
理想的阿爾茨海默癥診斷方法得是便宜和易于操作的。它不僅能告訴我們是否患上了阿爾茨海默癥,還能告訴患者病情的嚴重程度。最重要的是,理想的診斷方法應該像在年度體檢中接受的其他常規檢查一樣簡單且無痛。
換句話說,血液檢測會是一種理想的診斷方法。就在兩年前,科學家們對于是否存在簡單的阿爾茨海默癥血液檢測還存有疑慮。研究人員們已經尋找了很長一段時間,但每次新的實驗室檢測顯示出一些希望,下一個嘗試它的科學家卻會實驗出與之相異的結果。
蘭迪·貝特曼(Randy Bateman)是圣路易斯華盛頓大學的教授和研究員。作為最早的發現者之一,他的團隊識別出阿爾茨海默癥患者的血液在眾多測試中存在具有一致性的變化。自從2017年夏天他公布研究以來,其他研究人員也發表了類似的發現,還有很多人在努力完善這個診斷方法(包括發明脊椎穿刺檢測的瑞典團隊)。
在接下來的一兩年內,血液檢測很有可能被用于招募患者進行阿爾茨海默癥的藥物試驗。這令人非常興奮,因為這意味著實驗室將能更快地招募到更多病人,同時科學家將能在更短的時間內弄清楚某種藥物是否有效。這也意味著將來有一天,你能很容易地在醫生的例行檢查中進行這種檢測。
但如果我們能夠找到一種侵入性更小的方法來診斷阿爾茨海默癥呢?我最近遇到了一位名叫羅達·奧(Rhoda Au)的研究人員,如果她的研究被證明是成功的,也許有一天,我們可以簡單地通過聽聲音或者觀察如何用筆寫字來預測你是否會得這種病。
奧博士負責弗雷明漢心臟研究中的神經心理學研究,該研究已經持續70多年追蹤一個城鎮中居民的健康狀況。一些參與者最近已經患上了阿爾茨海默癥——并且奧博士有這些病人這段時間參與健康評估的數千份音頻文件的使用權限。
當你說話的時候,有很多事情在發生。把詞串在一起組成句子的整個編譯過程很復雜。如果能用電腦分析一個阿爾茨海默癥患者多年來是如何說話的,你也許能發現一些細微的變化,然后在還未顯現阿爾茲海默癥癥狀的更年輕的病人身上尋找相同的言語模式。如果你能足夠早地發現這些變化,你甚至也許能從一開始就防止人們患上阿爾茨海默癥。
我們還不知道語音分析是否有效,這還處于研究的早期階段,我們甚至還不知道應尋找什么樣的言語模式變化。但我對未來充滿期待,到那個時候,判斷人們阿爾茨海默癥患病風險的大小有可能就像使用手機應用一樣簡單,你可以讓應用提醒你講話中出現的危險信號。
對于診斷方式來說,如今是一個充滿奇跡的時代。隨著技術越來越先進和精確,科學家們在診斷疾病方面正在取得驚人的進展。對阿爾茨海默癥的研究已經受益于這種更深入的了解,我也期待在未來看到其他革命式診斷方法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