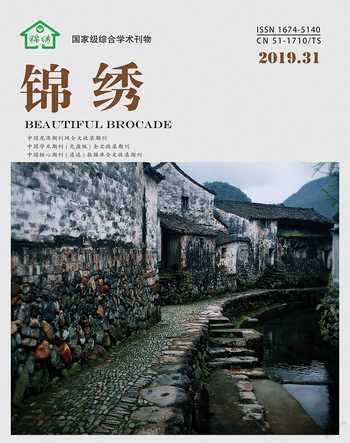遠方的燈塔
蔣宇恒
蕩一葉輕舟,從豆蔻年華駛向半老徐娘,從青蔥韶華航向耄耋遲暮,生命的海洋百舸競發,輾轉奔流。與擺渡的人相伴的,或是躊躇滿志,亦或是迷茫懵懂,每個人都需要光芒,光為迷茫的船只指引方向,為彳亍的游子帶來慰籍。燈塔,它就那樣佇立在遠方,離得愈近,光也越明亮,生活也會開闊明朗。那看似遙不可及的遠方,卻也恰恰觸手可及。
因為——燈塔,就是“我”,是我們自己。遠方的燈塔,也就是“遠方的我”,是我們每個人所追求的,理想中的自己。
“遠方的我”宛如燈塔,是多少人歆慕的翹楚,多少人魂牽夢縈了多少歲月韶華。同時,與之相對立的“近處的我”也是生活中客觀的存在,有如一座斑駁的古塔,攀滿青苔。在弗洛伊德的理論中,將“我”分為“自我”、“本我”、“超我”,分別對應與社會產生聯系的調停者,無意識的生活本能,以及在意識上存在的限制準繩。三者就好比燈塔的塔身、階梯、燈具,缺一不可。
“遠方的我”是在對“我”進行足夠的認識以后,達到的三者制衡并于社會協調的狀態。而“近處的我”則是因三者產生沖突,生活出現矛盾、迷茫,囿于現實而無處遁逃的自己。是因為“自我認知”偏差所創造出的扭曲的“我”。也就是在日復一日疲沓和碌碌不盡的勞苦之后鏡子里那個耷拉著臉的自己。愈是困于這種狀態,生活也就愈發的晦暗,好似船只卷入汪洋里的漩渦;燈塔的光芒也顯得更加難以觸及。
遺憾的是,現實生活中,大部分人的生活是被“近我”主導的,而非被“燈塔”所指引的。想要接近“我”,就要對“我”有所認識和篤信,被燈塔所指引也一生,也正是不斷認識自我的一生。只是,在這樣功利化的社會環境下,“自我認知”變成了一個難題。
蘇格拉底曾提出,人這一生最難得的事莫過 “認識你自己”。
許多人,不知不覺地,在自我的活動之中,將別人的注視和肯定當做我自己的可能性,構建出一種“預言的自我實現”。父母一輩的人認為電子商務有“錢途”,我們就跟著潮流去從商;認為做官有面子就去為官。于是,我們漸漸疲沓于千日如一的工作,抱怨起城市庸碌的節奏擁擠的地鐵,開始為生機為面子拉鼻子扯臉,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將天賦、愛好統統拋擲腦后,碌碌一生。奔忙、偽裝的僅僅是為了博取一個“讓他人覺得我活得很好”這樣的“自我滿足”?不知何時成了“活在別人眼里的人”。薩特所言的“他人即地獄”,黑塞筆下的佛陀喬達摩最初所歷經的苦痛又何嘗不是這樣?社會對“自我”過度改造,使得“自我”對“本我”,即所熱愛、所向往的事物產生了質疑。同時又給“超我”套上了緊箍咒,勒令潛意識接受這個病態的自己,并把它視作常態。“遠方的燈塔”也隨之消失在了水平線之際。這樣的我們,是否還有心在意遠方泛起的微光?
哲學上有個詞叫“行上同調”,指的就是這樣病態的個體背后的,反烏托邦式的社會狀態——前一輩因為數十年前社會生活條件不足而形成的傳統觀念被視作常理傳承。晚輩自我認知能力薄弱,恪守陳規,導致整個社會的意識行進緩慢。病態的社會認知,慢慢造就貧富不均、社會階級固化。“寒門難出貴子”、“不敢有上進心”之類的話變得理所應當。別說是成為“燈塔”了,這樣的社會形態,這樣迷茫的我們,難道不是遇難船,它的光明又在何方?這樣的我們,這樣活在別人眼里的我們,這樣迷失在螺旋中的我們,又有什么資格成為那座燈塔呢?
這個被賦予定義的“我”之所以時而離我們近、時而離我們遙遠,是因為,自我滿足的欲望、世俗的塵囂讓我們看不清自己,了解不到自己所熱愛、所向往的事物,讓燈塔愈發遙遠難及。觸手可及的心靈,恰恰成了離自己最遠的地方。
“認識自我”的旅程,也正是去往那座燈塔的航路。在這條路上最重要的便是從“本我”——即本源出發,從自己內心真正、渴望熱愛的事物出發,由“本我”驅動“自我”去融入社會,并且讓“超我”主導堅持。導演李安在年輕時屢受挫折,不被看重,多少人勸過他放棄、轉行;但正因為他篤信著內心中對編導的喜愛與堅持,一部部佳作才得以面世。“學會熱愛這個世界,不再以某種欲愿與臆想出來的世界、某種虛偽的完善的幻想來與之比擬。學會接受這個世界的本來面目,熱愛它,以歸屬于它而心存欣喜。”黑塞在《喬達摩》中最后的升華也更是體現了這種“本源之愛”的意義與重要性。不知你是否還記得,年少時,那個坐在學步車里因為有趣夢想著成為司機的你,那個做完大掃除因為自豪夢想著成為清潔工的你,那個搭著積木因為愉悅夢想著成為建筑工人的你。這些不計較現實因素、社會低位的夢想本身很渺小,卻值得贊許甚至敬畏。
只是,“本我”卻又要在“社會現實”前接受審閱,不論遵從哪種方式,都逃不開三者的彼此制約和循環,“遠方的燈塔”似乎真的難以到達。這是論述的結論,同時,也是事實。
因為“遠方的燈塔”本身也是“彼岸”的一種形態。是形而上,可知而不可感的。
每個人的生命里,都客觀地存在著“遠方”。然而,是否曾有人認真地思考過,你真的到達過遠方嗎?你所定義的遠方究竟在哪?到達所謂的“遠方”以后,又將駛往何處?進一步看,倘若將人生比做航路,其終點是什么?是夢想?是目標?那么在實現之后,人生的意義又在何處?《理想國》中,蘇格拉底也曾發出這樣的疑問。
某種意義上說,生命本身就是“去往遠方燈塔”的永恒之旅。我們一直在路上。“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莊子曾對類似的命題做出過很好的解答——遠方是無法真正“到達”的,因為世界上每個角落里,都存在著遠方。“遠方”又未嘗不離我們近?它存在于我們生命中的任何一個時刻,關鍵在于對它的把握,也就是對自我的把握。“遠方的我”是一種理想的狀態,是光源。離光源越近,生活也就愈發敞亮。這與佛教的“到彼岸”思想吻合。佛教認為,人這一生,不斷地在“此岸”和“彼岸”間游走,到了對岸以后,“此岸”反而成了“彼岸”,輪回無盡,因果不息。“近我”、“遠我”之間也存在這樣的協調,因此過度的勞苦也是沒有必要的,要學會在求索中適度滿足。
在不斷尋求的過程中,勢必體會痛楚,體會人間是非滄桑、煎熬百態。在人生的旅途中一次又一次墮落、改變。在“認識自我”的過程中,意識生命最本質的追求,擺脫痛苦,變得徹悟、豁達。來到最理想的位置——積極前進的狀態。“遠方的我”所指的狀態,即是“三種我”和社會之間的動態平衡狀態。在更接近它的地方,點燃星火。因此,這座燈塔才顯得格外重要。燈塔就是“我”,照亮遠方的燈塔,就是我們自己。讓自己告訴自己,人生的路該怎么走,讓每一天過得滿足、充實,不留下遺憾。
白夜已盡,黑夜已然來臨,我心中的燈塔正燈火通明。驀然回首時,方知心海一片燈火闌珊。回頭望望,滄海茫茫;光明隨風,吹過百年;蒹葭蒼蒼,永在船上;羈旅匆匆,希冀皎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