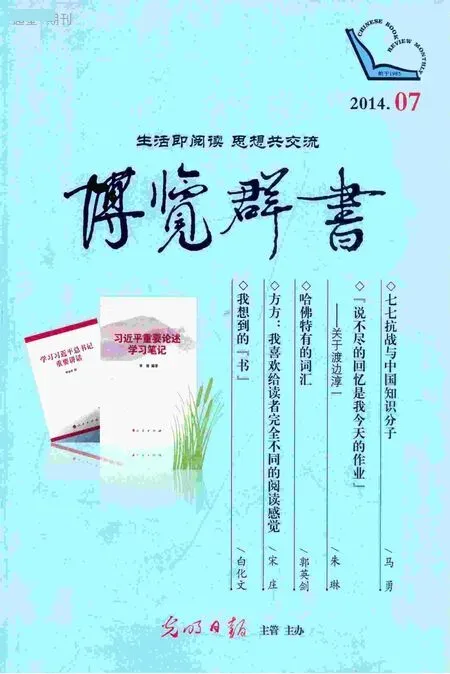林語堂與論語派雜志的政治性
黃開發(fā)
上世紀(jì)30年代,以林語堂為代表的論語派是一個(gè)自由主義的文學(xué)流派,提倡幽默、閑適筆調(diào)的性靈小品。其政治傾向主要是通過《論語》《人間世》《宇宙風(fēng)》《西風(fēng)》《逸經(jīng)》等熱銷的小品文雜志體現(xiàn)出來的,并形成一種期刊政治。這種期刊政治見諸于編輯方針和策略、小品文、作者群和讀者群等方面。在上世紀(jì)30年代的歷史語境中,論語派的小品文雜志成為具有高度政治性的問題,引起多方關(guān)注。
壹
林語堂創(chuàng)辦小品文雜志,倡導(dǎo)閑適筆調(diào)的性靈小品,重評(píng)晚明小品,翻印明人作品集,在文壇上掀起陣陣熱潮,以至于時(shí)人把1933年稱為“小品文年”,把1934年稱為“雜志年”(主要小品文雜志),把1935年稱為“古書翻印年”。這些潮流彰顯了論語派的政治傾向,并產(chǎn)生廣泛的社會(huì)效應(yīng)。以林語堂為首的論語派又與北方以周作人為首的苦雨齋派互相配合,形成聲勢(shì)浩大的言志文學(xué)思潮。這直接改變了文場(chǎng)主要派別之間的力量對(duì)比,影響了各派別所提出文學(xué)主張的合理性與合法性,于是引發(fā)了一系列激烈、持久的文學(xué)論爭(zhēng)。
《論語》半月刊在編輯策略上走的是雅俗共賞的路子,出版后銷量大好,引起讀書界的廣泛關(guān)注。林語堂介紹說:“聽說論語銷路很好,已達(dá)二萬(不折不扣),而且二萬本之論語,大約有六萬讀者。”(林語堂:《二十二年之幽默》)該刊成為當(dāng)時(shí)最受歡迎的幾種雜志之一。而且從《論語》到《人間世》,再到《宇宙風(fēng)》,出一本火一本,辦刊質(zhì)量也穩(wěn)步提升。
林語堂主編《論語》時(shí),利用各種關(guān)系,引來許多著名的作者,并且積極發(fā)現(xiàn)和培養(yǎng)新秀。章克標(biāo)說:
林語堂邀請(qǐng)魯迅寫稿,魯迅也寄來幾次。林又向北京的舊友如周作人、劉半農(nóng)等人約稿。邵洵美則因同徐志摩《新月》雜志方面的人接近,而得到潘光旦等人的支持。也還有熱心的人主動(dòng)來稿的,如老向、何容等及“大華烈士”簡又文,還有姚穎女士等等,因此,的確是逐漸興旺的樣子。
另外,徐訏也是因?yàn)橥陡濉墩撜Z》而與林氏結(jié)識(shí)的。林語堂不斷總結(jié)辦刊經(jīng)驗(yàn),調(diào)整方向,到了《人間世》《宇宙風(fēng)》,更是名家云集,佳作連篇。《宇宙風(fēng)》第十三期(春季特大號(hào))發(fā)表《宇宙風(fēng)讀者公鑒》,其中有云:
今后本刊,一本初衷,對(duì)內(nèi)容力求精彩,雖不敢說雄視文壇,總做到視同類雜志能無遜色。長篇約定有老舍趙少侯二先生合作之牛天賜續(xù)傳《無書代存》;主要的短篇方面,周作人先生的風(fēng)雨談,豐子愷先生的緣緣堂隨筆,都蒙續(xù)予撰惠,按期刊登。語堂的小大由之更不必說。又本刊絕無門戶之見,對(duì)于海內(nèi)外著名作家,無不竭誠敦請(qǐng)撰述……過去十二期中,有再版到六七次者。
海內(nèi)名家聚集,言語間充滿了自豪。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論語派三大主力雜志集聚了一大批思想觀念相近的自由主義作家。在《論語》刊行之前的1930年5月,馮至、林庚、馮文炳等編輯出版帶有沉潛傾向的《駱駝草》,僅出了26期,并未引起多少關(guān)注。1932年,周作人寫信向《現(xiàn)代》編者施蟄存推薦李廣田的散文,曾感嘆“北平近來無處可賣(指文章發(fā)表——引者)”。到了林語堂主編的《論語》,情形大變。上世紀(jì)30年代,自由主義作家受到進(jìn)一步打壓,被邊緣化,運(yùn)交華蓋,《論語》等雜志創(chuàng)刊,給他們提供了陣地。《論語》等予以培植,發(fā)表關(guān)于他們的人物志和照片,大力推介,因此他們對(duì)林氏是懷著知遇之情的。老舍在為《論語》創(chuàng)刊兩周年而寫的賀詩中云:“共誰揮淚傾甘苦?慘笑惟君堪語愁!”(老舍:《論語兩歲》)有人發(fā)表文壇八卦式的文章,把《論語》中常發(fā)表文章的八個(gè)臺(tái)柱式人物擬為“八仙”:呂洞賓——林語堂,張果老——周作人,藍(lán)采和——俞平伯,鐵拐李——老舍,曹國舅——大華烈士,漢鐘離——豐子愷,韓湘子——郁達(dá)夫,何仙姑——姚穎。(五知:《瑤齋漫筆·新舊八仙考》)何仙姑指女作家姚穎。《宇宙風(fēng)》創(chuàng)刊號(hào)發(fā)表姚穎的《改變作風(fēng)》,文末附有“語堂跋”,其中說:“本日發(fā)稿,如眾仙齊集,將渡海,獨(dú)何仙姑未到,不禁悵然。適郵來,稿翩然至……大喜,寫此數(shù)行于此。”這說明林語堂本人也是很認(rèn)可“八仙”之稱的。
貳
《論語》第49期“群言堂”一欄曾以“論語何不停刊?”為題刊登讀者來信,其中說:
我國文壇,自林公創(chuàng)刊論語之后,一紙(其實(shí)每期都?jí)蚨囗摚╋L(fēng)行,四方響應(yīng),凡有屁股(報(bào)屁股),莫不效顰。幽默二字,從老教授都聽不慣的地位,一躍而成為小學(xué)生耳熟能詳?shù)膷湫旅~,尤為投稿者晨昏顛倒,寤寐思求的對(duì)象。于是笑林廣記,一見哈哈笑之類的書籍,被人捧為高頭講章,竹枝詞,打油詩,風(fēng)頭尤其十足。而刊物的命名法,也起了“奧伏赫變”,仿古贗本,最為摩登,什么“中庸”“孟子”“聊齋”“天下篇”等半月刊,書攤上觸目皆是。
從上可見《論語》等雜志的廣泛影響。
據(jù)茅盾介紹,自1934年1月起,定期刊物越出越多。專售定期刊物的書店——中國雜志公司也應(yīng)運(yùn)而生。“有人估計(jì),目前全中國約有各種性質(zhì)的定期刊物三百余種,內(nèi)中倒有百分之八十出版在上海,而且是所謂‘軟性讀物,——即純文藝或半文藝的雜志;最近兩個(gè)月內(nèi)創(chuàng)刊的那些‘軟性讀物則又幾乎全是‘幽默與‘小品的‘合股公司。”(茅盾:《所謂雜志年》)還有人指出,繼1927年以后書業(yè)的大發(fā)展,1932年以后則進(jìn)入蕭條時(shí)期。雖然一般書業(yè)不景氣,而雜志業(yè)則逆勢(shì)成長,出現(xiàn)了“雜志年”,幽默小品流行起來。
論語派的三大主力雜志取得巨大的成功,引起了跟風(fēng),小品文雜志紛紛出版。如論語派的《文飯小品》《逸經(jīng)》《西風(fēng)》,左翼的《新語林》《太白》《芒種》等。論語派雜志占據(jù)了顯著的文化空間,政治影響擴(kuò)大,左翼有針對(duì)性地創(chuàng)辦《太白》和《新語林》等來爭(zhēng)地盤。陳望道回憶道:“《太白》雜志是在魯迅先生的直接關(guān)懷和支持下創(chuàng)辦的。一九三四年創(chuàng)辦這個(gè)雜志,是想用戰(zhàn)斗的小品文去揭露、諷刺和批判當(dāng)時(shí)黑暗的現(xiàn)實(shí),并反對(duì)林語堂之流配合國民黨反動(dòng)派‘圍剿而主辦的《論語》和《人間世》鼓吹所謂‘幽默的小品文的。”(陳望道:《關(guān)于魯迅先生的片段回憶》)“配合”之言受時(shí)見所縛,名實(shí)不副,而“反對(duì)”之語則道出了實(shí)情。
《芒種》與《太白》雜志編輯出版專集《小品文和漫畫》,以強(qiáng)大的作者陣容,否定論語派倡導(dǎo)的“自我”“閑適”的小品文傾向。曹聚仁說:“‘太白社曾以‘小品文與漫畫為題,征求當(dāng)代文家的意見,那五十多家的意見,都是否定那自我的中心,閑適的筆調(diào)的。”(曹聚仁:《〈人間世〉與〈太白〉·〈芒種〉》)左派所辦小品文刊物《新語林》《太白》《芒種》均與論語派對(duì)壘。徐懋庸、曹聚仁編輯出版了《芒種》半月刊,茅盾在對(duì)前三期進(jìn)行了一番考察后說:“這一個(gè)半月刊,現(xiàn)在(四月中旬)已經(jīng)出到第三期了。這也是‘小品文的刊物,是反對(duì)個(gè)人筆調(diào)、閑適、性靈的小品文刊物。”從前三期看,“《芒種》還嫌太深,與創(chuàng)刊號(hào)上《編者的話》預(yù)期的讀者對(duì)象——‘拖泥草鞋的朋友們——不符。”(茅盾:《雜志“潮”里的浪花》)《太白》也銷路不佳,只辦了一年半就停刊,結(jié)果反而擴(kuò)大了《人間世》和論語派的影響。
左翼人士著重從社會(huì)學(xué)的角度來看待論語派與小品文現(xiàn)象,忽視了由商品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和中產(chǎn)階級(jí)的興起帶來的市民階層文化消費(fèi)需要的增強(qiáng)而為論語派提供了社會(huì)基礎(chǔ)。作家作為中產(chǎn)階級(jí)的特殊群體是精英文化的創(chuàng)造者和消費(fèi)者,而精英文化與城市市民的大眾文化之間有著交叉性,共享著現(xiàn)代都市許多文化資源和價(jià)值趣味。在價(jià)值觀上,后者更重視庸常的日常生活,因而疏遠(yuǎn)精英文化高蹈的政治性理想。市民階層憑借其占有的經(jīng)濟(jì)資本和文化資本,分享了部分為我所需的精英文化資源。論語派作家為了吸引更多的市民讀者,擴(kuò)大自身的市場(chǎng)份額,就會(huì)遷就他們的要求和趣味。大眾文化從功能上來說是娛樂性的,保守的,與左翼作家的宏大敘事背道而馳的。宏大敘事對(duì)日常生活進(jìn)行排他性的選擇和改造,使之成為映照在意識(shí)形態(tài)中的理想化鏡像,同時(shí)對(duì)與文化理想不合拍的日常生活進(jìn)行揭露和批判,從而引起日常生活主體對(duì)日常生活消極性、不合理性的反省和批判。論語派作品與這種五四以降主流的啟蒙主義的精英意識(shí)迥乎不同,肯定世俗價(jià)值,表現(xiàn)出更突出的平民意識(shí)。不過,論語派與市民文化的關(guān)系,并不是一味地迎合,而是曖昧的,半推半就的。顯然,與市民讀者沉浸其中的大眾文化的親和,走雅俗共賞的路子,為論語派提供了獨(dú)立的話語空間,無論是左翼文學(xué)、京派文學(xué)還是右翼文學(xué)的場(chǎng)域中,都沒有大眾文化的棲身之所。
除了編輯雜志,林語堂還編著出版英語讀本,并因此成為“版稅大王”。1928年,他所編三冊(cè)《開明英文讀本》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面向初中生。出版不久即風(fēng)行全國,并且取代周越然編輯、商務(wù)印書館出版的《英語模范讀本》,成為全國最暢銷的中學(xué)英文教科書。1933、1934年,林語堂收入頗豐,徐訏在《追思林語堂先生》一文中替他算過一筆賬:開明書店英文教科書的版稅每月大約七百元銀洋,再加上中央研究院的薪金、幾本刊物的編輯費(fèi),每月收入在1400元左右,而當(dāng)時(shí)銀行普通職員月薪不過六七十元。唐弢后來在《林語堂論》一文里在談到胡風(fēng)《林語堂論》發(fā)表的歷史語境時(shí)說得明白:
在號(hào)稱“雜志年”的1934年,林語堂先生繼提倡幽默的《論語》之后,又創(chuàng)辦了“以自我為中心,以閑適為格調(diào)”的小品文刊物《人間世》,同時(shí)還贊揚(yáng)語錄體,大捧袁中郎,所編《開明英語讀本》又成為暢銷書。從林先生那邊說,可謂聲勢(shì)烜赫,名重一時(shí),達(dá)到了光輝燦爛的人生的頂點(diǎn)。
林語堂變?yōu)橐粋€(gè)成功人士,這增加了其人生道路和政治傾向的吸引力,擴(kuò)大了他的政治影響,也很容易加重左翼方面的憂慮。
在《大荒集·序》中,林語堂自稱“大荒旅行者”,“在大荒中孤游的人,也有特種意味,似乎是近于孤傲,但也不一定。我想只是性喜孤游樂此不疲罷了。其佳趣在于我走我的路,一日二三里或百里,無人干涉,不用計(jì)較,莫須商量。或是觀草蟲,察秋毫,或是看鳥跡,觀天象,都聽我自由。我行我素,其中自有樂趣。而且在這種寂寞的孤游中,是容易認(rèn)識(shí)自己及認(rèn)識(shí)宇宙與人生的。有時(shí)一人的轉(zhuǎn)變,就是在寂寞中思索出來,或患大病,或中途中暑,三日不省人事,或赴荒野,耶穌,保羅,盧梭……前例俱在”。這樣的一個(gè)“大荒旅行者”走進(jìn)十里洋場(chǎng),沒有投靠任何政治勢(shì)力,雖有一些對(duì)市場(chǎng)和市民讀者的迎合,但大體上可以說是依然故我,結(jié)果贏來擁躉無數(shù),成為文壇上的大明星。這構(gòu)成了其他政治身份作家所代表的價(jià)值觀的挑戰(zhàn)。
叁
以魯迅、茅盾、胡風(fēng)等人為代表的左翼作家對(duì)論語派的小品文傾向進(jìn)行了尖銳的批評(píng),這是上世紀(jì)30年代文壇的主要事件之一。我已在別的論文中進(jìn)行過專題探討,此處不贅。與此同時(shí),“雜志年”現(xiàn)象也引起了左翼人士的廣泛關(guān)注,他們從期刊政治的角度進(jìn)行了社會(huì)分析式的闡釋,力圖把握和引導(dǎo)雜志出版的輿論導(dǎo)向。應(yīng)該看到,上世紀(jì)30年代,內(nèi)憂外患頻仍,國事阽危,對(duì)論語派雜志和小品文所體現(xiàn)出的文化政治傾向的批評(píng)無疑具有歷史的正當(dāng)性與合理性。
傅逸生在《現(xiàn)代》雜志上發(fā)表的論文《中國出版界到何處去》。他說,繼1927年以后書業(yè)的大發(fā)展,1932年以后則進(jìn)入蕭條時(shí)期。一般的書業(yè)不景氣,而雜志業(yè)逆勢(shì)成長,出現(xiàn)了“雜志年”。他引用《人文》月刊的統(tǒng)計(jì):1932年收到全國雜志877冊(cè)。1933年為1274冊(cè),1934為2086冊(cè)。據(jù)個(gè)人在各雜志公司調(diào)查之結(jié)果,除政府公報(bào)外,共為280到300種的數(shù)目。誠為名副其實(shí)的“雜志年”。其中,逆勢(shì)而起的就有“幽默小品的流行”。他評(píng)論道:
時(shí)代在一個(gè)陰沉沉的時(shí)候,只有用反語,諷刺,和短小精干的小品文來發(fā)泄。《論語》,《人間世》,《華安》,《華美》及各報(bào)紙副刊之能為人注意,當(dāng)然是有他底時(shí)代意義的。不過,這許多東西,因?yàn)樗麅H是一種幽默諷刺,所以,終究不能解決讀者的許多問題,現(xiàn)在,幽默小品的時(shí)代,顯然的已在向下了。
作者預(yù)言,隨著時(shí)代的進(jìn)展,“迎合個(gè)人牢騷及悲觀思想的幽默品,將愈趨于頹廢墮落,富于前進(jìn)性而有社會(huì)意義的諷刺品與寫實(shí)小說,將有更進(jìn)步的成績供給讀者”。他指“幽默小品”迎合個(gè)人牢騷,思想悲觀,不能滿足讀者認(rèn)識(shí)時(shí)代及其方向的要求,并預(yù)斷其“頹廢墮落”的前途;相反,前途光明的則是左翼文學(xué),“富于前進(jìn)性而有社會(huì)意義的諷刺品與寫實(shí)小說”是左翼作家的勝場(chǎng)。
茅盾發(fā)表《雜志年與文化動(dòng)向》一文,重點(diǎn)介紹了傅逸生的文章。然而,他對(duì)“雜志年”的估量與傅逸生不同,強(qiáng)調(diào)“雜志年”是“文化動(dòng)向之忠實(shí)的記錄”,是多種“思潮”交流決蕩而產(chǎn)生的結(jié)果。其中,“好的傾向”也在針鋒相對(duì)地發(fā)展著。(茅盾:《雜志年與文化動(dòng)向》)這“好的傾向”無疑是以左翼《芒種》與《太白》等雜志為代表的。在他的論述里,“左翼”與包括論語派在內(nèi)的“言志派”的對(duì)立呼之欲出。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