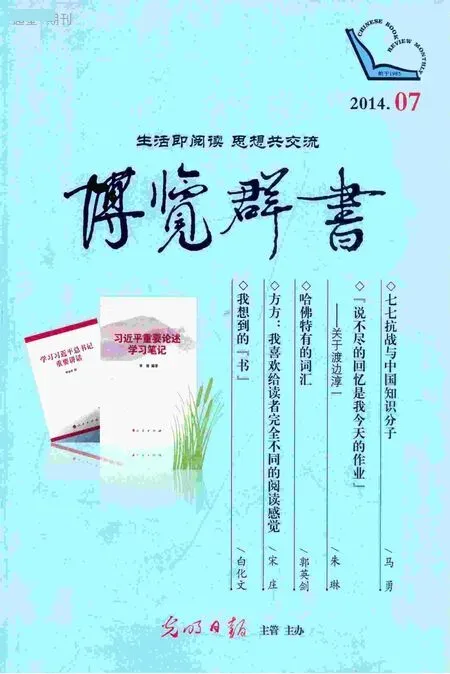從“為什么去延安”到“我不臨古畫”
王見
讀完盧新華編著的《張仃——中國藝術的驕傲》一書,一個滿頭銀發,拄著拐杖,腰板直挺,目光堅毅,在光華路校園來回走動的身影又豁然在目。
感謝編著者,他復活了張仃。
張仃是我們的老院長,對我們來說還是一種敬仰,甚至是一種包含神秘的敬仰。
然而從某種意義上講,張仃是一個謎,張仃是一個傳說。特別是在張仃先生生命最后的幾年里,面對喧囂的現實,他超然、緘默、冷寂、平靜。似乎張仃遠離了社會。我們似乎也疏遠了張仃。而后,先生走了,我們對老院長的敬仰和神秘感只剩稀薄的記憶。
但《張仃——中國藝術的驕傲》讓我們又見彩虹,又見一個充滿人格魅力,平凡而偉大的張仃。
這本書有一個非常突出的特點,就是編著者以平實的文字敘事和史料與歷史圖片互相印證手法,將20世紀中國跌宕起伏的歷史重大事件與張仃的藝術人生緊密關聯,并將張仃藝術人生的路徑和人格魅力以及作出的杰出成就和貢獻的因果關系,以清晰的邏輯關系展現了出來。其寫作方式與傳記性寫作手法完全不同。所有有關張仃藝術人生的歷史碎片,縱橫交錯,又似八面來風,都被編著者精心地綴合成一副歷史的、現實的肖像。其用心至深,用功甚力,很難得。
編著者說,“張仃的藝術創作涉及漫畫、年畫、宣傳畫、舞臺美術、實用美術、工藝美術、動畫電影、展示設計、裝飾畫、壁畫、中國畫、書法、藝術理論和批評等諸多領域。……像他這樣涉獵,探索如此廣泛的藝術領域的藝術家,藝術教育家是極罕見,極特殊的。”因此,他深思熟慮,把張仃復雜的人生經歷和多樣的藝術創作貢獻和成就,研究歸納成八個篇章。由此構建了張仃的學術地位構架,理清并開辟了張仃研究的學術新線路,也成為當下研究張仃的嶄新開端。
“張仃是中國現當代具有重要影響力的革命文藝家和藝術教育家。” 這是編著者的重要認定。這個認定也來源于全書概括的主題詞:“張仃中國革命文藝的先鋒,中國藝術創新的旗幟”。
“張仃的人生與中國革命事業和新中國同行”,“他一生的藝術創作價值和思想以及許多的重要作品與中國革命和現代文化藝術史緊緊連在一起”。這是編著者概括確認的張仃藝術人生的特征。此言不虛,此識甚確。
編著者梳理了從張仃民族救亡的“漫畫”開始到革命文藝,從延安“大美術家”到“新中國國家形象的首席藝術設計師”的發展路線,為我們理解張仃創辦工藝美術教育,并形成現代設計教育體系的重大成就,提供了內在聯系和邏輯關系。因此,我們才能明白張仃為什么總是擔當著比較重要歷史角色,“成為一個歷史時代和國家文化藝術的象征,并成為中國現代美術史的標志性人物”的原因。
對于張仃的“仃”為什么是孤苦伶仃的“仃”?張仃為什么畫漫畫?張仃的“漫畫”如何成為張仃革命思想和從事革命文藝的緣由?民族救亡的“漫畫”如何成為張仃作為革命文藝的底色等問題,編著者用精心選編的張仃漫畫和簡要的文字做了來龍去脈的敘述。
張仃從十幾歲到六十多歲創作的很多漫畫告訴我們,不論在“白區”上海,還是在“紅區”延安,無論是對國計民生的針砭時弊,還是國際共運和世界局勢的政治表態,張仃的藝術思想和文藝工作都與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各個歷史階段同步進退。
“我為什么去延安”?
一個“胸有萬丈霓虹志”的革命青年兩到延安,曲曲折折。編著者講述了張仃從魯藝到文抗作家俱樂部,再到陜甘寧邊區美術家協會主席的起起落落,朝氣蓬勃。讓我們感受了張仃浪漫主義的激情如何在黃土高坡因地制宜的智慧與艱辛,理解了理想主義的“摩登”與革命文藝“現實”的樂觀與溝通,清楚了毛澤東 “不要自滿,要更精,更好,更進步”的題詞,與1942年張仃主持的邊區大生產運動成果展的重大關系。也找到了張仃在新中國開國之后,所以能承擔一系列有關新中國文化形象設計工作的歷史伏筆。延安八年,成就了 “摩登”藝術設計家,鍛造了“杰出的大美術家”。
實際上,這一段敘述為我們梳理了張仃從延安革命文藝的工作到擔任新中國開國之后一系列設計工作的發展線索,領悟到“大美術家”的真正含義,非常重要。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說,“新中國國家形象的首席藝術設計師”的工作,實際上就是張仃在延安邊區政府“大美術”工作的延續。
有關張仃新中國開國之后,從國徽設計到開國紀念郵票設計,以及張仃在中南海辦事處擔任國家重大項目設計的歷史,在中央美術學院開拓展覽設計教學的工作等,編著者也都通過嚴謹有序的敘述,澄清了張仃既是具體工作的組織者,執行者,同時也是創作者的事實,令人信服地展現了張仃作為藝術設計家,為新中國國家形象,新中國文化形象,新中國文化精神所立下的汗馬功勞。為我們今天準確認識張仃藝術工作的文化立場,藝術創作等提供了重要的研究依據。
有關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的成立及教學思想產生的前前后后,是一個相當龐大復雜的歷史階段。編著者用了32頁的篇幅,是8個篇章敘述當中最長的文字。這一段歷史,這一段文字,也是張仃在工藝美院將近三十年的領導與教學工作的歷史回顧。從中可以讀出張仃個人的藝術思想與現實政治要求的沖突;教育理念與國家之需的矛盾;意識形態與藝術創作規律的平衡等。使人真正體會到張仃的智慧品格、實事求是的精神、人格魅力。什么叫作以黨和國家的利益為重,什么叫作忍辱負重,什么叫作不計較個人得失,都能在這一段歷史的敘述中找到具體的史實、事實和答案。
這一段歷史很難寫,所以這一段歷史敘述,顯示了編著者對歷史現象的深刻洞察和理解,顯示了編著者駕馭歷史宏大敘事的能力和判斷,對主觀認識的調節和節制,以及深厚的研究功力。
機場壁畫和焦墨山水是張仃藝術成就中后期的兩個高峰。有關機場壁畫,編著者有三個研究重點,來自他對幾十年中國文藝界的深入研究和親身經歷。
一是詳述了1979年9月26日下午,首都機場新建候機樓的一場盛會,著意提點了機場壁畫特別的歷史時刻和特別的歷史意義。作者認為這一藝術事件,已超越壁畫和藝術本身,實際上成為中國向世界宣布中國改革開放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走向。
二是道出了機場壁畫的本質意義——“首都機場壁畫開放的同時,‘極左‘僵化‘保守與‘開放‘自由‘創新的兩種思想展開了爭鳴,引發了社會各界關于‘美‘人性‘現代性‘思想解放等話題的激烈爭論,打破了文藝界沉悶的學術僵局。這一學術爭鳴的源頭來自中央工藝美術學院,來自張仃思想解放的先聲。”
三是彰顯了機場壁畫的重大意義,在于從此開啟了“中國壁畫藝術的復興”何種公共藝術的興起。
對中國民族文化的自信,尤其對民間藝術的重視,是張仃藝術觀念當中最為顯著,最為主動的特征,且由來已久。這是中國文化立場的大問題,張仃從不含糊。所謂的“城隍廟加畢加索”,實則就是把中國古代的民間藝術提升到現當代文化藝術的層面。
所以,編著者的結論是:張仃“是現當代中國文化藝術界、堅守民族文化自信,探索有中國特色藝術教育和藝術風格體系的杰出代表”。
編著者對機場壁畫的深入認識和研究,也使我們驀然回首——張仃畫在機場的《哪吒鬧海》,實則是一幅現當代中國繪畫當中最重要的、最有劃時代意義的杰作。張仃,在如此重大的歷史關頭和重要場合使用“哪吒鬧海”這樣一個家喻戶曉的古代文化經典,其民族題材,民族形式,民族精神,民族特點當然顯而易見,但究竟還向我們昭示了什么,編著者給我們留下了值得深思,值得研究的課題。
“他的焦墨山水是獻給人民的最后絕唱。”編著者對張仃焦墨山水的這種認識有無盡之言,有無盡之意,有無盡之思……同時編著者又以出色的藝術眼光為我們呈現了張仃焦墨的高明,也讓我們看到了張仃焦墨的經典——蒼茫高遠的《阿里古格》,田園風光的《石廟子公社》。《巨木贊》的崢嶸,《千佛洞》的探幽。隨吟《今天雨水多》,思古《寒盡不知年》。《櫻桃溝》《臥佛寺》《農家院》《楊樹林》“俯拾皆是”。 落筆是太行之巍峨,揮墨是十渡之峻峭。以質樸之心寫無華之像,以極簡之法,融黑白兩“道”之儀。這就是焦墨的張仃。也是編著者筆下晚年的張仃。
一支毛筆,一瓶墨汁,“大道至簡”。不摻水,不呼號,十年穿行,六上太行。風餐露宿,“鏤月裁云”。進藏區,回延安,西入騰格里,南游武陵源。心無旁騖,鉛華脫盡。七十歲老人的十年遠征——找尋“夢里的山”;十年如一日守住“中國畫的底線”。這是灰娃之言,也是編著者為張仃的焦墨山水立照。
“登昆侖兮回望,心飛揚兮浩蕩”是張仃題在巨幅焦墨“昆侖頌”上的詩句,也是先生精神的自畫像。張仃登高原,昂首闊步,望昆侖,豪邁高歌。與古人“年來萬事灰人意,只有看山眼不枯”的悲頹之氣大相徑庭。
張仃還說:“我不臨古畫。”
為什么?我們不得其解。但當全書讀罷,掩卷沉思,聯想五十年前張仃與李可染,羅銘的江南寫生,我們似乎漸漸就能若有所悟——張仃今天創造的“焦墨”山水,就是為了明天的“古畫”范本。
張仃奈何以“臨古”束手縛心?!
當然,我們只能笨拙地猜度。因為我們還沒有足夠超前的眼力明白張仃的焦墨;歷史也沒有給我們足夠的時間,讓我們認識焦墨山水的分量及其意義。而且,歷史經驗也告訴我們,也只有當張仃離我們越來越遠的時候,他的焦墨才可能離我們越來越近。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當張仃焦墨山水的出現,就注定在中國山水畫史當中開天辟地。 “焦墨山水”實際是對傳統中國畫作出了創造性的現代貢獻。
所以,張仃的焦墨山水是一面“閃耀著光輝的中國藝術創新的旗幟”。
《張仃——中國藝術的驕傲》是由在原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工作了幾十年盧新華教授編著。他曾代表學院長期負責與張仃先生的工作聯系,他又是1978年入校的學生,那么對張仃先生不僅有深厚之誼,又執弟子之禮。所以他能謹慎地沿著張仃的足跡,嚴謹地梳理大量文獻資料,精準地選取了重大歷史事件,對張仃復雜的藝術和人生經歷,做提綱絜領的概括,以其穿透歷史的深邃眼光,把張仃藝術和人生的傳奇以及神秘感,還原成質樸無華的歷史敘述。他對張仃崇高的敬意和深沉的思念已經與他自己的藝術實踐及對藝術和設計的深刻認知渾然一體——下筆是心手感應的春秋,落墨有歷史風雨的涼熱。
感謝《張仃——中國藝術的驕傲》,讓我們能隨時與敬愛的老院長鮮活的人生相逢并對話。
(作者系廣州美術學院教授、廣州美術學院學術委員會委員、廣東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清華大學張仃藝術研究中心研究員、清華大學吳冠中研究中心研究員;敦煌研究院特聘研究員,敦煌研究院特聘學術委員會委員,敦煌研究院特聘巖彩畫創作中心藝術委員會主任委員。)